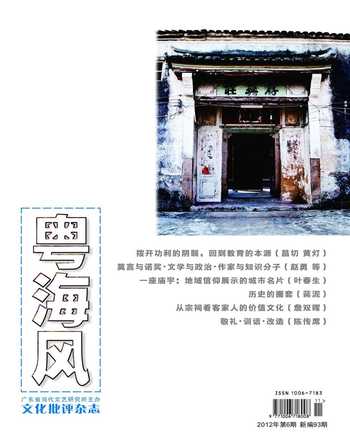就“文学史”敬答严家炎先生
2012-04-29王鹏程
严先生:
您好!收到您的来信,惊恐不安。原以为先生定不会理睬我等之愚陋,岂料先生如此襟怀,晚学自责不已。同时也为自己的疏浅和无知而自惭,冒犯不敬之处,罪不可逭,尚望先生万勿自扰。
以我之陋见,《二十世纪文学史》的上、中两册以及下册的绝大部分章节,确如您及学界的诸多老师所言,厚大精深,很有分量。而拙文所涉及的一些章节,实在令人难以恭维。我知道一点学术界的规则,也知道您年事已高,不能每一行文字都亲自过目。但作为参编者,即使自己无暇请别人代笔,最起码也应该认真地把关,这是对自己的尊重,也是对您的尊重,同时也是对学术和读者的尊重。我之所以写文章,正是因为没有对学术和读者的尊重。当我在课堂上给只相信教材的学生反复纠错时,一种道德上的“义愤”也在不断地升级,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岂容这般的草草敷衍。正是这种“义愤”使得我不能为尊者或名家“讳”,我觉得自己可能很浅陋,但这种“义愤”应是没有错的。
您谈到我论述中的一些武断和偏颇,确如其是,提供的一些材料也开我眼界。但我也有一些疑惑,比如宗璞的《我是谁?》的问号问题,几本流行的文学史都没有,您和冯先生的谈话是否能作为依据,是不是以最初刊发时的原貌为准妥当一些?当然,这些都是枝叶问题。如果您留意,会发现我的主要目的是比较和陈思和《教程》的相似问题。您说的我“责备现在这部文学史介绍作家时,没有采用规范的统一格式”也显然是误会了问题的指向。我觉得,可能因为这儿拼一点,那儿贴一点,才导致作家介绍时出现的这些问题。再如杜鹏程和柳青的相互影响问题,我们也不能因为杜读过《铜墙铁壁》就说他受过柳青的影响,这得有可靠的依据。否则的话,就这个问题谁也讲不清了。还请您有空批评。
您在来信末尾提到我的分析“缺少分寸感和准确性,失去了一个‘度”。是的,正如您所言,我过于意气、过于激动,但我的分析多多少少还是有依据的,并不是信口雌黄。“误人子弟”、“嚼饭与人,徒增呕秽”的话是重了点,但您如果仔细读一下论及《白鹿原》的部分、论及莫言的部分(对着陈思和的《文学史教程》读),我相信,大多数行内的人是难以忍受的,只是希望,这套教材如果再版,能作修改是最好不过了。在我读过的文学史中,下册的错讹多到了令人不可忍受的程度。教材和一般的学术著作不同,影响面积太大。以我校而言,这一年级十余个班级四五百人在使用。如果学生用其作为考研的参考资料,这些差错难免会影响学生的成绩甚至或前途。这也是我冲动撰文的原因。
文章刊出后,接到几位师友的电话,说我“惹了事”,甚至是“自找麻烦”、“自毁前程”,我一笑置之。不过说实话,我自己也有些后悔,当然不是怕前面所提的“麻烦”,而是觉得这种事情我可能少见多怪,自己列一个勘误表,印发给学生就行了。我给您写信的意思,也只有想让您(笔者按,原信少“让您”二字)知道此事而已,别无他意。当然也没想过您能回复。您和孟繁华、程光炜先生都是我十分仰慕、尊敬的学者,你们的著作无论是在我的学生时代,还是如今,都提供给我丰富的营养。但这种仰慕和尊敬不能让我对错误和敷衍闭上眼睛。我一直主张,对年青学者可以宽松一点,对于著名学者要严厉一些。因为著名学者的背后,有很多目光;而年青学者,正在成长。就我而言,鼠目寸光,学识浅薄,又易激动、易偏激,因而有自知之明,能做一个认真的教书匠即可,“前途”是没有的,这是我“犯上作乱”的原由,也是我对师友告诫关爱一笑置之的原因。
感谢您,能语重心长地指出我的问题。在一个说假话盛行的时代,您的坦诚、关爱使我如沐春风,感念不已。再次为我自己的浅薄无知向您道歉、请罪,不敢奢望您的原谅,只是希望此事不带给您些微影响。同时,麻烦您,若有机会,转达我对程、孟二先生的歉意。若有机缘,定当当面谢罪。专肃
即叩
钧安!
晚学王鹏程顿首上
四月十二日
又:
严先生:
您好!有几点需向您说明:
一、收到您的来信之后,我很纠结,不回复,没礼貌;回复,怕冲撞您。我自始至终都没有冒犯之意,只是向您说明此事而已。拙作写成后,曾征询教研室同事意见,他们觉得有必要向您说明此事,这也是我给您写信的主要动力。
二、此文执笔者为我,录入电脑者为鲁老师,她曾修改润饰,因而出现您指出的叙述主体不清的问题,特向您及刊物道歉。
三、上课时,有老师纠正下册中的错误,学生说:“您说人家错了,为什么您不去编?”老师只能哑笑。本、专科学生,大多只信书本,因而纠错是十分必要的。
您乃学界泰斗,年高德劭。吾侪狂妄无知,冒犯之处,惶恐不安,唯望先生勿以自扰。
王鹏程再拜
四月十四日
(作者单位:咸阳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