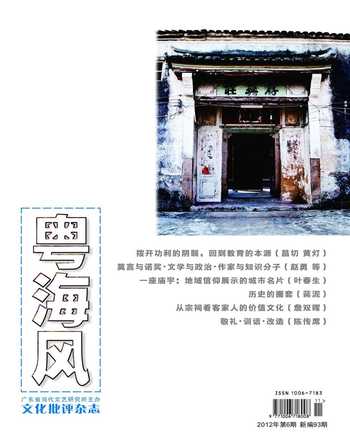“继续革命”视野中的反官僚主义小说
2012-04-29闫作雷
闫作雷
引言
反官僚主义作为官僚理性秩序的对立面有一种或潜在或显在的“继续革命”诉求,这主要表现在共和国新一代左翼知识青年的文学创作和实际行动中。这里彰显的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或“激情和理性的冲突”,而是内在于革命逻辑和建国后不得不然的“自我否定的机制”之中,他们的作品显示,延宕革命理想和目标的官僚主义与“继续革命”诉求之间有着难以调和的冲突。“当代文学”中的各个阶段,比如“百花时代”、大跃进时期、1960年代初和“文革”等,是“当代历史”不断自我否定进程中的连续性一环,而非断裂。
当然,不同时期的反官僚主义有着不同的政治目标和表现形式,但那种内在的“继续革命”诉求却是相通的。1955—1957年“百花时期”反官僚主义的主体是充满革命热情和社会主义理想的左翼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以个人的方式对抗官僚集体;他们响应了1955年毛泽东加快农业合作化速度的政策和进入“社会主义高潮”的号召,然后以“干预生活”或“真正的社会主义”为口号向当时所谓“保守思想”和官僚主义者开火。“文革”及其前夕的反官僚主义者则是具有高度无产阶级觉悟的工人、农民和复员军人等。他们以集体的方式反对个别的官僚主义者;他们响应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因此“两条路线斗争”的模式更明显地具有了“阶级斗争”的性质。“人民”被调动起来——这特别类似于中国革命兴起时的情形,革命依靠的对象,以左翼知识青年始,以工农革命终。
在“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时期,1960年代以后响应“阶级斗争”的作品被否定,而“百花时期”那些“干预生活”的作品则作为“重放的鲜花”在“反官僚主义”这一主题上得到肯定。然而此时的“反官僚主义”含义已经不同于前两个时期“继续革命”意义上的“反官僚主义”;当时通过“重放的鲜花”实际上是要建立官僚统治秩序,修复前此被破坏的官僚理性。因此就产生一个悖论:那些要求“继续革命”的反官僚主义文本作为“重放的鲜花”,要恢复的“正”却是建立官僚理性秩序——那些内部充满了“继续革命”冲动且参与到当时“政治辩论”中去的小说文本在新时期初期却成了“去政治化”进程开始的标志。
“百花时期”的反官僚主义
1955年是很有历史意味的一年[1],这一年中共高层发生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速度的争论直接影响了“当代历史”的走向,这一争论的结果也鲜明地反映到文学创作中来。尤其是“鸣放”初期那些出自青年作家之手的反“保守思想”/反官僚主义的作品是直接参与到这一争论中来的,这些作品在当时被作为“干预生活”的代表作——不过它们与另一些所谓揭露社会“阴暗面”的作品的诉求是截然不同的[2]。回到当时的语境中看,这些青年们反对保守僵化,主张“热情”和“创造”的作品才真正符合当时“干预生活”这一口号的初衷。唐挚最先提出的“干预生活”的口号,主要目的是为了鼓动人们要有参与生活和“社会主义高潮”运动的热情。作者充满“热情”地写道:“冷淡,永远将是一部作品的致命伤,因为这总是意味着作家和人民生活的某种距离。”“作家,必须是热爱自己的人民和生活,必须是大胆干预生活,用全心灵去支持一切新事物的猛将!”[3]显而易见,作者所说的“干预生活”是要“加速”生活,去“干预”生活的“常规”节奏和毛泽东所谓“小脚女人”似的官僚主义者。
分析当时的争论不难发现,中共高层对农村合作化和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分歧的焦点是:比较稳健地按常规发展,还是依靠群众的热情加速发展?主张后者的毛泽东认为农村工作部的“保守派”(即主张收缩,放慢合作化速度)代表了资产阶级和地主、富农的利益,认为他们没有顾及农村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贫下中农”的利益,没有看到后者“走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从1955年7月31日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开始,毛泽东对坚决收缩的“保守思想”进行了猛烈批判,并将其上升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到这年年底,“保守派”被彻底打了下去,中央农村工作部邓子恢他们被迫作了检讨。毛泽东认为现在的问题不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而是保守干部们被“胜利吓昏了头脑”,他们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他们只是用苏联的经验“来为他们的爬行思想作掩护”。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用富于文学性的语言写道:
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分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4]
毛泽东认为这不仅仅是“保守思想”的问题,而且是“脱离群众”的问题,而这种指责在当时意味着是官僚主义作风的表现;而且不仅仅是官僚主义的问题,还是阶级立场、阶级斗争的问题。
毛泽东也首次把眼光投向青年,因为他们“最有生气”、“最少保守思想”[5],而此时怀着理想主义、要求“继续革命”的王蒙们就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了,他们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向“保守思想”和官僚主义开火。
1950年代后期,毛泽东越来越关注“一五”计划和采用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后果。知识分子的贵族化和官员的官僚化所导致的官僚体制形成了一个有其特殊利益的“管理阶级”和“俸禄阶层”。也就是说采用“列宁主义”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开始形成保守思想和官僚主义;在毛泽东看来,这种专业化、科层化和官僚理性秩序将社会主义的理想和目标无限延宕了——手段本身成了目的。因此毛泽东试图打破这种经济上高度集中的管理方法和政治上日渐僵化保守、没有了革命理想和社会主义热情的官僚主义体制。
在“社会主义高潮”和整风运动的背景下,1955—1957年出现了一些青年作家所写的反对“保守思想”和官僚主义的作品。在1957年整风开始之前的所谓“鸣放”的第一阶段,青年作家们主要批判的是“保守思想”,而“保守思想”实际上也就是官僚主义的代名词,而且对这些“保守思想”的指责已经上升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而在1957年整风开始之后的“鸣放”的第二阶段,青年作家们反对的主要是“三害分子”(指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这一时期,由于受到国际环境和毛泽东整风时期批评官僚主义的讲话的双重影响,北京大学爆发了“5·19学生运动”[6]。
左翼青年作家对“保守思想”和官僚主义的批判显示着建国后形成的官僚理性秩序与青年们要求“继续革命”的冲突[7]——当然,这既与他们“真正的社会主义”要求相关,也与他们响应了毛泽东的号召相关。
以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为例。这篇小说被普遍忽略的背景就是,当时关于农村合作化速度的冲突之后整个社会所出现的反对“保守思想”/官僚主义、要求进入“社会主义高潮”的时代氛围。而反对“保守思想”/官僚主义和要求参与“社会主义高潮”正是“继续革命”的两个维度。
“社会主义高潮”一语在小说中多次提到,其中一次很有代表性,即林震、赵慧文两个青年人的谈话:“两个月前,北京进入社会主义高潮,工人、店员,还有资本家,放着鞭炮,打着锣鼓到区委会报喜,工人、店员把入党申请书直接送到组织部,大街上一天一变,整个区委会彻夜通明,吃饭的时候,宣传部、财经部的同志滔滔不绝地讲着社会主义高潮中的各种气象;可我们组织部呢?工作改进很少!打电话催催发展数字,按年前的格式添几条新例子写写总结……最近,大家在检查保守思想,组织部也检查。拖拖沓沓开了三次会,然后写个材料完事。……哎,我说乱了,社会主义高潮中,每一声鞭炮都刺激着我,当我复写批准新党员通知的时候,我的手激动得发抖,可是我们的工作就这样依然故我地下去吗?”不难看出,这篇小说的“继续革命”诉求主要表现在对官僚主义、保守思想的批判上,后者的“冷淡”与整个社会乐观昂扬的热烈气氛不协调。具有保守思想的官僚主义者不仅对“社会主义高潮”没有热情,而且还对青年人的热切响应冷嘲热讽,“有时,又觉得区委干部们的精神状态是随意而松懈的,他们在办公时间聊天,看报纸,大胆地拿林震认为最严肃的题目开玩笑,例如,青年监督岗开展工作,韩常新半嘲笑地说:‘吓,小青年们脑门子热气起来啦……林震参加的组织部一次部务会议也很有意思,讨论市委布置的一个临时任务,大家抽着烟,说着笑话,打着岔,开了两个钟头,拖拖沓沓,没有什么结果。”
而曾经是北大自治会主席的热血青年刘世吾现在已经变得僵化保守,他已经“看透了”,某种程度上已经被官僚化的“组织”给异化了,他只有在新来的年轻人林震身上才能看到自己的影子——曾经的热血、激情和不妥协的“战斗精神”——这也是小说中刘世吾并非完全是一个负面人物的原因,他说:“那时候……我是多么热情,多么年青啊!我真恨不得……”“可是我真忙啊!忙得什么都习惯了,疲倦了。解放以来从来没睡过八小时觉。”他理解林震所做的一切,但是现实却是“那又如何呢”。这篇小说无意识中显露的不仅仅是青年人和官僚主义者的矛盾冲突,而且还有官僚组织的无处不在的异化力量。
这篇小说发表后受到毛泽东的关注。毛泽东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到这篇小说并为之辩护。毛泽东如此关注这篇小说的原因在于:首先,它是一个只有22岁的青年作家写的,且文章的内容与毛泽东一贯相信青年人具有创造精神和较少保守思想的看法是一致的;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这篇小说让毛泽东看到了一种希望,小说中的年轻人尽管还不成熟,但是他有着拒绝保守僵化的“继续革命”诉求。正是这篇小说在反官僚主义和反保守思想表层之下还有一个“继续革命”的诉求和追求“真正社会主义”的冲动,才是毛泽东为这篇小说辩护的真正原因。
对于毛泽东来说,他看重的绝不仅是王蒙的小说提供了一个反官僚主义的标本,而是他对小说中林震那样的青年人抱有更高的期待——期待要求“继续革命”的青年能够克服“一五”计划的负面后果及日渐形成的官僚主义现状。所以,虽然小说中的正面人物还没有完全成熟,但总起来说,毛泽东还是很认可这个人物的。青年人林震有着永葆革命热情的“继续革命”诉求和比较高的无产阶级觉悟,在他身上毛泽东看到了一个新的、潜在的“继续革命”的主体(青年/学生),所以他“力挺”这篇小说,把否定这篇小说的李希凡和马寒冰批评了一顿[8]。
毛泽东对这篇小说不满意的一面,也不在于林震的“战斗性”不强,而是他还没找到一个“合作者”、一个能够领导他“继续革命”的领袖或者精神指导者去战胜官僚主义。毛泽东最终绕开官僚集团直接面向青年人(包括青年学生)并号召青年人打烂这个体制,重组一个“继续革命”(不忘记革命目标)的、有着“自我否定性的国家体制”(这当然造成了灾难),因为“反右”和大跃进而延宕到了十年之后。可以说这篇小说标示青年毛泽东主义者的初步出现,他们与十年后的青年学生有着相同的精神气质,只不过,这种精神的连续性因“反右”而暂时中断。——左翼内部的自我否定是更激烈、更为有力的自我批判。
“文革”及其前夕的反官僚主义
1957年的反“三害”及随后的“反右”联系着“文化大革命”。“反右”加固了官僚化的统治,一种“政治终结”[9]的局面再次出现。毛泽东其后发动的进一步冲击“按常规走路”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大跃进又遭失败;而大跃进之后,在毛泽东看来的“资本主义复辟”政策又使其将党内的政策分歧上升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高度。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这一方面有反官僚主义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政治终结”焦虑的内在必然。
1960年代初调整时期的政策,在毛泽东看来是“资产阶级复辟”。实际上,毛泽东对之前中共八大的决议和社会主要矛盾的结论是不满意的。他认为“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毛泽东认为阶级斗争不能“缓和”,因为“树欲静而风不止”,资产阶级要“吹台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说党内的“整改”“也包含两条路线的斗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党内存在这三个东西,这个账要挂到资产阶级身上”。[10]这样,党内的整风也就具有了阶级斗争的性质。
“反右”之后的毛泽东越来越向此前那些被打成“右派”的左翼青年的主张靠拢——毋宁说他们本来就是一致的。事实上,当时的“反右”并没有仔细区分那些真正反对社会主义的右翼言论和左翼内部的“继续革命”诉求,因此,今天的“右派”一词带有一种本质主义的遮蔽性,它容易让人产生“压迫—反抗”和自由主义者受难的想象,尽管这也是事实,但当时的情况无疑要比这复杂得多。左翼知识青年反对官僚主义、要求“真正社会主义”和“继续革命”的诉求却成了他们反社会主义的证据,这不能不说荒诞之极;他们的“蒙难”不是因为自由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主张,恰恰是由于他们反对自由主义和坚持“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缘故。他们响应了毛泽东的号召,但是在“反右”之后却被否定。实际上,他们的精神气质和十年之后的青年学生非常接近,而十年之后,这些青年通过小说的形式又一次出现,尽管前者已经是否定和批判的对象,但是,从“百花时代”的左翼青年,从十年之后浩然小说中的年轻人再到“文革”中的青年学生,他们那种左翼革命内部的理想主义激情和“继续革命”诉求却是一脉相通的。
毛泽东在“文革”前夕号召“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的时候,呼唤一种具有彻底的无产阶级觉悟和不妥协精神的新人出现。然而实际上,在“百花时期”的整风——民主运动中这种新人已经出现了,只不过很快被“反右”运动给夭折了;“大跃进”时期这种新人又开始出现,最后终于在“文革”中成长起来。例如赵树理的《“锻炼锻炼”》(1958)中出现了一个叫杨小四的年轻人,他是村合作社的副主任。小说中另一个重要人物社主任王聚海,是一个“和稀泥”的“和事佬”的形象,也就是毛泽东所谓的对阶级矛盾“缓和”的“八大”式人物,他对“小腿疼”和“吃不饱”这样的落后人物抱有同情的态度,还有他那种对年轻人要“锻炼锻炼”的官僚主义作风,引起了杨小四的不满。这篇小说具有从“百花时代”的反对官僚主义/ “干预生活”的小说向浩然的鲜明阶级斗争(在中国“当代历史”的语境中“阶级斗争”实际上是反对官僚主义的另一种形式)的小说过渡的性质。王聚海对落后人物的“宽容”,马上就会被指责为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他是马之悦等人物的雏形。而杨小四这个对资产阶级思想不妥协的年轻人,富有理想,有能力,没有中年干部的思想负累,他如梁生宝一样,是曼海姆所说的那个离开了村庄又回来的年轻人(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的青年主人公都是回村的复员军人),他可以从更高的社会主义和革命理想的角度打量这个村庄。杨小四是潜在的萧长春、高大泉,他与王聚海的矛盾已经出现,只不过此时还没有发展到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程度。——赵树理的本意可能并不是如此,但这篇小说显示的那种政治无意识却具有一种历史中间物的性质。事实上,这是当时小说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这在其后出现的工业题材反映两条路线斗争的小说中得到充分表现。这些小说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党委书记和厂长之间,前者主要依靠工人们的社会主义热情和精神力量,后者被表现为僵化保守,不相信工人们的创造性,只依靠“规章制度”且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官僚主义者[11]。可以看出,这仍然是“百花时期”左翼青年的“继续革命”和官僚主义、“保守思想”冲突的延续[12]。
分析《艳阳天》[13]中的萧长春和“百花时期”左翼青年的历史联系是有意味的。“1957年麦收之际”——这是《艳阳天》中的“故事”发生的时间,这也是当年左翼青年作家反“三害”和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发生的时间——的萧长春们与左翼青年作家笔下的人物或北大学生运动中的谭天荣惊人地相似。焦淑红对乡长李世丹偏袒马之悦的行为质问道:“上级怎么样?上级不办正确的事就行吗?”“他(指萧长春——笔者注)当了九个月支部书记,他领着大伙儿跟天斗,跟地斗,跟投机分子斗,跟地主富农斗,也跟那些要走资本主义的富裕中农斗过;现在还给他拉开一个新的阵势,还要跟一个错误的上级斗……(李世丹)心里没有群众,现在又发展到给敌人加油,给群众泼冷水。这是原则问题,路线问题,李世丹损害了党的利益;在一个党员来说,没有比党的利益更高的利益了,应当豁出个人的东西,坚决保卫它;如果在这样的问题上让步,那就是最大的罪过!”李世丹要求释放马小辫他们,结果遭到“群众们”的反对。
这里要稍微说到1957年整风时期(也就是“1957年麦收之际”)北大学生运动中的代表人物谭天荣。当年要求“继续革命”的谭天荣在1957年对待“三害”也是如此地坚决,他声称“活着,就得战斗”——向“三害分子”战斗[14],他的革命觉悟和战斗激情一点不比萧长春和他的“同志们和战友们”差。李世丹对“群众”“造反”的指责恰如当年《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的质问,当时谭天荣对《人民日报》的转向批评道:“人民日报组织的十字军,充分表现了没落阶级的情绪”,“红色的是火焰,白色的是剑;这是最后一场战斗!让真正的勇士们前进吧”[15]。像“1957年麦收之际”的萧长春把党内分为走社会主义和走资本主义的两类一样,谭天荣等左翼革命青年也是把党分为“进步势力”和“保守势力”两类——他们的批判对象其实是一样的[16]。如果说谭天荣(后来被划为“右派”)对当时的中国现实作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我们就不能说《艳阳天》没有这种批判——实际上越是类似《艳阳天》这样被称为“颂歌”的作品反而越是最有现实批判性,它的受欢迎不仅仅是因为它符合了当时的政策和有“农村生活气息”,更重要的还有它对现实最激烈的革命批判——那种“现实”肯定不仅仅是凭空“虚构”出来的——这些作品典型地反映了那个时代“自我否定性的国家体制”所具有的特征,它来自于左翼革命内部的自我否定和批判;事实上,这些作品与“林震”们以及北大整风时期青年学生的批评是殊途同归的。
因此,浩然的小说也可被反向称之为“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因为“批判”与“肯定”实在是只隔一层纸。浩然这种用“大民主”对待党内官员的方式正是“百花时期”的青年学生所希望的“狂风骤雨”的整风方式。不过差别在于,浩然小说中的李世丹是一个“右派”(他是一个事后的“右派”,这是小说的暗示)的形象,这样小说才有叙述的合法性,不过悖论或裂隙也就此产生:这个“右派”也正是当年激进的青年学生所批判的“保守势力”和“三害分子”[17]。整风转向之后,正是“李世丹”们清算了那些左翼青年作家和激进的青年学生,并把他们的“造反”、反对官僚主义、要求“继续革命”和“真正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为定为“右派”的证据,如今浩然的小说把这种“被颠倒的历史又颠倒了过来”,这不能不让人惊异:当年左翼青年作家笔下的“林震”们以及现实中的谭天荣不是又“杀”回来了吗?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同一个时期的革命青年“萧长春”和谭天荣却是截然相反的命运——这不仅仅是权力移位的结果,而且是1957年那场运动的必然后果。
余论
1955—1957年“百花时期”那些被称为“干预生活”的反官僚主义作品和1960年代以后那些反映两条路线“阶级斗争”(内含着反官僚主义倾向)的小说,在“文革”结束之后的新时期的命运是截然不同的。在所谓“拨乱反正”的政策下,前者被当作应该返回的“正”得到肯定,后者作为应该清除的“乱”被完全否定[18],而否定它们的理由却经历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在“文革”刚一结束时,对“文革”及“文革文艺”(如浩然的小说等)的定性为“极右”,当时似乎还要坚持“文革”“继续革命”的理念,因此只有将对立面定为“极右”才有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但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一定性就被否定,“文革”及其文艺被定为“极左”。
当时对“百花时期”那些“干预生活”小说的肯定是基于它们的“反官僚主义”主题,但是当时一些评论者立刻注意到“反官僚主义”的“极左”性质,因为在他们看来,“反官僚主义”是和“文革”紧密联系着的,这些评论者认为“文革”正是建立在“反官僚主义”的叙述之上的[19]。这种看法虽然在当时被认为是“左的”,但是它从左翼革命的内在逻辑出发作出的观察,实际上是正确地看到了“当代历史”的连续性,因为那两个时期在“反官僚主义”以“继续革命”的诉求上是一脉相通的。
这就意味着“百花时期”的那些作品作为“重放的鲜花”必然会经历一次改写,以合于当时对稳定政治秩序的要求。吴舒洁注意到,《重放的鲜花》的出版并不意味着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终结,相反,它恰恰是要以“反官僚主义”来批判前三十年“极左”思想并以此干预现实政治。然而更重要的是,作者注意到了《重放的鲜花》所谓的“官僚主义”是对“百花时期”的“官僚主义”的重写。它将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以“群众路线”和“大民主”(“阶级斗争”)来反对官僚主义的方式,做了一次意识形态的置换,即变为依靠“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来寻求“安定团结”的“秩序”的方式;一句话,新时期初期所谓的“反官僚主义”通过将官僚主义算在“封建主义”头上的方式,实际上内含了重建“官僚理性”(包括技术理性)的意识形态诉求。在这一置换中,不仅文学转换了新的功能,而且整个社会也开始了“去政治化”的过程[20]。
也就是说,从1955—1957年“百花时期”、1960年代之后的“文革”到“拨乱反正”的新时期,“反官僚主义”流变的历史也就是“当代中国”在其“自我否定性”中延续、改写和重建的历史。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
[1]毛泽东说:“在中国,对于许多人来说,1955年,可以说是破除迷信的一年。1955的上半年,许多人对于一些事还是那样坚持自己的信念。一到下半年,他们就坚持不下去了,只好相信新事物。”参见毛泽东:《<所谓一切乡并非一切都落后>一文按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493—494页。
[2]这些作品总起来说还是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要求的,因为它们在批判现实的同时还有一个鲜明的、要求“继续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指向,这与当时那些所谓“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对现实的仅仅批判是不同的。因此,我们应该对那些后来被称为“毒草”的作品作具体分析,因为它们的诉求是不同的。
[3]唐挚:《必须干预生活》,《人民文学》,1956年第2期。
[4]毛泽东:《<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一文按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522—523页。
[5]毛泽东:《<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突击队>一文按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533—534页。
[6]事实上,要求“继续革命”和追求“真正社会主义”是“百花时代”左翼青年的普遍诉求。1957年5月北京大学青年学生发动了“5·19学生运动”,学生们的言论及贴出的大字报,虽然主张、意见不尽相同,但其中一个主要的诉求就是反对官僚主义和“继续革命”。关于这次运动的经过和当时青年学生们的具体言论,可以参看北京大学思想教育委员会编《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内部参考,1957)及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印《校内外右派言论汇集》(内部参考,1957);另外,对“百花时代”左翼青年作家要求“继续革命”的反官僚主义作品和“鸣放”后北大学生运动的经过、诉求等的详尽分析,可参看笔者的论文:《“百花时代”左翼青年的反官僚主义话语(1955—57)》,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7]韦伯在其《以政治为业》的著名演讲中预言了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不可避免的官僚化命运,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建立的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只能是“行政管理专政”(dictatorship of administration):“情绪高昂的革命精神过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因袭成规的日常琐务,从事圣战的领袖,甚至信仰本身,都会销声匿迹,或者,更具实效的是,变成政治市侩和实用型专家常用行话的一部分。在为信仰而从事的斗争中,这一发展尤其迅速,因为领导或发动这种斗争的,通常都是真正的领袖,即革命的先知。情况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在这里,就像领袖的每一架机器一样,获胜的条件之一,就是将一切都空洞化和事务化,简言之,为了‘纪律的缘故,变成精神上的无产者。信仰斗士的追随者,取得了权力之后,通常很容易堕落为一个十分平常的俸禄阶层。”参见韦伯《以政治为业》,《学术与政治》,三联书店,2007年,第113—114页。
[8]“李希凡现在在高级机关,当了政协委员,吃党饭,听党的命令,当了婆婆,写的文章就不生动,使人读不下去,文章的头半截使人读不懂。”毛泽东替王蒙“解围”:“最近北京发生了一个‘世界大战,有人叫王蒙,大家想剿灭他。总而言之,讲不得,违犯了军法,军法从事。我也是过甚其词,就是那么几个人,写了那么几篇文章。现在我们替王蒙解围,要把这个人救出来,此人虽有缺点,但他讲正了一个问题,就是批评官僚主义。”参见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万岁》,出版者不详,1967年,第114—115、175页。
[9]韩毓海在《革命中国的兴起及其话语纷争》一文中提出这一概念。他还认为,“政治的终结”造成了一个类似于资产阶级的中间管理阶级:“现代社会的高度集中化,有可能使社会统治权力,既没有集中在无产阶级,也没有集中在拥有财产的资产阶级手里,而是集中在‘现代官僚阶级手中”,“正是由于现代社会的这种发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建立在所有制方面的对抗,变得不那么清楚了——‘集中化的后果是,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没有受到无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支配,而是被‘经营和管理社会生产的‘官僚所支配。”参见韩毓海编著:《20世纪的中国 学术与社会》,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1页。
[10]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繁体竖排版,1977年,第509—510、506页。
[11]实际上,在中国“当代历史”的语境中,所谓“阶级斗争”从来不是或很少是“无产阶级”同建国之后那些拿“定息”的真正“资产阶级”(也包括民主党派)的斗争,而主要是指党内的路线之争及坚持社会主义理想的革命者同官僚主义的斗争。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提到了如何彻底消除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体制”以及最终消灭国家的问题。但是消除官僚制和消灭国家只是最后的目标,在“社会主义阶段”,“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参见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70年,第88页)。因此,尽管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中国大陆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但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形式还是存在的;而且,虽然没有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但却形成了官僚理性和技术理性的统治(韦伯所谓“行政管理专政”)。因此,中国“当代历史”中的“阶级斗争”尽管外在的口号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但是其主要表现形式却是党内的路线斗争、“政治理论辩论”以及“继续革命”与“政治终结”的冲突。
[12]有评论者分析这些工业题材的小说,认为其写作模式可概括为“‘激情与‘理性的争斗”。参见徐刚:《“激情”与“理性”的争斗——1950—1970年代工业题材文学及其文化政治》,《文艺理论与批评》,2011年第5期。
[13]这里要分析的是《艳阳天》(第三卷),本文用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的初版本。
[14]谭天荣:《致朱志英同学》,《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内部参考),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委员会编印,1957年,第50页。
[15]《这是为了反对三害》,此文是谭天荣对《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的回答,见《校内外右派言论汇集》(内部参考),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印,1957年。
[16]有论者也发现了《艳阳天》和之前相同题材小说的连续性:“这部作品从整体来看,与建国初期表现农村合作化题材的小说有千丝万缕的瓜葛。这首先是一种思想哲学观念上的联系,使前后作品都有让阶级斗争情节赖以确立的基础。”——之所以有这种“思想哲学观念上的联系”是因为它们面临着相同的、贯穿“当代历史”始终的“政治终结”与“继续革命”的冲突——这种冲突在“当代历史”的非常语境中表现为“阶级斗争”的形式。参见董之林:《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6页。
[17]从林希翎当时的思想状况可以发现当时激进的青年学生对“保守势力”和“三害分子”的“痛恨”,他们与“同一时期”(“1957年麦收之际”)的“萧长春”一样嫉恶如仇。林希翎说“反官僚主义人人有责”:“在青年报上有文章说小资产阶级看问题有偏见,会发生匈牙利事件,害怕小资产阶级片面地反对官僚主义。我看只要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人都有偏见。主席没有偏见还革不了命,赫鲁晓夫的报告没有偏见吗?工人罢工没有偏见吗?工人最有偏见。工人对不合理的事情非常不满。我国五亿多小资产阶级,五亿人不反对官僚主义,什么人反对官僚主义呢?五亿小资产阶级总比官僚主义好得多吧,五亿人总是宝贵的,除开五亿,剩下一亿,这一亿中真正的产业工人没有许多,工人和小资产阶级有许多联系,这样归根到底只剩下了领导者。这个论调等于不让大家反官僚主义,我说:反官僚主义人人有责,甚至是反动的人。”(《我的思考》,见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 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唯一的不同是,萧长春的“阶级斗争”和反对官僚主义已经没有了受“小资产阶级偏见”指责的担忧。
[18]董之林注意到新时期小说那种要和“错误的时代划清界限”以开辟一个文学“新纪元”的努力,但是其创作仍与“十七年”和样板戏有着众多联系。参见董之林:《亦新亦旧的“新时期”小说》,《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70—271页。
[19]王若望:《反官僚主义和“干预生活”》,《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
[20]参看吴舒洁:《〈重放的鲜花〉与拨乱反正》,《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