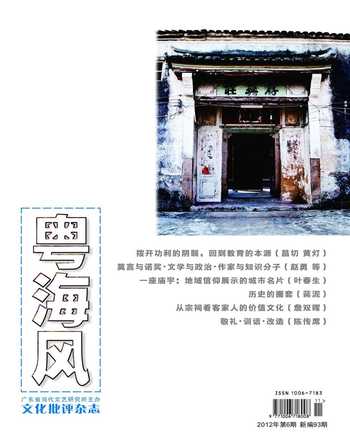“剧本荒”与网络改编热
2012-04-29康建兵
康建兵
当代戏剧特别是近十余年来的戏剧一直遭遇戏剧危机的严重困扰。从1980年代初起围绕黄佐临先生的《漫谈“戏剧观”》一文展开的对“戏剧观”的争鸣以及对戏剧危机的探讨,及至本世纪初由剧作家魏明伦在岳麓书院关于当代戏剧之命运的演讲再度引发的讨论,戏剧界也一直在为当代戏剧把脉,最后综合各家之言发现,当下戏剧从里到外都有病,其中最要命的病根是“剧本荒”。当下的戏剧危机首先危在缺乏剧本,不是数量上缺乏,而是缺乏原创性的好剧本。黄佐临在半个世纪前谈到的他心目中那种“最理想的剧本”在当下寥寥可数。
当下戏剧遭遇着剧本质量上的“无米之炊”,这种情况不独是戏剧的窘境,也是电影和电视剧面临的大难题。在以往对戏剧命运的讨论中,大家常常将三者搁到一块儿谈,将电影特别是电视的发达视为造成戏剧危机的祸首之一。而就在中国互联网在新千年刚开始便势头猛进时,魏明伦则看到网络对戏剧的影响,认为我们进入“电视电脑的时代,就是居室文娱,斗室文娱的时代”。[1]然而,对戏剧与网络关系的探讨却一直未得到应有重视。应当说,造成今天居室斗室文娱现象的出现,网络“功不可没”。互联网时代的戏剧与影视不再是冤家,而是在快速推进的媒体融合进程中被整合进新媒体,其间关系也从竞争走向竞合。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隔离了人与人在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交流,反之网络又促成斗室中的人与人在网络上实现集群虚拟交流,网络自身这一悖谬特性也与戏剧发生关系,其表现之一就是一些流行网络文学对当下戏剧影视带来的诱惑和影响。
戏剧遭遇“剧本荒”,戏剧自身也在百思其变,比如奉行“拿来主义”。这里说的“拿来”,既指从一批优秀小说或者传统经典剧作那里取经,以共享艺术精华,展现多重魅力。比如近年来舞台上常见的还是那批常排常演的经典剧目,或者改编当代著名小说入戏,或者邀请小说家操刀剧本。于是,莫言的戏剧《我们的荆轲》、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和余华的小说《活着》等都被搬上舞台,这确实为当代戏剧注入一剂强心针,也是我们应当大力提倡的。正如莫言所说:“小说家写话剧,应该是本色行当。”但在不断“拿来”中也出现了戏剧搭顺风车现象,不仅搭影视剧的顺风车,也搭网络文学的顺风车,省心省时省事。特别是由于影视“剧本荒”之荒谬和荒芜程度不亚于戏剧,因而也纷纷向网络文学要奶喝,戏剧影视三者归一,殊途同归,都在网络文学中挖剧本。当代美国戏剧学者罗伯特·科恩曾说:“从舞台实践的角度而不是从理论的角度来看,戏剧是一种相当保守的事物。”[2](P288)如果将科恩的判断置于网络时代的中国当代戏剧场域,可以发现戏剧与网络文学发生关系后,其舞台实践不是相当保守,而是十分活跃。
回首过去十余年,当代戏剧不仅向网络文学要素材,而且有时候还同影视赛跑,往往一部网络文学的影视版还没杀青,戏剧版反倒捷足先登。一时间,话剧《杜拉拉》、《步步惊心》,越剧《第一次亲密接触》和粤剧《梦惊西游》等纷纷登台亮相,轰动一时,戏剧也因对影视剧的间接改编或对网络文学直接改编而沦为二度乃至三度改编户。但即便如今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等都对网络文学“网开一面”,终归网络文学还是被视为下里巴人,不为阳春白雪的精英文学真正接纳。改编自网络文学的戏剧版也常常脱不了“赶潮”或者“要市场不要艺术”等非议。进而,即便戏剧与网络文学发生关系十余年,却未能触动学界去思考网络改编剧以及戏剧与网络文学的关系,这也应了布莱希特一句话:“大众戏剧通常被认为是幼稚的,乎庸的,学院式的美学要么不理睬它,要么贬低它。”[3](P137)
我们不妨先来梳理一下当代戏剧与网络文学亲密接触的过程。戏剧与网络发生关系可以追溯到互联网在中国的起兴初期。从1990年10月中国开始参与国际互联网活动到1994年4月被国际正式承认为有互联网的国家,国内互联网这一新兴媒介在快步发展的同时,顺势催生了一批与网络有关的新生事物,其中网络文学发展迅猛,并在1998年至2001年迎来黄金时期。1998年3月22日到5月29日,台湾的蔡智恒在网上电子公告栏发表长达34篇连载的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在台湾和大陆文学界掀起网络文学热潮。此后,一大批网络小说陆续面世,有的以惊人的阅读量和下载量异军突起,引人关注。而戏剧与网络文学发生关系正是从开网络文学先河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开始的。2000年12月1日晚,北京“70”剧社将《第一次亲密接触》改编为同名话剧,在清华大学艺术中心首演。2001年3月20日,同样改编自这部网络小说的同名话剧被北京人艺搬上人艺小剧场,成为当时国内影响最大的网络题材话剧,北京人艺也由此成为国内主流剧院开戏剧改编网络文学之先河。此后,不少成名于互联网并被出版成书或被改编为影视剧的著名网络文学都出现了戏剧版。比如,李唯的《跟我的前妻谈恋爱》、张小花的《史上第一混乱》、六六的《双面胶》、三十的《下班抓紧谈恋爱》、鲍鲸鲸的《失恋33天》等都被改编为同名话剧。有的被改编为戏剧后剧名稍有改动,如唐浚的《爸爸,我怀了你的孩子》被改编为话剧《恋人》,李可的《杜拉拉升职记》被改编为话剧《杜拉拉》。慕容雪村的“青春残酷系列”《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天堂——打左灯向右拐》和《多数人死于贪婪》均被搬上舞台。不仅话剧界出现网络文学改编热,连戏曲也跃跃欲试,而且戏曲触网也是从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开始的。比如,上海越剧院于2003年将其改编为同名越剧上演,开戏曲改编网络文学先河。广东粤剧院在2004年将今何在的《悟空传》改编成青春粤剧《梦惊西游》。2008年,广州红豆粤剧团又将慕容雪村的《天堂向左,深圳向右》改编为粤剧《广州淘金人》上演。2012年,上海越剧院再度出击,购得流潋紫的网络小说《甄嬛传》的越剧改编权。
对于当下戏剧出现的网络文学改编热,我们通常将其归为两个主要原因,其一即戏剧“剧本荒”,其二是剧院出于票房考虑,故搬演之。就前者来看,如前所述,“剧本荒”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问题在于,假设戏剧没有出现“剧本荒”,是否同样会出现对网络文学的改编呢?戏剧与其他文学样态之间常常互为主客,从古至今相互改编是戏剧的一个传统,不足为奇。而要从网络文学改编戏剧,必然得有互联网新媒介的出现以及网络文学发达的时代才有可能。以互联网为主要支撑的新媒体对当今的文学艺术产生的影响非常明显。作为艺术载体和传播媒介的网络不仅对戏剧的传播起着媒介作用,载体本身所衍生的新文学艺术样态也会对戏剧产生影响。那些发端于互联网并且已经从网上到网下都发生了轰动效应的网络文学不可能不为戏剧所关注和改编。戏剧自身特有的观照时代和求新变异的艺术特质也会使其注意到网络文学的出现、存在和影响。人类戏剧特别是20世纪戏剧从来不曾拒绝过任何新兴艺术或新媒介的融入,为我所用,并衍生出一些新的戏剧类型和戏剧形态。早在1990年代末国内就有研究者喊出“网络戏剧——未来的戏剧”[4]口号,当下又出现了手机戏剧、博客戏剧等说法,这些命名是否得当还有待商榷,但其客观存在却是事实。近年来学者邹华斌提出“大戏剧”观念,认为“不管何种载体、何种形态的戏剧,都有它发生、发展、演变甚至消亡的历史过程,都值得研究”,“用‘大戏剧的观念来观照戏剧,其形态和内涵多姿多彩。”[5](P2)学者王廷信也指出:“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会以不同的手段创造戏剧……那么会不会出现‘网络戏剧?我想也是有可能的。”[5](P9)关于网络戏剧的说法,是应该侧重从网络的媒介载体功能着手考虑,还是应该更多以网络文学提供的题材或者关于网络自身的故事题材考虑,不一而足,但戏剧改编网络文学热却预示了网络对戏剧的影响走向多元以及网络戏剧出现的一些征兆。因此,将当代戏剧置于这一大时代来考虑,足见戏剧与网络文学发生关系是必然趋势,“剧本荒”只是佐证戏剧对网络文学改编热的必然,但它却未必全然是祸首。
就后者来看,有人指责改编网络文学是“要票房不要艺术”。如果说从网络文学改编的戏剧几乎都有极高的上座率和票房成绩,倒也是事实。北京人艺的《第一次亲密接触》首演起在人艺小剧场创下了连演57场且场场爆满的奇迹。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恋人》首轮14场演出也是场场爆满。其他网络文学的戏剧版演出也是如此,常常是戏还没上演,前几轮的票早已告罄,一票难求。有的改编剧先在小剧场演,但周末为满足观众需要就得加座或临时改到大剧场演,这种情形似乎在1980年代戏剧的短暂春天时才易出现。北京的戏逍堂在2010年以百万天价购得《鬼吹灯》的话剧改编版权,可以管窥网络文学给戏剧制作方抛出多大的票房畅想。而一部改编剧打出名堂后,地方剧团很快移植排演,同样反响不错。北京人艺在2011年还隆重重排《第一次亲密接触》,以纪念该剧演出十周年。网络文学改编剧也让一些年轻导演崭露头角,如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80后导演何念就经常选择热门网络小说予以改编,《跟我前妻谈恋爱》、《双面胶》和《杜拉拉》等均由其执导,何念还监制了一批其他网络小说改编剧,同样获得成功。
但仅仅将剧院的票房考虑视为戏剧网络文学改编热的出发点也有失偏颇。一些网络文学之所以走红,原因很多,有情节吸人眼球的,有团队精心策划的,有不少是炒作的,但往往流行作品都比较关注当下现实生活特别是一些热点问题如情感、婚恋、伦理和职场等,这些容易引起年轻群体的兴趣。当然,随之而来的是一些公式化、概念化甚至庸俗化的套式泛滥。另外,一部网络文学被改编为戏剧时,多由名导执导或明星参演,戏剧也借了网络文学的人气,但还得在舞台表现艺术上下一番功夫。网络文学大都长篇累牍,动辄几十万字,改编为电视剧后也是长剧,而要将其时间、地点浓缩在方寸舞台上的有限时间里更不容易。从这个角度来说,改编网络文学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戏剧可以借着网络文学的东风,省去宣传环节,有一定的源自网络文学和影视版的观众群的保障,往往戏未上演就赚足人气,在改编上也有影视版参照;另一方面,戏剧既要为搭顺风车而顶着各方面压力,还得顶着戏剧带给自身的压力。演砸了不仅得罪观众尤其是得罪难得进剧场的年轻观众,更容易在他们心目中败坏了本已是冷清艺术的戏剧的口碑。或许正因为如此,当下戏剧的网络文学改编虽然出现了一定热度,但几乎就是北京和上海的“双城记”,如再算上广州,顶多就是“北上广”三足鼎立。北京和上海的戏剧活动最活跃,剧团众多,思潮涌进,更有北京人艺和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等牵头,出现网络文学改编热自不待言。广州地处开放前沿,敢于尝鲜,包容性强,粤剧又以“善变”著称,因而出现网络文学粤剧版也属正常。实力派剧院参与网络文学改编,无论在题材把握还是艺术创新上都会有一定保证。
魏明伦曾说:“当代戏剧的特征是观众稀少。不是没好戏,而是戏再好,也少有观众上门。”[6]好戏自然是有的,魏明伦就写了很多好戏,但像魏明伦、李龙云、刘锦云、过士行、陈亚先、郭启宏和郑怀兴等能写出好戏的当代剧作家却不多。从网络文学改编的戏多半不是魏明伦认为的“好戏”,却能让一部分观众心甘情愿掏钱买票进剧院,值得我们思考。有人说这些观众中有的只是网络文学迷或网络文学影戏改编版的迷,他们追的不是戏剧,而是网络文学的效应,甚至有的观众直言他们之所以看《和空姐同居的日子》只是冲着剧名去的。但不管如何,这总比那种“台上振兴,台下冷清”的局面好,也比那些拿到“工程奖”后便被束之高阁的阳春白雪好。就像曲润海先生所说:“有的戏真的是阳春白雪,但获奖后便束之高阁,再无人问津,甚至寿终正寝了,阳春白雪又能怎么样呢!而下里巴人,雅俗共赏的戏却没有真正受到提倡和支持。”[7]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在2008年根据汤显祖的《牡丹亭》创演的一部优秀同名舞剧摘得中国舞蹈“荷花奖”在内无数大奖,并于2011年1月登上纽约林肯艺术中心这一世界艺术圣殿。这部备受赞誉的好戏虽然也在国内一些城市巡演,但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几乎是既看不到也看不起,甚至剧团所在地南京的观众也很难一睹风采。该剧编导吕玲老师去年还向笔者坦言,虽然他们也想在南京公开售票演出,以飨家乡观众,但又担心有票房压力,于是作罢。而网络文学改编剧至少能让一部分观众特别是越来越稀缺的年轻观众走出网络,走进剧院,去感受剧院的神圣,感受剧场戏剧艺术的真正魅力,感受人与人之间活生生的现场交流,这也算是一个功绩。
当然,那些走红的被戏剧人看中的网络文学自身的质量也良莠不齐,像《甄嬛传》等引起不小争议的作品更需要戏剧人在改编时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虽然向网络文学改编剧既要票房又要艺术有不小的难度,但若能起到一些借他山之石来攻戏剧这块玉的效果未尝不可。对于网络改编剧的走向,我们不妨本着“不排斥、不提倡、不棒喝”的态度,将其交给观众去裁夺。良好的戏剧生态需要百舸争流以激活世界大舞台,也要承认和允许分流现象的存在。北京人艺在2011年不仅重排《第一次亲密接触》,也将莫言的戏剧《我们的荆轲》搬上舞台。如今,将两者相提并论似乎更不太恰当,但这不正说明人艺的革新姿态和包容精神吗?!这种“巴人”和“白雪”同台表演的景况难道不应是良性发展的戏剧生态理应秉持之道?!当然,终归我们不仅需要饱含思想深度、人性关怀和“艺才”丰呈的好戏,也要让观众尤其是普通老百姓能够看得到、看得起这些好戏。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
[1][6]魏明伦.当代戏剧之命运——在岳麓书院演讲的要点[J].中国戏剧.2002.12
[2]罗伯特·科恩.戏剧(第6版)[M].费春放主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3]贝·布莱希特.布莱希特论戏剧[M].丁扬忠、张黎等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
[4]孙文辉、浩歌.未来的戏剧——网络戏剧[J].东方艺术.1997.6
[5]邹华斌、李兴国.大戏剧论坛(第2辑)[C].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7]曲润海.从台上台后看中国当代戏剧之艰难[J].中国戏剧.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