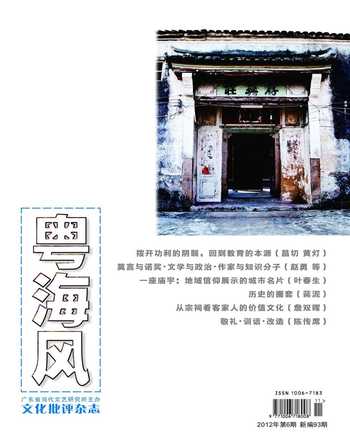领袖摄影与“第二历史”
2012-04-29汤天明
汤天明
一
历史是客观世界运动发展的全过程,这里的“客观世界”可以理解为“人类社会”(排除了科学意义上的“自然史”),经历漫长的约定俗成,“历史”一词也可用于指称“关于历史的文本”,如“清史”、“民国史”、“当代史”,实质上只是对这三个历史阶段的叙述与分析。巫鸿认为,“客观世界运动发展的全过程”,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第一历史”,“第二历史”则是对第一历史的叙述,“第二历史因此不但记录和保存着第一历史,同时也改动甚至取代着第一历史”[1]。
在丰富的“第二历史”中,作为视觉政治的领袖摄影是重要的视觉文本,它是对政治人物形象的直观呈现和与合法性建构,贯穿于整个政府形象的输入与输出过程,对公众的政府形象认知产生着巨大的效应。因而也受到了宣传、文艺、新闻机构的高度重视,成为政治传播的重要环节,持续构建着一个以照片为主体的视觉“拟态环境”。
“拟态环境”概念由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一书率先提出,它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像摹写”,而是以现实为蓝本,由传播机构经选择性报道、加工后形成的“象征性现实”,由于大多数公众只能通过传媒了解外部世界,长期浸淫在这一拟态环境之中并受其制约,公众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就会发生偏差。“拟态环境”说显示出教育、宣传、出版等传播机构在议程设置、建构认知和历史书写中的巨大效能,若上述传播主体不能把握公正、客观原则,从而扩大“拟态环境”与客观现实的差距,就会造成公众的认识偏差与认知困境。
意识形态的建构与灌输,不可避免地需要“事实”的参与,“事实”是理论的佐证,一旦公众接受了“事实”,记忆就会被同化,进而更易认同意识形态的说教。新闻界、史学界作为记忆工作者,对于摄影图像的大量使用,等同于掌握了创造“第二历史”、“拟态环境”的视觉武器,巩固了自身记忆权威的身份。
二
摄影的传播特性在于,不管照片与事实有无差距,传播者总是把它当作“真实”本身加以传递,对于照片,读者也内建着对真实的天然期待。然而,领袖摄影是如何建构“事实”的呢,照片中的“事实”,与作为第一历史的史实之间,是高度一致,还是存有差异?我们不妨以肇始于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摄影图像为标本,考察照片、史实与政治建构三者的互动关系。
在“救亡压倒启蒙”这一现代史主线的主导下,自延安时期起,在根据地宣传、文艺部门的统一指挥下开展的摄影活动,一直将“革命”与“战争动员”作为工作主题,沙飞的“武器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革命现实主义思潮,都从不同侧面对摄影施加影响甚至直接规制。急迫的军事动员诉求和一元化的根据地政治体制,赋予了摄影以至高无上的工具属性,这一属性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不断得到巩固和强化,进而深刻地成为摄影工作者的高度自觉和摄影机构的工作规范,也深刻地规制了领袖摄影的拍摄、制作与传播。
延安时期,各根据地都成立了制度化的摄影机构,塑造出沙飞、吴印咸、石少华、徐肖冰等一批红色摄影名家。以毛泽东像为主的领袖摄影,成为延安政权铺展革命意识形态、建构政治合法性、凝聚军心民心的重要手段。从上述名家的文字论述及领袖摄影实践来看,“摆拍”在当时尚未成为得到官方认可并广泛实施的拍摄方法,领袖摄影在风格上偏向真切、生动、自然,显示出朴素的“决定性瞬间”思维,政治人物的个性、风格甚至魅力,都得到了比较客观的记录(但非“呈现”)。甚至,毛泽东因为劳累或营养不良而显示出的“不雅形象”,摄影师也能够相对自由地进行记录,杨昊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毛泽东图像研究》中,就有这样的一段记载:
笔者曾经得到吴印咸老人的一个亲戚赠予的一张毛泽东延安时期的翻印照片。照片中毛泽东坐在一张板凳上,上身松散地披一件旧布衣服,头发蓬乱,面容消瘦,颧骨突起,以略显惊奇的目光,望着右前方那位正在操纵老式摄影机的身着八路军军服的红色摄影师。[2]
不过,这种自由拍摄所获得的照片,却并未得到同等自由的传播,“吴印咸老人的一个亲戚”所揭示的,是“不雅之作”所依赖的人际传播路径,官方宣传、档案系统则出于“政治正确”的考量,有选择地保留了能够显示毛泽东正面、光辉形象的照片,而永久地封存了同样作为现实记录的不雅照。正面的唯一性与“负面”照片遭遇封杀,显示出官方在传播过程所秉承的“选择性”,这不妨视同为《1984》所指出的“新话”,前者是视觉空间的窄化,后者则是文字语言的萎缩,在一个只有正面、没有负面的宣传环境中,信息的极度限制,等同于剥夺了滋生批判性思维的土壤。一直到今天,“纪实摄影”这种具有强烈的揭露、批判精神的摄影门类在中国仍未获得充分的发展,也显示出上述“选择性”思维的历史传承。
吴印咸所摄《艰苦创业》,是毛泽东本人最喜欢的照片之一。照片所摄取的是1942 年毛泽东在延安给120师干部作报告的场景,这是“整风运动”中的一个事件。窑洞背景前的毛泽东身穿粗布制服,裤子上打着两块补丁,脚穿土布鞋,没有会议桌或演讲台,茶杯放置在毛泽东左侧的一张木凳上,勾勒出后来被称作延安精神之一的“艰苦朴素”的主题,而毛泽东紧拧的眉头、交叠比划的双手、从容不迫的站姿,又显示出一种深刻、自信和敏锐。如果为照片评价设置业务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复合坐标,《艰苦创业》只可称作业务精品,在史实与价值层面,它被割裂了与整风运动的联系,成为一个孤立的宣传产品和视觉符号,《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高华著)所描述的毛泽东在整风中的凌厉,在照片中得不到任何呈现,当然,也不会有更多的照片去陈述官方所不愿意承认的那些事实。
1943年,毛泽东在招待陕甘宁边区英雄大会上发表讲话,吴印咸所拍摄的几张照片,同样是“业务判断”坐标中的精品。在照片中,瞬间抓取是显而易见的拍摄手法,仰视暗示着领袖的高大,黑色背景则令毛泽东成为唯一主体。最值得一提的是“虚”的运用。在大多数领袖图像中,“实”(清晰)都是最基本要求,仿佛有一切为之屏住呼吸的威严感,而吴的两张照片,左图为景深之虚,右图则在景深虚化的基础上增加了低速快门造成的“动虚”,这种极具西方色彩的“模糊影像”,或许与吴印咸早期接受的美术训练和在上海的从影经历有关。只不过这种鲜活的形式感并没有产生新的政治意义,它因循的仍然是传统的正面建构模式。
“突出光辉、回避负面”的视觉书写,只是建构“第二历史”的方法之一,作为对“第二历史”的解构,艺术家张大力《第二历史》展览和影像传播活动,则揭示出后期修改机制在领袖摄影传播中的巨大宣传效能,具有丰富的政治学、历史学涵义。这项启动2003年的视觉工程的基本逻辑是:通过搜寻尘封的图片档案,寻找利用虚假照片建构历史的痕迹,将原始图片和通过暗房修改后的图片并列在一起并注明来源,以提供摄影造假的确切证据,并举行公开的展览以扩大这项研究的社会影响。分析《第二历史》展览所收录的关于毛泽东的虚假照片,可以总结出后期修改的一些基本模式和造假目的。
第一种是删除特定的历史人物。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参加谈判,摄影师吴印咸拍下了毛泽东在机舱前向欢送人群挥帽致意的照片,作家方纪在《挥手之间》一文中写道:“请感谢我们的摄影师吧,为人们留下了这刹那间的、永久的形象;这无比鲜明的、历史的记录!正是在这挥手之间,表明了一种深刻的历史过程,表现了主席的伟大性格。”而事实情况是:站在毛泽东左侧且在原照片中露出头部的美国特使赫尔利,在后期修改中被抹去了,毛泽东的形象更显独立,美国在和平进程中的历史参与也被消解。
在这类照片中,有一些修改并不是在图片的初始传播状态下进行的,它们起初以原貌示人,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和新的历史书写需要的产生,才会引起制像和宣传部门的注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曾有一幅四人合影,而后来在整风运动中因路线斗争而败北的博古被抹去,照片上的四人降为三人。一幅毛泽东与彭真在十三陵参加劳动的照片,随着彭真在“文革”中的失势,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动,彭真几乎被天衣无缝地抹去,代之以一位工作人员的背影,而抹去刘少奇的照片则更为常见。上述政治人物在照片上的消失,不仅意味着他们在某一时期的政治失败,更意味着他们将从历史上消失,只有当权力对这些人物作出重新评价时,历史文本才有可能回到其原貌。领袖摄影的这一删除模式,在相近的绘画界也不乏案例,例如,受到高层人事变动和政治路线斗争的影响,董希文的《开国大典》前后经历多次修改,依次删除了高岗、刘少奇两位参与开国大典的前高级领导人。
第二种是抹去有违意识形态和政治正确的历史痕迹,一幅毛泽东与朱德进行工作交谈的照片中,朱德军帽上的青天白日徽被抹去,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事实被人为弱化甚至抹杀;在一幅毛泽东乘车检阅部队的照片中,修版师删去了高高昂起的火炮口,消除了被定性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可能。第三种是删除“多余”人物或物体,或者是通过照片裁剪等手段,扩大人物所占比例、纯化照片背景,从构图上突出主体形象,使其成为唯一的视觉中心,以凸显领袖人物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1950年12月毛泽东访苏时的一张照片,背景中的其他中苏领导人都被删除,只保留了毛泽东和斯大林两位领袖。
第三种是人物替换或增添模式,《第二历史》提供了一些报纸的小样,能够清楚地看到,编辑圈出了需要替换的人物,并在周围的空白处粘贴了可供替换的新的人物图片。一张毛泽东的视察图片,原图中毛泽东向群众挥手,却并未投以目光,编辑将毛泽东的头部涂抹成彩色,在小样上粘贴了身着同样服装、但头部向右倾斜的毛泽东,通过这样的替换,毛泽东的亲民色彩得以塑造或加强。
第四是上色与润饰模式,通过暗房着色,赋予画面更多的色彩,强化其“红光亮”的传播效果,通过对皱纹、牙齿颜色、皮肤细腻程度的修改,美化领袖形象。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拍摄的《毛泽东在陕北》(一名“毛泽东在保安”),是最为著名的毛泽东照片之一,斯诺夫人洛伊斯·惠勒在谈到这张照片的拍摄经过时说,当时斯诺想拍一张很神气的“官方的”照片,但毛泽东穿着随便,头发又长,他感到不合适,和斯诺在一起的马海德摘下了斯诺头上的红军八角帽,戴到了毛泽东头上[3]。这张原为黑白照的照片,经过历次修改,不仅变为彩色,毛泽东的形象也得到了修整、润饰与美化,时年43岁的毛泽东在照片上显得比较年轻,显示出一种深谋远虑、坚毅果敢的气质和灵秀之气,照片随着斯诺的《西行漫记》一起面世,对外部了解身处与世隔绝的黄土高原的毛泽东,提供了一份打破神秘感的形象资料[4]。
出于保证政治正确的需要,照片的后期修改机制成为与拍摄同等重要的制像流程,而非拍摄过程的附属品。上述虚假照片在问世初期是为了意识形态的建构,在意识形态延伸的过程中,需要使用更多的谎言来掩盖之前的谎言,而不能出现“谎言链条”的断裂。这促成了谎言像滚雪球一般不断壮大,即便是经历了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思想启蒙以及新闻改革,即便照片打假在近年来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官方也不愿承认这类政治照片的虚假本质,各类学术刊物也仅限于对非政治类假照片进行批判,显示出传统宣传模式的封闭性和对谎言链断裂的担忧。
三
经历长期的历史积淀,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树立绝对政治权威的背景下,且伴随着历次政治运动与个人崇拜思潮的崛起,领袖摄影在建国后27年间日渐成熟,领袖制像的规程、手法都达到了巅峰状态。其中,毛泽东标准像的出现,是领袖模式走向顶峰的重要步骤。
标准像是一种肖像,但它更是有目的的独立制像,肖像构图只是标准像的外在形式,而组织化的制作与传播,以及政治建构、历史书写的意图,则是标准像的内在属性。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领袖图像往往是较为随意、轻松的生活和工作记录,新中国成立之后,辐射全国的宣传、教育、新闻、出版系统的建立,为领袖图像的大范围传播提供了物质条件,在此背景下,用于悬挂、张贴、陈列的标准像呼之欲出。用杨晓彦的话说:“尤其在视觉方面,确立领袖的标准像,使之成为一个广泛流传的政治象征,随着领袖地位的建立,也成为党对外宣传的重要内容。”[5]
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并无真正意义上的标准像,1949年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毛泽东像,是毛泽东1945年在延安拍摄的头戴八角帽、身穿粗呢制服的照片。1950年初,时任新闻总署副署长兼新闻摄影局局长的萨空了偶然看到《工人日报》上同时刊登的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照片,受到斯大林标准像精致画面的感染,他立即提议由新闻摄影局负责拍摄、制作毛泽东的标准像,得到了毛泽东本人的同意。但随后由齐观山、陈正清、郑景康和侯波四位摄影师拍摄的照片都不太理想,当时的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建议不妨从现有照片中挑选一张,经暗房加工后制作成为标准像。最终选定的,是毛泽东会见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时的合影,其中的毛泽东呈半侧面,由暗房高手陈石林负责制作,照片经毛泽东本人审定后正式发行。不到一年时间,就印制发行了2000多万张,中国人民银行于2000年发布的新版20元和l00元人民币上使用的毛泽东头像,还是依照这张标准像印制的。1951、1959、1964年,陈石林又分别制作了毛泽东的第2、3、4张标准像。
“像”的技术纪实特性,令其成为一种用以提供“身份确定”的工具,这在每一种社会制度下都是成立的。但在制定了“制像”制度的国家,标准像的出现,为领袖图像设立了国家标准,新闻、出版行业在传播标准像方面的“不遗余力”,是标准像扩散的制度保障,标准像在公共场所和私人空间的广泛悬挂,是树立领袖权威的重要环节。自领袖标准像诞生之后,“像”作为领袖权威的直接代言,经常在新闻照片中出现,以模拟领袖的“在场”状态,在这类照片中,标准像成为仪式化的道具,摄影也成为一种政治仪式。
毛泽东标准像的制作者陈石林,1929年生,幼时辍学,进入一家照相馆学习照片制作,1948—1950年就职于香港大光明电影公司,1950年回到北京,进入中央新闻摄影局和新华社摄影部工作,由于具有很强的业务能力,他最终升任新华社摄影部技术组组长、翻修组组长和全国领袖照片工作组组长。这里的“翻修组”和“全国领袖照片工作组”,能够从建制上说明“像”以及“像”的制作技术在当时的重要地位。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接班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全国各省要求马上悬挂华主席像,中央决定由北京新华印刷厂统一制成高质量的胶版,分别派专机送到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由各省的新华印刷厂日夜加班赶印,及时发行到各地机关厂矿和农村。胶版到达时,一些地区挂起“隆重迎接敬爱的华主席像”的横幅,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很显然,标准像带有很强的个人崇拜色彩,暗示了政治领袖无所不在的政治影响,也时刻提醒着“像”的观看者们保持忠心。在某些国家,领袖图像甚至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2012年出现的一条《朝鲜14岁女生保护金正日画像被淹死获嘉奖》的新闻报道,就颇值得我们玩味。
四
1949年以后,非标准像类的领袖摄影,较之先前也更具正规化、模式化色彩。《毛泽东和韶山中学师生们在一起》、《毛泽东与亚非拉朋友在一起》通过以毛泽东为视觉中心的构图方式,凸显领袖的主体地位;吕相友的《身着军装的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构图上则是以毛泽东为唯一主体,背景纯净、画面简洁,毛泽东身着军装,戴着红卫兵的臂章,表情严峻、凝重,举起的右手并未营造出画面的动感,却给人一种时间停止的想象。而“文革”爆发当年的一张照片,更能显示出领袖摄影的工具、象征色彩,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一张毛泽东畅游长江后穿着睡衣在游船上招手的照片得以流传,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在追求正统、严肃的中国,睡衣与政治似乎是格格不入的,但这张照片的问世和传播,或许正是一种极大的政治,在“文化大革命”的气氛之下,毛泽东为江青题照的“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所蕴含的政治气概,与畅游长江的非凡体力所隐喻的政治勇气和政治决心,不是更为匹配么?无论如何,这张图片内建着一种鲜活的张力,相较于呆板、僵滞的正襟危坐,它提供了更多的解读空间。当然,这种活力是由毛泽东非凡政治领袖的特殊身份和不受外界束缚的特殊性格决定的,它不是一种制度化的鲜活,在本质上,仍然是工具性的摄影传播观。
毛泽东图像与其个人权威的紧密关系,令拍摄晚年毛泽东的摄影师面临巨大的困惑,一边是被摄者衰老的面容和多病的身体,一边是严厉的传播政策,使得拍摄任务具有前所未有的复杂性。长期担任毛泽东专职摄影师的杜修贤,就经常因不太理想的领袖照片而受到质疑与指责。据刘丽峰编著的《最后的传奇:杜修贤摄影作品》介绍,杜修贤遭遇的指责包括:“为什么将毛主席拍得苍白无力?”“你们是资产阶级新闻还是无产阶级新闻?”“我们对《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五幅照片深感不满。我们认为,这样的照片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故,是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形象的污蔑,是我们广大工农兵群众所不能容忍的。”[6]可见,在政治高于一切的时代语境下,摄影对客观世界的复制、记录功能,已经被彻底扭曲了。而摄影师不遗余力的修改甚至造假行为,也是与对“潜在危险”的恐惧绑定在一起的,如果照片破坏了领袖的光辉形象,不仅是一个业务能力的问题,更是一个政治事件。
随着主流意识形态对“个人崇拜”的否定,“领袖”已经成为特定时代的产物,“领袖摄影”也为“高层摄影”、“时政摄影”等新提法所取代,然而,极左年代积累的摄影模式,仍然被赋予了明显的传承,虽然图片造假已经没有得到辩护的可能,但作为一种现象,它在高层摄影中仍有体现,2004年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期间,新华社发布的一张拍摄于90年代的高层图片中,某位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职务的领导竟然被抹去了,这让人想起那张毛泽东追悼大会的图片,“四人帮”当时尚未被捕,而照片发表时,四人同时消失,“文革”时期“四人帮”常用于抹去政治对手的手段,最终却被用于抹去他们自己,令其成为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摄影现象——造假者亲手构建的强大的谎言机器,仿佛一个巨大的、且具有自我强化能力的雪球,最终将造假者本人所吞没,它所显示的,是权力在事实面前的膨胀、嚣张与凌厉。
对于割裂了照片与史实的领袖摄影,理论界存有一种不算主流但也绝不弱势的看法——“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条件”。笔者的观点是,过度追究摄影界的责任,显然是有失偏颇的,摄影界对领袖的摄影记录或摄影塑造,无论如何都是一笔宝贵的视觉资料。对于应否归结于“时代局限”和“社会条件”,则应展开具体的分析,所谓“时代局限”的潜台词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对“那个”时代的批判,是以今天“这个”时代的变化为前提的。但问题在于,“这个”和“那个”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连续和继承,为什么造假这一手法,直至今天仍然大量存在?可见,“时代局限”论是对历史的人为割裂,在某些时候,它甚至存有回避、抹杀历史反思的倾向。而独立的、被赋予自由权利的“记忆工作者”的缺位,也为权力试图掩盖真相的天性制造了莫大空间。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1]巫鸿:《第二历史:改造历史的历史》,载《美术馆》,2010年第1期
[2]杨昊成:《毛泽东图像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4月,第19页
[3]甘险峰:《中国新闻摄影史》,中国摄影出版社,2008年7月,第48页
[4]杨昊成:《毛泽东图像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4月,第19页
[5]杨晓彦:《新中国摄影60年》,河北美术出版社,2009年9月,第32页
[6]刘丽峰:《最后的传奇:杜修贤摄影作品》,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