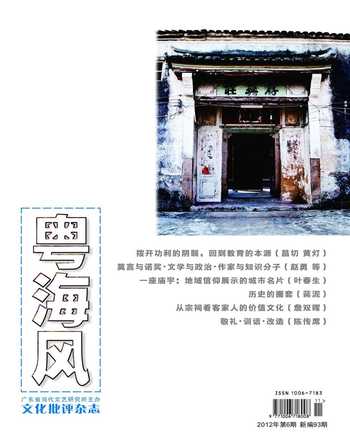农民是什么人
2012-04-29王际兵
王际兵
一
以“农民”来说事,是当代社会生活与话语中的普遍现象。其中文学艺术塑造了大量的农民形象。但是,即使上溯几千年,中国文艺也没有说清楚道明白农民是啥玩意,是啥模样。关于“农民”的述说,依然在路上,也只能在路上,并不存在一种所谓本真的农民形象。
我国古典文艺作品,刻画了不少农业劳动者的形象,但是他们并不成其为独立的农民群体,而是隐匿在广大的庶民和奴隶之中,尽管他们就是其中最大的群体。在庶民之上还有士、有贵族、有帝王。传统的等级社会是以政治和经济权利的区分为主导,可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贱民稼穑君子取禾,尤其是政治等级构成了阶层划分的基础。等级低下的庶民(或曰贱民)通常作为一个疾苦的对象,为文艺作品表现出来,而且他们的疾苦与其说是经济的,毋宁说是政治的。上层阶级通过权势剥削甚至剥夺他们的一切真是太容易了,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而从《范进中举》的生动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介庶民考而优为士以后,政治话语权便立即带来了经济上的回报,这也难为主人公喜极而疯了一回。庶民有了富足的经济条件,当然也可能向上面的阶层攀升,只是这个过程一点也不轻松,倘若找不到政治的依靠,他的富足很容易成为过眼云烟。政治地位的优先性,导致了政治身份遮蔽其他身份,所以古代经典中在场的是庶民是劳苦大众,是他们低贱而饱受压迫的生活,职业身份倒不鲜明。以农事活动作为主题的作品当然也有,如《诗经》里的《芣苢》、《驺虞》等;更多的还是以农事为起点书写等级压迫,立意在讽刺,如点到即止的《七月》,如大肆挞伐的《伐檀》。更不用说,那时各个社会阶层都没有完全脱离土地,帝王显然是最大的地主,贵族与士同样要依靠田产生活,他们亦可称为农民或者高级农民乎?“归去来兮”的陶渊明会是一个有文化的农民吗?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使得古典叙事模式有了改变,虽然白话新文学里劳苦大众仍然是身份低贱、生活疾苦,政治与经济的压迫犹如摆脱不了的梦魇,但是对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开始出现新的解释。如《阿Q正传》、《祝福》,在封建礼教的桎梏下,人们除了“被吃”无路可走;如《春蚕》、《多收了三五斗》,困守传统生产和交换信念的人们,不得不面对丰收成灾的困境;如《边城》,山村朴素的生活无法应对现代性的侵蚀,无奈日渐凋敝落败……作家的两只眼睛不再完全盯着外部世界,有一只转向了大众自身,他们发现大众的疾苦一定程度上是自己因袭陈旧的观念造成的,因而“哀其不幸”的时候又“怒其不争”。启蒙主义思想观照的是文化意识的落后,是一群文化落后的人物,是一片文化落后的地域。在此,有了“乡土文学”的说法,如作家沈从文不惮自言“我实在是个乡下人”。文艺话语流行从空间上界定人物的身份,其中也写农民,也写农事活动,然而这些农民与农事活动只是乡土的一个部分。“乡土”概念的确立,对应的是城市,是一种新的文明,是在西方文化的催化下形成的新社会。如社会学家费孝通1947年在《乡土中国》的开篇写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第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而乡土呢,甚少受到西方文化的催化,抱残守缺,不能应对时势的变化,所以,阿Q、祥林嫂及未庄或曰鲁镇的鸟男女们,老通宝,旧毡帽朋友,翠翠及湘西山民,等等乡下人,无不成为传统文化所吞噬的生命,必须通过启蒙来拯救他们的命运。如此,中心与边缘的位置关系悄然地跟文明与落后的文化关系画上了等号。田园山野渐渐不复理想的生活空域。
乡土的希望在城市,乡下人的“疗救”是变成城里人。宛如《从文自传》说道:“我想我得进一个学校,去学些我不明白的问题,得向些新地方,去看些听些使我耳目一新的世界。”(《沈从文文集(第九卷)》,第223页,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作家沈从文当年从湘西蛮荒走到都市北京,就是要寻找新的文化,这也成就了他,《边城》正是他带着新的文化意识对故土文化忧伤的凝视。只是希望一旦实现,难免要变成失望甚至绝望。沈从文也终究写下了讽刺城里人的作品。何况走向城里的乡下人,丢盔弃甲乃至丢失性命的实在难以胜数,成功者又何尝不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骆驼祥子从乡下来到城市,买了车,有了老婆,终究还是被荼毒了。城市也并非一个乡下人安身的好地方!没有了希望的沃土,最后的希望在于过程,也就是“走”的行动:“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全集(第一卷)》,第51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只是鲁迅的呼唤,又有几个乡下人能够听见,能够听进去呢?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奠定了后来几十年的写作方向。“工农兵”的提法,强调了职业身份的重要性,使农民、农村、农业独立成为文艺的客体对象;“服务”的提法,指明了作家认识世界的视角和态度,作家应该仰视而不是俯视农民。众所周知,赵树理的小说率先形成了新的叙事模式。通过《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及《登记》、《“锻炼锻炼”》等作品,农民被塑造为社会前进的一种动力,被描述为“进步/落后”的意识形态类型:农村干部、年轻人一般是进步的,坚持崭新的观念,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上年纪的人通常是落后的,固守传统的观念,不过这些“中间人物”在事实的教训当中逐渐转变,使得新的战胜旧的;作为陪衬的则是一些顽固的坏分子,如地主、恶霸等。尽管具体的情况略有差异,《白毛女》、《吐鲁番情歌》、《山乡巨变》、《创业史》等作品,都普遍在人物的职业身份上赋予意识形态及道德品质。农民不仅仅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而且是或进步或落后的人;农民在革命者的带动下,不自觉的改造意识变成了自觉的改造行动,掀起了一场“山乡巨变”,现代文学中失落的希望之路,被他们牢牢抓在了手中。这种把职业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的叙事,内在地应和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而且把个人的经济状况与意识形态叙述成了反比关系,越富有者越反动,越贫困者越革命。当它僵化地发展到“文革”时期,职业身份已经抽空至虚无,意识形态则无限膨胀,农民完全成了一个“进步/落后”的标签。不过,比起工人阶级必须是坚定的革命者形象,农民形象还是丰富多了,至少还可以成为选择题吧。
新时期文艺创作对待意识形态的态度是暧昧的。官方不仅在号召,也通过荣誉、资金、传媒等施加影响,但是生硬地粘贴意识形态话语只能使文艺堕落为口号,受众并不买账。在历史教训和古风西雨的引导下,作家们艰难地探索农民生活。《李顺大造屋》、《乡场上》、《鸡窝洼人家》等,渐渐把主流意识形态落实到故事情节——即人物生活的变迁上,人物自身则更多地成为文化观念下性格、心态的再现。由此,文艺深化了观照农民的道德与心理视角。它其实已经长期潜伏在现代文艺的文化意识视角和共和国文艺的意识形态视角之中,它原本只是其他作为目的的视角所附带的结果,由于创作的大肆渲染,由于在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中意义之源的迷失,曾经的所谓结果逐渐遮蔽了目的,走上了前台,尽管还偶尔折射目的。农民于是变成了一个土气的群体。“农”离不开土,“农”是在土上活动,“农”的根本意义就是土,农民就是土气的人,换个好听点的说法,农民接了地气。陈奂生、高加林、白嘉轩、福贵……一面是简单,善良,憨直,一面是自私,狭隘,狡黠,多点这少点那都无妨,综合起来就是一个“农民”。这种形象也折射在那些非农村题材的作品之中。相沿成习,农民一眨眼成了一种品质的代名词!骂一个人邋遢,称之“农民”;骂一个人老实,称之“农民”;骂一个人不通时务,称之“农民”……影视文艺发达以后,作为戏剧表演的要求,更是强化了这种印象式符号式的认识。
二
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塑造农民形象最成功的“大腕”是赵本山。1990年11月中华喜剧美学研究会在桂林召开第四届年会并以赵本山现象作为会议主题。人们普遍反映赵本山表演的人物毫不矫饰造作,好像是刚从观众中走出来的现实生活中的活人;甚至有人表示赵本山的局限之一即是“将所有的人物都化为东北的农民形象来表现”(《笑星赵本山》,第73页,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赵本山秉承东北戏曲“二人转”和东北方言的精华,在黑土地上孕育生长,刻画了“原汁原味”的农民生活和土得掉渣的农民形象,大俗即大雅,这已经形成了一场“文化革命”,与其他文艺货色的不景气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作为1980年代以来小品艺术崛起的杰出代表,赵本山有其自身的价值。但是,把小品看作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经典文艺,认为赵本山具有“文化革命”的意义,总觉得有些痴人说梦,其中的供给毕竟太稀薄。用个不完全恰当的比方,词起于唐朝,首屈一指的却是后来的宋词,因为宋词中涌现了更丰厚更伟大的作品。我们的小品在文艺类型上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而在丰富性和深刻性方面却还欠缺火候。它的流行是常见的通俗作品的流行。赵本山所标榜的“我是农村出来的,就知道只有站在土地上,接了地气儿,这样的东西才会真实好看,一部电视剧也承载不了更多的责任。我的电视剧剧情和人物的确有缺陷,但魅力就在于真实”(《赵本山发飙:我不高雅,也不装高雅》,《广州日报》2010年4月13日),其实是扯虎皮做大衣。以农民的名义发言,并不具有天然的正义立场和绝对的文化价值。有“地气儿”的东西,并不一定“真实好看”,遑论还有很多“缺陷”。如果说大众喜欢的是真实的农民,观看实际的农民生活不是更加直接、更加直观吗?赵本山能够自诩其农民叙事的真实,实乃因为那些演出复制于前人的思想模型,承继了既有的观察视角,投合了已经大众化的农民想象。他无力也无意识为我们提供一个“新”的观察农民的角度。
赵本山的演出讲述的都是农民中的能人。因其“能”,所以这些人处于农村与城市、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交汇、冲突之中,这样尤其见出了人物道德、心态的矛盾,营造出喜剧性的效果。本山摸索的这个门道,有助于刻画农民的土气,刻画土气的农民在现代社会的尴尬,却并没有开拓一个崭新的认识角度,讲述道德与心态之外的故事。在一个凝固的视角之下,他演不出多少新玩意。因其如此,他的表演中见不到那些捆绑在土地上穷困终生的农民——那些“土”得最彻底的人。其中年青一代的农民也是乏善可陈,他们要么像主流意识形态所鼓吹的那样进步了、文明了,要么是因袭老辈人,犹如小沈阳的格言“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对于如今已经无限分化的农民,那些套用既往模式的叙述只能是隔岸观火。在此,我们不妨引入名噪一时的《中国农民调查》一文中的话语:“我们发现,原先存留在我们印象中的那一幅幅乡间风俗画,不过都是遥远而虚幻的田园牧歌,或者说,是过惯了都是浮躁生活的城里人对乡间的一种向往。而现实生活中的农村并非如此,或者说,农民眼中的农村并非如此,他们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他们活得很累、很沉重。”赵本山的“真实”之中多的是那种自以为是的想象和虚构。他的火爆流行反映了大众文化中回避现实、自我调适的一种精神,却并不指向我们心灵的追问。诚如王蒙的话说,“不论是从灵魂工程角度,还是从优秀作品鼓舞人角度,还是从文艺需要鲁迅式的大师或是现代社会需要有机知识分子的福柯角度,谁都难以认同赵本山——刘老根式的文艺。以精英、骨干、领导的观点,这些演出都属于低俗之属,不用举例”。如果我们把流行与时尚作为“革命”,那么我们将天天处于“革命”之中。这倒是很能满足某些人自命老子第一、惟我盛世繁荣的心态。这种阿Q的想法不愧深得“农民”文化的真传!
三
在大众的经验里,一向是以实力(权力、势力、武力、人力……)为准;而在知识的传统中,历史才是最好的老师。一切知识都是以历史为前提,并且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演变,纯粹的理性批判和浪漫的感性想象都只能成为一种参考。关于农民的言说也不例外。尽管我们身处一个有着几千年农业生产传统而且形成了深厚的农耕文化的民族,尽管我们也许出身于农民家庭甚至依然经历着农民的生活,只是经历不代表理解,我们所认识的农民往往还是某种实力、某种角度规定下的农民。“真实”的农民只存在于不断探寻的过程之中。对于特定时代的人群来说,尤其需要走出种种时代话语的遮蔽。
我们的文艺作品也正在滋生新的况味。如韩少功的小说《马桥词典》,以词语为线索,侦探马桥村人的生命故事,描述他们如何为语言的牢笼所幽闭,如何承受普通话的整饬,如何通过方言来涌动冲破禁闭的本能。作品述说了语言对于命运的规约以及事实的再造,反映了人们在社会适应中无意识的顽强的自我保存。这里对农民的观照已然趋向独到的思考,与低下的政治地位、落后的文化意识、进步或落后的意识形态、光明与黑暗的道德品质,形成了一定的差异。农民其实可以不是群体而是个人,是一个个有着不同“语言密码”即不同生命经历与感受的个人。又如贾樟柯的电影《小武》,寥寥几个镜头刻画小武的农民父母,实在有惊鸿一瞥之感。相形之下,西方作品经常在人物活动中投入哲理沉思,而不纠结于职业等现实事务,往往能够形成恢弘深广的认识。即使是巴尔扎克那部为恩格斯称赞的写作了十六年的未竟小说《农民》,所刻画的竟是一群按照生存本能而行动的农民,他们的贪婪成性、无耻至极,想尽了阴谋诡计对付有产者,也许将会毁灭文明。在农民的身上挖掘人性的卑劣,虽然也是一种立足于阶级地位的道德品质观照,可是比起国内的作品又何其彻底!只要我们往远处往别处多看几眼,倒也不难看到别样的农民及其故事。对于大众来说,仅仅满足于通俗文艺,满足于强势传媒实在是太片面了!
从远古的全民事农到后来官与民、城与农的分化,农民的身份、形象与故事林林总总,因时代而变,因地域而变,殊不知也因个人而变,换句话说,农民并不是一个自足的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中它具有不同的意义。若把“农民”这个能指当作“原著”,作为所指的无数文艺作品就是“译文”,是作家运用自己的表达方式与风格(或曰站在特定立场、角度)的翻译。这些作品既作为文化产品为人们所消费,又作为文化模子(范式)塑造人们的思维。我们可以尊重这些模子或范式,但是不能仅仅拘泥、附和它们。哲学有言:任何东西的确定性并不是这个东西本身,它总是超出被确定的状况。所以说,农民是什么人,也就是我们自己是什么人,最“真实”的答案是寻找新的观察角度,建构新的文化范式,我们应该创造自己的故事。真正的文化革命孕育在具有解蔽意义的作品当中。
(作者单位:广东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