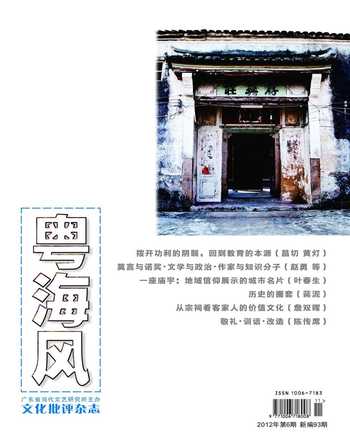拨开功利的阴翳,回到教育的本源
2012-04-29昌切、黄灯
昌切、黄灯
一、“去行政化”只是一个伪命题
改革的核心不就是把政教分开吗?政教分立,办不到。办不到的事,你提它作甚!所以,教育部门的“去行政化”,如果不与政治体制改革联动,是不可能的。
黄灯(以下简称黄):昌切老师,历年的“两会”,教育都是一个热门话题,例如,高校“去行政化”的呼声就很高,但对此的分歧也很大,赞成的人多,其中熊丙奇的呼声就很响,但也有一些忧虑的声音,认为去行政化很难,人大校长纪保成和中山大学前校长黄达人可为代表。您对此有何看法?
昌切(以下简称昌):实际上,“去行政化”应该叫“去集权化”,行政化是集权化的表现形式。教育部的规划草案里没有这样提,或者说提得比较模糊。教育是社会的一个特殊部门,由于集权,教育的一些特性被忽略甚至被抹去,形成了用行政管理方式来管理教育的模式。教育管理部门成了政府的机构,完全按行政的一套运作。
黄: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如果不触及政治体制改革,“去行政化”几乎没有可能?
昌:是的。行政肯定是要的,世界上没有一所大学没有行政。“去行政化”的意思,我想是尊重教育规律,去掉无视和抹去教育特性的那些管理方式。
黄:那您说的教育规律具体指什么?
昌:这个涉及面太大。首先要看高等教育是干什么的,在社会中处于什么位置。我把高校看成人类知识的集散地。人类知识在高校集成、集中并传播、发散出去。人类社会越来越复杂,人类知识越来越丰富,高等教育也就越来越专精。
黄:也就是专业化越来越明显,专业设置越来越细。
昌:越来越专门化。既然大学是人类知识的集散地,那么它必然会以传承知识和创造知识为己任。要完成这两个方面的任务,一个必备的前提是:自由!在中国,就不同的学科而言,情况是不一样的。理工科没有问题,但人文和社科领域的问题非常大。你看得到的,中国建国后的知识生产,是由政府部门主导的。上面下达政策,下面按照它的政策去落实。就拿我熟悉的中国现代文学这个学科来说吧。1950年政务院教育部搞了一个高校文法两院的课程草案,规定高校要讲授现代文学。现代文学被确认为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学,内容是新文学、白话文学,而不包括文言文学和用白话写的俗文学,如鸳蝴派的作品。随后王瑶、丁易、蔡仪和刘绶松的讲稿接连问世,于是有了中国现代文学这门学科。最初还有些摇摆的地方,经批判和调整,可指责的东西少了。到了唐弢本,就定型了。80年代以来不知出了多少现代文学史,大都是从一个模子里敲出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不过是中共党史的一个分支。现在的知识生产也是如此,只是采取了课题规划和学科评估的变通方式。这两个东西都是行政按国家的意志在搞。
黄:上世纪80年代采用课题的方式像现在一样吗?
昌:也有,没有这么多,覆盖面没有这么大,也没有这么热。
黄:我们还是回到集权那个问题。
昌:集权可分为纵向集权和横向集权。一个权力中心,自上而下,一竿子插到底,这是纵向集权。把社会各部门的权力统统集中到一个权力部门,这是横向集权。50年代的院系调整,便是横向集权的好例。你看我们国家教育的性质,与文艺是不是一样的?有区别吗?我看没有。以前都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现在都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是集权的必然结果。这种情况下的“去行政化”实际上分权。办得到吗?不可能。教育部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相对独立的权力机构,它必须服从权力中心的指令,它的基本任务是在教育领域传达和贯彻权力中心的旨意。
黄:因此,也可以说,教育行政化是与生俱来的,这个问题并不是今天才存在,只是由于在当下处境下,行政体制改革的要求越来越强烈,教育行政化的弊端才凸显出来。
昌:比较一下很有意思。国外的大学,像德国的大学,基本上都是公立的,教职员工的薪水来自各个州府。虽为公立大学,但办学基本上独立的,州府干预不了。常见的是它出钱,你骂娘,政府是掏钱买骂。大学的行政摊子很小,如歌德大学,也就是法兰克福大学,一个校长,两个副校长,真正管事的是总务长,底下只有人事、学生等几个具体办事的部门,工作人员少得惊人。院系和研究机构的行政摊子更小,像系主任,就一个,换得勤,由教授轮流做庄。这个大学设有一个立法机构即议会,议会里面有四个专业委员会,大概由九十多人构成,其中人数最多的是教授,其次是学生,第三是教辅人员、助理研究人员,第四才是行政干部和辅助人员。议会的职责是决策和监管。行政部门按议会的决策行事,受议会制约。
黄:显而易见,歌德大学的行政管理是从下往上的,是完全服务型的,整个运作完全以服务为中心,但我们的大学,好像完全倒过来了,指令不是来自教育的主体——教师和学生,而是来自上一级的教育部门,行政成为执行上面命令的力量,根本不会顾忌到教师和学生的感受。
昌:对。学校主要是教授和学生的学校,教授和学生是学校当仁不让的主体。行政部门只有执行权,而且受议会监督,预算多少,经费怎么走,都不是它能决定的,搞行政纯粹是服务。再看看我们这里,行政部门之多、之大,都到了什么地步?不是有“处长一走廊,科长一操场的”说法吗?有个重点大学,一个百把人的学院,居然有一正八副九个院级干部,如果加上党的系统和相当于院级的干部,那是个什么数字?关键在于政教一体,行政是最大的学术资源,谁拥有行政权力,谁就能获取相应的学术资源。你的行政级别越高,意味着你越容易成为大学者,事实就是这样。
黄:在我们的行政化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很微妙的问题,就是党政关系的问题。企业里面,可以很明确提出厂长负责制,但大学里面,提的始终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一个大学,到底是校长为主导,还是书记为主导,在表述的时候,始终很含糊,很多时候,这两者的力量对比,完全取决于个人状况。比如说,有些书记强势一点,可能很多决策就由书记说了算,有些校长强势一点,可能校长的地位就会高些。这种状况带来的一个直接问题,就是导致了两套行政机构。
昌:党也有一套机构。还有群团组织。党团机构的工作与行政机构有些是重叠的。这源于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确立的“党指挥枪”的原则。党领导一切,这个是不能动的。所有成绩都归功于党。“去行政化”是个有限的宛转的提法,只能是一个伪命题。一直在说教育改革,却一直没有大的动静。变化不大,完全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反而是行政的权力越改越大。改革的核心不就是把政教分开吗?政教分立,办不到。办不到的事,你提它作甚!所以,教育部门的“去行政化”,如果不与政治体制改革联动,是不可能的。
黄:“行政化”的根源确实和政治体制密切相关,“去行政化”的真正实现也有赖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但在我们当下的教育中,所有问题的出现,也总是被情绪化简单地归结到教育体制改革的滞后。我所关心的是,在行政体制改革还不能立即实行的情况下,我们的教育是否可以在局部进行一些调整,或者进行一些突破,甚至是大胆的尝试,是否可以更多的回归到教育的本质。
二、回到教育的本源
把学生培养成为一个成功的人?还是把学生培养成为一个独立、具有创造性、人格完善健康、具有基本的社会公德的人?现在的教育在这方面好像没有任何犹疑,都是很明确地选择了第一个方面。
昌:教育的要义是很清楚的。它要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这是对教育的基本要求。社会需要交通、航海、采矿方面的人才,那我们就培养这些方面的人才。社会的需求很多,所以大学里面的专业设置也就与之相应。
黄:从社会需求的层面而言,教育确实如此,所以很多高校都将就业率的高低一个学校的办学水平联系起来,很多高校甚至直接用就业率来决定一个专的前途,是办还是不办,是让它发展,还是让它萎缩。除了社会的需求外,教育本身还涉及到人自身的培养,涉及到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和人格培养。
昌:这是我想谈论的第二个方面。教育还有一些虚玄的东西,人文素养的东西,不干实用的东西,人本身的提高的问题,目前在这方面遇到的问题最大。
黄:把学生培养成为一个成功的人?还是把学生培养成为一个独立、具有创造性、人格完善健康、具有基本的社会公德的人?现在的教育在这方面好像没有任何犹疑,都是很明确地选择了第一个方面。什么是成功的人呢?诸如考试成绩好啊,能够找到一个好工作呀,能够出人头地啊,与此相关的,诸如竞争啊,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啊,升学率啊,就业率啊,高考独木桥啊,都是成功的标准已经深入人心的体现。我们中国父母的心态就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我昨天和一个师兄聊天,他女儿在一个省属重点小学读书,很多高干子弟集中的地方。学生们私下攀比的就是谁家官大,谁家更有钱。这个学期她本来可以评到三好学生,但最后没有评上,家长都替她难过,她反过来安慰父母,说是没关系的,无所谓,他爸的官大,三好学生给别人是很正常的,几岁的小孩就认定了这个,心理没有受挫感了。当然,也从小在活生生的现实中,接受了一套“潜规则”的价值规范。这些潜移默化的东西比什么灌输都有效得多,一旦认定,就是深入骨髓的。
昌:是的,是这样的。社会流行的东西已经渗透到学校里头去了。这是一种教育,这本身就是一种教育。从小学、初中、高中、甚至大学,无不如此。功利性的原则已经渗透到方方面面。大学里盛行功利原则,它的衡量标准,对学生的评价就会出问题,比如要求学生怎样怎样,就不断宣传,谁谁进了美国的什么名校,谁谁进了什么大公司,谁谁当了什么大官,谁谁进了外交部,谁谁做了某要人的翻译。
黄:我们的教育好像缺乏一种共识,尽管表面上说什么四有新人。但现实是,对人的评价,基本上就是看你是否成功,一个人有没有价值,就看他是否成功,而不会从别的层面来评价,所有媒体广告也无不如此,成功人士的形象和物质需求结合到一起,共同塑造了一种价值追求。
昌:这是单质化。一个孩子从小到大,家长、亲友、老师和同学,还有舆论宣传,告诉你的都是功利化的东西。只有一条道,你别无选择。学生求学,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学习成绩好不好。城里的孩子学习成绩不好,老师和家长就会说,“你看你,你将来就配扫大街。”扫大街是低贱的,这种坏观念就是这样来的。这种教育不是杀人吗?这是人性的丧失。
黄:其实教育和被教育本身是令人愉快和充满快乐的一个过程。一个蒙昧无知的个体通过教育,获得了基本的素养和生存本领,这和小动物在大自然的环境中获得个体的成长,没有本质的差别。一个农村的孩子可能从小会觉得家乡很美,会觉得在农村生活一辈子其实也挺幸福的,但通过教育,他对自己的身份可能会带上一种耻辱感,尤其是走到外面以后,这种来自身份上的耻辱感会更加强烈,他慢慢知道,当一个农民其实不是一件光荣的事,劳动也不是一件光荣的事,种田更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换言之,我们的教育一开始就被一种“目的性”特别强的东西所控制,所以“被教育者”一开始就有一种“被教育”的感觉,而这种感觉给他带来的是被迫感,是屈辱感,是表里不一样的分裂感,从个体的角度而言,他对这种教育是抵制的,是不情愿的。教育者也越来越难以感受到教育的乐趣,在一种功利化的环境下,教育本身所具有的创造性的乐趣也越来越少。教育的目的不是让一些孩子成功,而应该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够获得充分的发展,都能够凸显个体的价值。
昌:人的潜能是多方面的,好的教育是开发人的多方面潜能。但现在基本上只开发读死书这一种潜能。谁知道这种教育扼杀了多少天才。一个人可能在某一方面很有才能,但没被开发出来。这是教育的失败。教育有相关的两面,不管是哪个教育学家,他谈教育都不可能离开这两面。一面是人,一面是社会,两面都要求教育多元化。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读书的。如果一个人不适合读书,不会考试,即便他在其他方面有非常大的潜能,他也可能被学校闷死。这是功利化教育最失败的地方。
黄:我昨天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触目惊心的新闻,现在很多中小学的老师要求家长带孩子去医院做智商测试,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孩子的学习成绩不好。如果医院测出的结果低于70,学生的成绩可以不计入班级的平均成绩。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好的教育将弱智教育成正常人,但我们的教育却已经走上了将正常孩子逼成弱智的境地。我们的教育已经无知、短视、功利、冷漠到了如此程度!
昌:事实上,我们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也知道学生发展的多种可能性,所以在应试教育中也提素质教育。不过提归提,提也是白提,应考才是硬道理,所以素质教育到现在并没有一个好结果。功利化的标准非常实在,大都是实用性的,符合王国维所说的中国人现世的和乐感的品格。现在大学生选专业,一般都是实用性的,人文学科一直很冷。我们这里的历史系十多年前就很难招到第一志愿的考生。文学也好不到哪里去。我参加了好几次校园开放日活动,家长和考生经常问的问题是多少分才能进文学院。回答很简单:只要达到武大的录取分数线。
黄:这也使我想到目前的“国考”,公务员考试。一些热门的部门是几千个人竞争一个职位,这种现象像一面镜子,最能照出社会的本相和我们教育迷失到了什么程度。一方面说明行政的力量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和实际的利益挂钩,另外一方面,我们的教育也已经彻底将一种实用的东西,根植到了学生的内心深处,使学生能自然地判断,什么是对自己未来的生存最有用的。我总认为,这种疯狂的背后其实恰恰隐藏某种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他们需要找到一种可以真正依靠的东西,但现在,作为弱势群体的大学生,显然已经没有任何可以依赖的东西,他们的大学生身份在大学并轨以后,已经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恒定的东西。当然,表面上看,学生的选择更自由了,但学生的焦虑感也更强了,尤其是农村来的孩子,这种天生的焦虑意识会多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公务员考试能够获得成功,他们的这种拼搏显然是能够给他们带来保障的。“国考”的盛况,其兴盛的真正原因也许和这个有关吧。但不管怎么说,整个大学,整个教育界,无论教育机构,教育者,还是被教育者,弥漫着一种和人的发自内心的探索世界的冲动无关的实用实利原则,这种无孔不入的功利化的原则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的骨髓中。
昌:这种商业的实用原则,正好跟大学的信条是违背的。公认的现代大学之父是德国的洪堡大学,也就是柏林大学。洪堡大学的办学理念被归结为“洪堡五原则”,其中学术自由、学术非功利化和学术无权威的信条尤其值得我们重视。有一所大学很特别,它就是有名的巴黎高师。它每年从全球招一千多本科毕业生。它是不授学位的。它这样做是要告诉你,来这里是求知、求真理的,不是来谋取什么的,要拿文凭请到别的学校去,它要满足的是你好奇和求知的本能。尊重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这正是从洪堡那里来的。我看过一个电视片,记者问巴黎高师的一个副校长:萨特为什么不去领诺贝尔奖?校长的回答很轻松:这是我们的传统。搞学问不是为了获奖。再举个学术无权威的例子。数学的最高奖是菲尔兹奖,相当于诺贝尔奖。法国的获奖者大都出自巴黎高师。它还出过总统和一些非常有名的思想家、作家,如司汤达等等。可是这所学校没有任何伟人的挂像和塑像。按理说,这些伟人不是学校的荣誉吗?巴黎高师的解释是:他们不能成为学生的榜样。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探求真理,必须超越权威。当年蔡元培入主北京大学,他搞的兼容并包就是从洪堡那里来的。所以陈独秀可以和辜鸿铭搅在一起。可是现在,我们的大学已经丧失这种最重要的原则了,行政主导,评价已经坏了,评价系统可以说一塌糊涂。
三、功利的评价导致底线的丧失
至于评价,也就是所谓级别,什么权威、核心之类,也是集权的产物。一个衙门化,一个商业化,两结合便把大学变成了官方市场。没有底线了。
黄:从这个层面来看,行政主导才是导致功利化办学的关键。但作为知识分子最为集中的一个群体,这种几乎全军覆没的状况背后是否颇能说明一些什么问题呢?上次西安交大造假案,弄得沸沸扬扬,其实现在学界关于造假的新闻早就不是新闻了。而且我还注意到,现在造假的已经不是一些默默无闻的年轻人,一些手头掌握了很多资源的、职位很高的人,也敢公开造假,这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群体现象,造假已经和诚信没有任何关系,也和一个知识分子、或者说一个学者的学术良知和学术坚守没有任何关系了。尽管很多人会从人性弱点的层面来为这些造假的人辩护,但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知,他们良知的丧失是否意味着我们的社会早已经跨出了最后的底线呢?或者说,我们的社会已经没有任何底线呢?那些敢于反抗的、那些残存学术良知的人,那些敢于在现有的体制下说出真相的人,现在真的越来越少,其处境也越来越艰难了。
昌:那些敢于说出真相的人,大都是体制外的,不是退休了,就是身居国外。方舟子在美国,揭露浙大造假案的那个人在荷兰,要是在中国早被按在水里憋死了。西安交大的造假案是由几个退休教授捅出来的。肇事者表面看是那个长江学者,实际上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西安交大,因为他的荣誉也就是学校的荣誉,所以他的事情也就是学校的事情,把他推上去也就是把学校推上去。为了息事宁人,出面的不是西安交大的学术委员会吗?它代表组织。教育部搞了百来个人文社科基地,经常要组织检查,什么硬件软件啦,烦琐得很。要达到要求还真难。不过不要紧,总会有人帮你做的。谁?学校。缺什么补什么,要什么有什么,一应俱全,再盖上大红章子,不容你不信。你不是你,你代表学校,你获得或失去什么,关系到学校的声价。行政的指标多如牛毛,而且还在增加,什么多少基地、一级学科点,几个院士、学科评议组成员之类,搞学科建设就成了争这争那。好多学校报院士,一给就是好几十万上百万的公关费。行政啦行政,多少罪恶假汝而行。
黄:在这种情况下,教师没有任何尊严感。他的日常工作受到各级行政力量的监督,一个教务处可以管一个教授在课堂的表现,可以像管理一个小学教师一样地检查他的教案,可以在班上安插信息员,其实就是相当于特务里面的卧底,目的就是为了监督老师的上课情况,这种管理上面的俯视姿态,已经毫不顾忌到一个教师的尊严。更为关键的是,一个教师的价值,很多时候是处于一种行政的评比中的,他必须评职称,不评职称,可能最后饭碗都保不住,但只要走向评职称这条路,实际上,他就不得不接受种种的评价标准,诸如论文的数量呀,论文发表的级别呀,是否出版专著呀,是否获得课题呀,而这些论文、课题、获奖总是和级别联系在一起的。什么权威、核心、国家级、省级、厅级之类的。从来没有任何一条标准说,就看你成果本身的价值怎么样。这些条件像一张无形的网,将一些鲜活的生命,一些本来很有学术抱负,本来很有学术潜力的人网住,在这部网中挣扎几年以后,可能也就慢慢习惯了网中的生活了,可能也就喜欢在网中的生活了,不知不觉中,就被异化掉了,有没有尊严感对一个教师而言,他们可能自己也不在乎了。所以每次看到武大的半山庐,每次从中大陈寅恪故居前经过,我就感到恍如隔世。一种真正的精神的光芒的消失不是从某个地方消失了,而是消失在某种具体的制度下面。不是我们当下的人比不上前人的智慧,而是我们当下的人难以呼吸到那种自由的空气了。当我们大学教授的地位已经比不上一个行政的科长的时候,当我们的大学教授不得不看别人脸色行事的时候,当我们的大学教授敢于拿自己的信誉打赌,去从事学术造假的时候,当我们的大学教授已经不可能从内心感到一种崇高的荣誉感,他们的身份只和某些具体的利益相关的时候,我们的教育已经走向怎样的歧途,每一个人心里都知道。
昌:是的,高校的老师一点权力也没有。每年的教学奖,大都被领导拿走了。一天到晚在那教书,带那么多学生,一点用也没有,因为你如果不去活动,和教学本身有关的奖最后都会被弄行政的拿走。有所重点大学,去年获得国家教学奖的,主持人都是学校的高官。行政资源真是太重要了,有没有是大不一样的。谁管你什么真知不真知,快乐不快乐。
黄:在这种情况下,虚假之风必然兴盛。很多造假者心安理得,就算查出来,也不怕,也不觉得羞辱。造假的不是我一个,造假的也不是我一个学校!很多国家重点大学,很多211大学都这样,我怕什么?
昌:前两年的教学评估,闹了不少笑话,评估大员们得了不少实惠。吃得进去就吐不出来。有什么可怕的?我代表的是组织嘛。你作为一位大学教师,你敢揭发谁呢?你知道的再多也不会说的。不信你试试,看是个什么结果。较真是很痛苦的,较真的不是傻子就是呆子。有些人习惯了,玩起假的东西来如鱼得水。
黄:与此密切相关的就是,与评价体系相对应,现在很多杂志,尤其是人文杂志,已经变得差不多了。
昌:变成了卖场。
黄:就是直接拿来卖,不看文章质量,只要有版面费,直接可以发表。
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发了文章可以晋升得利,帮你发文章的可以撑起腰包。杂志社来钱靠版面,跟大学的文凭一个样。大学只有一个东西值钱,那就是文凭。想想看,拿文凭做买卖,个人做得到吗?需要一个行政的联动机制。想要文凭的人很多,但不是那么容易,但对于官员和老总来说,实在是太简单了。主要还是行政的问题,交换是外在的表现形式。至于评价,也就是所谓级别,什么权威、核心之类,也是集权的产物。一个衙门化,一个商业化,两结合便把大学变成了官方市场。没有底线了。
黄:没有底线了,什么都能做!
昌:是的,你看那个交换,都是什么人在做?有些学校,每年挤出一些正式的招生指标去做交易。相对来说,研究生以上的好做,名大利也大,做起来方便。另立标准,别择“权才”。标准是双重的,甚至是多重的,因人而异。
黄:现在很多学校都以培养官僚为荣,一到校庆,就说从我们这里出去的部级干部多少、厅级干部多少,没有说培养多少一流的科学家、学者、培养多少作家、思想家之类的。
昌:建国前,仅人文领域,就出了好多大师,后来有谁?大家彼此彼此,都差不多。这也是钱学森提出的问题。失去特性的教育只能产生无个性的学人,想要顶尖的人,做梦去吧。就此而言,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可谓“功不可没”。政教合一,苏化了。
黄:上世纪末的那股高校合并风,可以说是登峰造极的表现。表面上看是整合资源,优化办学,实际上还是行政的力量在干预,还是那些当权的在进行利益博弈。
昌:苏化之外,后来又袭得美国的一些皮毛,如五年一晋职等,实质并无变化。美国晋职有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个内容。学校初评,通过后把被评者的代表作送两位同行专家匿名评审。两位都肯定,通过;都否定,pass;一位肯定,一位否定,送第三位专家,他肯定则通过,否定则pass。我们是这样吗?不是。做不到的。我们也试过匿名评审,但很快就变味了,有的论文还没到同行专家手里,电话就打过去了。中国是人情国度,不足为奇。最后还是得靠由行政部门主导的由一大堆各类专家组成的职称评审委员会来评,还是得依靠一套死板的评审标准。
黄:伴随而来的是大量的学术垃圾,是成果原创性的严重匮乏。科研成果很多时候仅仅成为获得一些利益的条件。没有了敬畏,没有了创造的激情和乐趣。
昌:以前我常说评职称是最简单的事情,搞一帮小学生,认得字,会做算术,就行了,要专家干什么!专家是没有用的,只是豪华的摆设,用鲁迅的话说,是“做戏的虚无党”。再回到杂志审稿上来。国际知名的刊物,像英国的《自然》、美国的《科学》,像《分子细胞学》之类,人家的审稿专家是全球一流的,稿子经匿名评审发表出来,一般是可信的。我们这里的人文社科杂志没这套程序,有决定权的是编辑。编辑的能力和喜好,编辑的交际圈,决定了杂志的质量和品位。这个搞法不对,等于把学术评价的权力交给了编辑。
黄:我们现在发表文章,几乎不管专家不专家,大部分看关系。一些重点大学的博导啊、教授啊,最好是什么学部委员,他们手头拥有大量的公共资源,他们可以拿这些资源去交换。诸如,发表文章、捞取课题、安排学生就业等等。实际上已经存在明显的团伙化倾向。在这种情况下,杂志的发表机制和作者的投稿行为已经构成了一种可怕的恶性循环。什么都可以交换,什么都能够交换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现在的很多学术会议,打着会议的牌子,实际上就是提供了一种交换的场所。当然也不排除一些真正的知识分子,但整个的学术风气已经非常坏了。
四、坚守自由和宁静的内心
做学问不是出自兴趣,出于好奇,你会快乐吗?我们实在是太势利了,内心充满功利。
昌:刚才讲过,大学是人类知识的集散地,主要有两个功能,一个是传承知识,一个是创造知识。一个国家的知识水平取决于它最好的大学。我们国家的知识水平不高,北大、清华有责任,但主责不在两校,而在教育的被集权。创办一流大学,照现在这个样子搞下去,没戏。教育作为一个整体没有特性,教师作为个体没有个性,同质化,一个模子,怎么弄出大师来?前不久讲中国现代学术史,讲到鲁迅、王国维,就觉得被郭沫若称为“双璧”的《中国小说史略》和《宋元戏曲考》是不可复制的。而我们现在的文学史,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的,都基本是一个面相。问学生看教材记不记得住作者,回答是记不住。作者不重要,教材上印不印有他或他们的名字无关紧要。署了名等于没署,我把这叫匿名写作。这样的教材是集权制的产物,是根据行政化的知识生产规则生产出来的,雷同化,同质化,既无个性也无创造性。在这样的体制下做这样的学问,我越来越觉得毫无生趣。我认识一位德国学者,他搞中国研究,纯粹出于兴趣和好奇。他原是学地球物理的,偶然接触到一本介绍禅宗的小册子,感到神秘,就有探究的兴趣,于是改学汉学。我们还有好奇心吗?太生疏了。做学问不是出自兴趣,出于好奇,你会快乐吗?我们实在是太势利了,内心充满功利。
黄:我们受到的干扰太多了!不管是内心还是外在。一个教授,在教书做学问之余,可能一天到晚还要填无数的表格,生活的完整性就被这些无趣的表格破坏掉了,这只是一些表象,更为重要的是,内心的完整性、内心对某种价值的确认也被破坏掉了。整天处在一种毫无理由的评价体系中,天长日久,这些形式化的东西会改变一些非形式的东西。慢慢的,习以为常了,能接受了。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很多人不满意这种生活,但少有人公开地背叛这种生活,可怕的惰性和惯性,有时真的已经像一个泥潭一样将我们困住。
昌:这个跟中国知识人的传统有关。古代的知识人是士子,西文译成officer-scholar,是很确切的。经学是官学,不是私学。这是我们的传统,知识只是进阶的依据。
黄:也就是“学而优则仕”。
昌:对!它就是你谋生的一个手段。亦官亦学,官学一体。
黄:这样看,教育体制改革的难度和我们的传统的价值观念的桎梏有关。
昌:肯定跟文化有关。中国古代的家族制本身就是集权制。传统的东西不容易消失。因袭的负担太重了。换汤不换药,有些表面的东西迷惑了我们。官本位的根源在集权制。它不是重智的,智是依附性的。古代未仕的落魄文人,如蒲松龄、吴敬梓等,只配搞点小说。
黄:像屈原,屈原还是觉得自己失败。他的这种挫败感来自于没有实现的政治抱负。他的那么多作品,其悲悯的情怀到现在都令我们动容,他内心高洁、也高傲,他没有从一个文化人的角度来认识自己的价值。屈原这么一个冰清玉洁的人,最后都挣不过复杂肮脏的现实,最后还是只能以死明志,是否也恰恰证明了中国知识分子无法逃脱的“人事”的宿命呢?
昌:在中国高校,“人事”太重要了。我们提创办一流大学,不突破集权制下的人事网络,必将是一句空话。创办一流大学,不是做不到的。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历史并不悠久,很快就成了一流大学。歌德大学复校后不久就产生了至今名满全球的法兰克福学派。香港科技大学,90年代初创校,现在亚洲已名列前茅。道理似乎并不复杂:一个是投资,创造一个好的硬环境;一个是体制,创造一个好的软环境,好的软硬环境可以吸引全球一流的学者来投,所谓筑巢引凤是也。全球聘人,如今国内的机制办得到吗?形式上办得到,实质上办不到。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引进了不少海外人才,但还没有形成一个一流的学科。原因恐怕在于限制太多,软硬环境不理想,来了很快就会被闷死。像英超的曼联和切尔西,西甲的巴萨和皇马,软硬环境都不错,拿大钱全球聘一流和超一流的球员,就能保持一流水平。可是你做不到。这不是说说就能办到的。自生产是生产不出一个一流大学来的。流动是必须的。我非常喜欢孩子般的好奇,对这个世界,孩子总是充满求知渴望。屈原《天问》里的问题就是孩子的问题,老子的也是,什么混沌、阴阳啦,都是孩子的问题。孩子的问题原是世界原初的问题。现在世界上的问题再多、再复杂,都可以追溯到其起点。起点永远是简单的。
黄:回到原初的问题,就是要恢复我们内心的宁静,要恢复内心的自由。我记得陈平原说过这样的话,一个好的学者,他需要的不是金钱,也不是权力,而是时间。他的意思是,对一个真正有创造力的人而言,给他创造的时间和空间,就是给他生命。说到底,我们当下的教育体制对教育最大的伤害,就是不但使教育者丧失了创造的乐趣和自由,也使被教育者失去了生命的激情和活力。
(作者单位:昌切,武汉大学黄灯,广东金融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