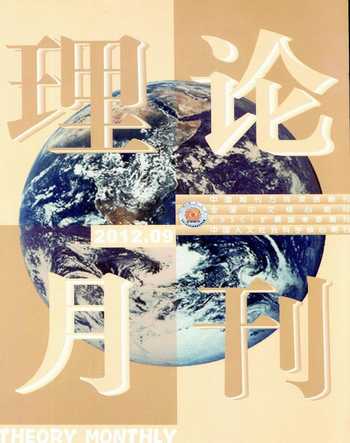从自然宗教到公民宗教
2012-04-29李育书
李育书
摘要:卢梭同时提出了自然宗教和公民宗教,自然宗教主张信仰自由且具有内在性,公民宗教主张信仰应由政权决定且具有政治性,上述表面矛盾的思想实际上有着内在一致性。其一致性在于:卢梭站在启蒙的立场上。确认了信仰自由的原则,也意识到启蒙以来的政治与信仰两方面的危机,公民宗教就是上述危机的解决方案。通过公民宗教,卢梭既建立了对现代政治认同感与政治合法性,也构造了现代社会中世俗化的信仰体系。
关键词:自然宗教;公民宗教;公意;世俗化;启蒙
中图分类号:B565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9-0068-05
一、自然宗教
卢梭宗教思想的首要部分就是自然宗教(naturalreligion)。自然宗教思想在《爱弥儿》第四卷的“信仰自白——一个萨瓦省牧师述”里面得到了系统表述。“信仰自白”是萨瓦省副主教对爱弥儿关于信仰问题的一场告白。“总的说来,《信仰自白》具有一种理智结构的高度单纯性和明晰性”,借“信仰自白”卢梭系统地阐述了自然宗教主张。
1.自然宗教的主张
卢梭主张自然宗教,认为信仰是内心的信仰,它是人们发自内心的、出于情感对上帝的尊崇,它不依靠教会组织,也不依靠一直以来教会所阐释的教条、奇迹、礼拜、原罪等各种教义,“真正的宗教的义务是不受人类制度影响的,真正的心就是神灵真正的殿堂,不管你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教派,都要以爱上帝胜于爱一切和爱邻己作为法律总纲。任何宗教都不能免除道德的天职,只有道德的天职才是真正的要旨。在这些天职中,为首的一个是内心的崇拜,没有信念就没有真正的美德”,因而自然宗教也是普世性的宗教。
在自然宗教思想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卢梭的“三个信条”。他的前两个信条论述的是“上帝存在”。首先,“我相信,有一个意志在使宇宙运动,使自然具有生命”,是为信条一。由此,“如果运动着地物质给我表明存在着一种意志,那么按一定法则而运动的物质就表明存在着一种智慧”,是为信条二。正是凭借这两个信条,卢梭确信了他的“上帝”,“这个有思想和能力的存在,这个能自行活动地存在,这个推动宇宙和安排万物的存在,不管它是谁,我都称它为‘上帝”。卢梭的信条三讨论的是自由问题,“人在他的行动中是自由的,而且在自由行动中受到一种无形实体的刺激,这是我的第三个信条”。
卢梭的三个信条明确表明的立场是:信仰上帝,人是自由的。在这三个信条中并没有讨论上帝如何创造、上帝的质、世界的本原和目的这些传统的神学话题,“由于我深知我能力不足,所以除非对上帝和我的关系有所感受使我不能不推论上帝性质的时候,我是决不论述它的性质的”。卢梭论述了三个信条而不论述具体教义的原因在于:我只需通过信条来确信上帝,做一个有信仰的人,而不是一个无神论者,这是基本的要求。当然,这样论述还有更深的原因,那就是:自然宗教需要淘空教条的羁绊,以此为公民宗教(civd religion)的教义保留空间,订立教义教条不是自然宗教的任务,而是公民宗教的任务。
2.自然宗教的自由内涵
卡西尔曾经指出“卢梭的宗教,首先旨在成为一种自由的宗教,正是从这一点上,它引出了自己的特点和根本性质”,在卢梭这里,自然宗教的自由内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主理性;二是道德良心。
在自主理性方面,卢梭一再主张信仰是内在的,其自然宗教作为自由之宗教首先是摆脱外在束缚的自由。人们通常把新教看作自由的宗教,并这样来总结新教中的自由的,“启蒙运动和新教的原则是个体主义自由的原则,这些原则包括:不受国家控制的宗教自由;不受教会控制的良心自由,每个人在良心上自我决定自我负责,直接对上帝负责;不受圣洁、传统、教会权威影响的信仰自由;从下面建立的‘信徒聚合的权利”,与此类似,卢梭也要求宗教信仰摆脱政权、教会、圣经、传统权威等控制约束,只靠内心信仰。
如果说,卢梭主张内在信仰不过是在重复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的话,和近代宗教改革差别尚不明显,那么卢梭对“良心”的重视就开始凸显他与宗教改革者们的差距。卡西勒评价说,“无论是加尔文宗还是路德宗都不曾在根本上克服潜在的缺陷:它们用信仰《圣经》取代了信仰传统,从而只不过是转换了这一学说的中心而已。但对卢梭而言,自我体验最深沉的,实际上也是唯一的形式,乃是良心的体验。”在卢梭看来,人类已经有了道德自由,这就要求人类去承担起他们所应承担的道德的责任。对此,卢梭指出,上帝已经给了我们良心去爱善,给了我们理智去认识善,给了我们自由去选择善,我们已经具有了行善的条件而没有行善,那么“我做坏事只能说我愿意做坏事,如果要他改变我的意志,这无异于要求他去做他要求我做的事情,要求他代我干活”。卢梭对自然宗教自由属性的论述,基本是站在启蒙的立场上,承接了宗教改革的成果,首先要求是摆脱教会权威的束缚,把宗教信仰变成内在的信仰,在内在信仰的基础上,要求一种道德意义上的自由,这种道德自由既确立了人在道德上崇高地位,同时也为下文公民宗教预备好了道德内容。
卢梭的自然宗教核心主张其实就是两点:要信上帝,要单凭自己的良心自主地信仰上帝。这就置卢梭于两面作战的境地,他既受到了教会的迫害,又要批判唯物主义无神论。这一点从他的信仰历程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卢梭一生的信仰历程非常曲折,他出生在日内瓦共和国,生来就是一个加尔文教徒,但后来受华伦夫人的影响皈依了天主教,再后来重皈加尔文教。他因《爱弥儿》而被教会当局斥责为没有信仰,被到处驱逐,著作遭公开焚毁;同时,他又因坚持宗教信仰与启蒙领袖伏尔泰成为终身死敌,与早年好友“百科全书派”代表狄德罗反目为仇,认为他们都是没有信仰的无神论者。卢梭一直坚称自己是信仰上帝的,认为自己是世上最虔诚的人,“世上再没有人比我相信福音书了”。
二、公民宗教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的最后部分《论公民宗教》中提出了公民宗教思想,初看之下,卢梭的公民宗教思想似乎与自然宗教思想大相径庭。然而,《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是同时发表于1762年的,要说卢梭在这两本书里观点迥异显然不能令人信服,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公民宗教呢?我们还是先来了解公民宗教的主要内容。
1.概述三种宗教
卢梭在《论公民宗教》中首先叙述了历史上世俗国家权力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并且据此把宗教区分为三种:人类的宗教(Religion of the Man),公民的宗教(Religion of the Citizen)与牧师的宗教(Religion of the Priest)。
人类的宗教,也就是“一般的或普遍的宗教,系与各国家各民族特殊的或具体的宗教相对而言的”,它没有庙宇、祭坛、仪式,只有内心对上帝的崇拜以及对道德的永恒义务,它是纯粹而又朴素的福音书宗教,是普世的宗教。公民的宗教是一个国家的典章规定的,规定了国家的神,有法定的教条、教义和礼拜的宗教,公民的宗教是排外的,它认为除了自己的宗教之外的宗教全是野蛮和不敬神的。第三种宗教即“牧师的宗教”则“给人以两套立法,两个首领。两个祖国,使人们屈从于两种相互矛盾的义务,并且不许他们有可能同时既是信徒又是公民”,在卢梭看来,喇嘛教、日本人的宗教和罗马基督教都是这样的。其宗教权威与世俗政治是对立的。
卢梭认为这三种宗教都有缺点。其中“第三种宗教的坏处是如此之显著,如果还想要加以证明的话,那简直是浪费时间”,因为这种宗教完全破坏了社会统一,使人们没有服从的对象,使人们陷入自相矛盾的制度。对于“公民的宗教”,卢梭认为,它能够把对神的崇拜和对法律的热爱结合起来,祖国成为神,效忠国家即是效忠神灵,这种神权政体能保证公民对国家的忠诚热爱。这是其优点,但它也有一个根本的缺点,那就是它是建立在谎言和谬误之上的,它使得民众的虔诚变得迷信盲从,实际上是取消了人内心的真实信仰,而且当它变坏时又会变成了排他且专制的宗教。卢梭认为“人类的宗教”是真正的、建立在福音书之上的基督教,在这种宗教中,“作为同一个上帝的儿女的人类也就认识到大家都是弟兄,而且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那个社会是至死也不会解体的,”但这里的“那个社会”不是尘世的社会,而是基督徒的“天国”,因而不会解体。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既然把基督徒结合在一起的“那个社会”不在尘世而在天国,那么,这种宗教与政治就不再有任何特殊联系,宗教也就不能对国家发生作用。这种宗教非但不能使公民依附于国家,反而使公民脱离了国家,在那里“支撑国家的东西都不存在了,国家就衰弱了。”
卢梭是“从政治上来考察这三种宗教的”,在这三种宗教里,卢梭评价最低的是“牧师的宗教”,而牧师的宗教正是当时西方社会的普遍状况,它带来了两个头领,造成了人们的普遍混乱。卢梭肯定了“公民的宗教”的积极方面,认为它把信仰统一起来,这是卢梭所要借鉴与吸取的。卢梭对“人类的宗教”之论述其实就是他对“自然宗教”之理解,自然宗教表述了人类普遍的信仰,但是其信仰是软弱无力的,不足以组织一个政治社会,这正是公民宗教所要克服的不足之处。因此,公民宗教正是对这三种宗教进行综合的必然结果。
2.公民宗教的主张
我们知道,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本意是研究人类在文明状态下通往自由之路,信仰自由似乎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宗教可以使他们热爱自己的责任,这件事却是对国家很有重要关系的”,而且宗教还会涉及政治和道德,因此主权者需要建立一种宗教,在这种宗教中,主权者需要规定一篇公民信仰的宣言,这宣言不是严格的宗教教条,它只规定社会中的情感,那些不信仰的人要被驱逐,被驱逐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不信神,而是因为他们的反社会性,因为他们不可能真诚的爱法律,爱正义,也不可能在必要时为尽自己的义务而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样,主权者就为这个国家建立起了公民宗教。
公民宗教的教条并不复杂,内容包括“全能的、睿智的、仁慈的、先知而又圣明的神明之存在,未来的生命。正直者的幸福,对坏人的惩罚,社会契约和法律的神圣,——这些就是正面教条。至于反面的教条,则我把它只限于一条。那就是不宽容。”在正面教条之中,“神明存在”和“未来有生命”是对上帝的确信,相比较而言,正直者的幸福,对坏人的惩罚,社会契约和法律的神圣这些政治性的教条更易得到主权者重视。因为这些世俗标准是由主权者来界定的。至于反面教条的不宽容,其实是对教会的不宽容,同时宽容一切只要不违反公民义务的宗教。
3.“集权”的公民宗教
一直以来,就有学者批评公民宗教的集权属性。大致说来,其“集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主权者决定信仰。信仰自由本来是自由的应有之义,但是因为宗教能够把对上帝的信仰与对国家的热爱统一起来,可以让公民全身心地投入到事业当中去,因此,主权者开始审定教义,决定公民的信仰内容。于是服从公意就是遵从主权者,道德戒律变成了信仰,违背道德要求就是对神的不敬,内在的信仰重新受到了主权者的干涉。第二,世俗化的考察体系。公民宗教的教条基本都是世俗化的标准。福音书意义上的基督教虽可带来善良的生活,但还是被卢梭所否定,因为它是反社会的,它不能让人们在尘世结成一个有机体,反而让人类的社会走向消亡,国家走向解体。卢梭在《爱弥儿》中也曾说过,“凡是爱国者对外国人都是冷酷的……不要相信那些世界主义者了,因为在他们的著作中,他们到遥远的地方探求他们不屑于在他们周围履行的义务”。这样说来,公民宗教的最重要的教条其实就是正直者幸福,坏人受罚,尊重契约和法律,这些教条实际上只是一个世俗社会中的正义原则而已,神明存在、相信来世并不在世俗正义原则之内。
4.自然宗教和公民宗教在卢梭思想体系内的一致性
上文已经提及,《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都是1762年同年出版,仅从出版时间上就可以推论两者不应有太大矛盾。再从两书的形成过程来看。《社会契约论》的观点形成很早,早在1743年就已经形成,之后卢梭担任了驻威尼斯公使的秘书,期间写下了“论政治机构”的论文,该论文阐述了《社会契约论》的主要观点,不单如此,在《日内瓦手稿》中卢梭也有关于公民宗教章节,对公民宗教也有所表达。而自然宗教的观点形成也很早,卢梭在《忏悔录》中称《爱弥儿》是其“二十年的思考,三年的劳动”的结果,文中爱弥儿和副主教的关于信仰的对话,其实可以看作是卢梭对自己信仰历程的回忆,牧师所告诫的“不要因为面包而改变信仰”正是卢梭对自己早年寄居华伦夫人处改信天主教这一经历的自责,在《新埃洛漪丝》中,朱丽死前对于信仰的告白也表述了“信仰自白”的很多内容,一定程度上预告了“信仰自白”内容的问世,可见自然宗教和公民宗教思想都是卢梭深思熟虑的结果,不是仓促之作,都能反映卢梭的真实思想。
很多学者也认为,两书是密切联系的,“通常可以看出,《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是紧密联系的。他的政治著作主题是如何塑造有德性的‘人;在《爱弥儿》中,卢梭的工作是提升一个人使之具有美德”。我们也可进一步发掘这两种观点内涵的一致性。其实公民宗教和自然宗教有着密切的关联。“公民宗教要以自然宗教为基础”,自然宗教对公民宗教的基础作用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自然宗教培养自由的人,有了自由的人,公意才得可能成为正义;另一方面也只有自然宗教这样的信仰才能允许实行公民宗教,允许社会国家至上,因为是自然宗教完成了现代性的“祛魅”,最终的信仰是道德律令而不是神坛,自然宗教也完全得以成为自由的宗教,否则怎能允许国家至上呢?最多也就是“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在这个意义上说,卢梭自称的虔信只是对善、对良心、对道德的虔信。
三、在自然宗教和公民宗教之间的政治与信仰
1.政治建构
依据上文的分析,自然宗教和公民宗教的特征分别在于自由与集权,二者在卢梭的思想内似乎并不矛盾。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这两个目标都是卢梭在政治建构中力求实现的,或者说,他的政治建构是在追求自由和集权的统一。要实现个人自由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重返自然状态,一是新订社会契约。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已断言重返自然状态是不可能的,人们早已忘记了回到自然状态的道路。《社会契约论》的目的也是在文明状态中找到一条通往自由之路。因此,要实现这个自由只能重订社会契约。建立公意国家。公意(general will)是所有人的意志中相重合的善的部分,因而也是主权者的意志,“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在公民宗教中,公民对国家的忠诚、对主权者的服从就是对公意的遵从,因为自由就是“服从人们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法律”,因此,服从公意国家和个人自由并不对立,“他认为建立在社会契约之上的政治体系倒能向它的公民提供一系列不同类型的自由”,公意国家才是自由的实现。自然宗教中的自由在政治社会是不现实的,它只是自由的原则,也可以说只是自由的自然状态,自由必须要在政治生活中得以实现,“一系列的论证都说明,自然状态并不存在值得保护的自由,人们只有名义上的自由却没有责任,这种自由不能带来善却能带来伤害。”公意国家本身是自由的人们订立契约的结果,是人为了摆脱自然状态的不便和文明社会的奴役而在尘世建立的,它的目的就是保障参加者的自由,生活在公意国家不但不会丧失自由,反而得到了有秩序保障的自由,就如黑格尔所评价的,“人是自由的,这当然是人的实质本性;这种本性国家里不但没有被扬弃,事实上倒是开始被建立起来了”,公民宗教正是借助于国家这一貌似集权的形式来实现自由的。
2.世俗化的信仰体系
卢梭在自然宗教中完成了现代性的启蒙,宗教已不再依赖于外在权威,他律变成了自律,上帝变成了内在的良心。这是现代性与启蒙带来的普遍成果,但这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外在宗教变成了内在自由之后,如何克服现代性的主观主义、如何建立有效的信仰就成了卢梭要思考的问题。建立新的信仰体系也就成了卢梭的任务,“公民宗教的建制虽有体制内的作用,但它的本质在于确立公民的信仰。”
自然宗教为公民宗教打下了基础,它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宗教变成了内在信仰,其二,自然宗教只有“信仰上帝”这一形式,其内容需要公民宗教来填补。在卢梭的论述中,自然宗教内容只有上帝存在,更多的内容卢梭不去推论,只去追问自己的良心,这就为公民宗教的内容留下了空间。教会应该过问的戒律、仪式变成了公民宗教中的道德律令。宗教的具体教义由公民宗教来填补,自然宗教的论述为公民宗教的教义留下了巨大的空间,这个空间最终将是世俗的、政治的。
3.通向政治的世俗化信仰
世俗化的信仰必须要有具体的内容支撑,信仰需要靠政治性的内容落实下来。在卢梭那里,政治和信仰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需要通过卢梭的宗教思想来理解他的政治建构,再通过政治建构来理解宗教思想。通过自由和主权者的集权表面的矛盾来理解政治思想,政治的集权又是为了他的公民宗教,公民宗教既是巩固政治又是构建信仰,公民宗教是站在自然宗教基础上、在现代性祛魅的基础上重建当代人的信仰体系。公民宗教对现代人的信仰体系具有重要意义,现代性完成了祛魅和世俗化,再也没有神圣之物,但是人类又离不开信仰,需要在自由平等立场上重建信仰,这就是公民宗教。虽然卢梭一再声称自己的虔诚,但卢梭的上帝只是自己内在的良心,不再是外在的权威。没有了外在的他律,怎样才能树立人们的价值信仰。这是卢梭真正要考虑的问题,也是公民宗教的深刻之处。
卢梭的上帝不再是教堂里受到顶礼膜拜的神,而是建在道德良心之上的,良心才是“里面的上帝”,神学服从于道德和理性,信仰具有了世俗性。同时,《社会契约论》中的政治是这样的,那里没有奴役,人人平等,都服从于至善的公意,公意是不会犯错误的,因而是至善的,政治也就具有了至善性。政治成了信仰的内容,信仰的内容由政治来填补,同时,政治得到了合法性的认证,受到了信仰的庇护,于是乎,这个社会里人们不需要跪在神坛面前颤颤栗栗,却需要在公意面前兢兢业业,政治具有了至善性和神圣性,信仰和政治都指向至善,在这里它们重合了。政治和信仰的重合,可以实现卢梭一直推崇的目标:人们只服从一个首领,把对上帝的爱和对祖国的爱统一起来,既可以培育自由的现代人,也可以培养负责任现代公民,在此,卢梭的世俗化的信仰也就变成了政治化的信仰,或者说,卢梭的世俗化信仰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化的信仰。
四、对公民宗教的重新审视
1.卢梭的个人经历与公民宗教
卢梭的童年生活是在日内瓦度过的,日内瓦是加尔文教的堡垒,当是实行政教合一的体制。卢梭一生颠沛流离,始终以日内瓦公民自居,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卢梭对日内瓦的认同,而日内瓦体制所提供给卢梭的最深刻的启示就在于:仅靠宗教不足以培育良好的公民,自由的宗教之外还需要政治精神。另一方面,卢梭童年熟读普罗塔克的《名人传》,自幼崇拜斯巴达和古罗马的公民精神,这无疑使他兼具了古罗马的公民精神。这些也许是卢梭提出公民宗教的最初灵感来源,但卢梭不是简单照搬日内瓦或者是斯巴达。他的论述可以说是完成了现代性旅程后的回归。
2.神权政治的批评与回应
长期以来,很多学者对卢梭抱有批评态度,其中,卢梭的著名批评者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在《旧制度》中指责卢梭的国家是“在俗之人的隐修院”,这一批评很有影响。甚至成了后来人们批评卢梭的理论来源。很多批评者认为卢梭的学说是在构建一个神权政治,这样的神权政治带来了政治上的集权主义,在思想上摧毁了原来的信仰体系,并且该学说实际上是通过要求人们信仰现实政治的方式来维护与加强政治的集权,在之后的政治实践中也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其实,对卢梭神权政治的批评并非没有道理,卢梭把政治与信仰结合在一起,这种建构在现实生活中或许存在一定程度的极权危险,卢梭自己甚至也意识到这种危险,所以一再强调“公民的宗教”和“公民宗教”之间的区分,一再强调公意永远正确,要克服上述危险的确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前提。但批评者们对卢梭的神权政治分析上其实是有不足之处的,一是对卢梭学说的缺点分析不到位,问题找得不准;二是只谈思想后果忽视思想本身的价值。
首先,卢梭学说容易招致批评,它潜藏着两点危险:一是公意的形成机制,二是政治与信仰的重合。首先是卢梭的“公意”问题。卢梭区分了公意和众意,虽然“卢梭的公意原则倾向于为所有公民介绍理性的内容”,但是公意究竟如何形成的,在卢梭的学说中有着很大的一块空白,公意最后被个别意志随意填补。黑格尔就曾经批评卢梭的公意根本上仍然是个别意志,“是特定形式的单个人意志”。这是卢梭政治学说在实践中带来集权的原因所在。其次是政治与信仰重合问题。对政治的信仰需要以政治的至善为保证。批评者们出于对政治善的怀疑,他们抵制这种把信仰和政治捆绑在一起的做法,批评卢梭的主张是一种神权政治。的确,如果政治恶和信仰绑在一起,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尤其是当信仰被政治滥用之后。因为,政治和信仰相互捆绑在一起后,会互相给对方一个“加速度”,政治和信仰都会不断壮大自身,一旦出现问题也难以从内部改变。事实上,近代以来也出现过政治盗用信仰的现象,人们出于政治化的信仰通常也不会再去怀疑政治,人们既成为专制的牺牲品,同时又在推动这种暴政。遗憾的是,很多批评者们并没能完全厘清卢梭学说容易走向极权的内在机理。
其次,我们不应完全以后果来评价思想,而是应更多看到思想本身的价值。首先,卢梭不满足于政治的工具价值,要为政治本身确立价值,这是他对现代性带来政治价值失落的洞见,也是他提出公民宗教的出发点,要让道德的人同时成为现代公民。他清楚政治与信仰的重叠是有风险的,所以一再强调公意是至善的,是不会犯错的,在这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背后值得我们对他的现代信仰体系做出深入审视。就如日里(Patrick Riley)指出的,“卢梭不仅仅想把公意世俗化——让它不再是理论的;他想赠给人类一个真正有抉择能力的意志。这个意志可以用来反对世俗教育——这个教育也是共和教育,虽然它曾被孟德斯鸠雄辩的描述过,但它在现代社会已经消失了。”恢复业已消失的共和精神和德性,才是卢梭真正的目标。其次,世俗化之后,彼岸世界、精神性的世界已经逐渐远离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目光都集中于此岸的世界,甚至集中于此岸具体的物质,带来的是普遍的物质主义盛行和精神的无信仰。在这种情况下,卢梭的公民宗教,把信仰和政治结合在一起,无疑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信仰对象,而且,这个现实的对象本身得到了善的保证,与普遍的无信仰或物化的信仰相比,信仰此岸善的政治无疑更有意义。
其实,就公民宗教所遭受的批评而论,很多学者都倾向认为公民宗教是促使人们结成政治社会的动力,孙向晨先生在其论文《论卢梭公民宗教的概念及其与自然宗教的张力》指出,单从自然宗教组成政治社会是缺乏动力机制的,公民宗教成了政治社会的“黏合剂”,国外很多学者也持此见,斯特劳斯指出,“唯有公民宗教才能够产生公民所需要的情感”,“除了公民宗教以外,能与早期立法者的活动起到同样作用的就是风俗”。登特(N.J.H.Dem)认为,“卢梭要让每个公民都应得到同等程度的尊重与照顾,要确保这种需求在世俗社会占有最高地位,这就需要世俗的(也是道德的)纽带把大家结合在一个共同体之中”,这一纽带就是公民宗教。这种解释从另一个角度很好的诠释了公民宗教的意义,但遗憾的是,这些意义并没有得到批评者们的重视。
3.公民宗教的现代意义
公民宗教关注的中心问题既是信仰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世俗化以来,信仰失去了外在权威的约束之后变得软弱无力,自由变成了放纵,这就需要世俗标准来约束与坚定信仰。同时,政治缺乏世俗外的推动力,无法确立政治的至善标准,政治的合法性与推动力陷入危机。卢梭站在启蒙立场上表达了自主信仰的内容,同时他通过公意与契约赋予政治以道德性,针对世俗化过程中信仰的内在化、软弱无力,提出了公民宗教,因此可以说自然宗教、公民宗教都是非信仰的时代之信仰表达,公民宗教是在完成自然宗教尚未完成的任务。通过自然宗教和公民宗教这一表面的矛盾来理解卢梭的政治和信仰体系的建构,能更深入理解卢梭思想的现代意义。
对于当代政治来讲,卢梭揭示了如下两点内容:善的政治可以培育公民精神;信仰可以通过世俗化的标准来建立。如果政治没有对善的追求就不能成为信仰的对象,“上帝死了”之后随意塑造一个上帝是不可能成功的。信仰只能建立在世俗化的标准之上。在卢梭的学说中,现代信仰只能是世俗化的信仰,这个世俗化的内容也必须要以善的政治来填补,而政治善又必须以公意为前提。可以说,这一整套学说联系非常紧密,目的也很清楚,就是建立政治合法性和现代信仰体系。但是这个体系很脆弱,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就会让整个学说走向它初衷的反面,“公意”何以是真正的“公”,公民宗教何以体现自然宗教的内在信仰,这都是需要加以深思的。我们并不主张政教合一的体制,但是并不能因此忽视现代政治的宗教与道德基础。而卢梭“政治——宗教——道德”三合一的理论建构把政教合一的模式转变成对政治道德基础的追求,在这一点上他的思想极具现代意义。
对于现代信仰来说,自然宗教是对现代性规则的确认,公民宗教是现代性背景下民众信仰的重建。启蒙以来,思想家们要么是走向彻底的唯物主义路线,信奉无神论;要么认识到应该有个上帝。于是在空中自己创造一个上帝,伏尔泰提出“造一个上帝”,费尔巴哈主张人道主义宗教,但这些主张都是无力的,这种信仰是主观随意、没有内容的。在卢梭看来,这些观点都是唯物主义不信上帝的表现。卢梭要把他们这样的思想落实下来,于是提出了公民宗教。公民宗教在世俗的基础上,有了新的落脚点,那就是政治。公民宗教的信仰教义由主权者根据政治标准进行审定。有了具体的政治内容,和政治结合在了一起。卢梭既建立了信仰体系,又把信仰体系具体落实下来了,把普遍的无信仰转变成对世俗政治生活的肯定,卢梭的这一探索无疑给人们一种新的启发。
责任编辑文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