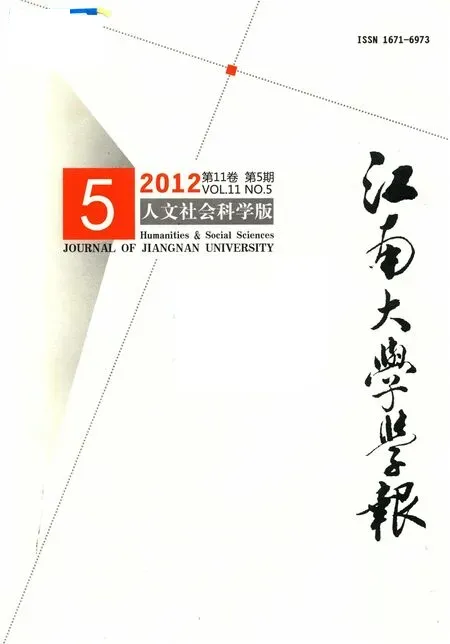论孔子的人-心秩序观
2012-04-18王军
王 军
(南京大学 政治系,江苏 南京210093;江苏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镇江212003)
平王东迁之后,西周初年建立的礼乐制度逐渐崩毁,失序成了当时最大的特征。在孔子看来,失序最根本的原因并不是现实礼乐制度的破坏,而是人们内心对秩序的忘却。于是,为了重现西周的盛况,孔子从整顿人心秩序入手,提出了独具特色的人-心(内心)秩序观。本文拟在阅读《论语》及相关文本的基础上,对孔子的人-心秩序观作一简要梳理。
一、安与乐:理想人-心(内心)秩序的特点
理想人-心(内心)秩序的第一个特点为“安”。何谓安?《说文》云:“安,静也,从女,在宀下。”[1]150《论语》中所说的“安”,主要有两层含义:其一,物质意义上的,比如“居无求安”[2]9,可理解为生活上的安定,这是建构内心秩序的基础;其二,精神层面的,也就是内心感受,《论语.阳货》篇载: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
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
曰:“安!”
“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2]188
在这段关于三年之丧的讨论中,孔子将是否“安”作为礼仪取舍的内在标准。这里的“安”显然是一种内心感受,可理解为内心的安宁。当然,在孔子看来,安于什么,还是评判一个人仁与忍的重要标准,因此,通过“察其所安”[2]16还是避免被蒙蔽的重要途径。
理想人-心(内心)秩序的第二个特点是“乐”。《论语》开篇就说: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2]1
此处的“说(悦)”、“乐”、“不愠”都可以理解为广义的乐,但又不尽相同,首先,强调的重点不同:“说(悦)”强调的是由于内心的觉悟而产生的喜悦和满足之感;“乐”重在表现由于志同道合而产生的快乐,在一定程度上可理解为因被别人认可而产生的成就感,所谓“说在心,乐主发散在外”[3]47是也;“愠”则凸显君子不强求为人所知道的自得。其次,三者的层次不同:“说(悦)”仅停留在“独学”的层面,仍然只是学者自己的事情,或者说只处在内圣阶段;而“乐”则有“求同道”、“相与析”的共鸣,已经逐步向“外王”阶段靠拢,所以程子才会说:“乐由说而后得,非乐不足以语君子。”[3]47当然,最难的还是“不愠”,朱熹云:“及人而乐者顺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难。”[3]47因为,理论的推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甚至是困难重重,如何面对这种情况?这确实需要一番修为,所谓:“学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3]47这也是为学、为道者必须努力达到的境界:你必须有别人不接受你的心理准备,做不做在自己,成不成,只能看天意了,这时,只能达观一点,这种达观,是在认识到真理、发现有同道者、并在推行中遇到困难之后的坦然之乐。
当然,最有名的还是“孔颜乐处”: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70-71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2]59
以上即常为后儒所称道的“孔颜乐处”的出处。显然,此处的乐绝非单纯的物质享受所达到的快感,正如程子所云:(孔子)“非乐疏食饮水也,虽疏食饮水,不能改其乐也。”[3]97又云:“颜子之乐,非乐箪瓢陋巷也,不以贫窭累其心而改其所乐也。”[3]87还说:“箪瓢陋巷非可乐,盖自有其乐尔。”[3]87既然这种乐与物质享受无关,那么必须追问:孔颜之乐,“所乐者何事”[3]97?且看朱熹的解答:“圣人之心,浑然天理,虽处困极,而乐亦无不在焉。其视不义之富贵,如浮云之无有,漠然无所动于其中也。”[3]97这一解释显然带上了极浓厚的理学色彩,未必是孔子的原意;但朱熹的另一处解释则很具启发意义:“程子之言,引而不发,盖欲学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为之说。学者但当从事于博文约礼之诲,以至于欲罢不能而竭其才,则庶乎有以得之矣。”[3]87易言之,这种乐与“博文约礼”之教诲,以及在为学、为道的过程中所带的欲罢不能的状态息息相关,这显然更多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快乐与自足。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孔子所提倡的乐虽然重视精神层面的愉悦,但绝非不要物质层面的享受,而是强调人对物质的追逐要在精神的约束之下进行。这主要体现在孔子对义利关系的论述之中。在孔子对义利关系的论述最有名的就是: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2]39
范宁云:“弃货利而晓仁义则为君子,晓货利而而弃仁义则为小人也。”[4]267朱熹云:“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3]73范宁的解释较平实,朱熹的解释较抽象,但这两种解释,都认为君子重义而小人重利,并且认为重利不如重义,这容易给人造成孔子轻视利乃至不要利的错觉。其实不然,因为此处的义还可以解为宜,《礼记.中庸》云:“义者,宜也。”[3]28宜也就是恰当,也即是说,君子言义,不是不要利,而是求其应得之利。并且,孔子并没有否定利,甚至言利:“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2]69并提倡“因民之利而利之”[2]210的为政方略。孔子反对的是见利忘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71易言之,孔子的基本态度是“见利思义”[2]149、“义然后取”[2]150。
可以这么说,在人-心(内心)秩序问题上,孔子主张用精神主导物欲,用道德理性主导感性欲望,但并不否定人的基本欲望。那么,怎样才能做到人-心(内心)秩序的“安”与“乐”?易言之,应该安什么?乐什么?孔子给出的方案是仁与礼。
二、仁与礼:理想人-心(内心)秩序要遵循的规则
理想的人-心(内心)秩序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在孔子看来,主要有仁与礼两个方面。
首先要依仁。孔子重视仁,其最终的目的就是唤醒内心对礼乐秩序的自觉。反之亦然,要维持内心的良性秩序,必须遵循仁:“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2]36而在现实中,仁又是一种十分难以达到的境界,所以孔子才会感叹:“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2]57孔门高足中,德行第一的颜回也只能三月不违仁,更遑论他人?虽然如此,还是要努力据仁而行。
显而易见,是一个充满艰辛的过程,因此,要实现仁,还需要其他的德性。首先是知:“仁者安仁,知者利仁。”[2]163知与仁的关系颇似认知与道德关系的问题,一般来说,健全的心智与恰当的认知有利于道德水平的提升,因此说“知者利仁”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不能说有了健全的心智和恰当的认知必然会成为有道德的人,知毕竟不等能同于仁,孔子也不认为从知必然能推出仁。然后是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2]35仁的实现,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一旦遇到阻力,是坚持下去还是退却不前,就成了十分重要的问题,也正是因为困难,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2]157的勇者气概就显得十分重要而可贵了;但勇毕竟只是仁的助力,仁可以统摄勇,反之则不行:“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2]146而且,勇必须由义节制,所谓“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2]190此处的义可释为“宜”,即勇要适度、不可过分。总而言之,仁是最根本的,可以统摄包括知与勇在内的诸多德性;若分而言之,知、勇与仁又有所不同,也是实现仁必不可少的条件。
但是,如何依仁或为仁,必须有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关于这个问题,孔子弟子有若的论述尤其值得注意:
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2]2
有子看到,孝悌之人很少犯上作乱,于是断定:“孝悌乃为仁之本”。这就提供了为仁的基本思路:从人最自然的感情——孝悌出发,并将这种感情不断强化与推广,从而逐渐达到仁。这种思路是否可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理解孝悌及其与仁的关系。朱熹注:“人能孝弟,则其心和顺。”[3]48程颐曰:“孝弟,顺德也,故不好犯上,岂复有逆理乱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则其道充大。孝弟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弟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3]48程朱都以顺解孝悌,认为,通过对父母、兄长“顺德”的培养、强化与推广,就可以逐渐实现仁。这种解释是符合儒家一贯的传统的,正如杨树达先生所言:“爱亲,孝也;敬兄,弟也。儒家学说,欲使人本其爱亲敬兄之良知良能而阔达之,由家庭以及其国家,以及全人类,进而至于大同,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也。然博爱人类至于大同之境,乃以爱亲敬兄之良知良能为其始基,故曰孝弟为仁之本。”[6]4但是,孝悌并不就是仁,小程子云:“谓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盖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曷尝有孝弟来。然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3]48
现在的问题是:儒家将孝悌当做为仁之本,而很多时候又特别强调顺,是否强化了国人的顺民意识而不利于培育国民的公民意识?确实如此。汉代以来,封建帝王通常标榜以孝治天下,看中的正是孝悌重视顺的特点。其实,孝悌乃人类建立在血缘关系上、自然而然、割舍不断的情感,将这种情感推广到全人类乃至人与万物之间,显然有利于良性秩序的建立。问题是,任何事物都有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最终孝悌、仁义被后世统治者一并窃之。
其次是守礼。如果说仁重视的是主体的自觉,那么礼则更重外在的约束。内心秩序的形成,固然离不开主体的自觉,但也离不开外在的规则,这对于尚未完全体会到仁之实质的人尤为重要。或者说,仁是唤醒内心对秩序的自觉,而礼则树立了一个外在秩序的典范,这种典范如果内化为主体的德性,也能形成主体内心的秩序,从而处理好人与内心的关系。所以,孔子尤其重视礼:
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2]78
孔子所提倡恭、慎、勇、直,但不能过分而要恰到好处,因此需要礼加以节制。因为,“无礼则无节文”,[3]103恭、慎、勇、直就会变成劳(劳扰不安)、葸(畏怯多惧)、乱(犯上作乱)、绞(急切刺人),[5]200-201这显然不利于内心的安与乐,也就无法实现理想的人-心(内心)秩序。因此,要实现理想的人-心(内心)秩序必须守礼。
如何守礼?易言之,怎样才算守礼?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2]8什么是和?邢昺疏:“和,谓乐也。乐主和同,故谓乐为和。夫礼胜则离,谓所居不和也。故礼贵用和,使不至于离也。”[4]46钱穆的解释与此类似:“礼主敬,若在人群间加以种种分别。实则礼贵和,乃在人群间与以种种调融。”[5]17将“和”理解为人群之间的融洽关系从字面上看固然可以,但却限制了礼的范围,忽略了礼还有调节天-人、人-心关系的作用;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解释与“和事佬”中的何相去不远,容易造成不讲原则的后果。朱喜的解释不同于此:“和者,从容不迫之意。盖礼之为体虽严,而皆出于自然之理,故其为用,必从容而不迫,乃为可贵。”[3]51朱子以从容不迫注和,虽然可以避免前一种解释的缺陷,但仍有未尽之处,而且与古训违背。且看《礼记.中庸》对和的解释:“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3]18杨树达认为:“事之中节者皆谓之和,不独喜怒哀乐之发一事也。《说文》云:‘龢,调也。盉,调味也。乐调谓之龢,味调谓之盉,事之调适者谓之和,其义一也。’和今言适合,言恰当,言恰到好处。”[6]28综上,《中庸》与杨树达先生的解释显然更合适。易言之,守礼关键要恰当,不能“过”亦不能“不及”,更不能“泥”(教条)。“过”与“不及”当然不好,但现实中“泥”,也就是教条的做法危害更大,“泥”的最大坏处就是将礼之精神——仁给闷死了。
因此,守礼要“和”,就必须理解礼的精髓在仁,或者说,守礼与依仁是不可分割的,这也是孔子一贯的主张: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2]123
皇侃疏:“尅,犹约也。复,犹反也。言若能自约俭己身,返反于礼中,则为仁也。”[4]819朱熹注:“仁者,本心之全德。克,胜也。己,谓身之私欲也。复,反也。礼者,天理之节文也。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盖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3]131相较之下,皇疏更直接,而朱注由于加入了更多理学的内容而显得比较牵强。然而,朱注也并非一无是处,他意识到克己复礼,其实牵涉到人-心(内心)秩序问题,而孔子接下来举出“非礼勿视、听、言、动”四目,显然有通过断绝对非礼关联而实现内心平静从而达到理想内心秩序之目的。从这段对话,还可以看出,孔子将“克己复礼”当做“为仁”的基本途径。这可能会引起一个疑问:孔子一方面用仁解释礼,认为仁乃礼之内在精神;另一方面又主张克己复礼乃为仁之途径,那么,仁与礼究竟是什么关系?这关系到孔子对礼的解释。在孔子那里,礼绝不是单纯的仪式或典章制度,而且还根植于人的内心,是仁的外化;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自觉地将本有的仁外化为礼,而且有些人还会忘却礼,迷失仁,因此需要遵循由圣人制定的礼并努力将其内化,在内化的过程中,也必然会唤醒内在的仁,最终达到内外和合。如果将儒家理解为人学,那么仁应该更为根本,因为礼说到底仍是为了实现人的价值。进而,可以这样说,依仁与守礼乃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个由内而外,一个由外而内,最终都是为了实现良性的秩序,做到内圣与外王的统一,都是为了人的发展与完善。
三、学与思:实现理想人-心(内心)秩序的途径
理想的人-心(内心)秩序的特点是依仁守礼之后达到的安与乐。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人心丧乱,欲望横流,人们早已忘却了秩序为何物。那么,如何唤醒人内心对秩序的信念?孔子给出的方案是学与思(内省)。
其一,学。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开私学之教育家,孔子尤其重视学。这除了智力上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学乃关乎政治稳定的行为:“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2]63,64也就是说,由于人心丧乱、欲望横流所造成的越礼行为,可以通过学得到纠正。因此,孔子才会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2]67在德性培育的过程中,学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
“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2]184
仁、知、信、直、勇、刚是孔子提倡的美德,但是,如果离开了“学”而单纯地喜好这些,往往会陷入愚(愚蠢)、荡(放而无归)、贼(伤害)、绞(急切不通情)、乱(犯上作乱)、狂(狂妄抵触人)等弊端。正是因为如此,孔子认为好学乃十分值得称道的优点,但真正称得上好学的人少之又少。据《论语》所载,孔子提到的好学之人一共有三个:其一,孔文子,“敏而好学,不耻下问”[2]47;其二,颜回,“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2]55;其三,孔子,“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2]53怎样才能称之为好学?孔子给出的标准是: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2]9
从这个标准看,学显然不是单纯的求知行为,而更多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行为,这种行为有利于内心的宁静,从而形成良性的人-心(内心)秩序。
其二,思。学不能离开思,孔子所说的思可理解为内省、反思。正如曾子“吾日三省吾身”[2]3中的“省”一样。无论就知识学习还是德性培育来看,思——反思、内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知识的学习过程中,深入的思(反思)可以调动学习者的主动性,从而实现对知识更为深入的理解;而在德性的培养过程中,认真的思(内省),则可以让学习者认识到自身的不足,进而提升学习者的道德水平。当然,孔子所说的思,更多地仍是道德层面的反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2]39不断地思(反思、内省),必然能促进良性人-心(内心)秩序的形成。
最后,学思并进。在孔子看来,学比思重要,所以谓:“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2]168也就是说,思必须以学为基础。离开了学,思有可能陷入空想。特别是在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知识增进更是日新月异。而学的目的就是吸取前人创造的既有成果,试图撇开一切既有成果全凭一己之力进行创造,其结果必然和人类初期的成就相差无几,很难取得什么提高。当然,孔子最基本的主张是学思并进:“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2]18朱熹注:“不求诸心,故昬而无得。不习其事,故危而不安。”[3]57程子云:“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五者,废其一,非学也。”[3]57易言之,只有将学与思结合起来,只有将学与思结合起来,才能做到学思并进,有效地实现“安”且“乐”的人-心(内心)秩序。
[1]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5]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三联书店,2002.
[6]杨树达.论语疏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