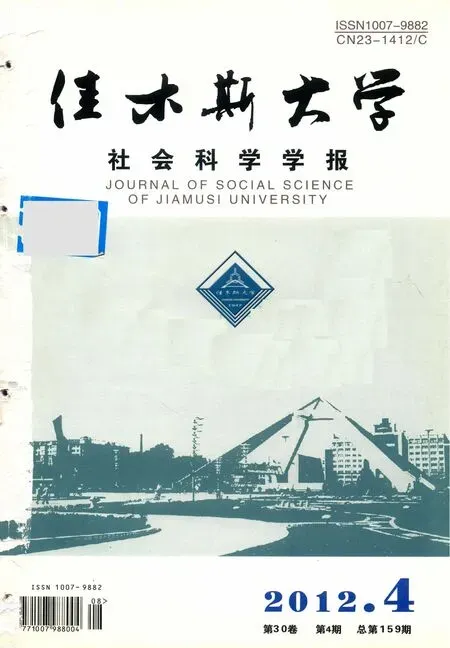女同文学叙事比较
——以霍尔和邱妙津的同性恋代表作为阐释文本①
2012-04-18陈闽璐
陈闽璐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贵阳550001)
女同文学叙事比较
——以霍尔和邱妙津的同性恋代表作为阐释文本①
陈闽璐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贵阳550001)
英国20世纪初的女作家拉德克利夫·霍尔的《孤寂深渊》,是英语文学中的第一部女同性恋小说,被誉为“女同性恋者的圣经”。《鳄鱼手记》是当代台湾著名女同性恋作家邱妙津最成熟的小说之一,突破了之前同题材作品情欲规避的传统,在台湾女同性恋文学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霍尔和邱妙津本身都是同性恋者,这两部都源自于作家本人切身体验的作品,通过不同的母题、叙事风格和叙事策略,展现了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女同性恋者应对男权与异性恋社会的方式的差异性。
女同性恋;《孤寂深渊》;《鳄鱼手记》;母题;叙事风格;叙事策略
拉德克利夫·霍尔(1880-1944),是20世纪早期英国著名的女同性恋作家。她的成名作《孤寂深渊》,是英语文学中的第一部以女同性恋为题材的小说,被誉为“女同性恋者的圣经”。26岁时自杀于法国巴黎并以遗书引发文坛“地震”的台湾女作家邱妙津(1969-1995),同样是一位女同性恋文学的书写者,她最成熟的小说《鳄鱼手记》突破了此前同题材作品对于同性情欲的刻意规避,在台湾乃至整个华语文学世界中都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孤寂深渊》讲述的是一位名叫斯蒂芬·戈登的年轻女子,自幼钟情于女性,长大后逃离了家庭,流亡海外。一战爆发时,斯蒂芬加入了医疗队,成为救护车驾驶员,其间与一位名叫玛丽的女子邂逅相爱,并开始同居。后来为了换取所爱之人的幸福,让玛丽安心去过“正常人”的生活,斯蒂芬选择了自我牺牲,让自己永远陷于孤寂深渊中。邱妙津的《鳄鱼手记》则以女主人公拉子的大学生活为背景,以生活手记的形式,叙述拉子作为一名女同性恋者的隐秘心理和悲情挣扎。对应于书名,在拉子的手记里穿插着以鳄鱼为主角的书写片段。鳄鱼的形象,正是对女同性恋者的影射,它与故事的主人公拉子实际上是一种同构关系。鳄鱼从被发现到最后的自焚,与拉子在同性爱欲中的挣扎与自我毁灭,构成了完全的对应,从而表达出对女同性恋者独自面对隐秘情欲的现实困境的思考。
作为东西方女同性恋文学的代表性作家,邱妙津和霍尔源于她们本人的切身体验的女同性恋的书写,在故事的母题选择、叙事风格和叙事策略等方面,体现了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女同性恋者应对男权与异性恋社会的方式的差异性。本文试图通过具体非文本分析与对比,就这几方面的问题略陈管见。
一、母题对比
放逐,是一种与人类相伴而生、延续至今的社会现象,也是文学的永恒母题之一。“基本上,放逐母题牵系着的是被迫远离乐土,远离一个情感上认同的家,因此它可以转化成失乐园或乌托邦的寻求,人在这些未确定的空间里寻找归宿感”[1],同性恋作为异性恋的性爱“他者”,始终以被放逐边缘人的身份存在。而“放逐母题”同时在霍尔和邱妙津的同性恋小说中悲情呈现。同性恋的放逐形式,一般分为外在放逐和内在放逐两种。外在放逐表现为同性恋者被家/国驱逐出门,对现实环境逃避。统观《孤寂深渊》和《鳄鱼笔记》,便会发现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没有固定的家园,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交往的也都是“圈中之人”。《鳄鱼手记》中的大学生拉子,喜欢把自己幽禁在租住的小屋中过自我封闭的生活,不喜与人来往,爱好逃课;《孤寂深渊》中斯蒂芬被母亲驱逐出从小成长的莫顿庄园,以外出学习之名移居他乡。不管“逃课”还是“移居”,都是主人公外在放逐的表现形式。
相对外部世界的放逐来说,内在的自我放逐,是指同性恋者把主流社会对他们的污蔑、排斥内化为自我意识,使自己陷于认可同性恋身份与排斥同性情欲的矛盾之中,并因此而自我谴责、自我否定。本质上,这是外在放逐的深化和变异。不论是霍尔笔下的斯蒂芬还是邱妙津笔下的拉子,她们对自身身份的认同都经历了一个恐惧的阶段,在《孤寂深渊》中,有这样的描写:
恐惧,真正的恐惧,因为这种恐惧感到羞愧……那一夜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她讨厌自己那副身材,宽宽的肩膀,扁小的乳房,全身的线条直得象个运动员。她注定要拖着这个身子过一辈子,就象一副恶毒的镣铐锁住了她的灵魂。这个充满激情却毫无生命力的身子……她一直想摧残它,因为她早已为此感到痛心……她双眼含着泪,对自己的仇恨变成了怜悯。她开始为自己的身子而伤感,手指怜惜地抚摸着乳房……[2]
在《鳄鱼手记》中,拉子也对自身产生过恐惧:
一直到此刻我仍然不真的明了那种恐惧感,它到底来自哪里?却受着奇怪性欲的压迫与恐吓度过青春期和大学时代的一半。我安慰自己,我是无辜的,恐惧感是自生在我体内,我并没有有伸出手搬它进来,或参与塑造自己的工程,帮助形成这个恐惧感蔓生的我。但我的生命就是这样,成长的血肉是搅拌着恐惧的混凝土,从对根本自己和性欲的恐惧,恐惧搅缠恐惧……变成整个活下去的恐惧怪兽,自觉必须穴居,以免在人前现出原形。[3]
相对而言,内化于心的流放感,更甚于外在的流放形式。内在的自我流放是最彻底的放逐,它使同性恋者们成为异性恋社会的被逐共犯。它是潜藏于同性恋者心中,反复折磨他们的心魔,也是酿造同性恋悲剧的罪魁祸首。
二、叙事风格对比
虽然被放逐是两部小说主人公共同的命运,但两位作者在叙事上却呈现出不同的风格。邱妙津采取的是一种类似喃喃自语的内心独白的叙事文体,对灵与肉、内在与外在等进行形而上思辨与反省,重在描写情和欲的诸般面貌,面对传统规范和主流文化,呈现的是消极旁观、防卫自辩的态度。霍尔则是以笔为武器,进行了激烈的反击和控诉。两者虽都为悲情写作,前者呈现的是消极的基调,而后者却是积极的。
邱妙津成长于正统文化氛围中,她的作品发表于台湾解严初期。当时的台湾社会对同性恋文化的认同是模糊不清的,持保守意识的大众文化视其为异端和败类,具有先锋意识的社会精英表现出宽容和理解,同性恋文化在正统道德观念与异端文化的夹缝里无声喘息。在这样的情况下,邱妙津对同性恋文化的认知,本身也充满了困惑、矛盾、忧郁和痛苦。她的“书中刻画了沉痛而且惨烈的女同性恋关系,突显了女同性恋之间的爱欲情狂及挫败失意”。[4]在对拉子错综复杂的情欲书写里,邱妙津透露出的是悲观、绝望、控诉、猜疑、自恋、自弃甚至自毁挫败的色彩,将情欲创伤表露无遗。拉子的思想充塞着自我认同与自暴自弃的冲突,一方面对异性恋的优势地位有清楚的认知,屈从于它;另一方面则是自身已经内化于思想外现于行为的男性认同的不想放弃。
从前,我相信每个男人一生中在深处都会有一个关于女人的“原型”,他最爱的就是那个象他“原型”的女人。虽然我是个女人,但我深处的“原型”也是关于女人。我是一个会爱女人的女人。[3]
尽管拉子明确宣称自己只爱女人,然而,她仅仅认同了自己同性恋的身份,却对自己的身体欲念始终怀有一种深刻的原罪意识。她不断对抗着自己的欲望,也抵制水伶对她的身体引诱,但逐渐显现的情欲,却一步一步逼使拉子直面自己的先天命运。然而,她又对女同性恋者的身份始终深怀一份自卑怯弱的曲折抗拒心理。于是,她显现出一种焦虑和渴望交缠的复杂情感。
世界怎么能这么残忍,一个人还那么小,却必须体会到莫名其妙的感觉“你早已被世界抛弃”,强迫把“你活着就是罪恶”的判刑塞给他。我根本不知道我到底是谁,隐约有个模糊的我像水印在前面等我,可是我不要向前走,我不要成为我自己。[3]
一方面,拉子理性清醒地认知着异性恋的优势地位,并屈从于它。内化的社会歧视和对自身性向的绝望,从拉子对待水伶的方式上有着鲜明的表现。她冷落投奔向她的水伶,借此来转移内心无处发泄的同性爱欲。拉子的绝情,使水伶的同性情欲找不到出口,在折磨与压抑下走向癫狂,开始自虐和虐人。拉子和水伶就像深陷于异性恋牢笼的困兽,她们在互相戕害中走向各自人生的悲剧。另一方面,拉子已经内化于思维外现于行为的男性认同,导致了她对男性权力的模仿和对自我身份建设的混乱、困惑。这在拉子与水伶关系中的主导态度和对待吞吞、至柔时所表现出的宽厚、容忍、大度等兄长气质中都能体现。她规划和安排着水伶的生活,当她意识到只有异性恋的正常生活方式才是可接受和应当接受的时候,就罔顾水伶的感情需要将她推回正常社会;但在知道水伶的新恋情的对象也是个女性时,她又无法接受自己败给另一个的“她”,于是转而以强烈的进攻势头争取与水伶重修旧好。如此挣扎、痛苦甚至觉得羞耻的感知,一直深深盘踞在拉子女同性恋者身份认同的整个过程中,凄怆地证明了传统“性别”规定的顽固以及残暴。
邱妙津试图杀出一条“血路”,可是性别认同符号与世俗爱情合理架构的枷锁根深蒂固,当时的前路那样黯然,只要踏进这个漩涡,似乎从此任何选择都终将归于土崩瓦解的苦痛,谁也没能逃脱伤裂的命运。小说中所展现的她的近乎自虐的告白,以及强烈的爱欲、霸道的占有,令人惊悚,读后让人有悲寒直逼心底之感,我们看到了一个同性恋者“始终难解的心理纠结与自成回路的思想缠绕如何一步步结成没有出路的硬茧。”[5]她终究没有穿越创伤,在1995年用一把水果刀刺入心脏,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如同她在小说中写的:
这样的世界分分秒秒在破碎,爱在破碎,希望在破碎,信念在破碎,像站在火山口,我所爱的人一个个掉进火山里,身上每个细胞仿佛都在起火燃烧,痛苦的意识把一秒钟延成无望,“毁灭的时刻到了”的声音在踢打伙我的脑袋。[3]
相比邱妙津带有自我毁灭意味的创伤叙事而言,霍尔的《孤寂深渊》却有着强烈的捍卫和抗争的色彩。她在给出版商的信中写道:“我是带着强烈的使命感来写这本书的……令我感到骄傲的是,我能够提起笔为那些毫无还手之力的人仗言——她们从呱呱落地的时刻起,某种阴秘的自然造势就把她们与社会分离开,但她们却极其需要社会的帮助。”在她看来,“这既不是一种厄运,也不是被有意纵情享受的一种变态,它是在特定处境下被选择的一种态度,就是说,它既是被激发的,又是自由采纳的”。[6]她化悲情为力量,反抗主流社会对同性恋者的放逐,在《孤寂深渊》中,霍尔为同性爱情作了道义上和医学上的辩护,使人们看到,同性恋者虽然不幸,但仍能够成为有所作为的公民。
霍尔认为同性恋者既没有违反自然,也没有发疯,和其他任何人一样,完完全全是人们称作正常人中的一份子,只是还没有找到在社会中合适的位置,但是她坚信这样一天一定会来的。她用她的笔鼓舞所有的同性恋群体不要退缩害怕,而是要平静、勇敢地面对自身,鼓起勇气,光明磊落向全世界证明,同性恋者能够和人类中其他人一样,达到同样的无私和优秀。霍尔借小说中主人公斯蒂芬的口还谈到同性恋情公开的问题:
有些人耻于公开自己的情况,只求平静生活而消踪匿影。这是背叛了自己和他们的同类。其实世界对于性倒错者往往智力优秀这种情况承认得越早,那它的禁锢就会取消得越快,而且这种迫害也就会停止得越快。
霍尔认为同性的爱也可以至死不渝,甚至更久远。在她看来,世人称赞那些所谓的正常人,容忍他们的不忠、谎言和欺骗,却对同性恋挑剔、苛责,这是残忍而不公平的。于是她大声疾呼:
起来保卫我们吧!承认我们啊,上帝,在全世界面前,也把生存的权利给我们!
霍尔在这部小说中所注入的远远超出“同性恋小说”所能涵盖的内容,不仅很多同性恋者觉得它照亮了自己的灵魂,对于非同性恋的更广大的读者,也有同样的启示和激励。它所宣扬的是如何振作精神,奋斗不息;如何永葆崇高情操,避免沉沦自毁。整个作品所挥洒的心灵之美和气质之雅,不仅使读者深受感染,也给人以健康向上的熏陶。这部小说一出版,心中怀有难言之隐已久的女同性者以及他们的父母亲友,就如饥似渴地暗中批览,从中寻求慰藉、启示和勇气,也有不少长期隐忍的性倒错读者,是在读过这部书之后,挺身而出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开始过起这类人的正常生活。
三、叙事手法对比
在《鳄鱼手记》里,邱妙津数次将主人公物化为一头鳄鱼,隐喻纠结矛盾的同性恋的欲望形态。鳄鱼某种程度上象征着同性恋者在异性恋霸权社会中孤绝、受抑的尴尬困苦存在处境,邱妙津以符号表征的方法强化了拉子内化的恐惧和焦虑。鳄鱼是作为拉子的互涉性形象塑造的,二者共同喻示着同性恋文化的一体两面。从鳄鱼被发现、关注,到被报道、诱捕和迫害,以及最后的自焚,体现了同性恋文化公开亮相后所遭遇的社会舆论的文化围剿。作者出于自身已内化的异性恋思维,将女同性恋者的形象鬼魅化、妖魔化;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她对异性恋体制的指责才更为激烈、尖锐、愤怒、痛苦乃至绝望。在作品中她的言行走到了异性恋社会理解的极限,她以鳄鱼分身所作的怪胎展演,以社会为假想观众,娇媚万分地上演女同性恋的自恋、自在、友善大度,挑逗读者的想象;同时,以幽默、诙谐、夸张的调侃和戏谑的方式,讽刺异性恋主义与“恐同”心理,挑战既有的性与性别观念,批判男权异性恋的霸道。但是,这场讽刺喜剧却犹如含泪的笑,在嘲讽之余,也深刻呈现了异性恋霸权无所不在的监控与压迫,这种监控与压迫将女同性恋丑化、污名化,其间的辛酸与悲凉更胜拉子的浓烈悲情。第一人称拉子的告白写作模式是“个人”经验的叙说与再现,加强了可信度与真实感,而以寓言体”形式出现的鳄鱼,则诉诸群体,以诙谐讽喻的口吻批判社会各种光怪陆离的现象。邱秒津大胆让这看似矛盾的两种文体呈现在手记之中,巧妙地开启了另类的书写空间。
霍尔是一位很有修养的严肃小说作家,她以雅洁优美的文字构建她的作品。在《孤寂深渊》中,她的文笔真切自然,细腻浪漫,不同于邱妙津,凡是情欲方面的着笔都很含蓄。在小说里,除了故事中的人物以及故事情节,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语言的魅力,自然之美在其笔下倾斜而出,山坡上金色的光芒;杜鹃的初次啼叫,忽然出现的一片空无一物、宽广无边的黑暗和虚无;忽然出现一种无可名状的恐惧的感觉等等。在作者笔下都得到了自然的流露,她通过触觉、味觉和嗅觉,将自然风光真切地描绘了出来,她拥有一个非同寻常的女子的特殊才能,运笔凌厉、视角高远,将拟人、比喻、象征以及排比,骈语,警句等修辞手段运用自如,毫不牵强,她站在自己同类人的立场,身负为她们代言,为她们请命的重担,这又使得她的作品,富有一种高雄劲健、清丽脱俗的格调,毫无糜腐粗劣之态。又因她高瞻远瞩,以其自身经历深深明白此类人的命运一时难以更改,从而深怀孤愤,使她的这部作品通篇溢有苍凉悲壮之气。
李银河在《同性恋亚文化》一书中指出:“同性恋现象是在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行为模式,古今中外,概莫能外。”[5]女同性恋文学发展至今,已经作为女性主义文学的一个分支而被文学与学术界所认可与接受。它带给人们的,是对传统性别身份的僭越和新的主体可能性的思考。通过对邱妙津《鳄鱼手记》和霍尔《孤寂深渊》这两部作品的在母题选择、叙事风格及叙事策略上的对比,我们能够更为深入地了解女同性恋者的心灵世界和生存状态,也可以发现,以艺术的方式来反映女同性恋者内在心理与外部环境的种种问题的女同性恋文学,正在形成一个独立的叙事声音和叙事立场。
[1]简政珍.放逐诗学——台湾放逐文学初探[J].世纪华文文学论坛,1991,(2).
[2]拉德克利夫·霍尔.孤寂深渊[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
[3]邱妙津.鳄鱼手记[M].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1997.
[4]刘亮雅.世纪末台湾小说里的性别跨界与颓废:以李昂、朱天文、邱妙津、成英姝为例[J].中外文学,1999,(11).
[5]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
[6]朱伟诚.另类经典:台湾同志文学(小说)史论[A].台湾同志小说选[C].台北:二鱼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5.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esbian’s Literature——According to Radcliffe’sThe Well of Lonelinessand Qiu Miaojin’sCrocodile Note
CHEN Min-lu
(Literature Department,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Guiyang 550001,China)
Radcliffe was the famous British female poet and novelist,she wrote the bookThe Well of Loneliness,was the first English literature of lesbian fiction,which is known as lesbian’s bible.Qiu Miaojin,who is the famous female writer in Taiwan,wrote the book calledCrocodile Note.It is a wonderful works which has a theme about lesbians;it breaks through the evasion of traditional in Taiwan and has the exploring significance in lesbian’s literature history.These two works both are created by the writers who suffered huge mental stimulation and mental traumaThey charged and criticized the society through the different narrative strategy
lesbian;The Well of Loneliness;Crocodile Note;the motif;narrative strategy;narrative style
I106.4
A
1007-9882(2012)04-0084-03
2012-05-25
陈闽璐(1988-),女,福建福州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责任编辑:黄儒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