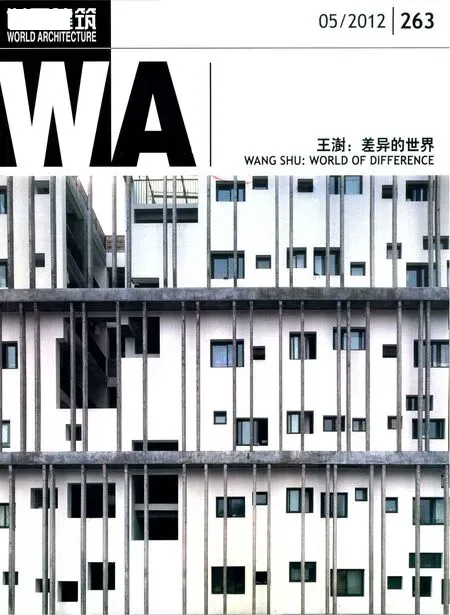我们需要一种重新进入自然的哲学
2012-04-14王澍WANGShu
王澍/WANG Shu
把中国建筑的文化传统想像成和西方建筑文化传统完全不同的东西肯定是一种误解,在我看来,它们之间只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但这种差别却可能是决定性的。尽管用“西方”、“中国”这样的概念进行比较有把问题简单化的危险,但在最基本的哲学问题上,确实有一些重要的不同。在西方,建筑一直享有面对自然的独立地位,但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建筑在山水自然中只是一种不可忽略的次要之物,换句话说,在中国文化里,自然曾经远比建筑重要,建筑更像是一种人造的自然物,人们不断地向自然学习,使人的生活回复到某种非常接近自然的状态,一直是中国的人文理想,我称之为“自然之道”。这就决定了中国建筑在每一处自然地形中总是喜爱选择一种谦卑的姿态,整个建造体系关心的不是人间社会固定的永恒,而是追随自然的演变。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中国建筑一向自觉地选择自然材料,建造方式力图尽可能少地破坏自然。而在我特别喜爱的中国园林的建造中,这种思想发展到一种和自然之物心灵唱和的更复杂、更精致的哲学状态。园林不仅是对自然的模仿,更是人们以建筑的方式,通过对自然法则的学习,经过内心智性和诗意的转化,主动与自然积极对话的半人工半自然之物,在中国的园林里,城市、建筑、自然和诗歌、绘画形成了一种不可分隔、难以分类并密集混合的综合状态。而在西方建筑文化传统里,自然和建筑总以简明的方式区别开来,自然让人喜爱,但也总是意味着危险。费恩(Sverre Fehn)在接受一次访谈时也谈到:挪威人喜爱自然的方式是直接而简单的,在挪威的文化中,不存在面对自然的一种哲学(Made in Norway)。
我认为,今天这个世界,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需要在世界观上进行批判和反省,否则,如果仅以现实为依据,我们对未来建筑学的发展只能抱悲观的看法。我相信,建筑学需要回复到一种自然演变的状态,我们已经经历了太多革命和突变了。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它们的建筑传统都曾经是生态的,而当今,超越意识形态,东西方之间最具普遍性的问题就是生态性的存在问题,建筑学需要重新向传统学习,不仅学习建筑的观念与建造,更要学习和提倡一种建立在以地方文化差异性认同为根基的生态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的价值在中国被贬抑了一个世纪之久,而中国的快速发展付出了过大的资源与环境代价。在我的视野中,未来的建筑学将以新的方式重新使城市、建筑、自然和诗歌、艺术形成一种不可分隔、难以分类并密集混合的综合状态,所有那些以全球商业化价值为归依的过大的城市和过大的建筑终将瓦解。
我相信,一种将超越城市与乡村区别、打通建筑与景观、强调建造与自然关系的建筑活动必将给建筑学带来一种触及其根源的变化。可持续与经济相结合的考虑将为建筑学从传统景观意识到现代感觉的变化注入新的观念和方法。在我已经完成的杭州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园,800 亩土地,16 万m2,30 栋建筑,就以非常实验性的方式体现了我的观念:就地取材,旧料回收,循环建造。建筑就是景观,景观不仅体现在对自然地理的适应、调整,敏感对话,甚至将真实的自然也变为生活场所建造的一种元素,根据对“自然之道”的理解,保留了原有的农村地貌、耕地和鱼塘,微调自然地理特征。事实上,对中国大城市日益单调和混乱的现状,很难不抱有绝望的情绪,它们都在以以全球商业化价值为归依迅速地同质化,而象山校园,不仅是一座大学校园,也不仅是以一种回应中国传统“书院”的教育建筑尝试,它是包含着一种新的城市模式的实验企图的,从建筑类型、群体密度、建筑尺度、材料回收、建造方式和体系到田园混合的位置格局与美学意趣,它是关于一种以地方文化差异性认同为根基的生态的存在方式进行整体呈现的努力,是我用从乡村调查中体会到的“自然之道”去反向影响城市的努力,也暗含着我一直以来的主张:今天的中国城市发展需要重新向乡村学习。
本质上,现代建筑都是工程师式的建筑,从一种幻想出发,设定想要的材料,设定一种工作方式,即使这种材料远在千里之外也在所不惜。或者为了降低能耗,进行更复杂的材料与工艺制造。我更喜爱工匠的态度,尽管并不排斥材料研究与工艺试验,但工匠总是首先看看有什么现存物可以利用,什么建造方式对自然破坏最少。好的建筑应该建造简单,易于维护,并应根据地方的实际经济、技术、造价、建造体系和建造速度采用合适的技术。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出发点,现代建筑师总是认为,建筑创作的好坏取决于方案的哲学思考,很少去想的是,工作方式和职业体系有着更基本的哲学决定性,更重要的是,在这个高速建造的特殊时代,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数量,意味着建筑师的工作几乎是粗暴地影响着广大民众的生活,这就要求建筑师必须对自身的职业有独立的批判态度,建筑师要有清楚的世界观和德行。
2003 年,我们在鄞州中心区明州公园里设计了“五散房”,用400m2的一座画廊建筑第一次把旧料回收、循环建造的做法实现,这种做法实际上也来自宁波民间。同样重要的是,业余建筑工作室的基本工作方式,从田野调查入手,和一组地方工匠长期配合,由小型建造实验开始,逐渐形成大型建筑的设计与施工工法,被清晰地建立起来。
更重要的是,这个小实验影响了人们的观念,在一味追求巨型新建筑建造的浪潮中,让人们重新体会到小建筑和旧的现存物的价值,人们重新开始热爱能产生地方价值认同的事物。同时,这也是我们的基本工作方式,小建筑实验是为了更大规模的推广。这种设计观念已经不是西方现代建筑的那种以个人美学追求为最高标准的作品观,而是另一种建筑观念。
回收旧料,“循环建造”,并不是我的发明,而是正在被遗忘的中国建筑一直以来的伟大传统。如果说“五散房”是遵循上述原则的小型实验,在3 万m2的宁波历史博物馆上,回收这一地区正在拆除的旧建筑上的废料,进行大规模的循环建造实验,就是对这种价值观的彻底贯彻。而这些旧建筑材料如果不回收,并被创造性地再运用,就不能体现它特殊的价值和尊严。这类工作能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在几年前都是不可想像的。实际上,宁波历史博物馆上使用的“瓦爿墙”技术,已经是对传统建造用现代技术改造的结果,宁波传统建筑上从来没有高达24m 的“瓦爿墙”,新的做法经过反复实验,发展出一种间隔3m 的明暗混凝土托梁体系,保证了砌筑的安全。内衬钢筋混凝土墙和使用新型轻质材料的空腔,使建筑在达到特殊的地域文化意味的同时,获得更佳的节能效果。
使用大量回收材料,除了节约资源,在新建造体系下接续了“循环建造”的传统,也是因为这类砖、瓦、陶片都是自然材料,是会呼吸的,是“活的”,容易和草木自然结合,产生一种和谐沉静的气氛。与之相应,我理想中的建筑总是包含大量建筑内的外部腔体,建筑内是有“气”存在的。
宁波博物馆采用了简洁的长方形集中式平面布置,就现代博物馆功能需要而言,这是最高效的组织形式,同时,这使平面落地面积最小,使施工建造法对自然的破坏最小。景观设计以这一地区低矮丘陵地貌为特征,以重返自然为意趣,避免过度设计。在宁波这个号称“小曼哈顿”的CBD 新区,在围绕四周的高层办公大楼之中,这个建筑就表达了面对这个世界的决然不同的态度。
近年来,我提出“重建一种当代中国本土建筑学”的主张,宁波博物馆的设计就是这种主张的探索和具体实践。意味着从当代现实与观念出发,首先取决于以自然之道为约束的人文地理和以“山”、“水”为沉思对象的景观诗学为背景,重新审视熟悉的建筑学体系。对“自然之道”的认识与体验,将重新成为设计与建造活动的出发点。博物馆从设计语言上看,重点表达了“介于自然与人类之间的”的观念,平面是简洁的长方形集中式布置,但两层以上,建筑开裂,微微倾斜,演变成抽象的山体。这种形体的变化使建筑整体呈微微向南滑动的态势,场地北部为一片水域,建筑因而具有刚从水中上岸的意向。而在建筑内部,两层以上为一高低起伏的公共活动平台,从建筑整体分裂出的5 个单体,和而不同,围绕这个平台,又成传统城镇的格局与尺度。传统中国关于“山”、“水”与建筑关系的美学被有深度地重新转化了。我曾经说这栋建筑的意思出自宋代画家李唐的“万壑松风图”,但我更在意的是,不只是这么说,而是如何让人直接在现场体会到。
如果说,这种深度的诗意表达多少还是抽象的,博物馆在外墙材料上的探索就使抽象的诗意有了具体的物性和质感。外墙由“瓦爿墙”和“竹条模板混凝土”混合构成,使用“瓦爿墙”,除了它能体现宁波地域的传统建造体系,质感和色彩能完全融入自然,它的另一个意义在于对时间的保存,回收的旧砖瓦,承载着几十年甚至百年以上的历史,它使得博物馆一建成,就凝聚了几十年甚至百年以上的时间,而工匠在砌筑时的即兴发挥,使它更加鲜活。“竹条模板混凝土”则是一种全新创造,“竹”和江南地域存在感的物性关系,“竹”的弹性和对自然的敏感,都使原本僵硬的混凝土发生了艺术质变。
可以想像,就像中国园林的建造,宁波博物馆特殊的材料做法使它已经变成了有生命的环境,需要滋养,于是我们可以把建筑当作植物对待。它刚建成的时候肯定不是它状态最好的时刻,10 年后,当“瓦爿墙”布满青苔,甚至长出几簇灌木,它就真正融入了时间和历史。
之所以要探索一种中国本土的当代建筑,是因为我从不相信单一世界的存在,事实上,面对中国建筑传统全面崩溃的现实,我更关注的是,中国正在失去自己关于生活价值的自主判断。所以,我工作的范围,不仅在于新建筑的探索,更关注的是那个曾经充满了自然山水诗意的生活世界的重建。至于借鉴西方建筑,那是不可避免的,今天中国所有的建筑建造体系已经完全是西方方式,所面对的以城市化为核心的大量问题已经不是中国建筑传统可以自然消化的,例如,巨构建筑与高层建筑的建造,复杂的城市交通体系与基础设施的建造,作为主流的钢筋混凝土现浇建造体系。不过,我的视野更加广阔与自由,例如,我会越过西方现代建筑的抽象概念,与它实际存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建筑现实去对话。对中国自身的建筑传统,我也保持同样的态度。这样一种不同的建筑学,需要从最基本的问题重新入手,建筑师在今天都喜欢把“自然”挂在嘴上,但多是抽象地谈,形式的谈,象征的谈,却几乎没有可以重新进入真实的自然事物的方式。就最基础的建造问题来说,当然,我们不得不想办法把传统的材料运用与建造体系同现代技术相结合,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提升传统技术,这也是我在使用现代钢筋混凝土结构和钢结构体系的同时,大量使用手工技艺的原因,这不仅是中国建筑遇到的难题,也是全世界正在向现代性转型的地方都困惑的难题。技艺掌握在工匠的手中,是活的传统,是地方文化差异性的根基。如果不用,即使在形式上模仿传统,传统必死,而如果传统一旦死亡,我相信,我们就没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