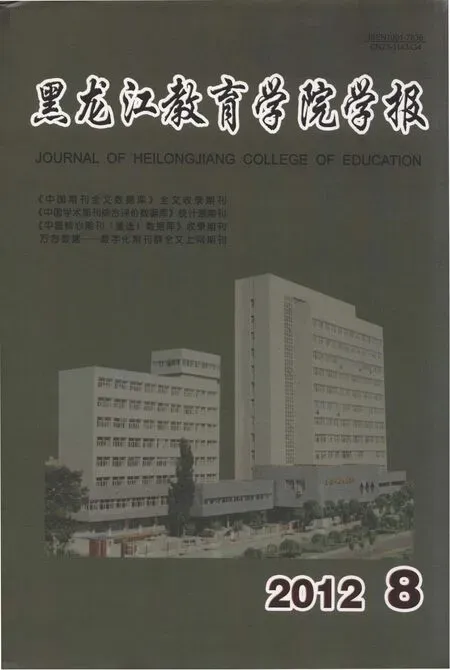丁玲延安时期作品的浪漫主义情结
2012-04-13林璟辉
林璟辉,李 玲
丁玲延安时期作品的浪漫主义情结
林璟辉,李 玲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长沙410205)
有人说丁玲延安时期的作品,都是描写残酷的敌我战争的现实主义作品,经历生活的重重变故和苦难,她已经是一位现实主义革命作家。但是,一个作家的经历固然重要,而性格,才是决定作品具有独特的作家自我风格的要素。丁玲就是一个乐观浪漫的人,她延安时期的作品,虽然是描写革命,但作品中处处体现着她的浪漫主义情结,尽管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她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性格进行创作,但丁玲延安时期的小说,都有其浪漫主义性格的渗透。
丁玲;延安时期;文本作品;浪漫主义情结
一
有人说丁玲延安时期的作品,都是描写残酷的敌我战争的现实主义作品,她本人也是一位经历磨难,经过斗争考验,全身心投入革命,为革命大声呐喊的现实主义革命作家。一个作家的生活经历虽然对他的文学作品有直接影响,因为作家往往用自己熟悉的东西作为创作的材料,不同的个人生活经历,会积累广泛而特别的创作素材。但是一个作家的性格,才是决定作品具有独特的作家自我风格的要素。性格有天生具有的部分,也有生活中形成的部分,性格一旦形成,是相对稳定很难改变的,作家会用它接触见识到的东西,用具有自我性格的思维方式和观察角度来进行创作。丁玲就是一个乐观浪漫的人,尽管在革命斗争时期,在残酷的敌我斗争中,她的延安时期作品都是在描写革命,呼吁革命,推动革命,作品中也描写血腥、暴力、愤怒和觉悟,但作品中却蕴藏着一丝挥之不去的浪漫主义情结,尽管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她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性格进行创作,把自己的这种浪漫主义情节明白完全地展示在文本中,但丁玲延安时期的小说,却有其浪漫主义性格的渗透。
二
丁玲的浪漫主义性格的形成,和她从小的生活环境分不开,与她母亲开明的教育密不可分。丁玲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童年时家境衰败,她跟着母亲长大。母亲带着她一起到学堂学习,在村里人看来,这是不符合规矩的,但在丁玲心里,能够跟着母亲结交的阿姨们一起学习,这是很愉快、很浪漫的;长大后,年轻的丁玲想要按照自己的愿望去生活、去学习,母亲便很开明地节省自己开销资助她和挚友一起外出求学,虽然清苦,但有着追求真理的信念,相信好友真挚的爱情,她精神乐观,非常浪漫地在苦中作乐,对生活的体验有着担心却并不害怕。
母亲带着丁玲摆脱封建家庭的桎梏,从小的家庭离异,非但没有造成丁玲自卑懦弱的性格,反而是母亲的独立自主,有知识而有觉悟,使得丁玲勇敢执著。虽然生活清苦,但物质上的匮乏更是让丁玲无所顾忌地追求自己理想,去寻找体现自我价值的生活。母亲不仅是在精神上的支持,鼓励她去闯荡,而且为她筹备资金,直至丁玲生下孩子,生活变故时,也交由母亲抚养。母亲是丁玲的强力支持,是丁玲乐观、勇敢、浪漫主义性格形成的最重要的影响。
瞿秋白也形容丁玲:“是一个需要展翅高飞的鸟儿,飞的越高越好,越远越好。”[1]丁玲就像一只自由的鸟儿,在这样的环境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浪漫而狷介的性格,这在其早期作品文本中多次反映出来。
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中,丁玲讲述自己的性格时说:“我们对当时的平民女校总感到不满,我们决定自己学习,自己遨游世界,不管它是天堂或是地狱。当我们把钱用光,我们可以去纱厂当女工、当家庭教师,或者当佣人、当卖花人,但一定要按照自己的理想去读书、去生活,自己安排自己在世界上所占的位置。”可以说,丁玲的浪漫主义的性格,从小便形成了,虽然被黑暗的社会暂时压制,被悲惨的生活遭遇不断剥离,但始终都在。丁玲虽然经历变故,曾经悲苦凄凉,她的作品也有过转型,在延安时期是创作了许多反映敌我残酷斗争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品,但是她骨子里是一个浪漫的人,有着不可解开的浪漫主义情结,这在她延安时期的作品文本中都有所体现。
三
经历了被捕、失去丈夫的丁玲,以知名女作家的身份,逃离国统区来到抗战最前线延安,毛泽东特别作了一首《临江仙》赠与丁玲:“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毛泽东在延安抗战紧张的间隙做诗给女作家,这还是第一回。诗歌因丁玲被国民党软禁而笑谈戏称其为“出牢人”,更把丁玲作为著名作家,写出具有影响力作品的工具——笔,形象地称为“三千毛瑟精兵”。这不仅非常符合丁玲浪漫主义的气质,更以轻松似朋友的口吻,欢迎丁玲这位从大城市来的知名作家转型为革命队伍中的坚强女卫士,成为抗战的一员,成为抗战的宣传呐喊者。这样的生活变化对丁玲的文学写作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她开始探讨自己创作的方式,摸索个人主义作家向革命作家转型的定位。
丁玲延安时期的作品,文本情节都是以真实斗争作为依据,这些都是丁玲来到延安,来到战争最前线后经历到的。这个时候的丁玲,刚刚接触残酷的革命斗争,专注凝神,紧中有松地写出延安时期的第一部作品《一颗未出膛的枪弹》。作品表现的是当时共产党提出联合国民党一同抗战的正确政策,这个政策对于中国的未来的巨大影响,表达我党对抗日战争的正确认识和在我党指挥下整个部队对抗日政策的深刻认识,突出我党士兵的视死如归,鼓舞我党部队昂扬的斗志和宣传国民党官兵对民族大义的认同。
这篇小说写的是小红军掉队了,一个老太婆出现在小红军面前,得知他是红军,说:“还是春上红军走过这里,那些同志真好,住了三天,唱歌给我们听,讲故事。咱们杀了三只羊,硬给了我们八块钱,银的,耀眼睛呢!后来东北军跟着来了,那就不能讲,唉……”[2]国民党军队在围剿红军,从“春上”开始,持续了近一年。在外有日本人入侵的关键时刻,国民党军队却死死地盯着红军追击。斗争的残酷和持久,从老太婆一句淡淡的叙述中可以窥见一斑。从东北官兵口中,我们进一步得知,国民党的东北军是一直围剿红军,不仅持续时间长,而且追击地域广,“还是慢点走的好,就怕他打后边来,这种亏我们吃过太多了。”在东北军和红军的围剿与被围剿中,国民党兵精粮足占有主动权,共产党节节撤退偶尔也做自卫的还击,双方都有过损失,一点点的掉以轻心失去的就是性命。在这里,丁玲文本中渐渐表现出了战争的残酷,敌我斗争的残酷。虽然国民党占据优势,但兵不厌诈,红军运用战术,从后面包抄,国民党东北军是吃过太多这样的亏了。在这样有着深仇大恨的残酷现实中,丁玲的描写却让人意外,敌人准备枪决小红军,小红军却说:“还是留着一颗枪弹吧,留着去打日本!你可以用刀杀掉我!”也就是这样一句话,使读者感到意外,使作品得到广大读者的共鸣,使小说广泛传播开去,作品顿时从严肃的暗淡的革命斗争的题材中,擦出了一抹浪漫主义的情愫,也把我党的正确决策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另一部作品《新的信念》中,丁玲选取了一个民族求生存反侵略的宏大题材,以一位妇女遭受战争强暴为切入点,把这一事件作为引爆民族仇恨、反抗侵略的导火索,政治文本意图极为明显。小说的故事,一开始阴云密布,战争的残酷从血淋淋的村子的惨状里完全展示出来,这是对把中国推向水深火热的灾难深渊的丧尽天良的日本侵略者的强烈控诉。陈老太婆在日军入侵的村子里提心吊胆地活,知天命的年纪却惨遭日军蹂躏。当她向家人讲述亲眼看到的日本侵略者对妇女们罄竹难书的罪行时,所有人都害怕了,媳妇们的脸青了,孙女儿不停说害怕。陈老太婆此时故意惊骇她们,希望自己能够煽起众人对日本侵略者愤怒的火焰。但她看到自己的儿子时,却停住了不知所措。她讲述了那么多遭受蹂躏的妇女,但在和儿子媳妇们讲述自己时,却“怕儿子们探索的眼光,而且她觉得羞耻,痛苦使她不能说下去。”[3]在这个情况下,丁玲以她特有的浪漫主义情结,把作品引导到最终陈老太婆克服自己的恐惧,向家人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更在家人的鼓励下,在村民大会上宣讲自己的经历,痛斥日本侵略者灭绝人性的兽行,表达自己所遭受的不可想象的摧残和愤怒。不掉一滴眼泪并非不伤心,在众人面前不退缩并不是不害怕。耻辱!只有牢牢记住这耻辱,只有共同体验经历和共同感受到耻辱,才能化陈老太婆的愤怒为大家的愤怒,化仇恨为民族的仇恨,这种仇恨最终凝聚成为向侵略者讨还血债的复仇力量。这个故事的结尾选择,是一个大胆的决定,丁玲思想深处的浪漫主义情结,带领着她走向在当时社会并太可能实现的美好的结局,也表现了丁玲的浪漫主义情结。
四
经过在延安几年时间的生活和工作,丁玲的作品内容和风格虽然保持了革命现实主义的风格,但丁玲延安后期的作品,以批判主义的手法描写抗战内容,改变了作品中个人英雄主义的追求和战争可圆融、可妥协的个人预见,排除纯粹的抽象与雕饰,排斥之前作品中那种虚无缥缈的幻想,真实地呈现延安地区社会生存的本真样态,反映特定的战争年代的转变时期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性格。落笔的时候,还是从细微处不自觉地受到了性格中浪漫主义情结的影响,表达个人对现实的不满和美好愿望,文本形成了具有作者独特的批判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结合的风格。
丁玲所批判的现实,是个人预设中没有达到理想状态的现实,具有浪漫性质和个人色彩。丁玲在《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作品中,所描写的革命区的工作环境、医疗水平、人情世故等等,无一不是真实具体的,她通过把人物置放在历史的复杂的社会关系中,通过人的理想与现实矛盾去揭示和批判革命根据地的现实,这也让丁玲因为其作品的个人浪漫主义情结没能很好切入当时的现实社会,付出了不可想象的代价。
《我在霞村的时候》讲述的是一个18岁的女孩贞贞,在日本人烧杀抢掠村子的时候被日本人抓走并强暴。与《新的信念》中陈老太婆不一样的是,这个女孩并没有从敌人那里逃跑出,作者极具浪漫主义情结地安排贞贞做了一个默默的地下工作者,帮助游击队从日本军队那里获取情报。而且描写她从日本军那里回来,没有表现出人们想象中那样的凄凄惨惨,借村子里人的口中表达,她似乎既达到了为游击队拿情报又没有受委屈的目的,甚至过着让人艳羡的生活。“有人告诉我,说她手上还戴得有金戒指,是鬼子送的哪!”“说是还到大同去过,很远的,见过一些世面,鬼子话也会说哪……”[4]文本中的贞贞,在中国封建乡土“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千年规训对失节妇女的礼教中,面临着道德困境。从名字中,我们可以看出,父母社会对贞贞的期望,就是做一个贞洁的女子,做一个遵守道德规范的小女子。而贞贞在惨遭日寇蹂躏凌辱后,隐姓埋名地潜伏在日军中,不顾村子里冥顽不灵的村妇指指点点,说三道四,牺牲自己的身体套取游击队所需要的情报,并顺利地完成任务,得到帮助远离村庄,过上了自己理想的生活。
另外一篇小说《在医院中》,讲述的是一个国统区接受正规产科教育的年轻人陆萍,放弃去大城市的机会,一心要为革命作出自己的贡献,毕业后来到离延安四十公里的一个新开办的医院工作。陆萍是一个开朗积极的姑娘,是一个知道一些人情、很乖巧的姑娘,会在科长面前显示自己的能干,会适量地挑好听的话说。但在弥漫着保守、落后、苟安习气的氛围里,陆萍立刻感觉到了麻木的工作人员和懈怠的工作态度以及落后的工作环境会对革命工作,对同志战友造成严重危害。消毒不够彻底直接导致伤口感染,工作人员的冷漠消极耽误病人很多时间,做手术的房间烧碳取暖造成医生昏迷等等,出于对党的忠诚,出于自身专业,她挺身而出,大胆向医院管理者提出建议,但是长时间没得到答复、没看到改变,陆萍不甘陷入绝望的巨大的网,她挣扎着疯狂地对医院里一切不合理的人和事物发起了主动猛烈的进攻。作品一出,引起了很多质疑,甚至有人尖锐地提出,我们革命区有这么多黑暗,这么多陋习吗?这中间显著的矛盾并不是医院的设备与医疗条件落后,而是普泛于群众中的愚昧、落后、冷淡、麻木的精神状态。这样的问题是几千年来落后的知识文化导致的小农意识在民族战争背景下的表现,是真实存在的,而丁玲试图用陆萍这样一个乐观开朗的医务工作者的疾呼,引起人们的重视,这虽然是个人浪漫主义情结对革命的期待,但却给她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让她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她却一直执拗地坚持着。
五
丁玲经过长期的革命生活,逐渐认识到革命的严酷性,认识了革命的现实,丁玲热爱着延安和人民,拥护中国逐渐看到光明的革命行为,她用她不满于现状的浪漫主义的性格和对革命的责任感、作为作家的使命感,从热烈的单一基调中沉思起来。尽管作品都是描写革命,但作品中时时表现出她的浪漫主义情怀。在延安时期艰苦的创作中,虽然受过无数人的质疑和指责,但她“飞蛾扑火,非死不止”的浪漫主义情怀,却是始终不曾缺失的。
[1]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G]∥丁玲文集(第四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116-118.
[2]丁玲.一颗未出膛的枪弹[G]∥丁玲文集(第五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95-96.
[3]丁玲.新的信念[G]∥丁玲文集(第五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19-20.
[4]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G]∥丁玲文集(第五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65.
Romantic Complex of Ding Ling's Works in Yan'an Period
LIN Jing-hui, LI Ling
(Hunan First Normal College,Changsha 410205,China)
Some people say that Ding Ling's works describe brutal realism of war,and she herself is also a realistic revolution writer after experiencing changes and hardships in life.However,important as a writer's experiences are,it is the character that acts as the element determining the writer's unique personal style.Ding Ling is an optimistic romantic,whose works in Yan'an period,though describing the revolution,embodies the romantic complex everywhere.Although in that particular historical context,she can not create works in accordance with her own personality,Ding Ling's works in Yan'an period all have the infiltration of her romantic character.
Dingling;Yan'an period;text works;romantic complex
I206.6
A
1001-7836(2012)08-0126-03
10.3969/j.issn.1001 -7836.2012.08.048
2012-02-21
林璟辉(1983-),女,湖南长沙人,讲师,文学硕士,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李玲(1981-),女,湖南邵阳人,讲师,教育硕士,从事语文教学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