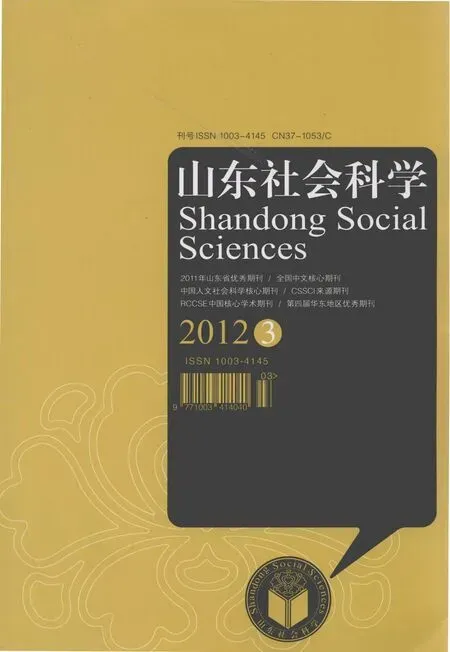梁启超与马克·布洛赫“新史学”思想比较研究
2012-04-13宋学勤
宋学勤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北京 100872)
梁启超与马克·布洛赫“新史学”思想比较研究
宋学勤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北京 100872)
从比较史学的角度入手,沿着年鉴学派“两大史学主张”即“建立总体史的意图”与“史学和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实践”的产生路径出发,认真比勘马克·布洛赫与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可以发现二位史学巨匠治史理念的“不谋而合”。马克·布洛赫“新史学”思想的成熟是建立在西方各种人文各学科成熟发展的基础之上,梁启超“新史学”思想则诞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中,但足见其史识卓绝。梁启超在其中西融会与古今贯通的学术背景下,在如何回答“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这两个史学上的最根本的问题上,不仅是在国内发时代之先声,而且也是站在当时的“国际前沿”的,以此也可以进一步窥见梁启超新史学久远影响力的奥蕴。
梁启超;马克·布洛赫;总体史观念;跨学科思想;史料观
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不仅与美国史家鲁滨逊有异曲同工之妙①参见宋学勤:《梁启超、鲁滨孙“新史学”思想比较研究》,《中州学刊》2003年第1期。,而且与当前在国际史坛上居于主流地位的法国年鉴学派史家的“新史学”思想亦有不谋而合之处。法国年鉴学派是当代西方史学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流派,也是西方新史学中最有代表性的流派。年鉴学派不是有着固定组织的学术团体,而是一批怀着共同信念从事史学研究的学者,其创始人是法国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学界对法国年鉴学派的研究已有很多,但很少有学者注意年鉴学派的史学思想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之共性的存在,所以也很少有学者将二者的方法论放在一起探讨。1929年1月,《经济社会史年鉴》杂志的创刊,标志着年鉴学派的建立,而巧合的是,这正是梁氏去世之年月。因此,分析二者之间共通之处颇有意味。由于年鉴学派经过几代的发展,思想与理论繁富,但年鉴学派的“两大史学主张”,即“建立总体史的意图”与“史学和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实践”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影响,这也是年鉴学派范型的革新之处,可这些范型的基本特征在布洛赫的“新史学”思想里已初见端倪。由于年鉴学派“新史学”思想的驳杂性,笔者仅从年鉴学派创始人马克·布洛赫入手,沿着年鉴学派“两大史学主张”的产生路径出发,认真比勘布洛赫与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以期发现二位史学巨匠的“不谋而合”。
一、马克·布洛赫的“总体史”观念与跨学科思想
总体史(Universal History)是布洛赫著书立说的核心概念。布洛赫写道:“历史研究不容划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即使在你的研究领域内,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而只有通过众人的协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历史。”②[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8-39页。吕西安·费弗尔也说过,《经济和社会史年鉴》的两个修饰词,特别是“社会”一词,是马克·布洛赫考虑到历史的无所不包而特地选定的。他说:“我们完全知道,在眼下,‘社会’作为一个形容词,由于含义太多而最后变得几乎毫无意义……我们一致认为,正因为该词的‘模糊’,它才根据历史的旨意被创造出来,用以为一种自命不受任框框约束的刊物充当标题……所谓经济和社会史其实并不存在,只存在作为整体的历史。就其定义而言,整个历史就是社会的历史。”①[法]雅克·勒高夫:《新史学》,《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即使在具体历史事件的研究时,布洛赫仍然强调总体史的视野,他说单一历史事件实际并不单一,因为它“产生于总体的社会状态”。“一个教义包含着人类环境的所有问题”,“小小的橡子可以长成参天大树,但离不开适宜的土壤和气候条件,而这些条件又超出了胚胎学的范围。”②[ 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27页。因此,贯彻总体史的观念,就必须打通学科畛域,而且他们还强调:“历史应该成为社会科学的核心和心脏,应该是以社会的、心理学的、伦理的、宗教的、美学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等各种观点对社会进行研究的一切科学的中心。”③孙娴:《法国现代史学中的总体史观》,《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这表明了历史学的综合性与统领性特点。
在《年鉴》的创刊号卷首寄语中,费弗尔和布洛赫写道:“我们都是历史学家,都有共同的体验,并得出了共同的结论,我们都为长期的、从传统分裂状态中产生的弊病而苦恼。目前的状况是,一方面,历史学家在研究过去的文献史料时,使用着陈旧的方法;另一方面,从事社会、近代经济研究的人,正在日渐增加。这两个方面的研究者,互不理解,互不通气。现在,历史学家之间,在从事其它研究的专家之间,存在一种不相往来的闭塞状况。当然,各行的研究家,都致力于自己的专业,在自己的庭院中辛勤劳动,如果他们关心一下邻居的工作,就十全十美了,可以却被高墙阻隔了。我们之所以站出来大声疾呼,就是针对这种可怕的分裂的。”④[ 日]井上幸治:《年鉴学派成立的基础》,《国外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正如彼得·伯克所评价:“它是喉舌甚或是喇叭,鼓吹主编们呼唤跨学科的新史学方法。”⑤[英]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1、19-21页。吕西安·费弗尔与马克·布洛赫相识于1920年,两人分别被斯特拉斯堡大学任命为教授与讲师,他们的办公室靠在一起,门总是开着,两人都以跨学科的方式思考,这为他们跨学科边界的思想交流提供了便利。两人的日常聚会在1920年至1933年期间持续了13年时间,围绕在这两人周围的是极其活跃的跨学科群体,如社会心理学家夏尔·布隆代尔与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⑥⑥[英]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1、19-21页。他们志在营造一种跨学科研究的学术新范式。
打通史学与社会科学,使史学社会科学化和社会科学历史化,这是年鉴学派对历史研究方法的重要贡献之一,也就是借用其他社会科学深入研究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规律。“特别反对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分离,批评各种历史专家‘筑起高墙,精心培育各自的葡萄园。’”⑦《 经济社会史年鉴》(创刊号)(1929年),转引自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顾良、施康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3页。勒高夫评价说:“新史学在任何领域中的开拓性著作全都表现出它们不受任何专业限制的雄心壮志。”⑧⑧[法]雅克·勒高夫:《新史学》,《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布洛赫明确地指出撰写《封建社会》的目的就是要“对一种社会组织结构及把它联为一体的各原则进行剖析并做出解释”。他引进了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心理学的概念,综合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充分体现其总体史观念。正如彼克·伯克所说:“《封建社会》的确是布洛赫最涂尔干式的书。他一直不停地使用conscience(集体意识)、memory collective(集体记忆)、representation collectives(集体表象)之类的语言。”他认为,“在本质上说,该书关注的是涂尔干研究的一个中心主题——社会整合。在本质上说,这一整合或‘依附纽带’的特殊形式,是以功能主义的方式进行解释的。”这样使他的著作更具“社会学色彩”⑨[英]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1、19-21页。。伊格尔斯亦认为:“他们无限地扩大了历史学家的视野,不仅在空间上突破了西方文明的框架,探索非西方的、原始的文化和规律,而且在主题和方法论方面扩大了历史学家对人类社会生活各个侧面感兴趣的范围,其中包括生物学的方面以及幻想和神话形式的领域,同时还探索到不仅是‘史前的’、而且是近期的、各种各类非书面的表达方式。他们把历史科学和最广义上的‘人文科学’结合起来,不仅就古典的社会科学或是行为科学而言,而且就结构人类学、精神分析学、最现代形式的艺术、文学和语言学而言,都是如此。”⑩[ 美]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赵世玲、赵世瑜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85页。高度评价了年鉴学派的跨学科研究。年鉴学派第三代史家拉杜里曾这样评价布洛赫:“如果用一个简短的公式来说明这位大师的功绩,我们可以概括为社会学方法和历史展望的时间深度这两个方面。马克·布洛赫主张的社会学方法,就是要坚决地脱出历史事件、纯政治因素和历史人物的框框,以便更好地抓住真实历史的动力,即成千上万的低层人物和成千上万的杰出人物。这两个‘成千上万’把那些在时代广告橱窗充当摆设的人像(如扣人心弦的贝雅尔和威名赫赫的路易十四……)抛在一边,自己创造着真实的历史。”⑪[法]勒华·拉杜里:《新史学的斗士们》,《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第4期。可谓深谙布洛赫的治史理念。
如果说年鉴学派的第一代学者奠定了方法论基础,那么第二代、第三代学者则在布罗代尔的领导下,继承、发展了这个传统,并逐渐扩大了年鉴学派的影响。以致有学者认为,“布罗代尔巨大影响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他的史学主张往往被等同于年鉴派的范型。”①鲍绍林:《西方史学的中国回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03页。但布罗代尔本人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年鉴学派的模式形成时期应为1929—1940年,而他这一代人“并没有提出什么新思想、新概念”,只是提供了一些“实例”、“公式”,证实并实现了第一代人物的纲领而已。这种自我评价是比较实事求是的。②[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顾良、施康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5页。作为年鉴学派的奠基人,布洛赫在史学理论与具体的历史研究两个方面都有着卓越的建树,为新史学的范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被称为“法国史学革命的领袖”③[英]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二、梁启超的“全体之史”观念与跨学科思想
正如雅克·勒高夫指出:“任何形式的新史学都试图研究总体历史。”④[法]雅克·勒高夫:《新史学》,《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是在对传统史学的批判与反思的基础上产生的,他提出了根治中国传统史学“二病”的方案:一是没有“全体之史”观念。“知有一局部之史,而不知自有人类以来全体之史也。”“夫欲求人群进化之真相,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观察之,内自乡邑之法团,外至五州之全局,上自穹古之石史,下至昨今之新闻。”他看到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必须为“为史界开一新天地”,大力主张拓宽历史研究的范围,要研究智力、产业、美术、宗教和政治等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二是没有跨学科思想。“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关系也。”他认为历史学的进步,必须注重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广泛吸取多学科的先进方法。他明确阐述道:“夫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人类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即日本所谓经济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其他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然后他又提出:“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⑤梁启超:《新史学》,载《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41页。倡导扩充史学家的修养及于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领域。这根治“二病”的方案就是为新史学所规划的方向,这两个方案的提出同样蕴涵着梁启超的深邃的总体史观念与跨学科思想。作为“理论和实践并重的史界巨灵”⑥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2页。,梁启超身体力行,不仅仅是把他的思想停留在理论层面。“任公虽好引其他学科的公理公例入史,间中且不免误解误用,但通常不取教条主义态度。”⑦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2页。可以说,梁启超对新知识的感悟力是超前的。他的“全体之史”观念与跨学科思想即是他于20世纪初年对历史学前景的预言。
而且梁启超晚年不断发展他的观点,他指出,近代史学进步的特征之一就是“为主观的观念之革新。以史为人类活态之再现,而非其僵迹之展览。为全社会之业影,而非一人一家之谱录。如此,然后历史与吾侪生活相密接,读之能亲切有味,如此,然后能使读者领会团体生活之意义,以助成其为一国民为一世界人之资格也。”⑧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载《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 年版,第4087、4088、4088、4139 页。而“新史之作”就是要记述“活动之总成绩及其因果关系”,“实乃簿录全社会之作业而计其总和”;是要记述“一社会一时代之共同心理,共同习惯,不能确指其为何时何人所造,而匹夫匹妇日用饮食之活动皆与有力焉,是其类也。吾所谓总成绩者,即指此两类之总和也”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载《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 年版,第4087、4088、4088、4139 页。。所以他所计划的中国通史应分为三大部:一是政治之部,包括朝代、民族、地理、阶级、政制组织、政权运用、法律、财政、军政、藩属、国际、清议及政党十二篇;二为文化之部,包括语言文字、宗教、学术思想、文学、美术、音乐剧曲、图籍、教育八篇;三为社会及生计之部,包括家族、阶级、乡村都会、礼俗、城廓宫室、田制、农事、物产、虞衡、工业、商业、货币、通运十三篇。⑩梁启超:《原拟中国通史目录》,载《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600页。这种设想不可谓不宏大,不可谓不全面。⑪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载《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 年版,第4087、4088、4088、4139 页。而且还表现出研究历史的一种全球性眼光,主张写一国之史应联系到世界各国发展状况。探讨它与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的互动效应。“史之为态,若激水然,一波才动万波随。旧金山金门之午潮,与上海吴淞口之夜汐,鳞鳞相衔,如环无端也。其发动力有大小之分,则其荡激亦有远近之异。一个方寸之动,而影响于一国;一民族之举足左右,而影响于世界者,比比然也。”⑫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载《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 年版,第4087、4088、4088、4139 页。他举例说:“刘项之争,与中亚细亚及印度诸国之兴亡有关系;而影响及于希腊人之东陆领土,闻者必疑其风马牛不相及。然吾征诸史迹而有以明其然也。实则世界历史者,合各部分文化国之人类所积共业而成也。吾侪诚能用此种眼光以观察史迹,则如乘飞机腾空至五千尺以上,周览山川形势,历历如指掌纹,真所谓‘俯仰纵宇宙,不乐复何如’矣。然若何然后能提絜纲领,用极巧妙之笔法以公此乐于大多数人,则作史者之责也。”所以他列举了四个关于“中国史之主的”的研究课题,其中有两项都是蕴含全球性眼光的,一是“说明中国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其与世界他部分文化相互之影响何如”。二是“说明中国民族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性,与其将来对于人类应负之责任。”①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载《梁启超全集》,第七册,第4091、4105页。1924年,他在为清华大学职业指导部所作的讲演中,也再一次申明借鉴社会科学治史的愿望。他说:“中国人要想在自然科学中,对于世界有何贡献,实一极难之事。在社会科学方面,虽比较有新发明之可能性,但也是很难。惟史学方面可以供我们发明开辟以贡献于世界的矿地却异常之多。如果用西洋的科学方法以研究中国数千年来很丰富的史料,实一极容易而且极伟大之事业。”②梁启超:《文史学家之性格及其预备》,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38页。他对跨学科治史方法一再强调,并对跨学科思想作了进一步思考,提出了如何避免史学与其他学科的结合,导致历史学科丧失主体地位的问题。梁启超不仅提出理论,而且他还能躬自实践,所以他能撰成《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等专门史研究。“历史上各部分之真相未明,则全部分之真相亦终不得见。而欲明各部分之真相,非用分功的方法深入其中不可。”③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载《梁启超全集》,第七册,第4091、4105页。即今天我们所说的作“窄而深”的研究,但梁启超的思维并没有停止,他理想的新史学应是在认识“局部之史”的基础上去认识“全体之史”,而根本途径即为在理清“史学与他学之关系”的基础上层层推进。他认为,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是双程的,史家可吸取人类学、社会学的成果来澄清古代史的神话和传说,但亦可借落后地区的调查与研究以坚证、否证或修正有关的社会学、人类学理论。在他看来,史学与社会学的关系是平等互惠的,所以他经常用社会学原理述史论事。但地理学公例所给他的“通其一万事毕之乐”,并不下于历史社会学。在1902年前后,他一连写过好几篇文章,④如《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亚洲地理大势论》、《中国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等。从地理学的角度来论述历史。到其晚年在其一系列学术史文章中,也一再阐发其地理思想。⑤如《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而且他还用生计学(经济学)的方法解释历史、析理国际关系等等。他的这些理论表述,在我们今天的史学研究都得到了明证。
可以说,在总体史观与跨学科治史方法上,梁启超与布洛赫是不谋而合的。今天看来,21世纪的新史学的建构目标或方向仍是“总体史”。因此,无论中西,现代史学潮流都是以“总体史”为指归。作为“新史学”根本研究范式的“总体史”实际上更多地是就方法论意义而言的,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态度和新的研究视角”。其中视角的转换和视野的开阔又是最具关键性的,它主张对历史进行“全景式”或“全辐式”的把握。在研究方法上,采取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的结果,能够尽可能地展现历史的多面相、多纬度,更接近于历史的客观事实。
不仅如此,在治史理念的更新过程中,其史料观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三、史料观念的更新与发展
史料是史家之食粮,没有史料观的更新,也不会有“新”史学的发生。马克·布洛赫与梁启超在史料观方面都有些精彩论述,同时也体现了二位史学巨匠多元史料观的“趋同性”。
在史料的运用上,布洛赫提出所有可以帮助历史学家观察人类活动与精神痕迹的事物,都可以作为史料的新观点。在《法国农村史》中,布洛赫批评了前辈学者库朗日迷恋起源的偏好,提出放宽视野,“从今到古倒读历史”,以便更好地理解过去的文献。“为了说明过去,人们必须看一看现在,或者至少也该先看一看离现在最近的一段过去。”“谁看到了陷阱,就不会往里掉。”⑥[法]马克·布洛赫:《法国农村史》,徐中先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7页。我们知道,传统史学的史料范围比较狭窄,史料类型也较单一。大多是以文字形式出现的史料,而由于文献史料大多记载历史上的政治、军事等事件,因而写出的大多为政治史、军事史、人物史,这就极大地限制了研究对象的范围。这在某种程度上说,片面的史料观限制了史家的视野,同时也制约着史学研究的发展。依据传统史料观,布洛赫可以用来撰述《法国农村史》的史料极其匮乏,因为文献中对法国农村社会的历史仍缺乏记载。如他自己所论:“从18世纪起,法国农业生活才得以见诸历史书籍,而不是在以前。直到那时,除了几位只关心烹调法的专家外,作家们极少考虑这方面的事,行政官员亦无更多的关注。仅有几本法律著作或几部习惯法向人们提供诸如公共放牧制之类的农耕基本法则。”①[法]马克·布洛赫:《法国农村史》,徐中先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4、5页。史料是史家的食粮,没有史料便没有史学。基于此,布洛赫提出“以一种离我们较近时代的光芒去照耀遥远的过去,尤其当我研究农业经营制度时。……在有些情况下,为了说明过去,人们必须看一看现在,或者至少也该先看一看离现在最近的一段过去。这就是文献资料状况要求农业问题研究采取的方法,我们将看到这样做的理由。”②[法]马克·布洛赫:《法国农村史》,徐中先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4、5页。并且“这些相对较晚时代的文献资料应该成为我们研究法国农村史——我理解的农村史应既包括农业技术又包括多少紧密地支配着经营活动的农业习惯——必须遵行的出发点。”③[法]马克·布洛赫:《法国农村史》,徐中先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4、5页。布洛赫强调,由于我们更为了解晚近的情况,也由于从已知推导未知更为谨慎,必须“从后向前看历史”,布洛赫非常有效地使用了这一方法。④[英]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这也极大地突破了传统史料观的局限,体现了一种新的史料观。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中,他又再次表述了他的认识,他认为“各时代的统一性是如此紧密,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⑤[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1992年版,第36、45、18页。在古今结合的治史思想的指导下,史料观得到的更新,现代的文献资料乃至地名、图片都可以成为史料,为史家提供研究线索。“如果认为研究每个历史问题都具备专门的资料,那简直是幻想。相反,研究越深入,就越可能从不同来源的资料中发现证据。宗教史家怎么会以查阅少量神学手册和赞美诗为满足呢?”⑥[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1992年版,第36、45、18页。布洛赫在《封建社会》中所运用的史料,除了为传统实证史学所推崇的类型之外,还大量使用了诸如考古资料、诗歌、遗嘱、祈祷文、传奇文学、请愿书、教会档案、绘画、雕塑等,涉及种类非常广泛。由于史料不断地被发现,也不断地改写着历史学家的研究结论,决定了历史再认识的不断进行。布洛赫认为:“史学的不确定性正是史学存在的理由,它使我们的研究不断更新。由于全新的开拓,我们肯定可以理直气壮地声称自己将更执着于历史。只要不懈地努力实现自身价值,史学的不完善性与完美无瑕的成功,同样是富有魅力的。”⑦[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1992年版,第36、45、18页。正如勒高夫在《新史学》中所说,“新史学扩大了史料的范围”,它“扩大了历史文献的领域,它使历史不再限于朗格鲁瓦和塞诺博斯所依据的书面文献,而扩大到各种文书、图像画片、考古发现和口头资料等。一个统计数字、一条价格曲线、一张照片或底片,或古代的一块化石、一件工具或一项信物,对新史学来说,都是头等重要的文献资料”⑧[法]雅克·勒高夫:《新史学》,《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
梁启超对史料的重视及其史料意识之开阔不在布洛赫之下,正如有学者所提出,梁启超所缔造的新史学传统中,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历史思考的是他的史料观念。⑨黄 进兴:《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试论“新史学”的诞生及其所面临的困境》,载《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2页。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专列一章《说史料》,将史料分为两大类型,一是非文字的史料,含有口碑性质的史料、古迹遗物等;二是文字史料,包括旧史、关系史迹之文件、史部以外之群籍、类书与古佚书辑本、古逸书及古文件之再现、金石及其他镂文诸类。
而且他还把史料观念的更新视为近代史学进步的两大特征之一:“是故新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已。近今史学之进步有两特征。其一,为客观的资料之整理:畴昔不认为史迹者,今则认之,畴昔认为史迹者,今或不认。举从前弃置散佚之迹,钩稽而比观之;其夙所因袭者,则重加鉴别,以估定其价值。”⑩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载《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87页。
梁启超指出,由于旧史学的记叙重心在君主,对国民社会生活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而遗漏了大量的重要史料,它所反映的并不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全貌。更新史料观念,对某些史料的价值重新加以估价,更是他史学观念变化的重大表现。旧史家所认为极重要的一个人的嘉言懿行,而“在吾理想的新史中,本已不足轻重”。而一些记录田野生活的杂记野史却是能反映社会状况和社会经济的史料。“在寻常百姓家故纸堆中往往可以得极珍贵之史料。试举其例:一商店或一家宅之积年流水帐簿,以常识论之,宁非天下最无用之物?然以历史家眼光观之,倘将同仁堂、王麻子、都一处等数家自开店迄今之帐簿,及城间乡间贫富旧家之帐簿各数种,用科学方法一为研究整理,则其为瓖宝,宁复可量?盖百年来物价变迁,可从此以得确实资料;而社会生活状况之大概情形,亦历历若睹也。又如各家之族谱家谱,又宁非天下最无用之物?然苟得其详赡者百数十种,为比较的研究,则最少当能于人口出生死亡率及其平均寿数,得一稍近真之统计。舍此而外,欲求此类资料,胡可得也?由此言之,史料之为物,真所谓‘牛溲马勃,具用无遗’,在学者之善用也。”①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载《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113页。从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史料意识之宏阔,“牛溲马勃,具用无遗”,从这些能够反映社会日常生活的史料中,可以发掘中华民族文明的方方面面。
从二位史学巨匠史料观的考察上,我们亦可大略窥见他们开拓新史学蓝图的勃勃雄心。
四、余论
从方法论起源的意义上说,梁启超的原创性与马克·布洛赫相比,应当说是难分伯仲。因为时空的存在,梁启超不可能受到布洛赫史学思想的影响。笔者能找到的梁启超受法国史学界影响的一条证据则是李宗侗所记载的:“梁先生到欧洲去的时候,我恰好在巴黎,他请了很多留法学生给他讲述各门的学问,恐怕史学方法论亦是其中之一。不过他另补充上很多中国的材料,但其原则仍不免受外国人的影响。”②转引自《西方史学输入中国考》,载杜维运著《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298页。尽管如此,我们可以推知,留法学生给梁启超所讲述的只能是在当时风行一时的法国实证主义史家班汉姆、朗格诺瓦与瑟诺博斯等的史学方法论,③详见杜维运:《〈中国历史研究法〉探原》,载杜维运著《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1年版。而梁启超治史视野之宏阔,又远非实证主义史家们的理论所范围。为了更详尽地说明此问题,我们可以追溯一下马克·布洛赫以及年鉴学派新史学思想的渊源。
年鉴学派发展的历史渊源于欧洲的文明史学。“伏尔泰已为新史学画好蓝图。”④[法]雅克·勒高夫:《新史学》,《史学理论》1987第1期。19世纪上半叶,夏多布里昂和基佐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19世纪中期的法国史学家米希勒继续“表现了对政治史的拒绝和对总体史的追求”⑤[法]雅克·勒高夫:《新史学》,《史学理论》1987第1期。。米希勒之后,法国经济学家弗朗斯瓦·西米昂在《历史方法与社会科学》一文中指出,历史学要发展,就必须打破传统史学的三个偶像,即政治偶像、个人偶像与编年纪事偶像。西米昂这一反传统史学的呼声,在当时法国的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但是对年鉴学派影响最大的当推法国历史学家亨利·贝尔(1863—1954)。贝尔于1900年创办了《历史综合评论》杂志,他主张可以以历史学为中心统一人类的知识,历史学可以成为科学的科学。这种历史学并不像实证史学那样支离破碎而无意义,也不像新康德主义历史哲学所说的那样具有随意性与相对性。贝尔力图将史学置于一种既具有科学性又具有宽宏视角的地位,为此,他提倡历史学家打破过分专门化所造成的历史研究的狭隘性,主动同其他学科的专家进行合作,运用历史学、历史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方法解释历史。⑥参见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89页。亨利·贝尔的史学观点后来得到了年鉴学派的高度评价。有人甚至把贝尔看成是年鉴学派的真正奠基人。《历史综合评论》还直接培养了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就曾于1907年和1912年先后参加了《历史综合评论》的编辑工作。1929年,费弗尔和布洛赫退出了《历史综合评论》编辑部,联合创办《经济与社会史年鉴》,从此开创了一个与传统史学截然不同的新史学流派——年鉴学派。
可以想见,梁启超新史学与“年鉴学派——新史学”是诞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中。梁启超所生活的时代是中国知识分子民族觉醒的时代。而梁启超又是同时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救亡图强是时代唯一的主题。作为具有深厚国学底蕴的梁启超,认识到历史教育的作用,认为全民认识自己的历史是提倡民族主义,使四万万同胞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的基础:“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⑦梁启超:《新史学》,载《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39页。梁启超是由于现实政治的刺激而转入史学研究的。他以非凡的远见所设想的“新史学”蓝图是以救国救民为宗旨。因此,与其庞大的新史学设想相比,梁启超的具体的历史研究实践并没有达到极致,很多思想没有得到践行。相较而言,布洛赫以及年鉴学派的“新史学”思想则更具学术性,他们的新史学理论与方法都是在长期的史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所以在史学方法论方面较为完善,所以也能在西方史学界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正如有学者所总结:“作为一种新的史学范型,史学理论只是其核心与内在结构,一系列成功的研究才是其真正的表现。年鉴派通过一系列史学领域内的新突破而确立了自己在法国史学界以及在西方史学界的地位,同时又通过在具体历史研究中作出的不断创新而获得了不断的发展、更新,并逐步确立了自己的规范与权威。”⑧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98页。当然,马克·布洛赫以及年鉴学派新史学思想的成熟更是建立在西方各种人文各学科成熟发展的基础之上,没有人文及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成熟发展,年鉴学派新史家们要想取得这样的成就也是不可想象的。19世纪后期,社会科学的各门新兴学科在西方迅速发展起来,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地理学等逐渐成熟而且产生了众多的流派,他们用各种丰富多彩的学科理论与方法来解释现实与历史以及人文和社会现象。如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1858—1917)的社会学派强调社会学应把社会整体而不是个体行为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社会学的任务不是研究个别事实而是社会事实,同时指出比较研究是社会学中最主要的方法,这对马克·布洛赫的影响甚深。①迪 尔凯姆,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社会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1891年被任命为法国第一位社会学教授。1898年,他创建了法国的《社会学年鉴》。马克·布洛赫在巴黎高等师范学习时,社会学家迪尔凯姆也在那里任教,涂尔干的杂志《社会学年鉴》对他影响很大。如鲁滨逊总结:“这些新的社会科学,都有人在做专门的研究,他们已经使历史学家惯用的许多名词的意义全部改变了,如‘种族’、‘宗教’、‘进步’,‘古代人’、‘文化’、‘人类的天性’等等。他们推翻了历史学家的旧说,解释了许多历史学家使用自己的方法再不能解释的历史现象。”②[美]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59页。而梁启超所处的时代,尽管历史学本身是一门已经发展成熟的学科,从理论上讲,历史学可以同一切现成的或将要发展成熟的学科相结合。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些人文及社会科学学科才刚刚引进(如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统计学等),且局限于少数一些有留学背景的学者中间,在中国还算新鲜事物,其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并不为人所熟知。③如 在20世纪20年代末形成的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应该是受西方科学方法影响较大,曾远赴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攻实验心理学、生理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学科。时人罗家伦解释说:“要明白他这个举动,就得要明白当新文化运动时代那般人的学术的心理背景。那时候大家对自然科学非常倾倒;除了想从自然科学里面得到所谓可靠的知识而外,而且想从里面得到科学方法的训练。认为这种训练在某种学科以内固然可以应用,就是换了方向而来治另一套学问,也还可以应用。这是孟真要治实验心理学的原因。(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傅孟真先生年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历史学要同其他一门学科相结合,一定要有某种能够互相补充和反馈的关系存在,否则这种结合便没有意义。
所以说,由于当时“中国的现代科技和社会科学尚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而无法如欧美等国那样为‘新史学’的实践提供较为坚实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法论成果,甚至缺乏为一般社会理解和接受的基础(因科学水准低),这就使其影响力始终只停留在思想面,而很难在中国现代史学的实践中扎下深根并结出可观的成果”④胡逢祥:《“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坛与西方现代史学》,《学术月刊》1996年第2期。。而梁启超能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提出如此开放、具有前瞻性的史学思想,是与他早年留学日本以及晚年受西方学者影响有关,但也足见其史识卓绝。梁启超在其中西融会与古今贯通的学术背景下,在如何回答“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这两个史学上的最根本的问题上,不仅是在国内发时代之先声,而且也是站在当时的“国际前沿”的,以此也可以进一步窥见梁启超新史学久远影响力的奥蕴。
K092
A
1003-4145[2012]03-0013-07
2011-03-15
宋学勤,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梁启超新史学的当代解读”(项目批准号为07CZS002)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蒋海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