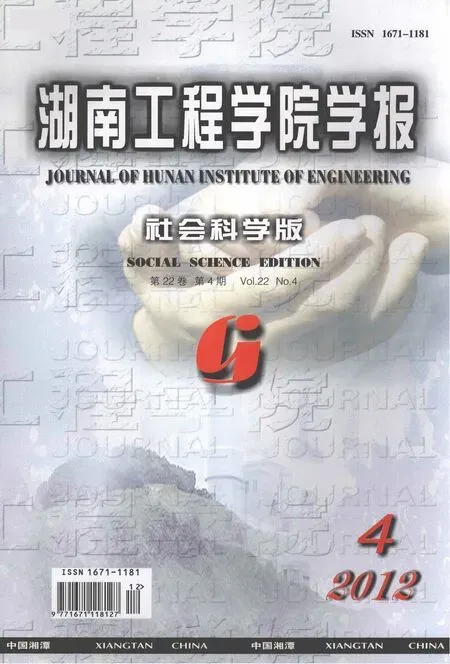对钱穆《师友杂忆》一则重要记述的补正——兼及朱怀天生平事迹考辨
2012-04-13傅宏星
傅宏星
(湖南科技学院国学研究所,湖南永州425100)
作为研究钱穆先生生平与学术最为重要的文本,《师友杂忆》吸引了太多的关注目光。该书近二十万字的篇幅,自老人八十三岁高龄开始撰写,八十八岁完稿,历时五年。书里详细记录了钱穆一生中所遇之师友和所遭之机缘,亦文亦史,亦庄亦谐,娓娓道来,感人至深。其《序言》写道:“忧患迭经,体况日衰,记忆锐退,一人名,一地名,平常自谓常在心中,但一临下笔,即渺不可寻。有时忽现脑际,未即写下,随又忘之,苦搜冥索,终不复来。而又无人可问。”[1]43因此书中会不会有大量记忆不够准确之处?钱穆的上述告白和无奈,恐怕也不全属谦辞,而是实情所以不能简单对待。比如第四章《私立鸿模学校与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中第五节、第六节记述了他与青年时代的挚友朱怀天之间的交谊,则存在一些明显的错误。虽说白璧微瑕,但也不能忽视。尤其是当前海内外学者对此多有征引,难免以讹传讹,故笔者不揣浅陋,试作辨析。
一 朱怀天生平事迹
朱怀天,名允文,字怀天,生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世居江苏松江县(今上海市松江区)西门外钱泾桥。[2]《事略》3早孤,独有一母。兄弟三人,朱怀天居次,因家庭贫困,养不起唯一的弟弟,乃由相识人家领养,已经易姓,只是时常往来而已。
朱怀天天禀聪明,自幼又笃志好学,考入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后,最崇拜其师吴公之。凡师之日常言行,及其讲堂所授,怀天皆牢记在心,纤细弗遗。而在朱怀天去世后,吴公之曾说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在)二十年奔走,学界不以(在)为无似,而始终不鄙弃者,无若怀天然。则怀天可谓(在)平生一知己矣!”[2]《序》4似乎这对师徒关系非同一般,不仅惺惺相惜,而且亦师亦友。
吴在,字公之,江苏金山县(今上海市金山区)人,秀才,曾留学日本。1912年,他与凌铭之创办上海南洋女子师范学校。先后任教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和北京清华学校。曾撰著《宥言》一册,共八篇,皆申论马克思主义。盖早年游学东瀛,恰逢日本共产主义大师河上肇登坛说法,国人周佛海等皆出其门。而吴公之衍畅其说,用庄子《在宥篇》之意,取名《宥言》。《庄子》曰:“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所谓“宥言”,即“吴在之说”也,以此自名一家之学。
1916年夏,朱怀天于省立二师二部毕业,随即应聘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以下简称县四高小)担任国文教员,始与钱穆为同事而兼舍友。任教未及一月,怀天忽得家讯,其母逝世。遂告假奔丧,旬日返校。夜寝,常常大哭而醒,或梦寐中大呼,由钱穆叫醒。连夜如此,累月皆然。而日间平居,却绝不流露出一丝哀容。钱穆自此始识其纯孝由衷,不免肃然起敬,乃与怀天相处益亲。年假后,怀天回校,携回佛教书籍六七种,皆其师吴公之为之选定。盖因怀天丧母心伤,故劝以读佛书自解也。
除了国文之外,朱怀天在县四高小还先后讲授算术、英文、修身、史地、理化、体操、图画、音乐、商业等高小课程,学生成绩无不斐然可观。其为教也,修己诲人,循循善诱。在学生眼中,朱老师“端庄宁静,中立不倚,超然有独立之志;精神活泼,思想开通,颇有世界观念”。其所授各科,同学皆能“自由发展思想”,“洞然知其所以然,而无稍有暗昧者。”如讲国文,“多选兼爱、平等、清心、悟道、克己之文,以及墨、老、庄、列诸子之书。至若东坡、渊明之文,先生亦未尝不择一二也。”如授历史,“重于学术之进步,忽于政治之优劣,曾慨然谓生等曰:政治者,万恶之源也!”[2]《事略》3闻其语,学生则知其平等、博爱、大同之心尽于言表。
朱怀天恣性诚笃,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上海罢市,远近城乡皆震动。县四高小全校师生结队赴四围乡村演讲,怀天热血喷迸,声泪俱下。其平日与人相处,“极和易,得人欢”。故钱穆乃知其论学时虽有偏激,然其本源皆发自于内心深处,称赞道:“惟当以一字形容曰‘爱’,爱国家,爱民族。虽言佛法,然绝无离亲逃俗之隐遁意。他日学问所至,必归中正可知。”[1]98
1919年冬,朱怀天返松江,忽得其在上海时旧同学邀其赴南洋。当时他已在县四高小任教几近四载,久蛰思动,遂决定于暑假后辞职前往。临行前,尝函告友人说:“我南洋行期已定本月二十八号,乘英国船 Paracy 号。”[2]《翰札》9忽以背部生疽而返家。初谓不严重,只自我催眠即可疗治,缓于求医,俗语“病来如山倒”,竟不治而卒于民国九年(1920)阴历8月3日,年仅二十三岁。
朱怀天喜好作诗,其日常起居琐节以及意兴议论之所到,往往见之于诗。怀天之诗,大率“疏淡有情而不拘拘于声律词藻”,日积月累,凡装订成六小册,约四五百首。与钱穆订交后,每成一诗必相示,又相与唱和,曾别录为《二人酬唱录》。据朱怀天1918年6月日记:“晨,《酬唱录》钞全,计得诗六十八首,词一首,凡我与宾四日常言行之可录者可记者,要不外是矣。声一又有诗来,作五首报之。”[2]《日记》7声一即钱穆之兄长钱声一。由此可知,朱怀天与钱氏兄弟皆有唱和。
朱怀天博览群书,多所颖悟,于佛学老墨,尤有研究。自谓:“问学十年,得于师授者寡,出于自发者众。”[2]《日记》5其师吴公之亦曰:“(在)于怀天谬有一日之长,然怀天之学固怀天所自得。(在)未能有以益之也。”[2]《序》3可见朱怀天为学重躬行,多偏于自学自得,他平日每读一书,辄有随笔。因此,钱穆编辑《松江朱怀天先生遗稿》(以下简称《遗稿》)时,特别重视读书笔记,认为由此可以窥见朱怀天为学之特色。
二 朱怀天与钱穆的交谊
关于朱怀天与钱穆的结识,在《师友杂忆》里有一段生动的记述。当朱怀天进入县四高小任教时,钱穆已在该校整整教了两年书,但此刻因病迟到。见到新室友后,钱穆对朱怀天说,学校出门两条路:一条左向通市镇,可以吃喝玩乐;一条右向通郊野,可以“散步塍间,俯仰天地,畅怀悦目”。你先来几天,大概已和同事们去过街市了。我通常一人右行。以后你喜欢往哪一边走?怀天立刻表示愿与钱穆一路走。两人遂相视而笑,结为知己。
两人每日黄昏前必相偕去校外散步,入夜则各自规定之读书时间毕,又同在院中小憩,方始就寝。钱穆与怀天均任国文一个班的作文课,时间同在周末,必须尽日夜批改完毕,俾可星期日偕出远行,或整日,或半日,择丛林群石间,杳无人处,或坐或卧,畅论无所不至,迄夜方归。
所谓亲职教育,是指以不同形式的教育方案和活动,教育或提供学习资讯给为人父母者、未来将成为父母者与幼儿实际照顾者,以提升父母亲角色的责任和教养子女的能力,成为有效能的父母,满足子女的发展需求,培育身心健康的下一代。
钱穆在教师休息室中有一张书桌靠西窗,坐南朝北。怀天的书桌在其座后靠南窗,坐东朝西。怀天之佛学书籍,钱穆亦就其桌上取来,一一读之,尤爱读《六祖坛经》。此当为钱先生治佛学之始。
过去我们常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1918年春,朱怀天的老师吴公之则给他俩送来了共产主义。据朱怀天1918年4月日记:“公之吴师既以《宥言》寄来,读未竟,宾四以其所思者作《辟宥言》三千言。读之与私心有所刺谬者,因更作《广宥言》一篇,约得六七千言,皆就《辟宥言》所言者更辟之。曰‘广’,为继公之言后也。此篇之作,亦所以示志也。初读《辟宥言》,拟即此而止,无所阐发,既成数段,亦拟作后以自省而不为宾四见。时宾四适以事归,既来校,问于《辟宥言》有所说乎?则嗫嚅不能出口,意不欲人见也,终以宾四之相问,有不能已者,因出示之。而附作意于篇首,庶以知其所由作也。”[2]《日记》5于是两位小学教师田间散步,讨论共产主义就成了一段时间的主题。朱先生赞成,钱先生反对,并且各自写了文章辩驳。你来我往,相争不已。
某日,钱穆告诉怀天:“君治佛书,又遵师说欣赏共产主义,然则他年将逃世避俗出家居山林为一僧,抑从事社会革命为一共产党人。一热一冷,一进一退,君终何择?”怀天曰:“君尊儒,言必孔孟,我恐兄将来当为一官僚,或为一乡愿。”钱穆言此四者都当戒惕,幸各自勉。
当时钱声一方肆意陆放翁诗,朝夕讽诵,亦常作诗自遣。钱穆与怀天乃休战言和,改为吟诗唱和。钱穆提议即景出题,比如当晚归,即以“林中有火”四字各作四言诗四章,以此四字,押韵如何?怀天回答好。自此又为五言、六言、七言,古今绝律,或出题两人同咏,或一人成诗,一人追和。如是积月,成诗日多。两人遂商量合成一集。最后,钱穆提议当可径名《二人酬唱录》,不仅纪实,“亦期我二人能不分彼我,同跻于仁。”怀天认为合意,书名遂定。
两人又读鲍芳洲催眠术书而喜之,曾召学生作练习。后见报载鲍芳洲在上海面授,只一周即可毕业。朱怀天遂前往学习,归来后勤练不止。而钱穆仍习静坐,尤喜天台宗《小止观》。其书亦自怀天桌上得之。1918年夏,钱穆辞去县四高小教职,复回私立鸿模学校任教,从而结束了与朱怀天的同事关系。次年,又转到后宅镇泰伯乡出任第一小学校长。两人虽不同在一校,但还是经常联系和交流。
朱怀天与好友交流的最后一首诗是《留悔》。诗中有句云:“亦尝悔发芒刺背,日记着之资省改。”钱穆认为:“悔可改、可除、可灭而不可留。悔之深痛,斯改猛速,不当云留悔也。”写一覆书当面交给了怀天。怀天嗟叹无言,不意“其遂成谶也”。没过几个月,朱怀天就病逝了。钱穆时在后宅,得到好友的噩耗后,遂赶往梅村,检其遗书,征集散佚,计划为怀天编印遗稿。其致吴公之书曰:“今者怀天死,穆忘其无似,拟为怀天刊印遗集。知怀天者终于知,不知怀天者终于不知。怀天固无求有人为之刊集,集亦恐无增损于怀天。然亦存者自了心愿,完结此一段因缘耳!”[2]《序》3
古人云:“一死一生,乃见交情。”为纪念亡友,钱穆整理遗稿并作序,其《序言》说:“余拟为怀天作一传,为其遗集作一序,又编抄其诗为《怀旧录》,入遗集中。不意初动手而咯血,又患脑衰,不能卒事。……匆匆草此,弁诸册首。传、序、录三者,以俟后日矣。”[2]《序》1遗憾的是,传、序、录此后终未写出,只留下了这一篇短序。
1.论著。朱怀天文章不多,但读书随笔颇有心得,故钱穆“屡向其家索取无有”,则已散佚不可得。今收入五篇读书随笔(《读法华经概论》、《读八宗纲要概论》、《读维摩经概论》、《读老概论》、《读庄概论》)和《会心录》(《书庄子后付友梅》、《书说苑后付漪人》、《读书怪语序》、《事理》、《论时两首》),共计十篇文章。
2.翰札。收入朱怀天与友生信函十六通。
3.日记。收入朱怀天1918年1月至1920年8月日记。由于朱怀天的随笔大都遗佚,钱穆乃特别重视其日记,认为日记“可以见怀天之为人;见怀天之为人,而怀天之为学,亦可识也”。可是朱怀天的日记,“皆奋笔疾书,字迹潦草,骤视之一字不识,细审乃可略诵”。钱穆手抄一过,“真不识者阙一空格,不识者多则删去一节,然已得十之八九矣!惟九年日记体例一变,字亦可认;五年日记最难读,故勿钞;六年已缺,始自七年至九年八月,凡二年有半。”[2]《序》1
4.诗词。朱怀天遗留下来的诗词不少,钱穆“读其诗三四过,皆可爱,取舍不得其道;又欲钞其诗入《怀旧录》。及既病计,不如仍此怀天生前十馀首者,或转足当怀天之意”[2]《序》1。故《遗稿》中,只收录了朱怀天生前自己选送梅村四小校刊的十二首诗词,而未见《师友杂忆》中所谓的“二人集”。
5.《广宥言》。收入朱怀天《广宥言》全稿。此文作于1918年5月3日,约计八千馀字,含自序和论辩二十则(或二十二则)。
《遗稿》以“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校友会”名义印行,铅印平装,一百一十二面,由无锡锡成印刷公司代印,非卖品。除学校师生外,并分赠国内各图书馆。虽然存世稀少,获睹匪易,但终存天壤,朱怀天先生的著作,也总算保留下来了一部分。笔者见到的一册,即属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藏书,登记注册于1921年9月27日。尤可痛惜者,朱怀天约计四五百首的诗稿,从未刊布,至今下落不明;而日记则由钱穆保存。对日抗战时,钱家藏书尽失,好友日记亦在其中。苍海桑田,物是人非!朱怀天去世五十七年后,已是耄耋之年的钱穆先生开始写作《师友杂忆》,遥望故国,知己何在?并深情地回忆了他青年时代与朱怀天的交往。“回念余自一九一二年出任乡村教师,得交秦仲立,乃如余之严兄。又得友朱怀天,乃如余之弱弟。惟交此两人,获益甚深甚大。至今追思,百感交集,不能已”。[1]103
三 《师友杂忆》的几点补正
朱怀天自谓:“尝自怪天下之大,知我者何小也。夫知己一为难,今我于松也,幼时□□亦曾一度得人矣。沪也有吴师公之,锡也有钱子宾四。使我易职一地,即得一人。窃自幸知己之最易求矣,特恐后日之无此顺利耳!”[2]《日记》11无非是慨叹知己难求,自幸此生已得两位知己,即“沪也有吴师公之,锡也有钱子宾四”而已。
一般而言,学者个性和思想的成熟,其实来源于多方面的影响,有一个长期的发展积累过程。钱穆自1912年出任乡村教师,到1922年秋转入无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任教,整整十年时间,对其影响至深且巨者,无过于秦仲立和朱怀天,也难怪他会说:“余与怀天三年之生活,如水乳之交融。于怀天之人中有我,于我之人中有怀天。盖此二人者,几乎相渗透而为一人矣!怀天死,我之一部之渗透于怀天之人之中者,亦从而死。我犹生,则凡怀天之一部之渗透于我之人之中者,亦犹生也。”[2]《序》2轻视或无视这种存在及其重要性,将会使我们虽面对钱穆先生浩瀚的精神世界,却对其中的秘密失之交臂。一方面,我们只有通过阅读朱怀天唯一流传下来的著作文本——《松江朱怀天先生遗稿》,探究朱氏如何使钱穆“获益甚深甚大”,对于深刻认识钱穆早期个性特色的养成与学术思想的形成,当不无裨益。另一方面,尽量厘清朱怀天与钱穆的交往过程,才能更好的“知人论世”。
首先,关于朱怀天的学历,目前有两种说法:第一,《师友杂忆》称其“新毕业于上海第一师范”,显系无据。第二,《遗稿》中由朱怀天的学生顾荫生撰写的“生平简介”,明言朱老师“在省立二师二部卒业”,并被多种相关材料佐证。众所周知,在北洋政府时期上海隶属于江苏省,按教育部规划,江苏省被统一划分为九大学区,上海为第二学区,所以在今上海市黄浦区尚文路设立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而江苏省立一师、省立三师则分别设在苏州和无锡。
其次,《遗稿》明确记载朱怀天死于民国九年(1920)阴历8月3日,年仅二十三岁,除了《日记》和《翰札》提供了最为重要的信息之外,书中还有三份材料可为佐证,即《朱怀天先生事略》(两篇)和《生平简介》,均持此说。反向推算,自然可以知道他比钱穆年轻三岁,而非《师友杂忆》所言“怀天较余年轻一岁或两岁”。
再次,关于《二人集》,完整的名字应为《二人酬唱录》。我们姑且不谈《二人集》是否收入后来所谓的《朱怀天先生纪念集》(以下简称《纪念集》),无论是《师友杂忆》,还是《遗稿》,均称“编”而非单独“自印”或“发表”,此无庸赘言。然自罗义俊先生《钱宾四先生简谱》将其编入1919年“著述”之列:“诗集,自印本,与朱怀天合著。”此后,郭齐勇、汪学群、陆玉芹等学者不察,竞相沿用,迷而不返。
最后,关于《纪念集》与《遗稿》的关系,恐怕最值得玩味。根据《师友杂忆》的记载,《纪念集》主要有日记、诗词(“二人集”)、《辟宥言》和《广宥言》等四部分,似乎是两人的著作合集;而《遗稿》则为论著、翰札、日记、诗词、《广宥言》等五部分,全部都是朱怀天的个人著作。但两书类目非常相似,惟《遗稿》明显比《纪念集》多一些内容而已。假设两书都存在,应该在朱怀天去世后一两年内出版,不可能拖的太久,但目前的情况是:一者下落不明,线索全无;一者已经找到,就出版于朱怀天去世周年纪念之际。如果《纪念集》在《遗稿》之前出版,为什么《遗稿》中又不见任何蛛丝马迹?如果《纪念集》在《遗稿》之后出版,有这个必要吗?但目前缺乏强有力的证据,也不好妄测。最近,笔者有幸读到了钱穆在1935年之前写的一篇自述短文《苦学回忆》,其中有一段文字正好涉及到这部《遗稿》,才让我恍然大悟。文曰:“时松江朱君怀天,与余同事同学,上课以外,两人之生活如一人,卧同室,朝夕同卧起,一书轮流同读。散步则同行,相互为讨论。朱君年少于余,聪明过余,而体质不如,惜不永年。至今思之,深为悼怅。余为编其遗文,刊《松江朱怀天先生遗集》一册,今北平各图书馆中或有之。”[3]“遗集”即“遗稿”,字虽错了一个,但肯定是指同一部书。不论《纪念集》和《遗稿》孰先孰后出版,这里为什么单单只说《遗稿》而不及《纪念集》?它还给我另一个启示:《遗稿》本身也具有“纪念”的意义,因此,所谓的“纪念集”与这部《遗稿》才会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据此是不是可以断定:钱宾四先生《师友杂忆》中所说之“朱怀天先生纪念集”,其实就是《松江朱怀天先生遗稿》。
由于学者普遍都相信世间存在过一部“朱怀天先生纪念集”,所以根据《师友杂忆》的相关文本,也产生了种种猜测,尤其是关于该书的内容和出版时间方面,各家说法五花八门,乱做一团。1992年出版的《钱穆纪念文集》,是笔者见到的最早的两种说法:其一,罗义俊先生《钱宾四先生简谱》将其编入1920年“著述”之列:“《朱怀天先生纪念集》,自印行。”[4]309其二,胡美琦女士《钱宾四先生著作(专书)目录》则将其列入1919年:“自印,分赠当时国内各图书馆收藏。”[4]327如果仅仅是出于猜测,前者尚可说得通,后者则完全莫名其妙,无异于朱怀天生前之“自撰墓志铭”。1994年,李木妙先生《国史大师钱穆教授生平及其著述》中“钱穆教授年表”1919年一条:“是年乃钱氏读书、静坐最专勤的一年,又与朱怀天合撰《二人集》诗选,后合‘辟宥言’、‘广宥言’、‘续辟宥言’、‘续广宥言’等共八篇为《朱怀天先生纪念集》。”[5]105又将其写入“钱穆教授著作目录”中:“《朱怀天先生纪念集》,上海:自刊本,民国8年初版。”[5]120不仅延续了胡女士的说法,而且增加了出版地“上海”。试问:他能拿的出证据来吗?第二年,李先生正式出版《国史大师钱穆教授传略》(即前述著作的修订版)时,他或许得到了什么新材料,于是“钱穆教授年表”1919年一条,文字则改为:“是年乃钱氏读书、静坐最专勤的一年,他又与朱怀天合编《二人集》诗选,后又辑‘辟宥言’、‘广宥言’、‘续辟宥言’、‘续广宥言’等文。”[6]157并在“钱穆教授著作目录”中删除了“朱怀天先生纪念集”。1998年,台北联经版《钱宾四先生全集》第五十三册收入《〈松江朱怀天先生遗稿〉序》,文末标注写作时间为“民国九年七月”,让人忍俊不禁。因为此时朱怀天犹在人间,何来“遗稿”之说?权威的说法尚且如此,其它的说法就不一一列举了。
此外,通观《师友杂忆》全书,钱穆在大的时间把握上,已经是非常精准了,时间标记都显而易见,很少有问题,但个别情况也会出现交叉现象,极易造成读者误读史料。比如,第五节谈到钱穆与朱怀天阅读《宥言》的往事时,还未结束,但为了说明怀天“恣性诚笃”,又有意穿插了一段他在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下乡演讲的经历,读者稍有大意,就会以为接下来的内容发生在五四运动之后,再继续读下去,当第六节开头出现“时为一九一八年之夏季”这个时间标记时,甚至还会怀疑钱穆“老迈昏聩”、“时间错乱”。2011年新出版的《一代儒宗——钱穆传》一书,在此处就犯了类似的问题[7]31,其实两人研讨共产主义之事发生在1918年4-5月间,而非1919年4月;若是后者,那时宣扬共产主义之声早已洋溢中土,如果钱穆还要说:“时中国共产主义尚未大兴,而余两人则早已辩论及之矣。”则风马牛不相及,无具体所指了。
综上所述,《师友杂忆》中有关朱怀天的记述,至少有四点讹误可供补正:第一,关于朱怀天的学历,他毕业于“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而非钱穆所说的“上海第一师范”;第二,关于朱怀天的年龄,他出生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比钱穆年轻三岁,而非“怀天较余年轻一岁或两岁”;第三,关于《二人集》,完整的名字应为《二人酬唱录》;第四,关于《朱怀天先生纪念集》,此全系钱穆记忆偏差,而所谓的“纪念集”,实为《松江朱怀天先生遗稿》。此外,刘桂秋《新发现的钱穆佚文〈与子泉宗长书〉》、薛巧英《钱穆〈师友杂忆〉订误补正》、张京华《钱穆先生的一种集外佚著》等文,均指出《师友杂忆》中部分章节存在某些记忆不够准确之处,态度严谨,足资考辨。很显然,钱穆《师友杂忆》中确实存在这类似是而非的表述,亟待发覆补正者还有不少,不容回避,此亦当代研治钱学者之一大责任。
[1] 钱 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M].北京:三联书店,1998.
[2] 朱怀天.松江朱怀天先生遗稿[M].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校友会自印本,1921.
[3] 道 明.钱穆先生的“苦学回忆”[J].教育短波,1935(26).
[4] 政协无锡县委员会.钱穆纪念文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5] 李木妙.国史大师钱穆教授生平及其著述[J].香港:新亚学报,1994,17.
[6] 李木妙.国史大师钱穆教授传略[M].香港: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
[7] 徐国利.一代儒宗——钱穆传[M].武汉:湖北人民出 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