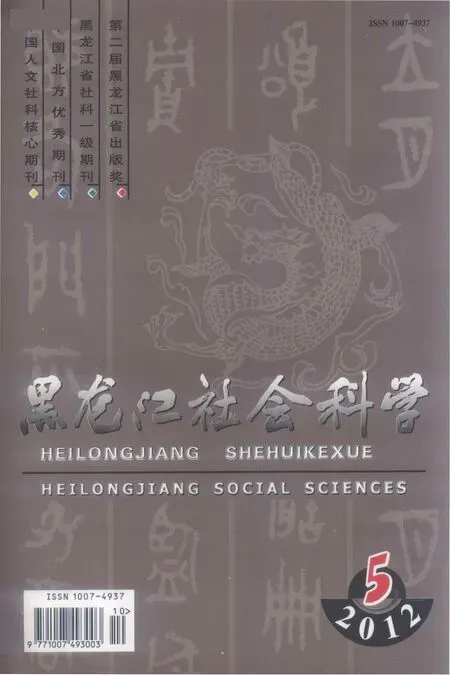现代社会福祉概念与中国特色社会福利制度框架建设研究
2012-04-13刘继同
刘继同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北京100191)
一、中国社会建设、社会建设目标与新型现代社会形成
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首次明确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由此拉开中国社会建设序幕,标志中国进入社会建设时代,构建和谐社会成为最显著的时代特征[1]。中国社会建设目标是“建设新型社会”,建设新型社会的目标是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前提和社会和谐主要内容是“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意味着和谐社会实质是“中国版福利社会”,凸显福利在社会和谐中的地位[2]。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目标,又是构建和谐社会和改善民生的主要范围内容,还是构建和谐社会最基本的制度化途径,典型体现和谐社会的“福利”属性和社会政策目标。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看,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是狭义社会现代化的核心目标、主要内容和手段,标志新型现代性社会和社会结构的形成。社会现代化的普世主题和永恒的主体是改善民生,谋求公平正义,提高全民生活质量,改善全社会总体社会福利水平,创造幸福美好新生活[3]。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社会环境、权力结构、法律制度、人口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阶级结构、文化生活及国际地位均发生史无前例和翻天覆地的结构性变化,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和国民生活正在经历全面、系统的“大转型”,新型现代社会的轮廓已清晰可见[4]。
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建设新型现代社会范围内容、过程和途径主要涉及生态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五大亚体系建设的社会过程和互动关系模式。五大建设之间的关系并非是“水平排列”,也非“毫无关系”,而是存在内在逻辑与结构关系。政治文明建设的主题是社会权力分配和确定国家的政治制度,为社会秩序奠定“政治基础”。以物质财富生产和积累为主的经济建设是社会建设的“物质手段和经济途径”,为社会生活提供物质基础。生态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是社会建设环境、内容、过程和结果的“外在表现形式”,只有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狭义社会建设才是社会建设的“目标和内容、主体和主题”,处于社会建设核心位置。这意味新型现代社会建设性质是中国版“民生福利型”社会建设,意味中国迈向社会福利和社会福祉时代,发展社会福利制度与社会服务体系的时机已经成熟。
二、中国社会福利时代来临与现代性社会福祉概念框架
2010年是中国儿童福利元年、家庭福利元年、残障福利元年、老人福利元年和总体性社会福利元年,标志中国进入社会福利、儿童福利、家庭福利、残障福利和老年福利时代,标志中国进入社会政策、社会立法、社会治理、社会服务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时代。中国社会福利时代来临的重要标志是“社会福利和社会福祉”概念日趋流行,相关的研究激增。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福利研究发展脉络与结构变迁特征是,中国社会福利“从政府定位”转向“民生需要为本”的定位,“发现”中国已形成社会福利学科领域和基本体系[5]。但是,1949年以来,由于在革命和“左倾”意识形态盛行处境下福利“负面形象”的社会建构,人们普遍将“福利国家”等同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大陆长期匮乏社会福利概念与理论研究。1986年以来,中国喜欢使用“社会保障”概念,社会福利成为社会保障组成的“小”概念,城市“单位型”福利制度盛行。由于中国社会福利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长期严重滞后,中国社会“有社会福利实践,但无福利理论研究”的原始落后状况突出反映在福利概念上。目前,社会福祉、社会福利、社会政策、社会服务、社会保障、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公益、慈善、社会工作等诸多核心概念混杂一起,混用的现象十分普遍,各个概念之间边界不清[6]。甚至包含公共政策与公共服务、社会政策与社会服务,以及公共政策、社会政策与福利间关系。毫无疑问,核心概念的大众理解、学术理解、行政理解和社会文化建构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因为核心概念社会理解与社会建构直接涉及相关社会制度建设、政策导向和资源分配模式。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结构、社会需要与社会生活发生重大变迁,其中最重要的社会结果是,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战略重点已由“以社会保障制度为重点”,升级为“以社会政策与社会服务为重点”,健康、教育、住房和就业服务成优先领域。这意味中国社会福利制度正经历全面性、系统性和结构性历史转型,正由传统社会福利制度向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结构转型,如何重构现代社会福利概念框架和制度框架议题应运而生。
本文根据世界各国普遍遵守的“国际惯例”和西方“福利国家”制度建设的历史性经验,从社会福利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角度,首次建构现代社会福利概念框架,目的是清晰地阐述社会责任的社会划分机制,妥善处理国家、市场与市民社会三个部门之间的关系,科学划分国家责任、市场责任(企业责任)、民间社会责任(社区责任、家庭责任)和个人承担社会责任、权利、权力、义务之间的社会边界,区分公共政策、社会政策与福利政策之间的制度性差异,为政府职能转变,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创新,尤其是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社会建设,创建中国特色福利社会和福利制度框架建设,奠定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和社会福利理论基础,以推动中国社会福利制度与服务体系建设。需要指出的是,任何理论概念框架都是个广泛的大概念,其范围内容常远远多于制度框架。因制度框架与服务体系是“现实和实际”的,核心概念框架与思想是“理论和理想”的状况。而且,福利理论概念框架中所表示的社会福利制度中各种亚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互动模式也是高度简约化和理想化的,社会福利制度框架内部“实际”的运作机制和互动关系模式应复杂多样,并且处于永远不断的发展变化过程之中,凸显现代社会制度与社会生活复杂性。最为重要的是,现代社会福利概念框架与制度框架无法涵盖“隐形和看不见”的“社会福利文化”,社会福利文化恰是社会福利概念框架与制度框架的灵魂和“看不见的无形之手”[7]。这意味社会福利概念与制度框架是正规与非正规、有形与无形、现代与传统因素的“混合体”。
现代社会福利概念框架主要有三类服务组成:一是最高层次社会福祉,即中文的幸福感,它主要由主观福利和客观福利两部分组成,主观福利服务部分已超越政府职责和责任范围。二是正规服务,正规福利主要是指由政府、企业和民间社会提供的制度化的社会服务活动。三是传统的非正规福利服务,主要是各种民间慈善、公益事业与社会互助、社会利他活动。三类服务覆盖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既有精神情感领域的服务,又有物质生活领域的服务。三类性质服务组成的社会福利概念框架说明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是全面性、整体性和全人的。现代社会福利概念框架的层次结构分明,社会福祉处于人类生活的最高层次,社会利他取向的各类社会互助处于最低层次,中间又细分为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等若干社会福利体系层次。社会福利概念框架中不同层次结构是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特征之一,反映福利结构分化程度。公共服务和传统非正规服务组成福利制度中“社会基础结构设施体系”(social infrastructure)。所谓社会基础结构设施体系泛指确保社会生活与社会有序运行的所有社会安排与社会活动。社会基础结构设施体系特征是有些体系与活动处于社会生活的“地下”,是“看不见的”。现代福利概念框架显示,以社会救助与社会保险为主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框架最基本的部分,主要针对所有劳动者和各式各样贫困人群,是确保社会生活的社会安全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人需要结构发生重大转变,以健康、教育、住房、社会保险需要和福利服务为主体的“社会服务”需要已成最主要的需要。在全球化背景和全球化治理处境下,全球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已成人类社会重要议题。
三、社会结构转型、福利国家形象与社会治理模式转型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环境、社会结构、社会需要与社会制度发生重大结构转型,以经济革命和狭义社会生活革命为主体的“社会革命”,改变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模式,全面性、系统、深刻、快速性和结构性的社会结构转型过程已创造一个崭新的新型现代社会。新型现代社会的实质是社会结构现代化,核心是现代社会体系与制度框架形成的发展过程。首先,中国社会哲学、现代社会观类议题应运而生,成为社会政策与学术研究的基础问题。自20世纪初“社会哲学”传入中国后,经过漫长的沉默之后,90年代又在中国再次兴起。中国新型社会哲学主题是“和谐社会观”,和谐社会观验证社会哲学“社会病理学”基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哲学基石由“斗争哲学”变为“和谐哲学”不仅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具体来说,中国现代社会哲学、和谐社会观说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框架发生根本性转变。长期以来,中国社会中“国家大、社会小”,国家“覆盖、等同”社会的状况发生革命转变。
国家由“凌驾”社会之上转为社会“组成部分”,国家、市场、市民社会三部门理论产生。社会福利、社会建设、社会服务、社会管理、社会治理、社会公平和社会秩序类议题产生。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商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改革开放政策与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转型等多种国际、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性力量的共同影响下,尤其在现代化背景下,中国社会基本完成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结构性转型[8]。中国社会基本实现由一个传统、封闭、稳定的社会向现代、开放、高风险社会的转变过程。同时,各式各样和形形色色“现代社会问题”应运而生,如失业、贫困、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保险与风险防范、环境污染、教育不公、传染病和公共卫生、住房福利与家庭问题等。如何有效防范、及时回应和用制度化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满足人们不断提高的社会需要,改善生活质量和社会总体福利水平,成为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创新的主要工作目标和任务。
新型现代社会形成的最主要标志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结构性转变,主体是国家功能角色转变,主题是政府职能角色地位作用和社会治理方式转变,实质是政府承担责任范围的扩大,关键是欧美国家的主要职能角色和国家形象通常由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血缘国家”开始,经由奴隶社会的“宗教军事城邦国家”和“奴隶帝国主义国家”,中世纪的“宗教和封建化国家”,近代的“经济和工业化国家”,当代的“民主政治和福利化国家”,转变为目前的“科技军事和社会性国家”形象,说明“福利国家”是所有工业化与现代化社会发展必由之路[9]。这意味“福利国家”是所有现代国家性质宗旨、职能角色和国家形象演变的历史发展阶段,凡是走上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国家,福利国家职能角色与形象是社会现代化的核心。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尤其是欧美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尚在蔓延背景下,中国是否需要大力发展社会福利?国家在福利制度建设中应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作用?如何妥善处理“福利国家”与“福利社会”的关系?中国是否必然会走向“福利国家”之路?中国应建设什么样的福利国家?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福利国家与福利社会等议题产生。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发展的历史经验证明:现代民族—主权国家是社会现代化的历史产物。现代国家的基本职能是社会发展规划、促进经济发展、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社会治理。只有“福利国家”形成后,才能形成“福利社会”。没有福利国家的福利社会是难以想象的。现代国家的职能范围不断扩大,由关怀穷人、儿童和家庭、病弱者、伤残者、老人、失业者,扩大到所有公民,政府承担社会责任范围随之不断扩大,形成由“摇篮到墓地”的福利制度。社会福利制度与福利国家形象成为现代化国家建设的主要内容、基本途径和发展方向。纵观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尤其是1949年以来变迁过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经历了“政治中国”→“经济中国”→“福利中国”的转变,福利国家形象建构成时代主题。简言之,政府职能转变、社会问题丛生、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创新殷切呼唤“社会福利共识”。
社会现代化的核心和主题是在现代开放社会中,在不确定、风险日益增强的社会处境中,如何通过制度化方法,防范和预防社会风险,化解社会矛盾,满足社会需要,回应社会期待,例如推动政府职能角色转变,建构福利国家形象,大力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扩大社会治理的社会基础,建立现代社会稳定与社会治理机制,确保社会公平、秩序和质量。这是所有现代国家与现代社会面临的普遍问题,直接关系政党、政权的合法性和国家权威性,这对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社会风险、结构性紧张状况日益凸显,维护社会稳定高于一切和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的转型期中国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理论、政策意义和全球意义[10]。从广义现代社会、社会问题、社会需要、社会建设、社会秩序、社会治理与稳定机制角度看,民主政治、公民权利、法治建设、结社自由、公民参与、立法、行政、司法间的权力制衡,既是“政治性”的社会稳定机制,又是最高级的社会稳定机制,还是最隐蔽的社会控制手段。政治善治是社会治理和社会善治制度前提,是政治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最高层次[11]。现代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例如产权制度、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资本市场、投资和价格体制,是确保经济生活秩序和经济交易行为成本最小化,经济效益与个人福利最大化的经济机制。西方国家历史经验证明,发达完善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是“最好和最高级”的社会稳定机制,原理是市场竞争、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和供需决定交易价格的“看不见的无形之手”发挥作用,形成“社会问题个人化”的社会稳定和社会治理机制,从而防范大量潜在的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和谐。需要指出的是,与西方福利国家的“政治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建设”的时序顺序截然不同,中国特色发展模式、时序是“经济发展→社会建设→政治改革”,发展质量有待历史检验[12]。
社会福利制度与社会服务体系建设是现代社会治理中社会性和文化性色彩最浓的机制,主要通过社会投资、社会预防、社会参与、社会服务、解决社会问题和促进社会发展等功能,发挥社会安全阀、社会稳定、社会治理与社会发展等作用,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制度模式。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以来,世界各国现代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如何解决社会问题,防范社会风险,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控制、社会稳定、社会治理与构建社会和谐目标。在济贫法时代,社会救助体系的“社会控制与社会管理”功能远远大于社会服务性功能。社会救助体系的主要功能是“规管穷人”,而非“服务穷人”,目的是通过控制维持社会秩序。19世纪晚期德国建立社会保险体系后,通过社会保险的机制“预防社会性风险和社会投资”,以解决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老弱病残孕、鳏寡孤独和失业、工伤时基本生活和发展问题[13]。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闻名的贝弗里奇报告描绘现代福利国家制度框架与社会服务体系,以医疗卫生服务、基础教育、住房服务、家庭福利服务和就业支援服务等为主的“社会服务”,在社会保险体系之上,国家和社工开始为全体国民提供全民性、专业化与个性化社会服务。比较而言,全民性、专业化与个性化社会服务的“全人发展功能和社会福利功能”最突出[1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福利国家体制、民主政治体制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有机结合起来,资本主义社会与国家体制发生革命性转变,“民主—市场—福利资本主义”成为典型形态[15]。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救助与社会保险“体系框架”基本形成,以社会救助与社会保险体系为主“社会保障制度”成为中国社会福利制度框架的战略重点与优先领域[16]。目前,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趋势有二,一是中国逐步形成“民主—福利—市场社会主义”体制,另一方面,以医疗卫生、教育、保障住房、老弱病残为主的“社会政策框架与社会服务体系”形成,专业化与个性化社会服务体系成中国社会福利制度框架的战略重点与优先领域[17]。简言之,中国社会转型、福利国家形象建构与社会治理模式转型共同聚焦现代社会福利制度。
四、福利现代化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福利制度框架建设
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转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统筹城乡社会协调发展,福利制度改革发展,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创新和构建中国版福利性和谐社会伟大历史实践,不约而同聚焦“社会福利现代化”议题。狭义社会现代化的主体与主题是社会福利现代化。福利现代化既是个基础性福利理论与福利政策议题,又是个福利制度化建设与历史性议题。综观世界各国历史发展进程,先后形成八大类型的社会福利制度模式,反映制度建设多样性。一是英国以公民社会权利为基础的“社会服务型福利国家”,这种模式主要盛行英联邦国家。二是德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以公民社会权利为基础的“社会保险型福利国家”,这些国家普遍实行全民健康和养老保险制度,并为应对老龄化创建长期照顾保险制度。三是美国为代表和唯一特例以公民社会权利为基础的“市场化机制提供社会服务模式”。四是以挪威、瑞典、丹麦为主将公民社会权利和市场机制有机结合的“北欧福利模式”。五是拉丁美洲以西班牙和欧洲福利制度为蓝本,体现本土社会特征的“拉丁美洲模式”。六是亚洲主要是东亚、东南亚国家,以殖民地历史经验为基础的“东亚社会福利模式”。七是以原苏联为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如中国、越南、古巴等国的“社会主义福利模式”。八是以非洲国家为主体,通常以其欧洲宗主国社会福利制度为蓝本的“非洲社会福利模式”。不言而喻,所有类型的福利国家、福利社会与社会福利制度均处于不断的发展变迁过程中。如果从“福利现代化”角度看,只有英国、西欧和北欧福利国家基本实现社会福利的现代化。
什么是福利现代化、福利现代化主要标准是什么,是个尚无人涉足的基础理论政策议题。笔者以为,福利现代化是福利价值观、福利政策、福利组织、福利体系和制度现代化过程。实际上,某种意义上说,福利现代化的衡量标准和测量角度是个多层面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具体来说,某个国家与社会的福利现代化程度与所处发展阶段可从如下的角度衡量和测量。首先,社会福利概念、理念、观念的现代化,这是社会福利制度现代化中最重要的价值基础。社会福利概念、理念和观念现代化程度主要体现在人们对福利概念内涵外延的社会认知上。其次,社会福利制度与社会服务体系性质已清晰区分为公共服务、社会服务与社会救助服务,慈善、公益、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社会福利、社会福祉间错落有致,传统非正规服务、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社会福利制度与社会福祉体系之间形成统一制度框架。第三,社会福利制度理论基础是公民社会权利和国家福利责任理论,而非父权式权威、恩赐。英国著名学者马歇尔将公民权利分为公民政治权利、民事权利和社会权利三类,政治权利主要适用政治生活,民事权利主要适用经济生活,社会权利主要适用狭义的社会福利领域[18]。责任的社会划分和国家、公民权利、责任、义务的社会划分是社会权利和国家责任理论内涵,社会需要和人类需要满足的理论是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结构分化运行机制的理论说明[19]。第四,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目标是全民生活质量的改善,是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福祉和谐,是人的全面发展,是经济社会的协调均衡和可持续发展,是为全民缔造幸福美好的新生活,而不是单纯、畸形的经济增长,单纯、畸形的物质福利,单纯、畸形的国家发展和权力崇拜。第五,社会福利制度的服务对象是全民,而非局限于某些困境人群、弱势群体和劣势群体,社会福利制度范围广泛,既包括公共服务、社会服务和针对老弱病残孕鳏寡孤独的个性服务,又包括主要适用劳动人群的社会保险,主要适用贫困人群的社会救助,还包括慈善公益事业。第六,社会福利制度个性化与社会服务组织专业化,专业社会工作者扮演主要和核心角色,社会福利“法治化”程度较高,社会福利行政管理体制是整合一体化,而非部门化分隔[20]。第七,社会福利现代化的最主要衡量指标是公共财政制度现代化状况。现代公共财政制度框架结构分化为纯粹公共财政、以社会服务为主公共福利财政、社会救助和应急财政三类。
五、简要讨论与基本结论
中国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发展试验,战略目标是建设世界历史上人口数量最多、体系规模最大和福利性的新型现代“和谐社会”,其制度建设难度之大、社会复杂程度之高,社会矛盾冲突之激烈和对全世界社会影响之深远,都是史无前例和难以想象的。在全球化和中国和平崛起背景下,中国应建设什么样的新型现代和谐社会已非中国“内政和国内事务”,是构建“和谐世界”和“全球治理”的最重要部分[21]。
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社会结构转型与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社会结果是,国家形象由政治国家,经由市场国家和经济国家形象,开始向福利国家形象转变,中国特色福利国家形象呼之欲出。中国新型现代和谐社会建设面临的最主要挑战是,如何将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狭义的社会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四大领域有机统一起来,妥善处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间关系,如何在政府统治和社会治理权威严重削弱,市场经济机制与体制具有浓厚政治经济学特征,传统文化价值和道德观念面临市场严峻冲击,社会结构性紧张状况与矛盾冲突愈演愈烈的背景下,一方面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框架建设的宏观社会环境、主客观条件亟待改善,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框架建设迫切需要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支撑。这既是中国社会福利时代来临和现代社会福利概念框架形成背景,又是中国社会结构特征。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框架与构建和谐社会实践,创造独特的“转型福利学”。
本文首次界定现代社会福利概念框架范围内容和各种亚福利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模式,为社会建设、建设社会和调整国家—社会间关系,为探寻社会治理的最优模式与最佳途径,为中国特色社会福利制度框架设计奠定理论基础,实质是描绘社会建设“路线图和时间表”,指明社会现代化和建设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清晰界定国家、市场与民间社会责任边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实践说明:福利基础理论研究状况决定福利制度框架的建设状况。总体来说,现代社会福利概念框架与制度框架主要由正规服务与非正规服务两大部分组成,正规服务主要由公共服务、社会服务、社会救助和应急救援四类服务组成,政府是责任主体,非正规服务由自助、互助、慈善、公益四类服务组成,社区、企业、家庭和个人是责任主体。与此同时,现代正规社会福利概念框架主要由政治福利、经济福利、狭义社会福利和文化福利四方面组成,共同组成现代正规福利体系和服务,是现代国家福利制度最主要组成部分。世界历史经验证明,以人为本和充满人文关怀的社会文化和社会环境,尤其是社会和谐状况,通常是以现代社会福利制度为基础的。这意味着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与社会服务体系,是中国社会福利时代真正“国家最高利益”与真正的“新国策”,重要性怎样强调都不过分。
最为重要的是,以现代社会福利概念为基础,本文首次界定中国特色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框架范围内容与亚体系之间层次结构,为构建福利化和谐社会奠定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基础。目前,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建设已到社会福利制度框架设计的历史阶段,社会福利现代化的内涵外延、现代“福利国家形象”建构是福利性和谐社会建设必由之路,政治中国→经济中国→福利中国战略转型的主客观条件已成熟,“社会福利共识”已经形成,中国社会发展与制度创新已到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期,总体制度框架设计成为最重要工作。因为社会制度框架与国家责任承担的设计质量、总体质量决定总体性的社会质量与生活质量。中国改革开放实践说明:制度框架设计和顶层设计至关重要,发展方向错误的社会成本难以估量,狭义社会福利现代化的内涵外延与“福利国家”是福利性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由之路。像市场经济机制一样,社会福利制度功能作用角色也是“中性和工具性”的,关键是制度安排。欧美主权债务危机说明:“现代”福利概念与制度框架并不一定等于“好”的社会福利制度。
[1]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 〔英〕诺曼·巴里.福利[M].储建国,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4] 〔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冯刚,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5] 彭华民,万国威.从沉寂到创新:中国社会福利30年学术轨迹审视[J].东岳论丛,2010,(8).
[6] 陈永生.“社会福利”概念的探析及我国社会福利模式的选择[J].学术动态,2009,(1).
[7] 毕天云.社会福利场域的惯习:福利文化民族性的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8] 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9] Wilensky,H.L.& Lebeaux,G.N.Industrial Social and Social Welfare:The Impact of Industrialization on the Supply and Organization of Social Welfare Serv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M].New York:The Free Press:1965.
[10] 刘少杰.改革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化解风险型社会矛盾[J].科学社会主义,2010,(3).
[11]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2] 韩冬雪.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社会建设—政治改革[J].探索与争鸣,2010,(5).
[13] 劳动部保险福利司.我国职工保险福利史料[G].北京:中国食品出版社,1987.
[14] 〔英〕贝弗里奇.贝弗里奇报告: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
[15] 〔丹麦〕哥斯塔·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M].苗正民,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16] 胡晓义.走向和谐:中国社会保障发展60年[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9.
[17] 王思斌.社会政策时代与政府能力建设[J].中国社会科学,2006,(4).
[18] 〔英〕T.H.MARSHALL.公民权与社会阶级[J].刘继同,译.国外社会学,2003,(1).
[19] 〔英〕莱恩·多亚尔,等.人的需要理论[M].汪淳波,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20] 〔日〕桑原洋子.日本社会福利法制概论[M].韩君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1] 潘胜军,李禄俊.提升国家形象 构建和谐世界[J].社科纵横,2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