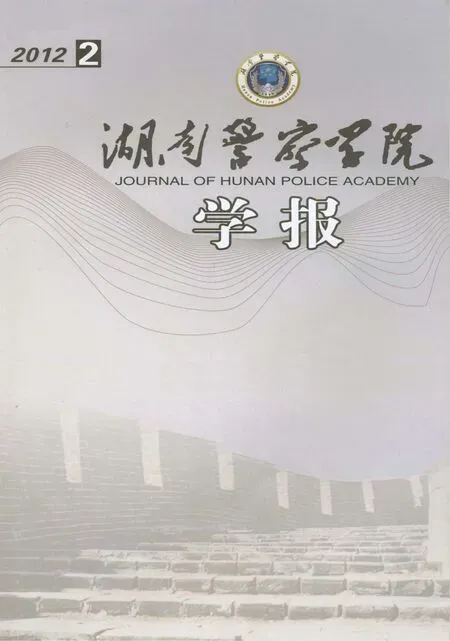国体政体之分的两种版本
2012-04-12涂四益
涂四益
(广东商学院,广东 广州 510320)
国体政体之分的两种版本
涂四益
(广东商学院,广东 广州 510320)
大陆学界一般认为国家的阶级性质为国体,政府的组织形式为政体,台湾地区的学术界则认为国家采取共和制抑或君主制为国体,采取立宪制抑或专制统治为政体。这两种对于国体和政体的区分都有逻辑上的困难。政体不过是对于政权典型特征的概括,国体、政体概念之分,应该予以抛弃。
国体;政体;国家结构形式
“体”的意思,为根本、本性,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体”。以“国体”、“政体”、即国家或政府的根本来翻译英文government和reign,其实深得信达雅之妙。——在西方、特别是欧洲大陆,国家(state)往往就是指政府。我国原本将国体和政体作为同义词使用,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第一次将“国体”和“政体”区分开来使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则赋予这两个词以新的含义。时至今日,台湾学术界的主流仍然沿袭梁启超的用法,而在大陆,国体问题已被口号化,政体问题则在毛泽东意义上的“政体”含义和政体原初所表示的政府的根本和本性的含义这两极之间摇摆不定。
一、梁启超意义上的国体和政体
蔡锷首义的“护国运动”,所护之“国”(共和国)正基于梁的国体概念。护国战争前云南方面向总统袁世凯所发第一封电文之“自国体问题发生,群情惶骇,重以列强干涉,民气益复骚然”[1](P1)、以及战争后蔡锷为梁启超《盾鼻集》所作序之“今国体既不失旧物”,其中的“国体”都是梁启超意义上的国体。
梁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中说:
夫立宪与非立宪,则政体之名词也。共和与非共和,则国体之名词也。[1](P86)
按照梁意,是采取君主制还是采取共和制,属于国体问题;国家是否立宪,即是否采取限制最高统治权力的有效的制度,属于政体问题,国体比政体更具根本性。是否存在最高统治者的世袭制,一般被认为是区别君主制与共和制的根本标志,但梁认为,这一标志——至少在袁(世凯)已享有超级总统权限的体制下——并非关键:
夫君主共和之异,亦在元首继承法而已。此种继承法,虽今元首在世时制定之,然必俟今元首即世时始发生效力。至易见也。彼时所发生之效力,能否恰如所期,则其一当视前元首生前之功德威信能否及于身后,其二视彼时有无枭雄跋扈之人,其人数之多寡,其所凭藉,是否足以持异议。吾以此标准以测将来,无论为君主为共和,结果常同一也。[1](P91-92)
按照梁启超之意,君主制度的决定性意义不在于其法律结构层面,而在于君主制下国民的心理状态。这就涉及到了政府形式与共同体的关系。按照梁启超:盖君主之为物,原赖历史习俗上一种似魔非魔之观念,以保其尊严。此种尊严自能于无形中发生一种效力,直接间接地以镇福此国,君主之可贵,其必在此。虽然,尊严不可亵者也,一度亵焉而遂不复能维持。[1](P94)
梁认为,倡导立宪的政论家本应利用满清皇室的魔力和平推行立宪制度,但辛亥革命诸公悍然主张变更国体,致使国内政局乱无宁日,现在,旧皇室既经亵渎而魔力荡然无存,又无新的人物具有这种魔力,再悍然推行君主制,必然导致生灵涂炭和使国家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君主制抑或共和制,实乃中华民族生死之攸关,这是梁启超辛亥前反对革命,此时又置生死于度外反对袁世凯称帝的理由。但梁启超并没有分析君主制的重要性(在梁著文时)是君主制问题本身的重要性,还是时代赋予的重要性?如果是后者,世易时移,是否采取君主制也许会变得无关大局,梁启超的国体政体之分,就是为一时之需去改变语言用法的不明智之举了。
很明显,君主制的问题并不是在所有历史时期都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君主抑或共和、立宪抑或专制,都是对国家政治法律结构的规定、或者是对国家政治生活的事实描述和概括,并不能先验地确定君主制问题相较立宪制问题更为重要。英国的清教革命并没有推翻君主制度,但这一点并能抹杀清教革命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十月革命不是在计较俄罗斯的共和国性质,希特勒的极权主义也不牵涉帝制的复辟。也许和梁启超的结论正相反,对近代现实的政治生活而言,立宪与否比共和与否更为重要。更进一步地,共和制之下的民众也会对政治体制抱一种梁所言的“似魔非魔之观念”,如美国民众对美国宪法的情感。是否采取君主制取决于民心的向背,或者大而化之关乎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的条件,是否采取立宪制度也同样如此。
有人认为梁的“‘国体’和‘政体’涉及的都是国家政权组织形式问题”[2](P4)。其实不然。虽然君主制抑或共和制与政权的组织形式密切相关,但在梁启超那里,是否实行立宪政制主要限于政权的组织结构方面,而是否采取君主制则关键在于共同体的支持方面,立宪政制是关系到政府的,所以叫“政体”,君主制抑或共和制则关系到全国,所以叫“国体”。——被等而视之使用的国家和政府这两个概念,在这里虽然还都在表述权力,却被一分为二了。但问题的要害在于,政府治理的其他要素,即君主制抑或共和制之外的其他要素,也可能关系到共同体的支持方面,因此也应该被视为政府——或者政治——的实质性内容。
梁启超的国体政体之分其实来自于东瀛。日本一度是立宪党人和革命党人的主要根据地,双方的理论资源都主要来自于日本,而其时日本的穗积八束等人正主张国体和政体之分,即主张国家是否坚持君主制为国体问题,其他问题则为政体问题。只是穗积八束的这种观点,在当时的日本就只是一个支流,在之后更为日本宪法学所抛弃,这一点,美浓部达吉的《宪法学原理》有清楚的叙述。只是梁启超和中国的革命党人全都受了穗积八束这种论调的影响,以至于民国宪法学、直至现在的台湾地区宪法学,仍坚持梁启超意义的国体、政体之分。
二、国体和政体的新区分
(一)国体和政体区分的新标准
赋予“国体”和“政体”以新内容的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
按照毛泽东国体也就是国家体制的观点,可以分为三类:
全世界多种多样的国家体制中,按其政权的阶级性质来划分,基本地不外乎这三种:(甲)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乙)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丙)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2](P676)
在这三类国家体制中,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被认为是旧民主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被认为是“除苏联外,正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酝酿着。将来要成为一定时期中的世界统治形式”,而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则被认为属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所采取的过渡的国家形式”。在进行上述分类之后,毛泽东给出了国体的新定义:这个国体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闹清楚。其实,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资产阶级总是隐瞒这种阶级地位,而用“国民”的名词达到其一阶级专政的实际。这种隐瞒,对于革命的人民,毫无利益,应该为之清楚地指明。“国民”这个名词是可用的,但是国民不包括反革命分子,不包括汉奸。一切革命的阶级对于反革命汉奸们的专政,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要的国家。[3](P675-676)
毛泽东认为他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国体的概念问题。接着他开始讨论政体:
至于还有所谓“政体”问题,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精神,必须表现在政府和军队的组成中,如果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叫做政体和国体不相适应。[3](675-676)
对于抗日战争时期应该奉行的国体和政体,毛最后总结[3](P675-676):
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我们现在虽有中华民国之名,尚无中华民国之实,循名责实,这就是今天的工作。
毛泽东将政体归为民主集中制,即以普选为基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为什么以普选权为基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能够保证政权的实质在于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而不是资产阶级专政或者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看不到其中的逻辑链条。虽然如此,毛泽东的国体和政体之分,即政权(政府)的构成形式意味着政体,而政权(政府)应该保护的利益则关涉到国体,看上去似乎确有道理。
(二)新标准的困难
区分使用政体和国体作,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进行辨识,或者说如果区分出国体的载体和政体的载体。政体的载体自然是政府的组织,国体的载体呢?难道国体的载体不也是政府组织吗?国家的整体性法律框架除了政府组织之外就是国民基本权利的规定,但国民基本权利并不以阶级作为权利的主体,并不能成为国体的载体。
除了政府组织和公民权利之外,宪法中可能还会规定国家的重大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如我国五四宪法规定的“国营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和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国家保证优先发展国营经济”,但这些国家政策实际上是赋予政府组织以权力和责任,因此仍然应该属于政府组织的内容:对政府组织的规定,并不能局限于规定作为空壳的政府机构,还包括这些机构的法定权力和职责,国家政策正是政府组织的权力和职责的表现。
很难说毛泽东的政体只是单纯的形式而不包含实质性内容。毛泽东认为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体形式为人民代表大会制,但这个人民代表大会制本身就是形式和实质的统一:这个人民代表大会制必然包括普选权、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控制各级政府等实质性的权力运行规则,没有这些运行规则、或者说徒有其表的空壳般的人民代表大会,就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也就不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体。另外,缺乏实质性内容的、纯粹形式的政体并不是真正的政体。前苏联的政体——按照苏联宪法规定——形式上是苏维埃制度,即一切的国家权力都归于国家苏维埃,但苏联真正的统治形式是苏联共产党对于国家事务的绝对控制(苏联一直没有实现真正的党政分开),所以,前苏联的真正的政体不是苏维埃制度而是党国体制。
事实上,经典作家并不在政治层面对国家性质和国家政体进行区分。恩格斯曾断言民主共和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合适的政权形式,恩格斯这时候并不将民主共和国认为是区别于政体的国体。列宁则称苏维埃政体为巴黎公社的后继者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合适的政权形式,因为它本身就反映着无产阶级的政治利益,与此相对的是,议会制共和国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合适的形式,它最忠实地反映和保卫了作为阶级的资产者的利益。不能说保护无产阶级的政治利益或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的国家——国体——是一个东西,相应的苏维埃制度或议会制度——政体——又是一个东西。社会各阶级的政治地位和政权组织的形式,必须放在一起来说。
按照马克思的基本原理,国家属于政治的上层建筑,本身并无本质可言,真正的本质在于生产方式、也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国家本身只能是一种政治形式,而这种形式反映的阶级利益,则属于社会的范畴。国家和社会是有区别的,因此,政治制度反映的阶级利益,本身不属于国家的范畴,因而不能称之为国家体制、或国体。
三、苏联关于国家本质和国家形式的理论
苏联宪法和政治理论中也有国家性质、政体和国家形式这些概念,但含义却完全不同:我国将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的特殊形式——视为国家的本质、即国体,将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视为国体(见上述《新民主主义论》引文),苏联的宪法理论则将无产阶级专政、将苏维埃共和国视为国家体制的形式,视为国家的形式。
前苏联政治学家契尔金在论述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时,列举了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几项基本特征:反对剥削、真实的人民性、国家的创造作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道主义。接着,契尔金写道:
以上这些特点表明,社会主义国家是特殊类型的国家。以往的任何国家,其本质都主要是由阶级镇压所决定的,而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活动中,阶级镇压并不是主要的因素。在剥削阶级和剥削因素被消灭以后,阶级镇压的职能都已经被取消了。这意味着国家本质一个主要方面的变化,即国家最初是作为一个带强制性的政治组织出现的,其后逐渐发生变化,最终会完全消亡。[4](P294)
可以看出,契尔金对国家本质的表示完全集中在国家的社会特征上,国家的本质是政权的社会特征,而不是权力运用的方式,无产阶级专政则正是社会主义国家权力运用的基本方式,因而只能是国家形式而不会是国家的本质。当然,在契尔金这里,无产阶级专政并非社会主义国家唯一的国家形式,因为苏联还有全民国家这一概念。契尔金写道:
社会主义国家的形式具有明显的多样化特征,但是,从其中区别两种基本的形式则是完全有可能的,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和社会主义全民国家的国家形式。前者采取了多样的形式。如1871年的巴黎公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民主共和国及其它一些形式;全民的社会主义国家形式目前仅存在于苏联,它形成于六十年代。[4](P301)
契尔金对国家形式的分类与我国理论界对国家形式的分类有所不同。我国将国家形式分为政权组织形式和国家结构形式两类,但契尔金为代表的前苏联政治理论认为国家形式有三项内容[4](P47)。
一般说来,国家形式由三个部分组成:政体(共和制、君主制)、国家的结构(单一制、联邦制)和国家体制的形式(Form of state regime)(资产阶级的民主政体,资产阶级的集权政体)。
关于国家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区别,契尔金的解释是[4](P50):
国家体制(State regime)(国家——法律体制)这个词是指对政权进行管理的各种方法和手段的总和,它说明国家的职能方面。应当区分国家体制与政治体制(Political regime)之间的区别。国家体制是由国家机关的活动所形成的,而政治体制是由整个社会中全部政治制度的活动而形成的。
契尔金的政治体制比国家体制的含义更为宽广,比方说像共青团、妇女组织乃至儿童团的活动,都属于政治活动,因而属于政治体制的范畴,但却不属于国家体制的范畴。另外,契尔金的政体也不是政治体制(Political regime):政治体制不但是静态方面的社会的政治组织机构,而且包括动态的社会政治组织所形成的政治秩序和政治体制,而契尔金的政体,则只是“从国家的最高机关到基层组织(如,地方代表机关)之间的整个体系”[4](P48),是基于静态方面的、国家机关的组织构架。
前苏联宪法理论将政体、国家结构和国家体制区别使用,自然也值得检讨。提出苏联宪法学的相关概念,是为着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并不要求以国体来指称阶级性质,用政体来指称政权组织形式。
四、政体一词的适当含义
(一)政体一词的另一种含义
虽然国体为阶级本质、政体为政权组织形式的定义构成新中国理论上的正统,但政体一词也在另一层含义上被广泛地使用。如广为人知的亚里士多德的关于政体的六分法,即君主制与僭主制、贵族制与寡头制、共和制与平民制,这些政体都着眼于是否采取君主制(相对于梁启超意义上的“国体”)、也都着眼于社会各阶级在国家(城邦)中的地位(这又相当于毛泽东意义上的“国体”)。孟德斯鸠的政体三分法也是如此。另外,政治学中被频繁使用的政体概念,如亨廷顿在《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出的执政官政体、达尔所提出的“多头政体”、二战之后一度占据政治学统治地位的自由民主政体与极权政体之分,以及官僚政体、发展中国家政体等等,这些概念,都无法套入毛泽东的政体概念,但在当代中国都获得了广泛的承认。
事实上,这另一层意义上的政体概念,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合理的概念。这一层含义上的政体,也就是政府治理的根本属性,是从政府治理的形式构架、决策程序、效能和政府与共同体的关系出发,所得出的思维层面上的、政府治理的最基本的特征,是对逻辑上的政府治理形式的逻辑归类或者对现行各个政府治理方式的经验的归纳。
(二)对“政体”的语源分析
对“政体”一词的语源分析也支持将政体指涉政府治理的根本属性的用法。
至少又三个英文单词被广泛地翻译为“政体”:polity、government和reign。《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对polity的注释是:“1[U]formorprocessofgovernment政权形式;政体。2[C]society as an organizedstate国家组织;政府。”[5]reign的含义很简单,就是指统治。Government作为不可数名词除了意指统治和统治权力外,也表示统治的方式方法,这后一种含义就被政体、体制或者治理的方式。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的constitution,一般被翻译为结构、体制和宪法,但在亚氏的书中就是指政府形式,因此我们将它翻译为政体。
在英文中,political reign和political system这两个词汇用得更为广泛、而且常常被不加区分地使用,它们在中文中也被相当广泛地被翻译为政体,虽然在日本学者山口定的《政治体制》中,译者分别以“政治体制”和“政治系统”来翻译,而且山口定认为应该将政治体制和政治系统分开使用。另外,加有表示统治、治理的词缀archy和cracy的单词,一般也翻译为某某政体,如美国政治学家创造的新词polyarchy被译为多头政体,democracy和monarchy被分别译为民主政体和君主政体。
(三)政体含义的不确定性、政体的实质
1.不同的视角与不同的政体概念
从词源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政体一词,最好对应于与抽象的统治和治理。既然是抽象的治理和统治,就不会包括某种特定的统治和治理的全部要素,而只包括统治和治理的本质性性或典型性要素。何种统治和治理的要素会被视为本质的或典型的要素呢?关于政体的学说史表明:不同的观察视角会导出不同的政体概念,这些不同的概念都有自己的价值和局限性,而绝无绝对的对错之分。
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其标准是政治共同体的阶级关系(统治权是寄托于一个人、少数人或者多少人)和正统性原则(政体的正态与变态之分);总统制、议会内阁制和委员会制的分类,其标准是政治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二战后一度占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政体与极权主义政体之分,是将支撑体制的正统性原则——是否确保自由的原则——作为政体划分的标准;亨廷顿的执政官政体,其确定的标准则是政府的统治能力;达尔对霸权政体和多头政体的区分,其标准是社会对权力的影响渠道和影响程度;萨尔托里对政体的分类,适用的标准是政党体制。二战以后对政体划分理论纷纭复杂、层出不穷,这些频繁变易的政体划分,自然都是因为学者们看重不同的政府治理的因素。每一种划分确实都有自己的局限,但毫无疑问,每一种划分也都有自己的适用价值。
2.历史的因素
政体分类标准的变易,某种程度上也是政府本身的角色变易的反映。前现代社会的政权组织结构对政体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前现代社会中的“社会”的因素往往不够发达,几乎所有重大的政治决策都单纯地来源于统治集团掌控的统治机构。但在现代运转良好的民主社会,政权组织本身更直接地接受环境的压力,也必须更灵活地与环境的要求相适应,相对于前现代国家,社会对国家权力的直接作用要更加强烈,单单研究国家组织结构,已不再能够说明现代社会的政治生活了,现代国家已经更多地从强制的职能发展到对社会的管理职能。按照日本学者山口定的归纳[6]:
一般说来,在“国民国家”(即民族国家,本文作者注)这个“政治系统”中,“民主化”或“自由化”的程度越低,越容易形成以“政府”为顶点、向下依次为“政治体制”和“政治共同体”的锐角圆锥形结构;与此相反,“民主化”或“自由化”的程度越高,越接近于形成以“政府”为核心、向外依次为“政治体制”和“政治共同体”的同心圆结构。
成熟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政体学说、或者说对政府权力的研究早已达到相当深的层次。而只有深层次的理论才能抓住复杂的政治现实,并为政治建设提供切实的、有启发性的指导。将国家的本质和国家形式截然分开、并且教条地确定一种政府的要素为国家本质,无助于拓深对政治权力的运行的研究。
3.国家层面上的政体与其他组织意义上的政体上文中谈到政体、政府,都是着眼于民族国家的层面,但政体之既为统治和治理,就决不光局限于国家政权的范围内。在民族国家这一整体社会之下的单位,包括作为自治单位的地方和其他的组织包括从事公务的公务法人以至于私人性质的巨型公司,政体也是一个有分析价值的词汇。当然,最具政治意义的单位在现在仍然是作为民族国家的整体社会,因此,在一般的政治学著作中,如果没有明白的标示,政体往往就指民族国家的政治统治和治理。对于超国家单位而言,具备相当统合力的国际组织如欧盟,谈论其政体问题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对整个国际社会或其他过于松散的国际组织,谈论政体就显得不现实了。
五、结论
在民主已无可疑义地成为最基本的政治价值的时代,梁启超的国体和政体之分已经丧失了任何正面的意义,而将国体定位于阶级本质、将政体定位于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不但会将社会和国家(政权)混同起来,而且会使政体变为纯粹的政府组织形式,因而使得政体的含义贫弱化①中国大陆有“政体”和“国家结构形式”之分,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归之为“政体”之外的“国家结构形式,这自然进一步窄化了政体概念的范畴。其实,即使按照毛泽东的术语,将政体定义为政权组织形式,联邦制抑或单一制、中央集权抑或地方分权这些国家结构形式的内容,也是应该属于政体内容的。。对国体和政体的区分,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也不符合政治学的传统理论和现状。
从现实的层面来看,民主社会的基本追求是拉近社会与政权的距离,要求政府的权力必须响应社会的需求,在这种背景下,强调国体和政体的区别、或者说政权的本质属性和形式特征的区别,不但是对政府权力的简单化,而且容易使对权力性质的研究空洞化、对权力形式的研究的表面化。政体一词原本是从政府治理的形式构架、决策程序、效能以及政府与共同体的关系出发,对政府治理的最基本特征所作的抽象,因而既包括国家的本质也包括国家的形式(含一般而言的国家结构形式)。目前大陆和台湾两岸宪法与政治学区分使用国体和政体概念的做法,都应该予以抛弃。
[1]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九册)[M].北京:中华书局,1932.
[2]严家其.国家政体[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A].毛泽东选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苏]契尔金.宪法与政治制度[M].周伟、刘学信、任高潮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
[5]《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Z].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137.
[6][日]山口定.政治体制[M].韩铁英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8-9.
Two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state system and the Government System
TU Si-yi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Business Studies,Guangzhou,510320)
The educational circle of Chinese mainland generally believes that the class character of the government is the state system and the organization form of the government is the government system.While in Taiwan,the educational circle holds that the state system refers to whether a country adopts a republic or a monarchy,whileas the government system refers to the different forms of government,whether constitutional or authoritarian.Both explanations may have logical difficulties in that the government system is just a generalization of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gime.However,the division of the above two concepts should be abandoned.
the state system;the government system;the state structure form
D621
A
2095-1140(2012)02-0030-06
(责任编辑:左小绚)
2012-02-26
涂四益(1969-),男,湖南华容人,广东商学院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宪法学与宪政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