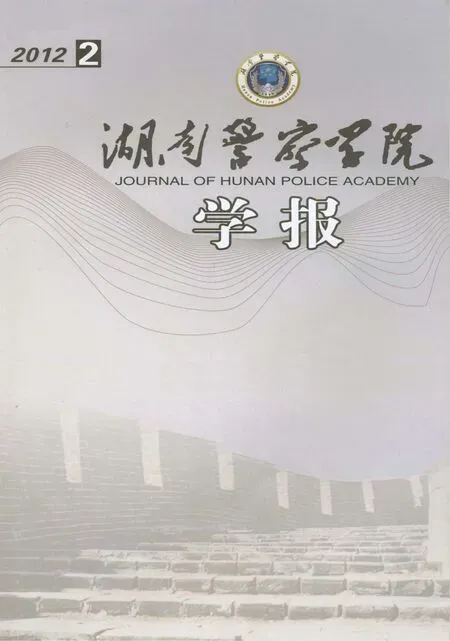法制现代化视域中少数民族习惯法存在的合理性分析
2012-04-12李小苹
李小苹
(甘肃政法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当代中国农村法治
法制现代化视域中少数民族习惯法存在的合理性分析
李小苹
(甘肃政法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专栏主持人语:无论社会如何变迁,秩序的建立是社会良性运行的基石。在乡村秩序的重构中,传统的礼治秩序在传承和瓦解中顽强地抗争着,国家制定法是悄无声息地融入还是肆意强行占领?乡村秩序格局嬗变中的最佳模式是传承传统、吸收现代基因并将之本土化。如果至上而下的行政权力仅仅延伸至乡村的组织架构中,而不是深入基层民众的生活,内化为一种信仰,乡村秩序的重构将举步维艰。
关注当代中国,请关注当代中国农村!
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制定法的实施在少数民族地区遭遇瓶颈,与少数民族习惯法发生碰撞,二者在少数民族地区认同度的差异,让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少数民族习惯法。少数民族习惯法既不是国家制定法的附属物,也与习惯有区别。在现代法制社会,不论是从少数民族习惯法形成的规律的角度,还是从其对社会控制的角度,或者从它对国家制定法的作用的角度来看,少数民族习惯法仍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少数民族习惯法;法制现代化;合理性
少数民族习惯法,是广泛存在于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社会存在。在少数民族地区,习惯法以其强大的生命力、独特的形式填补了国家制定法的缺位。但是,随着国家政权的渗透,国家制定法这种完全异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强势文化的进入,打乱了原来的习惯法调整体系,国家法和习惯法发生了碰撞。这就带来了一些列问题,比如:国家法应当让步吗?应当作出怎样的让步?二者之间的碰撞和冲突如何调适、消弭?等等。国家法让步与否与少数民族习惯法存在的合理性有关,存在的合理性问题解决了,才能谈得上国家法应不应当让步和在多大程度上让步。对于前一类问题,学界讨论得很热,但是对于后一问题,鲜有论述。在现代法制社会中,少数民族习惯法存在的合理性问题是前提性问题,其他问题的解决依赖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一、问题的提出——传统法学理论对于习惯法的界定
我们对于习惯法的最初认识,来源于传统法学理论。传统法学理论认为,“习惯法反映国家认可和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习惯……在国家产生以前的原始习惯并不具有法的性质。”[1];“习惯法是经国家认可并赋予国家强制力的完全意义上的法”[2];“只有经过国家认可的习惯才能成为习惯法”[3]。这些概念在理论上似乎是自足的。因为,传统法学理论认为,阶级性或国家性是法的重要特点之一,因而作为产生于民间的习惯法,如果它没有经过“国家认可”这一环节,就不能成为法。这样的认识表面上照顾到了国家法(包括制定的和认可的)的权威性,但却无视这样的现实:在少数民族地区,大量存在着未经国家认可或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但千百年来承载着该地区民众的信仰和价值理性、对该民族地区社会秩序控制有效的少数民族习惯做法,其具有的法的实质效力不可否认。在法律社会学和法人类学的推动下,近年来,法学理论界对于习惯法的界定渐趋符合实际①笔者认为,少数民族习惯法是习惯法中的一种,所以此处及下文关于“习惯法”的讨论也适用于少数民族习惯法。,认为习惯“这种行为模式获得社会成员或统治者的认可,成为习惯法,便具有了法律的约束力,因而便具有了法的效力,成为法的渊源之一。”[4]此说认为,习惯法能否成为习惯,要么获得社会成员的认可,要么获得统治者的认可,其中有一点与传统的法理学教科书有本质区别,即肯定了虽不具备形式要件(国家认可或国家强制力保障)但具备实质要件(获得社会成员认可)的习惯为习惯法,这一点的理论价值是值得肯定的,这个意义上的习惯法也是本文关注的对象。这里我们暂不关注经统治者认可而形成的那部分习惯法,因为严格来讲,被统治者认可,纳入并融入国家法的范围之后,究竟它还是不是习惯法有必要另文讨论。
二、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关系以及与习惯的区别
对于少数民族习惯法概念的界定,必须揭示它的特有属性,如它有哪些不同于习惯、国家制定法的属性,此外,还要揭示出它与国家制定法的关系:它能否与国家制定法混同,或者认为它隶属于或附属于国家制定法。关于这一点,我们可能要更多的关注法律社会学和法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这也是法学现代化的一种途径。因为法学本身不是自足的,它必须及时吸纳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以拓展对法的认识的限度。说到底,对法的认识,法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等等,他们对法的内涵的解读是不统一的,这也给法的现代化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法律社会学和法人类学研究在法学界被逐渐重视,也说明了这一点。高其才认为,“习惯法是独立于国家法制定法之外,依据某种社会权威和社会组织,具有一定强制性的行为规范的总和。”[5]很多学者对这一定义本身及其意义进行了多方面的肯定。笔者认为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它廓清了本文语境中的习惯法这一研究对象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关系:它是“独立于国家法制定法之外”的,与国家制定法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二者是并列关系,不是包含关系或者附属关系,它不像国家制定法那样与国家有着天然的联系。揭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讨论和研究少数民族习惯法的主要目的就是关注国家制定法之外的、少数民族习惯法对少数民族地区秩序建构的具体作用,这是讨论其他问题,比如国家制定法要不要退让、如何退让、二者如何调适等问题的基础和前提。
习惯法与制定法不同,把它与习惯进行区分也是必要的。根据上述传统法学理论对于习惯法的定义,似乎“获得社会成员的认可”就成了区分习惯与习惯法的标准。习惯在辞海中是这样定义的,由于重复或多次练习而巩固下来并变成需要的行动方式;或者指经过不断实践以能适应新情况。客观的讲,习惯法是由习惯发展而来,很难说习惯没有“获得社会成员的认可”,否则它就不能成为“习惯”。那么,习惯法与习惯的区别到底是什么?这里要考虑两个问题,其一,习惯法之所以有别于国家制定法、习惯、习俗,涉及到习惯法的内涵问题。其二,准确界定习惯法的外延,把习惯、习俗等事物排除出去就不会导致习惯法概念的泛化。有观点认为,习惯法的成立要件包括四个方面:1.人人确信其为法;2.一定期间,同一事项反复同一行为;3.习惯所支配之事项系法令所未规定之事项;4.不违反公共秩序。在实质上,是以上述1.2为基础;在形式上,则要决定于法院,法院认为其不违反公序良俗,并适用了,才认为其具有法的效力。[6]这其实还是传统判别标准,似乎离开了国家性(法院的适用),习惯法就不成其为习惯法,就很难将习惯与习惯法进行界分,因为除了“人人确信其为法”这一要件,根据其他的要件判断,习惯法与一般的习惯、习俗还是不能清楚地区分。
关于习惯与习惯法,有学者专门进行过论述,认为“习惯或风俗习惯包括的范围很广,是本民族全体成员共同自觉遵守的规则。习惯法则是民族内部或民族之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调整、处理人们的相互关系,由社会成员共同确认的,适用于一定区域的行为规范,它的实质是惩处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的法则。”[7]不过,我们还要对这一描述进一步修正:首先,少数民族习惯法侧重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这些关系是利益关系,它规范的是具有社会性、对他人利益有影响的行为。相较而言,少数民族习惯只是一种惯行,这种惯行只与自身有关,所包含的行为无涉他人,不具有社会性,或者虽有社会性但不会对他人利益造成影响。如民族地区的人们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样的房子,对这个环境中的其他人没有利益上的影响,因而只是一种习俗,或者是习惯;而如果从事了杀人、偷盗等行为,损害他人人身、财产等利益,这个行为就不仅仅是个人行为,而是带有很强的社会性的行为,从而进入了少数民族习惯法规范的范围。其次,涉及的社会关系不同,导致赖以实施的力量不同。少数民族习惯法虽不具有国家强制性,但具有一定程度的强制性,自发遵行的内化强制与外化的物质力量强制结合,外化的强制力量一般是民间社会组织或群体认可的权威机构(如西南少数民族的“寨老”、“族长”、“山官”、“榔头”;西北少数民族的“部落头人”等);而习惯的遵守主要来自于人们的内心信念。再次,形成方式不同。如果我们详加考察,就会发现,习惯法有的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逐渐自然形成并不断传承下来的,而有的是民间组织或群体成员约定的(如青海藏族习惯法多源于一些早期制定的部落法规);而习惯一般为自然形成。
三、现代法制社会中少数民族习惯法存在的合理性
在少数民族地区,习惯法以其很强的生命力、独特的形式展示着它的魅力。但是,随着国家政权的渗透,国家制定法这种完全异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强势文化的进入,打乱了原来的习惯法调整体系,国家法和习惯法发生了碰撞,结果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8]这里涉及到传统与现代、传统习惯法与现代文明法律的碰撞问题,也涉及到通常意义下的进步与落后、文明与愚昧的分界,同时,在中国还有另外一层深刻的内涵,那就是中西问题,具体来讲就是中西法律及其思想的碰撞、融合或者对接问题。费孝通先生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依据价值中立的原则,指出了原有礼治秩序与法治秩序冲突,他从社会结构与功能的层面上看到了,合理的有序的秩序建立的困难,这个困难透露出传统礼治秩序被打破,甚至破坏,现代法治又不能如愿建立的困境。从法学角度讲,就是法的一大社会功能,即维护社会正常、合理秩序的功能没有依主观愿望而建立。这就涉及到如下的问题:完全依照国家制定法重建秩序?还是国家制定法作一定程度的退让?这些问题,也涉及到现代法制社会中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存在合理性问题。
(一)从少数民族习惯法形成的规律的角度分析
法是由习惯起源的,由习惯到习惯法再到成文法,这是法的发展规律。在成文法出现以后,社会关系的一部分仍然由习惯法来调整,所以,习惯法并没有因为成文法的产生而灭迹,习惯法仍然是人们很大一部分行为的调节器,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
我国分布着很广的少数民族亚社会,它向来都处在自治或半自治状态,少数民族的生活不同程度地受到当地社会传统习惯的影响。“在藏族聚居的中部有一个社会发展层次较西南部和东北部更显后进状态的夹层区。这个夹层地带,人们的法律生活还不同程度地受到古老的部落法规的惯性影响”。[9]少数民族人民在观察、思考和总结历史生活,不断的自我调整、自我约束,创造了本民族的特有的相对独立的规范制度——习惯法。可以说,习惯法是特定民族文化的源头,体现着民族精神,它有着长久的生命力。习惯法因为“成于斯长于斯”,它在民族地区的影响超越了成文法。正如卢梭所形容的,这种法律“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创制精神。”[10]卢梭在这里也看到了民族习惯法是特定民族自身精神的体现,特定民族精神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习俗、制度等,而这样的硬制度在调整社会关系时、在调整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甚至法律关系时,由于制度、习俗或者习惯法来源于其民族文化精神基础上,更容易在实践中被认同、遵循。同时,其内生性文化精神是推动社会创制的源头活水,可以随着社会实践的变化、发展而推动制度创新(包括法律制度的创新)。
作为在长期的历史中形成的一种社会的天然安排和内生的秩序,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形成和存在,有它的合逻辑性。德国法学家萨维尼认为:“法律只能是土生土长和几乎是盲目地发展,不能通过正式理性的立法手段来创建”。[11]他认为,一个民族土生土长的法律制度是其文化的自然体现,二者之间本质上没有冲突、断裂,是自然而然的合乎逻辑的统一,任何试图通过主观的意愿、意志在原有文化基础之外寻求法律制度的立法者,都是徒劳;每一个民族的法律制度,都生于民族内部和由内部的力量推动,不能由外部强加或者由谁的意志推动。少数民族习惯法是最符合该地区人们日常生活习惯的,其生命力和地位远远超过国家制定法。特定民族的民族语言、民族意识为该民族习惯法提供了载体,其影响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少数民族习惯法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灭。埃利希的“活的法律”理论认为,虽然,这种法不象制定法那样的公开,那样明确,但在人们生活中,它有着非凡影响力。
(二)从少数民族习惯法对社会控制的角度分析
基于前述分析,少数民族习惯法建基于特定民族文化之上,二者有质的统一性,这样二者相互推动便成为可能。否则,二者在质上的不统一、冲突,必然导致价值冲突,特定的民族文化精神因素诸如习俗、习惯、道德、伦理等不能为制度提供软性支持,那么单方面的制度的约束力便会下降,甚至制度在实践中会被否定。相反,二者在统一性的前提下,不仅文化精神因素能为制度的建立提供支持,同时为制度的实施提供软性的社会环境,在其运作时更为顺畅。当然制度不是一味受制于文化精神因素,它对文化精神的维护提供了硬约束力。少数民族习惯法正是建基于其民族文化之上,它在实施过程中,由于有其社会文化环境的软性支持,它对特定社会的控制力变得更强,而且执法成本也相对较低。
少数民族习惯法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通过各种方式为当地民众所传承和接受。它因为具有以下特点而达到了对社会的有效控制。首先,其涉及的范围很广,人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以及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按照本民族的习惯法行事。其次,每一方面的规定都很详细,这样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很有效,也很经济,与法治相比高效率低成本。很多问题因为以调解的方式处理了,所以还可以节约诉讼费用。再次,它在少数民族地区认同度高。作为一种长期传承下来的制度形态,少数民族习惯法经过社会群体的吸纳和运用,逐渐融化在人们的思想意识当中,并内化为民族心理,所以在少数民族地区人们中有着亲切感和高度的认同性。
(三)从少数民族习惯法对国家制定法的作用的角度分析
首先,国家制定法在形成时,是着眼于整个国家的全局性、统一性问题,考虑的主要是宏观的、大范围的调控。因此,一方面,国家制定法的统一属性,使其具有很强的跨地域性和跨民族性,这会导致了国家制定法更多地是关注那些直接关系到统治秩序的社会关系,而对其他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问题往往难以兼顾,要么只能作出原则性的规定。因此,少数民族地区的诸多问题,国家制定法是很难解决的。相对而言,少数民族习惯法则能够调整国家制定法所触及不到的社会关系,这就很自然地填补了国家制定法的空白,满足了少数民族社会的规则需要。另一方面,国家制定法的许多具体操作因为过于一般和概括,在有些情况下是很难把握的。在不同的少数民族聚居区适用时,国家制定法的这些可操作性和微观指导性相对欠缺的弊端就会渐渐暴露出来。相对而言,少数民族习惯法的规定很具体、详细和明确,它来自于少数民族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因而与人们的生活更为贴近,从而比原则、抽象的国家制定法更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
其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少数民族习惯法是国家制定法的基石。如同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少数民族一样,国家制定法的产生和发展也伴随着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滋养。国家制定法的产生、成长和完善,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在借鉴和参考各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基础上完成的。中国最早的国家立法“禹刑”中的五刑制度这一对中国古代社会有重大影响的刑罚制度,就是以我国西南苗族习惯法中的“五虐之刑”为蓝本而确立的。[12]在法律多元化的今天我们可能更能够发现和发掘少数民族习惯法对于国家制定法的借鉴和参考价值。如国家民事诉讼法关于调解制度的规定,就是借鉴了在中间人主持下对双方的纠纷进行调解的习惯法;我国刑事法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刑事和解制度,也是参考了少数民族习惯法中和解的运作模式,即对于刑事案件,一定条件下,当受害方的要求为加害方满足后,允许和解。而“地处边陲的少数民族在边境贸易中所形成的一些习惯法性质的交易规则,早已被边境双方的国家在国家对外经贸法规中予以认可。”[12]可见,少数民族习惯法中有供国家制定法汲取的合理因素,少数民族习惯法是国家制定法形成、发展和完善的基石。
除此之外,我国目前司法执行力量相对薄弱,尤其对于环境恶劣、通信交通落后、地处偏远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国家制定法更显得鞭长莫及。如果执行少数民族习惯法既可获取公平结果而且成本又低时,有什么理由不选择适用少数民族习惯法而一定要适用在此情况下不见得经济的国家制定法呢?而且从优化司法资源的配置角度看也不是不合理的。
各少数民族都是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的一员,中国的法治实践离不开这一现实。国家制定法不是万能的,也不是无所不在的,各少数民族习惯法有其适用的领域,有些领域国家制定法鞭长莫及,国家制定法应当在能够而且应当覆盖的范围内充分发挥作用,把其他领域交由民间法(包括少数民族习惯法)和道德来调整。“如果用法律去改变应该用习惯去改变的东西的话,那是极糟的策略。”[13]少数民族习惯法作为一个民族族群内部适用的自律规范,作为一套在本地区行之有效的司法资源,作为“本土资源”的当然构成要素,是能够而且应该与国家制定法融合起来,为现代法和“法治”服务的。
四、结语
现代化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认识的过程,随着法律实践的不断深入,法学理念认识的深化,我们有必要对少数民族习惯法存在合理性作进一步分析,这种进一步认识、分析本身就是法律观念现代化的一种表现。传统上,我们虽然一再强调法学辩证法,法律实践辩证法,但是在真正的实践、认识过程中,又不同程度地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传统的少数民族习惯法在非此即彼的二分法中取消了其合理性的讨论,其合理性不是一个可以讨论问题。在现代化逐步深化的今天,我们对传统节日、节庆、祭日尊重已经回归到理性的轨道、法的轨道,这说明整个中华民族在文化自觉中取得了成绩。同样有理由相信,少数民族习惯法在现代化逐步深化的过程中,对它存在的合理性讨论会有一个肯定的答案。当然这个肯定的答案不是谁取代谁的问题。
法制现代化,“并不是要求把什么都变成现代的东西,而是用现代的眼光、思想、头脑去重新评价,重新诠释我们古人所创造的辉煌法律文化(尤其是习惯法),让它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4]在我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应当在肯定不同民族的习惯法文化在各自独特背景中形成和存续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基础上,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为多元法文化的相互理解、借鉴和融合开辟道路。
[1]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4.87.
[2]孙国华.法学基础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41.
[3]沈宗灵.法理学(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89.
[4]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130.
[5]高其才.论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文化[J].中国法学,1996,(1).
[6]杨仁寿.法学方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205-209.
[7]吴大华.论民族习惯法的渊源、价值与传承——以苗族、侗族习惯法为例[J].民族研究,2005,(6).
[8]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三联出版社,1985.43.
[9]戈明.中部藏族部落法规初探[A].张济民.渊源流近——藏族部落习惯法法规及案例辑录[C].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2.1.
[10][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73.
[11]何勤华.西方法学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210.
[12]李洪欣,陈新建.少数民族习惯法对国家法制现代化建设的作用[J].广西民族研究,2007,(2).
[13][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310.
[14]王学辉.关于少数民族习惯法文化与法制现代化的思考[A].谢晖,陈金钊.民间法(第一卷)[C].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2.142.
On the Rationality of M inority nationalities’Customary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System M odernization
LI Xiao-ping
(Gansu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Lanzhou,Gansu,730070)
In the process of legal modernization,the state law collided with 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custom law in the minority regions.We must reconsider the different acceptability of the state law and the custom law in minority areas.The custom law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 are not appendages of the state law,they are different from habits too.In our modern legal society,the existence of the custom law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s rational from the point of either its formation rule,or its influence on social control or on the state law.
the custom law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legal system modernization;rationality
D921.8
A
2095-1140(2012)02-0005-05
2012-02-13
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藏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调适”(项目批准号11BFX011)。
李小苹(1974- ),女,甘肃陇西人,甘肃政法学院民商经济法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环境法学、法理学研究。
叶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