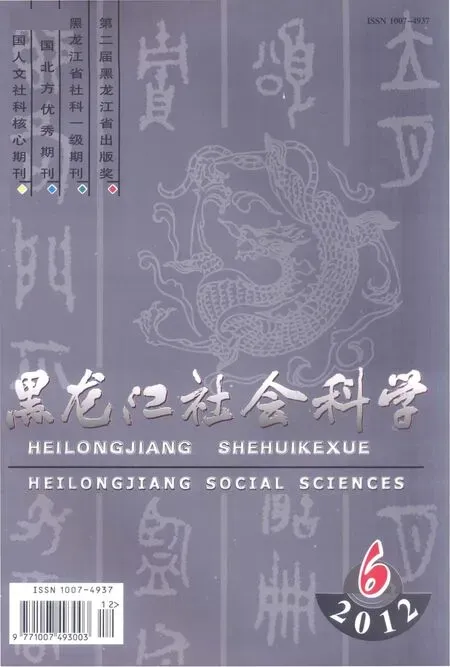后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研究
2012-04-12莫雷
莫 雷
(南开大学哲学院 ,天津300071)
后马克思主义是当代方兴未艾的一个潮流,其意识形态理论呈现出与马克思完全不同的理论特色。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拉克劳和墨菲围绕霸权的斗争展开了他们的意识形态模型,另一代表人物齐泽克则在批判拉克劳和墨菲的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征兆理论。他们的意识形态理论不仅针对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新的阐释,而且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新形式进行了深入的批判。
一
拉克劳和墨菲认为,随着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社会斗争形式的多样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面临着两方面的危机。一方面,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预设了普遍的主体概念,预设了无产阶级在本体论上的中心地位,另一方面,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将社会理解为“理性的透明秩序”,无法容纳社会的差异性和社会斗争的多样性。他们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关键之处都在于重新理解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
在他们看来,“‘普遍’绝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而只是对应于一个总是有限的并且可改变的特殊之间关系的‘名称’系列。”[1]204因此,他们一方面要否定普遍性,但又为普遍性保留了一个位置,将普遍性与“名称”系列对应起来。普遍是空白的、有待去填充的先验的匮缺,他们把这种普遍性称为虚空的能指。意识形态的斗争就是围绕着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落差展开的。
为什么这种普遍性是一种虚空能指的普遍性?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普遍性是一个悖论性的因素,它如同空的战场,但又总是被各种特殊性所填满,而且随着各种特殊内容的不断扩大以及复杂性的增加,这些特殊性逐渐具有了普遍性的维度,成为“部分的普遍化”,普遍性也因此可以获得相应的具体的内容,不再是抽象的和形式的普遍性。经过这样的转换,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两者不再是严格的对立,“只有普遍性/特殊性的二分被取代时,霸权才存在;普遍性仅仅体现在某些特殊性之中,并且它颠覆了这些特殊性,但是相反,如果不成为普遍化作用之所在,没有任何特殊性能够成为政治的。”[1]51
问题是,在多种特殊性的链条中,究竟哪种内容能够填补普遍性或者宣称自己真正代表了普遍性?哪种特殊的内容会在争夺霸权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制胜的关键何在?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多样的政治话语的竞争取决于“可读性”(readability)。也就是说,当各种特殊的政治话语相互竞争时,如果某种话语可以更好地将普遍性霸权化,如果它可以更好地组织起整个社会的叙事,将整个社会的矛盾冲突以一种更容易让社会整体接受的方式组织起来,那么,这种特殊性的话语就更具有“可读性”和可信性,它就能够在争夺普遍性的霸权中取得胜利。因此,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意识形态的基本模型就是霸权的斗争。“所有表面上普遍的意识形态概念,都总是由某种特殊的内容来加以霸权化,来渲染其普遍性,并说明其功效。”[2]244
这种霸权的操作是如何进行的?霸权的操作总是表现为将空白的普遍性霸权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是政治主体化的过程。因为“‘主体’就是那完成霸权操作的行为者——将普遍缝合至某个特殊内容之上。”[2]254具体来说,主体如何完成霸权操作的行为?他们认为主体必须在话语结构中来理解,主体就是主体立场,各种主体的话语立场是平等的,因而可以置换,可以不断重新组合。既然争夺霸权的斗争总是指向普遍性内部的不同内容的替换,霸权操作的行为者也就不可能固定不变,而要随着霸权的斗争的多元化不断实现主体的新形式。随着主体形式的增加,民主斗争的形式也会增殖。
总之,霸权的斗争不仅是拉克劳和墨菲提出的激进民主的多元主义策略,而且也是他们的意识形态的基本模型。
二
齐泽克对拉克劳和墨菲的霸权理论有深刻的认识,在他看来,由于这种霸权的斗争总是将普遍性联系于某个偶然性之上,总要由某个特殊性和偶然性的因素来体现空白的普遍性,所以霸权的斗争就总是呈现偶然性的特点。
为了避免拉克劳和墨菲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困境,齐泽克认为必须重新思考他们的理论前提,即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为此,他引入了“征兆”(symptom)这一范畴。“严格地说,‘征兆’是一个特定的因素,它颠覆自己的普遍基础,犹如属颠覆其种。”[3]也就是说,征兆是颠覆普遍性的例外,它以自身的存在颠覆了整个系统的存在。通过征兆揭示的某种例外,我们可以颠覆意识形态虚假的普遍性。因此,齐泽克认为,征兆是意识形态的崩溃点。
从这种对征兆的解读出发,齐泽克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已经是“征兆性”的了。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的具体程序是一种内在的排他逻辑。也就是说,普遍性内部包含了某个特殊性,这个特殊性将打破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比如说,自由是个普遍概念,劳动力的自由却是一种特殊的自由,当工人“自由”地在市场上出卖他的劳动力时,他恰恰失去了自由。因此,劳动力的自由作为征兆恰恰颠覆了自由的虚假的普遍性。齐泽克认为马克思对自由、平等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都体现了这种征兆性的解读。
既然征兆就是意识形态的内在的崩溃点,意识形态批判就要揭示普遍性的虚假性,把它拒斥的内在的排除点作为真实普遍性的唯一点。为什么内在的被排斥点是真实普遍性的代表?齐泽克主要运用了黑格尔的观点重新思考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在他看来,没有中立的普遍性。普遍性不是对具体内容的共性的抽象和概括,相反,普遍性都建立在对某些特殊内容的排斥和压抑的基础上。由于这些被排斥的在等级制度中没有恰当位置的特殊内容阻止了普遍性的完全实现,暴露了普遍性的虚假性,它们恰恰具有了政治上的普遍性的意义。以希腊“人民”为例,齐泽克认为希腊“人民”之所以具有普遍性不是因为他们在人数中占多数,也不是因为他们处于社会等级制度的最底层,而是因为他们在社会等级制度中没有恰当的位置。他们越是参与到社会政治行为中,越是发现自己已经被排除了出去,这种特性将会直接颠覆社会的虚假的普遍性,使他们成为真正普遍性的代表。齐泽克认为我们应以同样的方式来理解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之所以代表全人类,并不是因为它是最底层的、最受剥削的阶级,而是因为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活矛盾’,也就是说,它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的根本失衡与矛盾。”[2]319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排斥物”和“剩余物”就使他难以被资本主义的社会体系所同化,他将宣告这些努力的最终失败。因此,无产阶级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征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
从以上对希腊“人民”和无产阶级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意识形态批判就要对普遍性中的具有结构必然性但又无法找到适当位置的特殊性进行征兆性的解读。但是,齐泽克认为仅仅阐释征兆还不够,还必须认同征兆。“这种认同征兆的程序,正好(但也必要)对立于标准的意识形态批判,即在某种抽象普遍概念背后辨认出某个特殊内容,亦即将中立的普遍性斥为虚假(人权中所谓的人,其实是白人男性业主……):我们哀衿地标举(并认同)具体实存秩序中的内在例外/排除之处,亦即那‘厌弃物’(abject),将之视为真正普遍性的唯一所在。”[2]317通过这种对普遍性的新的解读,意识形态批判的程序发生了某种颠倒,不是要揭示普遍性的虚假性,而是要认同征兆,将普遍性所必然排斥的特殊性确立和提升为真正的普遍性,从而实现意识形态批判。
三
我们先来比较拉克劳、墨菲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这两者的差距十分明显。正如齐泽克评价的那样,“对拉克劳来说,这个落差是普遍性的缺席完满与某个偶然特殊内容(作为这个缺席完满的替身)之间的落差;对马克思来说,这个落差则是普遍性的(特殊)内容内部的落差,亦即普遍性的‘官方’内容与其不被承认的前提(这种前提包含了一整套的排除法)之间的落差。”[2]250这种不同源于他们对普遍性的不同理解。拉克劳和墨菲认为普遍性是虚空能指,等待着某个特殊内容的填充,所以,普遍与特殊的冲突就不是发生在普遍性的内部,而是在两者“之间”。也就是说,普遍性与特殊性是相互外在的,特殊性对普遍性的填充使普遍性具有了暂时被固定下来的含义,因此,两者的矛盾只能以一种偶然的、链接的方式得以外在的解决。而马克思在理解社会及意识形态概念时,是从普遍性的内部来理解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统治阶级为了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利益,总是宣称自己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是全体人民普遍利益的化身,因此,各种特殊的利益就被压抑和排除。因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处理的是普遍性与其被排除的特殊性之间的内在的冲突。
由于对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的理解存在差异,拉克劳、墨菲与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大不相同,两者的意识形态批判路径也截然不同。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恰恰是发现普遍性背后所掩盖的特殊利益,比如,普遍人权实际上是白种、男性、有财产者的权利,并不如它所宣称的那样是普遍性的化身。也就是说,这种虚假的普遍性本身就是意识形态。而拉克劳“则不愿意立刻将普遍形式本身斥为意识形态(掩藏了某个不被承认的特定内容),而是坚持认为空白的普遍性与其限定的内容之间有道鸿沟:空白的‘人权’普遍概念与其原来的特殊内容之间的连结是偶然的——也就是说,一旦被提出,‘人权’就开始成为一个空白意符,而其具体内容为何,则是可以透过竞争并加以扩展的。”[2]251因此,他们的意识形态批判就演变为霸权的斗争。
如何理解拉克劳、墨菲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差异性?在齐泽克看来,两者都揭示了普遍性的虚假性,揭示了普遍和特殊之间的裂缝,不同的是,马克思从普遍性偏袒某种特殊利益的角度来论述,拉克劳则把这种普遍性看成是空虚的框架,各种特殊性围绕着它展开霸权的斗争。齐泽克试图找到能将这两者结合起来的途径。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要从普遍、特殊和个别三者的关系来理解,“我们这时应该考虑到三个(而非两个)层次:空白的普遍、使空白普遍霸权化的特殊内容,以及个别,亦即削弱了这种霸权内容的病症性过剩。我们立刻可以看到,在什么意义上,个别即是普遍与特殊的辩证统一:个别(病征性过剩)证明了普遍与特殊之间有所落差:证明了,普遍在其具体存在之中总是虚假的(由某种特殊内容霸权化,因而包含了一系列的排除)。”[2]252-253经过齐泽克的改造,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的虚假的普遍性便被拉克劳和墨菲的被特殊内容霸权化的普遍性所代替,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落差便被征兆(病症)所证明。由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在后马克思主义的视阈下获得了新的解读。
在后马克思主义视阈下,拉克劳、墨菲和齐泽克对意识形态理论的解读主要是在话语的层面、心理的层面展开的,他们力图将这种普遍与特殊的冲突从话语层面和心理层面扩展到社会和政治层面,从而对各种意识形态展开批判。这种解读有助于从新的视角回答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斗争形式的多样性所提出的新问题,因此,他们的解读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他们力图将话语的分析和心理的分析扩展到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尝试并不总能成功,因为两者存在着异质性。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相比,他们的共同问题在于缺乏历史性的维度,缺乏对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及克服意识形态的具体道路的现实思考。
[1] 齐泽克,拉克劳,巴特勒.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关于左派的当代对话[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2] 齐泽克.神经质主体[M].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
[3] 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