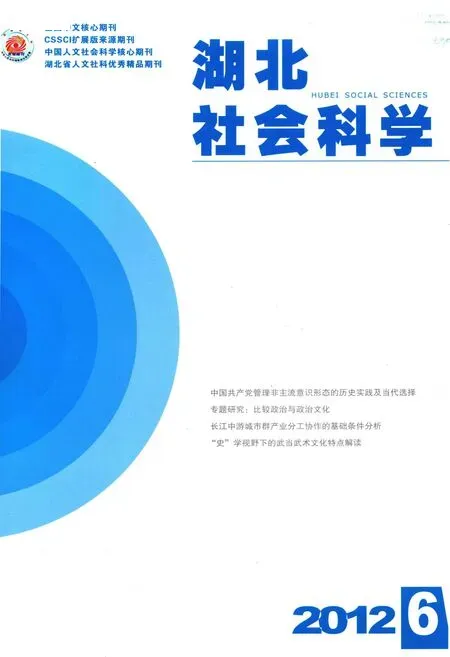游戏与图像
——略论赫伊津哈的两个命题
2012-04-12冯炜
冯炜
(浙江工商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游戏与图像
——略论赫伊津哈的两个命题
冯炜
(浙江工商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任何与游戏命题相关的研究都无法绕过赫伊津哈的“游戏论”,游戏论代表着文化批评的一种范式,作为对文化中游戏成分的研究,该命题影响了无数学者,也是赫伊津哈的文化观念的集中代表。赫伊津哈的另一个命题是贯穿学术生涯的“历史图像”,这一命题召唤出了历史研究中以图像为基本论证要素的“图像证史”方法和理论,在当代文化的“视觉转向”背景下,赫伊津哈的历史图像观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因此,在赫伊津哈的诸多理论中,“文化游戏论”和“历史图像观”两个命题尤其值得深入探讨。
赫伊津哈;游戏;图像;历史;艺术
近十年来,与布克哈特(Jacob Christoph Burckhardt)齐名的文化史大家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1872-1945)开始引起国内学术界关注。在此之前,这位历史学家的学术思想只是片断性地出现在相关研究当中,其思想研究单独成篇的文章屈指可数,这种状况与赫伊津哈在文化史上的地位颇不相称。实际上,经典文化史学家的学理一直未曾远离学术视野,布克哈特自不待言,就连兰普雷茨(Karl Lamprecht,)也曾是研究热点,奇怪的是,被公认为学术大师的赫伊津哈的整体思想竟然一直乏人问津。所幸的是,随着近十年来“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研究的高歌猛进,国内学术界对古典文化史理论的整理不断深入,赫伊津哈的学术思想逐渐浮出水面。综合评判赫伊津哈的学术成就,可见文化批评和历史研究两个,文化批评成就首推“文化游戏论”,历史研究成就当属“历史图像观”。
一、游戏的有限性
“文化游戏论”是国内学界对赫伊津哈理论研究的热点,以至于人们偶尔会忘记他是一个历史学家。确实,相对于为他赢得学术地位的《中世纪的秋天》(The Autumn of the Middle Ages),更具人类学价值的《游戏的人》(Homo Ludens:A Study of the Play-Element in Culture)概念明晰,且提供了一种研究范式,对中国文化研究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自然更能引起中国读者共鸣,但是,如果我们认为赫伊津哈的真正思想就是“游戏学说”,甚至认为他的学术重点是在文化批评领域,那就犯了一个错误。“游戏”(play)只是他阐发历史理论的一个概念,从本质上来说,他可被称为文化史家、观念史家甚至想象史家,也就是归根结底他还是一个历史学家,其文化批评总是是跟历史研究结合在一起,对历史的持续关注是其学术研究的重心,而文化批评家的身份只是历史研究之余的一个延伸而已。我们注意到,对赫伊津哈多有推崇的艺术史家贡布里希(E.H.Gombrich)认为如果有十个人读完《中世纪的秋天》,只会有一个人读完《游戏的人》,尽管后者更广为人知,[1](p262)这并不是说《游戏的人》更加晦涩难懂,实际上该书行文流畅、文笔清新且概念明晰,贡布里希的意思是说,读者并未真正深入了解赫伊津哈的文化游戏说。
对照赫伊津哈的其它著作,《游戏的人》更像是一次学术探险,在此书中所阐发的主要概念带有浓厚的怀疑论色彩,尽管在相关阐述中他高度肯定游戏的价值,但他同时也认为,游戏是靠不住的,甚至是残酷的,只要对现象做出是“游戏”还是“严肃”的判断,人的道德良知立即就会成为检验的试金石:“一旦真理与正义,同情与宽容成了我们行为的判断,我们焦虑的问题就失去了意义。一点点同情就足以使我们的行为超越理智的鉴别能力。我们的良知起源于正义和神恩,这就是我们的道德意识。良知总是以永恒的沉默淹没我们提出的问题。”[2](p245)——这是他在《游戏的人》结尾当中的一段话,在对游戏说进行种种精彩论述,堪称游戏的最具冒险性的阐述之后,他突然给整文以这样的颠覆性结尾,即使通读此书的人仍然对此迷惑不解。如果我们对赫伊津哈的游戏论与其研究就会发现,赫伊津哈认为,游戏是及其脆弱的,因为现实随时会侵入游戏的领地。严肃的警醒,会将一切游戏化为乌有,这个令人扫兴的结局几乎是无法避免的,问题就在于,游戏总是处在严酷现实的包围中,贡布里希曾举过一个例子:儿童们扮演海盗和侦探,一旦玩得入了迷,骑着它玩得不亦乐乎,因为他沉浸在自我创造的游戏中,分不清游戏和现实的界限了,而此刻一个大人突然会很扫兴地来破坏孩子的游戏情境,这个大人就成为了搅局者(Spoil sport)和破坏游戏者。[3](p20)“(搅局者)退出游戏之后,他揭示了这个游戏世界的相对性和脆弱性,他只是短暂地隐藏到游戏人的队伍中。他使游戏里的幻觉(illusion)荡然无存,illusion这个词涵义丰富,但基本的意思是‘游戏在进行’。由此可见,搅局者是必须要被赶下场的,因为他威胁着游戏人社群的生存。”[2](p13)在赫伊津哈看来,游戏的发展跟儿童的成长是一样的,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向前,人类最终将丧失游戏感。他谈到古典时期的战争富有游戏特性,是博弈(game)而不是战争(war),而现代战争却如此你死我活,“全面战争”(totalwar)的理论提出以后,战争的游戏成分被完全排除了。[2](p97)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这本书的出版日期是1938年,正是欧洲即将卷入人类史上最大规模战争的前夜,已经有过一次战争肆虐的欧洲即将陷入一场更大范围的灾难,有礼有节的游戏精神还有用吗?对比往昔,他感到深刻焦虑,从而开始怀疑游戏的价值。事实上,我们能看到这样一种自我怀疑精神完整贯穿在他的学术生涯中。
赫伊津哈在《游戏的人》的结尾处强调道德对游戏的破坏,这并不意味着他准备抛弃游戏的意义,而只是停下来反躬自省,游戏和道德究竟什么是更有意义的?他的回答是,如果只能选择,那就是道德,因为与道德属性相伴的是严肃和良知,人不能永远置身儿童状态,终究要长大面对残酷的现实世界,所以在道德形而上学属性这一点上,他与康德(Immanuel Kant)自然是一脉相承的。几乎找不到任何像他那样的文化批评学家,在辛苦构建了理论大厦之后却亲手将其推倒,当然,在理论基础上构建的任何学说不论多么光彩绝伦,终究是要在历史中被修正甚至被颠覆,而且这一切在同一本书里发生,就这一点来说,赫伊津哈对自己几乎是残酷无情的。但这并不会使他陷入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最核心的绝对理念始终是坚固的,他是一个坚决捍卫西方文化和古典文明的学者,读者恐怕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对此感觉还不甚清晰,不妨看看他的20世纪30年代的道德论著《明天即将来临》(In the shadow of Tomorrow),[4]在这本书里,他用一系列不容辩驳的口吻挺身捍卫西方文明。对信仰的坚持和对理性的捍卫使赫伊津哈承担了艰巨的思想任务,他认为,“文化的最终目的必须是形而上的(metaphysical),否则将不成其为文化。”[1](p276)“只有在坚定的、活生生的基本信仰的基础上,绝对真理的概念以及随之出现的道德准则的绝对可靠性才能与本能的生存意志的压力想抗衡”[1](p278)所以,他本质上是一个绝对主义者或普遍主义者,而绝对不是怀疑论者,更不会是相对主义者。
二、历史图像的呈现
由于游戏说的吸引力使得人们对《游戏的人》中的某个重要的观点视而不见了,这就是赫伊津哈的独特文化观点:重要的是游戏呈现出什么,而不是游戏为了什么。赫伊津哈认为,游戏呈现出高度形式化的特点,会通过一系列仪式性的视觉符号体现出来,这同时也是认识历史的关键。他认为历史最重要的就是“形式”,历史具有可以触摸的图像感,图像可以印证历史,这也是他在历史研究中的惯用手法。由此,我们注意到赫伊津哈的另一个重要命题:历史图像,这是他作为历史学家的最突出贡献。
实际上,在《游戏的人》中视觉图像随处可见,历史学研究,可看作是历史的视觉呈现,赫伊津哈把这种历史探究方式称为对艺术的最纯粹享受,[5]在这里他想到的是文德尔班的观点:“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复活过去的画面。他必须要打造现实里存在过的画面,就像艺术家描绘他当前的想象中存在的画面一样。”[6](p197-198)1905年,赫伊津哈在格罗宁根大学的就职演说中,有这样一段话:“它(审美态度)协助我们在脑子里唤起活生生的图像。正如文德尔班所言,自然科学的趋势是抽象,历史想象的倾向是构拟图像。再者,自然科学的一切知识必须要转换为严谨的概念,对其冷静的属性而言,一切形象都显得太张狂;相反,历史的任务则截然不同。如果历史要完成其使命——唤起过去的情景,它就必须要跨越纯概念的界限,生动展现直觉的回应,换句话说,他必须要召唤动态的形象。”[6](p205)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历史学家之所以不太情愿承认历史与艺术的关系,不是因为来自心灵深处,而是来自于想当然的认定,认为历史应该遵循严格的方法论。他认为历史研究与科学方法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历史其实与艺术创造更一致,因为“历史研究和艺术创作的共同特征是构建形象的方式,”[6](p195)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1919年,赫伊津哈写作了一部专门考察14、15世纪勃艮第与弗莱芒(主要是布拉邦特地区)的生活、思想与艺术的文化史著作《中世纪的秋天》。赫伊津哈的历史研究强调细节,虽然《中世纪的秋天》被认为研究的是14、15世纪法国、荷兰文化史,但其实书中极少涉及法国或荷兰省,主要是研究“勃艮第”和“潮湿的勃艮第”——一个16世纪以后被称为尼德兰地区的一部著作,更进一步说,此书的着眼点大多都来自勃艮第宫廷以及弗莱芒的“布拉邦特”地区的历史。这部历史学名著的写作灵感源于一次思考体验,在一次散步中,赫伊津哈思考着尼德兰画家凡·艾克兄弟(The Van Eycks)以及同时期北方写实主义画家的作品,忽然间就有了要把历史视觉图像呈现出的念头。[7](p38)该书的结构和主导思想展现出了他的深厚艺术修养,其中探讨造型艺术及艺术象征的章节占了一半以上的篇幅,所以不少人也把《中世纪的秋天》称作艺术史专著。
赫伊津哈认为历史意识是一种产生于图像的视域(vision)。他提出,图像是历史灵感的唯一重要源泉,在历史研究中,历史学家应该以图像为先,因为只有通过图像,人们才能真正看见往昔;只有通过图像,人们才能更富有历史感地理解过去。在他看来,离开艺术甚至无法形成一般的历史观念,他举的例子是:如果仅仅阅读教皇谕书,而不去观看中世纪泥金手抄本,谁都不敢说他能真正了解13世纪。[7](p37-38)这个观点正是基于视觉中心主义的客观现实。在西方,视觉中心主义的确立具有清晰的历史脉络,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感官等级制开始,到开普勒以后的现代科学的兴盛,再到笛卡尔的“我思”哲学的确立,还有15世纪古滕堡(Gutenberg)的活字印刷革命,这一切都在不断强化视觉中心的地位,形成了一种所谓的“视界政体”。[8](p10)不过,将图像当作历史证据来使用,在西方是从17世纪才正式开始的,直至20世纪初,德国学者瓦尔堡(Aby Warburg)创立了解读图像的方法,即“图像学”。根据哈斯克尔(Francis Haskell)在《历史及其图像》中的研究,有关图像运用问题的激烈辩论曾延续了三个世纪,辩论的双方一是吉朋(Edward Gibbon)等历史学家,属于怀疑论者,另一方是米什莱(Jules Michelet)、丹纳(Hippolyte Taine)等人,肯定图像证史的功能,[9](p5)最后的结果是图像运用派赢得了胜利。那次辩论最大的成果就是促使迎来了一个图像学的“英雄时代”,从而使得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一个艺术史的真正的黄金时光,瓦尔堡、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贡布里希等大批杰出的图像学家相继诞生。但是在通史领域,图像运用派并未占优,只是在文化史中运用图像不再成为障碍。从80年代开始,人文科学领域的“视觉转向”成为一个激烈讨论的话题,一批学者认为,作为历史的解释工具,图像比文字更有力,“图像证史”成为了历史学家关注的焦点,比如哈斯克尔在《历史及其图像》中系统证明了该史学实践的有效性。[9](p5)由此,赫伊津哈的学术思想重新进入主流研究视域。
正因为强调图像的作用,赫伊津哈的史学带有浓厚的视觉化风格,他曾经说,历史学家在他设计的形象周围,不仅仅画线条,而也要给它们涂上颜色,使它们变得很形象,还给它们充满幻想的暗示,“从羊皮纸文件上记录的世界里,涌现了真正的城市生活的图像。”[10](p144-145)赫伊津哈的这种历史叙述方式很容易滑向激情和臆想过度的浪漫主义,我们在他的早期论著中到处都能看到这种危险的倾向,尤其是当他以文化批评家的身份出现时,但是,他最终抵御住了浪漫主义的诱惑,支撑着他的全部生命并促使他抛弃浪漫主义艺术感转而坚定地寻求真理的,正是他对于绝对价值的信仰,他的绝对价值就是基督教的价值和理性的价值。[1](p275)这是一种正统的古典文化史模式,尽管后来的学者对此批评不断,但这一文化史模式并未随之沉寂,实际上,新文化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1997年所出版的论文集《文化史的多样性》(Varieties of Cultural History)当中表达了他对文化史的看法。他认为由布克哈特和赫伊津哈所代表的古典文化史模式无法被其它新的正统所取代,所以,伯克才提出以社会(文化)人类学来激发出一条创新研究路径。[11]
《中世纪的秋天》可以看作是把话语和图像互相交织在一起的游戏。荷兰历史学家威廉·奥特尔斯佩尔(William Otterspeer)认为在赫伊津哈的所有著作里,都能看到那种文本与图像相互交叉的现象,他把这个特点称为“用对比编织成的织物。”[10](p94)这就是一种视觉对照,或者可称为联觉现象。联觉不仅体现在图像与文本的交叉、历史与艺术的交叉,还有社会和历史的对比阐述,以及感官印象中的对比和交叉,敏感和迟钝、明亮和模糊,轻度和重度。这种感官的敏感性,这种靠联觉和气氛进行创作的方法,从一开始就是赫伊津哈的写作特点,其核心早就存在于他对语言来源的研究之中。如同已经说过的那样,他试图在其中抓住语言被创造的时刻,即话语自发形成的时刻,赫伊津哈假定,语言是在感官印象的抒情混合中产生的,即在联觉中产生的。[10](p161)图像与文本的关系早就存在于关注视线中,比如亚里士多德就论述过诗歌与绘画的平行关系,贺拉斯的名言‘诗如画’更是建立了图像与文本的亲密关系,西方历史上,关于图像与语言的关系的争论,可谓是一场“符号交锋”,所以,米歇尔(W.J.T.Mitchell)将图像与语词比喻为不同语言的两个国度,但它们之间保持着一个漫长的交流与接触的关系。他认为不要去打破它们之间的国界,也不要强调它们的区分,只要保持它们之间的交流即可。因为这些细节不可能虚构出来,而首先是一种初级观察的结果,所以它们显得非常“真实”。[12](p428)对赫伊津哈来说,图像与文本的关系不存在隔阂,正如他觉得历史研究与艺术创作是相通的,因为它们都旨在塑造图像。赫伊津哈曾将历史喻为“视像”,强调直接与往昔接触的感觉。后来,他还借助视觉语言,把文化史研究方法称之为“镶嵌艺术法。”[6](p195)
三、历史图像的深入
不仅赫伊津哈如此,像德罗伊森(J.G.Droysen)、布克哈特、哈斯克尔等著名历史学家都从图像中获得了丰富的营养,他们的思想和著作都充满了如同赫伊津哈历史研究中的“图像性”。[13]赫伊津哈特别强调历史学家捕捉过去和再现过去的能力,同时,他试图在历史叙述中综合个别与普遍的因素,对赫伊津哈来说,历史理解必须掌握历史的个体性与普遍性的脉络。[14](p51-53)比如,用唯名的概念赋予过去以一种形式,这在文化史的研究中是一个普遍现象,因此对赫伊津哈而言,对实在采取一种唯名论(nominalism)的观点也就意味着历史思想的扩充。[15]这是赫伊津哈历史图像的一个别致的观点。还有,赫伊津哈认为视觉符号可以引导出历史中的象征意义,在象征关系中可找到审美要素,即使更加抽象化的数字亦可传达出象征意义,数字成为象征的固有形式,也就有了审美意义,他发现在中世纪晚期历史的文化中这样的象征性联系比比皆是,比如,基于数字“十”和“十五”的象征体系会延伸出从主祷文到受难时刻,从诗篇数量到天然习性的符号。[16](p221-222)但是,赫伊津哈后来也发现,这种象征手法是僵化的,它们就像是单纯的数学运算表一样一一对应,当这些数字成为固有的思想原理之后,象征手法就会缠绕在思想的功能上,逐渐退化为纯粹的习惯以致成为思想的顽疾,这就像寄生植物一样,从而最终导致审美意义的丧失。[16](p222)这和赫伊津哈对中世纪文化衰落的理解是一脉相承的。
尽管研究者所在的时代与历史事件所在的时代不同,但赫伊津哈坚持历史学家对过去的理解一定与他自身的当代文化相关,我们今天对赫伊津哈的研究也是基于这一思路。本文为赫伊津哈两个命题的简略论述,以后将对其学术思想进行深入研究。
[1][荷]约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M].多人,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
[2][荷]约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文化中游戏成分的研究[M].何道宽,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
[3][英]E.H.贡布里希.艺术发展史[M].范景中,译.林夕,校.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
[4]Johan Huizinga.In the shadow of Tomorrow[M].New York:W.W.Norton&Company,Inc.1936.
[5]张献军.赫伊津哈.伟大的文化史学家[J].世界文化,2010,(9).
[6][荷]约翰·赫伊津哈.17世纪的荷兰文明[M].何道宽,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10.
[7]曹意强.图像与历史——哈斯克尔的艺术史观念和研究方法[A].曹意强.艺术史的视野——图像研究的理论、方法与意义[C].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7.
[8]吴琼.凝视的快感——电影文本的精神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9]曹意强.序·论图像证史的有效性与误区[A].曹意强.艺术史的视野——图像研究的理论、方法与意义[C].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7.
[10][荷]威廉·奥特尔斯佩尔.秩序与忠诚——约翰·赫伊津哈评传[M].施辉业,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
[12]曹意强.图像与语言的转向——后形式主义、图像学与符号学[A].曹意强.艺术史的视野——图像研究的理论、方法与意义[C].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7.
[13]龙迪勇.图像叙事与文字叙事——故事画中的图像与文本[J].江西社会科学,2008,(3).
[14]Johan Huizinga,"The Task of Cultural History"[A].Men and Ideas:History,the Middle Ages,the Renaissance[C].tr.James S.Holmes and Hans van Marl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
[15]盛少辉.台湾西洋史研究的理论与实际:一个尝试[A].历史:理论与文化(卷二)[C].1999,(7).
[16][荷]约翰·赫伊津哈.中世纪的秋天[M].何道宽,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J05
A
1003-8477(2012)06-0135-04
冯炜(1974—),男,艺术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讲师。
本论文受浙江省高校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资助。项目编号:1090JF2210009G
责任编辑 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