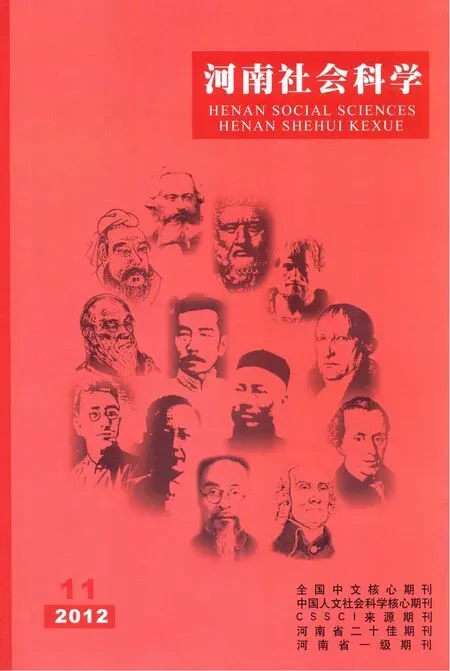长不大与不愿长大——《古炉》与《铁皮鼓》叙事人物比较
2012-04-12郭银玲
郭银玲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15)
一
小说创作,对于作家来说,必须面对的问题很多,其中一个问题就是:选择一个最为恰当的叙述人物。这正如利昂·塞米利安所言:“由于小说是对有意义的情感体验的连贯叙述,自然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由谁来叙述,或者由谁来讲述故事。”[1]也就是说,小说作为叙事的艺术,自然涉及叙述什么、谁来叙述以及如何叙述等方面的问题。这绝对不仅仅是所谓的艺术问题,其间蕴涵的是小说的艺术精神,体现的是小说家的文化精神建构及其审美价值、道德价值判断。甚至可以说,其间蕴涵着作家的写作伦理。也许正因为如此,历代的小说家们,都在叙事上追求着创新与突破,亦即建构起自己本时代的叙事艺术情态来。可以说,对于小说叙述者的创造与突破,已经成为20世纪小说艺术创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亦是现代小说对于传统小说艺术上超越的一个突出的标志。
在叙事人物上,20世纪以来的小说创作有一个非常特异的现象,那就是作家通过特异的叙事人物,来完成故事的叙述。作为叙事的人物,他们并非常态的而是异态的。外国的如卡夫卡的《变形记》,叙事人物是个变为大甲虫的推销员;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虽然有三个人物叙述故事,但最富有意味的叙事者恐怕还是傻子班吉;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也是“以一个小孩一天下午由他父亲带领去见识冰块这样一个情节作为全书的始端”[2];奥尔罕·帕穆克的《我的名字叫红》则是选择了一个幽灵作为叙述者等。就中国而言,为现代小说铺下第一块坚实基石的《狂人日记》,叙述者是个狂人即疯子;进入所谓的新时期,将孩子或傻子作为叙述人物更多,像韩少功的《爸爸爸》,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阿来的《尘埃落定》,贾平凹的《秦腔》、《古炉》,等等。
这些小说创作事实,似乎在证明着这样一个道理:小说作为叙事的艺术,优秀的小说家无不在叙事上狠下一番工夫,以尽力彰显其艺术特性功力。尤其是在叙事视角与叙事人物的选择上,作家们更是煞费苦心,把自己的艺术才能显现得淋漓尽致,给人以极大的阅读冲击力。也许是人们厌倦了司空见惯的正常人的叙述,或者正常人的叙述不足于彰显作家所要表达的生活感悟与生命的体验,他们便选择小孩或者傻子作为观察与叙事的视角与人物。也许正如有论者所言,“现代人生存的不确定性、尴尬性、困顿性、荒诞性,乃至虚无性,等等,致使20世纪的诸多文学艺术家们,做着如此的叙事艺术探索与建构,方能揭示现代人生存的内在精神状态”[3]。这便引发了笔者进一步深入思考的兴趣。
如果就中国现当代小说的叙事艺术创构而言,我们不可否认,从鲁迅的《狂人日记》以至今天,中国现当代小说家都或多或少受到了西方现代小说艺术的影响。对此我们不必讳言。西方小说不仅于文化思想精神上为中国现当代小说提供了丰富滋养,在小说的叙事艺术上,也提供了诸多的借鉴与启发。但从总体发展趋向来看,现当代小说是从模仿走向了自觉。问题不仅如此,我们更感兴趣的是,虽然中国在艺术精神的开拓上,似乎总比西方慢了那么一拍或者半拍,但是,中国的小说家们不仅于艺术精神上与西方实现着同构,而且也追求着自己的艺术精神建构。这似乎与前几年的世界一体化等文化文学思潮有着密切的关系。更为重要的,则是中国作家经过一个世纪,特别是20世纪最后30年的思考与探寻,已经意识到了在与世界实现同构中应当探寻自己的路径。其中一点,我们认为就是叙事艺术的自觉。
正是这叙事艺术上的自觉,方使我们具备了与西方进行平等比较的资格。我们认为在不具备艺术自觉意识时,我们是不具备与人家进行平等对话资格的。故此,此前与其说是在进行文学艺术的比较,不如说我们是在做着影响的探讨。也许这样认识问题有些偏颇,但毕竟我们的小说叙事艺术已经奏响了自觉。对此,我们虽然还无法确切地说这种自觉起始的具体年月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进入21世纪后,不管对于小说的成就作出怎样的判断,与20世纪末的30年相比,中国的小说创作艺术正在努力脱离着西方的阴影,并走向自觉。笔者正是在这种小说叙事艺术发展语境下,来展开本文研究对象的论述的。
二
贾平凹与君特·格拉斯是处于不同时代、两个国度的作家,之所以把他们二人联系在一起,那是因为他们所创作的两部作品《古炉》与《铁皮鼓》[4],在叙述视角与叙事人物的选择上,表现出内在的共性特征。如果就所叙写的生活内容来说,两部作品显然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一个叙写的是发生在中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一个叙写的是20世纪初到中叶德国所经历的两次世界大战。但是,在题意指向的开掘和艺术叙事方面,二者之间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这也许是因为伟大的作家在对于人、人类及其历史等的思考与探寻上,具有着相通的艺术精神。比如,这两部作品在叙事上,就存在着许多值得人们玩味的相通之处。其中,这两部作品给笔者留下印象最深的,首先是作家所选择的叙事人物。非常耐人寻味的是,贾平凹与格拉斯在自己的作品中,都选择了一个侏儒作为叙事人物。而且非常有意味的是,《古炉》中的狗尿苔和《铁皮鼓》中的奥斯卡,均有着不明的身世,有着超常的特异功能,有着一种超越现实之上的神性。
但是,相同之中,却蕴涵着不同的意味。狗尿苔与奥斯卡虽然同为长不大(高)的侏儒,其间的差异却是极其耐人寻味的。
根据作品以及作家贾平凹自己的一些说明,我们可以判断,狗尿苔出现在作品中,应当是13岁。据作品交代,他是有自己的名字的:夜平安。“但村里人从来不叫他平安,叫狗尿苔。狗尿苔原本是一种蘑菇,有着毒,吃不成,也只有指头蛋那么大,而且还是狗尿过的地方才生长。狗尿苔知道自己个头小,村里人在作践他,起先谁要这么叫他他就恨谁,可后来村里人都这么叫了,他也就认了”[4]。如果从寓意想象的角度来阐释,可以说狗尿苔是由于生存的环境恶劣才长不高而成为侏儒的。按照我们习惯的思维,从生存的家庭与社会环境角度看,他爷爷被国民党军队抓壮丁到了台湾,他是伪军家属。这样的家庭出身,其成长的环境就可想而知了。当然,我们还可作出更进一步的分析,那就是在50—70年代,整个社会不正常的生活,特别是饥饿等因素,导致了狗尿苔成为侏儒。这些解释似乎都有道理,但又似乎全无道理。但不管怎么说,狗尿苔成为侏儒,绝对不是他的选择,而是客观条件所造成的。这既包括自然社会,又包括他自身的身体本身的发育条件。因为侏儒大都是天生的,而不是人为的。就此而言,狗尿苔长不大,并非一种主体的意愿,而是一种客观的无奈。
而奥斯卡却不是如此,奥斯卡不愿长大,完全是一种自主的选择,其中有着更为自觉的意愿诉求。奥斯卡未出生便有着自觉的意识。他厌恶这个由大人组成的世界,并不想来到这个肮脏的世界。要说无奈,那也就是出生,他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永远待在母亲的子宫中。奥斯卡是在两个六十瓦的电灯和一只扑向灯泡的飞蛾的阴影下来到这个世界的。他已经预感到人世或者成人世界的黑暗,一出生就想返回娘肚子里去,可是脐带已被剪断,再也无法回到母亲的子宫中去了。虽然出生他不能作出选择,但他却可以选择自己生存的方式,其间所蕴涵的人生哲学意味却是极其耐人寻味的。在一次宴会上,他目睹了成人世界的无耻堕落,由此便产生了拒绝成长的意想,他试图以一次毫无破绽的假摔去实现这一目的。他如愿实现了极不想加入成年人世界的愿望,在3岁生日时,他以自我伤残的方式,一跤摔成侏儒,身高保持在94厘米。由此可见,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一切行为似乎都是自己的选择,或者,他是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的。
狗尿苔与奥斯卡的身世之谜,也存在着差异性。狗尿苔从何处来?只知道他是蚕婆到镇上赶集抱回来的,究竟“是别人在镇上把你送给了蚕婆的还是蚕婆在回来的路上捡到的”[4],他的父母是谁,究竟因何而把他丢弃,以及蚕婆捡到他的具体情景等,这成了一个永远的谜。也许蚕婆是清楚的,但是,蚕婆始终未透露其间的秘密。这与阿Q有着某种相似。阿Q据说他先前即祖上是非常阔的。特别有意味的是他们二者的姓。阿Q据说还姓过赵,只是赵太爷不允许他姓赵,这便是原本有姓,但现在却只能处于无姓的状态;狗尿苔却是任何人都不得而知他原本究竟姓什么,却有着现实的必须接受的姓,也许只有让狗尿苔姓现在的姓以及保持现在的身份,方能满足人们的发泄欲望期待。
奥斯卡的身世问题,也是集中在姓氏上,所不同的是,他不清楚,他究竟是谁的孩子,亦即母亲与父亲和表舅哪一位结合之后产生了他。在他的妈妈与法定的父亲马策拉特和表舅扬·布朗斯基之间,存在着三角爱情关系。奥斯卡是以一种怀疑或者想象的眼光,来审视这两个男人的,他们是奥斯卡可能的或假想的父亲。由于扬与他有着一双同样的蓝眼睛,因此便认为他可能的生身之父是扬。但是,奥斯卡最终还是无法就此证明究竟谁是他的生父,其结果也就只能是把这两个男人都当做自己“可能的”父亲。这中间的寓意是非常强烈的。现代人发出了“我是谁”的疑问,而在确定“我是谁”的时候,首要的是需要确定我究竟是从何而来,我的父亲究竟是谁。一个连自己父亲都无法确认的人,又怎能够确认自己的身份呢?
这两个人物都有着一种特异的神奇功能。狗尿苔的神奇功能是与生俱来的。狗尿苔有着一只可以闻到一种特殊气味的鼻子,问题不仅在于他所拥有的鼻子,更在于他的鼻子所闻到的气味,“怪怪的,突然地飘来,有些像樟脑的,桃子腐败了的,鞋的,醋的,还有些像六六六药粉的,呃,就那么混合着,说不清的味。这些气味是从哪儿来的他到处找,但一直寻不着”[4]。除此,狗尿苔还有另外一种特异功能,那就是能够听懂飞禽走兽花草树木的话,与它们进行对话交流。这究竟为何,狗尿苔自己也不明白,他表面上无所特殊,但他又是无所不知似的,而又知得浑然茫然。正因为如此,他既生活于现实的人群之间,却又超于人群之外。其实,他有着一个与世界万物相通的秘密通道,正是这个秘密通道,使得他可以透析着世人的心灵。
奥斯卡的特异功能是在他3岁有意摔了一跤后得到的,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按理说,奥斯卡摔跤是他有意为之,但是,摔后生理发生变化,可以尖叫击碎玻璃,则是意外之发现。我们说奥斯卡具有超常的智力思维,并且从一出生便有着一种极强的自主意识,他的一切行为,可以说均是在自觉意识下完成的。因此,他利用以声击碎玻璃之特殊功能,做出了许多令世人不解而又非常尴尬的事情。他还有一种特异功能,或者叫做天赋,那就是敲铁皮鼓。他几乎是无师自通,把铁皮鼓敲到了化境。存在于奥斯卡身上的这两种特异功能或才能,随着他恢复长个而消失了。
这两部小说的叙述人物之间,有着许多相似与相异的特征,在这里我们着重谈了几个方面。目的在于为下面的论述作出某种逻辑上的铺垫,而不是进行全面的论说,亦即选择了怎样的人物作为叙述者。
三
接下来需要探讨的问题是,作家选择如此特异的人物作为叙述人,究竟要建构一种什么的叙事情态。也就是说,从特异的人物视角,怎样讲述故事,又表现出怎样的特异之处。
作为叙述人,不论狗尿苔还是奥斯卡,他们均参与到了事件之中,使得叙述具有一种“身在现场”的亲历性。但是,他们参与事件的程度是有所不同的。就其身份而言,狗尿苔作为贯通性的叙述人,并不是作品的主角,或者说最具艺术亮色力度的人物不是狗尿苔,而是霸槽。也许是致力于生活化叙事的缘故,作者有意消解主人公式的人物结构模式,追求的是群星灿烂式的艺术形象创造。故此,霸槽、蚕婆、善人,以及刘大柜、天布等人,共同构成了故事的人物建构。而贯通这些群体人物故事的人物,便是狗尿苔。狗尿苔是通过自己介入事件之中而完成其他人的故事叙述的。因此,他不是一个完全的旁观者,而是故事演绎者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或者说,狗尿苔的故事,构成了古炉村“文化大革命”故事的有机构成。而狗尿苔的介入,又是处于故事建构的边缘,或者说他的行为并不能主导故事的发展,因为他不是故事的主要担当者。相比之下,奥斯卡则有所不同,他不仅是故事的叙述者、亲历者,而且还是故事的主要演绎者。从叙述上看,奥斯卡是在叙述自己的故事,在叙述自己故事的过程中,也叙述了别人的故事。因此,奥斯卡的叙述始终处于主动自觉的地位。如果说狗尿苔是以亲历者的身份,在叙述别人的故事中也叙述了自己的故事,那么,奥斯卡则是在叙述自己的故事中,来完成别人的故事叙述的。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虽然参与故事之中,但是,又不是事件的主导者,往往被拒斥于事件核心之外,故此,他们又成了故事的旁观者、局外人,亦即他们是事件见证者。这就使得他们的叙述更具有了客观真实性,增强了叙述的客观可信度。“如果小说人物作为叙述者,在同别人的关系上,他只是一个观察者,这就像我们每一个人在观察现实生活中的情形一样。他只能客观地去对待其他人物”[1]。作为孩子,他们显然不可能成为社会事件尤其是重大历史事件的主角。狗尿苔不可能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角,奥斯卡也不可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主角。他们均处于国家叙事的边缘地带。正因为如此,他们就犹如作为一个极为次要的角色站在舞台上,在看主角演戏,或者是在配合主角演戏。这就使得他们具有了更大的自由度,随时出场下场,但眼光却始终盯在舞台上。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我们说狗尿苔与奥斯卡都是旁观者和见证者。他们虽然没有主演“文化大革命”与世界大战这两场人类的悲剧,但是,他们始终见证了这两场悲剧。他们犹如穿梭于事件之中的记者,以自己的摄像机记录下了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给历史留下了珍贵的影像。
作为叙述者,狗尿苔与奥斯卡最为特殊之处,自然是体现在他们的身份——孩子上了。作家选择狗尿苔与奥斯卡这两个孩子作为叙述人物,用一种孩子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看待大人的世界,以孩子的心理来感受事物,表现着一个孩子的生活与心灵世界。但是非常有意味的是,不论《古炉》还是《铁皮鼓》,其作品所叙述的世界,都是大人的世界。“文化大革命”也好,世界大战也罢,应当说其主角都是大人。《古炉》中的村支书刘大柜、霸槽、天布、善人、蚕婆等,他们以各自的角色及其行为,构成了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内容。《铁皮鼓》中的母亲与父亲、表舅,包括祖母等的生活与行为,演化着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这两部作品的故事叙述,则不是主要由这些大人们来完成的,而是透过两个孩子的眼光表现出来的。这样,小说所体现的就主要不是大人眼中的“文化大革命”与两次世界大战,而是孩子眼中的“文化大革命”与世界大战。实际上这里已经蕴涵了历史现实建构与历史叙述建构之间的比对。或者说,一个是大人们演化的历史现实,一个是孩子所见证与感受到的历史现实。正是这两个既密切联系、而又有所不同的历史现实,即同构与异构的历史现实,构成了文本所叙述的历史现实。于此,我们所读到的则主要是一种孩子的历史解读建构,这更显示出“文化大革命”或者世界大战的残酷与丑恶来。
问题不仅如此。本来以孩子的眼光进行叙述,就已经够特殊的了,但贾平凹与格拉斯显然并不满足于此。故而,狗尿苔与奥斯卡都是具有特异功能的孩子,因此,他们不仅表现出与大人不同的观察,而且也具有与一般孩子不同的感受力和观察力。“如果用常态与异态来表述叙事建构,20世纪以来,异态或非常态叙事,则成为许多小说家进行创新叙事艺术的选择”[3]。于此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作家为何不仅以一个孩子的视角进行叙述,而且还选择一个具有特殊功能的孩子来审视叙述?
以孩子的眼光来观察这个世界,其间已暗含了以孩子纯真善良的心灵,与充满残酷与丑恶的历史现实的比照。也就是说,作家选择孩子视角进行故事的叙述,其间包含着作家所要反映的人类纯真的天性,对于伦理、战争、革命、人性、信仰、爱情等问题及其价值观念的道德判断,追求的是以现代的乃至后现代的叙事艺术表现方式,进而去对人类文明、进步等问题进行深刻反思。而这些叙事的完成,仅通过孩子的视角显然还不够,故此,贾平凹、格拉斯便选择了狗尿苔、奥斯卡这样超常的孩子作为叙述人物,来表现那个人类心灵扭曲的时代。
从另一种角度来说,小说的叙事,总是体现着作家的目的性,作家总是要选择最为恰当适宜的叙述视角与方式来达到叙事目的。《古炉》叙述的是在商州山区一个名叫古炉的小山村所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很明显,贾平凹是要深刻反思这段梦魇般的历史。此前,这方面的文学作品应当说还是很多的。但是,如何更深刻、更特异地叙述这段历史生活,使之更深入这段历史生活的内里与本质,贾平凹自然是经过了深入思考的。贾平凹自己讲,“当时我的想法是不想一开始就写整天批判,如果纯粹写‘文化大革命’批来批去就没人看了。如果那样,一个是觉得它特别荒诞,一般读者要看了也觉得像是胡编的;再一个就会程式化了,谁看了都觉得没意思,我就想写这个‘文化大革命’为啥在这个地方能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土壤到底是啥,你要写这个土壤就得把这块土地写出来、呈现出来。正因为是这种环境,它必然产生这种东西。写出这个土壤才能挖出最根本的东西,要不然就会觉得不可思议,怎么能发生‘文化大革命’这种荒唐事情?所以《人民文学》总编和责任编辑看了之后也评价很高,提出是有荒诞意味的一部大作。因为我觉得‘文化大革命’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一个荒唐的事情”[5]。由此可否说,贾平凹不仅要叙述“文化大革命”的现实性,而且还须叙述出它的荒诞性。或者说,生活、社会、人性等,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代,都被扭曲了,而以狗尿苔这样一个特异孩子的眼光去审视,能够更为深刻特异。
很显然,格拉斯对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反思,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德意志民族的反思,尤其是对于德国法西斯的批判与反思。他选择奥斯卡作为叙述人物,似乎更为突出地体现出:“出于一个特殊的目的在一个特定的场合给一个特定的听(读)者讲的一个特定的故事。”[6]奥斯卡正是在白色的病床上,向人们讲述他所经历的两次世界大战,或者说是,他所体验与感受到的两次世界大战。他更具有着人类正义与良知的意味,他是在以一种非常严酷冷峻的目光,审视着人类及人性的丑恶。因为奥斯卡不仅仅是个孩子,在人们的眼里他还是个傻子,其实,他更是一个撒旦。孩子、傻子加撒旦,就是奥斯卡。也正因为如此,奥斯卡作为叙述者,便具有了超越一般人的思维,他所叙述出来的两次世界大战,便融会了撒旦对于人类的审判。
当然,叙述人物在完成整个故事的叙述中,自然也有着不可到达之处。以人物作为叙述者,总是具有一定的限定性,总存在着目光不能所及的地方。这虽然可以由其他人物所补充,但更为主要的恐怕还得由作家来完成。亦即由一个超越人物之上的叙述者来完成。这个叙述者被称为上帝,其内里就是作家。故此,在《古炉》与《铁皮鼓》中,便有了两个叙述者:一个是作为叙述人物的叙述者,也就是狗尿苔与奥斯卡,另一个则是无所不知的作家自身,这就是贾平凹与格拉斯。关于作家超越于人物叙述之上的叙事问题,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本文就不做论说了。
[1][美]利昂·塞米利安.现代小说美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2]加西亚·马尔克斯.加西亚·马尔克斯谈《百年孤独》中译本[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
[3]韩鲁华,储兆文.一个村子与一个孩子——贾平凹《古炉》叙事艺术论[J].小说评论,2011,(4):120—124.
[4]贾平凹.古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5]贾平凹,韩鲁华.一种历史生命记忆的日常生活还原叙事[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2011,(1):63—72.
[6][美]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M].陈永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