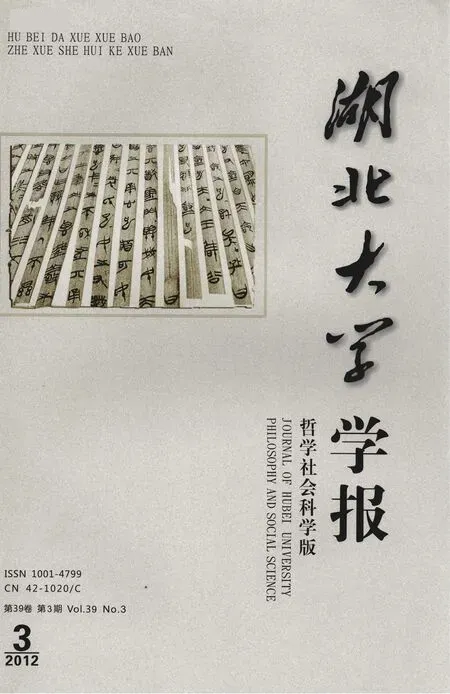告子人性论探析
2012-04-10周海春
周海春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告子人性论探析
周海春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告子的人性概念是从描述的角度对人的生物性事实的把握;“决诸”的范畴则起到从“是”推出“应当”的逻辑地位;“仁义”是内外关系域中的目的善;“不动心”是告子关于目的善的最高境界的思考。所以在告子看来,人性问题只是道德生发的基础,是道德活动的对象。“是”是改造的对象,价值是改造的结果,道德则是社会属性。
性;善;恶;仁;义
告子,生平事迹不详,《孟子》七篇有《告子》,《墨子·公孟》中也提到过告子。告,姓;子,男子之通称。告子,名不害。钱穆同意《墨子》《孟子》中的告子为一人,并估推其生存年代为公元前420年—350年。在这里所讨论的告子的人性论主要是以《孟子·告子章句上》为主要根据的。厘清告子的人性论有助于从反面说明孟子的人性论。
把握告子的人性论首先要注意告子对“人性”和“善”“恶”的区分,告子的一个基本思想是要区分“性”或“人性”概念和“仁”、“义”、“仁义”、善、恶概念。二者是不同的概念,不可把二者混淆。“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孟子·告子章句上》)告子说:人之“性”就像杞柳一样;所谓人的“义”,人做好事就像“桮棬”一样。不能把二者搞混了。认为人性就是仁义,就等于把“杞柳”当成了“桮棬”(用杞柳树加工成的洗澡、盛饭、装酒等的用具)。
一、性和人性:从描述的角度对人的生物性事实的把握
在告子那里,人性概念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人性概念的内涵是什么呢?从告子自己的表述来看,告子的人性概念是一个描述性的、认识性的概念。“古今中外思想家关于人性的不同观点,大致可以划分为评价性观点和描述性观点两种类型。评价性观点是用善恶概念看待人的本性的观点。描述性观点是只对人性作自然描述而不作善恶评价的观点”[1]30。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告子章句上》)“谓”有“说成”“叫做”等含义,可以看作是一个认识论的概念。“性”描述的是一个客观事实。“性”是对“生”的语言描述和说明。从现代哲学的角度引申开来,也就是说,“性”是一个认识论的概念,认识的对象是“生”。“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曰:‘然。’”(《孟子·告子章句上》)我们把“生”的东西说成“性”,就像我们把白说成白一样。显然二者是事实和对事实的语言表达,是事实和对事实的认识的关系。“性”和“生”之间是认识结论和认识对象的关系,是语言表达和表达对象的关系。
“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告子章句上》)。在这里,告子一再强调“人性”不分“善”和“不善”,就是强调“人性”概念是一个认识论的概念,是对人的事实性的认知,不等同于使用“善”“恶”等概念对人进行价值认识或者价值评价。在告子看来,首先要去认识人性这一事实。
性有产生、生命、生活、肉体等等不同含义。告子的“性”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生”。由于告子把人性概念看作是一个认识论的概念,自然“性”概念描述的对象就是一个客观事实,而不是一个价值事实。“性,犹杞柳也”(《孟子·告子章句上》)。“性,犹湍水也”(《孟子·告子章句上》)。这里把人性概念说明的对象说成是像“湍水”、“杞柳”一样。显然,在告子心目中,人性概念反映的是一个实体性的东西及其运动。
告子把人性概念看做是一个反映人的生物规定性的概念,自然有可能混淆人的物种属性和其他生命的自然属性之间的差异。告子的这一看法引起了孟子的不满。如果性“犹”杞柳的关系就等同于白“谓”白,就等同于生“谓”性的关系,从句子形式上就可以推导出一个陷阱。“‘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孟子·告子章句上》)孟子正是看到告子的这一说法包含的这一可能性,从句子形式上进行了推导。孟子显然使用了一定的辩论技巧,“白羽”是动物的类别具有的属性,“白雪”是无机界的现象,二者显然是不同类别的“白”。如果二者之间有“犹”的关系,自然就可以推出“犬之性”和“牛之性”、“人之性”之间有“犹”的关系,可以互相称谓,有“谓”的关系。就会得出“犬之性”谓“牛之性”,“牛之性”谓“人之性”的说法。把“生”说成“性”,牛、犬都是“生”的东西,人也是“生”的东西,那么他们都是“性”,就会混淆这些类别存在物的“性”的差别。告子是否自己坚持“生”的概念是一个大类的概念,就像“白”一样,其外延可以涵盖“白羽”、“白雪”、“白玉”这些不同小类表现出的白的属性和特征呢?从其肯定性的回答“然”来看,告子是承认“生”的概念和“性”的概念涵盖了一切物种的“生”,包括有机界和无机界。牛、犬、人之间从“生”这一点来看是有共性的。那么,告子是否就此否定了“人”的“生”的特殊性呢?这一点,我们无法从告子仅存的文本中得到明确的信息。在这个争论之后,紧接着有如下一段话:“告子曰:‘食、色,性也。”(《孟子·告子章句上》)在这段话之后,告子就谈了仁内义外的观点。从这段话来看,告子只是澄清了“性”的内涵和外延,这个内涵就是人的生活,尤其是肉体需要,外延包括饮食,喜爱美色这些物质生活活动。如果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这些活动显然具有和其他物种一样的自然性,但同时是以人的方式来进行的。饮食活动本身就是人自身的生产活动,且是以人类生产出相关的饮食对象为前提的,是以人的方式来进行的。这一点已经和动物界有了差别。告子是否也有类似马克思的看法呢?很难从句子中获取明确的信息。如果把这句话看作是对孟子混淆牛、犬、人质疑的回应,那么,我们大致可以认为,告子基本坚持的是人和其他物种在生物性上具有共性,如果要谈人的特殊性的话,就要从仁义和善恶的价值的角度来考虑了。
告子把人性概念看成是一个认识论的概念,且把说明的对象理解为一种具有物种性质的对象,会遇到一定的理论难题。不过,如果从人性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告子应该是坚持了描述主义的人性观点,又没有忽略人和其他物种具有生物共性。“特别是无论是评价性观点还是描述性观点,都把人性理解为人的特性,或者说理解为人不同于其他种类事物特别是动物的特征。这种理解是有问题的,因为这种理解忽略了人与其他种类事物相同和相通的共性方面,使人成为远离宇宙万物的孤零零的‘高贵者’”[1]33。告子坚持了描述性观点,但没有忽略人和宇宙万物的生物联系。
概括起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整体的印象。告子的性或者人性的概念不是一个道德价值概念,其说明的对象是“生”。“生”可以用来说明人和其他事物共有的自然属性,性或者人性的概念,也是说明人具有的和其他事物共有的自然属性的。但同时也可以认为“性”也说明了人具有的独特性,这就是“食色”活动。
二、“决诸”:事实之“是”如何推出价值之“应当”
在西方伦理学思想传统中,“是”如何推出“应当”是一个理论的难题。在中国伦理传统中,是否也有类似的思考,或者某些思考可以看作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答案呢?显然,告子的思考可以看作是触及了这一理论问题。
“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孟子·告子章句上》)“义”是一种善,但这个善是怎样在“性”中发生的呢?是通过改造加工才发生的。也就是说“性”和“义”的关系是材料和改造加工后物品之间的关系。告子在论证这一主题的时候暴露了他把握人的思维模式。他所说的“仁义”是一个人对一种材质进行改造得到的一个具体的、有一定人生或社会功能和价值的结果。“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告子章句上》)“决诸”依然是一个人为的改造加工性的概念。人为的加工工作导致人有正面价值和负面价值,导致人有善有恶,而就人性而言,无善无恶。
显然,在告子那里,加工改造就是值得肯定的一件事情,没有对人的人性的改造就没有仁义。在孟子看来,对人进行改造本身就不应该给予肯定的价值评价。“孟子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棬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孟子·告子章句上》)孟子显然把“杞柳”等同于整个“人”,改造杞柳,就等同于改造人,其实就是伤害人。因为,你不可能顺着杞柳的本性把它变成“桮棬”。一定是伤害了杞柳的本性才把它便成了一种有工具价值的事物的。在孟子看来,既然告子主张应该伤害树木的本性然后把它变成筐等用具来满足人的需要,那么告子也就会同样赞同伤害人的本性。
告子似乎没有对改造本身进行过多地价值的评价和思考,而只是把它看成是善恶价值产生的具有普遍性的根源和基础。在用“水”来讨论人性的过程中,告子和孟子涉及到了“决诸”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告子显然认为,加工对善恶价值来讲具有普遍性,是善恶产生的普遍性根据和基础。孟子则坚持“决诸”具有特殊性,或者仅仅是可能性之一,而且往往是导致恶的根源,是一种导致负面价值的价值活动。
“是”是如何推出“应当”的呢?如果我们把“桮棬”看成是“是”,“仁义”是“应当”,那么“是”过渡到“应当”,就是“决诸”。“是”是人对自身的“性”的描述和认识,而“应当”是人对自身的“性”的加工改造的结果。告子的这一思维方法大致可以看成是对象性的思维方式。从“我”出发把“我”和“性”的关系理解为对象性关系。“是”和“加工”概念都涉及人对自我的自我意识。“是”涉及的是人对自我的认识和描述,其结果用“性”来描述“生”;“决诸”涉及的是人对自我的改造加工,其结果是善恶。
如果把“义”理解为一种改造关系,就面临一个问题:是谁来改造呢?是自己,还是别人;按照谁的意愿来改造呢?谁的意愿可以成为改造的标准呢?改造的对象是什么呢?改造的对象应该是相对明确的,是人的生物性的材性,也就是告子自己所说的“性”或者“人性”。对这个层面有所加工并不一定会伤害到整个人。从这一意义上看,孟子的反驳并不完全符合告子自身的思想过程。“我”加工“杞柳”成“桮棬”,加工的主体是“我”,“桮棬”是对人有用之物。既然告子认为人的“人性”需要加工改造,就说明告子认为在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中的“人性”是会伤害这种关系的和谐的,所以需要改造。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告子把善恶产生的根据看成是人对自我的改造活动,其涉及的是人对自我的行动或者行为的关系。
在告子那里,“决诸”本身没有善恶,或者不应该对其进行价值评价。“告子曰:‘言义而行甚恶’,请弃之。”(《墨子·公孟》)说明告子很重视道德行为的善。“言”本身并不是善恶的根源,“言”更多地应该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是一个如何描述对象的客观事实性的问题。在告子看来,墨子只是讲义,而行为却是恶的。所以不应该追随这样的人。从有限的信息来看,告子似乎重视行为导致善恶,而不重视用善恶概念来评价事物。所以告子自然很反对用善恶等具有道德价值色彩的概念来说明或者认识“人性”。
告子提出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每个人都有价值追求,都是把自己的生活当作是有某种“意义”的生活来“活着”,来“过日子”的。这就是说,每个人都活在意义的追求之中。所谓的加工导致善恶,在告子那里坚持了描述主义的基本思维方法,而没有采用价值评价的观点思考。如果加工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追求活动,如果是价值追求活动导致了价值的分别,就要承认人本身就具有追求积极的人生意义的冲动。这就需要有对人的一切活动持有价值评价的认识方法。把“性”和“杞柳”放在一起考虑是用一个物来说明人。用一个种类的物来说明人的本性,是把人的一个生存对象用于说明人本身。这是一种对象性思维把握人的方式。用自然存在物、社会存在物是否能说明人呢?既可以也不可以。人是自由的存在物,人具有一种普遍性,可以具有其他一切物类的性质,如具有水生动物的“游泳”性质,鸟类的“飞机”性质。所以,可以用描述主义的观点说明这种生物的共性。但其中的任何一个具体的类别,包括具体的、历史中出现的人生存在样态都不能具体地限定人性是什么。因为人有美的尺度,有自由的尺度,并且能够按照自由的尺度去对待自己和万物。人可以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成为历史条件所允许的其所是的物种。这就需要对人有一定的价值性的观点来进行说明,否则对人的说明是不完全的,或者是不够深刻的。
三、仁义:人我内外关系域中的目的善
告子用“桮棬”类比“仁义”,说明在告子心目中“仁义”应该是体现功利性价值的。告子的道德论,如果从西方伦理学传统来观察,具有一定的目的论的色彩。目的论用行为目的和结果的善性来证明,强调对结果的计算。价值方面的考虑,追求什么,道德的根据在于它的功利目的或目标、后果等。
在告子这里,仁义存在于什么领域呢?显然是人与人、人与物的对象性关系领域,其中人是主体,他人和他物是客体,是一个主客体关系的领域。这个领域和“决诸”存在的领域显然有差异。“决诸”存在的领域主要是人对自我的关系领域,虽然其中也会涉及到人与他人或者他物的关系。告子认为“义,外也,非内也”(《孟子·告子章句上》)。什么叫做“外”呢?“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孟子·告子章句上》)。“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故谓之外也”(《孟子·告子章句上》)。显然,“义”是在“我”和“彼”的对象性关系、主客体关系中被讨论的。
在这一关系领域中思考“义”,“义”的内涵和伦理特征如何呢?“彼长”是客体,是对象;“我”是主体,二者的关系是“长之”。那么,分析“长之”的内涵就很关键了。“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说明“长之”中包含逻辑推理过程,在对象之间进行互推;“以长为悦者也”中的“悦”有喜悦的意思,用现代的语言说,大致可以认为就是以认识客体为根据形成的主观道德认识,主观的道德感。“义”是社会关系中高等级的人具有尊重、喜爱、敬畏一类的道德感;其前提是对高等级的人的认识。告子把“长之”等同于“彼白而我白之”,“彼白而我白之”显然只是一种客观的认识。从告子的说明,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告子的“义”的概念是一个描述主义的道德概念。元伦理学对道德概念和道德判断有不同的看法。“自然主义的描述主义者”[2]5认为道德概念描述的是世界之中的自然的或者超自然的东西。思想家使用的那些所谓的道德概念往往具有认识论的功能,是有描述性的。告子的“义”就强调了这种描述的功能。
对于这种把握“义”的方式,孟子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其一,如果把“义”理解为一种对外在事物规定性的描绘或者认识,则要对物进行区分。马的“长”是相对于马而言的,人的“长”相当于人而言的,把两个相对的“长”放在一起,如何客观的描述或者认识哪个是“长”呢?“白马的白”和“白人的白”是客观事物之间的共性关系,如果从这个共性关系求得在主客体关系领域中存在的“义”的客观性、普遍性和必然性,显然在逻辑上存在一定的困难。
其二,“义”被放在“我”和“彼”的对象性关系中,成为相对性的存在,就不能得到整体的揭示。“且谓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孟子·告子章句上》)当作为价值之源的人把人以外的某个对象作为自己的价值之物的时候,人自己同时也就成了一种价值之物。处于关系中的人的价值就是两种价值之物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价值之流,是派生的价值。如果是“长之者”为义的根据,是指以他人或者他物作为价值之源,作为价值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价值,迎合他人以获得外在的赞誉,个体的价值和行为以他人的取向为转移。“为人”状态下的个体价值被称为一种价值之物,自己的价值被对象化为物,降低到物的水平上。如果“长者”为“义”,在告子那里不是理解为“义”,而是理解为“仁”,并且这个内在的选择,也是针对具体对象的,而不具有超越对象规定的任何独立性和自决性,因而也就不具有相对于对象的超越性和普遍性。
“仁,内也,非外也”(《孟子·告子章句上》)。什么叫做“内”呢?“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是以我为悦者也,故谓之内”(《孟子·告子章句上》)。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根据主体的道德情感需要形成的对客体的道德认识。在告子这里,“内”是“爱”,不过这个“爱”是“我”作为“悦”的出发点和主体的,“悦”的对象是“吾弟”和“秦人之弟”,因为“我”是出发点,所以对这些对象的“爱”有选择,有取舍,有重点和分别。
对于告子的“仁”,二三子认为“告子胜为仁”(《墨子·公孟》)。墨子则认为:“未必然也。告子为仁,譬犹跂以为长,隐以为广,不可久也。”(《墨子·公孟》)墨子也认为告子的“仁”不具有普遍性,不可“广”,不可“久”;“跂以为长”,不具有自然性,勉强为之。
如果一定要给告子关于“仁”的思考一个定性的分析的话,可以说告子心目中的“仁”是“非自然主义的描述主义者”[2]5,非自然主义的描述主义者认为描述物是一些种类上完全特殊的东西。“仁”是说明“爱”的,说明“悦”的。“爱”和“悦”在主客体之间发生,因为外在事物有特殊性,从而主体有特殊性的情感反应,就叫做“仁”。“仁”具有描述主体的特殊性的情感反映的功能和作用。在描述主义者那里,道德判断有真实和虚假的区别,并且能构成自然的或者非自然的知识。在墨子心目中,告子也“言仁义”,“今告子言谈甚辩,言仁义而不吾毁”(《墨子·公孟》)。告子的“言仁义”主要不是用“仁义”评价人,而是注重“仁义”的描述功能。
四、不动心:目的善的最高境界
告子用人与物的关系为譬喻来说明人与人之自我的关系,也就是人之“性”,进而又在这一大关系背景下用“决诸”说明人的自“我”对“性”的改造形成善恶;接着又把“仁义”放在“我”和“彼”的关系中来考察,显然整个思维过程虽然涉及了人对自我的认识和改造关系,但总体上是在“我”和“彼”的内外关系中进行的。所以孟子说告子“外之”。“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孟子·公孙丑上》)问题不仅仅是内和外的问题,而是内和外所涉及的思维方式问题。告子是在人和对象之间形成的对象性思维的范围内思考内外问题的。在孟子看来,把“义”看作是我与你之间的对象性关系本身就是“外”了。孟子所理解的“义”是超越“人”“我”之间的对象性关系的。所以孟子说:“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孟子·尽心章句下》)
在告子那里,由内外之间的对象性关系构成的结果善的最高境界是“不动心”。告子也强调“不动心”,这个“不动心”在内外关系领域中,和孟子的“不动心”存在的领域和思维方法有差异。告子的“不动心”是什么呢?“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孟子·公孙丑上》)在告子这里,依然是在“仁内义外”的思维框架下理解“不动心”的。这里的“言”和“气”在逻辑地位上相当于“义外”,“心”在逻辑地位上相当于“仁内”,“不动心”就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说要坚持外在对象对于形成道德认识的决定性,而不能忽略这一点,即告子所说的“不得于言,勿求于心”;另一层含义是强调主观认识的重要性,即“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动心”强调的是在处理“仁内义外”的关系的时候,保持道德认识的客观实在性,一方面是对象的客观实在性;一方面是心灵上主观能动性。而孟子的“不动心”则强调“得于心”、“求于心”。而孟子的“心”的道德内容主要是“四端”之心。孟子的“不动心”不是被放置在他人和自我构成的内外关系中来理解的。“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孟子·公孙丑上》)。“气”不像告子所理解的那样是外在的对象,所以要“袭而取之”,“气”在孟子那里是“集义所生者”。在孟子看来,把“义”看作是我与你之间的对象性关系本身就是“外”了。孟子所理解的“义”是超越“人”“我”之间的对象性关系的。
从现代哲学的观念来分析,告子对人的分析,其实是分成了两个方面,而把人的一个方面叫做性,或者人性;而另一个方面是善恶。并且他强调二者的不同。告子是否也很重视人的道德方面在人的属性中应该占有重要的地位呢?从《墨子·公孟》来看,告子是强调对道德进行理性分析和加强道德实践两个方面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告子并不否认道德是人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甚至是本质的方面,不过不能用“人性”或者“性”的概念来说明。人性概念反映的是人的物种性质,反映的是人的共同性,包括与其他物种的共同性;而只有仁义概念才反映了人的特殊性本质。善恶作为人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如何产生的呢?告子认为是实践改造产生的。道德存在的领域是什么呢?是社会关系领域,仁义道德存在于他人和自我的关系领域,仁义道德离不开外在对象的认识,也离不开主观的能动性,离不开主观的道德选择和道德情感。道德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是在处理主观的道德情感和客观对象的关系的时候,不脱离对方,从而保持道德认识和实践的客观有效性。告子强调道德的实践性、社会性是值得肯定的,但也面临着论证首先的普遍性根据的困难。孟子从人性、人心中寻找道德的普遍性根据,墨子则以“天意”的名义,把“兼爱”作为社会应共同遵循的价值标尺。彼此争鸣展现了三个理论进路的优缺点。应该给予告子的人性论以必要的学术肯定。
[1]江畅.理论伦理学[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2]艾伦·格沃斯,等.伦理学要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B82-0;B22
A
1001-4799(2012)03-0041-05
2011-01-10
周海春(1970-),男,内蒙古扎兰屯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和伦理学史研究。
朱建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