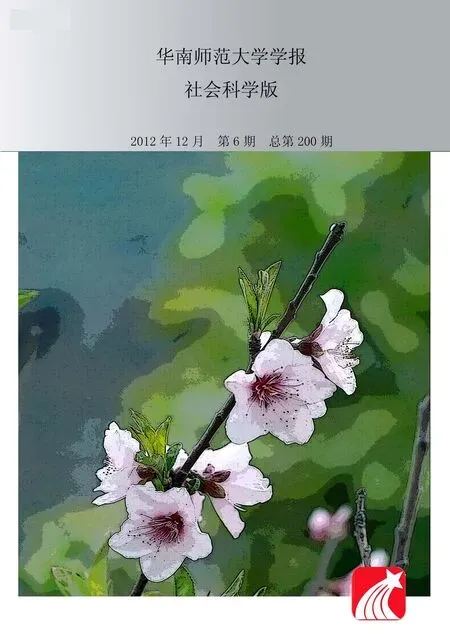清末广东:文化资本的更新与教育场域的回应
2012-04-09王建军崔红丽
王建军, 崔红丽
(1.华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2.华南师范大学 信息光电子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广东的传统教育发展到清朝,认同与顺应国家教育机制的取向几成定局。然而晚清西方文化的渗入,带来了新文化因素的增长,使广东人认同国家教育机制的进程出现了变数。旧有的文化政策,包括人们为提高文化能力而养成的惯习都已不能很好地应对与承载新文化因素的挑战,文化资本更新的问题便浮出水面。所谓文化资本更新,在晚清特定场合,即指文化资本中呈现出中西文化力量对比的冲突。这种力量对比的改变必然会引发教育场域中利益格局的重组,导致场域中的各利益相关者必然要对中西文化的博弈表明态度,并作出选择。那么,广东教育场域中的各利益相关者对此作出了怎样的回应,这些回应具有怎样的特点,本文试对此作一探索。
一、农工商群体的突破
以往我们总是把考察的眼光放在社会上层,观察西学东渐中清朝官员和知识群体的思想动态。虽然在鸦片战争前后,广东官员中有林则徐、邓廷桢,士大夫中有梁廷枏等已经具有了开眼看世界的作为,但真正对文化资本更新具有实际意义的回应动作却是由广东基层社会首先作出的,其突出表现就是农工商群体中有人将自己的子弟送进了教会学校。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容闳的入读西方学校。容闳家乡为香山县南屏镇,距离澳门很近。当时澳门马礼逊学校还在筹备之中,便委托英国传教士古特拉富夫人的私塾先行安置所招收的学生。容闳父亲的一个朋友在这所学校打杂,便常与其父母谈及这所学校,最终促成7岁的容闳被送进这所学校读书。容闳说:“惟是时中国为纯粹之旧世界,仕进显达,赖八股为敲门砖,予兄方在旧塾读书,而父母独命予入西塾,此则百思不得其故。意者通商而后,所谓洋务渐趋重要,吾父母欲先着人鞭,冀儿子能出人头地,得一翻译或洋务委员之优缺乎?”[注]容闳:《西学东渐记》,第67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希望儿子将来能得到一个翻译职位或洋务委员的优缺,这说明在文化资本以八股仕进为主导价值之时,容闳的父母已看到新元素在文化资本中的增长。因而希望在这新旧文化博弈的初始之时“先着人鞭”,以图将来“儿子能出人头地”,这种朴实的期望,最终促使其父母将其兄送进旧塾的同时,在1839年将容闳送进了教会学校。
比容闳父母更彻底的是唐廷枢的父亲,他将两个儿子都送进了教会学校。他的父亲唐宝臣是广东香山县唐家湾人,家境贫寒。虽然他也感觉到西方文化在文化资本中的增值,但家庭没有能力送两个儿子进西方学校。于是,1842年,唐宝臣以给马礼逊学校校长布朗当听差8年为条件,让唐廷枢与其兄唐廷植进入马礼逊学校学习。布朗接受了这个条件,使唐廷枢得以在马礼逊学校学习6年。唐廷枢以后在外国公司或在香港政府当听差,当翻译,当买办,于1873年担任了中国第一个国有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的总办。文化资本的更新导致了新的社会资本的积聚,这在唐廷枢身上也得到了印证。
在清末的广东这样的事例并不仅仅是些个案,而是有着一定的社会基础。1872年至1875年,中国分4批派出的120个赴美留学幼童,其中有84人来自广东,另外还有7名随着第二批自费前往美国留学。第一批学生在上海招考,因报考人数很少,容闳不得不跑回家乡和香港进行动员,曾国藩也特地要广东商人徐润劝说广东人送子应选。所以第一批的30个幼童,有25人来自广东。这多少能说明新的价值观念在广东基层社会有着一定的市场。其他如广东南海人何启1872年的英国自费留学,广东新会人伍廷芳1874年的英国自费留学,广东香山人孙中山1879年的檀香山自费留学,都可以作为佐证。
为什么清末广东的基层社会会有这样的举动?
在传统的教育场域中,处于社会底层的农工商群体是占据文化资本最少的弱势群体。传统的文化资本以科举取士为杠杆,将教育凭证的认定、经典的传承、意识形态的控制、民间教育资源的引导等各种要素统合了起来。民间社会只有获得了科举身份,才有可能帮助个人、家族、社区提升社会地位,才有可能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积聚创造条件。而农工商群体属于与科举基本无缘的群体。虽然科举制度并没有对他们关上大门,但他们本身所依赖的家庭背景,以及所拥有的社会资源,要想使自己的子弟获得科举的文化资本,其希望是十分渺茫的。从詹天佑父亲送其留学与清政府所签订的“甘结”可以看到:“情愿送赴宪局带往花旗国肄业,学习机艺回来之日,听从中国差遣。”[注]徐启恒、李希泌:《詹天佑和中国铁路》,第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其中的条文可能是由清政府所拟定,至少在统治者眼中,他们这个群体只有学习“机艺”的资格。在“道本器末”价值观念盛行的时代,这个群体注定是无缘科举的,是不能进入“士”这个行列的。
但从另一角度来看,这又成了农工商群体的长处。他们要改变在场域中的弱势位置,就必然会在文化变动中寻求突破。在洋货消费文化流行的清朝广东,这个群体一旦感受到西风欧雨的物质价值,他们便能从最直观最朴实的角度规划着本身的文化资本更新,以图在未来的教育场域内先拔头筹。另外一点,长期被边缘化的角色,也使得这一群体对传统文化资本中的科举身份并无更多的依赖性,反而推崇职业出路的多元观念,以学习一门技艺来盘算着未来。同治十年(1871),两广总督瑞麟上折,指出广州同文馆学生中,旗籍子弟学习认真,“惟民籍正学、附学各生,来去无常,难期一律奋勉,其学习西语者民间固有之,而偶有招入官馆肄习者,始愿不过希图月间膏火,迨学习一二年后,稍知语言文字,每有托词告病出馆,自谋生理,而于始终奋勉学成有用者,实难得人。”[注]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第268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这里所说的“民籍”,就是来自广东基层社会的普通“汉民”。他们学习西方语言,只求“自谋生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群体首先对文化资本更新作出回应的缘由。
当然,这个群体并非铁板一块。同样是为了争取更为优势的文化资本,农工商群体中的另一部分人则选择了应试科举。其典型的例子便是广东商人集团。他们通过与官府的互动合作,不仅在清朝获得了援例授官资格,而且在“康熙六十年题准广东盐商子弟照淮浙河东之例,遇岁科二试,取进童生二十名拨入广州府学,分拨南海番禺二学肄业。雍正元年议准广东商籍生员乡试,另编卤字号”[注]阮元修、伍长华纂:道光《两广盐法志》,卷23《职官·署庙》附选举,道光十六年刊本。,让他们的子弟也获得了读书应举的资格。乾隆二十年(1755),由盐运司范时纪及诸商捐建在广州创办了越华书院,专为商籍子弟藏修息游之所。由此看来,清朝的广东商人集团凭借财力在传统的文化资本框架下争取到了较为有利的位置。这个位置使最早接受洋货消费观念的商人集团,特别是活跃在十三行周围的大商人集团,在最初的留学浪潮中并没有更多的动作。可能的解释是,“绅商”身份的获得使他们对文化资本中的新元素采取了漠视的态度。
同样突出的事例是,清中叶以后,在广州城内云集了数百家以姓氏命名的联宗书院。这些来自广东各地的宗族创建联宗书院的一个重要考虑,是为了方便本姓本族子弟的求学应举。例如,尊奉苏洵父子为始祖的苏氏武功书院坐落在广州禺山之麓,苏氏族人看到“广州是岭南一大都会也。若置书院于此,我族子孙岁试、科试、乡试与夫负笈从师,或远或近,必皆由院而进,非徒朝于斯,夕于斯,得以聚首言欢,亲无失其亲也,而且可以藏修,可以游息”[注]《武功书院记》,《苏氏族谱》(广东),德有邻堂刊本,清光绪二十五年。。联宗书院以应试科举为号召,不仅有利于增强同一地区具有共同利益的同姓或异姓宗族联盟的凝聚力和社会地位的提升,而且也与国家文教政策相匹配,体现了宗族社会与国家文教政策同步接轨的教育追求。
由此可见,教育场域是一个充满着旨在维护或改变场域力量格局的斗争场所。作为处于弱势位置的农工商群体,他们的求变心理更为强烈,对传统文化资本的维护或更新会有更为急迫更为敏感的反应。利益的驱使导致了这一群体在新旧文化博弈中产生了分化,这一分化为清末广东新旧教育发展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二、士大夫阶层的质疑与批判
农工商群体虽然对文化资本更新首先作出了回应,但真正能影响文化资本力量对比的是士大夫阶层。士大夫阶层在文化资本占有中属于优势群体。他们依据所拥有的文化资本,以及由此所形成的文化能力,在教育场域中获得了一定的学术权力。这种学术权力使他们在教育场域中占据了有利位置,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影响文化资本取向的话语权,成为影响地方社会与国家教育机制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但他们在场域中所处的位置比较尴尬,他们既掌握了一部分的文化权力,但又必须受制于政治权力。当传统文化资本的实际社会效应与儒家社会理想之间的差距明显拉大,他们的立场便发生了分化。他们有可能因感受到西方文化的启迪,奋然而起质疑和批判传统文化资本的弊端;也有可能听命于朝廷,因循故步;或者取一种稳妥的策略,在传统文化资本的框架内走一条改革之路。围绕着文化资本力量对比的变动,清末广东士大夫阶层依据各自占有的学术资本力量,分别展开了各种策略的斗争。
最早对传统文化资本提出质疑的是广东的朴学群体。清朝中叶,在两广总督阮元的推动下,他们治学坚持“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原则,除传统的经史文辞外,也习天文算学历法、中西交通、航海等知识,打破了士人专作帖括学问的旧习,在广东推行开一股求真求实的学术风气。虽然他们的治学还属于中国传统文化范畴,但在八股取士盛行之时,立志学术坚守,也是一种社会责任感的体现,其终极追求还是指向经世。诚如阮元为学海堂题联所言:“集诸生于山水之间,刚日读经,柔日读史;当秀才以天下自任,处为名士,出为名臣。”他们发扬儒家经世致用传统,坚守为己、用世之学。朱次琦明确反对学生埋头于考据帖括等无用之学,强调说:“读书者何也?读书以明理,明理以处事,先以自治其心,随而应天下国家之用。”[注]简朝亮:《朱九江先生年谱》,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刊本。陈澧也指出:“然则学术日衰,人材日少何也?但为作时文计,而非欲明圣贤之书故也。”[注]陈澧:《东塾集》卷二。他强调说:“所谓经学者,贵乎自始至末,读之,思之,整理之,贯串之,发明之。……惟求有益于身,有用于世,有功于古人,有裨于后人。”
这是一个学术力量雄厚、社会基础广泛的群体,他们以学海堂起家,以菊坡精舍集大成,标榜出不同于一般书院的教学宗旨。这个群体也能紧跟形势,当朝廷显示出“兴学校”的姿态时,他们也适时办起了具有基础教育性质的新式学堂。如广州府绅士、内阁中书邓家让等人于1898年创办的广州时敏学堂,潮州府绅士、工部主事邱逢甲、翰林院检讨温仲和等,在澄海县属之汕头地方,1900年创办的岭东同文学堂,广州府绅士、翰林院侍读丁仁长、编修吴道镕等,1901年在省城倡设的教忠学堂,等。其教育取向以经世致用为原则,既采中学,也采西学:“学子读书,本期致用。今所购者,一以经济之书为主。中学之书,除四书五经人所共有外,若历代地理,历朝掌故,本朝掌故,近代名臣奏议,及时贤新著之书,不嫌博采,其经史子集,但取其有关经济者购之。西学之书,曰天算,曰地舆,曰格致,曰制造,曰政书,曰史志,曰交涉,曰公法,曰农矿工商兵刑诸书,分类广购,以扩见闻,而资讲习。”[注]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第748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比朴学群体激进的是新型知识群体。谓其“新型”,是指这个群体所拥有的学术资本已经具有了西方文化的元素。这个群体成员既有在国外留学有成者,如容闳、何启,胡礼垣、伍廷芳等,也有在国内感知西方文化而立志改革者,如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等。这是一个年纪轻、资历浅的群体,但他们对儒家文化所塑造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格追求却有着一致的认同和坚守。容闳通过中西文化的对比,深切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资本的落后,明确主张:“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注]容闳:《西学东渐记》,第89页。郑观应也是如此,他看到国家因落后而任人宰割,十分痛心,他说:“鄙人所著《盛世危言》一书,大声疾呼,使政界中人猛醒,知爱国保民之道也。”[注]《盛世危言后编》卷四,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第37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康有为一旦受新的知识所震动,便“舍弃考据帖括之学,专意养心,既念民生艰难,天与我聪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注]《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第417页。梁启超则以满腔热情欢迎着新世界的到来,他说:“地球既入文明之运,则蒸蒸相逼,不得不变,不特中国民权之说即当大行,即各地土番野猺亦当丕变,其不变者即澌灭以至于尽。”[注]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见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第47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
正由于他们有着初生牛犊的胆魄,因而对传统文化资本的质疑和批判已经触及到要害问题。在广东新型知识群体看来,传统文化资本所仰仗的知识空疏无用,不仅无益于人才培养,而且误国误种。何启、胡礼垣认为中国教育所施教的知识无非是些“浅陋之讲章,腐败之时文,禅寂之性理,杂博之考据,浮诞之词章”,这些知识“强国学之必致于衰,弱国学之必致于灭,非惟不可以救当时,而且足以累后世”。[注]《新政真诠》,《前总序》。郑观应指出:“中国之士专尚制艺,举凡人情、风俗及兵、刑、钱、谷等事,皆非素习,一旦临民,安能称职?”[注]郑观应:《易言.考试》,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20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他指出,八股取士制度导致学子“不得不以有用之心力,消磨于无用之时文”。面对社会转型,“中国文试而不废时文,武试而不废弓矢,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平日所用已与当日之所学迥殊矣。”[注]郑观应:《盛世危言.考试》,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291、301页。康有为指出,在八股取士制度下,“诸生荒弃群经,惟读《四书》;谢绝学问,惟事八股”,这样选拔出来的人才“竟有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若问以亚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瞪目,不知何语矣”。[注]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第102,104,154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那么,文化资本的更新,在知识价值取向方面应作何种的选择?郑观应认为应学习西方教育,提倡各种专门知识,才可能使国家真正富强:“西人壹志通商,欲利己以损人,兴商立法,则心精而利果,于是士有格致之学,工有制造之学,农有种植之学,商有商务之学。无事不学,无人不学,我国欲安内攘外,亟宜练兵将,制船炮,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讲求泰西士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如广设学堂,各专一艺,精益求精,仿宋之司马光求设十科考试之法,以示鼓励,自能人才辈出,日臻富强矣。”[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商战下》,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595-596页。何启、胡礼垣认为,真正有用的知识,应该在学习中国语言文字的基础上,采取分科学习,专攻一门。他们共列举了19种学科,即外国文字、万国公法、中外律例、中外医道、地图数学、步天测海、格物化学、机器工务、建造工务、轮船建法、轮船驾驶、铁路建法、铁路办理、电线传法、电气制用、开矿理法、农务树畜、陆军练法、水师练法等。[注]《新政真诠》二编,《新政论议》。康有为认为,要彻底改变知识空疏无用的状况,“从此内讲中国文学,以研经义、国闻、掌故、名物,则为有用之才;外求各国科学,以研工艺、物理、政教、法律,则为通方之学”。梁启超则更明确指出:“学非一业,期于致用;言非一端,贵于可行。启超以为所设经学、史学、地学、算学者,皆将学焉以为时用也。”
为了改变文化资本的力量对比,他们还运用自己所拥有的文化能力,借助他们所积聚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身体力行,从实践层面推动新文化因素的增长。
比如一口通商以来,广东商人在与外国商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先是创造了一种中葡混杂的“广东葡语”,后又创造了一种中英混杂的“广东英语”。这种英语在买办、通事、商人中十分流行,而且也能与外国人交流沟通。但这只是民间流传的语言,农工商群体没能力使它知识化,其传播也就十分有限了。1862年,广州经纬堂出版了唐廷枢的《英译集全》,这是中国人自己编著的第一部英汉字典,而且是用广东方言写成。唐廷枢在卷首说明:“这本书是一个隶籍广东的作者用广东方言书写的。它主要适应广东人和外国人来往、打交道的需要。”[注]唐廷枢:《英译集全》卷首语,现藏珠海博物馆。《英译集全》共收集了300多单词,分6卷,内容包括天文、地理、日常生活、工商业、官制、国防等,第6卷有“买办问答”。唐廷枢的文化优势在这里便显现出来。
容闳的作为就更有力量,他借助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官僚的推力,成功地促成了120名幼童的赴美留学。虽然这次留学最终在保守派的破坏下半途而废了,但其对留学儿童的启蒙意义却非同小可,“以故人人心中咸谓东西文化,判若天渊;而于中国根本上之改革,认为不容稍缓之事。”[注]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69页。
再就是办报。1874年,容闳在上海创办《汇报》,“《汇报》于同治十三年五月初创刊于上海,中国第一留学生容闳(纯甫)所发起,集股万两,投资者多粤人,招商局总办唐景星实助成之。”[注]戈振公:《中国报学史》,第122页,三联书店1955年版。唐景星就是唐廷枢,当时广东商人多齐集上海,仅来自广东香山一地的商人就有唐廷枢、徐荣村、徐钰亭、郑观应、吴健彰、容闳等。
民间创办的新型书院,当首推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其讲学“每论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欧美比较证明之。又出其理想之所穷及,悬一至善之格,以进退古今中外,盖使学者理想之自由,日以发达”[注]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第237,249,753页。,对学生思想的触动特别大。“万木草堂学徒,每轻视八股,于考据训诂,亦不甚措意,惟喜谈时务,多留意政治,盖有志于用世者。”
但是,广东新型知识群体和朴学群体对传统文化资本弊端的批判,从总体讲还属于各自为阵的个体行为,他们的批判比较多地还是停留在考试内容、考试方法的改良上,并没有真正动摇八股取士的根基。相反,对科举考试,他们一般是持认可和宽容态度。例如,主张实学的陈澧就认为讲学与讲时文二者可以并存:“即使弟子只为时文而来,然而百十人中,必有数人气质稍清,见识稍高,可以引而进之者。况讲书时自讲书,讲时文时仍讲时文,亦何害于其作时文也哉?”[注]陈澧:《东塾集》卷二。康有为也是如此。当时入读万木草堂的学生,大多对参加科举考试不感兴趣,“于是有父兄的家庭,大不以为然。谓不过考还读什么书,如果要入万木草堂,则学费就不给了。康先生乃力劝同学们,不要如此以妨碍前途。谓:‘我且过考,诸君何妨强力为之,以慰父兄之心呢。’”[注]夏晓虹编:《追忆康有为》,第244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
新型知识群体的这种宽容态度,又反映了当时广东士大夫阶层的主体还是追逐着八股时文而去。教育场域内的斗争空间是由拥有各种学术资本力量的利益者所构成的。在朝廷文化政策未作根本调整,社会传统心理根深蒂固的情势下,广东士大夫阶层的主体对新文化因素的增长还是取观望甚至抵触的态度。他们抵制文化资本的更新,根本的是要维护他们在教育场域中的优势地位,巩固他们所据有的社会资本。最早创办的时敏学堂就遭到传统社会的歧视。当年的学生邬伯健后来在回忆中说道:“犹忆未有学务大臣之前,粤中人士,对于余等,不指为康党,即指为耶教徒,偶一过市,辄闻鄙夷唾骂之声,起于背后,戚友相遇,亦往往以退学为劝。”1903年开办的广州群益学堂附近有某塾师的“子曰馆”,这位塾师十分不满学堂的开办,又看到群益学堂的学生穿着白色操衣,便在他的“子曰馆”门前贴一对联:“堪笑一群,羊毛仅有;何来三益,体用皆非。”[注]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第520-52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广东文化资本更新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样在士大夫阶层的新旧力量的抗衡与妥协中前行的。
三、督抚官员的推力
较之农工商群体、士大夫阶层,对文化资本更新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作为朝廷代表的督抚官员。他们在文化资本占有中属于强势群体。在教育场域中,他们以政治权力统摄着文化权力,控制着文化资本的分配与走向,对各利益相关者行使着仲裁和支配的权力,对维护传统文化资本有着本能的倾向。当然,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他们在朝廷许可的政策框架下,也尝试着文化政策的微调,并通过开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翻译西方科学之书这些微弱的改革试探着文化资本的更新之路。但他们绝不允许根本改变文化资本的力量对比。他们所努力的,就是在“中体西用”的框架下,用各种治理策略来维持着广东教育场域内新旧力量的均衡。
在治理过程中,督抚官员总是本能地采用维护传统文化资本再生产的正统性策略,即推行科举。从鸦片战争前后至辛亥革命前夕,在广东任督抚的官员多达33人,无论是主张洋务者,还是反对洋务者,对坚持科举的态度却相当一致。为了稳固清朝的统治秩序,借助科举之力来凝聚人心,广东督抚有意强化了学子博取科举功名的意向。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发生了土客大械斗。同治六年(1867)二月,广东巡抚蒋益澧基本解决了长达13年的土客械斗。在着手安置客民生活的同时,蒋益澧很注意加强兴办文教的措施。他奏请设立遵义书院,并偕同两广总督瑞麟奏请将客民读书子弟另编客籍,参加乡试,每20人取进一名[注]刘平:《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第316-330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这个做法得到朝廷的表彰。同年,总督瑞麟、巡抚蒋益澧又看到广东“学额日益广,试士日益众”,而广东贡院号舍严重短缺,于是积极向民间筹措资金,蒋益澧自己也慷然捐银200两,用以扩建广东贡院[注]史澄:《新西考棚记》,见(光绪)《广州府志》卷六十五·建置略二。。这样,广东贡院又增号舍三千间,共为一万一千七百八间。“是岁乡试之得与试者,万余人,取中一百九人,自开科以来所未有也。”[注]蒋益澧:《广东贡院碑记》,见(光绪)《广州府志》卷六十五·建置略二。
同样的,王凯泰于同治七年(1868)任广东布政使,他在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的支持和批准下,于同治八年(1869)创建了应元书院。应元书院之名,一是书院之地选在应元宫旁,二是会试第一名称为“会元”,三是殿试第一名称为“状元”。很显然,这是一所专门冲着科举考试而兴办的品牌书院。它的创办,为调动广东学子应试科举的积极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王凯泰认为:“近代以来,士以科举为荣,为之官长者亦借科举以为教,而其意则不止于是也。今以后书院之士学则有本有文,仕则有为有守,是余所厚望也。”[注]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中册,第1166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这一观点正是清末广东督抚的由衷之念。书院设立后的第一个会试年,1871年,应元书院的参试者就有9人中了进士,其中5人入翰林,还出了一个状元。第二个会试年,即1874年,应元书院又中进士12人,其中一人名列榜眼。光绪丙子(1876年)恩科会试,应元书院又出了进士9人。
广州不仅有一个应元书院,而且还有不同级别官员创办的省级、府级、县级的书院,加上众多的民间书院,实际上在广州已经形成了具有层级结构的书院网络。通过这个书院层级网络的互动和辐射,广东督抚官员已经建构了一个能够带动和影响所辖区域的文化教育力量和社会机制。[注]王建军、慕容勋:《论清代广州书院城市化》,载《华东师大学报(教科版)》2005年第1期。这个社会机制便是科举。正由于此,在清末教育改革愈益高涨的情势下,广东社会应试科举的热度并未减弱,且成绩不菲。据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讲,清代光绪甲辰科(1904)殿试是最后一次科考,其时参加殿试者共273名,其中直隶、江苏各22名,浙江、江西各20名,山东19名,广东18名,在18个省中广东排名第六。广东18人中,取中榜眼1人,二甲10人,三甲7人。探花商衍鎏以八旗汉军身份参加,实则也是出自广东。[注]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第114-115页中插图,三联书店1958年版。这种现象说明,清末广东督抚官员在运用科举之力来整合广东教育场域内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是相当成功的。
除此之外,广东督抚对朴学学风的推动也下了一番功夫。这种于旧学中多少能显现出一点新意的学风,是广东督抚认定“端正士风”的良药。诚如张之洞所言,广东商贾齐集,华洋错居,在这种“见闻事变,日新月异”的情势下,“欲端民俗,盖必自厚士风始;士风既美,人才因之。”[注]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下册,第2225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这种考虑既有利于清朝统治的稳固,又于文化资本的更新有所裨益。所以,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二十七日,英、法联军撤出广州。广东地方官府立即对遭受严重破坏的学海堂进行整治,如迅速修补完善了《皇清经解》及《广东通志》等大型文献,恢复了学海堂考试,修葺了学海堂的校舍。广东巡抚郭嵩焘于同治五年(1866)重新恢复了学海堂的专课肄业生制度。1868年,两广总督瑞麟扩大专课肄业生的规模,由10名增设为20名,并招收附课生20人。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广东巡抚吴大瀓又再增加专课童生10人。另外,同治五年(1866),广东巡抚蒋益澧与广东盐运使方浚颐在粤秀山应元宫旧址创建菊坡精舍,聘学海堂学长陈澧为山长,将朴学学风推向高潮。1871年,陈澧去世,广东朴学群体失去了领军人物,朴学学风也日渐衰微。1888年,张之洞创办广雅书院,以图再领风骚。“广雅”一名,取自“广者大也,雅者正也”的意思。广雅书院的课程分为经学、史学、理学与经济四门,体现了张之洞注重经史实学、实事求是、学以致用的教育主张,也反映了广雅书院在学风上与学海堂、菊坡精舍的承传关系。张之洞调任两湖总督,还在继续关心着广雅书院的发展。
当然,面对社会的转型,特别是身处广东这样的沿海地区,有部分的督抚官员,对传统文化资本的弊端有所认识,对新文化因素的增长也有所认同。他们站在国家求强求富的立场,认识到如果不对传统文化资本进行适度的更新,至少在人才储备这一点上,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广东场域内社会资本的更新,乃至影响到经济资本的积聚。他们针对旧文化政策无法应对和承载新文化因素增长的状况,会在体制许可的范围内采取适当的更新措施,以图在教育场域的博弈中争取主动。
比如广东地处海防前线,了解敌情,进而更深入了解西方国家情况,当是海防的首要功夫。林则徐在这方面称得上是开风气的功臣。他曾在广州设立译馆,翻译外国书籍和报纸。正如魏源所说的:“林则徐自去岁至粤,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注]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上》,见《魏源集》,第174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林则徐自己也说:“沿海文武员弁,不谙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因此“必须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定控制之方”[注]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21页。。林则徐还主持把翻译过来的外国人论述中国的言论,辑成《华事夷言》,并将日常积累和翻译的材料,编成《四洲志》草稿,叙述各国的历史、疆域和政治情况。林则徐的成果为近代中国“师夷长技”观念的形成打开了通道。
广东又是重要的通商口岸,培养洋务人才,特别是军事人才当是广东治理中不可推卸的责任。全国三所同文馆,广州居其一。1877年,广东督臣刘坤一捐银十五万两,奏明以之生息,为储养洋务人才之用。1880年,广东督臣张树声、抚臣裕宽于广州城东南十里长洲地方,就前款内拨银建造广东实学馆,内分制造和驾驶两科。张之洞到任后改名为博学馆,1887年,又将博学馆改为广东水师陆师学堂。张之洞认为:“近年天津、福州皆设水师学堂,而天津兼设武备学堂,以练陆师,诚以两者不可偏废也。广东南洋首冲,边海兼筹,应储水陆师器使之材,较他省为尤急。”[注]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第89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因此他在学堂内分设水师和陆师两科。1889年,张之洞提议在学堂内增设矿学、化学、电学、植物学、公法学五科。此外,晚清广东的洋务学堂还有,1884年在水鱼雷局内附设广东黄埔鱼雷学堂,1887年的广东电报学堂,1891年创办的广州商务学堂,1895年创办的广州铁路学堂,1896年创办的广州蚕桑学堂等。这些新式学堂的创办,冲破了传统教育的格局,从官方层面为文化资本的更新打开了缺口。
为推动广东经济的发展,也是广东督抚进行文化资本更新的一个考虑。两广总督岑春煊看到广东蚕业发达,以顺德最盛,南海次之。顺德一县,每年输入丝价不下千百万。但蚕农因循守旧,不思改进,导致在与外商竞争中,丝茧售价日低,出口日减。岑春煊指出:“推原其故,皆由于各国考求蚕业,不遗余力。举凡种桑之法,验种之法,饲养之法,缫丝之法,其所以为研究者,学校以专其事,社会以厚其力,学理之密,器具之精,悉纵前所未有。”他强调,“夫天演之理,不日进则日退,彼之所以日进,即我之所以日退。”所以,“粤省今日蚕业改良进步之道,殆不可不亟讲也。”于是,他于1904年奏请开办两广蚕业学堂。他认为如果能在广东培养一批专门人才,有效地指导广东各地的养蚕行业,广东的蚕业才可能增强竞争力。[注]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册,第209-211页。
以上种种,广东督抚官员在回应晚清文化资本更新上的三种选择都有所作为,虽然轻重程度不同。这只能说明,他们并不清楚未来的文化资本将趋向何方。但他们又不得不行使权力,不得不运作权力,以显示出他们在教育场域中的重要位置,特别是更不愿意因此失去在未来教育场域竞争中的强势地位。这是一种末世王朝的权力心态,表现出社会转型时期濒临没落权力的无奈之举。
据此似乎可以明白,处于开放前沿的广东近代教育为什么没有走得太远。在大一统的政治体制下,文化资本更新给广东教育场域带来的影响,最明显的就是导致了每个阶层的自我分化。这种自我分化是在一种平和的状态下进行的,并没有引发新旧对立和强弱相逼势态的出现,社会转型并未导致社会分裂。多元并存的文化资本在广东这个场域内的博弈和妥协,促成了清末广东教育发展的新旧并存格局,成就了广东教育多元、开放、包容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