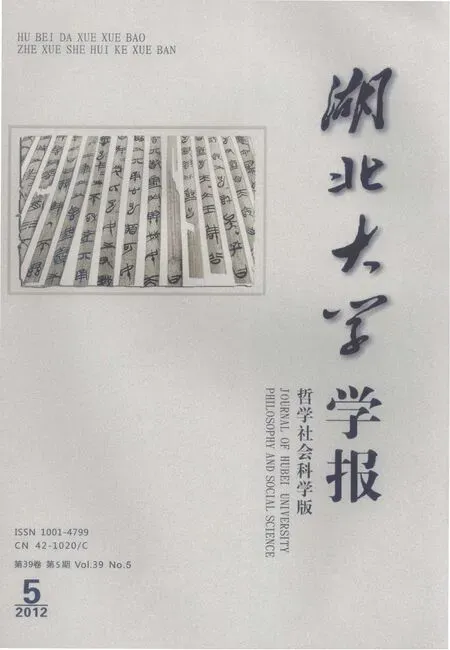荀子政治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转换
2012-04-09冯兵
冯 兵
(华侨大学哲学系,福建 厦门 361021)
蒋庆先生指出:“儒家的传统政治思想与儒家在历史上曾建立过的政治制度是建立中国式政治制度的最基本的思想资源与制度资源,若离开儒家的思想资源与制度资源,就不可能在中国建立起中国式的政治制度。”[1]126而荀子由于对人性之“恶”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与孔、孟比较起来,其“隆礼重法”的政治思想体系也就具备了更为充分的现实有效性。因此,要研究儒家的传统政治思想,荀子是必须得到高度关注的。虽然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荀子政治思想的研究掀起了一股热潮,但从其政治伦理,特别是制度伦理角度入手的专门研究却不多见。本文试图通过关于荀子朴素的制度正义观念,及其关注民生、“平政爱民”的民本意识等传统政治伦理思想的探讨,对其中的人治制度设计与人治精神进行现代反思,从而实现荀子政治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的部分转换。
一
荀子在他“隆礼重法”的制度建构之中,蕴含着朴素而又丰富的制度正义观念,对于当前执政制度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罗尔斯指出:“作为公平的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2]1但在荀子看来,由于“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因此,他指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又说“人情甚不美”(《荀子·性恶》)(下引《荀子》只注篇名)。强调人的本性是恶的。也就是说,人性之中生来就有破坏“作为公平的正义”的天然因素。于是,制度正义在荀子那里首先就表现为制度对人性的矫正与教化作用,他说:“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使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性恶》)然后指出:“故人无动而可以不与权俱。衡不正,则重县于仰,而人以为轻;轻县于俛,而人以为重,此人所以惑于轻重也。权不正,则祸托于欲,而人以为福;福托于恶,而人以为祸,此亦人所以惑于祸福也。”(《正名》)在这里,所谓的“权”、“衡”,是指衡量人们日常行为的具体道德与法律准绳,也就是礼法制度,而对于“正”的要求,就充分说明了荀子对于制度设计和运行的公正合理十分看重。细言之,又具体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尚贤使能。荀子强调“取人之道,参之以礼”(《君道》)、“凝士以礼”(《议兵》),将人事活动纳入礼制之下,以礼制规范为准绳,“外不避仇,内不阿亲”(《成相》),“不恤亲疏,不恤贵贱,唯诚能之求”(《王霸》),从而顺利实施“谲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儒效》)、惟贤能为用的人事制度,以充分保障国家政治的清明与有序,达到“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的理想效果(《富国》)。荀子通过对于德、能(包括才能与智能)与禄位官秩成正比的反复强调,已不仅限定于是一个施政的伦理原则,更将此上升到制度的理性要求;第二,公正严明。在荀子的礼法制度实施刑赏功能的过程中,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制度设计与运行原则:“庆赏刑罚欲必以信。”(《王制》)“信”,《说文解字》注:“信,诚也”,而用现代话语来解读,在这里则应当有着起点公平与过程公正的意思。因此,荀子一方面要求“君法明,论有常”(《成相》),礼法制度的设计必须准确明了,同时又要求在刑赏制度中“法胜私”、“刑称罪”,“刑罚不怒罪,爵赏不逾德”(《君子》),强调执法的客观公正,不徇私情。
前些年学术界关于孔、孟在“父子互隐”、“窃负而逃”、“封之有庳”的相关论述中所内蕴的伦理精神及价值判断产生过一场影响甚广的大讨论,刘清平先生等认为孟子对舜“窃负而逃”、“封之有庳”的行为的赞美表明了儒家思想具有滋生腐败的“温床效应”,反对者如郭齐勇先生等则着重强调了孔、孟原始儒家对亲缘伦理的强力维护在保障人类最基本的道德情感以及对人性的终极关怀等方面所具有的关键性作用[3]。但无论如何,我们在对孔、孟之儒学致以足够的“温情与敬意”和“同情”地“了解”之余,必须对其血亲伦理观念有一个科学、谨慎的认识和态度。而被认为是儒家“别宗”的另一个代表人物——荀子,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范本。荀子一方面承续了孔孟儒学的血亲伦理观念,并深刻体察到其在政治生活中根深蒂固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他又努力坚守着制度公正的基本原则,通过制度的自我规定性,对血亲伦理原则于制度公正所产生的破坏力,作了在他那个时代所能做出的最大程度的消解。他说:“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君道》)荀子以制度正义为根本的出发点,将孔孟儒学的血亲伦理原则和上述“塞私门”、“息私事”的制度公正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强调“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无私人以官职事业”(《君道》),又肯定了血亲观念在政治生活中的部分合理性,从而将两者作了一个调和:“贤齐则其亲者先贵,能齐则其故者先官”(《富国》)。在制度设计及制度运作的方面,荀子都充分注意到了制度的伦理价值导向中情与理的和谐统一。他说:“凡礼,始乎棁,成乎文,终乎悦校。故至备,情文俱尽;其次,情文代胜;其下,复情以归大一也”(《礼论》),认为礼制设计与运行的最佳状态就是将制度规范与人们的情感表达非常完美地结合。
而近几年来,我国政府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逐渐加大,并专门设置了国家预防腐败局,党的十七大也把反腐败工作列为重中之重。笔者以为,要真正抓好反腐败工作,就应当将制度反腐与道德反腐紧密结合起来①简而言之,制度反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将反腐败机构独立化,如设立国家预防腐败局等措施;二是建立和完善各项具体制度,缩小不法分子的腐败空间,从而增加腐败行为的成本。道德反腐则主要是从行政伦理和社会伦理等方面加强宣传教育,形成从上到下全民抵制腐败的社会道德风尚。,且把制度反腐置于首位。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制度文明建设的发展与完善。但中国是礼仪之邦,是一个十分看重世故人情的国度,传统儒家注重血亲故旧的亲缘伦理意识早已深深地铭刻在了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之中,它的影响几乎遍及我们生活中的每一部分。在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的亲缘伦理文化的国家里,要彻底根除当前社会中所出现的徇情枉法、任人唯亲等腐败行为和现象,在执政制度及制度伦理的建设与完善过程中,我们就不仅仅是要考虑到制度结构本身的合理与公正,还必须充分顾及这一重要的传统社会伦理因素。然而,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社会大众当中,当前都出现了这样两种极端的态度:有人坚持将其一棍子打死,全盘否定,认为传统文化已完全不合适宜,持一种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还有人受文化复古主义思潮的影响,对“国学”(国学的主体在很大的程度上说就是以孔孟为宗主的儒学)“信而好古”,顶礼膜拜,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但事实上我们既不可能也不应当试图去摆脱积淀了数千年的传统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当然,要不论精粗全盘接受也是不可理喻的。所以,对传统伦理文化中的消极因素我们只能通过充分发掘其内部的积极因子来予以消解,任何外来的力量都只能是治标不治本的。
对于当前我国以反腐倡廉等为重要目标的制度文明建设来说,荀子上述情理和谐的制度公正理念,就为我们提供了既符合传统道德文化心理,又不违背制度正义,且有一定可操作性的传统制度伦理思想资源。故而对于传统亲缘伦理文化在当前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客观存在和影响,在制度的设计与运行中,我们都应该在适当的程度与范畴给予尊重和理解。最关键的应当是对有违传统的社会道德心理和情感予以合理的疏导,而不是一味的压制,过度压制,不仅难见效果,反而有可能适得其反。惟有如此,我们的制度建设与运行才有可能达到一个低成本、高效率的理想状态。
二
荀子制度正义观念的伦理内核在于其“富民”、“养民”、“平政爱民”,以民生为中心的民本思想。不过,历史上曾有许多人质疑过荀子政治思想中的民本倾向,认为荀子“尊君统”、“尊君权”,是一个典型的君本论者,但荀子说“王者富民”、“裕民以政”,其“王者之政”、“王者之制”、“王者之法”等等,都是以民生民心为国泰民安的前提,从而或直接或间接地将其作为立制施政的目的和依据,却是事实。他曾明确地指出圣人制礼、隆礼的目的就在于人民的利益:“故礼之生,为贤人以下至庶民也,非为成圣也。”要求“礼以顺人心为本”(《大略》)。同样,尊君的制度要求也是为了民众利益:“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国,非以贵诸侯而已;列官职,差爵禄,非以尊大夫而已。”(《大略》)所以,荀子的政治伦理观念中是有着较为充分的朴素民本观念存在的,这不容否认。
荀子的民本观念的核心价值导向,就是统治者常怀“富民”之心,以民生为念。荀子指出:“故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民者安,聚敛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王制》)“富民”亦即“养民”,荀子说:“王者之法,等赋,政事,财万物,所以养万民也。”(《王制》)但人性本恶,统治者又当如何来顺应人心、长养万民呢?荀子指出,“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富国》),认为国家的安定与富足,最为关键的就是明确各种等差分别,以使社会秩序井然有条理。而“分莫大于礼”(《非相》),“礼”是统治者明分以使群的根本依据。其“明分使群”的政治理念不仅是从礼、法制度上对社会等级与社会分工的颇具强制性意义的判定,同时也是对民众权利与义务的明确规定。虽然荀子这种对权利的规定与现代意义上的“权利”界定相去甚远,而且事实上它对民众义务的规定要远甚于权利,但其中也确实体现出了荀子朴素原始的民本思想。因此,出于对民众正常物欲、情感表达的认可与肯定,荀子提出了“平政爱民”的执政理念,要求执政者顺应民心民情,从而特别强调了礼法制度“养民之欲,给人之求”的功能,“故礼者,养也”(《礼论》),“故人莫贵乎生,莫乐乎安;所以养生安乐者,莫大乎礼义”(《强国》),等等。
尽管荀子将社会公利与君主利益有意无意地混为一谈,其民生思想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富国》),担心“政险失民”而“君子不安位”的君权意识,有着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但在当前的政治文明建设中,荀子朴素的民本思想对于一个真正关注民生,“以人为本”的社会民主政治模式的形成,仍然于一定程度有着较为积极的传统伦理文化资源上的指导价值。具体表现在:
首先,我们的政府要切切实实地树立起人民利益至上的执政伦理观念。社会主义政治的根本性质就是实现和保障人民的利益。新中国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宗旨是人民当家作主,以人民的利益为中心,而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原则也正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的历届领导人所提倡的政治伦理观念,如毛泽东同志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胡锦涛主席提出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其核心内容都是人民利益至上的“爱民”精神。而关注民生是荀子“平政爱民”,以民为本思想的根本内涵和外在体现,在当前的执政伦理建设中,爱民、利民,“以人为本”,也同样体现为这一形式原则。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会议报告当中,“民生”是出现最多的关键词之一,关注和改善民生显然是当前一个主要的政治议题。而会议中所提出的让老百姓拥有“财产性收入”,缩小贫富差距的概念,各地方政府相继推出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利民措施,等等,其中也就充分体现出了党和政府将“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的现代政治伦理观念落到实处,讲求实效的务实作风。
其次,在深入贯彻上述政治伦理思想的具体政治实践中,我们的政府既要努力抓好经济建设,提升国民物质生活质量,切实解决并充分保障与改善民生问题,同时也要健全与完善我们的民主与法制,进一步完善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传统的民本思想强调的只是统治者对平民百姓的仁厚宽怀之德,荀子所提出的统治者“爱民”、“富民”的要求其本质乃是一种稳固君权、保障统治阶层利益的治道,而现代“以人为本”的政治伦理观念强调的则是主权在民,执政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行政机构和组织。但是,荀子“富民”、“养民”、“平政爱民”的朴素民本思想仍然具有平实而有效的借鉴价值。党和政府多次强调政府改革的目标是“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贯彻的也就是荀子的这一理念。所谓“服务型政府”,是指“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4]。而政府为人民所服务的最重要的项目就是充分保障各类规则和制度的公平与公正。由此可见,一个真正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制度健全而又运行良好的服务型政府机制和社会政治模式正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所在。
三
荀子的以民为本观念是在儒家传统的人治思想和宗法制度这一历史的理论背景之下提出的。现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通过民主制度本身的力量,充分保障了主权在民,可以对传统人治思想做出有效的控制。但如前所述,中国是一个宗法伦理文化底蕴相当深厚的国家,彻底根除人治精神的流弊远非一日之功,况且我国目前也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型时期,因此,加强对传统人治思想的现代反思仍然是很有必要的。以现代民主政治理论,结合我国的历史和具体国情,对荀子人治思想的现代反思不仅有利于深化社会主义民主改革,也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我们政府的形象。
荀子强调说:“人服而势从之,人不服而势去之,故王者已于服人矣。”又说,“天下归之之谓王”(《王霸》),认为王道政治最为关键之处就是“服人”,“服人”靠什么呢?他较少提及制度的规约力量,而是延续了孔孟德治思想的基本精神,指出“义立而王”(《王霸》),倚仗“道德之威”,追求的是贤人政治。这其中又有两个层次:其一,对于老百姓来讲,“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王制》),统治者公正严明,勤理政事,爱恤子民,做仁德之君方可有效;其二,对于臣属来说,“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王霸》),要获得臣属的忠诚驯服,君主的公正之德比制度的制约作用也更要显著。所以,“故王者先仁而后礼”(《大略》),“有治人,无治法”(《君道》)。荀子对君王仁义德性的重视高于礼法制度的建设,其“隆礼重法”的制度思想最终还是裹上了厚重的人治精神的铁甲。而其政治伦理思想中人治特征的最典型表现就是君权至上观念。《诗经》里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小雅·谷风之什·北山》)在荀子那里,这种君权至上的观念同样也是不容动摇的。荀子一方面指出,“礼义者,治之始也”,同时又强调道,“君子者,礼义之始也”(《王制》),礼义是最根本的治道,而“君子”(即君主,作者注)则是礼义的始创者和掌控者,于是,君主在逻辑上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国家的主宰了。另一方面,从现实生活来看,君主的作用似乎也是无可替代的,他说:“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能群也者,何也?曰:善生养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显设人者也,善藩饰人者也。”(《君道》)人类之所以能够形成有序的社会组织,就是由于君主“能群”,而且也只有君主才能担此重任。所以,荀子宣称道:“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正论》)在《仲尼》中又指出:“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也。”老百姓对统治者的至上地位是决不能有所亵渎和觊觎的,只能俯首帖耳地顺从,这就是其制度之“义”。
从积极的一面来看,传统儒家政治伦理思想推崇人治,极度重视为政者的道德品质,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为培养、塑造为政者清正廉洁、仁民惠民,“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政治品格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是当代如“廉政公署”等各种形式的行政纪律监察机构无法取代的。然而,其消极因素也显而易见:其一,人治思想将国家兴盛、政治清明的希望主要寄托在执政者个人的道德修养和道德表率之上,这种将治乱安危全系于一人的行政模式无疑具有极大的政治风险。荀子虽对此亦有所认识:“能当一人天下取,失当一人而社稷危。”(《王霸》)但他并没有提出也不可能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其二,明显的阶级立场使得它的高度集权化、专制化在一旦伤及统治者自身利益时,自然就会导致对现行制度的轻忽和藐视,从而大大加剧了政治腐败的普遍性和严重性。事实上,这种独断专行的人治思想残余在我国当前的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仍然有所表现,它无疑是要求去除人治、追求法治的现代民主政治进程中的一大障碍。
在几千年的封建君主制度下,统治者通过“三纲五常”等思想钳制和奴化教育,君权至上的人治制度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庶民百姓作为“子民”,其驯顺的奴性品格以及统治者“民之父母”的居高临下姿态在中国政治及社会伦理文化里有了悠久的历史积淀。针对这一延续了数千年的封建宗法伦理思想,在中国解放之后,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响亮鲜明地提出了“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的政治口号,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制度伦理的核心内容和指导精神。但是,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少数“公仆”和普通百姓的“父母官”心态仍然存在,甚至在今天,也还能够在一些宣传媒体中偶尔发现“父母官”一词的踪影。尽管“父母官”心态在较大程度上提升了许多行政官员的责任意识,为他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提供了传统道德心理上的支持,但在现代政治生活里,其副作用更为显著。主要表现为:
首先,行政官员容易因此滋生超拔于制度之上的特权意识。解放初期的中国“腐败第一案”中,刘青山、张子善就是因“父母官”的特权心态导致的心理失衡而酿成腐败大案,而更近者如陈希同、陈良宇,亦莫不如此。在当前市场经济大潮里,随着市场经济更为深入全面地发展,越来越多的普通群众“先富起来”,具“父母官”心态的行政官员将会面临更多的诱惑,也就更加容易心理失衡,这就愈发增大了腐败产生的可能性。
其次,由于少数行政官员的“父母官”意识也会使他们产生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在具体的行政行为中,就可能产生态度生硬、主观独断等低效率、高成本的行政方式。而相对应的是,随着社会改革与民主进程的加快,以及世界全球化意识的普及等等,人民在原有的社会主人翁意识的基础上,社会主体意识得到了更大的提高。我们的部分行政官员如果仍没有从“民之父母”的心态中解放出来,就比较容易造成干群关系的紧张,对当前的政治文明建设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都是极为不利的。这是以荀子等人为代表的传统儒家政治制度伦理思想中的君主专制及人治因素所残留的消极影响。
因此,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吸收和借鉴传统人治思想在“官德”建设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另一方面,深化对上述人治思想在现代政治文明建设中的负面效应的客观认识也是十分重要的。它可以推动我们的政府及政府官员转变自身“民之父母”的角色认识,促进执政制度的健全和完善,从而有效地消除腐败得以产生的传统伦理文化根源上的消极因素,为建成一个民主、理性、高效和富于公信力的现代服务型政府而奋斗,最终为共同建设和共同享有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政治制度保障。
[1] 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2]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3] 胡治洪.近年来儒家伦理论战述评——腐败之源还是德性之端[J].文史哲,2005,(6).
[4] 刘熙瑞.服务型政府——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行政改革的目标选择[J].中国行政管理,20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