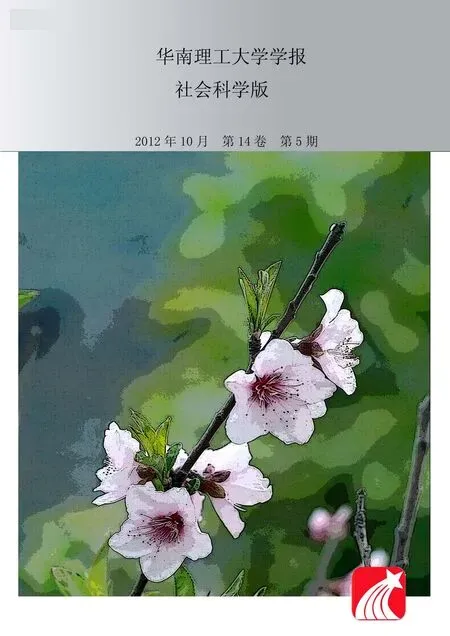乾嘉注释学视野中的《苏文忠公诗合注》*
2012-04-08何泽棠
何泽棠
(华南农业大学 人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2)
冯应榴(1740一1800),字诒曾,号星实,晚号踵息居士,浙江桐乡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进士。历官至鸿胪寺卿。著有《苏文忠公诗合注》(以下简称“《合注》”)、《学语稿》等。《合注》成书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最早刻本为乾隆六十年(1795)的踵息斋刻本,后有冯应榴之孙宝圻的同治七年(1870)重刻本。《合注》为五十卷编年本,汇集了冯应榴能看到的苏诗历代旧注,其中包括:(1)宋刊五家《集注东坡先生诗后集》;(2)题名王十朋所编《集百家分类注东坡先生诗》(以下简称“类注本”);(3)施元之、顾禧、施宿《注东坡先生诗》(以下简称“施顾注本”);(4)邵长蘅、李必恒、冯景删补施顾注本而成的《施注苏诗》;(5)查慎行的《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以下简称“查注本”);(6)翁方纲的《苏诗补注》,最后加上冯应榴自己的补注,称为“榴案”。
《合注》以精于文献考订与史实考证而受到历代研究者的好评。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指出:“窃谓王本长于征引故实,施本长于臧否人伦,查本详于考证地理,先生则汇三家之长,而于古典之沿讹者正之,唱酬之失考者补之,舆图之名同实异者核之,以及友朋商榷之言,亦必标举姓氏,其虚怀集益又如此。若夫编年卷第一遵查本,其编次失当者随条辨正而不易其旧,则先生之慎也。……是书出而读苏诗者可以得所折衷矣。”[1]2636吴锡麒则认为:“人皆称其诠释之学精,余独叹其兼总之功大。”[1]2638本文拟重点探讨在乾嘉时期重视考证的学风的影响下,《合注》对“以史证诗”方法拓展升华而成的“寓考证于注释”的方法。
一、《苏文忠公诗合注》的注释学背景
清代学术的根本是重视实证,反对宋明理学一昧用“心解”的方法追求“义理”。清代学术的核心是古典的考证学,无论经、史、子、集,清代学者一律先视作历史文献,治学基础包括: 1、文献学:版本、校勘、辑佚、辨伪;2、语言学:文字、音韵、训诂; 3、历史学:名物、地理、职官、典制、史实等的考证。
在这种学术背景之下,清代诗歌注释者普遍认为,前代诗歌不仅仅是一种文学作品,而且是一种历史文献,甚至首先将前代诗歌看作历史文献,其次才兼及文学作品的属性。对于清代诗歌注释者来说,理解诗歌的意义,不能单纯依靠“以意逆志”式的“心解”,最先应该考虑的是突破注者、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历史隔阂,知其人而论其世,才能接近作者的本意。于是,清代诗歌注释者将重点放在“知人论世”方面,解释诗意普遍采用“以史证诗”的方法,务求以史实为根据。这种解释思路,在清初康熙年间就已经深入人心。例如,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序》认为:“爰是校理旧文,芟柞浮蔓。搜遗补逸,不欲为空谬之谈,亦不敢为深文之说,总期无失作者本来之旨而已。”[2]赵殿成认为解释诗意必须以史料为凭据,并且对诗歌的意旨不敢挖掘太深,以免胶柱鼓瑟,甚至于求深反浅。朱鹤龄《李义山诗集注自序》亦云:“学者不察其本末,以才人浪子目义山,即爱其诗者,亦不过以为帷房暱媒之词而已,此不能论世知人之故也。予故博考时事,推求至隐,因笺成而发之。”[3]对李商隐诗这类托意深远的作品,要推求其意旨,更强调以史实为依据。此外,钱谦益的《钱注杜诗》等注释作品也普遍使用了“以史证诗”方法以考释时事。
因此,诗歌中凡是具有历史考证意义的各种因素,包括诗歌编年、人物生平、历史事件、地理、职官、典制、名物、风俗在内,成为注释工作花费精力最多的环节。这类因素,清代诗歌注释者一般统称为“时事”,如《读杜心解》的作者浦起龙指出:“凡注之例三:曰古事,曰古语,曰时事。”[4]所谓“古事”与“古语”,一指前代书籍中的故事,一指前人诗文作品中的语词,合起来就是诗歌研究者常说的“典故”。而“时事”则是相对于作者而言的,指作者所处的时代环境与社会历史背景,以及具体的历史事件。
在这种学术思维的影响下,康熙年间的苏诗注释者查慎行,尽管本人是著名诗人,但其补注苏诗,却较少探讨苏诗的文学属性,而将重点放在地理、职官、人物生平与史实的考证方面。
至乾嘉时期,考据之学发展到顶峰。乾嘉诗歌注释者的视野中,前代诗歌的历史文献属性进一步凸显,文学属性进一步弱化。乾嘉学者注诗,往往更加慎言意义,而专注于考证故实。相对于康熙年间的诗歌注释而言,乾嘉的诗歌注释者仍然偏重于用“以史证诗”的方法解释时事,但在方法上进一步考证化,加强了对历史名词与历史事件的考证,形成“以考证为注释”的特点,务求在严密考证的基础上探究作者的原意。如冯应榴之弟冯集梧在《樊川诗注自序》中指出:“自孟子有‘知人论世’及‘以意逆志’之说,而奉以从事者,不无求之过深。夫吾人发言,岂必动关时事?牧之语多直达,以视他人之旁寄曲取而意为辞晦者,迥乎不侔。……兹故第诠事实,以相参验,而意义所在,略而不道。”[5]冯集梧甚至不追求对意义的解释,只重视对地理、职官、典制、史实等的考证。
乾嘉时期另一位苏诗注释者沈钦韩长于经、史考证,注诗亦强调考证故实,他在《王荆公诗集注序》中指出:“夫读一代之文章,必晓然于一代之故实,而俯仰揖让于其间,庶几冥契作者之心。”[6]。沈氏所说的“故实”,就是地理、职官、典制等历史名词与各类历史事件。沈氏所著《苏诗查注补正》,在地理、职官、史实等方面作了严谨的考据,纠正了查注的不少错误。
除了时代的学术风气之外,冯应榴的家学渊源对《合注》的注释方法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冯应榴之父冯浩(1719一1801)精于诗文笺注,著有《玉溪生诗笺注》三卷、《樊南文集详注》八卷。其中《玉溪生诗笺注》颇得后代好评,该书在吸取朱鹤龄等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重点对李商隐诗中的典故、史实、典章制度等作出解释与引证,并能在此基础上探索作者的创作意图。在《玉溪生笺注发凡》中,冯浩认为:“说诗最忌穿凿,然独不曰‘以意逆志’乎?今以‘知人论世’之法求之,言外隐衷,似凿而非凿也。”[7]冯应榴之弟冯集梧亦尝撰《樊川诗集注》四卷,上文已述,该书注释的重点在于名物、地理、典章、史实,颇为精审。
在上述学术背景的影响下,《合注》将乾嘉时期重考证的学术思维与清代诗歌注释者普遍采用的“以史证诗”方法相结合,形成了“寓考证于注释”的方法,并体现了自身的特点。
《合注》的“寓考证于注释”的方法,建立在文献考订的基础上,体现了文献学与历史学的交融。冯应榴从文献学的角度对旧注进行了全面整理,这是由以下两个因素决定的:(1)乾嘉学风本身就很重视所引用文献的真实可靠性;(2)合注这种体例也决定必须对旧注作全面的整理。于是,冯应榴对各家注文作了适当的位置调整,删除了一些冗注,并重点纠正旧注在引用文献方面的错误,如引书不标书名、引书弄错作者、引文弄错出处、引文与原文不符、引文非所引之书所有等。冯应榴全面地将旧注注文与原书文字加以详细核对,一一改正上述错误,并汇成《苏文忠诗旧注辨订》一卷,附在《合注》之后。总而言之,《合注》的文献考订工作,即使在乾嘉时期也是首屈一指的。
在文献考订的基础上,冯应榴致力于历史考证,在编年、史实、人物、地理、职官等方面对各家旧注进行详尽地补正。
二、《合注》的编年考证
诗集的编年注本,始于宋代。宋代是编年史修撰的鼎盛时期,代表作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与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宋代编年史书开启了年谱的编撰,年谱实为微观的个人生活“编年史”。现存最早的年谱,是一批诗人年谱,包括北宋吕大防的《韩吏部文公集年谱》与《杜工部诗年谱》。宋代编年体史书还影响了文集的编纂,产生了编年本这一新的文集编排体例。如果说年谱是个人事迹的编年史,那编年文集则是文学作品的编年史。注释者以编年本为底本加以注释,从而形成编年注本,其优点在于能够随作品产生的年代逐篇注释,将作品与注释置于当代史事的背景之下,有助于理解作品的寓意。自宋代注家采用编年注以来,这种注释体例就一直为历代注家所喜爱,成为中国古典诗歌注释的主流。
宋代刊行的《东坡集》即为编年,施、顾注本就是在《东坡集》的基础上形成的编年注本。到了清代,苏诗注释者进一步讨论苏诗的编年问题,考证前代编年的错漏。如查慎行认为:“苏诗宜编年固矣,惟是先生升沉中外,时地屡易,篇什繁多,必若部居州次,一一不爽,自非朝夕从游,畴能定之。施元之、顾景繁生南渡时,去先生之世未远,排纂尚有舛错。”[1]2723他认为施、顾注本的编年亦存在错误,于是以邵长蘅整理的《施注苏诗》为蓝本,对其编年作了调整。冯应榴首先对苏诗的最初编年者作了考辨。冯云:“今所称《东坡七集》……其《前集》卷首以《辛丑十一月初赴凤翔》诗为冠,而《南行集》中诗皆在《续集》内,则《前》、《后》二集之诗必系先生及子由所编定,其《续集》诸诗皆经删削。是以宋刊施、顾注本亦照《前》、《后》集次序。”[1]1冯应榴指出了《东坡集》的真正编年者应为苏轼本人及苏辙,并进一步对旧注的编年作了严密的考证。
(一)针对类注本的编年考证
王十朋所编类注本,体例虽为分类,但其前身的苏诗集注本皆为编年。上文已述,最早无注的《东坡集》即为编年本,注家一仍其例进行注释,从四注、五注、八注、十注发展为百家注本。王十朋集百家注文之后,诗篇仍按编年排列,后来由著名学者吕祖谦将全书分为七十八类。
类注本的注家中,任居实比较重视探讨编年问题,但也存在一些错误,为冯应榴所纠正。例如《沈谏议召游湖不赴明日得双莲于北山下作一绝持献沈既见和又别作一首因用其韵》:
任居实注:熙宁五年壬子十二月作。
冯注:莲花开于十二月者绝少,况后《和沈留别》诗公自注云:“去时余在试院,而放榜在八月十七日”,则其误尤显然矣。[1]338
任居实断定本诗作于熙宁五年壬子十二月,却没有提出任何根据。冯应榴根据事物的常理,指出莲花开于十二月者极其罕见,对任注先是提出了质疑,后来又提出了佐证:苏轼与沈谏议同时唱和的另一首《和沈留别》诗保存了苏轼的自注,记录作诗时间为八月。两相参证,便可颠覆任居实的结论。
又如《和王晋卿》:
任居实注:元祐四年己巳作。
冯注:先生叙中先云元丰二年贬谪,又云不相闻者七年,则此诗决非元祐四年作矣。原注误。[1]1461
冯应榴根据苏轼此诗的自叙,指出任居实注的错误。《施注苏诗》、查注本皆将此诗编入元祐二年(丁卯)。
(二)针对查注本的编年考证
查慎行的《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亦为编年注本,全书50卷,第1~45卷为编年诗,编年顺序以邵长蘅《施注苏诗》为基础。施顾注宋本流传到清代,已阙十二卷,但全书目录尚存,邵长蘅在补充这十二卷时仍以原目录的编年顺序为准。但查慎行认为《施注苏诗》的编年存在不少的问题,因此根据自已的考证改动了原本的编年。事实上,宋代施顾注本的编年者并非注者,而是苏轼本人与苏辙,施元之与顾禧只不过是利用已编年的《东坡全集》进行笺注而已。此外,施、顾注本不收而见于明人所编《东坡外集》及邵长蘅所编《苏诗续补遗》者,凡是能确定编年的,查慎行亦将其移入编年的各卷之中。查慎行致力于苏诗的重新编年,成就虽高,失误亦多。尤其是施顾注本的编年只根据年份撮其大纲,并没有尽量根据月、日逐首细分,查注则细分年月。冯应榴肯定施注的做法而否定查注,并从以下方面纠正查慎行编年之误。
1.根据地理。例如《入峡》:
查注:《吴船录》:发泥碚村,六十里至恭州,自此入峡。……按《栾城集》,《入峡》诗在《巫山庙》之前,盖误以瞿塘为入峡也,今依《吴船录》附编《渝州》诗后。
冯注:余视学蜀中,自成都水程至夔州,凡过涪、忠诸险地,皆不称峡,至夔府以下方入三峡。《栾城集》编次并不误,查说非也。[1]15
嘉祐四年,苏轼、苏辙兄弟陪侍苏洵由长江水路出川,沿途二人有许多同题诗,《入峡》就是其中一首。关于这组诗,苏辙《栾城集》的编次与苏轼集中是一致的。冯应榴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栾城集》编次无误,亦即东坡《入峡》诗原编次无误。查慎行没有亲历二苏的行程,仅凭范成大《吴船录》中的记载而误判。
2.根据人际活动常理。例如《次韵子由除日见寄》,查慎行编入头一年即嘉祐六年辛丑卷中。冯注云:“汴京与凤翔相隔,子由于京都除日所寄,则和章必在下年。”[1]103冯应榴的意见无疑是符合事理的。
3.根据东坡的生平活动。例如《白鹤峰新居欲成夜过西邻翟秀才二首》:
查注:此二首施氏原本讹编丙子重九诗后,今改正。
冯注:题曰“欲成”,则尚未成也。新居成于四年二月,此诗编于三年九月之后,甚为惬当,《七集》本亦然,并不讹也,查说非。[1]2091
苏轼贬谪惠州时,在白鹤峰西建造新居,于绍圣四年二月落成。本诗题曰“新居欲成”,则施顾注本原先编在绍圣三年(丙子)九月重阳诗之后,并无太大的问题。查慎行显然持论过苛。
4.根据东坡文。例如《苏州姚氏三瑞堂》:
查注:此诗施氏本讹编密州卷中,今据《外集》改正。
冯注:先生《答水陆通长老书》云:《三瑞堂》诗已作了,纳去。是蒙求之如此其切,不敢不作也。又云:枣子两罨,不足为报,但此中所有只此耳。玩书语,意似为枣为密州特产,则此诗竟似在密州作。施氏原编不误,王本注转不确,查氏改编亦误也。今姑从之,而附辨于此。[1]541
苏轼的《答水陆通长老书》一文提到了《三瑞堂》一诗的创作已毕,又提到了密州的特产枣子,《三瑞堂》作于熙宁八年密州任上的可能性很大,加上施顾注本原先就编于密州卷中,因此冯应榴倾向于认为查慎行改编到熙宁六年杭州通判任上是错误的。但冯应榴治学态度非常严谨,在缺乏更确凿的材料的前提下,没有轻易地改动查注本的编次,只是将自己的意见附于注文之后,以俟后人补充。
5.根据《乌台诗案》。例如《颍州初别子由二首》:
施、顾注本、查注本二本皆将此诗编在《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陪欧阳公宴西湖》二诗之前。
冯注:在颍州与子由同访欧阳,陪燕赋诗。则相别在后,不应转编下二首之前。查氏似亦失详细也。况《诗案》云:“后十一月到杭州本任,作《初别子由》诗。”尤为可证。今以相隔不殊,姑仍其旧。[1]249
苏轼与苏辙在颍州拜访欧阳修,根据人际交往的常理,应当先有在欧阳修处陪宴赋诗等活动,然后才有兄弟分别,尤其是《乌台诗案》记录了《初别子由》的作诗时间。《乌台诗案》是苏轼本人在御史台的自供状,可信度高,因此可以冯应榴的结论是有根据的。
6.根据他人的生平事迹。例如《滕达道挽词二首》,施顾注本、查注本编入元祐七年。冯注云:“元发既卒于元祐五年,则先生挽词不应入于七年。”[1]179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四十九“元祐五年冬十月”条云:“乙卯,新知青州、龙图阁学士、右光禄大夫滕元发卒。”[8]根据滕元发(字达道)的卒年,施顾注本、查注本的编次显然是错误的。
冯应榴尤其着重于查注本编年的几类问题:
1.指出查慎行未辨别东坡原编年的错误。例如《和致仕张郎中春昼》,施顾注本、查注本编入熙宁五年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
冯注:先生于冬至后往湖州,此诗有“东风屈指无多日”句,当是在湖所作。至下首《再寄莘老诗》有“泥中相从岂得久,今我不往行恐迟”句,当是在盐官督役,未至湖以前作。原编似稍失次,查氏并未更正,今亦不另移矣。[1]376
熙宁五年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曾连续被差遣于外,先是十月之后督开运盐河至盐官,十二月运司又差往湖州相度堤岸,与诗中的“东风屈指无多日”正相符。而本诗的下一首《再寄莘老诗》有“泥中相从岂得久,今我不往行恐迟”之句,与苏轼督役之举相符,应作于督开运盐河之时,两首先后次序应互换。查慎行未能辨别出施顾注本编次的错误。
2.指出查不知年代而强分。例如《和陶诗》,冯应榴《苏诗旧注辨订》云:“《和陶诗》除《饮酒二十首》外固皆在岭南作,但年月有难细分者,不如诸本各自为卷之善。”[1]2670《和陶诗》是苏轼晚年的力作,非一时一地之作,很难断定具体的作诗年月,施顾注本将其单独列为二卷,放在全书之末,本来是最谨慎的处理方式。查慎行强行编入某年某月中,查云:“《和陶诗》一百三十六首,子由有序,自成二卷。细考之,惟《饮酒》二十章和于扬州官舍,余悉绍圣甲戌后自惠迁儋七年中作也,岁月大略可稽,分之各卷以符编年之例。其间亦有未能确指年月者,则慎以意推之,要难迁就他所也。”[1]2728《和陶诗》的大多数诗篇未能确指年月,查慎行“以意推之”,过于武断。
3.本可编年而不入编年。例如《出局偶书》:查本此诗编入卷四十八《补编诗》中。冯注云:“此诗王本所有,在“书事”类,旧王本在“杂赋”类。并据自题年月,应编于元祐戊辰冬卷,查氏不入编年,何也?”[1]2451此诗有苏轼自注,写明了作诗年月,未入编年诗部分,显然是查慎行的遗漏。
三、《合注》的时事考证
苏诗有“以议论为诗”的特点,许多诗篇与时事相关,苏轼在《乞郡劄子》中说过:“臣屡论事,未蒙施行,乃复作为诗文,寓物托讽,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9]甚至可以说苏诗是继杜诗之后的又一部“诗史”。解释苏诗的意旨,“以史证诗”是重要的方法,即考证苏轼及与其和答唱酬之人的相关事迹,并联系当时的重大事件,由此使读者置身于具体的历史背景之中来理解苏诗。宋代施宿所作的《注东坡先生诗》题下注,就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从题中的人物与事件出发,援引了大量宋代国史、实录、墓志、笔记、诗话、方志、文集中的材料,对与苏轼本人及与之唱酬寄赠之人的生平事迹作了翔实的介绍,展示与苏诗有关的时代背景,在熙宁变法与元祐党争的背景下解释诗意,由此揭示了该诗的写作背景与诗篇的寓意,并且以时事为依据解释相关的句意。这时的“以史证诗”方法,本质上还是“以史释诗”的思路,重在“印证”,即将苏诗的诗题或诗句与时事相互对照、印证,用各种文献材料中的史实解释说明、佐证诗意。查注本沿着这一思路对施宿注作了有力的补充。但仅仅继承是不够的,因为清代注释者离作者苏轼已有六七百年的时间间隔,清人能接触到的各种与宋代相关的史料,在历史的长河中泥沙俱下,必须通过严密的考证,去伪存真。乾嘉时期的“以史证诗”,除了“印证”之外,更强调“考证”。《合注》较之施宿注、查注的突破之处在于,冯应榴以主要的精力对诸家旧注所援引的史料进行严密的考证,纠正其中的不少错误,保证了“以史证诗”方法的有效实施,形成了“寓考证于注释”的方法。
(一)补正解题
在类注本中,赵夔是对题中人物生平最着力的注家,但同时错误也不少,其错误包括弄错人物身份的多个方面,包括姓名、字号、籍贯、世系、官职、卒年、卒地等。题中人物的生平,是理解诗意的重要背景材料。赵夔作为距苏轼不远的宋代注释者,犯下如此多的错误,令人遗憾,幸得冯应榴一一补正。如《京师哭任遵圣》:
赵夔注:遵圣尝为寺丞,卒于京师。
冯注:玩诗中“竟使落穷山,青衫就黄壤。归见累累葬,望哭国西门”等句,当卒于蜀中平泉官舍。尧卿云:“卒于京师”,误也。先生必于京师闻信哭之,故题云然。[1]690
本诗为苏轼悼念亡友任遵圣所作,赵夔未细品诗意,只是望文生义,从而想当然地认为任卒于京师,亦可能误导读者。
查注对人物生平与事件的错误叙述亦复不少。如《谢运使仲适座上送王敏仲北使》:
查注:《宋史》:王古,懿敏公素从子靖之子,第进士,历迁户部侍郎……堕党籍,责衡州别驾。独不载北使事。
冯注:《宋史》本传明载“奉使契丹”,即北使也,查氏误甚。[1]1880
在这首送别诗中,“王敏仲北使”是其中的关键字眼,而查注重点指出“独不载北使事”,显然对诗题提出了不正确的质疑。冯应榴指出“《宋史》本传明载‘奉使契丹’”,避免了混淆视听。
除了辨正旧注中的错误之外,冯应榴还补充了旧注中的疏漏,特别是一些历代旧注全都失注之处。冯应榴的补注善于使用南宋李焘所编《续资治通鉴长编》这一类的编年体史书,当纪传体史书阙载某人的传记时,冯应榴可以从《续通鉴长编》中抽取该人数年的行迹汇合在一处,起传记的作用。例如《送沈逵赴广南》,施顾注、查注都没有注沈逵。
冯注:《续通鉴长编》:熙宁六年十二月,诏新知永嘉县沈逵相度成都府置市易务利害。九年十一月,诏大理寺丞沈逵改一官,与堂除,论前任信州推官兴置银坑之劳。当即此人也。其战西羌事,无可考。[1]1209
从而交待了沈逵的来龙去脉。
(二)补正句意
1.直陈其事、与史实密切相关的句意。
如《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联翩阅三守”:
查注:子由初到陈州,时张安道留守南都,至熙宁七年,陈述古自杭州移知应天府。其一人无可考。
冯注:《续通鉴长编》:熙宁七年十一月,张方平为宣徽北院使,判应天府。方平辞,乃命与知青州滕甫易任。方平卒不行,归院供职。八年十月,张方平判应天府,是则方平于八年始继滕甫判应天也。至陈述古判应天,年月已见前《和拒霜花》诗注。合计三守中先陈襄,次滕甫,次张方平。查云子由初到陈州,张安平留守南都,非也。至安道于嘉祐中两知应天,其时子由并未相随,与此无涉。[1]902
苏轼此诗作于元丰二年,“联翩阅三守”指的是苏辙在熙宁至元丰年间陈州教授、齐州掌书记、南京判官等任上受应天(南京)知府管辖,前后历三任。查慎行的考证功力显然有所欠缺,只能列出两人,而且其中的张安道还是误入者。冯应榴综合《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数年的相关记载指出,张安道任应天知府是在宋仁宗嘉祐年间,与苏辙并无关系。苏辙所阅“三守”是陈襄(字述古)、滕甫、张方平等三人,从而正确地解释了诗意。
2.与地理、职官相关的句意。
地理、职官、典制一类的历史名词,是注释中的难点。这一类名词,作者在使用时未必有深意,但因为官制历代更易,地理屡朝变迁,后代注者与读者往往难以准确把握,从而导致误读诗意。
查注本把地理作为重点,但其中错误也不少,为冯应榴指正。例如《南都妙峰亭》“孤云抱商丘,芳草连杏山。”
查注:杏山,历代地志俱不载,惟《一统志》云:开封府钧州,后改禹州,杏山在城北二十里。《洛阳记》云:仙人刘根尝隐于此。
冯注:查注所引杏山在开封钧州,断非先生诗所指。今考《一统志》:归德府有幸山,在府城南三里。虽据明李嵩诗“最是翠华临驭地,上人今作幸山呼”,似因宋高宗即位于此始得名,而《栾城集》《次韵文务光游南湖》诗自注:湖前小山,曰杏山。考南湖在南都,则必南宋时方改“杏”为“幸”也。先生诗即指此。[1]1256
查注所引杏山在开封,而苏轼诗题中有“南都”,前句又有“商丘”,二者必非同一处。如查注所云,必然干扰读者对诗意的判断。冯应榴不仅指出了查注的错误,还且还考证出南都(即商丘、归德府)确有杏山,后改为“幸山”。
冯应榴亦善于补正旧注中职官典制方面的问题。例如《初到黄州》“尚废官家压酒囊”:
苏轼自注:检校官例折支,多得退酒袋。
冯注:《文献通考》:文臣料钱,一分见钱,二分折支。陆锡熊曰:自注所云折支者,谓以他物代钱也。退酒袋者,官法酒用余之废袋也。盖宋时俸料,每以他物折抵,退酒袋即折抵之物耳。又榴案:《通考》载杨亿言:半俸三分之内,其二分以他物给之,鬻于市廛,十裁得其三。今先生云检校例折支,并当一分见钱亦不得也。[1]994
苏轼自注所云,尚属简略。冯应榴引用《文献通考》的多处相关记载,详细地解释了折支制度的来龙去脉,对句意作出详尽的拓展性说明。
参考文献:
[1] (宋)苏轼. 苏轼诗集合注[M].(清)冯应榴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 (唐)王维.王右丞集笺注[M].(清)赵殿成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2.
[3] (唐)李商隐.李义山诗集注[A].(清)朱鹤龄注.文渊阁四库全书[C].108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82.
[4] (唐)杜甫.读杜心解[M].(清)浦起龙注.北京:中华书局,1961:6.
[5] (唐)杜牧.樊川诗集注[M].(清)冯集梧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新1版:3.
[6] (宋)王安石.王荆公诗集注[A].(清)沈钦韩注.续修四库全书[C].13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影印版:439.
[7] (唐)李商隐.玉溪生诗集笺注[M].(清)冯浩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822.
[8]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A].文渊阁四库全书[C].32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764.
[9] (宋)苏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