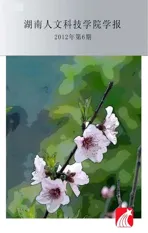论梅山民俗艺术学研究的基本理路
2012-04-08郭文成
郭文成,周 琳
(1.湖南人文科技学院美术系,湖南娄底417000;2.湖南人文科技学院计财处,湖南娄底417000)
“梅山”之名的由来,学者比较普遍认同的观点是因汉代长沙王吴芮部将梅鋗定居于该地而得名:在同治11年版《安化县志》和清光绪11年版《湖南通志》中都是记载梅山因梅鋗家居此而命名的实指具体地名。而梅山文化是一种特色明显的地域文化,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从梅山的民俗中发掘其审美文化内涵,揭示其基本特点和形成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梅山民俗艺术的文化内涵和基本理路,从而培育和提升我们的审美品质,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审美构建。
一 梅山民俗艺术学研究缘起
陶思炎先生在《应用民俗学》中指出:任何民俗事象和民间文学都不是可有可无的赘物,它在现代其承传的俗民社会中总是起着这样或那样实际的作用。这些作用就是功能,它作为传承的动力,构成这一民俗事象赖以形成的前提[1]。他还认为“民俗艺术学是在艺术学与相关人文社会科学交互作用的背景下形成的,此外,产业发展也在实践的层面上为民俗艺术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1]由此可见,民俗艺术学研究非常有必要到具体的地方民俗的原野上去实际考察,并且在这一片原野上建立了他们研究的基地。
自20世纪以来,齐美尔的社会学美学主导了一个重要的西方社会学传统。齐美尔将美学的基本观念运用于现代社会研究,认为社会从个体层面到整体层面,都是按照美学的对称性、远-近距离的相对性、部分与整体的协调性等基本原则构成和运动的。因此,根据他的观点,社会不是在隐喻的意义上,而是在本质的意义上是一个艺术品。而在20世纪后期,社会学美学发展为研究和描述后现代性社会(文化)的最主要的社会学理论。其中,德国社会学家卢曼(N.Luhmann)的理论特别值得注意。他恰好在100年后,明确回应了齐美尔“社会是一件艺术品”的观念,并将此观念作为自己的社会学研究和阐述的理论核心。但是,与齐美尔以现代性为理论语境不同,卢曼以后现代性为理论语境。因此,与齐美尔强调社会作为艺术品的整体性和对称性机制不同,卢曼强调的是后现代社会与艺术共有的差异、变化和不确定性。卢曼的理论突出表明,在现代西方社会学领域,“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的根本意义,不是表明在多大程度日常生活被普遍审美化了,而是审美性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范畴承担着解释后现代日常生活中的不可解释的现象的功能。同时,德国哲学家韦尔施(W.Welsch)将当代现实在整体上定义为“一种美学的建构”。相对于其他学者关注表面的、浅层的审美化,他着重揭示的是深层的审美化,即由康德认识论革命带来的认识论的审美化:美学变成了认识论的基础。韦尔施揭示了现代社会学的一个更深层的理论转型:借用康德以来的美学理论反思和描述现代社会,即社会学的美学化。社会学美学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艺术取代宗教在现代生活中普遍化,并且形成了现代生活的审美化特性[2]。
从梅山研究来看,当前的梅山研究还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但13年来的采风与理论研究还是取得一定的成绩,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梅山历史的研究。梅山历史,由今、古梅山,扩展到上古梅山的研究,特别是对蚩尤的研究,是卓越的。梅山的历史,是没有文字的历史,或者说是文字极度贫乏的历史,我们根据歌谣、神灵、菩萨、科仪、信仰、禁忌、习俗、生活方式进行研究。其二,梅山的宗教研究。一般认为梅山神灵是非准宗教,它界于宗教与非宗教之间,这是它区别其他宗教的分水岭。其三,梅山的艺术风俗研究,主要集中在歌谣,神像、建筑木板房等的研究[3]。纵观这些成果来看,研究的重心仍在于对梅山文化的研究对象、内容以及方法等的学科定位上,这的确是很重要的基础性的一步,但缺乏关于梅山文化深入的主题性研究。基于此,笔者认为还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其一,重点从节俗问题的角度来切入梅山民俗艺术研究,在当下重新反思民俗的审美意义;其二,试图探寻梅山节俗思想对于中国当下民族和谐的意义;其三,注重哲学、民俗学以及社会学等最新的理论来开辟梅山民俗艺术研究的新范式。
二 梅山民俗艺术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和主要观点
笔者认为要以梅山节日风俗为切入点,从艺术人类学的视域分析梅山民俗艺术的内容、机制、方法、载体、环境等与梅山文化形成的内在逻辑与机制关联性,同时以隆回县作为研究支点,以点带面来展开。由此拟从三个方面展开研究:
(一)梅山原生态民俗艺术的问题域
①节日与民俗:如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重阳。节日的区分为一般节日与特殊节日。梅山传统节日大都有自然时令方面的基础,对人生影响重大的自然变化在自然循环中凸现出来,这是梅山节日得以形成的客观基础。梅山节日体现出的主要文化观念有:万物有灵和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子嗣意识,审美和娱乐,这些观念都是从古代社会的实际生活存在处生发出来的。梅山主要的传统节日大都经历了一个节期由长到短、原始观念退化和后起观念补充进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带有浓郁巫祭之风的节日逐渐演变成了欢娱色彩浓郁的佳节良辰。②这里注重其民俗艺术的原生态性,主要从滩头的民间年画、花瑶的挑花工艺品、七江的“碳花”绝品、岩口的竹编技艺、罗洪的陶瓷艺术、桃洪镇的园林艺术等来展开,分析其独特的审美内涵与文化品位。
(二)梅山原生态民俗艺术的审美主题
节期和节俗活动是民俗节日的两大本质构成要素。时间对于传统节日的逻辑生成具有本质性的作用,传统节日主要是在时间的双重运动中生成的,即时间的形式化和时间的时间化共同促成了节日的诞生。其中,时间的形式化保证了节日在一个时间段内固定下来,为节日提供了固定的节期,它是节期的内在依据;时间的时间化则使这段特殊的时间的时间性凸现出来,从而使之葆有丰盈的意义,它是节俗活动及其文化内涵的内在依据。时间的双重运动共同奏响了人的节律化存在的音符。从经验的角度来看,时间的双重运动还促成了节日感的诞生,故本章对节日感也做了初步探讨。在时间形式化和时间时间化的双重作用下,节日从常日中显露出来,并显现出自身的特质,成为一段紧密关涉人生存在和人生意义的特殊时间。在这段时间中,民众获得了一种有别于常日的人生经验——节日感。节日感是一种特殊的时间感和关于存在的实感,它既是一种时间经验,也是一种存在体验,作为一种时间经验它是存在化了的,作为一种存在体验它是时间化了的。节日感是在人和存在的相遇中生成的,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共同“到时”促成的,故它不是现成化的关于过去的陈腐经验,而是常新的人生经验。
以隆回花瑶的节俗为点展开细致探讨,突出其原生态的审美主题。隆回小沙江瑶族就是“梅山蛮”的后代,那里至今保存着很多特色独具的文化遗存。这里被国家文化部誉为现代“绘画之乡”、“诗歌之乡”,被湖南省人民政府定为县域文化建设基地。隆回花瑶有着独具特色的三大传统节日,“讨念拜”和两次“讨僚皈”,通称“赶苗”,每次节日都有它特定的历史渊源。农历五月十五至十七日的“讨念拜”,源于明朝万历元年(1573年);农历七月初二至初四日的“讨僚皈”,源于元朝末年;农历七月初八至初十日“讨僚皈”,源于清朝雍正元年(1723年)。每逢节日,花瑶人民不论男女老少,举家出动,一律身着节日盛装,奔赴集会地点。这时也是阿哥阿妹赛歌对舞、谈情说爱的最好时期。花瑶的独特婚俗:花瑶具有婚俗在独特的地理环境下极富情致,媒人都是男子,称“媒公”。婚礼中的“拦门酒”,“打泥巴”,“打蹈”会让游客惊叹它的奇特之处。
(三)梅山原生态民俗艺术的审美意义
梅山民俗中凸显出梅山的宗教、艺术、风俗等复杂的内容。这里试图从艺术哲学、民俗学以及社会学等角度来透视。①梅山的宗教是半古老的、古老的。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宗教,已经远非原始形态了,是通过若干年的变迁成为了半古老的了。其最古老形式,当然是古老巫术。有符、诀、咒等,已经是非最古老的了。可是,符、诀、咒倒影了原始巫术。梅山神是十分奇特的神灵,张五郎是倒立的神灵,这在中国神界,是罕见的,独特的。他不享受正宗的香火祭祀,也是特殊的。在树下、山野,在旁屋、侧厅,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更是独具个性。梅山法术到现在,仍有其市场,仍有其功用,如捕捉泥鳅等。这是半古老宗教的特殊性标志。梅山神灵是非准宗教,或者说是降宗教,这又是其特色。同时又不完全等同于原始宗教,因为其原始宗教面目全非了。它界于宗教与非宗教之间,这是它区别其他宗教的分水岭②梅山的艺术也是很鲜明的。如歌谣,如被套戏,如草龙、如傩狮,如五子棋,如婚庆抛泥团,如建筑木板房等。艺术是心灵的再度闪光,梅山的艺术,古朴而灵巧,粗拙而凝重。③梅山风俗。风俗是相对稳定的,尽管在一定历史区间有变异性,但是,相对而言是静态的。梅山地区的旧俗、怪俗、骂俗,是很特别的,如中秋偷瓜、给树喂饭、捕猎见者有份等。
三 梅山民俗艺术学研究的创新点与意义
梅山民俗艺术学研究的创新首先在于研究角度新:有别于以往学界对于梅山文化研究的一般路径,专从美学这一角度探讨梅山节俗形成的内在逻辑与审美机制,从而实现了由“是什么”和“为什么”到“怎么办”的现实性转向,拓展了研究领域新视野。其次是理论建构新。以梅山节俗的功能和作用规律为切入点,分析梅山节俗的内容、机制、方法、载体、环境等与梅山文化形成的内在逻辑与机制关联性,就有利于形成一个全新的、系统的研究梅山文化体系的理论框架。再次是研究方法新。一是文献研究的方法,主要以重要文献作为第一手资料,深入梳理、挖掘关于梅山节俗美学的有关论述,同时注意分析、吸收国内外关于的相关研究成果;二是交叉学科的方法,注重以哲学、民俗学以及社会学等最新的理论来开辟梅山文化研究的新范式。由此,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取代以往局限于对梅山文化的定性探讨,开辟了梅山文化研究的新范式。
综上所述,梅山民俗艺术学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以梅山节俗的功能和作用规律为切入点,分析梅山节俗审美的内容、机制、方法、载体、环境等与梅山文化形成的内在逻辑与机制关联性,这有利于形成一个全新的、系统的研究梅山文化体系的理论框架,从而推进梅山文化的理论建构;而其实践意义在于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有利于促进梅山地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建设当代社会主义新农村[4]。
[1]陶思炎.论民俗艺术学体系形成的理论与实践基础[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11(4):82-86.
[2]肖鹰.美学与文学理论:对当前几个流行命题的反思[J].文艺研究,2006(10):12-13.
[3]郭兆祥.中国梅山文化研究述评初稿[M]∥中国第五届梅山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9:356.
[4]刘楚魁,刘红梅.研究梅山文化的意义管见[J].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08(5):4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