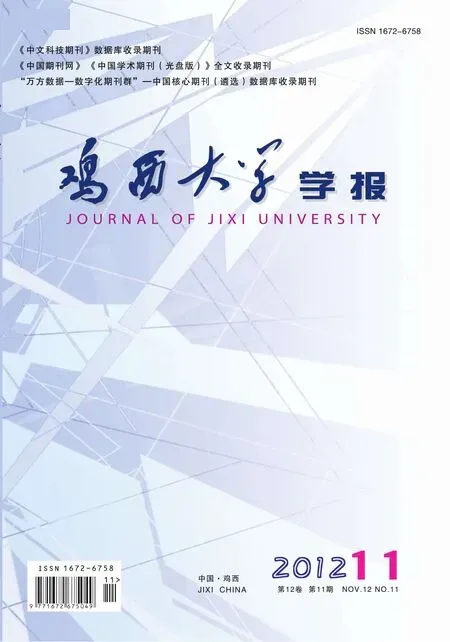从《客人》浅谈文学审美化的世界
2012-04-08张蓉
张 蓉
(西北师范大学,甘肃兰州 730070)
社会现实或生活世界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1]王祥夫的小说也如此——根源于现实。作者通过日常化的描述,以一贯悲天悯人的情怀不仅揭示在当前社会中,城市和农村这两种文明日益尖锐的矛盾,并以作者独特的感受体验和诠释,追问人生的哲思。因此,文学被认为是社会生活的翻版和真实写照。但是,文学现实与社会现实不同,尽管文学根源于现实这是毋庸置疑的。在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现实确切的说是被审美化艺术化的作品现实,王祥夫这篇短篇小说《客人》也不例外,现就以《客人》为例来探讨作品现实与社会现实的区别和联系。
《客人》取材于日常生活,这是这边小说显而易见的特点。理论上讲,作品被视为社会生活的翻版和真实写照。尽管文学的现实的可感性与社会现实是一致的,这也是文学现实与社会现实容易被混淆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文学现实并不能等同于社会历史现实。社会现实给作品以实践、借鉴,在文学作品中,作品现实是经过作者独特的艺术手段而建构起来的虚拟世界。小说《客人》通过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生活环境,创造出了具有这个环境特色的人物、故事情节。主人公刘桂珍一家生活在城市里,是当前城市生活的真实写照。而客人们,作者叙述“他们的衣着让人明白他们不是这个城市里的人,他们一定是乡下的,而且不是这里的乡下人,”有可能是“河南来的乡下人”。在这里,已经把主客人的身份交代的一清二楚,主人是城里在家待自己孩子共庆寿宴的,而客人却是主人公二儿子不愿招待的亲戚过来避难的。故事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开展。“主人”和“客人”们虽然是个别的,实质却是对同类形象共同性质的概括。但这种概括并不仅仅赋予了人物真实的形象,最重要的还有人物的生命以及对生命的反思。别林斯基说:“典型是熟悉的陌生人”。典型性是小说常用的创作方法,能使小说情节富有生动性,将人物带入一种典型的环境中,反映出大的社会环境中的人生百态。《客人》通过特定的环境来突显人物之间的矛盾,从而达到反映社会现实的目的。当前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在这个大的背景下,城市农村生活方式巨大反差,作者巧妙通过饮食和卫生习惯来表现。正面的描述城市中光鲜亮丽的生活,还有对一群来自农村的客人种种不合时宜的动作表情的处理,让读者去填补其中的空白,侧面了解当下偏远农村的生活背景。在众多富有生活气息的材料面前,作者独具匠心的以普通人的嗅觉作为暗线,突出一个“味”的变化来升级人物矛盾和深化文章的意蕴。文章在一开始,通过做饭的考究和房间的格局来突出饭菜的诱人香味,房间干净整洁。但在客人们的到来,这个房间的味道顿时变得光怪陆离:
“刘桂珍的大儿子耸耸鼻子,屋子掺和进了一种……气味,是臭,也不是,是腥,是一种让人从未领略过的陌生的味道,……那味道是从外边进来的这大大小小七个人的身上散发出的,一开始是微弱的,但很快就气势汹汹起来,简直就要压倒厨房那边飘过来的香气。”……“他们一出汗,屋子里的味道便更加浓郁了。像汤里放了白胡椒粉和格外多的味精。”……甚至连客人们的衣服上“一律都散发着怪怪的气味。”
这些怪异的味道其实突显出来的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真实经历。较发达的物质生活,让城市里干净整洁的居民带上属于城市的特殊味道。但来了这么一群“客人”后,我们的记忆和嗅觉好像被打开了,一切都变得灵敏起来,农村特有的味道难以让城市接受。在当前的社会,农村在城市里暗合的形象无外乎“脏乱差”,因此,“客人”们的味道尤其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中就立刻跟这个城市中最小的一个组成单位格格不入。尤其在排泄后给刘桂珍一家带来生理和心理的强大冲击和压力,彻底让刘桂珍一家失去了最后的的耐心。这样一个“香和臭”的环境对比刻画,在我们标榜着生命面前人人平等,却在现实世界面前不堪一击,一群看似没有区别的人,在强大的物质压抑下,早已划分成界限分明的两个世界两种等级。环境的对立,习惯的不同,从本来平面的视角,转向立体的变化,朴素平淡的生活掩映的不仅是对当前社会真实现状的描述,还有对生命的思考。“香和臭”的问题,此时,已转向作者对社会将要抛弃的这个底层人民的强烈人文关怀。通过“味”,自觉追问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当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在这种转型中,必定会带来一定的社会问题。作者在小心翼翼的处理客人到来的拘谨,但“味”所代表的时代隔阂,却成了城市和农村难以铲除的障碍。
在文学活动的四要素中,“文学——世界”的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之一。[2]文学与社会现实的联系也是十分紧密而且复杂的。不仅作者是社会的一员,[3]具有社会性,而且文学自身内容也具有社会性。但是通过作者运用典型化等文学手法表现出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复杂关系,但不能将文学世界与同现实世界等同起来。文学不是社会现实,而是一个独立的意蕴深厚的艺术审美世界。
从真实性来讲,不是指小说所叙述的事情必须是在日常生活中真实发生过的,而是要暗合“历史理性”。[4]追求事物的本质和其内在的意蕴尤为重要。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小说所构成的“现实”,实质上是小说自身所蕴含的世界的表现。从小说题目“客人”的理解上,“客人”意义的挖掘其实已经开始暗含小说的意蕴,形成小说自己的世界。作者独具匠心的以“客人”为题,并以主人公刘桂珍的视角来观察世界的。主人公刘桂珍是与主题“客人”相呼应的,并且小说的所有场景在刘桂珍的家中完成的,因此,刘桂珍不仅仅是小说《客人》的主人公,也是小说唯一的“主人”。因此,“主人”和“客人”对立的身份,更好的加深了读者的理解。小说一开始,是以刘桂珍老人为自己的七十大寿做寿宴开始的。做菜的细致和考究,充满了家庭的温暖和老人对孩子回家的期盼。刘桂珍的寿宴是宴请“客人”的。客人不言而喻,是刘桂珍自己的孩子们,大家在一起要为她的七十大寿做庆贺。但是由于二儿子一家不负责任的逃避,刘桂珍代替二儿子宴请了一批她意料外的“客人”——二儿子媳妇从乡下来的亲戚。在小说中,“客人”所指的第一种意义很容易被读者接受,就是刘桂珍二儿子的乡下亲戚。但第二种“客人”的意义在小说中很难被发现:这就是刘桂珍的家人。刘桂珍是独居的,并在七十大寿“这天早早就起来收拾了。大儿子,二儿子,三儿子,还有闺女,一共要来六七口子。”儿女都有自己的生活和生活空间,并不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在母亲大寿这天齐聚欢宴。七十岁的老人应该是颐养天年的时候,但老人却要操劳做一顿丰盛的午饭等待孩子的回归。这种看似合理的社会现象却是小说所要形成的独特的社会空间。人物关系自然而合理的安排,其实已经是被加工改造而具有意义的表现,并不是简单的对客观现实的描述。
这篇语气平淡,语言质朴的小说叙事时隐去叙事行为的痕迹,让小说场景时间自行呈现。借助普通的场景将小说的意蕴消解在生活行为当中。一个简单的动作,而我们理解的不仅仅是人物的内心世界,还有在这个人物后所暗含的社会历史环境而深化主题意蕴,帮助完成了小说的审美艺术世界。主客人到来刚开始吃饭时,刘桂珍一家虽然对客人的到来表示了宽容,尤其是刘桂珍和大儿子、三儿子的陪客。然而“刘桂珍的闺女在厨房里小声说:……我就不进去吃了。……刘桂珍的大儿媳便也表示了不满,说:我也在厨房吃一口算了。”女儿和大儿媳却躲在厨房避开客人吃饭。这种态度与现实中,城市对农村抗拒式的态度是是不谋而合的,为小说的发展埋下伏笔。《客人》所呈现出来的世界,客人们的悲欢无疑呼唤着同情与怜悯,但客人们苦涩的微笑和无言的沉默,却拒绝任何的俯视。刘桂珍一家给了客人去外面吃晚饭用的14元吃饭钱,在客人们离开后,“刘桂珍忽然在屋里发现了放在茶盘子里的那十四块钱。”由于城市条件的种种限制,刘桂珍的老房子不大,来的人又多,城市小家庭的空间根本容纳不起来十几个人。一件本来欢天喜地亲戚团聚的事情也变成了不可能。狭小的城市空间,造就了主客之间的苦乐忧愁。小说建立起来的陌生化形象触动了读者那麻木的心灵。客人做客的遭遇,农村人所带来的习惯,以及在陌生环境下的窘迫,无疑是每一个走进陌生环境或在城市中不断穿行的流浪者内心的体验,辛酸却无奈。这种暗合“历史理性”艺术创作,建立了文学自己独特的艺术世界。尽管这个世界与现实社会有很多不谋而合之处,但决不能等同于现实世界。这是小说自己独特的艺术世界。是审美的超验的世界。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王祥夫《客人》虽然篇幅短小,但却是意蕴丰富,将传统对社会历史现实和人生哲理的反思追问的主题放入平淡的叙述风格中,不仅让读者在熟悉的日常场景中品味表面平淡实质去层次内容丰富的生活味道,通过普通的的小故事写出了不平凡的意蕴,将社会主要问题巧妙边缘化的表现,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虽然作者在结尾的最后没有给出一个明朗的答案,但这个具有开放性的结局却让我们思考的更多。同一个时代下,社会历史的发展,带来了不同的文明的碰撞,反映了中国现阶段普遍社会历史现实。这种现实,在作者的引导下,通过小说传达给读者更深更丰富的意蕴,也让读者在这个独特的艺术空间进行无限的审美享受。
[1]童庆炳.文学理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陶东风,等.文学理论基本问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美]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4.
[4]童庆炳.文学理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