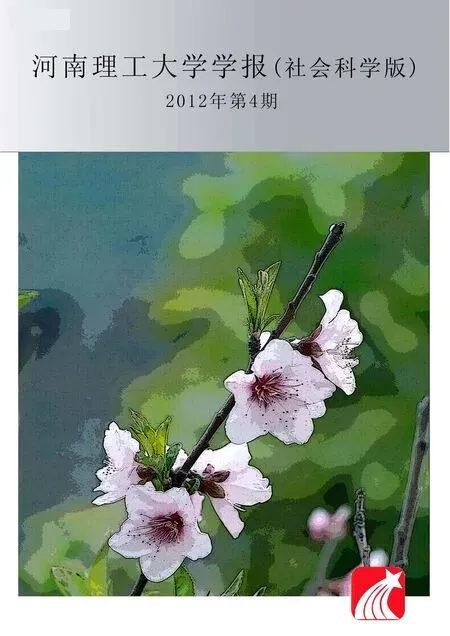明代诗赋外交的先声
——建文时期中朝交往中的文学诉求
2012-04-07马铁浩
马铁浩
(河南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河南 焦作 454000)
明代诗赋外交的先声
——建文时期中朝交往中的文学诉求
马铁浩
(河南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河南 焦作 454000)
明建文时期的右文政策使中朝两国从洪武末年紧张的外交关系中解脱出来,朝鲜遣使明朝达十八次,留下了李詹《观光录》等诗歌纪行;明朝所遣使臣也打破了洪武朝遗使以宦官为主的格局,代之以文臣和监生。建文帝在燕王靖难之师的压力下,被迫怀柔朝鲜,册封李芳远为朝鲜国王,并市马朝鲜,以备戎事。建文帝所遣使臣多长于诗文书画,他们在朝鲜或诗酒风流,或求诗于朝鲜君臣,在明代前期的中朝文学交流史上特立独行,成为正统之后大规模诗赋外交的先声。
建文时期;中朝交往;文学诉求
明建文帝时期的历史,随着永乐皇帝即位,逐渐湮灭沉寂。革除年号,焚毁史籍,《明实录》最终留下一段彻底的空白。明朝外交最为频繁的国家无异是其藩邦朝鲜。对于建文时期的中朝交往,明代文献只能付之阙如;幸运的是,《李朝实录》及《韩国文集丛刊》中当时李朝文人的诗文,为我们洞悉建文时期的双方关系保存了一些珍贵的记载。建文时期与朝鲜往来中最为重要的事件是战马贸易。建文帝与燕王朱棣的交锋需要大量战马支持,在礼部主事陆颙的建议下,建文帝遣太仆寺少卿祝孟献等市马朝鲜。这一事件不只是政治、军事上的外交活动,从使臣身份与使臣在朝鲜求诗、献画来看,其文化意义亦不容小觑。建文帝重文抑武,所遣使臣打破了洪武时期以宦官为主的格局,与永乐时期仍以宦官出使亦不相同,在明代前期的中朝文学交流史上,发出了一段独特的声音。
一、建文时期朝鲜使明及其诗歌纪行
纵观建文时期短短四年,朝鲜遣使明朝达十八次(包括中途而返者)。洪武末年李成桂废高丽王氏自立,与辽东屡生嫌隙,并在朝贡笺表中有侮慢之辞,中朝关系一度陷入紧张。建文即位后朝鲜首次遣使明朝,便是因启本言辞不逊之事,奉明太祖之命,管押孔俯等赴京的。随着明太祖去世,皇太孙朱允炆即位为建文帝,二国紧张的关系逐渐冰消雪融。从太祖李成桂到定宗李芳果再到太宗李芳远,朝鲜国王在这四年内频繁更迭,政权动荡不安,特别需要明朝皇帝的认同。建文帝册封李芳远,扭转了明太祖末年与朝鲜的紧张关系,开启了中朝交往的新篇章,虽逢明朝内乱,但朝鲜出使明朝的足迹一直没有中断过。
永乐称帝使建文四年的史实在实录中难觅踪影,《永乐实录》前九卷为奉天靖难事迹,不载与邻国交往。谈迁《国榷》建文时期有关朝鲜的史料亦仅有二则:其一,建文元年十二月,“朝鲜国王李旦请老,以子芳远嗣位,旦寻卒”[1]813;其二,建文三年六月壬午(二十五日),“太仆寺少卿祝孟献市马朝鲜”[1]825。《李朝实录》载中朝交往颇详,可据以将建文时期朝鲜使明情况简要叙述如下:(1)因朝鲜启本中有侮慢之语,撰者曹庶招供孔俯、尹须、尹珪三人,明太祖令管押三人赴京。建文即位年(李成桂七年)六月三日,管押使前判典客寺事郑连押解三人至辽东,闻明太祖崩,太孙即位,十月三日返回汉城。(2)李成桂逊位于李芳果,建文即位年九月五日,判三司事偰长寿、礼曹典书金乙祥以奏闻使使明,至辽东甜水站,会明太祖崩,中途而返。(3)建文即位年十一月三十日,判三司事偰长寿以计禀使使明,至辽东婆娑铺,辽东都司以非三年一聘之期不纳,中途而返。(4)建文元年(李芳果元年)一月九日至六月二十七日,右政丞金士衡以贺登极使、政堂河崙以陈慰使(行吊祭礼)、判三司事偰长寿以进香使同赴京师,赍回礼部咨文中许可李成桂逊位于李芳果。(5)建文二年(李芳果二年)六月二十日至建文三年(李芳远元年)三月六日,崔润和艺文春秋馆太学士李至以圣节使使明,建文帝遣陆颙、林士英等赴朝鲜答赐之,这是明初中朝关系缓和的开端。(6)建文二年九月十九日至建文三年三月六日,判三司事禹仁烈、签书三军府事李文和以贺正使如京师,献马三十匹,兼请印诰①。*①据《李朝实录》,建文二年十一月十三日,李芳远即位,遣李文和入京师献贡马,然李文和似未成行。(7)李芳果逊位于李芳远,建文二年十一月十三日至建文三年闰三月十五日,签书三军府事李詹、门下评理朴子安以奏闻使使明。(8)李芳远即位谢恩,并请诰命印信,建文三年二月三十日至六月十二日,三司右使李稷、右军总制尹坤、校书少监安允时、通事判殿中寺事李玄以谢恩使使明,曾与出使朝鲜之陆颙、林士英在途中相遇,归朝鲜时又与钦差章谨、端木礼同行。(9)因建文帝允可李芳远即位,建文三年闰三月二十六日,判三司事禹仁烈以谢恩使使明。(10)因明使章谨、端木礼赍赐李芳远诰命印章,建文三年六月十九日至十二月九日,门下右政丞李舒②、*②六月十九日遣使赵浚、安瑗,赵浚至金郊驿疾作,二十五日遣李舒代赵浚以行。右军同知总制安瑗以谢恩使使明,且请《皇明礼制》。建文帝未许《皇明礼制》之请,赐以《大学衍义》、《通鉴集览》、《事林广记》各一部。(11)建文三年八月十二日至建文四年(李芳远二年)一月六日,参赞议政府事赵温、司尹孔俯以圣节使使明③。*③据《李朝实录》,建文三年八月戊辰(十二日),初,孔俯点进献马,许人以驽马易良马,以至建文帝与燕王战败,李芳远欲脱孔俯罪,充书状官而遣之。(12)建文三年九月十三日至建文四年二月二日,直艺文馆李担、郦城君闵无疾以谢恩使使明,归言明使潘文奎来赐冕服。(13)建文三年九月二十八日至建文四年三月六日,参赞议政府事崔有庆以贺正使(一作贺圣节使)使明,归言燕兵势强,帝兵多败,中国骚然。(14)因明使祝孟献赴朝鲜市马一万匹备战,建文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总制朴经赴京师奏易换马数。祝孟献返辽东,朴经与之偕行,路逢明使端木智,不待命而返,宪司劾问,建文四年五月四日流之于通津。(15)因朴经未至京师,建文四年三月三日,又遣吏曹典书吕称使明,仍奏朝鲜地狭马少,难于易换。(16)建文四年三月七日至四月十日,参判承枢府事卢嵩以谢恩使赴京谢赐冕服,与明运马监生柳荣偕行,三月二十六日,至开州遇贼而返。(17)建文四年五月二十日至八月一日,承枢府提学朴惇之以谢恩使代卢嵩使明谢赐冕服,因辽东路梗,不得朝京,传写建文帝诏书而归。(18)建文四年八月二日,中军总制柳龙生以圣节使使明,是年六月建文帝已败亡,而朝鲜犹未知也。
由于中朝关系在建文时期刚刚缓和,文化交流没有真正展开,在这十八次出使之中,朝鲜使臣留下诗文纪行者很少。《燕行录全集》所载朝鲜出使纪行,洪武时期的郑梦周《赴南诗》、权近《点马行录》和《奉使录》之后,便是成化十七年成伣的《辛丑朝天诗》,建文时期明史文稿中似乎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实际上,从朝鲜文集中,还可以看到一些建文时期朝鲜使臣使明的诗歌创作。朝鲜使臣与明使偶有唱和,如李稷谢恩使毕,返朝鲜时与明使章谨、端木礼同行,在南京、安定聚星楼、蓬莱阁、沙门岛等处,都留下了赓韵之作,收入其《亨斋先生诗集》,如《次章寺丞题安定聚星楼诗韵》:“使星临海国,万里耀光华。相对凭风阁,如乘贯月槎。诗清神有助,兴逸意无涯。莫谓三韩迥,乾坤属汉家。”[2]出使明朝留下诗歌最多的要数李詹,其《双梅堂先生箧藏文集》卷二为《观光录》,收入其前后二次使明的纪行诗歌,前者即建文二年冬李芳远即位时李詹奉使奏闻明朝之沿途所作,达九十余首。建文二年十二月,燕王朱棣在东昌(今山东聊城)为盛庸、铁铉所败,次年三月在夹河(今河北武邑)之战中打败官军,重新确立了燕兵的优势。当时,燕地沦为战场,李詹出使明朝,自鸭绿江入辽东,经过东八站,从旅顺口入渤海湾,自登州上岸后,经黄县、朱桥驿、岱山、照县、分水岭、东海驿、清淮驿、界首站、高邮、邵伯驿、扬州、扬子江、龙潭、龙江驿等,最终抵达南京;归途亦然,自登州入海至辽东再返朝鲜。李詹虽未亲历战场,但对山东一带因战争和灾荒带来的民生凋敝,却有着深刻的体察,如其归朝鲜时在山东作《山东往还记所历艰危》云:“造物如儿戏,乘间或困人。识时须揭厉,知名且逡巡。冰合沙门岛,波腾扬子津。往来从一路,不忍见齐民。”[3]归至辽东时又做《行路难》云:“若有客兮乘仙槎,横渡银河朝帝宫。天阍咫尺足官府,俯视下界如螘封。春深朔野草不长,戎马蓟门尘冥濛。山东之民因蝗旱,老弱转乎丘壑中。浡海风涛耸银岭,征夫仰叹路未通。”[3]山东蝗旱,蓟门戎马,皇室相残,神州大地满目疮痍。可惜的是,这些感伤时事的现实主义诗篇在《观光录》中只有寥寥几首,大多数仍是即景抒怀之作,何以如此?对于建文帝的文治,李詹其实是诚心颂赞的,《五十寨途中》诗云“太平天子建文初,万国梯航赴广居。地接朝鲜山作轴,野分燕塞海涵虚”[3];但对于朝鲜使臣而言,明朝的政治变故并不足以令其对建文帝寄予深切的悲悯,《晨兴偶吟》云“诸将战功燕塞上,故园归计鸭江边。任他冀北无良马,且喜东方自晏然”[3],这里体现出的对建文帝削藩导致战乱的观望心态,才是朝鲜君臣最为真实的表达。半年后明使祝孟献赴朝鲜市马,朝鲜君臣延宕犹疑,正可以从这诗句中找到解释。
二、建文朝右文抑武与明使出使朝鲜
建文帝自幼好诗书及典礼文章,即位后一改朱元璋重武轻文之策,锐意于文治,归重左班,提升其品级,优容文士,改侍读、侍讲学士为文学博士,增设文翰、文史二馆。建文帝最为倚重方孝孺,国家大事辄咨之,日与其讨论《周官》法度,宽刑狱,并州县,减赋税,行井田,推行所谓的“建文新政”。这改变了太祖时期严苛恐怖的政治空气,一时焕发出新气象,但又不免迂执难通,重文轻武又使其仁弱轻敌,削藩问题以悲剧而告终。明代朱鹭曾感慨洪武、建文二朝文武离合之异,曰:“及建文帝注思讲学,恬武兢文,缙绅亲而介胄疏,于是翰苑有锡谥,尚书登一品,四稔之间,气若移焉。而文臣莫不踊跃致身,趋死如归。”[1]815建文朝在出使朝鲜使臣的派遣上,亦以文官和监生充当,绝无武官和宦官,这与洪武及永乐时期主要以宦官为使极不相同。据李新峰研究,洪武时期遣使朝鲜二十二次,留名者四十三人,其中宦官二十五人、文臣十一人、武官七人;永乐时期遣使朝鲜三十八次,留名者五十一人,其中宦官三十七人、文臣八人、武官六人[4]。以宦官为主而杂用文武官员出使,是明代前期遣使朝鲜的主要特征,但建文时期却迥异于这一风气。洪武时期只有在建交、封山川、赐谥等重大礼仪场合才以文臣出使,一般的诏敕谕旨多以宦官颁行。建文帝尊崇文教,专以文臣和国子监生出使朝鲜,甚至特别重视使臣的诗文书画才能,使臣在朝鲜诗酒风流、清不近货,改变了朝鲜君臣对宦官使节道路驿骚、求索无度的不良印象。建文帝对文臣的重视在文化意义上固然值得肯定,但他对武官和宦官的压制则不免带来政治上的恶果。武官临阵生心、叛附接踵,甘为虏缚者不一而足,宦官更是充当了燕王朱棣攻城克邑的内应,这可以解释朱棣即位后何以重用宦官而以其为使臣,以文臣为使的短暂历程随着“建文新政”的终结而归于沉寂了。
建文帝为何改变洪武法度而以文臣遣使朝鲜?一方面固然是其右文政策的体现,藉文臣的诗文书画才能炫示藩邦,赢得其亲近向化之心;另一方面则是当时政治形势逼迫其作出的外交选择,通过文臣出使贯彻其怀柔政策,拉拢朝鲜,购买战马,安定辽东,以便牵制朱棣在东北方向的军事掠夺,杜绝其对朝鲜的利诱。欲深知其中缘故,不妨先据《李朝实录》将建文时期明朝遣使朝鲜依次列举如下:
(1)明太祖崩,建文帝即位,遣使陈纲、陈礼(未言二人官职)出使朝鲜,二人过鸭绿江信宿而返,建文即位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讣音至朝鲜。(2)因李芳果遣崔润、李至赴京贺圣节,建文帝遣礼部主事陆颙、鸿胪寺行人林士英使朝鲜答赐之,建文三年二月六日至汉城,其时李芳远已于建文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夺权即位,二月三十日离开汉城。(3)对李芳远短暂的猜疑之后,建文帝随即遣通政司丞章谨、文渊阁待诏端木礼出使朝鲜,赍诰命印章册封李芳远为朝鲜国王,建文三年六月十二日至,六月十六日离开。(4)因陆颙之奏,建文帝遣太仆寺少卿祝孟献、礼部主事陆颙赴朝鲜市马一万匹,以备戎事。同行者另有国子监生十人,即宋镐、相安、王威(一作咸)、刘敬、栗坚、董暹、柳荣、郭瑄、张缉、周(一作朱)规;兽医二人,即王名(一作明)、周骥(一作继)。祝、陆及兽医二人于建文三年九月一日先至汉城,监生宋镐、相安、王威、刘敬赍运马价随后而至,其余监生似于辽东待命;十二月十六日祝、陆离开汉城,返辽东,兽医二人似亦从行。(5)因陆颙得心疾,朝廷遣兵部主事端木智代其市马。建文四年一月二十四日,端木智及监生栗坚、兽医周骥至汉城,五月二十日方与第三次赴汉城之祝孟献同返京师。(6)建文四年二月十九日,祝孟献与监生董暹、柳荣及兽医王名自辽东再至汉城市马,三月二十日祝返辽东。四日后日兵部咨文至,云“易换马七千匹,今已易来,朝鲜不能充一万匹,则不可强易,使臣可回来”[5]。(7)建文四年二月二十六日,鸿胪寺行人潘文奎至汉城,赐李芳远冕服,三月四日还京师。(8)因路梗未至辽东,建文四年四月十日,祝孟献三至汉城市马,五月二十日与端木智同还京师。
从以上简要的陈述中可以看到,自建文帝即位诏告朝鲜之后,建文元年、二年,明朝似乎忽视了朝鲜的存在,建文三年初却突然以朝鲜贺圣节为契机赏赐朝鲜,此乃何故?陆颙、林士英至朝鲜前,圣节使崔润、书状官李至还启“皇帝待慰甚厚,且谓戊辰年振旅之功莫大,使礼部主事陆颙、鸿胪行人林士英等赍捧诏书赏赐”[5](建文三年一月辛巳),戊辰为洪武二十一年,当时李成桂不从高丽国王辛禑寇辽东之命,自威化岛回师。建文帝在即位两年后方盛款朝鲜使节,奖谕其十三年前未侵犯中国。王崇武指出,这是建文帝被迫对朝鲜施以怀柔政策的表现,并援引陆颙等所赍诏书,论曰:“建文三年以前,帝之所以未及怀绥朝鲜者,盖因燕之势力尚未强大,此时则成祖率兵深入,辽东孤悬,朝鲜可举足重轻,诏文以‘毋惑于邪,毋怵于伪’相劝勉,明系惧为成祖所利诱。至‘益坚忠顺,以永令名’,则又希其积极之援助。”[6]410此后很快便册封李芳远为朝鲜国王,赢得朝鲜感恩戴德,都是出于怀柔之需。因此,随即遣祝孟献和监生等市马朝鲜,便是顺理成章的了。建文帝败亡前夕,令潘文奎使朝鲜赐冕服,敕书中云“朕之于王,显宠表饰,无异吾骨肉,所以示亲爱也。王其笃慎忠孝,保乃宠命,世为东藩,以补华夏”[5](建文四年二月己卯),这种痛切的骨肉之情,更可见建文帝对待朝鲜的心态。朝鲜学习汉文化,以文臣出使,自然是怀柔政策的最佳选择。这些文臣大都儒雅风流,虽偶纵情妓酒,却无征索陋习,不求金银唯求诗,大规模的中朝文学交流自此开始埋下了种子。
三、明代文臣与历事监生的文学诉求
建文时期出使朝鲜的明代文臣多有书画之才,如陆颙善画(见《明画录》),端木智善书(见《续书史会要》)。明朝使臣的书画风流,朝鲜文集和《李朝实录》中时可见之,如权近有《题伯瞻钓叟图》、《谢伯瞻梧竹图》,李詹有《题陆天使隔水相别图》,皆为陆颙画而作;李稷有《次朝廷使臣祝少卿所画宋君家屏芦雁图诗韵》,李詹有《古诗一篇投天使祝少卿请画》,皆为祝孟献画而作;《李朝实录》记端木智自诩其书为“天下第一笔”、“书法与王羲之无异也”[5](建文四年二月乙卯)。当然,最能体现文化认同的应是文学上的交流。建文时期是中朝文学交流的萌芽阶段,真正的诗歌交流还没有充分展开,除了陆颙等人与朝鲜文臣诗歌唱和之外,大多数明使只是求诗卷于朝鲜,藉此以见中华文化覃泽之远,准确地说,是希望在文字声韵的背后,寻求政治上的联盟和知音。因此,“文学诉求”一词更能准确传达建文时期文学交流的实际情形。譬如,章谨临别时,言“吾叔父章同闻,在建康路采石县,结庵居之,号曰澄心,敢请诸儒臣作澄心庵诗若文以给”,“上命领三司河崙、参赞权近、签书李詹及诸文臣,作诗并序以赠”[5](建文三年六月壬申①);*①六月丙子(十九日)又载:“章谨请牧隐李穑文集,(赵)浚以无全本答之。”监生刘敬押二运马一千匹还辽东时,“敬求诗卷于议政府,政府以闻,艺文馆应奉司,令时散文臣,作诗四韵或长篇,成轴以赠”[5](建文三年十月辛未);监生宋镐押三运马一千匹还辽东时,“祝孟献作诗饯赠镐,因曰:‘东方,文献之邦,请赓韵以饯镐。’上闻而许之,集文臣作诗,成轴以赠”[5](建文三年十月庚辰);监生相安押四运马一千匹还辽东时,“安不受上所赠马,求赆行诗,河崙、权近等,集文士所作诗四韵或长篇,成轴以赠”[5](建文三年十一月乙未);监生柳荣还辽东,祝孟献作诗饯别,李芳远“命参赞议政府事权近,赓孟献诗韵”,“领司平河崙及权近,集诸文臣诗,成轴以赠孟献”[5](建文三年十二月丙寅);潘文奎还京时,“上饯于迎宾馆,文奎儒雅风流,清不近货,唯求诗卷”[5](建文四年三月丁亥);监生董暹押六运马一千匹还辽东时,“端木智作诗赠行,领司平府事河崙会文士赓韵,成轴以赠”[5](建文四年三月丙午);监生栗坚、张缉等押七运马一千匹还辽东时,“坚等求诗,集诸文人诗,成轴以赠”[5](建文四年四月己卯);祝孟献、端木智等还京时,“孟献、智、监生、周继等请饯诗,且求权近序文,河崙、权近、李詹,集文士诗,近作序,成轴以赠”[5](建文四年五月己亥)。这些动辄“成轴以赠”的诗歌,大多已零落不全,现在从朝鲜文集中看到的似乎只是当时次韵或饯别诗的一小部分。朝鲜能诗者主要有权近、李詹、李稷,特别是权近,作为洪武年间代表高丽出使明朝的老臣,享有明太祖赐以御制诗的荣宠,在当时朝鲜文臣中,无论诗文还是性理之学,都代表着最高水平,故而其集中赠建文使臣的诗文最多亦最好,且时有为人捉刀之作。
明朝文臣之中,陆颙最富文采风流,然亦不脱才子任情洒脱之习。建文时期陆颙前后两次出使朝鲜,第一次刚到朝鲜五六日即进诗献画,逞其才俊,其进诗三篇得到了李芳远的次韵,题画诗亦得到了权近的唱和。如:“陆颙画《江枫钓叟图》,因书一绝云:‘江风木落影萧疏,山带秋容入画图。有客钓鱼人不识,汉家何处觅狂奴。’”[5]权近作《题伯瞻钓叟图》,又作《昨见钓叟图作太公赋之及观佳作乃赋子陵也故又次韵以太公压子陵》:“真钓求鱼计不疏,时来牧野展雄图。客星谩向桐江隐,加腹依然是仆奴。”[7]此外,权近《阳村先生文集》次陆颙诗还有《次天使淮南陆伯瞻颙春宴曲》等十余首;李詹《双梅堂先生箧藏文集》、李稷《亨斋先生诗集》、赵浚《松堂先生文集》亦偶有次韵。陆颙初到朝鲜黄州,爱妓委生,至汉城不忘,礼曹以乘驿召之,陆颙还至平壤时有二绝句,中云“离人一去来何日,不及春江有信潮”[5](建文三年二月己未),似即为妓委生而作。半年后,陆颙第二次出使,随太仆寺少卿祝孟献市马朝鲜,《李朝实录》载:“初,颙奉使到国,密与妓委生为奉使复来之约。及还……因奏:‘朝鲜,产马之邦也。若以绮绢市良马,可备戎事。’帝大悦”[5](建文三年八月己卯)。为了与爱妓的私密誓言,上奏建文帝可赴朝鲜市马以伐燕,近乎儿戏的风流故事,请求朝鲜给予军事援助这一庄严事件,看似出于玩笑和偶然。因陆颙于帝前妄言朝鲜无女乐,章谨诘之,待陆颙再至朝鲜,唯溺于和爱妓委生的儿女之情,时而欲自缢,时而病狂夜遁,甚至欲隐匿于朝鲜而不归明朝,成为朝鲜君臣的谈资和笑柄,以致明朝不得不以其心疾为由遣端木智代之。风流才子陆颙的出使,为建文时期的文臣外交奠定了一个基调,诗画风流成为其中的重要部分。至于林士英、章谨、端木礼、祝孟献、端木智、潘文奎等明代文臣,权近、李詹、李稷、赵浚、卞季良等文集中皆有次韵赠别之作,兹不赘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随从祝孟献出使的十位国子监生,他们在押运马匹返辽东之际,大多亦向朝鲜请求赆行诗卷,权近《阳村先生文集》卷九有《送相监生使还》、《次端木天使诗韵,送董监生使还》、《送周监生使还》,卷十八有《送董监生使还诗序》、《送栗监生诗序》,卷十九有《送张监生诗序》、《送周监生序》等。明代前期有监生历事制度,由于国子监积分法造成监生的长久淹滞,明太祖时允许国子监生在各部门实习,建文帝沿袭此制度,建文二年“定监生历事各衙门者一年为满,从本衙门考核,分上中下三等引奏”[8]。当时赴朝鲜运马者或即属于太仆寺或其他衙门下的历事监生。国家危难之际,采办军备成为这些儒生的重要使命。他们在国子监中所学以儒家经典及诏、告、表、策、律令、书数等实际技能为主,诗文非其所长,但在朝鲜,对诗文的倾慕和求索也为其军事贸易活动赋予了温文尔雅的色彩。
总体而言,建文时期的中朝文学交流并非双向展开。随着中朝关系的正常化,朝鲜使臣赴明越来越频繁,但留下纪行诗文者极少,只有李詹《观光录》可谓代表,彼此间的唱酬更是难得。而明使大量出使朝鲜则在建文三年和四年,中心事件是购买战马以备伐燕。明朝文臣及历事监生在履行公务之余,总不忘求诗于朝鲜,其文学诉求似乎压过了市马的急切之心。从《李朝实录》来看,无论是朝鲜君臣还是明代使节,对于建文帝及中国的艰难处境,似乎多持观望态度;但从文化层面而言,当时的文学交流虽然主要表现为单向的求诗,但确实可以视作正统之后诗赋外交的先声。只是建文朝历史的湮没,让人们遗忘了明代前期还有这么一段文采绚烂的历史。
[1] 谈迁.国榷[M].北京:中华书局,1958.
[2] 李稷.亨斋先生诗集[M]//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文集丛刊.首尔:景仁文化社,1990.
[3] 李詹.双梅堂先生箧藏文集[M]//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文集丛刊.首尔:景仁文化社,1990.
[4] 李新峰.明前期赴朝鲜使臣丛考[A]//朱诚如,王天有.明清论丛:第4辑[C].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
[5] 末松保和.李朝实录[M].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7—1966.
[6] 王崇武.读明史朝鲜传[A]//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历史编·明清卷[C].北京:中华书局,2009.
[7] 权近.阳村先生文集[M]//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文集丛刊.首尔:景仁文化社,1990.
[8] 黄佐.南雍志[M].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65.
[责任编辑 位雪燕]
TheDiplomacyReflectedinPoemandFuofMingDynastyThe Literature Appeal in Sino-Korean Relation During Jianwen Period of Ming Dynasty
MATie-hao
(SchoolofLiteratureandLaw,HenanPolytechnicUniversity,Jiaozuo454000,Henan,China)
The policy of worshiping the culture during Jianwen period improv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ng Dynasty and Li Dynasty of Korea. The Korean envoys came to China for 18 times, and Li Zhan wrotetheGuanguanglu. The Chinese envoys were the civil officials and the Imperial College Students, not the eunuch. Because of Zhudi’s pressure, Emperor Jianwen conciliated forcedly with Li Dynasty, conferred a title upon its king, and purchased the horses for the war. Chinese envoys skilled in literature and arts, they communicated with the Korean emperors and ministers by means of the poems. So Poem and Fu became a unique way to reflect Sino-Korean diplomatic relations after Zhengtong period.
Jianwen period;Sino-Korean diplomatic relations;the literature appeal
2012-04-1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CZW043)。
马铁浩(1979—),男,河南汝阳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
E-mail:matiehao2011@126.com
I206
A
1673-9779(2012)04-044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