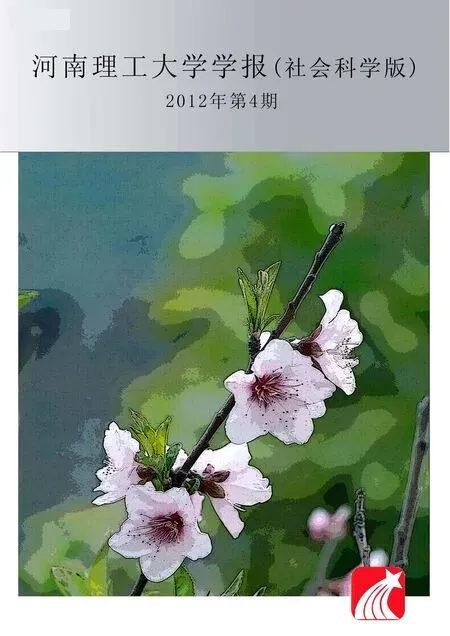论程婴之妻角色变迁的意义
2012-04-07宋根成
宋根成
(河南大学外语学院,河南开封475000)
中国古典悲剧《赵氏孤儿》是第一个从中国传到西方的戏剧文本。赵氏孤儿的故事最早见于《东周列国志》,后收入《左传》,西汉司马迁在《史记·赵世家》全面地讲述了赵氏孤儿的故事。南戏收有《赵氏孤儿冤报冤》,元杂剧有《赵氏孤儿》,而明传奇有《八义记》。《赵氏孤儿》有两个传本,一是《元刊杂剧三十种》,一是《元曲选》。这两个版本有出入,后者较流行,且比前者多了一个第五折[1]。
清朝康熙年间,法国传教士马若瑟将元杂剧家纪君祥的《赵氏孤儿》翻译为法语 (Tchao-chicou-eulh,ou L’orphelin de la maison de Tchao,tragédie chinoise),因为剧中倡导的儒家自我牺牲精神的核心价值为西方上流社会所称赞,所以很快被翻译成其他欧洲文字,被改编成歌剧或者话剧进入西方的剧院上演。出于对中国儒家文明的热爱和对卢梭所持的“文明否定说”的坚决驳斥,法国文豪伏尔泰以马若瑟的法文本为素材,于1753~1755年将《赵氏孤儿》改编成为新历史剧,名为《中国孤儿》(L’orphelin de la Chine),并于1755年8月20日开始在巴黎上演,引起了空前轰动。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其《宋元戏曲史》中,评论《赵氏孤儿》时亦称“即列于世界大悲剧之中,亦无愧色也”。
与西方古典悲剧表现英雄的主题不同,中国戏曲悲剧从其形成之初,就有表现弱小善良的小人物形象的传统,强调悲剧人物的正义性和无辜性,突出人情味。女性往往成为悲剧主人公的首选,这样的悲剧有《窦娥冤》、《潇湘雨》、《白兔记》、《琵琶记》、《桃花扇》、《雷峰塔》、《梁祝》、《杜十娘》和《赛琵琶》等。因此,中国悲剧是以女性为主导的——以女子为主人公。这种特性与西方悲剧恰恰相反。但是,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无疑是个例外。在西方悲剧中,为了表现悲剧人物的崇高精神 (包括恐惧与怜悯)和坚毅品格,主人公几乎全是男性,这样的戏剧有《俄狄浦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阿伽门农》、 《哈姆雷特》、《李尔王》和《奥赛罗》等。作为中国第一个走向世界的古典悲剧,《赵氏孤儿》在剧情上更加贴近西方的悲剧模式,除了没有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其他西方古典悲剧的要素在《赵氏孤儿》剧本中皆可以找到。
一、元明版本与程婴之妻角色设置
无论《赵氏孤儿》杂剧或《八义记》戏文,男主角都不是程婴。杂剧一本五折,为末本,主唱的角色第一折是韩厥,第二、三折是公孙杵臼,第四、五折则为孤儿赵武。 《八义记》程婴则由末扮,戏份虽不少,却始终居于配角地位,相当于京剧中的硬里子老生。从明代的《八义记》再到清代的皮黄戏,人物角色的重点开始向程婴角色倾斜,但始终缺失了程婴妻子的设置,这不能说是剧情设置考虑上的一大软肋。虽然国内戏剧研究界关于《赵氏孤儿》研究的论文数量繁杂,但是鲜有讨论程婴之妻角色意义的。没有程婴之妻,程婴哪里来的婴儿?亲生骨肉被舍弃掉,生身母亲怎么没有表达任何抗议的话语?母亲的失声既不合乎情理,也不符合逻辑。作为中国元代杂剧的代表,《赵氏孤儿》有其特殊的创作背景和历史投射。纪君祥作为一个政治上失意的文人,只能混迹于青楼茶馆,靠创作杂剧来抒发心中的愤懑及幻想。因为宋朝初灭,他仍思念正统,这个剧本《赵氏孤儿》的标题其实就隐含了对跳海而死的宋朝赵姓小皇帝的怀念。
自然而然,纪君祥对剧中全部角色的安排秉承了宋朝程朱理学的教义。宋朝时候的儒家重视义理,程朱理学在演绎古典经学的基础上,融入了儒家、佛学与道家的思想,重构了儒家的思想体系,最终程朱理学被统治阶级所采纳,成了官方哲学。这个学派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所谓“天理”构成人的本质,在人间体现为伦理道德“三纲五常”。“人欲”是超出维持人之生命的欲求和违背礼仪规范的行为,与天理相对立。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要求视为人欲,是封建纲常与宗教的禁欲主义的接轨。纪君祥很好地贯彻了程朱理学的精神。剧中所宣扬的“忠孝节义”即为天理,而为了赵家孤儿的牺牲行为 (一大批人因为保护一个幼儿而自杀或者被屠岸贾屠杀)就是顺应天理,是“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大义行为。女子们在男权和父权社会里,必须恪守“三从四德”,这造成女性话语语境的历史性缺失,纪君祥自然不会设计出程婴的妻子出面阻挠“换婴”“救孤”这种灭天理、存人欲的戏份了。
二、伏尔泰再创作与依达姆的角色演绎
在马若瑟版本的基础上,伏尔泰完成了历史悲剧《中国孤儿》,他特意加上了一个含蕴深刻的副标题—— “五幕孔子伦理学”。伏尔泰按照古典主义的三一律原则,把该剧时间跨度由20多年缩短为一昼夜,删除了原作中的弄权、作难、搜孤、锄奸、报仇等情节,加上一些爱情穿插,改编成了一部富有启蒙主义色彩的古典主义悲剧。故事的背景从春秋移到了元朝初期,元朝的皇帝是“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是一个嗜血征服者;他灭亡了南宋,回到北京时,惊讶地发现自己以前钟情的女人依达姆嫁给了南宋的大臣盛悌,正是这个盛悌冒死从蒙古人手里救出了大宋王朝的最小王子,为大宋保住了一根独苗。成吉思汗嫉恨不已,一方面逮捕盛梯,严刑拷打,追问赵太子的下落;一方面胁迫依达姆做出选择:要么与丈夫离婚嫁给他,要么和丈夫以及那个孤儿一起去死。盛悌打算拿自己的儿子顶替赵家太子 (当时被藏匿起来,并准备送往朝鲜),可是妻子依达姆,《中国孤儿》的女主人公,却出人意料 (中国人的视角来看)地强烈反对,哭泣说皇帝的儿子是儿子,自己的儿子就不是儿子了么?丈夫盛悌,为了拯救前朝太子违心地劝说妻子做出牺牲,答应成吉思汗。然而依达姆断然拒绝丈夫牺牲自己 (这和莫泊桑的《羊脂球》是何其的不同)。她面对操着生杀大权的成吉思汗慷慨陈词:当初自己拒绝成吉思汗情非得已,实在是父命难违,如今自己成了盛悌的妻子,自当誓死保守节操。无路可走、坚贞不屈的夫妻二人决定带着自己的儿子一起自杀,正在这关头,偷听到他们谈话的成吉思汗幡然悔悟,闯了进来,向他们道歉,决定不再杀戮汉人,而要遵从汉人的法律和礼仪道德。更令人感动的是,盛悌还被任命为元朝的宰相。一个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悲壮复仇故事就这样在皆大欢喜的氛围中,以一种帝王基督徒忏悔与博弈的方式瞬间结束了。
许多18世纪新古典主义理论家崇尚古希腊悲剧,认为男女之情不应当作为悲剧的主题,他们常常批评法国悲剧中爱情占的地位过分重要,违背了希腊悲剧的精神[2]。第一个翻译《赵氏孤儿》的马若瑟在宗教上属于耶稣会的索隐派。耶稣会更进一步主张在悲剧中彻底排除爱情,甚至尽量不要有女性角色,除了母亲、妻子或殉道的处女外。而《赵氏孤儿》中没有男女之情,唯一的女性角色是晋室公主,孤儿的母亲,而且她在第一折中就自缢身亡了。王季思先生曾在《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中点评《赵氏孤儿》说,“公主没有死的必要,后来有些改编都让她活下来,最后孤儿母子团聚。”[3]另一个女性角色,程婴妻子——婴儿的母亲则始终没有出场,一切的定计和决断都由程婴一人完成。元剧中恐怕没有其他戏比《赵氏孤儿》更符合这一系列的条件了。这就是为什么马若瑟舍弃了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等剧作家的杂剧,而独独选择了纪君祥的《赵氏孤儿》翻译介绍到法国。
伏尔泰曾在18世纪30年代创作了历史悲剧《凯撒之死》,以罗马悲剧的方式书写了共和制与君主制之间的斗争,并没有涉及女性角色或爱情主题。这部戏剧并没有让伏尔泰感到满意[4]。随后,在女性悲剧《梅洛普》中,他尝试性描写了一位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的母亲的复杂痛苦心理。20年后,他在改编《赵氏孤儿》的时候,实现了启蒙主义理想和中国儒家价值观的兼收并蓄,将爱情与母爱有机地穿插于故事情节中,极大赋予了戏剧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冲突气氛。其中伏尔泰创作性地创设了盛悌妻子——依达姆的角色,她哀怨哭诉,坚决反对自己的丈夫牺牲自己的骨肉去拯救赵家的后人,体现了一位母亲的善良天性;同时她不贪图荣华富贵,不畏皇权淫威,誓死捍卫节操,忠于现有的婚姻爱情,演绎了一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中国贤淑女性的光辉形象。如果说《窦娥冤》塑造了一个反抗封建黑暗吏治的下层善良妇女的悲剧形象,那么《中国孤儿》中的妻子“依达姆”则体现了坚强女性追求独立人格的勇气和信念。
伏尔泰对中国文明的热爱是他创作《中国孤儿》这部悲剧的外在动力,而他的哲学观和政治倾向则是内因。剧作中的每个人物都是为诠释孔子儒家伦理的伟大服务的。一旦涉及作品的核心价值,就不能不谈及伏尔泰的哲学观。伏尔泰沉醉于实现柏拉图式的开明君主制,同时倡导“自然权利说”,认为“人们本质上是平等的”,要求人人享有“自然权利”,主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又认为财产权利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这等于说伏尔泰一方面接受阶级不平等的现状与秩序,另一方面又渴望实现人人平等的理想生活。这个矛盾的信仰显然体现了他的宽容理念思想。他曾说过,“纷争不和是人类的大敌,而宽容则是唯一医治它的良药。”[5]《中国孤儿》中依达姆呼吁自己儿子的生命价值和太子的生命价值没有质的不同,则是西方的天赋人权思想的彰显。一个旧王朝的臣子和新王朝的开明君主最后冰释前嫌,一起为建设新国家携手前进,这幅景象是多么的理想化,切合了法国18世纪的社会现实危机。戏剧没有仿效中国传统的复仇模式,赵太子没有成为仇恨的工具,相反他生活在一个相互宽容的新国度里。在这里,他的父辈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因为遇到一个开明的君主,从而得到尊重、保全和传播。
伏尔泰对依达姆形象的艺术塑造真正做到了中西兼顾,既向往独立自由平等爱情的西方元素,又恪守中国的传统女性道德,刻画了一名集恋人、母亲、妻子于一身的人文主义新女性形象。在剧中第四幕第四场,依达姆对成吉思汗说,“我们的国朝是建立在父权上,伦常的忠信上,正义上,荣誉上和守信的信义上,换一句话说,孝悌忠信礼仪廉耻就是我国立国的大本。我们大宋朝虽已被推翻,可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是永不会灭亡的。”[6]在剧结尾,成吉思汗对依达姆感叹道:“大宋的法律、风俗、正义和真理都在你一个人身上完全表现出来了。你可以把这些宝贵的教训讲给我的人民听,现在打了败仗的人民来统治打胜仗的君主了。忠勇双全的人是值得人类尊敬的,我要以身作则,从今起我要改用你们的法律。”伏尔泰后来将《中国孤儿》诠释的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融入自己民主观—— “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是誓死捍卫你说这话的权利。”可以说,伏尔泰从中国儒家思想文化中找到了倡导开明君主制、反对君主专制的有力斗争武器。
据文献记载,1755年观看《中国孤儿》的法国观众都为依达姆一家的生死命运牵肠挂肚,甚至暗自希望依达姆答应成吉思汗的请求,牺牲自己,换取前朝太子和丈夫的安全无虞。可是剧情的设计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将对立的矛盾推向了极致,依达姆宁死不屈,即使面对的皇帝曾经是自己豆蔻年华时的恋人,她依然恪守自己的原则和操守。本来出现缓和的冲突瞬间又提到了生与死的抉择,不少法国观众原本放下的心又悬了起来,在哀婉悲悯之余,心中油然而生对中国女性伦理操守的敬意。而成吉思汗在最后时刻的幡然醒悟无疑更让那些熟谙政治争斗的权贵和教会高层感到羞赧,同时赢得了观众的理性赞许。有这样高尚情操的一个社会,在一个开明的君主统领下,国家的安定繁荣和物质文明只是时间的问题。当然,按照《阿伽门农》和《哈姆雷特》的人物思想与审美标准,《中国孤儿》的悲剧性无疑有所减弱,但是戏剧所弘扬的母性的崇高美未必较之古典西方悲剧逊色。
三、清代以后版本的程婴之妻角色突显
自明代以后,《赵氏孤儿》也开始了改编,但是基本没有跳出纪君祥的版本框架。自雍正三年以来,民间的皮黄戏开始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皮黄戏《搜孤救孤》也没有涉及程婴妻子。真正出现程婴妻子的角色来自清末的京剧传统折子戏《搜孤救孤》。剧本共分四场戏。剧情的变化中加入了第二场程婴与妻子商议舍子救孤,程妻不允,公孙杵臼也来苦苦相求,最后程妻勉强同意舍子,矛盾才算解决。人物重点在程婴身上,妻子戏份在整出戏中不多,只是配角。同伏尔泰的处理相比,《搜孤救孤》里程婴妻子的形象和性格无疑要逊色一些。同依达姆相比,程婴之妻延续了矛盾、理解和顺从的伦理性逻辑,缺了爱情和节烈的演绎戏份。她的角色设置和母子离别表演,是对程婴和公孙杵臼等忠臣义士英雄行为的必要烘托。而这样一个角色在清末的出现更是历史的必然,说明压迫中国妇女几千年的封建礼教已经开始崩溃,妇女解放意识开始萌发,主张男女平等的思想开始无意识地出现在戏剧表演艺术中。
到了20世纪80年代,潮剧开始复兴起来并走出国门。中国广东潮剧团在泰国演出经过改编的《赵氏孤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戏重在释情,也在剧情改编上做足了文章,成功塑造了3个为了正义而舍身的英雄人物:程婴、公孙杵臼和卜凤。全剧有重点地写了程婴献出儿子拯救全国婴儿的场景,增加了程婴妻子这一人物。再现了程妻的谆谆爱子之情,爱人 (推己及人)之心,终于在痛苦中舍子,保存了赵氏孤儿,保存了举国同庚孩子[7]。
中国的《赵氏孤儿》版本从历史性忽视程婴之妻角色到伦理性重视程婴之妻角色,再逐渐认识到该角色设置对于孤儿复仇悲剧叙事结构趋于完整性的重要意义,反映了人民观众对戏剧表演应该反映人伦理想的内在欲求。由于改编尺度的要求,妻子的形象不如丈夫程婴的形象那样悲壮,演绎不够全面,但是它预示着妇女意识的时代觉醒,是社会伦理文化逐步进步的一个表现。时至今日,这就是《赵氏孤儿》依然能够打动观众的一个重要因素:只有能够反映并且紧跟社会文化语境变化的戏剧,才能保证其艺术魅力和价值永不褪色。
四、结 语
按照结构主义批评家弗莱的理论,我们后退一步 (stand back),重新审视伏尔泰的《中国孤儿》悲剧,会觉得伏尔泰用了巨大的隐喻在这个话剧中。依达姆就是一个拟物化的人物形象。在伏尔泰的书写下,依达姆成为古代中国美德的象征,而她的丈夫盛悌,则是中国儒家道德 (传统男权思想道德)的化身;夫妇两人合在一起成为伏尔泰对古代中国精神 (阴阳和谐)的理解与再现。伏尔泰把仇恨与复仇、爱情与忠贞、背叛与牺牲、仁慈与宽容全糅合于一部戏剧,完美体现了中国儒家道德伦理的整体思想财富。如果非要诟病,也就是他以理想手法炮制的依达姆三角浪漫爱情和帝王宽容元素与历史的残酷和血腥格格不入罢了,而这也恰恰是伏尔泰“中为西用”演绎儒家伦理的成功和伟大之处。
无论伏尔泰对《中国孤儿》的再创作,还是历代中国《赵氏孤儿》版本,都是中国古代伦理价值观的一种尝试性解读和再现。伏尔泰之依达姆形象的塑造偏重于中西女性文化的糅合,而中国《赵氏孤儿》中程婴之妻角色的从无到有、地位从轻到重的演绎则是中国社会女性地位提高和女性意识觉醒的历史性同步写照。当然这里面,可以说是“成也萧何败萧何”,就是当初纪君祥设计公主自杀,程婴的妻子才被失踪和噤声以突出和成全公主杀身成仁的悲剧性。后来剧作家们改编了剧本,公主没有自杀,而是等到了和儿子相认团圆的一天。自然,爱子之心,人皆有之,母爱的人伦之情必然也让程婴之妻生出悲悲切切的抗议之言,从幕后走到前台。只有这样,女性伦理文化的叙事逐渐臻于完善,各位忠义之士的无私悲壮牺牲才愈加震撼。
本文是国内首次对《赵氏孤儿》历代版本的程婴之妻角色设置的系统论述,并同伏尔泰的《中国孤儿》程婴之妻依达姆进行了横向比较。程婴之妻角色缺失,既是时代伦理文化的要求,又是原著纪君祥版本的内在逻辑使然。而后来戏剧中角色的出现和演绎,是中国女性伦理文化语境的改善和女性意识觉醒的必然结果。寄望此文的一孔之见能够抛砖引玉,得到国内戏剧研究同仁的关注和批评。
[1] 宋绵有.元明清戏曲赏析[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3:89.
[2] 鲁进.马若瑟为什么翻译了《赵氏孤儿》 [EB/OL]. [2007-09-13][2012-04-11].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970745.
[3] 王季思.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上 [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70.
[4] 戴金波.伏尔泰 [M].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50.
[5] 李瑜青.伏尔泰哲理美文集 [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76.
[6] 葛力,姚鹏.启蒙思想泰斗伏尔泰 [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189.
[7] 沈吟.义薄云天悲壮动人:看《赵氏孤儿》 [N].新中原报,1981-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