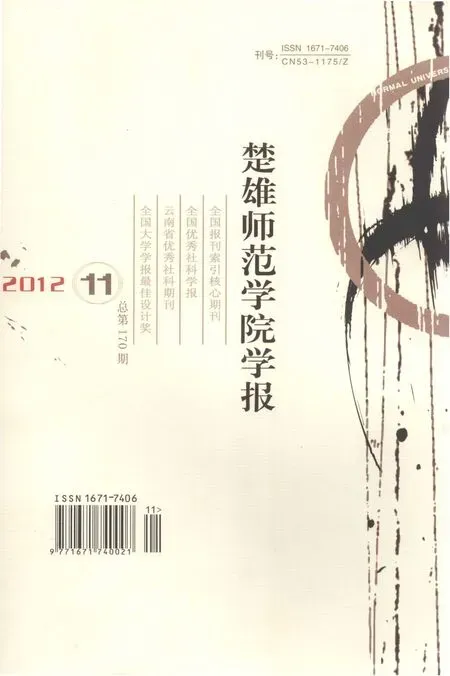关于汉语史和汉族人民的历史*—— 《汉语史略》之二
2012-04-02赵振铎
赵振铎 黄 峰
(四川大学,四川 成都 610064)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人类祖先在劳动中创造了语言,并且作为社会上最主要的交际工具使用它,人们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发展了语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为社会服务的语言也就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如果语言是静止的,没有发展变化,它就不可能很好地为社会服务,奴隶社会的汉语如果不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是无法为我们今天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社会服务的。
汉语的产生是很早以前的事情,那时没有记录汉语的汉字。当时的许多情况今天已经不清楚了,因而有了汉族起源的种种假说。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汉语是从原始汉藏语分化出来的。这件事发生在没有文献记载的远古时期。进入有文献记录的历史时期,汉语的历史和使用汉语的汉族的历史就能够比较清楚地观察到了。汉语的历史和汉族人民的历史是紧密关联的,要了解汉语的历史必需联系汉族人民的历史来进行研究。
黄河流域是汉族人民的摇篮,到了周朝,汉族已经扩展到周围很广阔的地区,加上汉语和周边民族的语言进行融合,形成了不同的汉语方言。到了今天有的汉语方言差别很大,达到互相之间不能够通话的程度。但是,不同地区的人,尽管方言不同,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汉人,原因是长期以来,汉语虽然有方言存在,但是汉民族的共同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它是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并且用书面语的形式巩固下来。长期的封建社会,政府要管理人民,办理公事,都需要一种能够起沟通作用的工具,这就是共同语。正因为这种共同语的存在,它使汉族人民能够很好地团结成一个统一的社会共同体,而不管他们的方言分歧怎样。这点和西方一些国家的情况不同。比方俄罗斯语、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使用它们的人互相之间通话并没有什么困难,但是它们属于不同的语言,因为它们的共同母语东斯拉夫语在很早以前就分化了,也没有一种像汉语共同语那样的语言来维系它们,所以它们应该是不同的语言。有些人不了解这点,含糊其辞地把汉语叫作汉语族,这是不足取的。汉语和它各个方言的情况,完全可以用汉族人民发展的历史来解释。
汉族不是孤立的,他的周围有不少其他的民族。古书上所说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指的就是这些民族。此外与汉族杂居的冀州有山戎、赤狄,雍州有白狄,豫州有伊洛之戎,晋有瓜州之戎,淮、徐有淮夷、徐夷,长江以南则被斥为“南蛮鴃舌之人”等等。汉族和他们接触,受他们的影响,想来会有一些他们语言的词被汉语吸收,但是今天汉语里面这些词少之又少,已经考察注明在案的实在不多,关于这点可以从汉语吸收外来成分的特点来说明。汉语吸收外来词最初用音译的方式,后来改变为意译方式。举晚近吸收西方语言的例子,如:“德谟克拉西——民主”,“赛因斯——科学”,“麦克风——扩音器”,“盘尼西林——青霉素”,“卡通——电影动画片”。但是也有一些词只有音译没有意译,如“咖啡”、“沙发”、“雷达”等,它们到今天也没有变成意译。王力教授在很早以前曾经说过:“意译是正常的办法,音译只是变通的办法,如果滥用音译,也就是滥用外来语,因为那样是表示汉语词汇贫乏到不能从基本词汇的基础上构成新词。”这话无疑是正确的。前苏联有个语言学家А.С.契科巴瓦曾经把汉语吸收外来词的现象称为“汉语词汇的不渗性”。
南北朝时期,鲜卑等少数民族在我国北方大片地方建立了政权,东魏、西魏、北魏、北齐、北周等都是,他们使用的应该是阿尔泰语系的语言。据文献记载,汉族和这些民族在语言上有过融合的情况,举几条例子:
《颜氏家训·教子》:“齐朝有一士大夫甞谓吾曰:我友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
这是当时一些汉族士大夫子弟为了讨好统治阶级上层而学习鲜卑语的情况。史书传记里面记载因为通鲜卑语而获得官职的不在少数,摘录一些材料:
《魏书·孟威传》:“孟威,字能重,河南洛阳人。颇有气尚,尤晓北土风俗,后以明解北人之语,敕在著作,以被推访。”
又《艺术晁崇传》:“崇弟懿,明辩而才不及崇也。以善北人语,内侍左右,为黄门侍郎。”
《北齐书·孙搴传》:“孙搴,字彦举,乐安人也。又能通鲜卑语,兼宣传号令,当烦剧之任,大见赏识。”
又《祖珽传》:“祖珽,字孝征,范阳到人也。……元康荐廷才学,并解鲜卑语,乃给笔札,就禁所具草。二日内成,其文甚丽。神武以其工而且速,特恕不问。然犹免官,散参相府。……珽天性聪明,事无难学,凡诸技艺,莫不措坏,文章之外,尤善音律,解四夷语及阴阳占候,医药之术,尤其所长。”
有一点值得注意,这些民族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汉族的文化,突出的如北魏孝文帝的力主汉化对后世带来的影响更大。因此,这些民族都注意学习汉语,他们上层都能够很好地使用汉语,且看下面这个例子。
《魏书·高昂传》:“于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惟惮服于昂。高祖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昂若在列,则为华言。”
随着这些地方民族政权的消失,汉族又恢复了统治,当时进入到汉语里面的一些鲜卑词也就随之消失了。这些现象的存在,只有从当时的社会历史上去寻找原因。
以上是就语言的整体来说的。如果就语言各个部门的情况来看,语言词汇方面有的时候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到语言历史和人民历史的联系。《尔雅·释畜》和《说文》有关的部首里面,家畜的名称区分很细,举凡毛色、年龄、动作行为、疾病等等都有专门的名称。试以“马”为例:
毛色 膝上皆白,惟馵。 四骹洁白,驓。 四蹢洁白,首。 前足洁白,騱。
后足皆白,翑。 前右足白,启。 左白,踦。 后右足白,骧。
左白,馵。 駠马白腹,騵。 骊马白跨,驈。 白州,驠。
尾本白,騴。 尾白,駺。 馰颡,白颠。 白达素,县。
面颡皆白,惟駹。 駠白,驳。 蕡白,騠。 駠马黄脊,騝。
骊马黄脊,騽。 青骊,駽。 青骊瞵,驒。 青骊繁鬣,騥。
骊白杂毛,駂。 黄白杂毛,駓。 阴白杂毛,骃。 苍白杂毛,骓。
(以上《尔雅》)
骐,马青骊文如博棊也。 骊,马深黑色。 騩,马浅黑色。
骝,赤马黑毛尾也。 骓,马苍黑杂毛。 骢,马清白杂毛。
騧,黄马黑喙。 骠,黄马发白色,一曰白髦尾也。
驖,马赤黑色。
驳,马色不纯。 馵,马左后足白也。 驔,骊马黄脊。 驠,马白州也。騽,马豪骭也。
年龄 莟,马一岁也。 驹,马二岁曰驹。三岁曰駣。 茎,马八岁也。
闽台方言合唱音乐的和声进行,常融入二度音、七度叠字音程等。在整体音响上比较协和,而平行四度也是闽南音乐的典型的特点,平行四度在传统和声里是不提倡的,而闽南音乐却常见平行四度这一特征。在闽南语合唱歌曲中, 为了在合唱中使和声保持一致,有时会应用大量相同节奏和声织体,如《情》《阮的希望拢在我心》就是比较典型的歌曲,分别采用了四部声、二部声合唱,合唱中的和声非常的整齐。曲式方面,常以中国传统音乐的多段式为主。近现代作品中也常见回旋曲式、三段五段曲式等。如《台湾好风光》即为典型的回旋曲式,四句式乐段结构,使得句式结构显得非常突出,具有鲜明的声乐艺术特征。
动作行为
骧,马之低仰也。 蠕,马摇头也。 讽,马行皃。 笃,马行顿迟。
骙,马行威仪也。 践,马行徐而疾也。 萢,马行疾也。 馺,马形相及也。
冯,马行疾也。 蟋,马步疾也。 蚕,马行侃侃也。 踯,马疾步也。
薜,马疾走也。 颿,马疾步也。 驱,马驰也。 蝾,马行疾来皃。
惊,马骇也。 蚣,马奔也。 驻,马立也。 薹,马载重难也。
(以上《说文·马部》)
这类字实在太多,没有必要一一指出。这里举的是有关“马”的例子,同样的, “牛”、“羊”也有这样的细微差别。这些字后来逐渐停止了使用。它反映了我国社会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畜牧社会时期,这个时期要求对家畜的名称有更细致的分类。随着畜牧时代的过去,这些词也就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人们也就不再使用它们了。
从原始氏族社会崩溃,社会进入到阶级社会,有了阶级分化,出现了阶级。尽管语言本身没有阶级性,但是阶级却要影响语言。比方古书里面谈到“死”,就因为社会等级不同而有不同的说法,如《礼记》的《曲礼》说:“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这可以从阶级社会有森严的等级制度来解释。
在秦汉时期,由于封建制度的形成和巩固,在词汇上也出现了一些表示君臣名分差异的词。如“朕”这个词表示第一人称“我”,在先秦时期人人都可以用:
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尚书·尧典》)
王曰:“舅氏!余嘉乃勋!应乃懿德,谓督不忘。往践乃职,无逆朕命!” (《左传·僖公十二年》)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楚辞·离骚》)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沬。(同上《招魂》)
第一句的“朕”是帝尧讲的,第二句是周天子周襄王讲的,第三句的“朕”见于屈原的作品,第四句的“朕”见于宋玉的作品。前两例使用“朕”的是君主,后两句则不是。可见在先秦时期“朕”的使用没有尊卑区别。所以晋朝郭璞在给《尔雅·释诂》 “朕,我也”条作注说:“古者贵贱皆自称朕”。到了秦始皇二十六年才规定“朕”作为皇帝的专称。从此以后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都是这样使用“朕”了。
此外这样的词还有:君王称人臣为“卿”,人臣自称为“臣”,称天子为“陛下”,在叙述的时候称天子为“上”。不仅如此皇帝还有不少专门用语,如皇帝住的地方叫“宫”,宫门叫“阙”,皇帝的妻子叫“后”,妾叫“妃”,皇帝到一个地方去叫“幸”,皇帝下的指示叫“诏”,人臣把皇帝的意图或命令叫“旨”,臣下给皇帝写报告叫“奏”,写的报告叫“疏”,这些词一直沿用到清朝帝制消灭。
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一些与佛教有关的词语也出现在汉语里面。南北朝时期一些人喜欢用佛教词语来取名字,如:吕罗汉、王文殊、庾沙弥、穆提婆、周罗睺、王僧达、王僧虔、王僧孺、王僧辩、明僧佑、明僧绍、杜僧明、韩僧寿、张僧晧、赵僧严、公孙僧远、江昙、滕昙恭、陈昙明、刘昙净、沈昙光、王昙首、夏侯昙深等,所有这些可以用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广泛传播来解释。[1]
两广地区有许多地名,它的前面都有一个“那”作为它的前加成分,如:
那伏 (新会)那州 (中山)那岳 (阳江)那花 (电白)
那浪 (合浦)那环 (琼山)那赛 (儋县)那宽 (钦县)
那六 (柳江)那然 (罗城)那研 (来宾)那龙 (河池)
那白 (武鸣)那甘 (宾阳)那崇 (百色)那岸 (田阳)
那更 (昭平)那博 (郁林)那登 (邕宁)那霞 (上思)
那鼓潭 (陆川)那伏墟 (台山)那落村 (清远)那落墟 (高要)
那吉墟 (恩平)那波病 (开平)那夹塘 (澄迈)那盆岭 (临高)
“那”是壮语水田的意思。壮语的语法结构是中心词的位置在定语之前。从这些地名看,原先壮族人民分布的地区比今天广得多。这是这些地区出现壮语地名的合理说明。①参看: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中华书局,1947年;罗常培《语言与文化》第五章,语文出版社,1989年。
至于语言结构规律的语法变化,要从历史上去找出它们与人民历史的联系,那将会有很多困难,即或勉强去寻找,在民族融合的时候会发现语言里面出现了一些特殊的语法结构,如南北朝时期,由于佛教的传入,翻译的佛教经典和一些有关佛教的文献里面出现了“于”嵌在及物动词和宾语之间的结构:
护于法者。(竺法护译《佛说海龙王经》)
击于大法古。(罗什译《发华经》)
得于圣道。(同上《童受喩》)
见于何物?(《八相变文》)
每弘扬于三教。(《降魔变文》)
这可以用当年汉译佛典受到古代印度语言语法结构的影响来解释。同样,上世纪初翻译欧美文献,受这些语言的影响,出现了所谓“欧化语法”,也可以这样去解释。但是也就仅限于这类情况,其余大多数现象要从社会历史里面去寻找原因都是困难的。
至于语言物质外壳的语音的变化,要在人民历史里面去找它们变化的联系,困难就非常多。北方话入声塞音韵尾的消失,是什么原因促成的?全浊声母变为相应发音部位的清声母,又是什么社会历史因素在起作用?恐怕很难找到它们的变化和汉族人民历史的联系的原因。前两个世纪恩格斯在给布洛赫的一封信里面曾经说过:“要从经济上说明每一个德意志小邦的过去和现在的存在,或者要从经济说明那种把苏台德山脉至陶鲁斯山脉所形成的地理划分扩大成为贯穿全德意志的真正裂痕的高地德意志语的音变的起源,那么,要不闹笑话,是很不容易的。”恩格斯认为要援引经济现象或者社会经济基础现象来解释德语里面的辅音变化的原因是可笑的。前面提到汉语史上的历史音变,要在汉族人民的历史中去找到它产生的原因是困难的,而且几乎是不可能的。
就语言的词汇来讲,也不是其中的每一个现象的出现都能够在历史上找到解释。上古时期汉语的“首”被“头”所代替,是什么历史原因造成的,恐怕难以找到。因此说语言历史和人民历史的联系不能够机械地去理解。对于任何语言里面的变化都硬要去找它们的社会历史原因,那会犯机械唯物论的错误。
当然,这并不是要否定语言历史和人民历史的联系。语言历史和人民历史的联系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那就是任何语言现象都有自己的历史,它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产生,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展,也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死亡。正是这样,把语言的各个要素,它的语音、词汇、语法各种变化放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去考察,将汉语分成若干历史阶段,讨论它在各个历史阶段所发生的变化,这就是汉语史研究的目的所在。
[1]吕叔湘.南北朝人名与佛教 [J].中国语文,198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