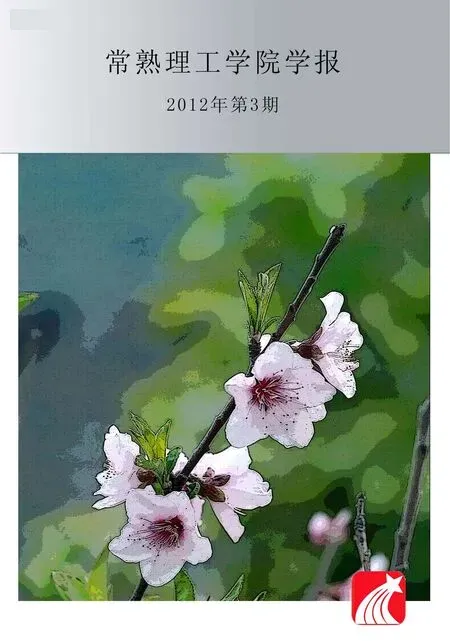文化转向视角下的翻译策略研究——以王尔德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两中译本为例
2012-04-02施秋蕾
施秋蕾
(常熟理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常熟 215500)
引 言
20世纪80年代,西方翻译研究出现了重要的转折,以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勒弗菲尔(André Lefevere)为代表的文化学派提出了翻译的“文化转向”,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自此,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语言层面,而是被置于一个宏大的文化语境来考察。
文化千差万别,如何实现不同文化间的有效交流,是保留原语文化的异质性还是将其本土化,这就涉及翻译策略的选择。有的译者主张归化,有的译者支持异化。归化和异化这两个概念最初由韦努蒂(Lawrence Venuti)1995年在《译者的隐身》一书中提出,源头可追溯至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813 年所写的《论翻译的方法》一文。[1]186-187归化和异化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翻译策略。所谓归化,是指“译者在翻译时采用一种透明流畅的译文,使原语文本对于读者的陌生感降至最低”[2]43-44;所谓异化,是指“译者在翻译时故意保留原语文本当中的某些异质性,以此打破译入语的种种规范”[2]59。
翻译策略的选择取决于翻译目的,同一原文由于不同的翻译目的可能产生迥异的译文。比如戏剧翻译,有的旨在搬上舞台,有的仅供阅读玩味。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是王尔德(Oscar Wilde)最出色的喜剧,文笔优美流畅,对话俏皮犀利,在文字游戏、隐喻,甚至是普通文化词中“抖包袱”、藏笑料。[3]文化要素对于喜剧的重要作用,给译者带来了额外的挑战。本文将从文化翻译的视角分析余光中、钱之德两个中译本的翻译策略选择及各自利弊。
余光中和钱之德显然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余译以归化为主,钱译则以异化为主,这主要是由他们不同的翻译目的所决定。余光中在译后记《与王尔德拔河记》中说:“小说的对话是给人看的,看不懂可以再看一遍。戏剧的对话却是给人听的,听不懂就过去了,没有第二次的机会。我译此书,不但是为中国的读者,也为中国的观众和演员。所以这一次我的翻译原则是:读者顺眼,观众入耳,演员上口。希望我的译本是活生生的舞台剧,不是死板板的书斋剧。”[4]127为了满足舞台演出的需要,余光中采取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力求台词语言自然口语化,充分考虑了观众的文化心理和接受能力。而钱之德虽然未对自己的翻译目的作出说明,其译本显然不是为了舞台而生。其实,巴斯奈特也曾在《仍陷迷宫——戏剧翻译再思考》一文中提出,“译者的任务是保留原文的不调之处,将其意义抉择留给他人。寻求深层结构以使译文‘可表演’并不是译者的责任。”[5]105她认为译者应当保留作品的异域特色,让读者或艺术指导自己去发现和体味剧本的韵味。由此可见,钱之德的异化策略也是有据可循的。
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比较余、钱两个中译本中文化信息的翻译效果。
一、剧名及主要人名、地名翻译
(一)剧名翻译
一部戏剧的成功离不开一个引人入胜的名字,因此剧名翻译可谓重中之重,不仅要表达清楚作者的用意,还应迎合目的语读者或观众的喜好。该剧名难点在于“Earnest”一语双关,既表示“认真”的处世态度,又音同“Ernest”,是剧中两位男主角给自己杜撰的名字,而他们爱的姑娘都因为这个名字爱上了这两个一点也不“Earnest”的花花公子。
面对这一棘手问题,余光中巧作变通,将“Earnest”译作“认真”,谐音“任真”恰为人名,较好地还原了作者的用意。又因为“认真的重要性”不太符合中国读者和观众的审美标准,故将其意译成汉语常用的四字俗语“不可儿戏”,读来朗朗上口,趣味盎然。不足之处在于,原剧名的双关未能保留,只能在文中表明。
钱之德则较为保守,从谐音人名入手,直译为“名叫埃纳斯特的重要性”。此异化译法稍显冗繁,带有异国特色,但“埃纳斯特”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意义不明,因此接受度不高。最重要的是,原剧名的双关也未在人名翻译中体现,只在剧名翻译注解中进行了说明,读者需做一番功课才可了解其中奥妙。
(二)主要人名翻译
因为全剧围绕人名展开,人名翻译显得尤为重要。主要人物的姓名绝非王尔德随意杜撰,而是精心设计的产物,上文提到的Ernest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因此成功翻译这些人名绝非易事。如果采取异化音译,异国特色将被保留,但原文巧妙的文字游戏将会遗失,甚至还会影响理解。纽马克也说:“虚构的文学作品中名字的涵义依然是个问题。喜剧、寓言、童话和一些儿童故事中,只有当国籍重要时才会翻译名字,比如民间故事。”[6]215
因此,余光中再次采用归化策略,以中国的命名方式翻译了主要人名;而钱之德则将异化进行到底,只是异化策略无法解决文字游戏带来的种种难题。
例 1: Algernon: You have always told me it was Ernest.I have introduced you to every one as Ernest.You answer to thename of Ernest.You look as if your name was Ernest.You are the most earnest-looking person I ever saw in my life.[7]11
余译:亚:你一向跟我说,你叫任真。我也把你当成任真介绍给大家。人家叫你任真,你也答应。看你这样子,就好像名叫任真,我一生见过的人里面,你的样子是最认真的了。[8]8
钱译:阿尔杰农:你总是对我说,你名叫埃纳斯特。我向别人介绍你,总是用埃纳斯特这个名字。你名叫埃纳斯特,看上去你就像名叫埃纳斯特,你是我平生见到过的最埃纳斯特的人。[9]212
钱之德再次给出注解,说明“埃纳斯特”是谐音,应为“认真”之意,但即便如此重复解释仍无法弥补译文逻辑和通顺上的不足。相比之下,余光中对此人名的翻译方法使文中所有难题迎刃而解,译文逻辑合理、语句通顺。
另一人名“Bunbury”的翻译也另藏玄机。该词是王尔德杜撰产物,却绝非信手拈来。它由“bun”和“bury”两词合成,“bun”意为小圆甜蛋糕,因此“Bunbury”可字面理解为“埋头于小圆甜蛋糕中”,由此可知此名主人寻欢作乐的特点。不同于“Ernest”与“Earnest”的谐音关联,“Bunbury”的深刻用意体现在构词形式上,翻译时也不可掉以轻心。
余光中仍采用谐音词来解决这一问题,考虑到人物“两面人”的特征,将其译为“梁勉人”。虽然音、意均与“Bunbury”相去甚远,人物特点却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同样,钱之德也采用了一贯的音译法,将“Bunbury”译为“邦伯里”,甚至是“邦伯里主义者”。该译为人名增添了些许神秘色彩,因为当事物被冠以“主义”之名,便给人以抽象深奥之感。但要了解人名深意,读者仍需研究一番。
除此两个主要人名,“Prism”也大有文章。据余光中理解,该名音近“prim”(古板),刚好符合Prism小姐的性格;又音近“prison”(监狱),暗寓“牢守西西丽”。综上考虑,他将其译为“劳小姐”,同时也影射了其“老小姐”身份。[3]131而钱之德再次将该名音译为“普丽斯姆小姐”,也未在注解中发掘其隐含意义,读者便无法从人名翻译了解到该人物的性格特征。
在译其他人名时,余光中采用了相同的策略,将大部分名字归化处理。例如,“Gwendolen”译作“关多琳”,“Lane”译作“老林”,“Lady Bracknell”译作“巴夫人”,等等。这些译名让中国的读者观众备感亲切。相比之下,钱之德均采用异化音译,保留了异国特色,但人名涵义需要读者自己发掘。
(三)主要地名翻译
地名翻译与人名翻译是相通的。“Woolton”、“Shropshire”、“Tunbridge Wells”在余、钱两位译者笔下分别被译为“武登乡”、“希洛普县”、“通桥井”和“武尔顿”、“希罗普郡”、“滕布里奇·维尔斯”。通过“乡、县、井”等字样,读者和观众可以感受到浓郁的中国文化特色;而钱之德的译名则保留了西方地名特征,有的略显繁复。
二、隐喻翻译
隐喻中常含有丰富的文化元素,也常是喜剧的笑点所在。成功的翻译可以帮助读者和观众了解外国文化,更好地体会其中幽默。然而,英汉文化各有特色、大不相同,某些元素植根于特定文化,非三言两语能解释清楚。例如,一些隐喻源自英语典故,其他文化背景的读者和观众很难快速理解。
例 2:Ah!That must be Aunt Augusta.Only relatives, or creditors, ever ring in that Wagnerian manner.[7]14
余译:啊!这一定是欧姨妈。只有亲戚或者债主上门,才会把电铃掀得这么惊天动地。[8]11
钱译:啊!一定是奥古斯特姨母来了。只有亲戚,或者债权人才用这种华格纳(常见译名为瓦格纳,笔者注)派头按铃。[9]216
余光中在《与王尔德拔河记》中说:“我个人是觉得好笑极了。因为这时华格纳刚死不久,又是萧伯纳一再鼓吹的歌剧大师,以气魄见长。可惜这典故懂的人固然一听到就好笑,不懂的人一定更多。”[4]129确实,若非了解歌剧、戏剧之人,多数不曾听说过华格纳,也未必知道王尔德和萧伯纳的关系。虽然普通读者和观众也能猜出华格纳一定是个声音洪亮、中气十足的人,却不能体会该隐喻的生动诙谐之处。出于上述考虑,余光中选择牺牲这一突兀的隐喻意象,归化译为中文四字习语,以求入耳即化。
钱之德则不愿舍弃原文的文化意象,再次采用异化翻译加注解说明的方法。遗憾的是,其注解太过简略,仅为“华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寥寥数笔,并未提供任何细节信息揭示隐喻的幽默之处。读者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体会其中的妙不可言。不过,钱译终究让普通中国读者认识了华格纳,并用“派头”二字弥补了直译“华格纳”的不足。因为中文里“派头”指一个人有气势,“华格纳派头”的声音一定是振聋发聩的。
例3:Her mother is perfectly unbearable.Never met such a Gorgon…I don’t really know what a Gorgon islike,butIam quite sure thatLady Bracknell is one.[7]23
余译:她的母亲真叫人吃不消。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母夜叉……我不知道母夜叉究竟是什么样子,可是我敢断定巴夫人一定就是。[8]22
钱译:她的母亲却完全不能忍受,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蛇发女妖……我确实不知道蛇发女妖是怎么个模样,但我确信布雷克耐尔夫人就是一个蛇发女妖。[9]228
“Gorgon”是希腊神话传说中的蛇发三姐妹,人见之立即化为顽石,常用于形容丑陋可怕的女人。钱之德的异化翻译创造了汉语文化中前所未有的意象,并用“女妖”来引导读者将此意象与可怕女人联系起来,丰富了汉语文化。但夫人头上显然没有毒蛇缠绕,其可怕程度也不至“女妖”,如此翻译会造成读者误解。余光中选择了中文里的“母夜叉”一词,可谓完美归化,因为“母夜叉”指“凶巴巴的女人”几乎人尽皆知,也正是巴夫人的真实写照。
例4:It is rather Quixotic of you.But I think you should try.[7]32
余译:你真是天真烂漫。不过,我看你应该试一试。[8]35
钱译:你的举动有些像堂吉诃德,但是我想你应该尝试尝试。[9]240
要解释清楚“quixotic”,绝非只言片语能办到。该词源于塞万提斯名作《堂吉诃德》,常用于形容浪漫、不切实际、爱狂想的人。即使读者听说过堂吉诃德,也未必清楚其性格特征。余光中的归化翻译解释恰到好处,而钱之德的异化处理则丰富了读者的想象,可谓各有所长。
纽马克曾说过,“如果一个原创的文化隐喻显得晦涩难解或是无关紧要,你可以用描述性的隐喻取而代之或只译背后涵义。”[6]112通过以上三例可知,余光中的归化策略与之不谋而合,将原语文化改头换面“重置”于目的语文化中;而钱之德的异化策略则坚持原汁原味地引介原语文化,使其在目的语文化中得以“重现”。
三、普通文化词翻译
大多数的文化词易于辨识,因为它们或为专有名词,或无法简单直译。但也有许多文化习语掩藏在通俗语言的外衣之下,它们看似浅显易懂,然而在翻译策略选择时依然存在归化、异化之争。
例5:This is no time for wearing the shallow mask of manners.When I see a spade I call it a spade.[7]46
余译:肤浅而客套的假面目,现在该除下来了。我要是见到一头鹿,就不会叫它做马。[8]53
钱译:现在不是说话藏头藏尾的时候。我是见到锄头,就说锄头。[9]259
原文第二句话来自英语习语“to call a spade(锄头)a spade”,意指“直言不讳、有话直说”,该短语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 1520年”[10],所以“spade”的文化意象并非王尔德随口编造,而是古已有之。看似平凡无奇的短短一句话,其实暗藏着中国读者和观众不熟悉的文化背景。
钱之德照例保留“锄头”的意象,他在注解中说,为呼应下文此处不能省略该意象。其实稍作变通后,原意象是可以变换的。只是“锄头”的习语简单易懂,虽然中文里没有类似表达,读者也能欣然接受,因此大可保留下来,丰富汉语文化。另一方面,余光中则将归化贯彻始终,由中文习语“指鹿为马”衍生出“鹿”和“马”这对新意象,替换原有的“锄头”。如若深究,“指鹿为马”的确切含义实为“比喻颠倒是非”[11]1619,与“有话直说”的反义词稍有出入,但其意象转换极富创意,仍令读者观众拍案称绝。
例6:Even these metallic problems have their melodramatic side.[7]30
余译:因为就连这些响当当的问题也不免有闹哄哄的一面。[8]32
钱译:甚至这些金属质的货币都具有了通俗闹剧的味道。[9]237
“Melodrama”指情节剧,通常事件离奇,人物夸张。尽管中国也有类似的戏剧,但该词源自英语的特殊文化背景,因此中国读者观众可能无法完全理解“melodramatic side”的确切含义。余光中采用归化,译出了对此类剧作的整体印象,钱之德则再次异化,辅以注解。虽然两种译文都突出了“闹”字,余译显然技高一筹,不仅明白晓畅,而且朗朗上口,原因是译出了“metallic”和“melodramatic”两词间的双重关联。首先,两词应当意义相对,余译突出了其中对比,而钱译则将“problems”误译为“货币”,且“金属货币”和“通俗闹剧”并无比照之意,令人费解;其次,余译注意到了“metallic”和“melodramatic”两词既押头韵又押尾韵,因而选择“响当当”和“闹哄哄”两个ABB重复结构作为补偿,而在钱译中,两种押韵均未得到体现。可见,在翻译文化信息时,还应考虑到上下文的呼应,慎重选择翻译策略。
再如“manna in the wilderness”[7]34之类的表达,深深植根于宗教文化,要在对话的有限篇幅里向中国读者和观众解释清楚几乎是不可能的。钱之德照例异化译作“旷野里天赐的吗哪”,并加上注解[9]243;而余光中依旧归化译成“天降食物于荒野”[8]37,省去了解释文化背景的麻烦。如果作为阅读文本,钱译显然信息量更大,但若是用于舞台表演,余译就更直白易懂,因为“吗哪”一词会造成理解困难,影响戏剧的演出效果。这一例子再次说明,译者在动手翻译前必须首先明确目的,只有这样才能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
结 语
通过以上三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余光中和钱之德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都是一以贯之的,虽都存在个别调整之处,但整体而言,余译归化显著,钱译异化显著。
从译本的接受情况看,余译在台湾、香港、广州等地多次被搬上舞台演出并取得巨大成功,而钱译却很少有人问津,[2]只是常被用来跟余译对比研究,且饱受诟病,常出现一边倒支持余译的现象,认为余译更具舞台表演性。其实客观而论,钱译虽然存在不少误译,但是其异化策略的运用是无可厚非的,因为译者的翻译目的不尽相同,而反映文化差异、促进文化交流应是翻译的首要目的。只是余译的机智归化更好地还原了王尔德玩弄文字的高超水平,这是钱译不能媲美的。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译者在归化、异化两大策略中面临更艰难的抉择。归化的翻译符合目的语文化规范,译文自然流畅,因而更易为读者所喜爱;但异化的翻译更尊重原语文化,能更多地让读者领略到原作的异域风貌。译者应当根据不同的文本类型和翻译目的,尽可能多地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更好地促进原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交流。
[1]姜倩,何刚强.翻译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2]Shuttleworth M,M Cowie.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K].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3]汪琳.余光中戏剧翻译的归化策略[J].巢湖学院学报,2010(1).
[4]余光中.余光中谈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5]Bassnett S,A Lefevere.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C].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6]Newmark P.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7]Wilde O.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M].London:Penguin Books,1994.
[8]余光中.不可儿戏[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
[9]钱之德.王尔德戏剧选[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
[10]第39讲打开天窗说亮话Call a spade a spade&Long for something[EB/OL].世博英语,(2010-04-11)[2012-02-09].http://www.360abc.com/article/833.html.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K].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