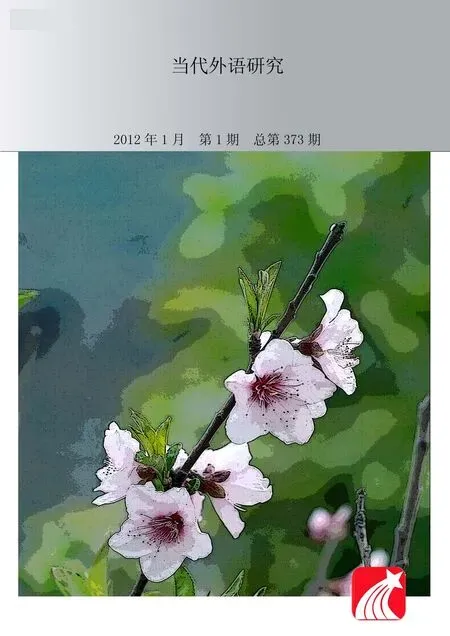现代汉语动补构式的标记性研究
2012-04-01钟书能
钟书能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510640)
1. 动补结构
动补结构是现代汉语中的一种重要而普遍的构式(construction),常指动词与补语之间具有动作与结果的关系,蕴含致使意义(吕叔湘1955;王力1994;梅祖麟1991;陆剑明、马真1996;李讷、石毓智1999;蒋绍愚1999;赵元任2001;石毓智2003)。朱德熙(1982:7)说“动补结构是现代汉语里非常重要的一种句法构造,印欧语里没有跟它相对应的格式”,动补结构也因此成为我国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一个难点。现代汉语的动补结构又分为动结与非动结两大构式:
1) 动结构式
(1) 那本书我买着了。(语法标记词“着”作补语)
(2) 老太太的眼睛哭肿了。(形容词作补语)
(3) 孟姜女哭倒了长城。(宾语作补语)
(4) 我打碎了爷爷的花瓶。(宾语作补语)
(5) 这个小女孩跑丢了一只鞋。(数量短语作补语)
(6) 老师解释得很清楚。(“得”字短语作补语)
(7) 她打扮得我都认不出来了。(“得”从句作补语)
(8) 他们打球打累了。(重动结构里嵌套的一个动补结构)
(9) 他把报纸撕成了两半。(“把”字里嵌套的一个动补结构)
动结构式中动词与补语之间具有明显的动作与结果的关系,这里的“结果”是一个意义宽泛的术语,包括动作导致的状态、程度、收获、效果等(石毓智2003:31)。语法标记词、形容词、副词、宾语、数量短语、从句等均可担当补语,蕴含一种结果。
2) 非动结构式
(10) 老师走到门口。(介词短语作补语)
(11) 这贾菌少孤,其母疼爱非常,书房中与贾蓝最好,所以二人同坐。(《红楼梦》第九回)(副词作补语)
(12) 感觉好多了。(程度短语作补语)
(13) 大家已经检查了两遍。(动量词作补语)
(14) 他们开始走进来了。(趋向动词作补语)
非动结构式(传统上常称为“动趋式”)中动作与补语之间不是“动作与结果”的关系,而是“动作与程度或方向”的关系,补语主要由介词短语、程度短语、动量词以及趋向动词等担任,补语并不指向结果,而是表示一种动作的方向或程度不断发展。
动结构式是现代汉语中常用的一种句式,非动结构式的使用频率远远不如前者。因此,从原型范畴的角度看,动结构式是动补构式的原型(prototype),同时也是一种无标记构式。本文拟以标记理论为基础,并结合原型范畴理论,重新审视现代汉语中的动补构式,深入探讨动补构式两个类型中的标记性程度的历史发展渊源。
2. 理论概说
2.1 标记理论
语言中的标记现象是指某个范畴内部存在的某种不对称现象。例如就“数”这一语法范畴而言,英语中的复数是有标记的,单数是无标记的。概括地讲,凡是有“数”这个范畴的语言,复数是有标记项,单数是无标记项,有关这种不对称现象的理论就叫标记理论。标记概念于20世纪30年代由布拉格学派语言学家N. S. Trubetzkoy在音位学理论中提出。他对音位对立进行了分类,分别是(1)表缺对立(privative oppositions)、(2)层级对立(gradable oppositions)、(3)均等对立(equipollent oppositions)以及(4)可中和对立(neutralizable oppositions)。例如,在表缺对立音位中,两个音位除了其中一个包含某一语音标记,而另一个不包含该语音标记外,其他特征完全相同,如英语中/b/和/p/之间的对立,这里的标记是浊音。其中具有浊音特征的音位称为有标记项,缺乏该特征的音位称作无标记项(参见沈家煊1997;张建理1999;王立非1991a,1991b,1994,2003)。
在标记概念的基础上,雅各布森(Jacobson)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并把该理论引入到语法与词汇的研究领域中,用来描写语法和语义现象(石毓智2006;曲志坚、费丽敏2007;王永祥2008)。标记对立中的一个成分表达的是明确的、限定的概念,而另一个对立成分表达的是宽泛的、不限定的概念。前者称为有标记项,而后者为无标记项。例如,woman与man的标记对立中,woman为有标记项,而man为无标记项。事实上,标记这一概念经过布拉格学派的推广,目前已经广泛应用到了语音、语法、词汇、语义、语用、心理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等语言分析的各个层面,并从最初的二元对立扩展到普遍与非普遍的对立、正常与非正常的对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标记和无标记的对立在语言分析的所有层次上都起作用,这叫做标记现象的普遍性(李淑康2010)。
2.2 原型范畴理论
原型范畴理论产生于当代语言学和哲学界对于经典的亚里士多德范畴学说的批判,尤其是维特根斯坦对于语义范畴“家族相似性”的深刻揭示。在原型理论之前,经典范畴理论一直占主导地位。该理论认为范畴由范畴成员共同拥有的一组充要特征来界定,并且这些特征是二元对立的,即一个实体如果具备了某一范畴成员的所有充要特征,那么它就是该范畴的成员,否则就不属于该范畴。建立在亚里士多德的经典范畴理论基础上的“充分必要条件”作为一种传统的释义方式,存在着很多缺陷。例如,充分必要条件把一个概念范畴的所有成员看成享有共同语义特征的等值词,排斥不具备某一特征的同类成员;或者说因为某一成员不具备某一特征而把该特征视为非必要条件。这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了该理论的释义功能。“充分必要条件”的这种观点体现了其死板、僵化的一面。其缺陷还表现在,由“充分必要条件”得到的范畴的边界是清晰的而不是模糊的。而事实上,范畴的边界常常是模糊的而不是清晰的。1953年,维特根斯坦在其《哲学研究》中,提出了对经典范畴理论和“充分必要条件”的质疑,并提出了“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原则。他认为是一种叫做“家族相似性”的相似关系将一些词联系在了一起。这种“家族相似性”包括很多方面,诸如体形、相貌、颜色等等。到了上世纪70年代,Rosch(1973)对自然语言的语义概念范畴的大量研究及其意义理论为原型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Rosch(1973:328-350)认为,任何一个属性在区别一个范畴时都不是必要的,“实体的范畴化是建立在好的、清楚的样本之上,然后将其他实体根据它们与这些好的、清楚的样本在某些或一组属性上的相似性而归入该范畴。这些好的、清楚的样本就是‘原型’,是非典型事例范畴化的参照点。”简言之,原型就是一个概念范畴中最典型的、最具代表性的成员。原型理论的这种区分是对“充分必要条件”缺陷的弥补。在原型理论中,词的意义是以原型范畴的形式而存在的。原型范畴是一个由原型和边缘构成的结构。原型是该范畴的典型成员,边缘是由该范畴中非典型的成员构成的。所以,原型范畴理论是一种既不同于经典范畴理论,又不同于传统语义理论的意义观(参见徐盛桓2003;束定芳2008;刘正光2006)。
2.3 重新分析理论
重新分析是语法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机制,解释历史上语言规则变化现象。Langacker(1987)在讨论句法变化时把重新分析定义为不涉及句法表面形式改变的一种或一类表达式的结构变化。根据Hopper和Traugott(1999),重新分析的推理形式是溯因推理。溯因推理法先观察结果,根据观察产生法则或解释性假设,然后根据这一法则或假设推定某事物属于某一情况。这种推理是说话人根据普遍原则作出某种假定时发生的推理现象。重新分析是溯因推理的结果:从结果得出某一结论,再回到规律和原则对案例进行推断。
3. 现代汉语动补结构的历史发展渊源
根据吕叔湘(1955)、梅祖麟(1991)、尤其是石毓智(2003)的系统考察,中古汉语中存在一种广泛使用的可分离式动补组合结构,梅祖麟(1991)、蒋绍愚(1999)、石毓智(2003)等均认为该组合的推动力首先来自于“V而V”连动结构中“而”的衰亡。古汉语中,连动构式必须使用“而”连接,如例(1)和例(2)。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左右,“而”的使用开始有所松动。到了魏晋时期已经很少用了,在北宋时期基本消失,两个动词可直接相邻,如例(3)与例(4):
(1) 公出,自其厩射而杀之。(《左传.宣公十年》)
(2) 息侯伐郑,郑伯与战于竟,息师大败而还。(《左传.隐公十一年》)
(3) 汉军败还,保雍丘,去击反者王武等。(《史记.傅靳蒯列传》)
(4) 一从骂破高皇陈,潜山伏草受艰辛。(《敦煌变文.捉季布》)
根据古汉语语法规则,如果两个以上的动词均为及物动词时,可以共用一个受事宾语(如例1、3、4、5),即所谓的“多动共宾式”石毓智(2003:54-59)。用下列例句阐述“多动共宾式”的另一种情况:如果相邻的两个动词,一个为及物动词而另一个是不及物动词,要共用一个宾语时,宾语可以移到整个句子的前面,或及物动词的后面,如:
(5) 岸崩,尽杀压卧者。(《史记.项羽本纪》)
(6) 百余人炭崩尽压死。(《论衡.明义》)
(7) 击陈柱国房君死。(《史记.陈涉世家》)
例(6)中,由于“死”是不及物动词,受事宾语“百余人”移到了整个句子的前面。同样的不及物动词“死”后面的受事宾语“陈柱国房君”移到了及物动词“击”的后面。石毓智(2003:54-59)进一步认为“击陈柱国房君死”这种句型的出现直接导致中古汉语中可分离式动补组合的兴盛。中古汉语中动补组合式的抽象格式为:V+X+R,其中R往往为形容词或不及物动词(形容词与不及物动词有一个共同语法特征:作谓语时均不带宾语);X可以是受事宾语、否定标记词或副词,如:
(8) 唤江郎觉。(不及物动词)(《世说新语.假谲》)
(9) 分肉食甚均。(形容词)(《史记.陈丞相世家》)
V+X+R结构中,为什么独立的句法单位V和R可以越过X融合成一个独立的句法单位(复合动词)呢?祝敏彻(1990:240-251)和石毓智(2003:66-198)等的系统考察认为在中古汉语里,不同的X成分造就了4种不同的结构,具体为
结构一:[V+受事宾语][副词/否定词+R]
结构二:[V+受事宾语][R]
结构三:[V][副词/否定词+R]
结构四:[V][R]
石毓智(2003:66-198)认为在古代汉语里,X成分不是必须出现的,例如,受事名词是已知的话就常常被省略,副词和否定标记只有在表义需要的时候才会出现。上述4类结构中的受事宾语、副词或否定词必须与[V]或[R]组成不同的直接成分,如受事宾语只能与动词组成动宾结构,而副词或否定词只能与修饰补语组成一个结构。结构一最为完备,结构四最为简单,不过其中的[V]和[R]要当作两个独立的句法单位看才符合中古汉语的语法规则。但是在中古汉语的各类文献中,恰恰是结构四的使用频率高于其他三类的总和。[V]和[R]在相邻的句法环境下经过双音化、使用搭配频率、语义选择重新分析成一个不可分离的粘合式句法单位。其他三类结构受结构四语法化结果的诱发也以类推(analogy)的方式把[V]和[R]组合成单一的句法单位。当然,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V]和[R]的凝固或组合历经了一千多年的语法化的过程(其间以[V]和[R]的双音化为主要推动力,还涉及[V]和[R]的搭配使用频率、语义选择等诸因素),最终使可分离式动补组合演变成现代汉语的动补构式。
动补构式的发展实质是动词和结果成分通过重新分析而使其间的边界消失。边界的消失不可能是一蹴而就,必然是循序渐进的。动补构式中的[V]和[R]必然经历一个从松散到紧密的语法化过程,也就是说必然是从低度融合到高度融合的重新分析过程。在低度融合阶段,虽然[V]和[R]之间不再允许其他句法成分插入,但[V]和[R]的组合还具有短语的性质。[V]和[R]之间的边界完全消失后就进入了高度融合阶段,两者完全凝固成一个复合动词,是一个单一的韵律单位。[V]和[R]之间不仅不允许插入任何其他句法成分,而且还可以像普通动词一样带受事宾语。
4. 无标记动结构式
回顾现代汉语动补构式的语法化进程,我们注意到了该构式的最原始推动力是连动构式,连动构式具有“致使”或“使成”本义。由于到了10世纪,连动构式中“而”这个连接词基本消亡,为了解决“多动共宾式”中动词有时因及物性不一致而必须让受事宾语移动这个问题时,可分离的动补组合在10世纪就自然产生了。从可分离的动补组合结构的出现一直到现代汉语的动补构式的建立,宾语的位置或移动始终是个焦点。
古代汉语中,“多动共宾式”(V1+V2…V4+O,最多4个动词可共用1个宾语)中的每个动词必须是及物动词,与宾语必须是动作与受事的关系。但是VRO这个结构出现后,古汉语“多动共宾式”中所有动词必须为及物动词的规则被打破了,因为VRO结构中的R常常为不及物动词或形容词。如果受事宾语一定要出现在VR后面,又不违背“多动共宾式”规则,唯一的办法就是让VR语法化为单一的复合动词,也意味这R只能虚化为一个语法标记,丧失独立词的地位。但是VR语法化过程不能突变,而只能是渐进的。因此,在VR完全语法化为单一的复合动词的漫长历史进程中,要让受事宾语O有个合法的位置,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位于动词V之后,要么位于整个VR之前。当然,位于动词V之后是个很自然的选择,因此公元10世纪左右,可分离的动补组合VOR结构开始出现在各类文献中,到12世纪达到非常完备的阶段。从15世纪开始,现代汉语的VRO动补构式逐渐取代中古汉语可分离的动补组合VOR结构,VR的完全融合必然导致O位移的问题,因为最早出现的VRO中,V一定是及物的,R可以是及物的,也可以是不及物的动词或形容词。然而到了12世纪之后,V也可以是不及物的了,而且与VR之后的受事宾语没有“动作—受事”关系,例如:
(1) 哭损我一双眼睛。(《张协状元》)
其中“哭”与“一双眼睛”没有直接的“动作—受事”语义关系,这里的受事宾语只能看作是整个补语短语“哭损”所赋予的。其实,现代汉语里也有不少这样的用法,例如:
(2) 跑丢了一只鞋。
Goldberg(1995)认为英语的动补结构作为一个整体构式可以赋予一个受事宾语,而且该宾语并不与构式中的任何一个成分发生直接关系。现代汉语的“跑丢了一只鞋”句式的用法无疑也是由整个构式赋予一个受事宾语的。
因此,从原型范畴理论看,现代汉语中的能带宾语的动结构式无疑是动补构式的原型,是动补构式中各类构式中的典型的、最为核心的成员。能带宾语的动结构式还可细分成两类。根据黄晓琴(2006)的研究,在可带宾语的动结构式中所带的宾语,常见的有两类:一类如“我听懂了他的话”等以“懂”、“明白”、“会”等及物动加补语构式所带的宾语,这些宾语都可不需要动词直接与补语搭配构成他动关系,而是由整个构式与宾语构成使动关系,此类宾语叫受事宾语,在动结构式中相对较少,不占主体地位。另外一类如“打碎花瓶”、“提高汉语水平”、“弄清楚情况”等,宾语与动结构式之间直接构成一种使动关系,此类宾语叫使动宾语,在动结式中相对较多,占主体地位。这种使动关系,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动结式的语义特征而得出,如:“提高——使位置、程度、水平、数量、质量等方面比原来高”。从释义中我们很容易看出这些动结式带宾语时所含有的“使动”语义特征,以及动结式与宾语之间的使动关系,这也是王力先生一直把动结式称为“使成式”的原因,因而我们把这类动结式所带的宾语称为“使动宾语”。汉语大部分动结式所带的宾语都属于这一类。从标记理论的角度审视,能带宾语(可以是受事名词宾语,也可以数量短语等),尤其是使动宾语的动结构式是无标记结构,是自然、常用的动补结构,无需特别标记,因此是无标记结构中的最为核心的句型。
下面是形容词作补语的动补结构:
(3) 我说累了。
在例(3)中,“说”的动作指向受事(句子没出现,但读者明白施事对象为“一堆话”、“不少事情”等),即主语是施事,结果补语“累”用来描写施事。由于两者的语义指向完全不同,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们是代表两个独立的事件:我说了(事件一),我累了(事件二)。正确的理解应该是:事件一导致事件二。由于诸如“说”与“累”的动补关系松散,即使历经一千多年的语法进程,它们发生重新分析的过程也很缓慢。因此,相对能带宾语的动补结构,其表示不含“使成”的“结果”更加宽泛。形容词做补语蕴含结果或状态的情况也可再分为两类。王红旗(1996)把形容词担当补语时分为状态补语与评价补语。在“老太太的眼睛哭肿了”中,形容词“肿”是状态补语,表示动作或变化所造成的相关的人或物出现的新的状态或动作本身出现的新状态(王红旗不同意用“结果状态”的说法,而用“新状态”代替),因为在“老太太的眼睛哭肿了”中我们可以预设“老太太的眼睛原来不肿”。而在“今天的菜卖贱了”中,“贱”是评价性补语,表示对动作或动作受事、结果的评价。很显然,具有状态补语的动补结构比含有评价补语的动补结构,其使用频率更高,也相对具有核心成员的地位。在“我说累了”这一类结构中如果一定要引进一个宾语,只能创造新的表达形式,即重动结构或动词拷贝,其结构为在同一句子里引进一个宾语和一个补语,如:
(4) 他们打球打累了。
在该构式中,受事名词必须是无定的类属名词(如书、肉、酒、人),不能是“一本书”、“那瓶酒”之类的有定名词。例如下面两句就不能说:
*(5) 他们打一个球打累了。
*(6) 他们打那个球打累了。
根据石毓智(2003)的考察,动词拷贝构式始见于清代的文献中,但崔山桂(2010)认为在明代已开始出现这类构式了。例如:
(7) 子胥,你报冤也报的够了。(《二胥记》)
(8) 不意天黑,有个谋刮棍,吃酒吃得大醉。(《雨花香》)
(9) 宝玉读《西厢记》读得入迷了。(《红楼梦》)
张旺喜(2006:62-64)在考察重动构式时还细分为两个类别:致使性重动构式和描述性重动构式,认为前者表现结果的偏离性,而后者表现动作行为的超常量。同时,他解释其结果的发生均由远距离原因造成,即不是同一事件结构中的直接原因的结果,这与该结构的历史发展是一脉相承的:是VO行为导致VR。
“把”字句作为处置构式与动补结构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刘小玲(2009)认为,“把”在唐代以前基本上是作动词使用,“把”本来是个普通动词,意思为“拿”或“握”,例如:
(9) 白娘子道:“你放心,这个容易。我明日把些银子,你先去赁了间房子却又说话。”(《警世通言》第二十八卷)
(10) 看来子贡初年也是把贫与富庶煞当事了。(《朱子语类》)
(11) 金令史心中好生不乐,把库门锁了,回到公而里。(《警世通言》第十五卷)
唐以后,把字逐渐虚化为介词,例(10)、(11)中的“把”字已经虚化成介词了。前面提到,10世纪后出现的很多句法结构均与受事宾语的位移有密切关系。在VR融合的渐进过程中,受事宾语必须从V和R之间移出,而这时能接受受事宾语只有两个位置——VR之后或VR之前。VR之后当是最佳位置,但条件是VR必须高度融合。如果VR已经融合,但有时不是高度融合,接受受事宾语会受很多语义条件的限制,剩下另一个唯一的选择就是移到VR之前。在谓语动词之前这个位置上的名词即可被看作是施事,也可以被视为受事。这时语言需要创造新的语法标记来有效地区别其语义角色。因此,语义特点适宜的连动构式中的第一个动词反而要丧失独立动词的地位而语法化为标示语义角色的介词,这是现代汉语处置式与被动式产生的直接原因。哪些可分离的动补组合句向重动构式或“把”字构式发展主要取决于受事名词的语义特征。有定名词,尤其是偏正复合名词(如:那个苹果,这栋房子,我的手表等)适合处置构式(吕叔湘1955)。因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把”字句与动补构式的密切关系了。
从上述各类动补构式的历史发展概貌中,我们基本上可以把握的是带宾语类的动结式是原型,带形容词、语法标记词、副词的动补构式属于VR非高度融合的产物,是一个次类。当然,动补构式中的补语还可以由从句承担,如“得”字从句的动构式,“把”字构式与重动构式与单一句型的动补构式相比,在形式上有了较大的改变,尽管其内涵实质表示的是动作与结果的关系。因此,从句结构的动补构式相对于单一句型的动补构式可视为边缘成员。
根据原型范畴理论,我们大致可为动补构式画一个从核心到边缘的连续统(continuum):
VR宾语→VR形容词或语法标记→VR从句
现代汉语的动补构式,尤其是动结构式,标记性明显。如无标记项的使用频率比有标记项的高,至少也一样高。此外无标记项的意义比有标记项的宽泛,或者说有标记的意义包含在无标记项之中。从认知上讲,有标记项比无标记项来得复杂,如“把”字动补构式与重动构式都是两种单句的组合结果,比单一的动结构式的形式与概念复杂。常用的成分不加标记或采用短小的形式,这是出于经济或省力的考虑,这就是常说的“齐夫定律”,Haiman(1985)则称之为“经济动因”(economic motivation)。由一些特征“自然关联”而构成的典型范畴以及范畴的典型成员具有认知上的显著性,它们最容易引起人的注意,在信息处理中最容易被储存和提取,在形成概念的过程中它们也最接近人的期待或预料。
5. 有标记动补构式
朱德熙(1982:128-129)认为V+趋向动词是动补构式的一个小类,如:
(1) 小明走进房间来。
(2) 我举起来一块大石头。
Givón(1991)认为“动作与结果一起表示一个典型的经验过程”。动作的结束需要终点(telic)标示,而动趋式恰恰表示行为动作继续发展的方向。如在“他们走出去”中蕴含“走”的动作行为可能会继续进行下去。石毓智(2003:156-165)认为从历史渊源看,动趋式与可分离式动补组合结构相似,其补语也是出现于受事宾语之后。在动趋式中,补语表示的是程度而非结果,动词与补语的融合程度缓慢,而可分离式动补组合结构在14世纪左右动词与补语已经达到高度融合,但是这个时期的动趋构式中动词与补语之间仍然可以插入其他句法成分,如:
(3) 乃分袂泣别,即遣青衣送出门外。(《搜神记》第十六卷)
(4) 亚父欲急攻下荥阳城,项王不信,不肯听。(《史记.陈丞相世家》)
(5) 夏,郑公子士、泄堵寇帅仕入滑。(《左传.僖公二十年》)
在例(5)中,“堵”与“入滑”之间插入了“寇帅仕”。在现代汉语中,这种用法仍常见,如:
(6) 他传进来一封信。
(7) 他传了一封信进来。
由此可见,动趋式中的动词与趋向补语仍处于融合阶段,还没有达到完全融合,其语法化的路子远远落后于动结式。
另根据张谊生(2001:135-152)的研究,现代汉语中有相当一些副词可以充当补语,可以分为组合型(补语与述谓之间必须使用“得”字),有时也作“的”字与粘合型(补语直接后附于述谓),可表顶级或高级两种程度意义。例如:
(8) 当时,看到其他孩子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走进学堂,我真是羡慕极了。(张克东《童年》)
(9) 皆大欢喜的仇家宝则爱煞了不少妻子和母亲。(皇甫萍《孰是孰非,有观众评说》)
(10) 今儿大水小梅俩结婚,哪一个老百姓的心眼儿里,都喜欢得不成。 (袁静,孔厥《新儿女英雄传》)
(11) 她既会持家又懂规矩,一点也不像二孙媳妇那样把头发烫得烂鸡窝似的,看着心理就闹得慌。(老舍《四世同堂》)
张谊生(2001:151)认为“现代汉语的副词绝大多数都是由古汉语的实词逐渐虚化发展而形成的。总的来说,汉语副词的形成,主要是在谓语前面的状语位置上实现的,但是也应看到,现代汉语中部分副词的虚化是在补语位置上实现的。”这种观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在中古汉语中,VXR这种可分离的动补组合结构存在了相当一段时间,从VXR向VRX漫长的语法化过程中难免有个别补语R就在VXR结构中虚化为副词。
动趋构式总的来说是表示动作与动作行为的继续关系,表示程度,与表示动作与结果的动结构式有很大的语义区别。因此,相对于动结式,动趋式无疑是有标记的动补构式。不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审视,动趋构式与中古汉语的连动构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连动构式的语法化导致了动结构式与动趋构式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因此把动结构式与动趋构式作为无标记与有标记的结构进行对立比较是有充分的历史理据的。
6. 原型与标记的关系
范畴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原型。Rosch(1994:515-517)等人曾考察过大量不同类型的范畴,如感知范畴“颜色”、语义范畴“家具”、生物范畴“女人”、社会范畴的“职业”、政治范畴“民主”、形式范畴“奇数”、临时性范畴“失火时要从房子中拿出的东西”等等。他们从一系列的心理学实验得出结论:任何一个范畴的各个成员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有些成员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更强些,有些则弱些;所有成员在一个范畴中的分布表现出一种趋中性(central tendency),越靠近中心的成员与越多的其他成员享有家族相似性,也越常参与人们的认知活动;处在范畴中心位置的是原型,它或者是一个范畴最具代表性或典型性的现实成员,或者是范畴各成员的抽象,作为衡量其他成员的范畴地位的标准。不仅同一范畴的结构是有等级性的(graded structure),所有范畴构成的范畴系统也是有等级性的。有些范畴是范畴系统的原型,这就是Rosch(1994:518-519)等人提出基本范畴(basic-level categories),与之相对的是上位范畴(superordinate categories)和下属范畴(subordinate categories)。基本范畴是大脑对事物进行最有效分类和组织的层面。在此层面上,大脑的经验范畴与自然界的范畴最为接近、最匹配,人们更容易感知和记忆。基本范畴是认知的重要基点和参照点,以此为基础,范畴向上发展为上位范畴,向下发展为下属范畴。在儿童的认知发展中,原型成员和基本范畴在时间上是最早的,在地位上是最优先的(参看程杰2004)。
在语言问题上,范畴化的原型理论表现为:(1)语言范畴具有原型性,即同一范畴中的语言成分具有不同的认知地位或功能地位,如在时态范畴中,一般现在时态是原型时态,它是儿童在习得母语时最早掌握的时态,是在语言交际中用得最多的时态,也是形式上最简单的时态;(2)语言范畴具有不同的抽象程度,有些范畴是基本范畴,有些则属下属或上位范畴,如在词汇范畴中有基本范畴词、上义词和下义词之分。这样,标记理论中的标记性和原型理论中的原型性就发生了关联。无标记的语言成分是一个语言范畴中的原型成员或基本范畴。从语言和世界的关系看,无标记成分往往指称世界中最具体的事物和身体经验;从儿童语言习得看,无标记语言成分首先被习得和掌握;从语言的进化看,无标记成分在语言系统中出现得最早;从共时的角度看,无标记成分构成了语言最基本的部分;从语言的运用看,无标记成分的使用频率最高;从功能看,无标记成分的搭配、构词等功能最强;从形式看,无标记成分最为简洁,最符合经济原则。可见,语言范畴是以无标记成分为原型,以有标记成分为非原型成员建立起来的,在无标记成分和有标记成分之间存在着一些过渡性成分,语言范畴的边界也是模糊的。Taylor(2001)对语言范畴的研究表明,原型效应在语言中无处不在,标记理论所反映的正是语言范畴的这种原型效应(参看程杰2004;石毓智2006;曲志坚、费丽敏2007;王永祥2008)。
7. 余论
语言中的标记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与人类的认知密切相关,人类认知的一个特点是,对越是熟悉的事物越能感知其内部的差异,越容易分出不同的种类(程杰2004;石毓智2006)。越熟悉的事物,内部成员越多样,结构越简单。越生疏的事物,内部成员越单调,结构越复杂。越是常见或常用的东西我们把它的结构看得越简单,制造得越简单。不懂建筑结构的人会觉得一栋大厦的内部构造非常复杂,而内行则认为不过如此。
在语言问题上,范畴与标记性有密切的关系。现代汉语的动补构式中的源泉要追溯到古代汉语中的连动构式,连动构式中“而”的消亡直接导致中古汉语“可分离动补组合”构式的产生。经过一千多年的语法化历程,现代汉语的动结构式完全建立,与之平衡发展的是动趋构式的建立。动结构式与动趋构式形成了现代汉语的动补构式这个大范畴,但从历史的角度审视,动结构式无疑是这个大范畴中的中心成员。但在动结构式中还可进一步细分更多的次范畴,动趋构式中也还可细分更多的范畴。范畴与范畴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现代汉语动补构式的发展进程有力地揭示了范畴与标记性的密切关系。
Givón, Talmy. 1991. Serial verbs and the mental reality of “event”: Grammatical vs. Cognitive packing [A]. In Hopper & Traugott (eds.).ApproachestoGrammaticalization[J]. Amsterdam: John Benjamin. 81-127.
Goldberg, Adele E. 1995.Construction—AConstructionGrammarApproachtoArgumentStructure[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aiman, J. 1985.NaturalSyntax[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pper, Paul J. & Elizabeth C.Traugott. 1999.Grammaticaliza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angacker, R.W. 1987.FoundationsofCognitiveGrammar[M]. Stand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Rosch, E. 1973. Natural categories [J].CognitivePsychology(4): 328-350.
Rosch, E. 1976. Structural bases of typicality effects [J].JournalofExperimentalPsychology:HumanPerceptionandPerformance(2): 491-502.
Rosch, E. 1994. Categorization [A]. In V. S. Ramachandran (ed.).EncyclopediaofHumanBehavior[C]. New York & London: Academic Press. 513-523.
Taylor, J. R. 2001.LinguisticCategorization:PrototypesinLinguisticTheory[M]. Oxford and Beij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程杰.2004.认知角度下的语言标记性[J].US-ChinaLanguage(1): 69-74.
崔山桂.2010.动词拷贝补说五题[J].聊斋俚曲研究(3):156-66.
蒋绍愚.1999.汉语使动式产生的时代[A].国学研究(第六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78-89.
黄晓琴.2006.试论动结式的三种宾语[J].汉语学报(3):69-72.
李讷、石毓智.1999.动补结构的发展与语法结构的嬗变[J].中国语言学论丛(第2辑):83-100.
李淑康.2010.英语反义形容词标记对立的原型效应[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02.
刘小玲.2009.《警世通言》中“把”字句研究[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高教版)(4):71-72.
刘光正.2006.语言非范畴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陆俭明、马真.1996.形容词作结果补语情况考察[J].汉语学习(1):3-7.
吕叔湘.1955.把字用法的研究[A].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C].北京:商务印书馆.125-44.
梅祖麟.1991.从汉代的“动、杀”“动、死”来看动补结构的发展[J].语言学论丛(第16辑):112-36.
曲志坚、费丽敏.2007.论形容词的标记性[J].外语学刊(2):110-14.
沈家煊.1997.类型学中的标记模式[J].外语教学与研究(1):1-10.
石毓智.2003.现代汉语语法系统的建立[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石毓智.2006.语法的概念基础[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束定芳.2008.认知语义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王红旗.1996.动结式述补结构的语义是什么[J].汉语学习(1):24-27.
王力.1994.中国语法理论[M].北京:中华书局.
王立非.1991a.布拉格学派与标记理论[J].外语研究(1):1-7.
王立非.1991b.关于标记理论[J].外国语(4):30-34.
王立非.1994.英语反义形容词的语义标记研究[J].外语研究(2):9-17.
王立非.2003.语言标记性的诠释与扩展[J].外语学刊(2):87-92.
王永祥.2008.缘何“多少”而非“*多多”[J].外语与外语教学(5):9-12.
徐盛桓.2003.常规关系与句式结构研究[J].外国语(2):8-16.
张建理.1999.标记性和反义词[J].外国语(3):29-33.
张旺喜.2006.汉语句法的认知结构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张谊生.2001.现代汉语副词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
朱德熙.1982.语法讲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
朱德熙.2011.20世纪现代汉语八大家:朱德熙选集[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祝敏彻.1990.《朱子语类》中的动词补语——兼谈动词后缀[A].王力先生纪念论文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240-251.
赵元任.2001.汉语口语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