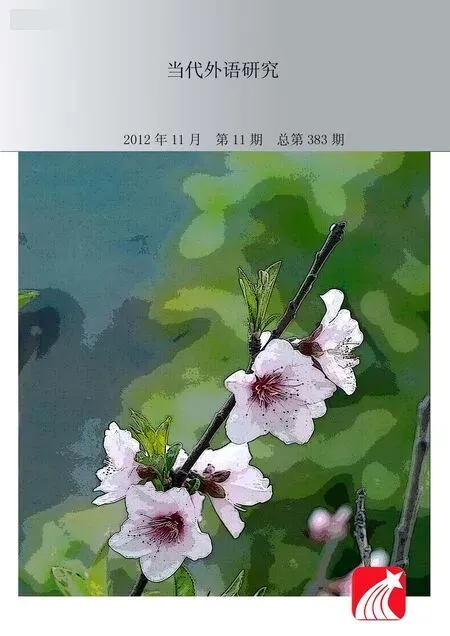教育语言学的学科内涵及研究领域
2012-04-01梅德明
梅德明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200083)
1.引言
教育最重要的手段是语言,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主要交流媒介也是语言。教育通过语言来实施,其内容通过语言来传递,其目的也往往通过语言来实现。教育者研究教育,对教育的研究即教育学;语言教育工作者研究语言、语言教学和语言的使用,对语言、语言教学和语言使用的研究即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对教育者来说,尤其是对从事语言教学的教师来说,语言是一门大学问,而教育的语言和教育过程中的语言使用更是一门大学问。教育学和语言学的结缘,带来的是一门更大的学问。它们关涉教育中的语言发展和语言使用问题,受教育者的语言权利和文化身份问题,语言教学的方法、手段和评价问题,语言学习的认知心理问题,双语及多语教育的社会公平问题,国家语言规划政策与语言生态多样性保护及传承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涉及了语言学、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传播学、法学等,构成了一门超大的学问,这门学问就是教育语言学,这些问题自然也是教育语言学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2.教育语言学的历史渊源
教育语言学源于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其时教育界遇到了一系列涉及语言教育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例如,成人的扫盲教育、教育中的语言障碍、多语交际的表达策略、弱势语言及方言的地位、母语为弱势语言者的社会身份、国家语言教育政策、言语社区与学校的关系、语言习得与语言发展等。
教育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人本主义和实用主义,其社会学基础是现实主义和多元主义,其语言学基础是描写主义和功能主义,而其教育学基础是平等思想和均衡理念。无论其动因如何,教育语言学是以问题为导向,以教育环境及教学过程中的语言学习问题为抓手,核心是研究教育中的语言问题,目的是满足受教育者的语言发展需求,促进受教育者母语能力、双语能力或多语能力的提升和使用。
教育语言学的开创者是一批关注并研究“教育中的语言”的语言学家和语言教育家,代表人物有Bellack(1966)、Halliday(1969,1982)、Halliday,McIntosh和Strevens(1964)、Spolsky(1972,1978)、Hymes(1974)、Wilkinson(1975)、Sinclair和Coulthard(1975)、Widdowson(1979)、Gannon(1980)、Stubbs(1980,1982,1986)、Goodman(1982)、Carter(1982)、Riddle(1982)、Brookes和Hudson(1982)以及Perera(1982)等。其中最杰出的教育语言学思想家和实践者为长期从事语言学、双语教育以及人类学等研究的美国新墨西哥州立大学语言学教授Spolsky。教育语言学(Educational Linguistics)这一学科术语就是他在1972年于哥本哈根举办的第二届应用语言学年会上宣读论文时首次提出来的。若干年后,Spolsky发表了专著《教育语言学导论》(1978),对教育语言学作了较全面的阐述。Spolsky认为,教育语言学隶属语言学,系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如同教育心理学隶属心理学、教育社会学隶属社会学一样,系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分支。他认为,一切涉及语言与教育的问题都是教育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在讨论教育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的关系时,Spolsky认为,教育语言学覆盖了更多的涉及语言的具体问题和实际问题。
当然,这里所说的教育语言学还是比较笼统的概念。事实上,在教育语言学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几大各具特色的学派,主要有“美国派”、“英国派”、“澳洲派”和“双语派”四种。
以Spolsky为代表的美国派体现出研究领域宽广和多样的特点。它以普通语言学的知识为学科基础,借鉴并采用其他社会学科的研究方法,如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研究语言习得的问题、语言使用的问题、教育环境中语言权力与社会地位问题等。
以Stubbs为代表的英国派强调语言学基础地位和核心作用。它坚持以普通语言学的本体理论指导教师教育,倡导以语言学的基本原理指导课程设置和课堂教学,强调教育语言学基于并超于教育学与语言学的科学嫁接;它基于普通语言学,但又强调以应用语言学为先导,同时不局限于语言学。Stubbs(1986)认为,教育语言学是一种“1+X”的理论,其中“1”为普通语言学,“X”为解决教育中实际问题的其他学科(尤其是心理学和社会学)以及多模态综合应用性研究方法,如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
以Halliday为代表的澳洲派立足于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语言为一套源于社会环境、用以表达社会关系的社会符号系统,教育语言学的核心问题是人的社会身份问题和社会关系问题。Halliday(1969,1982)认为,使用语言的人首先是社会人,教育实践本质上属于社会实践。教育双方(即教师和学生)的社会身份和地位,以及受教育者的文化程度和发展是教育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由于地缘和人缘的原因,澳洲派与英国派之间的关系明显浓厚于与美国派的关系。
第四派“双语派”中的“双语”是一个总体概念,含双语言/多语言教育、双方言/多方言教育、外语教育等。教育语言学主要产生于美、英、澳这三个母语为英语的国家,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理论学派。但是,对语言与教育关系的研究,对教育中的语言问题研究,不局限于教育中母语及母语使用问题的研究,也不局限于母语社区的语言、社会、教育问题的研究。其实,上述这些问题在双语或双言社区,尤其是外语社区更为突出。例如新加坡、印度、爱尔兰、阿根廷、比利时,以及我国的港澳地区等,多元文化社会、多种语言社区出现的教育中的语言问题数量更多,关系更复杂。此外,在我国大陆,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迅猛发展,推动着外语需求和外语教育的迅猛发展,尤其是英语教育的迅猛发展。英语这门国际通用语在我国大中小学的教育中的地位显著,得到受教育者前所未有的重视,而从事以外语教育教学理论为核心课题研究的应用语言学更是得到了空前广泛的关注。双语派的研究队伍庞大,全国各地都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
除了以上四大学派,还有国家语言教育政策派。从最近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举办的“亚欧会议语言多样性论坛”的会议主题和发言报告来看,各国的政府机构、各地区的行业组织和学会以及各教育机构的学术团体都对语言发展战略、民族语言生活、语言教育政策及实践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保护和促进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保护和复兴濒危语言和方言,这些努力都为教育语言学的研究带来了新的课题,进而促进具有国家特色、区域特色的教育语言学学派的形成和发展。
教育语言学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学理探索和方法研究的发展,同时也呼唤专业人才培养机制的建立。美国新墨西哥大学的Spolsky教授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Hymes教授于上世纪70年代率先成立了教育语言学研究生学位专业,开设了教育语言学博士学位课程。随后世界各地诸多高校也纷纷推出了教育语言学研究生学位计划、研究方向计划或学位课程,如美国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斯坦福大学、科罗拉多大学和蒙特雷学院,英国的伯明翰大学、曼切斯特大学、兰卡斯特大学、纽卡斯尔大学和沃里克大学。此外,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德国、沙特阿拉伯、泰国也纷纷设立了教育语言学学位计划。国内外更多的大学则将教育语言学的学习融入研究生TESOL/TEFL专业的学位计划或语言政策学的课程体系,如我国的华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和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院。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育语言学学科则成了引领教育语言学研究及学科发展的国际中心。教育语言学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也促进了教材开发和学术著述,其中Spolsky(1978)撰写的《教育语言学导论》和Stubbs(1986)撰写的《教育语言学》被公认为该领域的经典之作。
近年来国际学者发表的其他重要著作还包括Spolsky(1999)主编的《教育语言学简明百科全书》、Hornberger(2001)撰写的《教育语言学的研究领域》、vanLier和Hutt(2003-2012)主编的15卷本《教育语言学丛书》、Spolsky和Hult(2008)主编的《教育语言学手册》、Hult(2010)主编的《教育语言学的走向与愿景》、Hult和King(2011)撰写的《教育语言学的实际应用:区域全球化与全球区域化》、Hornberger(2012)撰写的《教育语言学:语言学要旨》等。
3.教育语言学学科定位的主要观点及述评
目前,语言与教育研究界对教育语言学的学科定位持四种观点:一、教育语言学系教育学与语言学两大学科结缘的“交界学科”(interdisciplinarity)。二、教育语言学系教育学、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相融合的“多界学科”(multidisciplinarity)。三、教育语言学系基于并且超越上述相关学科的“超界学科”(transdisciplinarity)。四、教育语言学系关于外语教学研究的“应用语言学”。
第一种观点明确无误地将教育学和语言学嫁接在一起,凡是涉及语言理论与语言行为的教育学研究与实践,或者凡是涉及教育理论与教育行为的语言学研究与实践,都属于教育语言学。这种观点触及了教育语言学的核心课题,因而针对性强。但是这种“交界学科”论的困难之一是混淆了教育语言学与语言教育学的界限,换言之,我们既可以说它是“教育语言学”,也可以说是“语言教育学”;既可以说它研究的是“教育实践中的语言问题”,也可以说研究的是“语言实践中的教育问题”;学科的落脚点可以是“语言学”,也可以是“教育学”;教育语言学学科既可以设在“教育学”属下,也可以设在“语言学”属下。“既可……又可……”,其结果是“未可”。
第二种观点坚定不移地排除了教育语言学的双学科性,鲜明地表明了教育语言学多界相交的多学科属性。这种观点不仅触及了教育语言学的核心课题,也涉及了主要课题,因而覆盖面强。但是这种“多界学科”论的困难在于其从学理上陷入了“多界即无界”的悖论,“什么都‘可以’”必然“什么都‘可以不了’”;什么都能干,必然无一能干好。
第三种观点“潇洒无比”地突破了前面两种观点的困境,不仅超越了教育学学科和语言学学科,而且也超越了其他学科。可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他人,这样的学科可能已不再是我们所理解的学科了。为了避免教育语言学系“万科之科”的误解,Kjolseth(1978)提出了教育语言学系“多中心、多方法、多层次”的学科的观点,Hornberger(2001)也提出了教育语言学应该是一种“领域宽而焦点窄”的学科的观点。本文认为,“领域宽而焦点窄”的表述只是一种关于教育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论,不能视为对教育语言学的学科定位,因为这回答不了教育语言学的学科属性和内涵。任何学科的科学研究(即使是哲学研究)都提倡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用通俗的话表述,小处着眼,大处着手,如同用芝麻去砸太阳,没有人会这样干;大处着眼,大处着手,如同驾驭火星去砸金星,傻人会这样干;小处着眼,小处着手,如同赶着蚂蚁赛跑,闲人也不愿意干。因此,“领域宽而焦点窄”的观点虽然在研究方法上是十分正确了,但其没有从学理上回答教育语言学的学科定位问题。
第四种观点将教育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等同起来,甚至认为它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这种观点得到了相当大的支持。某种程度,这恰如其分地概括了我国部分教育语言学倡导者和研究人员对这一学科的基本认识。例如,我国有一个隶属于“中国修辞学会”的二级学会“中国教育语言学研究会”,2010年5月22日于上海成立。2011年5月这个学会举办的第二届年会的主题是“以内容为依托的外语教学模式探索”,三项议题为“我国英语专业以内容为依托的教学模式(CBI)研究”、“我国大学英语教学语境下的特别用途英语教学(ESP)探索”、“关于大学阶段英语教学新思路的探索”。会议认为,大会的主题“充分反映和体现了外语教学法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不是一次普通的教学研讨,它更加关注外语教育未来发展的方向”。2012年4月举办的第三届年会则以“中国外语专业以学科为依托的教学模式(DBI)研究”、“基于学科的中国大学英语教学新理念探索”、“全球背景下的中国专门用途英语/俄语教学”为主要议题,继续将外语教学研究视为“教育语言学”的核心思想和主要课题。由于将外语教学研究视为“教育语言学研究会”的主要使命,无怪乎有人提出应该将此学会纳入或者隶属“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其会刊的刊名为“中国应用语言学”)。
将教育语言学等同于外语教学的观点在我国有相当的影响力和历史渊源。早在1996年张国扬和朱亚夫就提出了“教育语言学”即“外语教育语言学”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预设了“母语教育语言学”、“方言教育语言学”、“标准语教育语言学”、“双语及多语教育语言学”等概念的存在。而且“教育语言学”是否等同于“外语教育语言学”,这是值得商榷的。从半个世纪以来国际教育语言学界及相关学者的研究来看,外语教育研究可隶属于教育语言学的研究范畴,但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也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非全部。
从常理和学理两方面看,将教育语言学等同于应用语言学的观点也不足取。教育语言学是教育视角下的语言(这里的“语言”包括但不局限于外语)研究,而不是单一的外语教育研究。即使是以外语教学研究为主要使命的应用语言学也有自己学科定位,不可能成为教育语言学的替身,或等同于教育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的内涵丰富,研究范围广泛,从学界目前形成的共识来看,它至少涵盖两方面的研究:
第一,将语言学的理论和知识应用于解决其他科学领域各种问题的研究。除语言的教学外,还包括辞书编纂、创立和改革文字、失语症和言语病理、机器翻译、情报检索等一些与语言有关的领域。
第二,语言教学,尤其是外语教学的研究。例如,于1975、1978和1981年举行的国际应用语言学年会特别强调,应用语言学主要涉及语言教学,其中包括母语教学、第二语言教学和外语教学。此后举办的历届国际应用语言学研讨会议题中,外语教学研究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4.教育语言学学科的独立地位与核心内涵
本文关于教育语言学学科定位的观点是:教育语言学就是教育语言学,其学科范畴及内涵既不多也不少,既不增也不减,既不越界也不封界,既有核心也有边界。
教育语言学的核心是受教育者的语言权利和语言发展,它研究的根本问题是人的教育问题和人的发展问题。因而,教育语言学始终是以人为本,以受教育者为本,既是研究语言问题,也必须以人的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形式上是研究语言问题,实质上是研究受教育者的发展问题。
教育语言学源于教育学和语言学,因此学科基础就是教育学和语言学。教育语言学的边界是与其结缘学科的相关课题,如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民族学、区域学、经济学、传播学、法学等。教育语言学的主要课题为三大类:(1)基于教育的语言发展和语言使用问题;(2)学校环境中的语言教学(含外语教学)问题;(3)语言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问题。
换言之,教育语言学是一门不可替代的独立学科,也是一门课题明确的自立学科,既不借帆出航,也不随风漂游。当然,教育语言学与其相关学科接缘的特质决定了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带有多学科的标记,但是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并不表明教育语言学是一门既无目标又无定力的附庸学科。Kjolseth(1978)关于教育语言学的“多中心、多方法、多层次”的观点是有问题的。教育语言学的研究确实可以采用多种方法并以多层面的方式展开,但其研究绝不可能是多中心的。多中心则意味着无中心。教育语言学研究的问题多种多样,问题的多样性自然需要研究者以多种方法、多种途径加以解决,但教育语言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依然是与教育相关的语言问题以及语言教育问题。教育语言学的研究领域是宽广的,研究问题也有相当的深度,其宽广度是由教育语言学的工作范畴决定的,其深度是由教育语言学与各相关接缘学科的专业知识及其应用决定的。教育语言学家在各自的研究工作中采用不同的方法,有的关注宏观问题,有的关注微观问题,也有的关注介于两者之间的中观问题。无论是宏观、微观还是中观,关注的出发点、立足点、聚焦点始终是学生的语言发展问题,始终是教师的语言教育问题,始终是语言与教育的问题,归根结底也是人与社会的发展问题。
如前所述,教育语言学的研究涉及教育学、语言学、人类学、民族学、区域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传播学、法学等学科,这种融合相关学科的研究自然也为教育语言学家创造新的学术范式和研究方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教育语言学的研究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而实际问题的解决反过来又可促进问题的研究,课题研究和解决问题互为条件,互为因果、反哺共进。教育语言学的研究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理论问题或增加学术知识,更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实际问题的解决需要理论指导,进而用以指导实践。教育语言学研究者不是在书斋中闭门思过,闭门造车,主观臆想,自说自话;教育语言学研究的问题基于实际,源自实践,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具有实际意义。
语言学理论层出不穷,学术流派众多,论说精彩纷呈。从功能派到生成派,不同的理论对教育和教师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对语言及语言学进行了解可以使教师从理论和实际两方面意识到并充分利用学生、家庭、社会带到学校的各种语言资源和文化资源,更好地将所知的语言学、教育学等知识付诸教学实践。
5.基于教育语言学学科内涵的研究领域及课题展望
教育语言学的起点是教育中的语言教学,尤其是关注语言教育中出现的问题,学科领域已突破语言学本身,深入至教育学并延伸至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民族学、认知科学、法学等学科,从这些与语言学和教育学结缘的学科中寻求答案。
Hornberger(2001)认为,教育语言学的研究领域有三大特点:一是教育与语言的融合,探讨语言学对于教育的意义以及教育对于语言学的意义;二是以问题为导向,以教育实际为出发点;三是聚焦语言教学与语言学习。Hornberger把教育语言学的研究范围也分为三大类:一是研究语言行为与社会网络、文化身份之间的关系;二是研究课堂二语、外语、双语的学习及交际环境;三是研究双语及多语社区与学校。而Halliday(2001)认为,“教育语言学最具有超学科特性,它既不是教育学与语言学的交叉点,也不是语言学的分支。”
本文基本认同以上学者关于教育语言学具有“跨域”特性的观点,但不同意他(她)们的“超域”的论断。“超域”论在逻辑上讲不通,在学理上理不清,在实践中也行不通。任何一个学科必须有学科自身的中心和界限,倘若“超越了学科”,那么这个学科也就不成其为学科。若没有学科中心和学科界限,学科赖以存在的基础也就不复存在。一个学科既不可能超越自身,也不可能超越他人。超越了自身,也就失去了自我;超越了他人,也就失去了自我存在的必要。学科间的接缘和结缘、学科间的渗透和交融,既不是为了失去自我,更不是为了湮灭他人。我们要解开“科学即学科、学科即分科”的“科学主义”死结,借鉴“阴阳则相依、五行亦相存”的整体主义哲学观。“请不要走在我的前面,因为我跟不上你;请不要走在我的后面,因为我领导不了你;请走在我的身边,因为我们互为依存。”
教育语言学是研究“教育中语言”及“与语言相关的教育”的学科,它的学科内涵决定了“语言教育”必定成为其主要研究领域。囊括的领域包括:(1)语言教育政策,如国家语言政策与规划、语言发展战略等;(2)语言教育与个人发展,如受教育者的社会文化身份认同、学科知识学习和应用等;(3)语言教育与文化传承,如多民族国家的语言多样性发展、濒危语言和方言保护等;(4)语言教育与教师发展,如教师的语言意识、元语言知识、语言教育观、语言教学能力和运用能力等;(5)语言教育与课程建设,如学校的教育理念、培养目标、教学原则、课程设置、课程方案、教学方法、评价手段等。
教育语言学研究的主要课题包括:(1)语言生态系统与语言多模态体现;(2)少数民族儿童的教育平等和均衡发展;(3)语言多样性发展与弱势语言保护;(4)国家语言政策与课堂教学体现;(5)受教育者的语言身份与语言权利;(6)双语或多语教育与课程设置;(7)语言习得与语言教学和评估;(8)教育过程中的话语分析与教学应用;(9)受教育者表达能力发展与读写能力发展
这些研究领域及课题所涉及的问题是多样性的,例如:(1)双语教育所涉及的课堂的语言意识、课堂教学用语的确定、语言测试和评估方法等;(2)国家语言政策所涉及的语言教育政策和通用语言使用政策、少数民族的母语权利、双语及多语教育中的意识形态、教师的语言决策权及其使用规范等;(3)语言生态所涉及的多语地区的弱势语言保护和发展、濒危土著语言的复兴、通用语言与本地语言之间的冲突、移民语言的弱势地位、双语及多语间的翻译等;(4)语言身份所涉及的受教育者的社会身份和交际风格、双语者的语言社区归属感和双重语言及文化身份的冲突、侨民及其子女的母语保护和使用、双语社区的语码混用与语言转换困难等问题。
我们对新时期我国教育语言学的研究课题还有如下展望:(1)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及国际化人才培养过程中的英语教育政策和课程指导;(2)我国多民族语言教育政策的实施与语言及文化多样性的维护;(3)濒危少数民族语言及相关非物质遗产的拯救和传承;(4)汉语方言及相关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和传承;(5)世界范围内汉语的教育及中华文化的传播;(6)我国教育工作者的语言意识、语言心智、语言能力、语言学知识、教学语言技能等。
6.余论
教育语言学是一门融教育学和语言学为一体并与多学科接缘的独立学科,有明确的研究主体、研究课题和教育计划。它以人为本,立足人的全面发展,基于人的语言权利,以问题为导向,关切具体主题和具体情景,以跨学科的广角视野,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用各种可支配的教育资源,解决教育的语言问题和语言的教育问题。以教育语言学的视域来看,语言是权利,语言是课题,语言是资源;教师具有语言教育者和语言决策者的双重身份。
教育语言学重视科研与实践相长,重视研究与实践的反哺关系,它们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相互促进。教育语言学研究不仅仅是为了增加学术知识或社会知识,而是研究和解决语言教育中某个方面的实际问题。但是研究和实践是双向性的,教育实践也常可以促进科学研究。在教育语言学的研究中,研究的主题不是研究者大脑的产物,研究课题不是空对空。教育语言学的研究课题源自研究者的实践,是实际问题,具有实际意义。
与其他学科的紧密结缘确实是教育语言学的核心特征,着手解决具体问题的教育语言学确实也从其他相关学科寻求解决问题的指导理论和具体方法(Spolsky 1978),但是教育语言学还未建立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协调的知识体系。虽然教育语言学家有着共同的目标和明确的社会责任,但是从整体上看,教育语言学还缺乏明确的行动路线,还未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就教育与语言、人与社会、母语地位与双语需求、国家统一性与语言多样性等关键课题及其关系编织一套自成体系的整体联系。
近年来生态学研究成果及其发展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参考。生态学的理论是一种网状的、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整体观,以生态平衡、均衡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实质是以位于生物链顶端的人类的长期利益为本。
虽然生态学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并非新颖,但它在教育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性日益显现。人们在研究教育语言学的所有问题时,无论是研究个人的语言习得,还是国家的语言政策,还是具体的课堂教学法,人们越来越多地采取生态学的研究方法。例如,Leather和van Dam(2003)收集了研究影响语言习得的各种复杂情景因素的文章。Hornberger(2003)讨论了双语及或多语教育计划在构建、执行和评价方面的各种复杂因素,以及综合各种分析方法的价值。这些报告表明,任何孤立地研究涉及语言与教育的问题都无法奏效。报告还表明,在教育语言学的研究中所采用的生态学研究方法也是以问题为导向,并以整体观的视野解决结缘学科产生的各种问题。正是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预测生态学研究方法将在未来的教育语言学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
Bellack, A.A., H.M.Kliebard, R.T.Hyman & F.L.Smith.1966.TheLanguageoftheClassroomTeachers[M].New York: College Press, Columbia University.
Brookes, A.& R.Hudson.1982.Do linguists have anything to say to teachers?[A].In R.Carter (ed.).LinguisticsandtheTeacher[C].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52-74.
Carter, R.1982.LinguisticsandtheTeacher[M].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Gannon, P.& P.Czerniewska.1980.UsingLinguistics:AnEducationalFocus[M].London: Edward Arnold.
Goodman, K.1982.LanguageandLiteracy[M].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Halliday, M.A.K.1969.Relevant models of language[J].EducationalReview22: 26-37.
Halliday, M.A.K.1982.Linguistics in teacher education[A].In R.Carter (ed.).LinguisticsandtheTeacher[C].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10-15.
Halliday, M.A.K.2001.New ways of meaning: The challenges to applied linguistics[J].JournalofAppliedLinguistics(6): 7-36.
Halliday, M.A.K., A.McIntosh & P.Strevens.1964.TheLinguisticSciencesandLanguageTeaching[M].London: Longman.
Hornberger N.H.2012.EducationalLinguistics:CriticalConceptsinLinguistics[M].London: Routledge
Hornberger, N.H.(ed.).2003.ContinuaofBiliteracy:AnEcologicalFrameworkforEducationalPolicy,Research,andPracticeinMultilingualSettings[C].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Hornberger, N.H.2001.Educational linguistics as a field: A view from Penn’s program on the occasion of its 25th anniversary[J].WorkingPapersinEducationalLinguistics17: 1-2, 1-26.
Hult, F.M.& K.A.King.2011.EducationalLinguisticsinPractice:ApplyingtheLocalGloballyandtheGlobalLocally[M].Clevedon, Avon: Multilingual Matters.
Hult, F.M.2010.DirectionsandProspectsforEducationalLinguistics[M].New York: Springer.
Hymes, D.H.1974.FoundationsinSociolinguistics:AnEthnographicApproach[M].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Kjolseth, R.1978.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and its social implications[A].In J.A.Fishman (ed.).AdvancesintheStudyofSocietalMultilingualism[C].The Hague: Mouton.799-825.
Leather, J.& J.van Dam (eds.).2003.EcologyofLanguageAcquisition[C].Dordrecht: Kluwer.
Perera, K.1982.The language demands of school learning[A].In R.Carter (ed.).LinguisticsandtheTeacher[C].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114-36.
Riddle, M.1982.Linguistics for education[A].In R.Carter (ed.).LinguisticsandtheTeacher[C].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31-51.
Sinclair, J.M.& R.M.Coulthard.1975.TowardsanAnalysisofDiscourse:TheEnglishUsedbyTeachersandPupils[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inclair, J.McH.1982.Linguistics and the teacher[A].In R.Carter (ed.).LinguisticsandtheTeacher[C].London: Routledge and Keagan Paul.16-30.
Spolsky, B.(ed.).1999.ConciseEncyclopediaofEducationalLinguistics[C].Amsterdam: Elsevier Science Ltd.Pergamon.
Spolsky, B.1978.EducationalLinguistics:AnIntroduction[M].Rowley, MA: Newbury House.
Spolsky, B., & F.M.Hult (ed.).2008.TheHandbookofEducationalLinguistic[C].Malden, MA: Blackwell.
Stubbs, M.1980.LanguageandLiteracy:TheSocialLinguisticsofReadingandWriting[M].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Stubbs, M.1982.Language,SchoolandClassroom[M].London: Methuen.
Stubbs, M.1986.EducationalLinguistics[M].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van Lier, L.& M.F.Hutt.2003-2012.Educationallinguisticsbookseries[C].New York: Springer.
van Lier, L.1994.Educational linguistics: Field and project[A].In J.E.Alatis (ed.).GeorgetownUniversityRoundTableonLanguagesandLinguistics[C].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199-209.
Widdowson, H.G.1979.Linguistic insights and language teaching principles[A].In H.G.Widdowson (ed.).ExplorationsinAppliedLinguistics[C].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15-33.
Wilkinson, R.1975.LanguageandEducation[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张国扬、朱亚夫.1996.外语教育语言学漫谈[J].广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6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