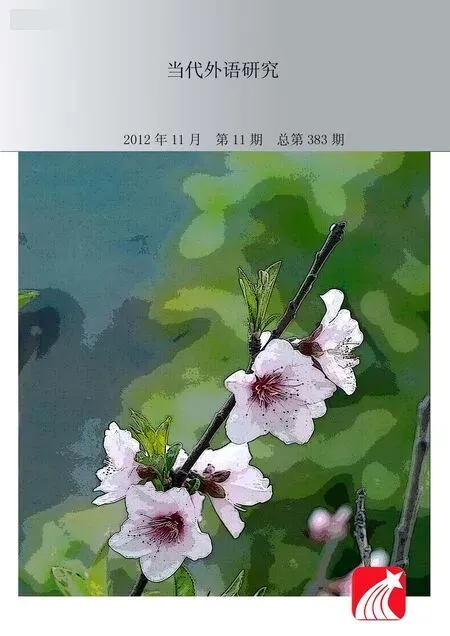“N1死了N2”构式的语用解释
——兼评移位观、话题观和糅合观
2012-04-01侯国金
侯国金
(四川外语学院,重庆,400031)
1.引言
(1) 王冕死了父亲。
在例1这样的“N1死了N2”构式里,“死”这个不及物动词或“一元动词”何以后接名词呢?这个N2为什么能是“父亲”而不能是“朋友”?该构式既然可以用“死”却为何不能用“病”呢?从上个世纪50年代至今,汉语界对此有不少讨论了。“词汇操作规则”(允许在动词的论元结构中添加一个题元角色)解释不通,“配价语法”(提出“变价”或“增价”)也解释不通(沈家煊2006)。
2.移位观和话题观
句法解释有两种“移位观”和一种“话题观”。徐杰(1999,2001)和韩景泉(2000)用领有名词的移位来解释例1的生成。其潜在的基础结构(深层结构)为:语句S由空位的NP和VP构成。VP是由V(“死了”)和NP构成:这个NP又是由NP(“王冕(的)”)和N(“父亲”)构成的。也就是说“王冕”是从动词“死”后的逻辑宾语移位到主语的位置。可是,“王冕”为何移位呢?寻求赋格?“非宾格动词”“死”不能给自己的宾语(姑且称为宾语)赋予宾格。“王冕的父亲”也不能获得“部分格”或固有格。那么,移位的好处是使自身获得主格,还使保留下来的宾语“父亲”(不再有定)获得部分格①。
朱行帆(2005)则用核心动词“死”的移位来解释该句的生成。其基础结构为:
[vp 王冕EXPERIENCE [vp 父亲死了]]
其中有一个没有语音形式的轻动词EXPERIENCE(简化为EXP,意为“经历”),由它向作标志语的“王冕”指派一个域外题元角色“经历者”,而VP“父亲死了”是这个轻动词的补足语。这一基础结构体现出“王冕经历了父亲去世这件事”这个意思。句子的生成方式是核心动词“死”向上移位并和EXP合并(merge,也称“合拼”)。可是,核心动词的移位有什么动因呢?沈家煊(2006)通过比较例1和例2,而且假设后者的基础结构和前者相同,从而质疑两者的“死”一个要移位而另一个不用移位的原因。再者,设定EXP类轻动词的结果是:(1)生成许多不合法语句的可能性,如:“王冕经历了父亲生病这件事”并不能说成类似例1的“王冕病了父亲”,“王冕经历了母亲改嫁这件事”也不能说成“王冕改嫁了母亲”;(2)排除合法语句的可能性。如“死了一个人”,轻动词(这里应为OCCUR,指“发生”)所能指派的域外题元角色没有任何论元可指派,从而违反了“题元准则”(theta-criterion)。有趣的是,胡建华(2008)发展了上述移位观,只是改EXP为抽象动词“有”,即“有”与V(P)“合拼”,又因为“有”跟“了”的相似性(比较“V了”和“有V”),生出例1类语句,意思是“对于王冕来说,存在着一个‘死父亲’的事件”。不同的是,胡建华试图引进语义的内容,称之为“句法和信息接口”。
(2) 王冕,父亲死了。(沈家煊2006)
潘海华、韩景泉(2005)认为,例1的“王冕”不是一般意义的主语,而是“话题”。它跟移位无关,是“在原位由基础生成的(base-generated)”(转引自沈家煊2006):
[CP 王冕 死了父亲]]]
“王冕”位于标句词组CP的指示语位置,而位于小句TP的指示语位置的主语却是空位e。由于主语空位在汉语里并不罕见,而“基础生成的话题不会改变动词的论元结构,所以不会有‘词汇操作规则’增添论元的问题”(同上)——因为汉语是“话题突出”(topic-prominent)型语言。话题观的问题存在于例1的“父亲”。他们认为非宾格动词“死”赋予“父亲”以主格。沈先生说,话题观比移位观进了一步,可是例2类语句又作何解释?
“死”类“非宾格结构为深层无主语句”(同上)。上例“父亲”在深层一定是动词后的逻辑宾语,只有移位才会造成它“出现在动词前空位主语的位置”(同上)。按他们对“N1死了N2”构式的解释,这里的逻辑宾语“父亲”要获得主格是不需要移位的。若解释说“父亲”移位是为了通过定指性特征[D]的核查(主语位置吸纳定指的名词短语)也是牵强的。例3和例4类语句的存在,证明主语位置不必吸纳定指名词短语。倘若说例2主语“父亲”跟话题“王冕”一样也是基础生成的(“父亲”为主格),就跟他们对例5的解释矛盾了:他们认为该例的“死”由于不能给深层逻辑宾语赋以宾格,“王冕的父亲”就只好移位到主语位置从而获得主格地位(于是有例5)。
(3) 王冕,一个亲人死了。
(4) 王冕死了他的养父。
(5) 王冕的父亲死了。
能否说例5的“王冕的父亲”是移位生成而例2的“父亲”就是基础生成的?而假设例5类语句也是基础生成的,就否定了“死”类“非宾格动词”深层无主语的特点,也推翻了“Burzio定律”(Burzio’s Generalization)②。顺便提一下胡建华(2008)的“定指前移观”和刘探宙(2009)的“焦点后移观”。两人的观点是句法-语用移位观,有合理成分,也有不合理成分(参见沈家煊2009)。
3.糅合观
沈家煊(2006)基于对移位观和话题观的批评,提出了“糅合观”——其理论基础是“构式语法”。“糅合”(blending)是“一种基本的认知操作,不限于语言,也包括思维和行为”。“糅合”能产生“浮现意义”(emergent meaning),这类句子“因此而丧失/获得”的意义就是糅合所产生的浮现意义③。沈先生有很多例子,主要是造词方面的糅合。如:“推介”是“推广”和“介绍”的糅合,“建构”是“建立”和“构造”的糅合。他的意思是,“糅合不仅是造词的重要方式,也是造句的重要方式”。那么,例1(=6xb)是如何糅合的呢?他认为是例5(=6x)和6b的糅合:
(6) a.王冕的某物丢了 b.王冕丢了某物
x.王冕的父亲死了 y.____
xb 王冕死了父亲
其大意是:本无“N1死了N2”构式,即y项为空缺,“生出这种创新说法之后,就形成a:b::x:y的格局”。y是x和b“糅合的产物”:b项截取的是它的结构框架,x项截取的是它的词项。因此,他称之为“类推糅合”,换言之,y是在x的基础上按照a和b的关系特别是参照b“类推”出来的。b这个“类推源项”里的“某物”是谓词的宾语和受事,而类推所得的y项里的“父亲”碰巧也是宾语和受事,“至少带有宾语和受事的性质”。另外,他说,在例6中,x和b两项之间有“前因后果”的联系,因此这种糅合也可以叫“因果糅合”。换言之,例1是用“因”来转指“果”,是用“父亲的死”来转指“失去父亲”。
(7) 王冕的父亲死了(因)+王冕失去了某物(果)→王冕死了父亲
4.各观质疑
我们先借用沈家煊(2006)的一些批评意见。句法或生成语法角度的“N1死了N2”构式分析或解释“没有达到理论内部的‘自洽’”。问题出在“小看了不同表层结构之间的差异”。沈先生认为,不论是徐杰的“移位观”(领有名词“王冕”移位),还是朱行帆的“移位观”(核心动词“死”移位),或是潘海华、韩景泉的“深层主格观”(没有移位),都有缺陷。徐杰小看了例1和例5的差别,朱行帆小看了“王冕经历了父亲的死”和例1的差别④,潘海华和韩景泉小看了例1和例2的差别。总之,沈先生认为,“N1死了N2”构式不是由“王冕”或“死”移位而派生,“父亲”也不是主语格。例1跟相关或类似语句属于不同的构式,构式不同,意义亦不同。他认为在例1中“父亲”身处动词之后当然算宾格而非主格,“至少是带有一部分宾语格的性质”,“语义上带有受事的性质”。例1类表“丧失”义,相比之下,例5和例2只表“王冕的父亲去世这一事实”。石毓智(2007)补充说,移位观“缺乏客观的标准来确立一个表层结构的基础形式”,“即使在同一框架里工作,不同学者的观点(也)针锋相对”,“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无法保证其结论的可靠性”。笔者基本赞同,并认为他们的句法解释虽然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我们到底应该相信轻动词“EXPERIENCE”、“OCCUR”还是“有”?其实每句话都可以说是深藏一个轻动词,这三个似乎都行:不是直接的“经历、发生、有”,就是间接的。
沈先生从认知、构式、语义的角度给予“N1死了N2”构式以新的解释,有自身的道理。语义相关、形式相近的构式,自然存在某种联系,若说某甲构式是基础构式,乙构式是派生构式,并通过类比而派生,想必不会有任何人反对,因为这是符合语感和常识的。然而,基础句是如何选定的?类比是必需的还是或然的?类比是如何生成的?“类推源项”b又是如何选定的?他说b的选定“并不是随意的”。于是他解释了所谓的6步“类推糅合过程”。其解释只是再现了汉语人的语感。“之所以选定b作为类推源项,首先是因为b能表达‘受损’”。非“受损”义的,绝非选择对象。不过,正如他所说,“然而不是凡是有受损义的表达式都能被选定为b,比如‘王冕被人抢了’显然也是表达王冕受损,但是不能选定为b”。于是他说,“选定b是因为有和b在意义和形式上都‘相关’的,又有和a在意义和形式上都‘相似’的x”。他得出的“倾向性预测”是:x和b之间越是容易建立某种概念上的重要联系,两者就越容易发生糅合。如果一种语言里‘王冕病了父亲’(相当于例13)成立,那么例1也一定成立,反之则不然。这当然是对的,因为符合语感。其“糅合观”正确地指出了,例1“父亲”既然在动词之后当然应该算宾格,“至少是带有一部分宾语格的性质”,“语义上带有受事的性质”。例1类表“丧失”义,相比之下,例5“王冕的父亲死了”和例2“王冕,父亲死了”只表“王冕的父亲去世这一事实”。沈家煊(2009)坚持旧观,且说例1(及其所属构式)是主观的“计较得失”(而非客观的“计量得失”)。
“糅合观”是对“N1死了N2”构式的一种有意义的新解释,至少是对句法解释的补充。不过,简单再现语感的说明不足以解释“N1死了N2”构式的生成机制。另外,以类比构词来“类比”造句,能有多少类比度?类比造句能解释语义和形式相近或相关的语句么?至少“构造新词的方式不能作为‘造句方式’的证据”(石毓智2007)。语义相近或相关的语句未必是互相类比(或甲从乙类比)而生的。最后,别说以“糅合观”来解释例1类语句的解释力如何,单说糅合造词或造句,就有不少值得研究的问题。为什么糅合?如何糅合?浮现意义何以得之?按他的话说,“糅合要受哪些方面的制约?”石毓智认为“糅合观”“明显与历史事实相悖”⑤。胡建华(2008)认为“糅合观”“所使用的糅合造句的句法框架仍然过于具体”,其解释或者说其对类似语句的预测不是“过强”就是“过弱”,过强则排除了合法(具有良构性)语句(如例13c),过弱则无法排除非法(不合语法的)语句(如例13b)。
5.从构式压制到语用压制
“压制”(coercion),一般是“构式压制”或“语义压制”的简称。在构式语法里(如Goldberg 1995,2006;Croft 2001;Michaelis 2003),“压制”指的是:当构式义与词汇义似乎冲突导致语义异常时,根据“压制原则”(override principle,也译“凌驾原则、控制原则”),构式义(处于“强势位置”)就会压制词汇义从而消解冲突并生成新的词汇义。也即,某个词项若与所在的句法环境出现不兼容的状态时,该词项以丧失部分词义来服从所属句法结构的大局。称为“构式压制”强调的是构式对词义的压迫和制约作用(因),称为“语义压制”强调的是所获得的崭新(临时)词义(果),即“浮现意义”(ad hoc/emergent meaning)。“压制”一词在认知语言学领域一时成为时髦词,连计算机科学也引为己用,指“一个实体与句法环境所要求的另一与之相关的实体之间的一种映射过程”(Ziegeler 2007:991)。我们看来自Goldberg(1995:153)的经典例子(斜体为笔者所添):
(8) Franksneezedthe tissue off the table.
(9) Theylaughedthe poor guy out of the room.
例8中的sneeze本是一元动词,在该构式里压制而“变价”成为三元动词,其中包括末尾的表方向的介宾短语。实际上,该构式只要有第二个论元,就必然有第三个论元。也可以说,sneeze历经词义派生(derivation)或“论元增容”(argument augmentation)的过程(袁毓林2004)。同样,例9中,laugh也是一元动词,用作三元动词,末尾的论元也是不可或缺的表方向的介宾短语。“句式的力量要大于动词的力量”(沈家煊2009),两例的动词受句式的压制而分别获得了“打喷嚏把某物喷到某处、大笑/嘲笑某人把他/她笑出了某处”的构式义(迁移义)。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汉语的“N1死了N2”构式,“VI+N”构式,“很N”构式,“被N”构式,“爱V不V”构式,“爱谁谁”构式,“还NP呢”构式,等等,都是此种压制的结果。
Goldberg(2006:22)说,“生成语句的不是语法而是言者”,此乃语用观。但是构式语法家笔下的“语用”都是不彻底的“语用”。这里补充以“语用压制”(pragmatic coercion)⑥——语境因素和语用目的导致构式偏离(deviation)或语义偏离的现象,就是构式或语义的“陌生化”(estrangement)。“偏离”什么?言者偏离正常的表达途径,听者偏离正常的解读途径。例1以及上述构式压制的例子都是如此。而且言者有时假装没有偏离而实际上已经偏离,听者不得不进入“花园路径”(garden path)从而进行“二次思考”(second thinking)或再思,以便得到充分的语(用)效(果)。
王寅(2011:353-79)所列举的“体压制、时压制、句式压制、状语压制、惯性压制、仿拟压制、选显压制、语义压制”等,无一不是“语用压制”。笔者区分了广义和狭义的语用压制。前者是“在语用原则(合作原则、关联原则、最省力原则、幽默原则、礼貌原则、调侃原则等)的支配下,选择一定的语用参数(交际者、语境、意图、行为、含义),对相关的社会语用手段或语用语言手段所实施的关联调变”,后者则是“语用者宏观上在某个/些语用原则的统辖下,微观上在某个/些语用参数的支配下,对言语手段(如语音、语法、语义等)进行一定的关联调变”。本文在讨论实体构式时取狭义定义。
让我们回到“N1死了N2”这一“部分图式性构式”(partial schematic construction)。本文开头对例1的疑问,如“死”这个不及物动词或“一元动词”怎么能接名词呢?这个N2为何不能是“朋友、同学、陌生人”呢?笔者发现已经存在认知构式语法的“传承压制观”,如袁毓林(2004)和帅志嵩(2008)。袁毓林认为,“死”是套用了二价及物动词“丧”的用法,由于受到表达精细化(elaboration)的语用驱动,动词迁就句式,即句式压制动词,而产生该构式(的用法)。帅志嵩则历时地考察了“死、丧、亡”和例1类语句,发现该构式产生的“动因是语义演变”。他先区分了两种句式,即甲式:N+V+N,乙式:N+V。他认为,“丧”用于甲式衍生出“死亡”义,而“死、丧、亡”在乙式是同义字,这就驱动了“亡、死”用于甲式。再者,由于“死”的使用频率远高于“丧”和“亡”,三个字的竞争以“死”的胜利告终——此时的“死”当然继承了“丧”用于甲式的“句法功能”。他发现,“死了N”或者说例1,再或者说“N1死了N2”构式,产生于晚唐五代时期的《敦煌变文》,到清代的《儒林外史》已较普遍。
在我们的语用压制观看来,例1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语用压制。制约它的是压制原则和更上一级的(可)表达性原则、最省力原则、关联原则和生动原则。
(10) 王冕弄死了父亲。
从语义上看,例1跟例5“王冕的父亲死了”接近,但是从结构上看,例1跟例2接近。仔细观察不难发现,例5和例10的语义都不是言语者的意思,或者说,距离言语者的“语用意义”(pragmatic meaning)(或“话语意义”(utterance meaning),“说话人意义”(speaker’s meaning))都有一定距离。这一点可从功能语言学的句子功能观(functional sentence perspective)得到部分解释。例1的主位是“王冕”,例5的主位却是其“父亲”,也就是说在语篇里起到的话题意义⑦的作用是很不相同的。例1指向的“王冕”,例5指向的是其“父亲”,只是借“王冕”(一定的关联性)来说事。例10的主位虽等同于例1,但是述位部分的意义却迥异。例1的述位意义是损失义,即“(小小的)王冕失去了父亲(从而不得不靠母亲一人抚养和教育或独立生活)”。例10的述位意义则是“王冕是直接或间接杀死父亲的凶手”。话语(尤其是主题句)对语篇构建往往能起到主题指向性(thematic orientation)的作用。例1所在语篇可能说的是“王冕”如何艰难地成长,而例9所在的语篇可能说的是“王冕”恶贯满盈。再请看例2“王冕,父亲死了”。跟例1一样,例2的主位是“王冕”,不同的是,该句有一个次主位,即二级主位,即“(他的)父亲”。其主题指向性基本同例1,区别在于读者能接受少数语句用来简介这个次主位“父亲”。请注意,例2跟例5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逗号而一个是“的”。当然功能完全不同:例2的主位是“王冕”,而例5的主位是“王冕的父亲”。
那么,例1的一元动词“死”何以后接一个以上的论元?既然上述解释似乎都有问题,语用压制又作何解释呢?
由于汉语的默认表达式是例5“王冕的父亲死了”和例10“王冕弄死了父亲”,而它们都不能表达言语者的意思,于是采用构式偏离和语义偏离:以例1的构式达到“死”的词义偏离,也即该构式中的“死”不是一元动词,不是不及物动词,至少可以说是临时当作了二元动词或及物动词来使用,所生成的偏离“死”的常规词义的构式义是“损失”义,即某某遭受了失去父亲的损失和打击。而且全句获得了不同于例5和例10的语效⑧。
假如例1由开始的误用演变为惯用,而如今已升格为正用(广为接受,具有良构性(well-formedness)),那么,下面诸例的正用性、惯用性或误用性,都不是绝对的,且都可以得到较好的解释。
(11) 王冕死了a)父母;b)爷爷;c)叔叔;d)婶婶;e)哥哥;f)弟弟;g)朋友;h)同学;i)校友;j)邻居;k)陌生人;l)敌人。
可见,在“N1死了N2”构式里,通常情况下(正用),N1为认知参照点、话题、体验者、领有者,“死了N2”是“N2死了”的事件,N2为信息焦点、隶属者(参见郭继懋1990;张翼2010)。N2前面不带领属性定语(因为语用隐含为隶属于N1)。“死”没有致使义,“死”字一般有体标记“了”,表示已经发生的悲剧(参见刘晓林2007)。“正用”的最一般情况是,N2跟N1有领属甚至血缘关系(“领主(属宾)句”的一种),N2年长于N1,N2之死对N1来说是很大的损失(“死”从“丧”传承的“失去、损失”义),因此也是打击(参见刘国辉2007)。试想,例1等改表完成“了”为表将来(未然)的“即将、会、可能”,即便作为惯用被接受,原先的整个构式却不复存在了,其构式效果也就不存在了,其相应的语用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其他情况为有标记:一般标记性为惯用,如N1不是人(如处所语词),N2是“婶婶、弟弟、朋友、果树、猪、鸡”,特殊标记性为误用或特用,如例11i-l——此时依赖数量词。同样:
(12) 敌人死了一个a)军(长);b)团(长);c)排(长);d)士兵;e)人;f)不重要的人;g)士兵的父亲。
对于死了父亲的士兵来说,这是很大的损失和打击,但是对于N1“敌人”的整个军队来说,这是不值得一提的小损失。因此,从12a到12g,是相对的“正用-惯用-误用连续统”,越靠前越是正用,越靠后越是误用⑨。甚至“病”例13a-c也是如此:
(13) 王冕家病了a)一个人;b)父亲;c)一家人。
“N1死了N2”构式改“死”为“病”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差别?原因之一是,“病了N2”不足以构成对N1的巨大损失或打击,即不够关联,不值得一提,除非加大“病”的“损失度”,甚至改变N1。沈家煊(2006)说例13a“比较合格”⑩,说13b介于“不可接受”和“不合语法”之间。再如:
(14) 赤壁之战前夕,曹军因不服水土至少病了五分之一的人马。
潘海华(1997)认为汉语有一条普遍的受害人插入规则(general maleficiary role insertion rule)使得受害人很容易插入到相关的论元结构之中。袁毓林(2004)则认为可以推而广之而成为“更加普遍的”“与事插入规则”(general dative role insertion rule),这就给受害者、受益者、目标(论元)等打开了绿色通道。该规则的启动受制于构式的意义。例如,当构式涉及受害者或受益者,并且他跟客体构成得失关系,而动词只有一个客体参与的时候(如例1、12、13等)。又如,当构式涉及施事、受事、与事以及他们之间的转移关系,而动词只有施事和受事的时候(如例8和例9)。
6.何以言“死”?
生死是人类乃至万物的大事,尤其是死。任何语言都有丰富的“死”词以及相关委婉语和习语。汉语的“死”字本表示与“生”相反的意义(如例1和例15,可是通过层层语用压制,可以表示:(1)不合意的“几乎死”的夸张语效,如例16;(2)合意的“几乎死”的夸张语效,如例17;(3)“像死一般不能动弹”的隐喻语效,如例18;(4)“像要死的样子拼命/猛烈”的夸张和隐喻语效,如例19;(5)“非常”的夸张语效,如例20,等等。
(15) 战死、杀死、病死、打死、掐死、毒死
(16) 累死、饿死、渴死、忙死、郁闷死、伤心死、瞌睡死、羞愧死
(17) 高兴死、兴奋死、幸福死、骄傲死
(18) 关死、锁死、卡死、焊死、扣死、钉死、捆死、填死(了洞口)、限死(了流通)、抓死(了两个工作环节)、管死
(19) 死战、死灌、死拽、死劝、死争
(20) 笨死、烦死、热死、脏死、臭死、笑死(人)、难看死、撑死、恨死、爱死、气死、死倔、死犟、死硬
以上种种假“死”有时具有模糊性和歧义性。如例16的词语都可表夸张的语效。例18也具有模糊性和歧义性,如“捆死”——捆绑得太紧从而致死人命,或者就是捆得很紧。
有趣的是,英语也有或真或假的“死”。种种假“死”都是语用压制所成。例21是假死,否则“我”怎么说话呢?说的是夸张自己要倒霉,如同死到临头。例22不是要对方真的“去死”,而是谴责、咀咒、驱赶对方。同样,例23不是说死了之后去娶她,而是说“渴望娶她渴望得要死”的夸张意义。以上三例都有转喻性质。甚至可以说例24,是形容词活用为副词,表夸张之意。可见,英语的“死”其语用压制的途径和语效跟汉语的“死”十分近似。
(21) I amdead.
(22) Dropdead!
(23) I amdyingto marry Rose!
(24) It’sdeadwrong.
最后,让我们看看两组“想死”例,重点讨论例26b和例26e的语用压制。
(25) a.我想你(了)。
b.我想死你(了)。
c.我想你死(了)。
d.我想你想死了。
e.我把你想死了。
(27) a.你想我(了)。
b.你想死我(了)。
c.你想我死了。
d.你想我想死(了)。
e.你把我想死(了)。
例25a-e,“想”的主体都是“我”。但是25c的“想”(“以为、猜测”之意)不同于其他“想”。例26a-e“想”的主体都可以是“你”,但是在实际交际中未必都是“你”,例26b若是陈述对方“想我”的状态,因为“何以知之?”的疑问而显得不值一提,而受到语用压制的结果是,意思相当于却更生动于例25a、b、d、e。例26c的“想”类似于例25c的“想”,可能是“以为、猜测”,也可能是“期望、指望”。例26e的陈述价值像例26b一样低微,虽然结构上等同于例25e,但是受到语用压制,居然得到相当于例25e的意思,和更生动的语效。
朱蓉(2011)论述了“V/A+死+了”构式(如“想死了、笨死了”)。她分析了能够进入该构式的175个较典型的汉字和85个较常见的词,从构式和非范畴化(decategorization)两个方面对该构式进行系统探讨。作者将构式分为(1)表示动作或状态的结果的A式;(2)既表示结果又表示程度的B式;(3)表示程度达到了极点的C式。作者认为,由A式发展到C式是非范畴化过程。“非范畴化具有语义抽象与泛化、形态变化特征的消失以及功能与范畴的转移”等特征,“其机制便是隐喻化”。这些当然是正确的。我们也认为这些全是语用压制的结果。(例证和分析从略)
无独有偶,日本语也有少数“自动词”,如表示“死亡”的“死ぬ”,表示“降雨”的“降る”等,用于被动式时表示受到物质或精神上的损失、影响或打击。如:
(27) 道夫さんがお父さんに死なれて,生活が困りになった。(道夫死了爹,生活很艰难。)
(28) 今日のハイキングは雨に降られてしまって,面白くなかった。(今天的郊游被雨淋了,不好玩。)
7.不了了之的结语
关于该构式的讨论还没有结束。刘晓林(2007)说,古汉语就有“死、来”的使动用法,如例29和例30,而我们讨论的构式和例1只是该用法的“残留”。刘晓林还认为该构式是广义(化的)存现句。
(29) 买臣深怨,常欲死之。
(30) 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刘探宙(2009)说“死”不一定表示损失(如“死了对头”),如同“来”不一定表“得”(如“来了讨债的人”)。关于这一点,沈家煊(2009)批评得对。这是句式(type)和句例(token)的差别(犹如“塞翁失马”之“得”),更是无标记和有标记的差别。关于得失的大小,得失到何等程度才可以说相关的语句,这是个语用问题,“取决于说话人认为得失的大小值得计较”(的程度)。(同上)
不同的语言学理论都可以对一种语言现象(如“N1死了N2”构式)进行解释,关键看哪种更有解释力。上面介绍的徐杰的“移位观”是基于生成语言学的解释,潘海华和韩景泉的“话题观”是介于生成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的解释,沈家煊的“糅合观”是认知语言学(认知构式语法)的解释。各观出发点不同,结论也不同,但是都不失为有意义的解释(尝试)。笔者尝试借用认知语用的解释——“语用压制观”。我们认为,一种解释不必为了自身所属流派的纯洁性而排斥其他流派的观点,可以多方借鉴。语用压制观归根结底是认知的解释兼语用的解释,适当借鉴了“话题观”和“糅合观”。
本文先介绍和简评了上述各观对例1进行的解释,以“语用压制”解释了例1及其所属之“N1死了N2”构式。“语用压制”导致构式偏离或/和语义偏离,即构式或/和语义的“陌生化”。听者途经语用压制的“花园路径”从而进行“二次思考”或“再思”,以得到一定的语效(如简洁、生动)。笔者指出,“语用压制”受制于多种语用原则,尤其是(可)表达性原则、最省力原则、关联原则和生动原则。
“死”词构式的语用压制如此,其他语词构式,如含非宾格动词的“死来类”和含非作格动词的“病笑类”(两类多半需要数量成分,参见沈家煊2009),其语用压制也大致如此吧,至少可以以语用压制观予以解释。
附注:
① 另一种解释是“王冕的父亲”整体移位到主语空位生成例5“王冕的父亲死了”。韩景泉赞成“王冕”移位却反对给“父亲”赋部分格:“王冕”移位后获得主格后通过“语链”将主格传递给逻辑宾语。潘海华、韩景泉(2005)和朱行帆(2005)等的批评集中在“王冕”的移位会造成“重复赋格”和“格冲突”。领有名词“王冕”本身有结构格(所有格),根本没有寻求赋格而移位的动因,况且“王冕”移位获得主格从而使得所有格加上主格造成“重复赋格”和“格冲突”(见沈家煊2006)。
② 根据该定律,凡是不能给主语名词赋予题元角色“施事”的动词也不能给宾语名词指派“宾格”。例如:不能说“* (It) sank a boat.”,可说“A boat sank.”。非宾格结构里,所谓的宾语不能放在宾语位置而必须移位到主语位置。同样,假如说“死”带了一个深层逻辑宾语“父亲”,却不能授予它宾格。(参见沈家煊2006;胡建华2008)
③ 沈家煊(2009)认为该构式的“浮现意义”是“移情义”(empathy)。他转引Kuno(1987)的意思:(1)独立成分比非独立成分容易作为移情对象;(2)句首和句末比其他位置更容易作为注意和计较的对象;(3)人比物容易作为移情对象。刘国辉(2007)也谈到该构式的“移情(流露)”。
④ 在胡建华(2008)看来他们的移位观是预测力或解释力过强或过弱的问题。
⑤ 他说例1类语句“可以上溯到13世纪,而用作“丧失”意义的“丢”到了18世纪才出现”。因此它不可能与例6b“丢”句糅合类推。
⑥ 最早提到这一术语的是王寅(2011:378),没有定义或阐释。
⑦ 即帮助构建语句之间的衔接性(cohesion),乃至语段和语段之间的连贯性(coherence),以及全文的话题性(topicality)或语篇性(textuality)。
⑧ 刘国辉(2007)讨论了类似构式的“超出常规认知期待”和“移情”的“构式后果”。
⑨ 胡建华(2008)认为例12e“比较勉强”。
⑩ 胡建华(同上)认为它和例12b都不合法。
Croft, W.2001.RadicalConstructionGrammar:SyntacticTheoryinTypologicalPerspective[M].Oxford and NY: OUP.
Goldberg, A.E.1995.AConstructionGrammarApproachtoArgumentStructure[M].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oldberg, A.E.2006.ConstructionsatWork:TheNatureofGeneralizationinLanguage[M].Oxford: OUP.
Kuno, S.1987.FunctionalSyntax:AnaphoraandEmpathy[M].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ichaelis, L.2003.Headless constructions and coercion by construction [A].In E.Francis & L.Michaelis(eds.).Mismatch:Form-FunctionIncongruityandtheArchitectureofGrammar[C].Stanford, CA: CSLI.259-310.
Talmy, L.2000.TowardaCognitiveSemantics.(Vol.II):TypologyandProcessinConceptStructuring[M].Cambridge, MA., and London: The MIT Press.
Ziegeler, D.2007.A word of caution on coercion [J].JournalofPragmatics39: 990-1028.
郭继懋.1990.领主属宾句[J].中国语文(1):24-29.
韩景泉.2000.领有名词提升移位与格理论[J].现代外语(3):26-72.
胡建华.2008.现代汉语不及物动词的论元和宾语——从抽象动词“有”到句法-信息结构接口[J].中国语文(5):396-409,479.
刘国辉.2007.“王冕三岁死了父亲”的认知构式剖析[J].重庆大学学报(社科版)(3):125-30.
刘探宙.2009.一元非作格动词带宾语现象[J].中国语文(2):110-19.
刘晓林.2007.也谈“王冕死了父亲”的生成方式[J].中国语文(5):440-43.
潘海华.1997.词汇映射理论在汉语句法研究中的应用。现代外语(4):1-13.
潘海华、韩景泉.2005.显性非宾格动词结构的句法研究[J].语言研究(3):3-13.
沈家煊.2006.“王冕死了父亲”的生成方式——兼说汉语“糅合”造句[J].中国语文(4):291-300.
沈家煊.2009.“计量得失”和“计较得失”——再论“王冕死了父亲”的句式意义和生成方式[J].语言教学与研究(5):39-51.
石毓智.2007.语言学假设中的证据问题——论“王冕死了父亲”之类句子产生的历史条件[J].语言科学(4):39-51.
帅志嵩.2008.“王冕死了父亲”的衍生过程和机制[J].语言科学(3):259-69.
王寅.2011.构式语法研究(上卷):理论思索[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徐杰.1999.两种保留宾语句式及相关句法理论问题[J].当代语言学(1):16-29,61.
徐杰.2001.普遍语法原则与汉语语法现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袁毓林.2004.论元结构和句式结构互动的动因、机制和条件——表达精细化对动词配价和句式构造的影响[J].语言研究(4):1-10.
张翼.2010.“王冕死了父亲”的认知构式新探[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4):17-20,86.
朱行帆.2005.轻动词和汉语不及物动词带宾语现象[J].现代外语(3):221-31.
朱蓉.2011.“V/A+死+了”构式的认知语用探讨[D].四川外国语学院硕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