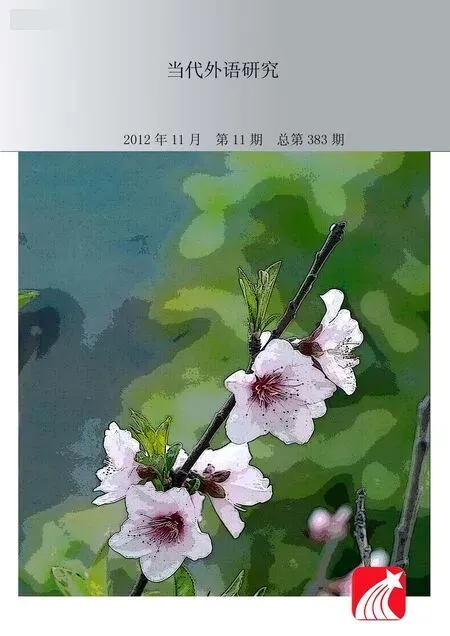缓和语的和谐取向及其人际语用功能
2012-04-01冉永平
冉永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510420)
1.引言
在人际交往中缓和手段(mitigating devices)、缓和语(mitigators)等广泛存在。自20世纪80年代,Fraser(1996)将“缓和”(mitigation)引入现代语用学研究之后,作为语用现象的缓和语已成为语用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但对其探究仍未充分,尤其是汉语交际中语用缓和语的类型与功能还有待深入探索,它涉及诸多语言形式、策略选择,包括一系列可更有效地实施言语行为,或有助于传递语用用意的策略;也包括具有语用用意(pragmatic force/illocutionary force)修饰功能的语用缓和现象及其人际功能(Schneider 2010;Thaler 2012)。也就是说,语用缓和的研究包括对具有人际缓和功能的语言形式或策略的探究,也可针对实现人际缓和用意的语言交际过程的研究。
缓和语是与驱使性、强加性等语用强化、语用凸现手段相对立的,其选择与使用受制于多种人际因素与目的,即语用缓和语的选择与使用具有充分的人际语用理据。对话语中语义信息的传递与理解并不重要,换言之,从语义信息传递的角度来说,缓和语的出现是多余或附加的,并不构成说话人希望传递的交际信息,也不是所在话语的语义内容,而是附属于某一主导言语行为的语用信息,也就是说,我们可将具有语用缓和功能的缓和语和主导行为进行分离。为此,Watzlawick, Beavin和Jackson(1967)指出了言语行为或语言使用的关系维度、人际维度等,如Brown和Levinson(1978, 1987)的面子论、Leech(1983)的礼貌论、Grimshaw(1990)的冲突论、Spencer-Oatey(2000)的和谐论等,涉及语言使用的人际修饰及其人际功能的不同语用取向,比如,话语冲突与话语缓和就是语言使用中两种不同的人际功能语用取向。
2.语用缓和语及其和谐取向
缓和语气、缓和语包括一系列可以使言语交际行为更加有效或更有助于实施语用用意的策略。作为一种语用现象,缓和往往涉及交际中的言语行为,尤其是说话人借助言语行为的行事用意(Thaler 2012)。Fraser(1996)讨论的缓和、缓和语或缓和手段是一种狭义的语用认识,主要涉及Brown和Levinson(1987)提出的面子和威胁面子的言语行为。其实,综观制约语言使用的各种语用因素,缓和语的出现受制于多种因素与目的。从广义的角度看,缓和语就是降低与削弱互动交际中某种语用因素的力度,减少交际中可能出现的人际冲突、面子威胁等风险与负面效应,从而推动交际的顺利进行,并朝说话人所期待的方向发展。因此,缓和语就是起类似作用的语言手段,包括词语、结构、话语片段、时态或体结构、语调、韵律等。缓和语是一个涉及众多策略的术语,体现说话人的元语用意识(Caffi 1999,2007)。
英语中的mitigation/mitigating等同于weakening、downgrading、downtoning以及softening,表现相同或近似的语用缓和现象。由于缓和语存在特定语境下的使用理据和人际语用功能,也就是说,缓和语有利于促进言谈互动交际中的人际关系管理,可见缓和语是与冲突性话语相对立的,因此被视为“语用缓和语”。我们也可以将其看成意在实现人际“和谐取向”(rapport orientation)的语言手段或语言策略,意在维护或提升人际关系,避免人际冲突等负面效应。
Caffi(1999)认为,缓和语的功能可分为两类:(1)实现交际互动的有效性,因为使用缓和语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交际互动,这体现了缓和语的策略性特征;(2)人际身份构建(identity construction),缓和语的使用是为了维护人际关系,比如调节交际主体之间的情感距离等。针对语言使用中的缓和现象,现有研究可大致分为三种情况:(1)缓和语出现的条件或环境,这涉及缓和语出现的语用理据;(2)传递缓和用意的语言范式(linguistic patterns);(3)缓和语对言谈互动以及言谈双方等的影响。在探讨缓和语出现的语用理据及其与缓和的语言范式之间的关系时,Czerwionka(2012)发现社交互动行为的“驱使性”(imposition)和说话人对交际信息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是影响缓和语使用的重要理据,并分析了三类缓和标记语:(1)人际标记语(interpersonal markers);(2)话语标记语(discourse markers);(3)认识标记(epistemic markers)。下面我们讨论缓和语的表现形式及其语用功能。
3.语用缓和语的表现形式与功能
语用缓和语对话语信息的传递与理解并不重要,也就是说,它们不构成说话人希望通过所在话语传递的交际信息,也不是所在话语的语义核心,而是附加给一个主导行为(head act)的语用用意或语用意图。换言之,我们可将起语用缓和功能的语言形式与其修饰的主导行为分离开来,缓和语修饰该主导言语行为。在人际交往中,缓和语的表现方式是多样的,可以是一个词语、称呼语、一个话语、几个话语等,它们可以出现在一个主导行为之中、之前、之后,但多数出现在主导言语行为之前。它们的作用是丰富的,可使某一以言行事用意更容易被对方接受,进而更有效地实施说话人的交际意图,或进一步帮助维护交际主体之间的人际关系等。但是,我们应该注意语用缓和语出现的几种常见情况:说话人的话语可能对听话人产生较强的驱使性,比如请求、命令等,或可能威胁到对方的面子或双方的人际关系,或说话人在提供信息时缺少证据、或缺少把握等。在类似语境下,说话人就需要使用缓和语或缓和策略等语言手段。
3.1 礼貌标记语的语用缓和功能
上面已指出,语用缓和语可以是一个词或词语。比如,汉语中常见的礼貌标记语“请”、“麻烦”、“劳驾”等,具有人际交往中的语用缓和用意,而仅非表示说话人的礼貌。例如:
(1) a.请把桌子上的书递给我。
b.把桌子上的书递给我,请。
(2) 我想问您的是,请问吸毒品是因为精神生活的缺乏而导致,他们接触了毒品融入到毒品里面,被毒品所诱惑,还是因为他们被毒品诱惑以后才导致他们精神生活的缺乏?
(3) a.麻烦大家再往前推一推。
b.大家再往前推一推,麻烦一下。
(4) a.劳驾劳驾,把这包东西给老王捎过去。
b.把这包东西给老王捎过去,劳驾劳驾。
上例可见,在汉语的言语(或口头)交际中“请”、“劳驾”等既可出现在请求或驱使性言语行为之前,也可以在该行为之后;“麻烦”用在说话人的请求、驱使或指使等言语行为之前是常见的,但当它出现在该行为之后时,人们习惯附加上“一下”、“一会儿”等辅助性弱化语,因而我们常见“麻烦一下”、“麻烦一会儿”等;也会出现“劳驾一下”、“劳驾劳驾”等,协助说话人降低所在言语行为的驱使力度。在书面语中,也会出现“烦请”的用法。不过,在书面语中它们往往置于言语行为之前。从语用功能上看,它们的出现能够降低、缓和所在言语行为所产生的指使力度,以及对听话人所产生的威胁面子的力度,从而更容易赢得对方的合作,以实现所期待的以言行事目的。对比以上话语(1a-4a),话语(1b-4b)的驱使性要强些,更多地威胁对方的负面面子。
Lee-Wong(1994)曾在中国、澳大利亚墨尔本、新加坡等地方对汉语“请”的使用进行过实用调查,研究“请”在等级、权力之类人际关系中的语用情况,发现它是一个表示礼貌或尊敬的标记语,但当它出现在具有驱使性的话语(如祈使句)中时,它的作用在于辅助实施请求,此时它是一个请求标记语(request marker)。例如:
(5) 谢老师,我有一件事要麻烦你,请你帮忙。
(6) 请您是不是给我写一封介绍信?
(7) 请你能不能把窗户开一点?
Lee-Wong(1994)研究后发现,一般情况下“请”是一个社交礼貌标记语,其功能在于缓和、减少话语所产生的驱使性,并表达一定的敬意;但同时,它往往和其他一些礼貌标记语一起出现,如表示礼貌的称呼语(如例5中的“谢老师”)及其他的礼貌形式(如例6、例7中的“…是不是…?”、“…能不能…?”)一起出现。其实,这一结果与Ng和Bradac(1993)所指出的减低话语负面影响等作用是一致的。在日常汉语交际中,“请”还出现在“抱怨”、“责备”等影响人际关系的话语中,此时它就具有人际语用的缓和作用。例如:
(8) 请别在中午休息时间给我打电话。
(9) 请别以为,有钱就有一切。
在类似话语中“请”所起的语用功能在于实施请求,但同时隐含了抱怨、责备等用意。可见,“请”在汉语中是具有一定权利特征的语言手段(empowering linguistic device),其语用功能在于减低或减弱某一言语行为的祈使性或指使力度。因而,在请求和命令性话语中,“请”所起的作用就是一个缓和性标记语,帮助说话人实现所期待的以言行事,或传递具有潜在负面效应的语用用意,如例8、例9。
除“please”和“请”以外,在实施请求或建议时,以“let’s...”和汉语中的“咱们”开始的话语也具有语用缓和功能,还多出现在不包括说话人在内的交际语境,这体现了说话人的一种语用移情。例如:
(10) Let’s stop our talking and work for a while.(老师对学生)
(11) Let’s take our medicine, John.(母亲对儿子,或护士对病人)
(12) 咱们是学生,应该好好学习。(老师对学生)
(13) 主持人:我相信一定会有作用的。待会儿节目结束,你先跟张路先生把这事说说。(笑声,掌声)张路先生,下一个问题你一定要当着我们球迷说清楚,为什么你的队员不给林德诺传球?(笑声,掌声)
张路:这个咱们不好说。咱们还是说说球员的心态。确实,外国运动员同等水平的收入比咱们的球员高,而且高很多,但这你不能去比,如果你要求他跟咱们队员同等收人,像刚才那位小同学说的,你可能一个都引进不了……。(《实话实说》,1996年10月27日)
例13中,面对主持人具有挑战性的提问,说话人使用了三个“咱们”:第一个“咱们”表示“我”,辅助表示拒绝;第二个“咱们”既可包括主持人在内的现场参与者,相当于“我们”,辅助表示建议或提议,也可只表示“我”;第三个“咱们”相当于“我们”。在很多交际语境中,“咱们”的出现可提高所在话语的接受性、亲和力,因为说话人把自己和听话人放在相同的视角,同时还具有移情的语用功效,以避免说话人显得高高在上,或避免凸现说话人的地位。
语用缓和就是对以言行事用意的一种操控(Thaler 20120)。操控的目的就是要降低特定行为实施的驱使性,这方面的研究已在Brown和Levinson(1978,1987)等针对人际面子的分析中提及过。驱使性行为总会威胁到听话人的负面面子,因此缓和语通常伴随面子威胁行为(Caffi 2007)。本研究中的礼貌标记语在语用学、社会语言学等传统研究中常被视为礼貌表达的重要手段,这本身没有问题,但却不能阐释礼貌表达的行为理据,这说明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礼貌与语用缓和等同起来。
3.2 称呼语的语用缓和功能
在人际交往中,呼语或称呼语(terms of address)是十分常见的,尤其是在权势、地位、身份等不均衡的社交语境中,在实施言语行为时说话人会借助一定的称呼语,表面上看似说话人的一种礼貌表现,或表达尊重,但实则是交际主体为了更有效地实施某一行为或传递用意而采取的缓和性用语。这同样具有人际关系管理的和谐取向,并使所在的言语行为更便于实施,也可将类似用语看成言语行为的语用修饰语。例如:
(14) a.把脚抬一下,二叔,扫一扫下面的灰。
b.把脚抬一下,扫一扫下面的灰。
(15) a.桂老师,再把刚才那个问题再讲一讲,不太清楚。
b.再把刚才那个问题再讲一讲,不太清楚。
(16) 主持人:a.你说,刘老师。
b.你说。
刘东刚:作为我来讲,适当开发一些游戏软件到网络系统里去,我认为是可以的……
以上三例(14a-16a)中,称呼语“二叔”、“桂老师”、“刘老师”都出现在请求类的驱使性言语行为之中,虽然它们并不是该行为的一部分,仅是该言语行为之外的附加语或附属性用语,却对该行为的实施具有重要的辅助作用,它们的出现可体现说话人的礼貌,或增加双方的亲和力,从而降低与缓和所在请求性言语行为的驱使性。如果将类似称呼语去掉,比如(14b-16b),所在行为的驱使性便随之增强,直接威胁对方的负面面子,自然不利于交际行为的顺利推进。不过,类似情况往往出现在说话人的地位或权势高于听话人的语境之中。有时候,说话人在向对方发出询问时,也可能附加上“请问/劳驾/麻烦+称呼语”等,从信息传递的角度看,类似附加语显得多余,但从人际交往的语用功能看,它们却是十分必要的。例如:
(17) 主持人:请问郑先生,你与孔子和张先生的观点是一致的吗?
郑也夫:对孔子学说我历来十分钦佩,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就这个小问题而言,我不赞同这种做法。(《实话实说》,1996年6月9日)
因此,笔者认为具有人际社交语用功能的礼貌标记语、称呼语等除了表示常规的人际礼貌之外,还具有降低所在言语行为驱使性,从而提高实施所在行为的可能性与可接受性。按照缓和现象研究的权威学者Caffi(1999,2007)的观点,缓和语或缓和策略的使用就是让说话-行事(saying-doing)更加有效。因此,类似用语就是一种具有语用缓和功能的语用修饰语。
3.3 模糊限制语的语用缓和功能
模糊限制语(hedges)就是让话语信息或说话人的用意变得模模糊糊、含含糊糊的词语或结构,分为变动型模糊限制语(approximators)和缓和型模糊限制语(shields)①。前者包括汉语的“在一定程度上”、“差不多”、“几乎”等,以及英语的sortof、kindof、somewhat、alittlebit、approximately、roughly等,它们可改变话语结构的原意,或根据实际情况对话语意义做出某种程度的修正,或给话语确定一个变动范围;在语用功能上,它们可帮助避免说话武断,使话语更具客观性。后者不改变话语结构的原意,话语中加上缓和型模糊限制语相当于增加了一个修饰,指出话语是说话人本人或第三者的看法,从而使所在话语的肯定语气趋向缓和,如汉语中的“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据人家说”等,以及英语中的I’mafraid、asfarasIcantell、Ithink、asiswellknown、thepossibilitywouldbe...等(参见何自然、冉永平 2009)。在特定语境中,以上提及的变动型模糊限制语和缓和型模糊限制语在人际交往中都具有语用缓和功能。
Caffi(1999,2007)等对模糊限制语的语用缓和功能进行过深入探析。在英汉交际中,以上常见词语或结构的出现受制于不同的目的,尤其是人际关系限制。下面主要从人际语用功能的角度出发,关注具有语用缓和作用的模糊限制语。
A.准确信息的模糊处理。
交际中,人们一般会向对方提供准确或精确的信息,但很多时候因各种原因,说话人却故意将该信息进行模糊处理,使其变得含糊其辞,或指代不清等。例如:
(18) ……据了解,一向说话直来直去的孙某性格豪爽,但也得罪了队里不少人,和队中某位大哥不和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他与教练组的不和更是导致他“下岗”的主要原因。(《重庆晚报》,2004年1月2日)
根据现时语境条件,该文作者甚至球迷都知道某位大哥指的谁,但该报道的题目与内容都采用了“某大哥”,进行人称的含糊指示。为什么不直接提及姓名呢?虽然作者知道“某大哥”指的是谁,但缺乏有关所指事件的直接证据;如果直接提及姓名,可能影响记者和“某大哥”之间的人际关系,或给对方带来负面影响;是否就是因为和“某大哥”之间的关系导致了运动员孙某退役,还难以定论;即使作者知道具体的所指对象,但因其影响很大,包括记者在内的很多人都不敢得罪。因此,任何一种情况的存在都可能影响作者或说话人选择模糊限制语,进行非确切的人称指示。就读者、听话人等信息接收者来说,“某大哥”之类的词语可留下一定的信息空缺,具有信息表达的不精确性。但从人际关系的角度来说,类似选择则具有语用上的恰当性,是人际关系管理的需要,如维护指示对象的正面面子。由此可见,交际中语言与策略的选择除了受制于信息传递以外,人际关系是一种重要的制约因素。再如:
(19) 昨日,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黄××对此事绝对是无言以对,她更大曝某许姓女演员和黄××关系暧昧,而且还表示绝对不怕此女演员告她。(《潇湘晨报》,2004年1月2日)
(20) 一青春貌美的范姓女演员,因主动给每部戏的导演“投怀送抱”,因此得道成星。按文中描述的情形,记者推测,该女星极有可能是指《还珠格格》中的俏丫头“金锁”。(《重庆商报》,2004年1月5日)
(21) “国足海口面面观——有人暗自加练有人上网冲浪(图)”(新闻标题)(《北京晚报》,2004年1月2日)
例19和例20分别使用了模糊指示语“某许姓女演员”和“范姓女演员”,其实根据现时的演艺背景及语篇语境信息,作者很明显知道具体的所指对象,读者也会心知肚明,但在涉及诽闻等负面信息时,类似的含糊处理自然存在很强的社交语用理据,受制于人际关系、面子等人际因素。例21是一则新闻标题,内容中还附加了图片,从文字的描写和图片信息来看,两个“有人”分别指示不同的具体人物,前一个“有人”指自觉加炼的某位足球运动员,带有表扬与肯定的语气,而后一个“有人”则指玩电脑游戏的三位足球运动员,隐含了批评或谴责的语气。但该模糊限制语的出现则降低了批评、谴责的直接性。可见,模糊限制语的使用与选择不是随意的,存在语用缓和的理据。
B.不确定信息或非准确信息的模糊处理
在说话人无法提供准确信息的交际语境下时,他往往会借助模糊限制语,或不确定性指示语,进行含糊表示。如例22中,“那山,那人,那饭菜”就属于不确定信息的模糊指示语,因为不必要或不可能精确地再现所指信息,此时它们的使用就属于信息传递的需要,而非人际关系的制约。
(22) 那是1973年的春节,那年头知青们前途未卜,情绪低沉,为减少孤独苦闷,我们分散在各村各队的十几个“留守男女”便相约到一个名叫“山田坑”的村子去过年。……多少年过去了,可那山,那人,那饭菜,却永远定格在我们的记忆深处。(《北京青年报》,2003年12月30日)
在发表个人观点与看法时,说话人常借助模糊限制语,以避免说话武断,尤其是在涉及缺乏足够证据或未经求证的信息时,说话人很容易选择类似结构或用语,以防出现错误时承担责任等;在信息不确定时,说话人更倾向于附加一定的模糊限制语,降低或减少所提供信息的不确切性。例如:
(23) 拿着十几封欲寄香港及外国的肖小姐说:“听说邮价涨了。”
服务员说:“其实,寄香港的信件在恢复20克到50克一级收费档次后,比以前便宜。”(《羊城晚报》,1999年3月8日)
(24) 辽宁中顺转让去向:新东家尚未正式露面。传闻收购中远的企业是已经拥有了中超球队深圳健力宝的张海及其幕后资金。(http://sports.sina.com.cn,2004年1月7日)
以上两例中,即使说话人提供的信息不正确,但会因“听说”和“传闻”的出现而避免或降低可能承担的相关责任。
C.负面信息的模糊处理
下面例25中的“报纸上说”表示信息来源。该来源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说话人故意附加的,但该结构的出现可以使后续信息的来源变得模糊或含糊不清,它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说话人责问的直接语气、批评的力度。这样,说话人既可以在向对方求证信息真实性的同时,也不会因为话语信息的负面性直接影响现时交际。另外,根据例(26)中的语境信息,“好像有点那意思”可以隐含男女之间的特殊关系,对待类似的非正面信息时,人们也是常借助模糊限制语,意在减少该信息直言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或负面效应。
(25) 记者:报纸上说,你骂了高原,还对记者说“窦唯真是流氓混蛋!真想打他两个巴掌!”是吗?
那英:没骂高原,我骂的是窦唯——你说他不该骂吗?……(《羊城晚报》,1999年3月26日)
(26) 王某从某饭店回来后对她说,打车时出租车司机没有收车费,还给自己留下了手机号,好像有点那意思。4月5日,王某又告诉宋某,那名出租车司机打电话约自己出去玩。随后,王某便用宋某的手机给对方打了个电话,当天下午就独自出门了。(《京华时报》,2003年12月23日)
就使用模糊限制语的目的而言,在涉及个人看法、观点、评价时,说话人借用它们降低个人观点的直接性、武断性,增加其可接受性。例如:
(27) 主持人:你觉得作为一个记者,他们这样做,你怎么评价?
观众:我觉得他们都对自己办的那份报纸都很敬业,肯定他们会有分歧,那肯定的。当着大家,可能要表露他们一些自己的东西,可能私下他们应该是好朋友,我觉得。(《实话实说》,2003年10月12日)
“我觉得”、“我认为”等模糊限制语一般会出现在表达个人观点、评价等的话语中。总的来说,模糊限制语的使用是受交际目的或语用用意的支配的,在很多语境中说话人使用类似结构的目的在于实现语用缓和,或缓和地实施特定的交际目的。因此,模糊限制语与说话人的语用意识密切联系。难怪,Verschueren(1999)把出现在言语交际中的well、kindof、Iguess、Imean、yousee、unlessI’mhearingitincorrectly等词语和结构统称为“元语用意识指示语”(indicators of metapragmatic awareness),也有学者将它们称为“话语标记语”(discourse markers)或语用标记语(pragmatic markers)(Fraser 1996)。在汉语中,出现在话语末尾的“吧”、“呢”、“吗”等在传统语法学中它们往往被称为语气词、小品词、助词或虚词等,以及“是吗?”、“对不对?”、“好不好?”、“行不行?”等结构,从语义信息传递的角度讲,它们都可视为末尾附加结构,没有实际语义。然而,它们的语用功能却是不可忽略的,如英语的well和汉语的“吧”就具有特定语境下丰富的语用缓和功能(冉永平2003,2004)。
4.支持性附加语的语用缓和功能
支持性话语(supportive utterances)也可称为支持性话步(supportive moves)。我们认为,它们是说话人提供的一种附加性话语或附加性言语行为。这类附加语在英汉的日常言语交际中都是十分常见的,它们出现于一个主导言语行为或主导言语事件的之前或之后。在信息上,该附加语所表征的信息往往显得多余、额外;但在语用功能上,它们与其他的元语用行为一样,可辅助主体言语行为的实施或辅助说话人传递所希望传递的语用信息,因此在它们之前或之后往往会出现一个主导行为或传递语用用意的主导性话语。通过对汉语中的语料分析,我们将支持性附加语分为两种主要情况:行为预备语和行为述因语。
4.1 行为预备语
行为预备语(preparatory utterances)出现在主导言语行为或表达主要的语用用意的话语之前。它们的出现首先表明说话人意欲实施的行为类型或表达用意,比如“问”、“说”、“请教”等,或者寻求对方的许可,以保证某一言语行为的实施等。类似话语同样可视为一种元语用评述——后言评述,因为话语本身直接反映了说话人意欲实施某一言语行为的语用意识。例如:
(28) 陈村:我想问一下,我们要讨论的广告也包括美国的广告吗?是不是说美国的广告就好了呢?我觉得他刚才说的非常有意思。……(被打断)
路盛章: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经济越发达广告越发达,……(《实话实说》,1996年6月2日)
(29) 观众2:我有个问题问杨先生,就是在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您举报您的亲戚、朋友,特别是干爹,在举报他之前,您跟他进行过思想交流,劝说过他没有?
杨剑昌:都劝过,他的顶头上司都劝过他,都找过他。(《实话实说》,2002年06月23日)
(30) 主持人:那就是说也有往银行存的。
占才强:有。还有的把乞讨的钱定期汇回去。
主持人:还一个问题,这位先生问能挣多少钱?他们进商场买东西吗?(《实话实说》,2003年10月26日)
(31) 冯春明:能问一下,您的丈夫做什么工作吗?
西苑:骨科医生,拿手术刀医病的。(《实话实说》,1997年11月3日)
例28和例29中,“我想问一下”和“我有个问题问杨先生”表明了说话人的后续言语行为的类型(“询问”)或直接表示说话人的用意(向对方提出问题);例30中“还有一个问题”所起的作用便是直接明示说话人的用意(即“还有一个问题要询问对方”);例31中“能问一下”表明说话人向对方发出了一种请求许可的附加行为,以缓和直接询问对方所产生的驱使性。从信息传递的角度来看,类似的行为预备语具有可取消性、可分离性,也就是说,它们的存在或分离对主体言语行为或主体话语所传递的信息并不产生直接影响,它们的影响仅是附加的、“元”语用的,也就是说,通过话语直接表示后续言语行为的具体类型,而非听话人根据语境信息推导出来的或暗示的。因此,从功能上,它们是说话人为实施后续行为或传递后续信息做准备的,它们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这一语用功能上,而在信息表达上显得多余,没有它们对方也知道说话人是在向对方发出询问或具有询问的意图,但作为一种策略性附加用语,它们的出现却可降低后续言语行为的突然性,或避免后续行为的驱使性而保护听话人的负面面子(Brown & Levinson 1978, 1987),进而维护交际主体之间的人际关系等。因此,这些也体现了它们的语用缓和作用,可见它们具有“废话”非废的语用功能。
4.2 行为述因语
行为述因语表示说话人实施某一言语行为时的原因或理由。比如,在人际交往中,说话人在实施某一请求或指使性言语行为之前或之后往往提供一定的原因或理由,以显示实施该行为的合理性、理由的充分性。在有的语境条件下,它们还可缓解驱使性言语行为等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并更有效地实现说话人的语用用意。例如:
(32) 我最近买了套房子,但装修的钱没有了,所以老王能不能借点钱给我?
类似例32的情况在言语交际中是比较常见的,说话人没有直接向对方提出借钱的请求,而是首先向对方提供买房、缺钱等信息,作为实施后续请求行为的预备条件。另外,在其他条件下,行为述因语的出现还可以起到为后续言语行为提供背景或前景信息的作用,在请求、询问等言语行为中,此类信息往往对听话人的回应构成一种范围上的制约。例如:
(33) 主持人:民警的工作很辛苦,咱们实话实说,你有没有怕他们的时候?
观众:怕倒不怕,因为我们这个岁数的人他们都尊重,没什么怕的……(被打断)(《实话实说》,1996年10月20日)
(34) 主持人:你真的要当那个教练,我想一定是有一套做教练的思路。你怎么做?(《实话实说》,1996年10月27日)
总的来说,从类似例子可见,交际中存在一些主导行为以外或主导信息以外的附加性话语。对人际关系来说,在很多语境条件中它们的出现都具有一定的语用缓和功能,或表现说话人的语用缓和用意。这说明,人际交往除了传递一定的语言信息以外,还是一个策略及言语行为修饰语的选择与使用过程。交际受制于一定的交际目的,实现该目的的手段就是提供与获取所需的关联信息,但因言语交际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尤其是人际语用因素,从交际所需和对方所提供的信息来说,说话人可能会提供一些听话人不需要的无关信息或边缘信息,这种情况的出现往往存在一定的人际语用理据,如实现语用缓和。
5.结语
本文探讨了人际交往中语言选择的语用缓和功能或语用缓和用意,意在揭示语言选择中所存在语用理据与人际和谐取向。从语义信息及说话人希望传递的目标信息的角度来说,交际中的很多话语可以是附加的,也可以是多余的。然而,从交际行为的语用取效来说,作为一种策略,类似话语的出现也是必须的,具有一定的语用理据,如缓和说话的语气、降低话语的请求驱使性或指使性、减少言语行为威胁对方面子的力度等,这些是以上所讨论的结构或话语的语用功能,也是语言使用中受制于人际关系的语用缓和取向。
根据Verschueren(1999,2000)的语言顺应论,我们应从认知、社会、文化等角度对语言使用行为进行综观。就语言使用来说,语用就是语言使用的选择过程,选择则是受制于社会文化语境、语言结构等因素的一个动态过程,同时也需要根据不同的语用意识而进行顺应、调节。因此,言语交际也离不开说话人的元语用意识(metapragmatic awareness),即说话人等交际主体在实施语用行为时,对意义、用意、行为类型、态度等所做出的一种自我意识反应。由于交际中说话人等交际主体所存在的语用意识、元语用意识,他们在选择语言、进行顺应时表现出来的自我意识势必会在语言形式或策略的选择上体现出来(冉永平2002)。言语交际中的缓和语气、缓和语或缓和策略就是与元语用意识密切相关的,因为语言使用过程是一个包括语言形式、策略等在内的选择—顺应—选择的过程,说话人或多或少地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哪怕有时候语言选择是自动的,但在多数语境条件下交际都受制于目的的支配。这体现了语言使用的自我反身性或元语用意识(Verschueren 1995,1999,2000)。
总的来说,缓和语体现的方式是多样的,具有特定语境下丰富的语用功能,如减少交际中可能出现的人际关系冲突、面子威胁等负面效应,从而推动交际的顺利进行;可使某一言行事更加有效地实施说话人的交际意图,或取得以言行事效果,或进一步帮助维护交际主体之间的人际关系等(Locher & Graham 2010)。人际交往中的语用缓和语、语用缓和用意、语用缓和效应等,还存在较多探索议题,比如缓和语的历时研究,不同时期是否存在不同类型的缓和语及其演变情况,以及话语冲突下的语用缓和实现方式、缓和效应等,都有待从社交语用学的角度进行深入探析(Bousfield 2008)。
附注:
① 这里的缓和性模糊限制语只是对模糊限制语的一种分类,其中的“缓和”不同于本研究中所涉及的缓和及缓和语。在互动交际中,变动型模糊限制语与缓和型模糊限制语都具有语用上的缓和功能。
Bousfield, Derek.2008.ImpolitenessinInteraction[M].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Brown, P.& S.C.Levinson.1978.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Politeness phenomena [A].In E.N.Goody (ed.).QuestionsandPoliteness:StrategiesinSocialInteraction[C].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rown, P.& S.C.Levinson.1987.Politeness:SomeUniversalsinLanguageUsage[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ffi, Claudia.1999.On mitigation [J].JournalofPragmatics31: 881-909.
Caffi, Claudia.2007.Mitigation[M].Amsterdam: Elsevier.
Czerwionka, Lori.2012.Mitigation: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imposition and certitude [J].JournalofPragmatics.Forthcoming.
Fraser, Bruce.1996.Pragmatic markers [J].Pragmatics6(2): 167-90.
Grimshaw, Allen.D.1990.ConflictTalk:SociolinguisticInvestigationsinConversation[C].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ech, Geoffrey.1983.PrinciplesofPragmatics[M].London: Longman.
Lee-Wong, S.M.1994.Qing/Please—a polite or requestive marker? Observations from Chinese [J].Multilingua13: 343-60.
Locher, Miriam A.& Sage L.Gramham.2010.InterpersonalPragmatics[C].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Ng, S.H.& J.J.Bradac.1993.PowerinLanguage:VerbalCommunicationandSocialInfluence[M].Sage Publications.
Schneider, Stefan.2010.Mitigation [A].In Miriam A.Locher & Sage L.Gramham (eds.).InterpersonalPragmatics[C].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Spencer-Oatey, H.2000.CulturallySpeaking:ManagingRapportthroughTalkacrossCultures[C].London: Continuum.
Thaler, Verena.2012.Mitigation as modification of illocutionary force [J].JournalofPragmatics44: 907-19.
Verschueren, Jef.1995.Metapragmatics[A].In Verschuerenetal.(eds.).HandbookofPragmaticsManual[C].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Verschueren, Jef.1999.UnderstandingPragmatics[M].London: Edward Arnold.
Verschueren, Jef.2000.Notes on the role of metapragmatic awareness in language use [J].Pragmatics10: 439-56.
Watzlawick, Paul, Janet H.Beavin & Don D.Jackson.1967.PragmaticsofHumanCommunication:AStudyofInteractionalPatterns,PathologiesandParadoxes[M].New York: Norton.
何自然、冉永平.2009.新编语用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冉永平.2002.言语交际中的元语用现象及其功能解析[R].第九届当代语言学研讨会论文,北京.
冉永平.2003.言语交际中话语标记语well的语用功能[J].外国语(3):58-63.
冉永平.2004.言语交际中“吧”的语用功能及其语境顺应性特征[J].现代外语(4):34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