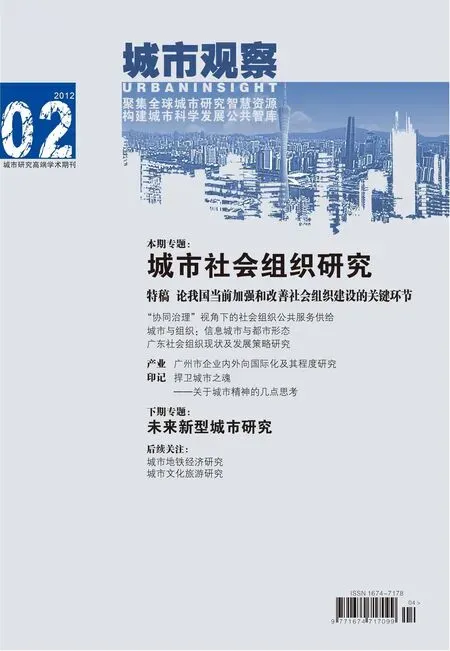城市与组织:信息城市与都市形态
2012-04-01汉娜诺克斯
◎ [英] 汉娜·诺克斯
城市与组织:信息城市与都市形态
◎ [英] 汉娜·诺克斯
如果我们将“城市”作为组织的场所会怎样?这个问题的提出,其隐含的意义也许解释了为何城市未能成为以卓越和专业为信条的组织研究领域的传统认知手段的一部分。分析学家们有可能在城市中迷失:对客体和主体、或者结构和代理的传统区分,在涉及城市的组织特性的术语时,往往会错乱。本评论文章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不再将城市作为组织理论家们在他们那些太过熟悉和沉溺的“组织研究与某某问题”(“某某”可以是本文探讨的“城市”)模式中的另一个关注目标。相反,我们希望思考城市和都市力量如何能够成为不断重新评估一种方式的场所,这种方式能让研究组织理论的学者可以通过社会和文化转型等问题参与其中。总而言之,这些文章反对我们将城市简单地视作追求秩序的一种意愿的结果以及由此产生的外部效应,而是呼吁我们对新的组织形式敞开怀抱。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感悟和想象才刚刚起步。
城市 都市 信息 布鲁诺·拉图尔 弗里德里希·奇特勒
一、引言
城市,或者更广义的都市社会环境,是研究当代组织演绎的最佳场所。迄今为止,学者在城市和都市形态的组织群体方面的研究乏善可陈。近年来,一众其他学科所关注的研究焦点,却在城市生活的沃土上掘出一道道平行的犁沟:譬如地理学家对空间力量的思考,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对移民和社区文化活动的关注,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对建成环境功能的探索,以及经济学家对商品和服务循环过程的研究。
本文通过将城市作为一个与组织有关的场所,全面回答了组织研究所获得的启示。所谓从新的角度进行探讨,并非将城市设定为研究组织理论的学者所关注的另一个焦点——即组织与城市,如此就成了换汤不换药的分析,只不过这个主题提供了新鲜的素材,使其能够在现成的理论碾磨机上得以搅拌翻腾——而是思考城市和都市力量如何能够成为不断重新评估一种方式的场所,这种方式能让研究组织理论的学者通过社会和文化转型等问题参与其中。从这个方面讲,由城市引申出来的关于组织的问题,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对组织设定和过程的认识范畴,尽管人们一直没有将城市当作一个组织群体问题来看待。本杰明、德·塞托、勒菲弗、齐美尔等社会学家都曾指出,城市对学术分析的重要性恰恰在于它作为一种组织形式的特殊性,尽管研究领域没有将城市视为一个组织群体问题,但这些学者们的观点仍然占据当代组织理论研究的中心位置。
格奥尔格·齐美尔在其论著《大都市与精神生活》(1903/1971)中描述现代城市的兴起时,他所说的大都市是指超越于一切个性的文明的舞台。对齐美尔而言,城市是永恒变革的场所,由城市关系的“波动和间断”(1903/1971,12)构成,它与按照“一种更加安详、更具惯性和更流畅的节奏”组建的乡镇(1903/1971,12)形成对比。使城市区别于其他社会形式的不仅是它的规模大小、地理位置、身份认同或经济实力,而恰恰是它所展现出来的组织特征。齐美尔认为,大都市组织特质的特殊性强大到不仅足以改变我们对外部现象之间关系的理解,现代城市的发展还激发出一场居住在这座城市的人们个性的变革。他认为,组织的都市形式是一类新的群体——大都市人产生的原因所在。这类新群体的卓越之处在于他们有能力演绎理性和知性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在他们与混乱和极度复杂的城市之间形成一道隔离,保护其以免受伤害。
假若,齐美尔的观点是针对工业化国家处在空前的城市化进程这一时间段的及时观察,那么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则是一个令人再度思考城市组织问题的原因。我们经常听说,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口将有50%以上居住在城市。有些人更认为如今城市生活已十分普遍,以至于讨论城乡划分的意义已然不大(Lacour and Puissant 2007)。将城市视为工业性、将农村视为农业性的意义也不存在了。如今,乡村更多地是作为通勤者的居所或旅游度假屋存在,而非面向内部的、拥有充满凝聚力的风土人情的“社区”;而城市空间则被重新设想为城中村,当前在许多具有卫星城的大城市中心,那些普遍存在的“文化角落”需要乡村的协助来展现一种社区关系,旨在填补重工业毗邻所留下的空隙。如果齐美尔在20世纪初对于城市环境的诊断是准确的,我们无法确定他所假设的这种差别现在是否仍然成立。我们或许会问,现在的我们是否如齐美尔所说的大都市人的表现形式?或者说城市里是否还有其他参与博弈的力量,在用一种连齐美尔都未曾想象过的方式,通过“叛逆”和“疏离”,与群体构成“统一体”?
纵观齐美尔撰文后一百多年来对城市的思考,在当代城市背景下,我们发现了组织力量的复杂性和广泛性。城市在兴建、拆除、建造和破败等模式中表现为一座记忆库(Benjamin 1999;Hart 2000);由频繁的交流引发的变革力量使得人们将城市想象为一部增长的机器(Molotch 1976),移民的历史重新将城市配置成大都会空间、差异的场所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容器(Hannerz 1980,1990;Toulmin 1992),提供了一个可以将世界本身重新想象为一个相互交流的网络和流动空间的好机会(Castells 1989)。城市既是变革的动力,也是研究组织的学者们在其他地方观察到的、可以重新审视和重新思考转型的场所。事实上,如果真如Chia (1999)所说,当代社会对组织问题研究的全情投入象征了一种主导模式,那么城市管理的历史以及当前城市秩序新方式的构想,就应当成为我们分析秩序与组织之间关系的核心。城市作为一个复杂的、分散的、过程性的空间,它受制于拥挤、无序和破败的崩溃所带来的威胁以及千差万别的利害关系。如果齐美尔认为城市的重要性在于城市货币经济的强化,在于它对新的生产关系、消费关系以及国家权力集中的依赖,那么为了确保秩序,当代城市管理就要将这些问题转化为信息。
二、信息时代的城市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信息技术的扩散一直是城市研究理论学家们最为关心的问题(Wheeler,Aoyama,and Warf 2000;Graham 2004)。对于信息技术的内涵,城市理论学家和城市规划师们的看法是,它们可能会给知识经济中空间动力的运作带来改变(Gillespie and Richardson 2000),可能通过计算机设计技术改变城市的建成环境(Mitchell 1995),或者影响市民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参与度(Norris 2001)。信息管理捕捉到了根据理性的编码、联系和信息流系统追求有序世界的精髓。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技术途径,信息通讯技术将确保秩序置于混乱之上,将知识置于无知之上,以此作为通往现代开放政治的途径。
曼纽尔·卡斯特尔(1989)关于城市组织的信息动力学的文章也许是最常被引用、也最能概括信息技术的出现给城市在组织上带来潜在激进影响的一篇文章。卡斯特尔对信息技术发展给空间带来的意义很感兴趣,他认为城市不应再被看作是具有凝聚力的社会空间。相反,他认为,在流动的全球化空间中,为了回应信息技术带来的可能性而产生的城市如何运作的动力学,已不再由地方所关切的问题和城市内在的关系所驱动,而是更多地由世界各地居住在城市郊区的高收入人群之间的交流互动所驱动。为了描述它是怎样产生的,卡斯特尔将焦点集中在信息主义、资本主义和技术变革这三个问题之间的相互影响上,并且记录下每一样的变化,因为它们在近几十年改变了美国的城市和地区。对卡斯特尔而言,信息主义的显见之处在于生产、消费和国家控制这三个领域越来越围绕信息化进程来进行组织。生产已然从小规模作坊式转变为以全套必须由信息技术连结在一起的分散或曰“分配”活动为特点的大型企业。随着市场营销成为了解顾客的核心手段,消费活动也成为信息化日益深入的对象;与此同时,国家在跟踪和监控公民行为的技术仪器上也投入巨额。
卡斯特尔所采用的形式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这在他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资本主义的看法中尤为典型:那时资本的重塑靠的是将利润置于劳动者权益之上;国家的角色由原来的政治法制和财富分配转变为对政治控制和财富积累的支持;再有就是资本流动的不断国际化。卡斯特尔对资本主义的特性在当代城市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看法与大卫·哈维和萨斯基亚·萨森的论述有不少相通之处。哈维的近作阐述了他对过去一个世纪城市化的看法,城市化与资本主义生产剩余价值的要求具有内在联系,剩余价值本身的集中就是使构成城市的人和过程集中的原因所在(Harvey 2008)。另一方面,萨森(1991)则说明了国际资本流动如何将具有许多卫星城的大城市打造成全球城市。
卡斯特尔将技术变革描述为一系列计算和通讯技术的同步发展,它使得大量信息的输送和传播成为可能。卡斯特尔将信息传输与文化发展联系在一起,他认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技术变革带来了一个变化,即没有必要再将手工生产和工业化生产、或者定制市场和大规模消费对立起来。信息技术与它们赖以成长的社会环境一道成就了一个更具适应性的工业组织。他指出:“通过增强所有流程的灵活性,信息技术为缩小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差距作出贡献”(Castells 1989,17)。虽然卡斯特尔关注技术变革带来的广泛效应,他也注意避免被指为技术决定论的拥护者,并且很早就定下目标,确保自己的论著不会去推断新技术与社会变革之间的直接因果联系,而是将这些新的技术手段看作是伴随着信息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的动力而发展的。
对于卡斯特尔,如果我们将向信息处理活动及相关的信息技术物质生产大爆炸的双重转变考虑在内,那么我们就能认识到分裂和不公平的过程是当代城市的特性。总而言之,卡斯特尔认为“人们生活的地方,权力通过流动性来实现”(1989,349)。正是这一复杂的信息技术生产过程以及对信息处理能力的普遍要求,两者在城市资本主义的大背景下产生,构成了他所说的“发展的信息模式”。通过这个术语卡斯特尔想到了城市力量偏离中心以及与此相关的城市作为一个有意义的实体的分崩离析。卡斯特尔面对的挑战是,如何改变发展的信息模式的方向,使全球流动与破碎的、部落化的地方认同能够重新结合。
关于城市高度理论化的经验让我们看到了关于城市的组织分析是怎样的。尽管大多数组织分析都起源于相对传统的组织类型中,卡斯特尔在全球化理论家和那些分析组织内部动力学的理论家之间架起一道桥梁,从而使我们能够想出一些方法,让研究可以对组织在城市层面所展现出来的范式和“结构”①一探究竟。这为研究组织的理论家提供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模型,用以理解资本的全球力量通过怎样的途径影响(特定地方的)人们对其生活管理和生活组织的干预。不管我们是否同意卡斯特尔对城市在全球流动性面前分崩离析的表现之诊断,他的确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定位,即说明城市如何在方法上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场所,让我们能够开始就城市组织的动力学问题展开探讨。
相反,那些准备研究城市组织问题的理论家则有意从一个完全机制的角度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他们对城市的分析从对一个机构本身的研究出发,比起市政委员会(Pipan and Porsander 2000)或城市开发组织(Schein 1996)这些将城市视作机构的空间,前者的角度更为传统。这也许并不让人感到惊讶,因为组织研究更趋一般化,更关注形式上的组织而非尝试更广泛地理解现代社会的组织特性(参见Chia 1999)。因此,将从事城市动力学研究的组织理论家的大部分研究称作城市里的组织研究比称作城市的组织研究也许更为恰当。然而尽管卡斯特尔对数据集进行社会学分析后得出的结论似乎超越事件发生的现场本身,但他更加倚重案例分析、人种学或者访谈等这些组织学者用来研究城市机构的研究方法,超越了我们的分析框架,带来了方式方法上的创新。近期关于组织研究领域的许多研究项目将我们的视线从机构动力学上转移开。这有可能结束“划时代转变”这种言过其实的断言——就连卡斯特尔也未能幸免这种倾向。譬如,芭芭拉·查尔尼娅维斯卡(2002)就曾运用比较的手段对华沙、斯德哥尔摩和罗马这三座城市进行了一次组织分析。比较与互动方法的运用,让她能够将其分析从对个别城市委员会的研究延伸为三个不同的地方更普遍的城市管理/组织过程的研究。查尔尼娅维斯卡认为,理解不同城市的关键在于认识它们的管理动力学,这种管理动力生发于她所说的“个人、团体、区域、组织、社区等既要考虑怎样国际化,又要考虑怎样保持本土特点”。
城市的信息基础设施的变化,正如我们所见,对于城市是全球化发生的关键场所的论断非常重要(Sassen 1991)。世界各地的大城市互相竞争全球城市的地位,就连小城市和发展中国家也不得不展示它们与全球的信息流和资金流的联系,并且自身也正朝着信息经济体的方向发展(Hultin 2007)。讽刺的是,网络技术的全球化潜力正是城市的场所营造活动产生的关键途径之一(Czarniawska 2002;Green et al.2005)。尽管像萨森这样关注全球资金流动的学者有被城市形成过程的观点同化的危险,芭芭拉·查尔尼娅维斯卡使用由国际化和本土化两个词组成的合成词则是一种重新思考全球进程与本地形态之间关系的尝试,其结果既非用技术决定论将这个领域击倒——在这个领域中连结性必然意味着全球性——亦非文化的固化僵硬,对场所的理解是靠其内在的动力,而对场所的研究则是通过“方法上的民族主义”。
三、作为信息的城市
如果方法的多样性是针对如何复兴城市作为组织的研究问题所给出的一个答案,那么对各种推理形式的开放包容则提供了另一条走出学科专业这个一直主宰着城市研究的死胡同的途径。例如,技术哲学领域的近作,就可以替代如前文所述的那类根据实证得出的、将城市视为一个被新信息技术变革改造过的场所的观点。
弗里德里希·奇特勒(1996)关于信息城市的论文极大地削弱了城市不过是由信息管理技术变革而来的这种看法。相反,他通过分析城市作为信息逻辑学本身的诞生地的构成,引出了城市和信息间更为深刻的关系。与卡斯特尔及其追随者的论断恰恰相反,奇特勒认为当代信息技术的意义不在于它们如何转变城市的组织动力学,而在于当代信息技术所赖以构成的物质逻辑起源于城市中某种原始的信息力量。对奇特勒而言,电脑主板上被用来在构成电脑的不同部件之间传递信息的那个零件叫做“总线(英语单词bus,也译作公共汽车——译者注)”并非巧合。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无意中构造出来的同音异义词,而是从城市交通运输领域直接借用到计算机技术领域的一个借用词。我们如今将这个时代很不严谨地称为信息时代,但对奇特勒来说,城市在此之前早已是信息化的了。
作为对城市动力学的分析,奇特勒的研究方法其目的不是在传统社会学分析的脉络中找寻统一的内在逻辑,也就是像卡斯特尔所依托的分析那样,通过积累和分析反映社会阶层的数据辨别出各种模式,或者让性别因素或经济状况成为城市如何组织的决定性因素。尽管奇特勒在文章中提到有一种相对连贯的逻辑让城市紧密结合着,但那并不是通过加总和平均得出的,而是通过对技术体系赖以建立和产生的语言以及物质进行更加辩证的、考古的分析得出的。
布鲁诺·拉图尔对巴黎的研究(Latour,Hermant,et al.1998)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出发,通过多重操作,了解他所跟踪的城市轨迹中哪些可以被解读为对城市进行彻底的信息分析,尽管这样做带有一个重要的前提。与奇特勒不同,拉图尔明确地远离信息理论所提出的信息逻辑,因为信息逻辑强调信息的交流潜力以及在允许信息“通过”时产生的噪音的摩擦效应。拉图尔对巴黎的研究建立在对该城各个地点的透彻了解上,也可以说城市就是透过这些地点由多种途径形成的。从负责制定街道命名的规划部门到高校管理者规划课程办公室,从负责饮用水供应的水务部门到巴黎街头咖啡馆里顾客与侍应之间的交流,拉图尔叙述着在巴黎同步发生的活动的细节,也正是这些“巴黎细节”,具有将巴黎塑造成为一个“自上而下的”构想出来的空间的效果。
城市的复杂性使其成为一个难以研究的对象,拉图尔正是受到这点启发。城市的规模无疑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决定到底要展开多少实证研究,而研究的着眼点又是什么。一座城市是由它的居民、物质结构、流经它的商品、管治这些实体的组织,以及除此之外的许许多多其他现象组成的。尝试理解所有这些秩序各异的实体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多少有些徒劳,再者,即便掌握了这里的每一种要素,也不太可能真正理解“城市”作为一个对象本身是怎样的。城市既大于其各部分的总和,又小于它们的总和;城市的精髓(如果这样东西真的存在的话)超越了其要素的细枝末节;而城市的身份似乎就是一种集体意义,即一座城市对其全体居民整体意味着什么,这仿佛已经锁定在城市的营销口号和经营活动里头。
为了厘清这些复杂性,拉图尔放弃使用抽象的描述方式,而是鼓励读者伴随他追踪构成城市复杂性的那些特定地点。对拉图尔而言,局部性是城市的一个特点,而不是一个需要克服的东西。根据他在城市里的考察,他悟出一个有价值的观点,即在我们的分析中怎样理解复杂的过程,以及怎样对付复杂的过程。
对拉图尔来说,度量、记录以及合理化城市空间的现代做法具有将城市打造成一个复杂的、适宜掌握技术的空间的效果。作为一个在历史上形成并且在政治上强有力的理解世界的方式,通过某种实践提供一个逻辑抽象空间的图景,这个图景中包括剥离不同秩序的表面影响,旨在创造一个标记、一个渠道或一个轨迹,从而能被追踪、重塑和重构,在此过程中城市得以重现。现代城市的诞生可以追溯到这类为了日后重组而展开的描述、铭记和抽象技术的出现(Foucault 1977;Rabinow 1989;Scott 1998)。②当代信息处理技术也可以看作以同样的方式追随着特点上现代化的技术,它们有能力处理越来越多的数据,展现出一幅世界愈来愈复杂化的图景(Dodgeand Kitchin 2005)。
相比之下,对拉图尔而言,复杂性就是各种秩序各异的事物之间产生的联系,而关于这种联系的描述必然有悖于上述抽象过程。复杂性是无法削减的,如果我们要描述一个如城市般的空间,但又不能再现也不能延续可以通过生成局部的抽象来理解城市的观点,那么我们就必须回归到描述复杂性这个问题上。
对拉图尔来说,复杂性不是复杂的他者,而是由不同的描述实践所产生的不同效果,就如同世界上不同的力量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一样。通过复杂性的描述来分析城市作为复杂空间的构成,拉图尔提供了一幅发展中的巴黎的图景,感觉上与城市缔造者的研究有着显著差别,后者是居住在给城市空间留下如此巨大的印记的规划师和设计师们的抽象概念里的 (Scott 1998)。拉图尔在研究这样一种形式的巴黎时所能够做到的,就是超越规划与实操、代表与经验之间的脱节,以及展示城市是如何在一个由复杂的社会物质实践带来的复杂理性化过程中产生的。巴黎的概念是一座无形的城市,这个说法让人惊讶,因为我们得出的唯一结论是,巴黎既存在又不存在——这个结论的确非同小可,它引发我们思考组织研究能为城市研究提供些什么,城市又能为组织研究提供些什么。
在之后的文章中,随着这些作者深入了解城市的缺位/存在,他们探讨文化和组织动力学,关注的焦点分别包括理性管理、小说、想象、集体行为以及经历等实践,通过这些模式我们能够富有成果地将城市作为组织空间来考察。第一篇文章,是De Cock写的,他将城市描绘成约翰·伯格小说中的那样。De Cock将目光投向伯格的作品中所体现出的城市和乡村的关系问题,犀利地批评了城市表现出的资本积累殖民力。他从伯格的全部作品中选取了三个例子,探索城市如何表现为边缘、排斥和压迫的空间。农民,作为边缘的代表,并没有像其他被城市排斥的群体那样被重新安置到其他地方,而是被置于一个当代城市经历的描述之中,那既像是压迫的寓言,又像是要摆脱城市这个由于资本的集中而产生一种主宰和控制的组织力量的专制的承诺。
Warren和Kaulingfreks将我们带回到通讯技术在当代城市中扮演的角色之中,不过他们用理性控制体系破坏了信息技术一贯的关联,将其注意力转向自组织的快闪族现象。他们特别关注“移动的俱乐部”,拆解和批评有关城市生活的分析,将其视为对社区的离间和缺失,指出我们需要通过重新思考社区这一概念本身,更好地欣赏城市空间中特定的关系形式。借用让-吕克·南希的文章,他们的论著把移动俱乐部作为“不具实操性的社区”的一个实例来考察,认为它不是一个由与理性规划有关的、对秩序和控制的追求推动的,而是通过纯粹的公众行动达到效果的自组织形式。不具实操性的社区既不是一种浪漫版本的社会凝聚力,也不是有组织的社会秩序项目,它实际上是一个描述信息时代城市生活政治的强大工具。
Beyes的文章则提及和延续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能通过关注破坏性的人为干预将城市理解为新兴体和不稳定的现象。他借用玛西(2005)的空间理论,以及朗西埃关于剩余的美学,探究维也纳一个有争议的艺术项目的设立,旨在通过诙谐模仿维也纳右翼呼吁驱逐移民和寻求庇护者出境的行为,吸引人们对有关奥地利移民的政治辩论的关注。Beyes展示了怎样通过新的更有力的方式揭示城市中的空间组织动力学,那就是在艺术暂时地打断和破坏传统上对我们认为是组织空间的特点的秩序的追求时,关注一种不稳定的政治信息。
Carter和Jackson的文章也详述了政治在城市的组织中所起的作用。通过对法西斯在的里雅斯特的建筑物上留下的铭文进行观察,两位作者受到启发。他们想知道如果认可了这些铭刻是一座城市的记忆、历史和意义,会带来什么样的分析潜力和学术责任。他们在城市中遇到了过去那个政治时代遗留下来的物品,通过对这些遗留所制造的分离状态和未知进行探究。他们提出了关于组织分析的可能性的重要问题,更通俗地讲,就是组织分析边界的问题。他们的疑问是,研究组织的理论家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挖掘信息对象并赋予它们意义?这能使我们对复杂的组织现象的理解告终吗?或者像Beyes所说的,这能像抹去美学剩余的政治描述力那样,删除或者减少组织的复杂性吗?
Phillips运用衍生法将城市在方法论上给予研究组织的理论学者可能性这个问题往前推进了一步。Phillips也对如何重新接触城市空间感兴趣。她漫步在购物商场这个熟悉的城市空间中,不以消费者的身份而以衍生法实操者的身份穿行商场,她重新发现商场这个场所与浪费有关的程度不亚于它与消费的关系,她还发现自己的注意力被像城市这样的组织空间形成过程中的无秩序趋势所吸引。
最后,我们以查尔尼娅维斯卡最先提出的观点来结束本文。她是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女性参与在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中的话语权与实践的角度,研究城市作为组织和非组织空间这一问题的。查尔尼娅维斯卡将城市划分为三个时代类型——近代、现代和后现代——她让读者思考女性角色是如何随着城市背景下各种破坏力量、无秩序角色、费解的主题以及变化的代理的不同而改变的。虽然女性经常被视为文明有序的城市管理发展方向的“他者”,查尔尼娅维斯卡还是希望我们能够从既依靠又承认女性曾经并且继续组织着城市方式的角度,重新思考如何看待现代追求秩序的意愿。
我们发现每一篇文章都通过对城市力量作为组织现象的分析尝试将城市呈现出来。每一篇文章提出的问题都对我们提出了质疑,要求我们从新的角度重新认识和审视城市。并且,在动摇对城市是什么和城市作为组织现象如何运作的传统描述时,每篇文章都用它们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们,对于组织复杂性的认识,我们还可以提出更加深刻的观点。这些文章所提出的问题向组织研究发出了挑战,采用新的方式理解城市作为组织的现象,采用描述的方式明确有力地表达城市所彰显的复杂组织。总而言之,这些文章反对我们将城市简单地视作追求秩序的一种意愿的结果以及由此产生的外部效应,而是呼吁我们对新的组织形式敞开怀抱。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感悟和想象才刚刚起步。
注释:
①使用“结构”这个词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将社会学体系中的结构概念具体化并带有将之与代理的概念对立起来的倾向。我们暂时用“结构”这个术语来描述组织通过其成员的实际操作所获取的形式的一种特征,而这么做前提是上述具体化问题对组织研究的学者们来说并不陌生。
②也可参见Toulmin (1992)里的一个思想实验,如果提出城市生活组织的模型是蒙田而不是笛卡尔,将会怎么样。
[1]Benjamin,W.1999.The arcades project.Cambridge,MA/London: Belknap Press.
[2]Castells,M.1989.The informational city: Technology,economic restructuring,and the urban-regional process.Oxford: Basil Blackwell.
[3]Chia,R.1999.Organized worlds: Explorations in technology and organization with Robert Cooper.London: Routledge.
[4]Czarniawska,B.2002.A tale of three cities: Or the glocalization of city management.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Dodge,M.,and R.Kitchin.2005.Codes of life: Identification codes and the machine-readable world.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23: 851-82.
[6]Foucault,M.1977.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New York: Pantheon Books.
[7]Gillespie,A.,and R.Richardson.2000.Teleworking and the city: Myths of workplace transcendence and travel reduction.In Cities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age: The fracturing of geographies,ed.J.O.Wheeler,Y.Aoyama,and B.Warf,228-48.New York: Routledge.
[8]Graham,S.2004.The cybercities reader.London: Routledge.
[9]Green,S.,P.Harvey,and H.Knox.2005.Scales of place and networks: An ethnography of the imperative to connect through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Current Anthropology 46,no.5: 805-26.
[10]Hannerz,U.1980.Exploring the city: Inquiries toward an urban anthropology.New York/Guildfor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1]Hannerz,U.1990.Cosmopolitans and locals in world culture.Theory,Culture and Society 7,no.2: 237-51.
[12]Hart,K.2000.The memory bank: Money in an unequal world.London: Profile Books.
[13]Harvey,D.2008.Right to the city.New Left Review 53: 23-42.
[14]Hultin,N.2007.‘Pure fabrication’: Information policy,media rights,and the postcolonial public.POLAR: Political and Legal Anthropology Review 30,no.1: 1-21.
[15]Kittler,F.1996.The city is a medium.New Literary History 27,no.4: 717-29.
[16]Lacour,C.,and S.Puissant.2007.Re-urbanity: Urbanising the rural and ruralising the urban.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9: 728-47.
[17]Latour,B.,E.Hermant,et al.1998.Paris ville invisible.Paris: La Decouverte - Les empcheurs de penser en rond.Available in English online as Paris the invisible city at http://www.bruno-latour.fr/virtual/ inex.html
[18]Massey,D.2005.For space.London: Sage.
[19]Mitchell,W.J.1995.City of bits: Space,place and the infobahn.Cambridge,MA/London: MIT Press.
[20]Molotch,H.1976.The city as growth machin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no.2: 309-32.
[21]Norris,P.2001.Digital divide? Civic engagement,information poverty,and the Internet worldwid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2]Pipan,T.,and L.Porsander.2000.Imitating uniqueness: How big cities organize big events.Organization Studies 21: 1-28.
[23]Rabinow,P.1989.French modern: Norms and forms of social environment.Cambridge,MA/London: MIT Press.
[24]Sassen,S.1991.The global city: New York,London,Tokyo.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5]Schein,E.H.1996.Strategic pragmatism: The culture of Singapore’s 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Cambridge,MA/London: MIT Press.
[26]Scott,J.C.1998.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New Haven,CT/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7]Simmel,G.1903/1971.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In 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 Selected writings (of) Georg Simmel,ed.D.N.Levine,324-39.Chicago,IL/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8]Toulmin,S.E.1992.Cosmopolis: The hidden agenda of modernity.Chicago,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9]Wheeler,J.O.,Y.Aoyama,and B.Warf,eds.2000.Cities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age: The fracturing of geographies.New York: Routledge.
Cities and Organisation: The Information City and Urban Form
Hannah Knox
What happens when we take ‘the city’ as a site of organization? The implications of posing this question perhaps explain why it has not formed part of the traditional epistemic apparatus of the organization studies community with its disciplinary claim to distinction and expertise.Analysts have a tendency to get lost in the city: the traditional modes of classification and organization that posit an object/subject,or structure/agent,tend to flounder when trying to come to terms with organizational features of the city.This editorial paper sets out a case for treating the city not as another object of attention for organization theorists in that all too familiar additive mode that recites ‘Organization Studies and ….’ (in this case ‘The City’).Rather we want to think about how cities and urban forces could be the site for an ongoing re-evaluation of the way in which organization theorists can engage with question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Collectively,these papers challenge us to go beyond seeing cities as simply the outcome of a will to order and the excess that this produces.Instead they ask us to open ourselves up to new forms of organization which,in this special issue,we have just begun to sense and imagine.
the city;urban;information;Latour;Kittler
F49
汉娜·诺克斯,社会人类学家,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社会文化变革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信息社会人类学、未来想象学、专门比较人类学等。
(编译:陈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