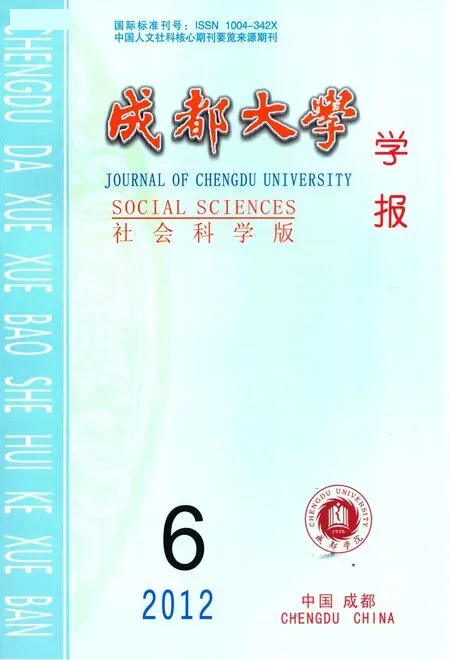三寸金莲哪去了?
——从林语堂英译本《浮生六记》看意识形态对译者的影响
2012-03-31徐寒
徐 寒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成都 610064)
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开始文化转向,研究者意识到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转换,开始强调翻译与权力,意识形态等文化要素的关系。作为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领头人之一,勒菲弗尔提出翻译即改写,受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的影响,其中意识形态最为重要[1]。而为了使其“改写”的作品被尽可能多的读者接受,译者往往会对原作进行一等程度上的调整,使其符合改写者所处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本文选取林语堂英译《浮生六记》说明意识形态对译者翻译策略的影响。
一
《浮生六记》是清代沈复于嘉庆十三年(1784年)所著的一部自传体散文。作者以平白朴实的语言娓娓道来其幸福的婚姻生活和平时的闲情逸致。虽然晚年遭遇家庭变故,伉俪情深却不得白头到老,但作者对生活的热爱、面对穷困潦倒的积极态度为后世所赞扬。《浮生六记》以其清新的格调、明畅的风格、生动的描写,引人入胜,并被译成多国语言广为流传,成为外国人了解中国古代风土人情的重要作品。
《浮生六记》现有三种英译本:林语堂最早于1935年将全文译成英文,他自称前后易稿不下十余次,分别在《天下》月刊和《西风》上连载,后来在英国的杂志发表,颇受推许;英国人谢林·布莱克(Shirley Black)于1960年第二次将其译成英文,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1983年白伦(Leonard Pratt)和江素惠(Chiang Su-Hui)合译该书,由企鹅出版社出版。
其中影响最为广泛的应该是林语堂的英文译本(简称:林译本)。有学者指出,“林语堂先生的《浮生六记》英译本,情感真挚,译笔灵动,优美流畅,流传甚广,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堪称翻译的典范。”[2]79然而,笔者将林译本同沈复原文对比发现,沈复在文中共有五次提到女性的小脚并持赞赏态度,林译本并未对其进行充分的翻译,或漏译,或直译,给并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西方读者造成一定程度上的理解障碍。林语堂曾在《论翻译》中强调“忠实是译者的第一任务”[3]264,为何他在此处却要“违背”原文作者的意愿呢?本文将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并探求其后的原因。
二
[译例一]
沈复:王怒余以目,掷花于地,以莲钩拨入池中。
林译:Wang looked atme in anger,threw the flowers to the ground and kicked them into the pond.
我国自古就有妇女缠足的陋习,到清朝尤为鼎盛,社会各阶层的妇女无论贵贱都纷纷缠足。沈复追求浪漫,崇尚自由,但他生在清乾隆年间,深受封建社会礼教的约束。当时男性对妇女的小脚可以说达到痴迷的态度,男性娶妻以大脚为耻、小脚为荣,沈复也不例外。古代诗文中如若提到妇女的小脚,则被视为增添美感的意象。宋代诗人苏东坡曾专门做《菩萨蛮》一词,咏叹缠足:“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立宫样稳,并立双跌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浮生六记》中沈复以“莲钩”代指王二姑的脚,实为一种赞美,也是透露了他对女性审美的标准,对于读者了解沈复其人以及当时的社会风气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近两百年后,林语堂翻译此段时,却未能译出“莲钩”这一重要的文化意象。西方读者大多不了解汉语言文化,译作是他们唯一获取原文信息的渠道。如果仅阅读林译本,则无法获取这一重要的信息。
[译例二]
沈复:芸曰:“脚下将奈何?”余曰:“坊间有蝴蝶屐,小大由之,购亦极易,且早晚可代撒鞋只用,不亦善乎?”
林译:“Whatam Igoing to do aboutmy feet?”she asked.I told her therewasa kind of shoes called“butterfly shoes”,which could fit any size of feet and were very easy to obtain at the shops,and suggested buying a pair for her,which she could also use as slippers later athome.
[译例三]
沈复:芸见势恶,即脱帽翘足示之曰:“我亦女子耳。”
林译:and seeing the situation was desperate,Yun took off her cap showed her feet,saying”looking here,Iam awoman,too
译例二、三讲述芸男扮女装随沈复参观灯会,为了掩饰小脚,买来“蝴蝶屐”,后来引起误会,不得已“翘足”证实女性身份。从原文来看,沈复并没有说明因为芸裹过小脚,所以需要遮掩才不至于露出马脚。中国读者深知我国的缠足风俗,小脚即是女性的象征,理解上并没有问题。这是原文本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共识”,并不需要点明,如果点明反而会画蛇添足,显得累赘。而对于不了解中国文化历史的外国读者,则可能产生疑问,为何男扮女装时需特别强调脚的伪装呢?为何看了脚就能证明自己是女性呢?诚然女性的手脚较男性小,那为什么是看脚而非手呢?林语堂在翻译这两段文字时,采取直译的策略,按原文译出未加解释。但“翻译是一个跨文化交流的过程,由于译入语读者对源语文化知识的缺乏,在理解译文中的文化词汇时会产生困难”[4],林译本有可能会对不了解中国缠足风俗的读者造成困惑。中国读者读到芸的“脚”会有一系列的文化联想,而西方读者只是将其当成一个普通的意象,并不了解其背后所包含的中国女性千百年来所承受的身心折磨。
[译例四]
沈复:余择一雏年者,身材状貌有类余妇芸娘,而足极尖细,名喜儿。
林译:I chose a very young one,called Hsierh,who had a pair of very small feet
[译例五]
沈复:邵鸨儿命翠亦陪余登寮。见两对绣鞋泥淤已透。
林译:and thewidow asked Ts’uiku also toaccompanyme to the room.Inoticed that Ts’uiku and Hsi- erh’s embroidered shoeswere already wet through and covered withmud.
译例四是说:沈复在外游侠时,遇见很像自己妻子的歌女喜儿,对其一见倾心。而让沈复对其宠爱有加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喜儿“足极尖细”。古代女子裹足,以三寸为佳,追求足部尖细之美。“足极尖细”如果直译为英语“She had a pair of very pointed and slender feet”西方读者如果读到这里,则可能感到惊讶,又尖又细的脚怎么会是一种美,这难道是反讽吗?林语堂将其意译为“a pair of very small feet”,则又丢失了原文信息。沈复突出“尖细”,这是高于“小”的另一种境界,“small”并不能充分表达作者的原意。
译例五中,林语堂将“绣鞋”译为“embroidered shoes”,从字面义来看,并没有什么错误。而此处沈复特别强调两位歌女的绣鞋被淤泥弄脏,是带有一种怜惜的情感。沈复热爱女性的小脚,而裹了小脚的女性必须时刻穿着“弓鞋”才能保证脚的优美形状。“弓鞋”上一般会有精巧的刺绣,因此此处沈复称“绣鞋”并不仅仅是“有刺绣的鞋”,而是他对女性小脚的指称。林译“embroidered shoes”则省略了这一信息,“会给不知情的英美读者带来异国情调的轻松愉悦之美感”[2]81,却不能使读者认真理解原文作者的意图。
三
“翻译家所做的不是一种简单的技术性的语言转换工作,而是一种赋予一种艺术以另一种面貌,让艺术作品在跨越了时代、语言、民族的界限之后继续保持艺术的魅力,让产生于某一民族和国家的艺术能为其他民族和国家甚至能为世界各国人民做共享的创造性工作。”[5]21《浮生六记》写于清朝,经过林语堂的翻译,沈复的自传能够在异国流传,西方读者也可以了解中国古代一对普通夫妇的闲适生活。然而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行为,许多在原语语境下普通的意象被译介到新的语境内则会丢失所承载的部分信息。中国读者阅读《浮生六记》,能从中了解到清朝男人对女性小脚的喜爱,而西方读者由于缺乏背景知识恐怕不会有相同的感受。
三寸金莲在沈复生活的时代,是美的象征,也是像他这种墨客骚人魂牵梦萦的女性特征。而这样一个美丽的意象在林语堂所处的时代,成为一种愚昧落后的丑陋象征。林语堂生于清朝末年的一个基督教家庭,从小接受西式教育,赴海外留学,归国后在国内多所高校任教。而清朝末年封建统治土崩瓦解,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其中也包括倡导女性放足的天足运动。林语堂翻译此书是20世纪30年代,此时辛亥革命已取得胜利二十余年,缠足这一陋习已为人深恶痛绝,逐渐废除。而他之所以选择翻译《浮生六记》,是因为他想要把芸——这个“中国文学史上最可爱的女人”的故事,流传于世,使西方读者了解一对平凡的两小无猜中国夫妇的处世哲学。文中的芸及其周围的许多年轻女性,活泼可爱,崇尚自由,敢于挑战封建社会的纲常礼教。而这样一群充满先进意识的女性实际上确实是一群小脚女人。欧洲上世纪初就爆发了女权运动,倡导女性自由,摆脱男性的压迫和束缚。在沈复眼里裹着小脚的女性是可爱的形象,但译介到西方,或许这一形象会大打折扣。
中国封建社会男性对小脚的痴迷暗含在沈复的描述中,符合当时的意识形态。而林语堂作为译者,将《浮生六记》译介到西方世界,如果单纯为了帮助读者读懂原文,那么有必要对文中的小脚做出解释。但作为译者,他受到所在社会意识形态以及英语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因这两组意识形态相互矛盾、冲突,原作者笔下优美的事物到了译入语文化中已经变形、扭曲、变质。或许正是由于此原因,林语堂译文中已不见沈复钟爱的三寸金莲。
“翻译的跨语言和跨文化性质,使得一些原本很清楚、很简单的词语,在经过了语言的转换进入一个新的语言文化环境之后,都会发生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形,从而导致出人意料的反应。”[5]162《浮生六记》向西方译介,文中多次提到的女性小脚这一文化意象,就在传播过程中消失了。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读者或许不会意识到原文还有这一重要的文化信息,这样一种变化与译者的翻译策略有着直接的关系,而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受到他所在时代意识形态的制约。林语堂学贯古今,兼通中西,经他翻译的《浮生六记》文笔流畅、引人入胜。但译者并不生活在真空当中,而要受到各种限制,经过层层限制得到的译文无法百分之百重现原文的风貌。正因如此,原文中三寸金莲的意象丢失了。
:
[1]Lefevere,André.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2]李玉良.林译《浮生六记》的得与失[J].山东外语教学,2005,(6):79 -83.
[3]林语堂.论翻译[A].罗新璋.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4]Blum -Kulka,Shohana.Shifts of Cohesion and Coherence in Translation [A].Venuti,Lawrence.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C].London:Routledge,2000.
[5]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6]沈复.浮生六记[Z].林语堂译.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