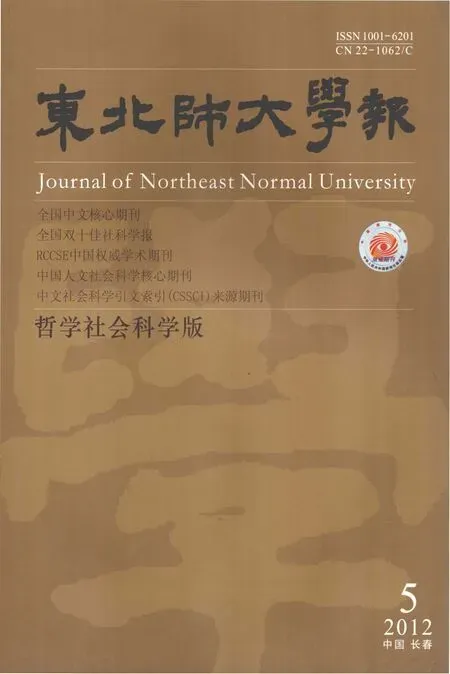经典重温的教育学意蕴*——在柏拉图与卢梭之间
2012-03-31侯素芳
侯素芳
(东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吉林 长春130024)
经典重温的教育学意蕴
*——在柏拉图与卢梭之间
侯素芳
(东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吉林 长春130024)
教育学的发展离不开经典的滋养,需要不断学习经典的教育情怀与建构教育学的方式。笔者从政治哲学的视角出发,重读柏拉图与卢梭的教育思想,对教育学的建构有三重意义:从自然正义到自然权利——教育思想价值取向的转换;从“统一”到“公意”——教育理论思维的传统与创新;从“隐微”到“直白”——教育思想叙述范式的个性化。
柏拉图;卢梭;自然权利;个体权利;统一思维;教育叙式
柏拉图与卢梭是国内外公认的教育思想史上的两座高峰。长期以来,众多学者不懈努力地开拓着通向两座高峰的道路,为后人研究做了大量铺垫。本文同样试图寻找解读经典的可能道路,并以此观照当下的教育研究,期望为教育学的建设贡献绵薄之力。
一、从自然正义到自然权利:教育思想之价值取向的转换
自然权利的思想在西方有着悠久的传统,自古希腊先哲们发现自然开始,人类就开始了对于人的自然权利的探寻历程。由苏格拉底、柏拉图创立的古典自然权利论为自然正义,强调基于理性基础上的人的道德完善,实质是个人对国家的义务。中世纪将神性重新纳入视野,托马斯认为人的自然权利中不能没有神学的地位,强调人作为基督徒的义务。现代自然权利论受自然科学发展的影响,自霍布斯开始力主排除托马斯自然权利中的神学。基督教神学用“自然状态”与“蒙恩状态”相区分,霍布斯则用公民社会取代了“蒙恩状态”,将自然状态中人的自我保全视为最基本的自然权利。卢梭同样倡导回归自然状态,提出人的自由、平等的自然权利。事实上,近代自然权利被纳入自然法后,以人的基本权利的面目步入国家宪法。自然权利是政治哲学的重要议题,柏拉图与卢梭都站在政治的高度分析、研究教育中的自然权利问题。
柏拉图的《理想国》追问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好的政治制度,在探讨理想政治制度建立条件的过程中引入教育问题,把教育看做是理想政治制度实现的一个重要条件。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好的政治制度?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编造了一个“高贵的假话”,他借助灵魂的不同等级,建立了一个金、银、铜铁三个等级鲜明、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各安本分的正义国家,这就是所谓自然正义。秉承自然正义的政治哲学,教育亦分成不同的层次,与灵魂中的欲望、激情、理性相对应分别进行情感、意志与理性教育以形成节制、勇敢、理智的美德。可以说,柏拉图的教育目的就在于协调人的情感、意志与理性,以培养正义的个人建构正义的社会。但是,这种自然正义是建立在等级特权基础之上的,实质是一种不平等的社会秩序,教育上亦是等级鲜明的,教育只是部分阶层的权利,自由只是部分人而非每个个体的,并且教育要服务于国家而非个体的发展,强调的是受教育者对国家的义务。
卢梭尽管在《爱弥儿》中郑重声称自己要培养的是自然人,而非公民,但借助教育建构理想公民社会的思想是不言自明的,《爱弥儿》中随处可见其对旧有社会制度的批判。什么样的社会是卢梭认同的好社会呢?一个包含自然权利于其中的实在法规治之下最接近人的自然状态的自由社会。卢梭在极大程度上吸纳了霍布斯关于人的自然状态及自我保存的思想,认同每一个人根据自然都具有自我保全的权利。但与霍布斯将人自我保存的欲望诉诸理性的算计不同,卢梭认为应将其归因于人的同情心。自然状态下人是自由、独立、平等、幸福的,通过社会契约去建立一个最为接近人的自然状态的公民社会,借助法律实现人人平等,而立法则奠基于个人自然权利基础之上的公意。《爱弥儿》实现了教育价值取向的个体转换,建立在人的自然权利基础之上的个体权利成为教育出发点。“一般的教育方法还有一个错误是,首先对孩子们只讲他们的责任,而从来不谈他们的权利。”[1]103,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受教育权利人人平等,唯其如此,才能保证建立一个权利平等的社会。
柏拉图的自然正义观确立了权利观念的理性主义传统,即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通过抽象的理性推理、而非行动或实践的历史方式,确认人的权利是人作为人应当具有的权利,政制的功能就在于为此权利的落实提供制度保障。他的自然正义是等级制,实质是特权阶层的个人对国家的责任与义务。而卢梭则有意摆脱形上的法则,试图采用历史的方法,从发生学的角度出发以自然状态作为研究的起点,认为自然状态下人有自由、平等与独立的自然权利。从上述政治哲学思想出发,二者在教育的价值取向上存在明显不同,实现了教育价值取向的转换,即教育从服务于国家发辗转向个体发展,从强调对国家的义务转向个体权利。虽然二者在教育的价值取向上意见分殊,但仔细追究不难发现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都在于对人的存在的本体论追问,这恰恰是政治哲学的特性——“政治哲学不过是对于真实传统的言说,它只是固执地守护着对‘人’之理型的标准,即便在经验的人群中,这种‘人’已经荡然无存。”[2]15
问题在于,今天我们如何看待自然权利?教育研究如何直面这种追问?“今日人们对于自然权利的需要,一如数百年甚至上千年来一样地显明昭著。拒斥自然权利,就无异于说,所有权利都是实在的权利,而这就意味着,何为权利是完全取决于立法者和各国的法院的。可人们在谈到‘不公正’的法律或者是‘不公正’的决断时,显然是有着某种意涵,有时甚而是非如此不可的。在下这样的判断时,我们指的是存在着某种独立于实在权利而又高于实在权利的判断是非的标准,据此我们可以对实在权利作出判断。”“拒斥自然权利注定是要导致灾难性的后果。”[3]2-4当任意而盲目的喜好成为行动的最终原则时,人们处于极度的疯狂。当下的教育也不过如此而已,要扭转疯狂的局面,需要一个标准。柏拉图与卢梭关于自然权利的思想为判断与评价人的存在价值确立了标准,同时也就为评判教育的价值确立了标准。对教育上的启示在于,在这个日渐疯狂的时代保持一个冷静的头脑,时常自问什么是好的教育、什么样的人是好人。同时,教育价值取向的转换需要教育学认真对待个体权利问题,为个体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提供观念上的支持。
二、从“统一”到“公意”:教育理论思维的传统与创新
“思想的‘前提’,是思想构成自己的根据和原则,也就是思想构成自己的逻辑支点,它具有‘隐匿性’和‘强制性’。其一,思想的前提是思想中的‘一只看不见的手’,是思想构成自己的‘幕后操纵者’,这就是它的‘隐匿性’;其二,隐匿于思想活动中的思想前提,它规范人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即规范人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内容、行为方式和行为内容,这就是它的‘逻辑强制性’。”[4]孙正聿在《前提批判的哲学理论》一文中指出,对构成思想的前提的反思就是对构成思想的根据与原则的反思,以此反观柏拉图与卢梭的教育思想,探寻他们思想的逻辑起点,可以发现,在二者的教育哲学思想中都隐藏着个体与社会“内在统一”的思想前提,他们的思想都为这种“内在统一”的思维方式所规范与强制。这种“内在统一”在柏拉图表现为国家的正义与个人正义同构,国家的美德与个人美德一致,国家的目的与个人目的相同,而在卢梭则表现为“公意”。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国家的正义和个人的正义是没有区别的,因为言辞中城邦的结构与个人的灵魂结构是完全相同的,如同国家由三种人即生意人、辅助者与谋划者组成一样,人的灵魂由理性、激情与欲望构成,“在国家里存在的东西在每一个个人的灵魂里也存在着,且数目相同。”“个人的智慧和国家的智慧是同一智慧……个人的勇敢和国家的勇敢是同一勇敢,使个人得到勇敢之名的品质和使国家得到勇敢之名的品质是同一品质,并且在其他所有美德方面个人和国家也都有这种关系。”“我们以什么为根据承认国家是正义的,我们也将以同样的根据承认个人是正义的。”“国家的正义在于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每一个人如果自身内的各种品质在自身内各起各的作用,那他就也是正义的。”[5]由此可见,在《理想国》中,城邦的整体利益就是个人的利益,城邦的幸福就是个人的幸福,城邦的目的就是个人的目的,二者是完全“统一”的。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公意”的思想,在揭示社会契约的意涵时卢梭写到:“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6]20所谓公意就是人民共同体的意志,即共同体所有成员的普遍意志,是每个个体将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转让给整个集体的结果,当然,转让的前提是集体的意志能够代表每个个体的意志。这样,公意即共同体的意志就将每个个体的意志纳入其中,使二者合二为一。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共同体与其各成员之间的约定是“合法的约定,因为它是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它是公平的约定,因为它对一切人都是共同的;它是有益的约定,因为它除了公共的幸福而外就不能再存任何别的目的……只要臣民遵守的是这样的约定,他们就不是在服从任何别人,而只是在服从他们自己的意志。”[6]40可以说卢梭的公意学说的前提仍然是个体与群体“内在统一”的思想。
柏拉图所设计的城邦具有“空间性”的本质特征,空间就是秩序[2]254。这种秩序的建构依据城邦各组成部分按一定的比例关系组合,当然组合最终的依据是每个组成部分的美德之高下,借助人的理性力量追求和谐的城邦秩序。这种空间理论强调整体的秩序和谐,而这种整体秩序的和谐依赖于个人内在灵魂要素间的和谐,所以教育的起点落实到个体的灵魂,特别是个体的理性的培养,哲学王的判断力是最重要的,但更为关键的是这种理性,这种判断力的价值取向却是整体的,个体既要有独立的判断,有自主的追求,又要受制于整体的要求,为了整体而放弃自我。事实上,在《理想国》中,柏拉图的理念论、知识分类学说都在从哲学的高度肯定“一”的价值,理念是决定一切个别事物存在的根据,个别相对于一般是微不足道的。柏拉图整体与个体的“内在统一”是以遮蔽个体为代价的,这种思维方式不足以解决他的悖论。卢梭的“公意”以共同体的同质性取代个人意志的差异性,同样将社会的整体性置于个体的特殊性之上,以社会的自由取代个体的自由。所以尽管在《爱弥儿》中卢梭郑重声称他要培养的不是公民而是自然人,但却指出学会自爱的教育不是真正的教育,而由自爱进入到爱人是爱弥儿的第二次诞生,只有此时,“我们对他的关心照料才具有真正的重要意义”,从自然天性出发的“自然人”首先是其理想国度中“公民”、“爱国者”、“民族的人”的统一体[7]。以整体自由取代个体自由,这与他毕生关注个人自由,力主保障个人自由权利是相违背的。这也正应了他自己所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6]4为了探寻人的奴隶生存状态合法性的根源以使人摆脱奴隶枷锁的努力,却又最终为人带来新的压制,制造了又一个悖论。
上述分析让我们看到,个体与社会的统一作为教育理论思维的前提已经成为教育理论建构的传统,对教育理论研究产生了长久深远的影响,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个无法解决的悖论。如何才能超越这个传统?这种学说的真正价值何在?问题关键不在于他们是否解决了这个悖论,而在于他们清醒看到这一悖论的存在,看到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正如施特劳斯谈到卢梭时的评价:“问题就不是他如何解决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而是他是如何看待那种无法解决的冲突的。”[3]260问题真的不能解决吗?抛开试图放弃这个问题的思想家不谈,尼采后的现代哲学家们已然另辟蹊径,例如罗蒂在总结了一些现代哲学家的努力后指出:“形上学理论希望向我们证明,自我发现和政治用途可以合而为一,从而把我们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结合起来。形上学理论希望提供一个不会分裂为私人与公共两部分的终极语汇。形上学理论希望同时达到私人小我面向的美和公共大我面向的雄伟。”公共与私人之间的对立是“无法在理论中加以统一”的[8]。既然无法统一,势必要打破“统一”神话,现代哲学家的方法就是将二者分离。“要克服这种悖论的后果,唯一的途径就是超越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及其元意识,确认‘个人之私’、‘个人之善’与‘社会之公’、‘公共之善’的‘游戏边界’,在‘后形而上学’视域中重思二者各自相对独立的游戏规则。”[9]这种分化的思路对于教育理论中如何解决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难题无疑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借鉴,打破“统一”神话,树立边界意识,为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分别建立行为规范,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采取不同措施保障个体权利是教育研究值得尝试的。
三、从“隐微”到“直白”:教育思想叙事范式的个性化
“在教育研究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思想与语言的错位:二者的发展总是不协调。一方面不断有新的想法出现,另一方面这种想法却由于理论语言传统的限制而很难加以表达。”[10]丁钢在《声音与经验:教育叙事探究》一书总序中的这段话,让我们的目光聚焦到表述思想的语言。事实上,学术研究领域的“宏大叙事”早已被质疑,批评的核心在于以抽象的理论语言难以表达丰富多样的事实,并由此发展为“转向叙事”的研究范式,以使语言在最大限度上接近所表达的事实。其实,无论是“宏大理论”还是“叙事转向”,目的都在于对“真相”的把握,所不同的是在表述思想的语言之间存在的巨大张力,突出体现的仍然是思维方式上的差异。语言到底能在多大的程度上逼近人的思想?这个问题本身表明了人们对于语言在思想表达功能上的态度转变,它打破了一直以来人们对于语言力量的自负。由此反观柏拉图的生动对话及卢梭的激情告白,豁然明朗,思想的表达原来可以如此不同。
柏拉图擅长“隐微”的言说,他用对话表达思想,作为一种非权力欲的言说,强调的是对人类的基本问题的体悟。“看似作为讨论起点的对某一概念(如勇敢)的共识,其实却是讨论所难以真正达到的终点,其原因何在?因为真正的定义乃是行动的自然合理的发生,这是真正的‘言说’,它所要求的不是对现象的逻辑表达,而是对本原的体悟。准确的定义只能在对本原的真正的体悟中达到,只有在这种体悟中,才可能做到在任何情境下合理地实现‘德性’的要求。”[2]234体悟的实现常用的手法是神话与譬喻,《理想国》中这个特点特别突出。借助于人们的想象及“了解之同情”,《理想国》为读者敞开丰富的内涵。比如关于牧羊人那可以让人隐形的神奇戒指,表面上看柏拉图在说无论什么样的人,只要有条件都会行不义之举,却隐讳地表达这样一个预示:“正义的城邦要消除隐私。”[11]再比如最著名的建国神话即“高贵的假话”和精彩的洞穴比喻,表面上在呼唤民众关切自己的灵魂转向,隐讳地暗示了哲学生活与民众生活冲突的现实性。“他隐微的教诲则是真正的转向只有极少数人才能达成,哲学生活不是每个人的志业,也就是默许哲学生活与民众生活之间的难以跨越,同时又有意唤起每个人哲学生活的可能性。”[12]特别是在阐发教育为实现心灵转向之内涵时所用的洞穴比喻,为读者敞开了巨大的意义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他强调的是人的认知、意愿与行动的统一,不仅有助于我们对问题本身的理解,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反思自我,反思自我的现实生活方式以及与理想的生活方式之间的距离,使人向着理想的原型回归,不断地进行自我“关照与行动”。
卢梭的语言表达方式特别“直白”。他的作品往往在开篇就鲜明地阐明观点,读来印象深刻。比如在《社会契约论》第一章的开篇即点题:“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这种变化是怎样形成的?我不清楚。是什么才使这种变化成为合法的?我自信能够解答这个问题。”[6]4在《爱弥儿》的序言中直书:“我们对儿童是一点也不理解的:对他们的观念错了,所以愈走就愈入歧途。”[1]2这种直白的真话也可以有不同的讲述方式。在《社会契约论》中采用的是唯理论[13]的方法,重视逻辑推理,在逻辑上奠定政治权利的理论基础;而在《爱弥儿》中则采纳了文学形式,以艺术手法诠释自然教育思想,其中有许多著名的叙事,比如为使爱弥儿形成财产观念的种蚕豆,培养好奇心、观察力的参与魔术表演,触觉锻炼中夜间去教堂取《圣经》,学习依据太阳的运行确定方位时的森林迷路,自然后果法等等,都已成为经典的教育叙事。
按利奥的“叙事性解读”,柏拉图不是在建立理想国,而是以“三大浪”在解构理想国,其中处处体现的是他的“知性真诚”,他在以巨大的勇气面对问题,不论这种真诚采用了哪种表达方式。即便是“隐微的教诲”,也是由于苏格拉底之死让他做出的明智选择,既能保护自己又要讲出真话。卢梭更是以“说真话”而著称,《忏悔录》的开篇与结尾都在表明一件事,“我说的都是真话”。他们极具个性化的表达风格来自于各自的生活体验,所言说的都是公共话题,这就是“知性真诚”、“说真话”背后的力量——出于对公众利益的关切,一种拯救危难的情怀及对于真理的执著,而绝不是一己之私利。他们的言说充分表现了语言与公共空间的本质关联。另外,柏拉图选择对话作为写作方式是出于对语词日渐抽象化和脱离语境的抗拒。借助于对话为我们上演了一幕幕生动的戏剧,“观众”置身于剧情之中,与剧中人物共同经历一场理性的探险,所收获的是语词的意义指向及潜移默化中心灵的提升,它绝不是语言游戏,更没有蓄意的化熟悉为陌生甚至出于包装需要而揉搓语言。卢梭的叙事虽然直白,但却有“揉搓”我们心灵的力量。二者写作风格上的巨大差异,充分彰显了思想、进而教育思想之言说的语言张力。
在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中,言说体现了希腊关于人的本质的认识,但这种言说不是现在意义上单纯的说,而是“言行的和谐”。亚里士多德总结“人的本质是作为言说者而存在”,说明言说是人的生命状态的表征,一个人如何言说也就如何生活。在此意义上讲,柏拉图与卢梭间的语言张力恰好说明了二者不同的生命状态。那么依此反观自身,我们的生命状态如何?进而教育学的生命状态又如何?毫无疑问,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反思我们的文化,因为我们及我们的教育学的生命都是在既定文化背景下展开的。正如人们所总结的,中国现代史有个根本特征,那就是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矛盾,一方面我们要学习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另一方面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又要批判现代西方文明,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任务的迫切性最终使现代性建设为之让路,造成现代性发展的中断,直到20世纪80年代重新开始启蒙历程,90年代受西方“后”学影响,在现代性尚未完成的同时,反思现代性思潮兴起,使我们处于既要建立现代性又要批判现代性的尴尬困境。在此过程之中的教育学同样经历了启蒙理性与政治理性的双重洗礼,当下也正在遭遇现代性与反抗现代性的双重拷问,经历现代性与反抗现代性的话语权的激烈争夺,其中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行政权的干预。要在说什么和怎么说的双重层面实现平等对话,情形并不乐观;究竟是谁在执掌话语权,也许情况相当复杂,但真正成为主流的声音一定是能抚慰众生心灵的。重温经典,解读其个性化的教育语言,起码可以让我们的教育言说增加一些清醒的自觉。
[1][法]卢梭.爱弥儿:上卷[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洪涛.逻各斯与空间——古代希腊政治哲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3][美]列奥·斯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M].彭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4]孙正聿.前提批判的哲学理论[J].社会科学辑刊,2008(1):4-5.
[5][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441C-D.
[6][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7]朱旭东.试论卢梭的现代民族国家教育思想[J].高等师范教育研究,1997(6):71.
[8][美]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M].徐文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68.
[9]贺来.边界意识和人的解放[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85.
[10]丁钢.声音与经验:教育叙事探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1.
[11][美]尼柯尔斯.苏格拉底与政治共同体——《王制》义疏:一场古老的论争[M].王双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77.
[12]刘铁芳.从柏拉图洞穴隐喻看哲学教育的可能性[J].教育学报,2008(8):9.
[13]李平沤.主权在民VS“朕及国家”:解读卢梭《社会契约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17.
On the Pedagogical Meanings of Rereading Classic Between Plato and Rousseau
HOU Su-fang
(Faculty of Education,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Rereading the educational ideas of Plato and Roussea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has three pedagogical meanings:first,from natural justice to natural rights——the transformation of value orientation of educational thought;second,from “unity”to“general will”——the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in educational theory thinking;third,from the“esoteric”to“frank”——the narrative paradigm of personalized education thought.
Plato;Rousseau;Natural rights;Individual rights;Unity thinking;Educational narrative paradigm
G40-09
]A
]1001-6201(2012)05-0205-05
2012-03-20
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9B047)。
侯素芳(1968-),吉林辽源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教育学博士。
* 本文部分内容源于本人博士学位论文:个体权利视域中的教育现代性的正当性。
[责任编辑:何宏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