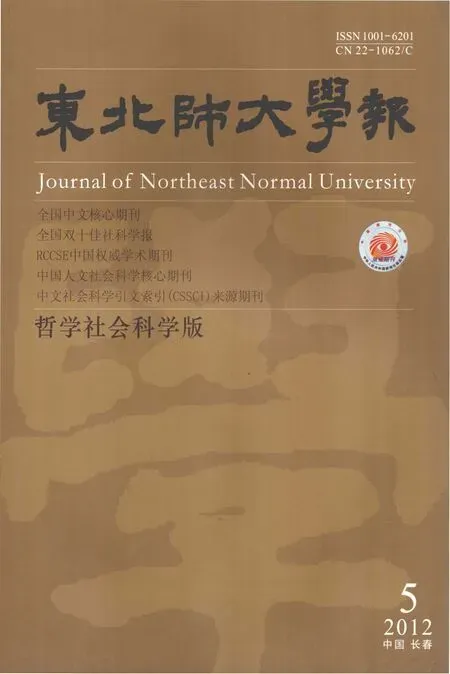我国警察裁量基准发展探析
2012-03-31李韧夫王星元
李韧夫,王星元
(吉林大学 法学院,吉林 长春130012)
我国警察裁量基准发展探析
李韧夫,王星元
(吉林大学 法学院,吉林 长春130012)
警察权力的控制是行政法学界关注的焦点,警察裁量基准是解决警察裁量内部控制的关键因素,是连接合理行政与合法行政之间的桥梁和纽带。警察权的膨胀使得包括立法控制和司法控制在内的传统外部控制手段面临巨大的挑战,警察裁量基准制度是行政机关面对这一挑战所应用的一种自我控制制度。警察裁量权的控制研究应当从以往关注程序研究的范式转为关注实体研究的范式,将警察裁量的基准作为研究重点之一。大量警察裁量基准投入应用的同时,制定主体不明确、评估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也阻碍着警察裁量基准制度的发展。完善警察裁量基准、规范警察裁量权,对于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与个案正义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警察裁量基准;内部控制;评估机制
一、警察裁量基准概述
Charles H.Koch.Jr.说:“行政法被裁量的术语统治者”[1]。理查德·B·斯图尔特论及警察裁量权控制的途径时谈到,明确警察裁量权的规则并使之法律化,只有依据事先已经知晓的规则并不偏不倚地予以适用,政府才被允许干预重大的私人利益[2]。警察裁量在实践中一方面数量巨大,种类繁多、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裁量的结果往往不能达到令公众满意的效果,这使得行政机关面对公众的质疑而努力寻找政治合法性与政治和理性之间的黄金分割点,警察裁量基准也已成为化解这一困境的关键,警察裁量基准研究是警察自由裁量研究由程序走向实体的必然发展脉络。
“行政裁量基准”的概念来源于德国,法学家毛雷尔对于裁量基准的定义为:“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将行政机关依据授权解释相关法律的行为规范化,并以此作为裁量的依据。”[3]余凌云将行政基准定义为对规范行政裁量行为的标准制度化。笔者认为,警察裁量基准是警察裁量的基本准则,其目的是实现个案正义而保障相对人合法权益,警察裁量基准由公共政策、行政惯例、行政规则组成。
二、警察裁量基准存在的问题
(一)警察裁量基准制定主体过多
警察裁量基准的制定主体过多一直是导致基层执法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涉及公安领域的行政主体不仅包括各级公安机关,还有相关政府部门,如中国共产党党委政法委员会(简称政法委)。上到公安部,下到部分事业单位的保卫部门都成为了裁量基准的制定主体。省、市、区县都制定了大量的裁量基准,这使得裁量基准种类多、数量大,一线执法的警务人员的业务水平在对裁量基准的掌握上存在难度。不同制定主体在制定裁量基准的过程中缺乏沟通,致使裁量基准制度之间关联性不强。
(二)某些警察裁量基准过于严格,影响行政效率
由于个案的复杂性,警察在面对具体的裁量事件时需要必要的回旋余地,进而更大程度上实现个案正义。行政效率与个案正义平衡往往需要警察在裁量过程中进行把握,过于细致和严格的裁量基准必将减损行政的效率增加行政成本。正如戴维斯的“线性官僚机构”(line bureaucracy)理论认为约束行政行为的规则和行政主体的裁量权分别是两个点,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达成二者之间的平衡。而这一平衡点的把握在我国当前的警察裁量基准实践中往往不令人满意。
(三)警察裁量基准执行不力,监督不足
警察裁量基准制度在实践过程中受到执法习惯和执法环境的影响,我国行政法治领域比较重视法律法规的直接规定,对于自由裁量领域重视不足,警察裁量的场合具有即时裁量的特点,对于执法人员要求较高,我国警察裁量基准数量众多,以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为例,仅涉及违章罚款的事项就多达94项。加之我国基层执法人员普遍专业素质偏低,导致整体对于警察裁量基准制度的执行不到位。对于违反警察裁量基准制度的行为的监督不足,一方面,警务公开力度不足,加之警察裁量基准制度数量众多、内容庞杂,导致行政相对人对于警察裁量基准制度及其内容不了解;另一方面,警察在执法过程中与相对人之间的裁量行为有“封闭性”,裁量结果有“及时性”。实践中践踏警察职责的行为监督起来却十分困难,一方面,相对人是“受益方”很难进行举报、申诉;另一方面,警察违法危险性低,违法行为没有第三方参与、见证,来自外界监督很难奏效。
(四)警察裁量基准配套制度不健全,保障措施不完备
警察裁量基准在实践中缺乏相应的配套制度,行政公开制度、公众参与制度和警察裁量基准制度受司法审查的相关制度的影响,没有及时得到发展。湖南省政府2008年颁布的《湖南行政程序规定》一定程度上为行政裁量提供了制度支持,余凌云教授认为,对于警察裁量权的程序性控制是最基本的控制,因此完善相应的程序性制度是警察裁量基准制度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但类似的制度在警察裁量基准领域比较少。警察裁量基准制度在推广方面重视程度不足,对警察培训机构投入不足,没有形成系统的培训模式,相比之下美国警察局重视警察培训,所有培训都要依据被培训者的工作表现和系统设计的需要进行评估,实行局长负责制,并设立培训委员会专门负责培训工作。
(五)警察裁量基准所涵盖的领域具有局限性
警察裁量基准所涉及的范围相当有限,相应的,其作用和功能也有限[4]。警察裁量基准制度可以应用于警察权的范围是有限的,以美国警察法为例,警察裁量基准制度无法调整警察组织的裁量权。警察裁量基准制度目前在实践中主要应用于警察处罚和许可领域,但是需要强调的是除此以外在抽象行政行为领域、行政政策领域也存在着很多形式的警察裁量权力,由于很多原因,这些领域很难寻觅警察裁量基准的身影。当今警察裁量权的主要问题在于,一方面当为而不为,即警察裁量权的不作为或称之为怠惰;另一方面不当为而为之,即存在裁量权力的滥用。
三、警察裁量基准的未来发展
(一)规范警察裁量基准制定主体
首先,在部委统筹的基础上明确地方警察裁量基准的制定主体,对于警察裁量权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关系进行权衡。我国地域广阔,城乡、区域发展存在较大差异,可以考虑以重点发展省级指导下的县、市级别的警察裁量基准,其优点在于一方面行政资源丰富,专业水平较高,另一方面兼具地域代表性,其制定的制度能够反映出当地的实际,而对于基层的制定主体要进行规范。国务院《关于规范行政裁量权的指导意见》中也对不同层级制定的裁量基准的效力进行细化,进而规范基层行政基准制定主体。
其次,大力发展行业协会等公益性组织参与到警察裁量基准制度的制定中来,提高公众参与的水平。以2005年北京成立的中国警察协会为例,成员主体为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及其社团组织,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NGO),接受公安部的业务指导和民政部的监督管理。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进行公安理论研究,各级警察协会是可以参与到警察裁量基准制定过程中的非营利性组织的代表,非营利性组织(NGO)可以更广泛地整合社会资源收集信息,NGO参与到警察权力控制领域是行政权力控制民主化的需求,成为推进民主事实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发挥非营利性组织在警察裁量基准制定过程中的作用,有益于制定更为合理规范的警察裁量基准制度。
(二)通过建立科学评估机制完善警察裁量基准制度
在工作中使用长效评估机制取代日常评估,评估作为一种制度化安排,已经成为了一种国际惯例。在我国,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都有权对警察裁量基准制度进行评估审查,本文主要研究行政机关的内部评估审查。2003年公安部指导境内公安机关进行警察法规和规范性清理工作,警察裁量基准就是重点之一。警察裁量基准评估的方法有以下几种: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方法。“分析优于定义”是科斯的名言[5]。通过比较项目的全部成本和效益来评估项目价值的一种方法。成本效益分析作为一种经济决策方法,将成本费用分析法运用于政府部门的计划决策之中,以寻求在投资决策上如何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方法进行评估处理后的警察行政法更符合实际的需求,更为实用。价值分析方法也是评估的重要手段,价值在英语中为value,法语中的valeue,德语中的wert,何中华认为:“所谓价值,既不是有形的、具体的存在所构成的实体,也不是客观对象与主体需要之间的满足与被满足的关系,而是人类所特有的绝对的超越指向。”[6]价值分析方法通过选择对象、情报收集和功能分析等几个主要的程序,寻找提高价值的途径。同Cost-benefit analysis相比,价值分析更关心道德与权力,因此符合价值分析的警察裁量基准更合乎公众的心理预期和价值标准。
警察裁量基准的评估标准涉及使用何种尺度对警察裁量基准进行评价,笔者认为这一标准至少应当符合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裁量基准应当符合公平正义。胡锦涛总书记2005年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的讲话中指出:“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力争使相同裁量基准下的相对人能够得到同等对待。其次,警察裁量基准应当符合实际,具有较强操作性,同时裁量相对人能够容易的知悉。警察裁量基准的内容和尺度应从实际出发,并以个案为落脚点,突出体现裁量过程中的应用性。同时,制定的裁量基准要清晰明确,易于了解认知,这样既可以减少执法过程中的矛盾冲突使裁量结果更容易被接受,也能促进行政相对人对裁量主体行为的监督。再次,警察裁量基准应当符合现代行政观念认同的成本利益关系,即制定并付诸执行的警察裁量基准所支付的成本是可接受的。
(三)提高警察裁量基准的公众参与
警察裁量基准的公开,不仅是促进公众有效了解警察裁量基准的前提,也是建设专业化警察队伍的重要途径,更是实施问责制的一种重要信息保障。不断公开和扩展的信息会成为追究责任的一种有利工具,如果对出现的问题一味地隐瞒,永远也不可能真正使责任追究到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建立规范的信息公开制度是服务型政府制度设计系统中一项基础性的环节。其中制定信息公开法,规制政府信息公开活动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7]。警察裁量基准公开的理论依据具体包括:人民主权理论和知情权(right to know)保障。人民主权理论,即国家最高权力属于人民。但在一个大众民主的时代,我们更需要提防的不仅是公共权威借人民主权的名义所进行的暴政,我们还需要提防的是人民主权本身,防止“多数人的暴政”,由此对于人民主权理论应当运行于合理的范围之内。知情权是指在公民与政府的关系中除法定的特殊情形外,公民在法律上有权获得政府档案和文件的权利。实践中,它具有请求权的性质,即公民有权要求有关国家机关公布它们应当公布的某些信息,因此一般也称为政府信息公开[8]。警察裁量基准的公开是人民主权和公众知情权的必然要求。信息公开是警察裁量基准高效运行的前提和保障,同时公开也是参与的基础。
公众参与是指社会群众、社会组织、单位或个人作为主体,在其权利义务范围内有目的的社会行动。公众参与强调及时、准确的交流和沟通,使公众更加了解政府和公安机关制定的裁量基准,公众参加决策过程并且防止和化解冲突。我国要实现宪政,这一目标我国行政部门同政党要求是一致的[9]。一直以来,公众参与的范围和参与的程度都是关注的焦点。随着社会法制建设的发展,更多的公众参与制度被强制性的规定下来,但从整体上看,公众参与范围较小,参与质量不高,参与多以被动的形式出现,实践中政府和公安机关缺乏对参与公众的尊重,强者往往以指挥调度的角色出现。公众参与警察裁量基准的制定现阶段比较少,局限于对于处罚和许可事项的听证程序,由于参与方没有最终的决定权,其参与基础就相对模糊。完善当前警察裁量基准的公众参与一方面要切实提高警察裁量基准公众参与符合秩序前提之下的有效性,同时要通过制度设计拓宽公众参与的途径。
(四)加强警察裁量基准的监督
“监督”二字在《后汉书·苟或传》中曰:“古之遣将,上设监督之重,下建副二之任。”“监督”的英文是“supervision”,是由“super”和“vision”两部分合成。前者是指位居上方,后者指审视。合起来就是“位居上方加以审视”的意思[10]。古往今来权力的使用,制度的运行都离不开监督,警察裁量基准作为规范警察裁量的制度,其本身也需要受到监督,可以划分为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前者主要包括:立法部门监督、司法部门监督、社会团体监督、公众监督和媒体监督等,后者指行政机关内部对于警察裁量基准的制定、执行进行监督。
立法部门的监督通过对警察裁量基准制定后的备案和审查实现,着重审查裁量基准的合法性、制定主体资格、制定程序等方面,对于裁量基准的内容审查较少。警察裁量基准的司法监督,由于我国当前没有把警察裁量基准列为法院审理的范围,所以实践中就出现了法院只能审查警察裁量行为,无法审查警察裁量基准,这对法院诉讼范围提出了挑战。社会团体监督随着我国NGO等公益性质社会团体的发展会在警察裁量基准监督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应推动立法保障公众监督和媒体监督的实现。
[1]Charles H.Koch,Jr.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J].54Geo.Wash.L,Rew,1986:469.
[2][美]理查德·B·斯图尔特.美国行政法的重构[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42.
[3][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594.
[4]徐文星.现代政府与行政裁量权[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299.
[5]于立深.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在行政法上的运用——以《行政许可法》第20、21条为例[J].公法研究,2005:113.
[6]何中华.论作为哲学概念的价值[J].哲学研究,1993(9):29-34.
[7]王丽莉.服务型政府:从概念到制度设计[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158.
[8]吴江.公共危机管理能力[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5:63.
[9]宋海春.依宪执政:以宪法思想的与时俱进为先导[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61.
[10]毛昭晖.监督学[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8:2.
On Discretion Benchmark of Chinese Police
LI Ren-fu,WANG Xing-yuan
(College of Marxism,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China)
Control of the police power is the focus of attention by the administrative law scholars,the benchmark of police discretion is a key factor to solve the police discretion internal control,is the bridge and link between the reasonable administrative and legal administration.As the expansion of police power,legislative control and judicial control,including traditional means of external control is facing enormous challenges,police discretion benchmark system for the executive to face this challenge,apply a system of self-control.Control of police discretion should be changed from the previous focus on program research paradigm to the physical study of police discretion benchmarks as one of the key.A large number of police discretionary basis,put into use at the same time,development of the subject is not clear,the assessment mechanism is not perfect also hindered the development of police discretion benchmark system.Improve the police discretionary basis;regulate police discretion,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administrative counterpart case of justice to achieve significance.
Police discretion benchmark;Internal control;Evaluation mechanism
D912.1
]A
]1001-6201(2012)05-0048-04
2012-05-04
吉林省教育厅“十一五”社科研项目(吉教科文合字[2010]第600号)。
李韧夫(1954-),男,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星元(1981-),男,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吉林警察学院学报编辑。
[责任编辑:秦卫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