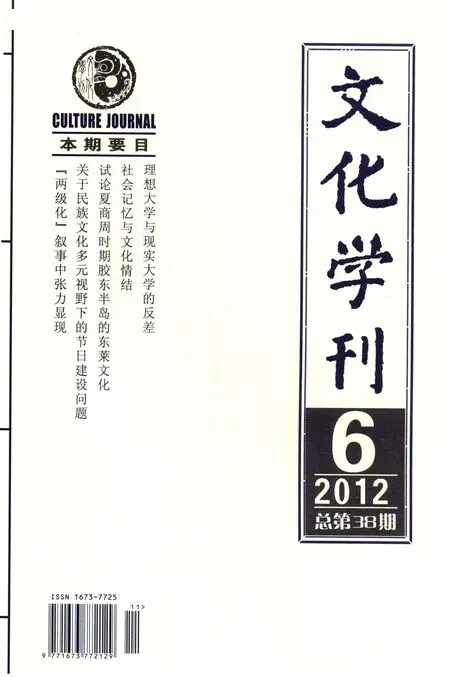“闳稽群籍,博约精审”:明代史学研习的拓新之作——《明人汉史学研究》评介
2012-03-20郭江龙
郭江龙
(作者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国古代史学发展演变至明代,到了一个较为特殊的阶段。宋代士人好谈心性,讲究义理之学;清代学者则黜虚崇实,重考据之学。明代处于学术理念全然不同的两个时代中间,在学术发展理路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对于明代史学的研习可探清自唐宋以来学术史的内在发展脉络,可达“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用。谢国桢云,“有明一代,史学最盛,若焦竑之《献征录》、王世贞之《四部稿》、何乔远之《名山藏》、郑晓之《吾学编》,恢弘典则,蔚为巨观。”而清代以降,学者对明代史学甚为贬低,尤以四库馆臣之流,厚诬明人,多有訾议,但闻明人史著,多有“明人恣纵之习,多涉疏舛”之语,诸如此议不可谓持平之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代史学的研究渐趋繁荣,综合性专著“浩如烟海,汗牛充栋”,有关明代史学史的研究,在最近出版的史学史著作中亦颇受重视,多现拓荒性佳作。近读朱志先博士的明代史学史专著 《明人汉史学研究》,获益匪浅,如饮甘醴,笔者不惴浅陋,特撰此书评,籍以浅抒己见。《明人汉史学研究》一书,凡43.2万言,蔚为大观,由湖北人民出版社于2011年5月出版。是书共有六部分,文章结构分为上、中、下三编。第一部分为绪言,探讨作者选题意义,学术史回顾与前瞻,文章结构与思路以及创新点和难点;第二部分为上编,“鉴往知来与劝善惩恶思潮下汉史研习的实践功能与道德价值”,介绍明代前期汉史研究重视“史鉴”功用的特点;第三部分为中编,“明中叶文学复古运动影响下《史》、《汉》的艺术性借鉴和学术性考释”,探讨明代中叶,思想文化领域发生变动之际,《史》、《汉》文本研究的新动态;第四部分为下编,“明后期理学裂变下汉史学的多样化趋向”,介绍晚明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理学)受到冲击,明代学者的汉史研究呈多元化发展;第五部分为余论 (明人汉史学研究的整体评价),对明人研究汉史学的特点、汉史学对明代学术的影响以及明人汉史学研究的不足进行综合归纳、缕述;第六部分为附录,其中作者罗列出诸多表格,包括“《千倾堂书目》中所列明人研究汉史著作一览表”、“明人《史记》、《汉书》、《后汉书》刊刻情况一览表”、“明人汉史评论著作情况一览表”等10个表格。
明代对《史记》、《汉书》等汉史文本研究较为繁盛,如作者所云:“明初朱元璋终身不离《汉书》,且‘迁固之言与经训并传’;明中期大量《史记》、《汉书》刊刻,批点《史记》、《汉书》蔚然成风;晚明评论、考证汉史亦是蔚为大观。”此前学界对明人汉史研究关注较少且较为局限。学界对此研究多是从文学评论的角度,探讨《史记》、《汉书》的笔法、文体等方面,从史学角度关注甚少。对明代史学评论关注仅局限于王夫之、李贽等几个大家,忽视了《史记评林》、《汉书评林》等汉史文本,未能从整体上把握明人汉史学的发展状况。另外,学界对于唐代、宋代以及清代汉史的研究已经展开,而且对于明人史学的研究已经涉及到元史学、宋史学、《史通》学等几个方面,对于明人汉史学的重视程度实为不及。因此,《明人汉史学研究》的问世,在此方面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学界的空白。作者在书中明确界定了“明人汉史学的概念”,即“明人对汉代史实及其载体的研习活动及其成果”①《明人汉史学》第11页到12页中“绪言”部分还明确界定了“明人”与“汉史学”的概念。“明人指曾经在明代生活较长时期,并受明代社会意识影响的人,包括服务于明朝的元朝遗老、明朝人及明遗民。”;“汉史学指后人对两汉的历史事实及其载录文本 (《史记》、《汉书》、《后汉书》、《汉纪》、《后汉纪》、《东观汉记》、《资治通鉴》等)”,进行学习、评论、考证、论述、刊刻、节录、摘抄等整理及研究活动所形成的成果和学问。。此外,是书涉及到四个层次,第一,汉代历史及其载录文本(即明人汉史学研究之对象);第二,明人对汉代历史及其载录文本的研习及其成果 (即明人汉史学);第三,明人汉史学对明代史学、学术、文化及社会的影响(即明人汉史学研究的历史地位)。综观是书,笔者最印象最深刻的特点有三个。
首先,作者突破了之前仅从文学角度研究明代《史》、《汉》研究诸文本的局限,从史学的角度对明人汉史学研究及其载录文本进行研习。关于对《史记评林》和《汉书评林》的研究,作者从其文本载体的内容及撰写方法入手,探析凌稚隆对《史记》研究的成就与贡献。作者指出《史记评林》具有“内容上的广博”、“体例上的严谨”以及“《史记》版本选择上的慎重”的特点。在撰写内容上,作者考证出“以明代为例,就有王鏊、何孟春、王韦、杨慎、许应元、王慎重、柯维骐、凌约言、董份、茅坤等人对《史记》所载史实作的评论和考证。并且对散见于各个名家文集中的有关对《史记》的评点之作进行了汇总。”作者认为《史记评林》在体例的编排上“是根据《史记》篇章的顺序,正文部分是《史记》的内容,并且保留了《史记》的原有风貌,而相应研究内容,则置于对应史事所在页面的眉首,或者在一篇的末尾加以佐评。不像其他一些评点本,只是把《史记》的内容进行概括罗列,然后加以评点。”关于《史记》版本的选择,作者发现“凌稚隆在对《史记》进行研究时,非常注意版本的选择,选用最好的宋本和汪本为底本,并且把不同版本进行相互校对,以免出现错漏之处。”对于《史记评林》以及《汉书评林》的研究,作者突破了文学角度研究的局限,从历史编纂学切入对其体例,版本以及编纂内容等方面进行广泛地研究。
其次,从细微之处入手,展开个案研究,以此深入探讨明人与汉史学的关系,进而从整体把握明代史学的发展脉络和面貌。晚明时期,市场经济发展,以“王学”为主流的思想意识形态受到冲击,学术思想氛围较为宽松,明人对于《史》、《汉》文本的研究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向。晚明遗民群体在特殊历史环境下,对两汉历史的研习是晚明汉研究多元化表现的一个方面。作者在明遗民汉史研究中,以顾炎武作为个案研究,从微观入手,通过对存有大量有关汉史学研究的《日知录》进行整理,来探求晚明学术动态的新变化。作者通过研究发现,顾炎武在其《日知录》的汉史研究中,充分运用了“排比史实,归纳其特点”的方法,他在研究中“罗列大量史实,最后以及其精简的语言点出问题所在,其归纳出汉代‘占法之多’、‘都乡侯’、‘《史记》、《通鉴》兵事’等条目,皆如上例,在芜杂的史实中,寻其异同,辨其是非,可谓‘徵引详赅,考据亦颇精审’”,达到了“错综其理,会通其旨”的目的。另外,据《明人汉史学研究》载:“《日知录》中所涉及汉史内容,有关治道之处,主要论及汉代的风俗教化及官制之事,常常是‘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论及两汉风俗教化和汉代官吏任用及权力分配两方面,作者亦援引《史》、《汉》,结合顾亭林于《日知录》中的札记论断加以评释,凸显了其在汉史研究中 “经世致用”的特征。对于顾亭林在汉史研究中所涉及的博约考证之学,作者也有重点论及。在顾氏《日知录》中,对于《史》、《汉》的研究有多条注解和考证,第二十七卷中专门为《史记》、《汉书》、《后汉书》设立条目,加以注解。对于汉史考据“疏通源流,考证其谬误”,作者考订出顾亭林对汉史的研究主要包括“考辨事实、指正脱字衍文、注释生僻字词、辨析后人所续之文等等”。更可贵之处在于作者在研究顾氏考辨、注解汉史文本的同时,对于顾氏汉史考证的瑕疵之处也加以整理、缕述。兹举其一例,在论述《后汉书·马援传》中关于马援拜“伏波将军”,这一称谓的前后文笔叙述次序问题上,①见《明人汉史学》第320页,作者引《后汉书·马援传》,卷24先叙,光武帝常言“伏波论兵,与我意合”,后又言“交趾女子征侧及弟征贰反,攻没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蛮夷皆应之,寇略岭外六十余城,侧自立为王。于是玺拜伏波将军”指出顾炎武在论述“伏波”称谓顺序时产生的误读。顾炎武认为这是范晔采择,摘录诸书“率尔成文”,忽略了前面叙述的“伏波”二字没有依据。作者在顾氏此论断中清楚地指出“此论比较勉强”,这种叙述次序可谓范晔所用倒叙之手法,而顾炎武称其为“率尔成文”,不太妥当,这属于顾氏对于史料的误读。作者对于顾氏汉史学研究的辨析、考证之细,由此可观矣。
最后,是书将明人汉史学研究、明代的历史背景与学术思潮相结合,作者在把握时代脉搏的前提下,俯瞰明代学术的发展状况。明代中叶,王学的兴起逐渐取代了理学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明代士人的汉史研究也随之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出现了新的风格变化。在万历之后,社会舆论控制逐渐松弛,学术氛围较为宽松,于是以王世贞、唐顺之、李梦阳等为代表的明代学人对汉史学的评论、解析屡现创见。另外杨慎、柯维骐等人对于汉史的考证也为明中叶汉史研究的多元化增添了新的元素。作者在中编“明中叶文学复古运动影响下《史》、《汉》的艺术性借鉴和学术性考释”中,便将明人汉史学研究与当时的社会思潮以及时代的变迁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作者认为明代中叶,在文学复古运动发展的影响下史学界对《史》、《汉》的研究亦兴起,表现在对汉史文本的研究与吸收。两汉史学文本古籍大量刊刻兴起,说明“明中叶,由文学复古运动引发的,对《史》、《汉》的文学性借鉴,已蔚然成风,其风格各异,气象万千,层次高下,各有千秋”在文学复古的影响下,出现了对汉史学尚具规模的评析与考证,最后汇聚成了经典的《史记评林》与《汉书评林》。
《明人汉史学研究》作为一部探讨明人对于汉代史实及其载体进行研究的专著,以明人与汉史学的关系为切入点,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学界关于明代汉史研究的不足。作者从四个层面深度剖析明代学人关于 《史》、《汉》文本的研究,从对文本载体的考证、史论、刊刻、摘节等多个方面对明代汉史研究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探析。作者在书后附录的10个表格亦突出了其综览群籍和博约考证的学术功底,关于明人《史》、《汉》研究的刊刻、节录、评论等诸表格所载书目信息详实、完备,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甚巨。《明人汉史学研究》的问世,确有明代史学研究拓荒之功,实可谓嘉惠学林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