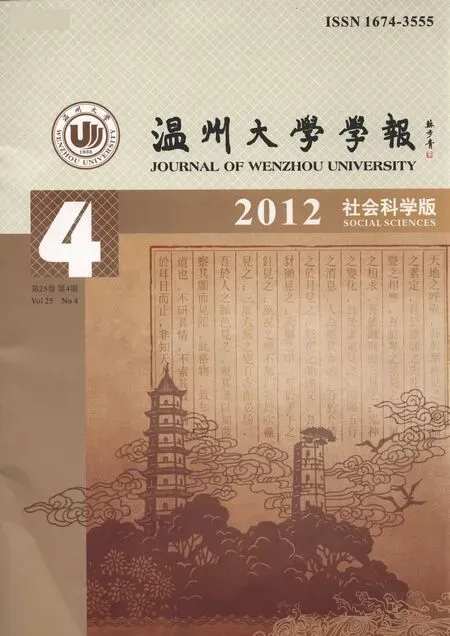“教案”概念考辨
2012-03-19冯雪梅
温 瑞,冯雪梅
(1.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北石家庄 050024;2.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教案”概念考辨
温 瑞1,冯雪梅2
(1.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北石家庄 050024;2.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教案研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教案”概念的多样性使教案研究混乱丛生,因此对“教案”概念的再探究实有必要。近代的学者基本能够把握教案概念的准确含义,只是在后来的一段时期,受政治上左倾思潮的影响,教案概念中揉入了反帝色彩,教案概念因此一度被曲解。由于严格意义上的“教案”概念给教案研究带来诸多掣肘,因此狭义、广义双重“教案”定义的提出实有必要。
教案概念;基督教;近代中国
教案研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20世纪80年代掀起的教案研究热潮直到今天方兴未艾,成果层出不穷。但关于教案研究始终存在着一个问题:“教案”概念的多样性。众多研究者给出了关于教案的多种定义,致使其概念混乱不清。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对教案概念进行探讨实有必要。
一、疑团始现:问题的提出
在查阅《教务教案档》①参见: 文献[12]: 237-637.吕实强.教务教案档: 第二辑[M].台北: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74:121-385.文献[10]: 109-397.时,笔者发现档案内所载的案例五花八门;在统计教案数量时,疑团始现:这么多的案例形形色色、光怪陆离,难道它们都是严格意义上的“教案”吗?于是,笔者开始有意识地梳理教案研究史,发现学术界并没有给统一教案概念这一问题以足够的重视,各研究者都是给“教案”自行下定义,导致教案概念丛生。这一方面缺乏严谨的品格,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教案研究的深入展开。
(一)百家争鸣:多元教案概念并存
20世纪80 – 90年代,整个大陆掀起了教案研究的热潮。此时,绝大多数学者对“教案”持“反洋教运动”或“反洋教斗争”的观点。兹举几例:“在近代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中,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和统治的斗争,即简称‘教案’或‘反洋教运动’”[1];“中国近代史上的教案即群众反洋教事件,是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正义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2];“频繁发生于19世纪后半叶的教案,亦称民教斗争或反洋教斗争,是中国近代史上颇具特色和影响的重大事件”[3];“教案,是近代中国官、绅、民联合发动,反对西方列强在华的基督教而出现交涉的案件”[4]。
当时已经有部分学者注意到了学术界把教案概念等同于“反洋教运动”或“反洋教斗争”这一问题。何桂春在《试论近代中国教案发生的根本原因》一文中提到:“从1848年3月的江苏‘青浦教案’到 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的五十余年中,以中国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各阶层人士反对西方教会侵略的斗争(有人称‘教案’,亦有人称‘反洋教斗争’),多达400多起。”[5]但作者并没有把教案和反洋教斗争进一步加以区别。徐梁伯提出应该取消“反洋教运动”这一概念,以“教案”代替,并对“教案”下了定义:“所谓‘教案’,即在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利用教会侵略中国,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和斗争,清政府以主权国家的身份行使自己的司法权,按照中外纠纷的性质,接受诉讼,立案处理的全过程。”[6]受文化大革命时期革命史学观念的影响,作者的观点带有明显的反帝色彩。当然,也有学者专门对教案概念加以辨析,如董丛林在《中国近代的“教案”、“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和“反洋教”辨析》一文中专门对“教案”、“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和“反洋教”三个意思相近的概念加以辨析,并提出了与众不同的“教案”概念:“所谓‘教案’,是指外国教会势力与中国人之间的冲突事件中‘诉诸官方以司法和政治手段解决的案件’。”[7]应该说这种提法已经比较客观公正。
进入21世纪,教案研究依然保持升温的状态,同时各研究者对教案概念的定义也更加科学。赵树好在他的著作《教案与晚清社会》中给晚清教案下了定义:“晚清教案是指中国官绅士民反对基督教会(教士教民)的事件,这些事件是经中国官方立案,并会同外国传教士或领事、公使处理的。”[8]该定义不像20世纪70 – 80年代那样带有盲目的反帝色彩,致使与“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反洋教斗争”等概念相混淆。
(二)重新释义:“教案”概念再探究
“教”,指的是基督教。一般来说,基督教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基督教在中国往往特指新教(俗称“耶稣教”),广义的基督教则“包括天主教、正教和新教以及一些小的派别”[9]1006。本文所提及的基督教是指广义的基督教;“案”,是指“涉及法律的事件或政治上的重大事件”[9]41。结合晚清具体社会情况,我们不难得出“教案”的概念,“教案”是指基督教在华传播的过程中,教会势力与非教会势力①本文所研究的“教案”强调教会势力与华人之间的冲突, 教会势力与外国人之间的冲突不予考虑.发生的冲突事件中,经官府立案并诉诸法律或政治途径加以解决的案件。“教案”构成要素有四:
其一,冲突双方必须涉及教会势力和非教会势力两方面的政治力量。教会势力主要是指案件中涉及到的教士、教民或者教堂,非教会势力则主要是指案件中涉及到的清朝官员、士绅以及普通民众。如果案件仅涉及到一方政治力量的话,则该案件称不上“教案”。例如:《教务教案档》载同治十二年(1873年)年法国驻华公使热福理照会总理衙门请求查办直隶省张里厅张正身霸占教民煤窑一案。经调查:该处“非教民之山”且“早经完案”[10]298。在此案中,法国驻华公使和总理衙门都卷入进来,此案的处理颇经一番周折。在对案件进行处理时,官府开始误以为被张正身霸占的煤窑主人是教民身份,后来经核实,实际上其并非教民。这个案件是中国人内部非教民之间的纠纷,因此不能算作“教案”。
其二,冲突双方矛盾的解决必须诉诸司法或政治手段,具体表现为经过官府立案解决。晚清时期,基督教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掩护下破门而入,其强行传教之举使中国人把其与侵略者视为同类,“他破坏了家庭;他干涉了祭祖礼节;他把那已经深入在他们生活中的佛教和道教的仪礼说成是邪教,而对于他们传统的先师孔子的训迪,并不称之为‘圣’;他要求他的教徒们,对于本乡村和家庭的祭典的维持,停止贡献。”[11]基督教强烈的世俗干预性致使民教之间摩擦丛生,大事小事多如牛毛。如果民教之间私下把矛盾化解,即没有经过官府立案,则该类事件称不上“教案”。例如:同治四年(1865年)直隶省武强县一个菜茄引发的命案。河南屯村孀妇魏马氏幼子魏奔楼摘食教民杨熊家的菜茄。这晚,杨熊找魏奔楼理论,二人争吵斗殴,杨熊被魏奔楼抛砖掷伤头颅,第二天因此毙命。田廷献乡约魏鸿太禀明县令冯文展。事关人命案件,不可不查,冯县令要求开棺验尸,杨熊之父杨俊豪坚决不从,并称私下里已经和解,此事与县令无关。该事件中,虽然有人毙命,虽然冲突发生在民教之间,但双方选择在私底下解决问题,没有经过官府立案侦查。因此,该案件不应计入“教案”之列。
其三,有具体的冲突形态,即有具体的事件生成才可称为“教案”,例如暴力斗殴、控告纠纷等,捕风捉影、闻风而起的照会算不上“教案”。同治九年(1870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被打死,外国修女、商人死伤多名,使馆、教堂和店铺被焚烧。西洋人见识了中国人反洋教斗争的决心,他们对自己的传教行为开始谨慎起来。天津教案之后,各国公使加强了对本国教会的保护,闻风动辄照会总理衙门请求查处某地反教或禁教情况。总理衙门也总是责令地方官员派兵调查,但调查结果往往是“查无此事”。据笔者统计,天津教案之后直隶省诸如此类的“查无此事”的照会事件有7件①参见: 吕实强.教务教案档: 第二辑[M].台北: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74: 282-332.文献[10]:278-32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室,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清末教案: 第二册[M].北京: 中华书局, 46-55.,这些照会不应计入“教案”之列。
其四,有教民参与并关涉教务的事件才算“教案”。晚清时期由于基督教的传入,教民具有多重身份②晚清教民在不同人的眼中有不同的身份: 在平民眼里他们是沾了“洋气”的“二毛子”, 在官方眼中他们是疏离大清的另类百姓, 在洋人眼中他们只是普通的大清子民.教民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参见: 邓常春.晚清教民的尴尬身份: “二毛子”、“另类百姓”、“大清子民[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6, (5): 217-221.,有些冲突是因其大清子民身份而非基督教信徒身份而起,故这类案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教案”。关于这一点,总理衙门在致地方政府的函文中也屡次强调:“通饬各属州县,嗣后凡遇教民滋事各案,必先审度案情关涉教务与否,倘与教务有关,自应按其所控,斟酌办理;若系干犯中国禁令,并不关涉教务,即由该管官照例讯断,不必因其习教稍涉宽纵。”[12]542
只有包括以上四个构成要素,才能构成严格意义上的“教案”。但学术界在研究教案时却出现了概念多样性的问题,为进一步澄清和界定教案这一概念,下文将分析教案概念的被曲解过程。
二、拨云见日:“教案”概念的被曲解过程考察
自基督教传入中国以来,传教士与中国民众之间就存在着程度不同的矛盾,有些矛盾进一步激化,遂形成“教案”。近代的学者基本能够把握教案概念的准确含义,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一段时期,受政治上左倾思潮的影响,教案概念也被带上“左”的色彩,教案概念中揉入了阶级斗争的理念,教案概念因此一度被曲解。
(一)时人对“教案”概念的理解
光绪四年(1878年),布政使川东道姚道酌拟民教善后章程11条,以期民教相安,其陈述中涉及到什么是教案的问题。“从前民教互斗,必关涉传教士,遇有伤死或拆毁教堂,方谓之教案,浸假而失其本意。凡遇民间词讼一有教民在内,或自知理屈讼不能胜,投入彼教。即向该主教捏诉。该主教司铎即出头扛帮,因而通谓之教案。”[10]1359姚道看到了教士乱用“教案”名目,以期把事情挑大,从而庇护教民,进而从中渔利的一面,故提出使用教案二字应当谨慎。同时,姚道无形中提出了他对“教案”的理解:必关涉传教士,需有伤死或拆毁教堂,不能因为关涉教民就称之为教案。姚道接着谈到:“要知教民平民皆是中国百姓,今之习教者,遍地皆是。词讼之内,有教民者指不胜屈,亟应将教案二字划清界限,嗣后凡遇民教互控,必关涉教事或传教士,遇有死伤或实系拆毁教堂房屋,方谓之教案。其教民与平民词讼,无论案情大小,均按中国律例,照约由中国自行办理,不得牵列教案名目。”[10]1359至此,姚道的观点愈加明朗,即必关涉教事或传教士,遇有死伤或实系拆毁教堂房屋者才能称为教案。民教之间冲突大大小小多如牛毛,怎能都按照教案名目处理?姚道意在言明地方官拥有对教案的处理权,以限制传教士胡乱干预诉讼的行为,从而减少民教之间的冲突。同时,姚道无形中表露了其对教案概念的理解。
光绪二十年(1894年),时任贵州开州知州的陈惟彦在《辨开州无教案》一文中也对教案的概念有所涉及。教民卢复生“赁刘裕兴屋设药肆,行踪诡秘,唆讼扰民,民愤甚,且酿事端”①[清]陈惟彦.辨开州无教案[C]//陈惟彦.宦游偶记: 卷上.民国7年排印本.1,陈惟彦将其护解出境,回其老家,将刘裕兴之房产充入中国之书院,不料法使横加干预,照会总理衙门,索还刘裕兴屋并告陈惟彦违背条约。总理衙门不明真相却屡催陈惟彦尽快把开州教案结案。陈惟彦据理陈述:“民教悉中国人,即应守中国之法,以中国之官治中国之民,以中国人之房产充入中国之书院,与教堂绝不相关,法主教乃云故违条约,某遍查条约,并无地方官不能治教民之条,更无教士可以干预地方公事之条……余复以开州并无教案,贵阳府函牍迭至,商略通融发还刘裕兴店屋,余复以此案与教堂毫无牵涉,如屋由外人索还,势必成为教案。”①3陈惟彦的反驳很明确地告知贵阳知府:教民卢复生索还刘裕兴店是中国人内部之间的纠纷,应由中国官员来处理,与教堂无涉,更与传教士无关,教案从何而来?因此,开州并无教案。陈惟彦在陈述开州民教纠纷时无形中透露了时人对教案概念某些方面的理解:并非有教民参与的民教冲突就是教案,如果民教冲突不关涉教务,则该类冲突事件不算“教案”。
(二)20世纪30 – 40年代学者眼中的“教案”
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关于教案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并取得一些成果。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有《清季教案史料》[13]二册,辑录了军机处档案中所存有关教案的各国照会;吴盛德、陈增辉合编的《教案史料编目》[14],内有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有关教案的中文史料目录,分为道咸年、同治年、光绪庚子前和光绪庚子及庚子后四个阶段;王文杰著有《中国近世史上的教案》[15],对教案的缘起、基督教在中国的传布情况以及13个典型教案进行了论述,它“是关于中国近代教案最完备的一部作品”[16];陈步青在《评<中国近世史上的教案>》一文中对“教案”亦有所提及,“最早传入中国之佛教,其时间远在汉代,即景教之传入中国亦远在唐初,此等宗教传入中国之后,与当日之士庶均颇能相安无事,因此乃无所谓教案,有之亦仅属统治者命令式的禁止,至于毁教堂,杀教士,以至于因此而与外国演成兵争之事则绝无。及至近世则不然……官府与民间反教之紧张情绪与日俱增,毁教堂,杀教士之不合理举动,亦层见叠出,教案之发生亦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7]他认为统治者、官府和普通民众都可成为“教案”冲突的一方,毁教堂或杀教士应成为构成“教案”必不可少的因素。
从以上分析来看,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诸多学者对“教案”概念的把握基本规范,并没有出现后来与“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反洋教斗争”等概念相混淆的情况。
(三)“教案”概念的变形
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政治上的左倾思潮和群众运动影响到了史学领域。同年,历史学界掀起了“拔白旗、插红旗”的史学革命运动,批判史学界的资产阶级思想,主张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史学,“对阶级观点的强调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被否定得只剩下了农民起义才有积极的意义”[18],“史学界的学术观点、理论探讨都变成了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斗争”[19]。文化大革命发生后,左倾错误思潮严重泛滥,“史学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19],历史被任意裁剪、解说,甚至歪曲、篡改、穿凿。这直接造成了史学界很多成果有失客观公允。
这一时期,近代中国教案的研究出现了“反洋教运动”、“反洋教斗争”、“群众反帝爱国运动”、“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等字眼。受史学革命运动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教案研究多带有浓重的反帝色彩。李时岳的《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20]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论述民教矛盾的专著,其从群众反帝运动的角度着手,正好顺应了当时国内政治运动的形式,接着有《反洋教运动》(《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的再版)[21],其观点与《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一脉相承。此外,还有南史所著《天津教案——1870年天津人民反洋教斗争》[22],天津历史研究所天津史话编写组编写的《火烧望海楼——1870年天津人民反洋教斗争》[23]以及一系列关于天津教案研究的论文,学者们多从反帝爱国运动的角度入手,定性天津教案为天津人民发动的一场反帝爱国运动。
受政治上左倾思潮的影响,史学研究中揉入了太多的阶级斗争的理念,教案研究也不例外。这直接导致了20世纪70 – 80年代“教案”概念与“反洋教斗争”、“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等概念混淆不清的恶果,泛滥的左倾思潮使原本相对科学的“教案”概念发生了变形。
三、问题的解决:“教案”双重定义的提出
(一)严格意义上的“教案”定义带来的掣肘
如上文所述,笔者对“教案”概念加以定义,并称此概念为严格意义上的“教案”定义。但当笔者严格按照此定义统计案件数量时,问题又出现了:教会势力与非教会势力之间的很多矛盾冲突不能计入“教案”名目之内。有些事件因未关涉教务而不能计入“教案”之列,有些事件因未经官府立案而不能计入“教案”之列,有些事件则因资料不全、结果不详而不能计入“教案”之列,教会势力单方面的照会则更不能计入“教案”之内。但以上这些事件均能反映双方之间的矛盾冲突,均有利于教案的研究。教案研究的初衷是对基督教在华传播过程中教会势力与非教会势力发生的矛盾冲突的研究,若要舍弃这些具体事例,就会导致研究内容的缺损。
(二)狭义、广义双重“教案”定义的提出
鉴于以上所述存在的问题和困境,笔者大胆提出“教案”的双重定义。上文中所述严格意义上的“教案”可以称为狭义的“教案”,笔者在此又提出广义的“教案”的定义,即:基督教在华传播的过程中,教会势力与非教会势力发生的所有矛盾冲突事件。一切能反映这二者冲突的案例均列其内。
广义“教案”概念理解起来相对宽泛,其提出目的是解决按照狭义“教案”定义进行研究所带来的问题。因此,我们应该倡导在史学界使用广义“教案”概念,特别是对区域教案进行研究时,这一概念的提出将大大有利于研究的进行。
[1]牟安世.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和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C]//四川省近代教案史研究会, 四川省哲学社会学会联合会.近代中国教案研究.成都: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 1-17.
[2]丁名楠.关于中国近代史上教案的考察[J].近代史研究, 1990, (1): 27-46.
[3]胡维革, 郑权.文化冲突与反洋教斗争: 中国近代“教案”的文化透视[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 (1): 20-29.
[4]廖一中, 李运华.论近代教案[C]//吴金钟, 刘泱泱, 马昌华, 等.近代中国教案新探.合肥: 黄山书社, 1993:1-11.
[5]何桂春.试论近代中国教案发生的根本原因[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0, (4): 95-102.
[6]徐梁伯.“反洋教”的提法应当取消[C]//四川省近代教案史研究会, 四川省哲学社会学会联合会.近代中国教案研究.成都: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 54-59.
[7]董丛林.中国近代的“教案”、“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和“反洋教”辨析[C]//河北史学会.历史与现实论稿.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1: 155-165.
[8]赵树好.教案与晚清社会[M].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 3.
[9]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M].第六版.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
[10]吕实强.教务教案档: 第三辑[M].台北: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75.
[11][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第二卷[M].张汇文, 姚曾廙, 杨志信, 等, 译.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234.
[12]吕实强.教务教案档: 第一辑[M].台北: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74.
[13]国立故宫北平博物院文献馆.清季教案史料[M].北京: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 1937.
[14]吴盛德, 陈增辉.教案史料编目[M].北京: 燕京大学宗教学院, 1941.
[15]王文杰.中国近世史上的教案[M].福州: 福建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会, 1947.
[16]刘本良.评《中国近世史上的教案》[J].上智编译馆馆刊.1948, (1): 40.
[17]陈步青.评《中国近世史上的教案》[J].文藻月刊, 1948, (1): 48.
[18]候云灏.20世纪中国史学思潮与变革[M].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108.
[19]李金铮, 邓红.“文革史学”初探: 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为例[J].史学月刊, 2002, (12): 5-11.
[20]李时岳.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8.
[21]李时岳.反洋教运动[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2.
[22]南史.天津教案: 1870年天津人民反洋教斗争[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62.
[23]天津市历史研究所天津史话编写组.火烧望海楼: 1870年天津人民反洋教斗争[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3.
Textual Research on Concept of Missionary Cases
WEN Rui1, FENG Xuemei2
(1.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China 050024;2.College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China 300071)
Research of missionary case is the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Chinese modern history research.Since the diversification of missionary case’s concept confused Chinese research of missionary case, it is necessary to re-explore the concept of it.Scholars of modern China have fundamentally grasped the proper meaning of the concept.But, owing to the influence of left-leaning political thought in certain period, the concept of missionary case had been passively added with meaning of “anti-imperialism” and been misinterpreted in a certain long time.Because there are many obstacles in the studying of missionary case caused by strict 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 it is important to define the concept of missionary case from both narrow sense and broad sense.
Concept of Missionary Cases; Christianity; Modern China
B978
A
1674-3555(2012)04-0089-06
10.3875/j.issn.1674-3555.2012.04.016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朱青海)
2011-02-22
温瑞(1986- ),男,河北泊头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晚清政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