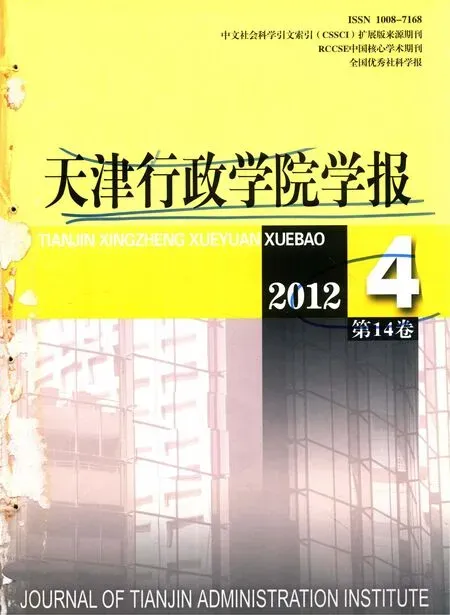大部制改革研究述评
2012-02-15蔡长昆
蔡长昆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大部制改革研究述评
蔡长昆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十七大以来,大部制改革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学界围绕大部制改革,尤其是对大部制改革的原因、路径、难点与阻力以及国外经验借鉴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我国大部制研究依然存在对大部制改革的理论基础研究不足,主要以“价值导向”和“功能导向”的“谚语式”研究遮蔽了经验性的科学讨论和理论积累等问题。未来我国的大部制研究应以我国历史经验、地方经验以及国际经验比较为基础,实现系统性的理论积累,以引导我国大部制改革进程。
大部制改革;述评;理论基础;经验研究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一直是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难点。建国以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虽有推进,但总体而言并不成功:这些改革没有在根本上打破“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1][2]。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这为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指明了新的方向,即大部制。在这一背景下,学界主要围绕四个问题对大部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为什么需要大部制改革;怎样推进大部制改革;大部制改革的难点和阻力有哪些;国外的大部制改革对我国有什么启示。
一、为什么需要大部制
我国大部制改革的原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我国面临的经济社会环境的挑战需要实行大部制,大部制改革是“大势所趋”;第二,大部制特殊的内涵和特征是我国应对行政管理体制缺陷的方案;第三,大部制改革对于我国政府改革具有重要的目的和意义。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化、行政体制与国际接轨的需要以及我国传统行政体制的不适应共同构成了我国大部制改革的背景。首先,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决定了公共行政体制的复杂化,要求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必须应对更加复杂的经济社会需要;其次,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浪潮既提出了大部制改革的要求,也提供了经验支持,行政体制的国际接轨要求我国行政管理体制需要参考国际行政体制——而国际上基本上实行大部制[3];最后,面临巨大的治理压力,我国传统行政管理体制在应对变革中的经济社会的挑战时捉襟见肘:我国传统行政体制应对能力的缺乏,部门之间的高度专业分工导致集体协调困难,权力分散使统一领导阙如,部门利益压倒整体利益、短期利益压倒长期利益[4]。以上三方面共同构成了我国大部制改革的背景。
大部制具有特殊的内涵和特征,这些特征是应对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缺陷的方案。虽然学者们基于不同的视角界定大部制,但基本同意汪玉凯的定义,即“所谓‘大部门体制’,或者大部制,就是在政府的部门设置中,将那些职能相近、业务范围雷同的事项,相对集中,由一个部门统一进行管理,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而达到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的目标”[5]。虽然学者们对大部制的基本概念界定达成一定的共识,但对大部制改革内涵的认识存在一定差异。张成福和杨兴坤集中于大部制改革的内部结构的研究,认为大部制改革的实质在于政府机构内部的职能整合、统一领导、运转协调、资源共享、结构优化以及机构精简[4]。李汉卿则认为大部制改革的本质不仅包括部门调整,而且也是一个政治机会,其实质是政府职能的重新调整,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契机[6]。对大部制改革内涵的两种不同理解一直贯穿于我国大部制改革的讨论中:一方面主要关注大部制改革的组织结构调整,倾向于从行政组织结构的角度研究大部制改革的逻辑;另一方面则坚持政治路径,认为大部制改革是深化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契机。两种不同取向的争论在对我国大部制改革的目的和意义的讨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大部制改革不仅具有特殊的内涵,还有其特殊的目的和意义。石亚军和施政文认为大部制改革的目的和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有利于减少职能交叉,完善行政运行机制;有利于落实“问责制”,建设责任政府;有利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突破和深化,是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7]。张创新和崔雪峰进一步认为,大部制改革与“小政府治理模式”有内在关联,所以大部制改革不仅有利于政府职能和结构的改革,也有利于“小政府”治理模式的实现[8]。李院林和陈国权总结了这些讨论,认为大部制改革的目的在于实现大责任制、大职能制、大服务制和小政府制四位一体的制度安排[9],这是对大部制改革目标定位的进一步推进,明确提出了政府职能安排的重新划分是大部制改革的关键,“小政府”是大部制改革的终极目标。在此基础上,李汉卿进一步阐释了大部制改革的“政治进路”,认为我国在“行政吸纳政治”的条件下,“大部制改革过程中如何充分吸纳反映民意,建立起政府与社会、公民的合作治理体制,也应是大部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基于民主公民权理论的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治理体制是实现此目标的可能路径选择”[6]。可见,对我国“大部制”改革的意义和目的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大部制”改革的目的逐渐从纯粹的职能整合和机构改革、提高行政效率转移到政治体制改革——先是“小政府”,接着是“民主治理”,这表明学者们对我国大部制的不同理解,使大部制改革的目标和意义出现了行政组织结构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分野。
经济社会环境急剧变迁,国际化和信息化背景使公共事务复杂化,以及我国传统行政管理体制应对乏力的挑战,要求大部制改革“势在必行”。但由于对大部制内涵的不同理解,学者们对我国大部制改革的目标和意义认识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分歧,利用职能整合和机构调整实现行政效率和公共服务绩效是公认的目标,但“小政府”改革以及“民主治理”是否构成了大部制改革的目标还有待进一步讨论。
二、怎样推进大部制改革
无论是从大部制改革的背景、还是从行政体制的现实来看,都迫切要求我国推进“大部制”改革。但由于学者对大部制改革的思路、内容和路径等问题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大部制改革的两种取向的差异也存在于对大部制改革的思路和内容的讨论中。关于大部制改革的路径,学者们分别从中央大部制改革的路径和地方大部制改革的路径两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大部制改革的思路是大部制改革的基本要素,大部制改革的内容则是大部制改革的范围和边界。对于大部制改革的思路,杨敏认为“大部门体制改革必须遵循自上而下的改革逻辑:一是按照决策、执行、监督分离的原则对整个政府机构进行重组;二是按照职能有机统一的原则进行整合,继而在大部委内部再实现决策、执行、监督分离”[10];陈天祥认可这一论点,提出大部制必须按照“转变政府职能以及决策、执行、监管三者适度分离等相关配套措施”的方向推进[11];毛寿龙特别强调在大部制改革过程中,“政府机构实行决策、监督、执行分开”是基本思路[12]。
学者们还从微观层面对大部制改革的内容进行了讨论。李军鹏认为,我国大部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职能整合和机构整合、内部协调机制的建设、执行制度建设、服务机制建设以及监督机制建设六个方面[13]。张成福和杨兴坤进一步认为大部制改革中职能整合的前提在于确保国家战略,实现国家核心职能,这需要依照“事权统一、指挥统一、权责相称、决策与执行分工的原则进行”;并依据“有所为、有所不为、有事有权、有权有限”的精神和原则,明确划分部门的权限;在此基础上,优化内部治理结构,强化部委机构政策制定的能力[4]。可见,这些学者对大部制改革的思路和内容的讨论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职能整合和机构重组,在组织结构上实现变革;二是决策、执行以及监督三分,将大部门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视为政治体制的变革。宋世明在大部制改革基本构成要素的论述中对这两个方面进行了综合,他认为大部门体制的实质是一种政府治理模式,包括两个部分:大部门体系和大部门机制,二者有机统一,缺一不可。大部门体系是由核心化的行政政策中枢及其办事机构、综合化的政府组成部门、专业化的执行机构三个要素形成的政府组织架构;大部门体系应采取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运行机制;大部门体制改革应该是政府组织架构调整与政府运行机制再造的统一[14]。
在大部制改革的思路和内容的指导下,学者们开始研究大部制改革的具体路径,主要在两个方面取得了进展:一是中央大部制改革的路径,二是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的路径。对于中央政府大部制改革的路径,沈荣华强调中央政府在推行大部制改革 的过程中应该 积 极 稳 妥[15](p.354)。倪 星和付景涛以英法经验为基础,重新设计了我国大部制结构。其设计思路是以我国政府的职能定位为基础,对现有政府部门的宏观职能进行亚职能解析,根据职能行使的效率原则和适应社会发展原则对亚职能进行组合以形成宏观职能,根据宏观职能优化组合形成“大部”,并在此基础上确认了完善部门间协调的机制,健全部内协调机制,明确部门领导间的分工与合作关系的重要性[16]。
由于我国大部制改革的复杂性,且受环境条件和历史制度的约束,在没有明确的理论指导和调查研究的情况下,仅凭西方国家的经验实现大部制组织结构的设计是有缺陷的,这说明现阶段学者们对中央政府大部制改革路径的整体设计缺乏合理性。相反,地方的实验给学者们一个新的经验基础来研究大部制改革的推进策略,因此,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的经验研究对我国大部制改革的推进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国家行政学院课题组对成都大部制改革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重复了上文讨论大部制改革的两个思路——决策分权以及结构调整[17]。彭澎根据广东大部制改革的经验观察,把改革模式区分为三种,分别是:以“行政三分”为重头戏的深圳模式,以“党政联动”为特点的顺德(及珠海)模式和因地制宜、统筹兼顾的广州模式[18],虽然彭澎并没有对每种模式进行具体的经验研究,但其分类对我国地方大部制改革的经验研究具有启发意义。与彭澎对大部制改革模式的分类相对应,付金鹏和陈晓原在我国大部制改革的地方经验基础上界定了三种大部制改革模式:职能统合性、规划协调型和党政合署型。不仅如此,他们还进一步比较和总结了不同模式的相对适用条件:职能统合型大部制是优先考虑的形态;规划协调型大部制可以成为一种补充形态;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党政合署型大部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19]。虽然对大部制改革研究中类型学讨论和探索适用条件的努力值得肯定,但对不同模式的内部机制和边界进行理论分析的研究仍然缺乏,需要更多经验研究加以补充。李文钊等对乌海市国地税联合办税的大部制实践的研究代表了这一取向,他们认为业务活动属性及机构服务对象的需求是决定机构改革的边界,以及机构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变量[20]。
总之,学者们对大部制改革的思路和内容的研究主要是以前文讨论的两种取向为基础的,这进一步决定了大部制改革的推进策略,特别中央政府大部制改革的路径推进策略。我国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的经验给大部制改革研究带来了新的对象,学者们对地方大部制改革的研究也从宏观的原则性论述转向改革模式的类型学讨论,并逐渐过渡到研究部门结构改革的内在变量,这应是我国大部制改革研究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三、大部制改革的难点及阻力
据现有大部制的相关研究文献来看,关于对大部制改革的难点和阻力的研究相对稀少且缺乏系统性,这可能是因为:一是国内的学者相对比较乐观:既然大部制改革“势在必行”,所以改革的阻力是必须破除的,也是可以破除的;二是我国大部制改革毕竟还没有成形,大部制的缺陷还没有表现出来。学者对我国大部制改革的难点以及可能面临的阻力的研究基本上是预测性的,且比较综合和宏观。
竺乾威认为,大部制改革可能面临着四个难点:部门之间边界的确切划分比较困难;部门整合带来的一体化加大了内部协调的难度;在缺乏一个统一的部门文化的条件下,大部制可能名实不符;内部管理和运行成本的增大以及对“大部”进行监督的困难[21]。丁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补充,认为大部制改革中的人员分流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阻力,所以“切实解决好机构改革中富余人员的分流问题,本身就是机构改革的重要环节,也是使大部制改革能够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22]。李丹阳进一步总结了六个难点,包括:履职理念再造的困难;设计新的权力运行机制;利益调整充满阻力;党政机构对接的困难;安置富余人员问题;对大部制的监督[23]。
学者对大部制改革的难点-阻力的粗略讨论已经说明大部制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系统讨论依然阙如,进一步说明我国大部制研究路径的选择存在缺陷,在研究条件的限制下表现出了内在困境。当下的大部制改革无论是在研究还是改革实践层面上都更关注“自上而下”的“国家构建”,政策执行的研究成果采用自上而下视角的批判对我国大部制改革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意义[24],大部制改革最基本的制度细节可能成为大部制改革的最关键要素①。
四、国外大部制改革的经验借鉴
由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历史缺乏大部制经验,所以对国外经验的研究是我国大部制改革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倪星和付景涛对我国大部制改革的整体设计就是在总结英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16]。学者们对大部制国际经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大部制改革的内部机制;二是大部制改革的制度配套问题;三是大部制改革的限度。
大部制的内部机制是指大部制改革的原则和运作规则,国外关于大部制改革研究经验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大部制必须以职能的有效划分为基础,有效的职能划分既体现在横向的各个部门之间,也体现在纵向的不同政府层级之间。在职能和任务整合基础上探索推行大部门体制是大多数国家成功施行大部制的关键[25],英国“希思改革”的教训就在于,依据服务对象等因素实行大部制不利于其有效运转[26];俄罗斯大部制改革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将一些完全不相关的职能纳入了一个大部之中[27]。不仅在各个部门之间有效划分职能非常重要,纵向政府层级之间的职能关系也必须理清,这也是其他国家大部制更为成功的原因[28]。第二,大部制的有效运作需要有效的职能整合,有效的职能整合是以有效的内部沟通和协调为基础的。几乎所有成功推行大部制改革的国家都有非常有效的部门内部沟通机制,英法之所以是成功推行大部制的典范即在于有效的部门内部沟通机制[29]。
大部制的制度配套是指大部制需要的制度环境条件:经济条件、社会条件以及政治条件。经济条件是指成熟的市场经济,成功推行大部制的国家基本上是具有成熟市场经济的西方发达国家,这说明成熟的市场经济对大部制改革的重要性[25]。社会条件是指是否存在成熟的第三部门和社会自治,有效推进大部制改革的国家基本上都有成熟的第三部门[28],社会自治和第三部门的存在意味着社会的自我治理可以有效替代政府职能撤退造成的职能真空,实现更为有效的治理[29];政治条件是指政府、市场和社会职能是否有效划分,成熟的市场经济和成熟的社会自治需要以有效的政府职能划分为前提。英国经验表明,当职能在政府、社会和市场之间有效划分时,公共服务的供给模式是多样化的[30],其他国家有效实行大部制改革也是建立在有效的政府职能划分基础之上的[28][29]。
国外大部制改革经验的研究也指出了大部制自身的限度。首先,利益相互冲突的部门不宜放入一个部门。其次,各个部门之间的力量应该平衡,一个部门如果太大往往成为“部上之部”,不利于政府职能的有效运转[25]。再次,部门设置的数量有一定的限制,并不是部门越大,部门的总数越少越好。英国大部制的经验说明内阁组成部门既存在一个上限,也存在一个下限[30];俄罗斯改革的失败提醒我们如果强行追求部门之“大”和总数之“少”往往耗散这一制度的优势[27]。
由于不同国家历史和社会背景的差异,在对大部制改革细节的关注相对缺乏的条件下,学者们研究得出的借鉴经验也是有缺陷的,但这些经验对推进我国的大部制改革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其中,Clarke的警告对我国大部制研究就非常重要:“现有组织理论有时能对微观层面的组织改组提供理想的解决方案,但对庞大而又高度复杂的政府部门来说,系统、科学的设计显得无能为力”[31],学者们对不同国家大部制改革的经验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结论,特别是周志忍对“过程”、“细节”和渐进性改革的强调[26],崔健对整体设计以及部门内部实现决策、执行、监督职能三分之缺陷的揭示,都对我国大部制改革具有警示意义[27]。
五、总结和评论
学界对我国大部制改革中的四个关键问题——原因、路径、难点与阻力以及国际经验——的讨论既说明国内学者对大部制改革的理论热情,也说明我国大部制改革研究的内在困境。学界从大部制改革这一问题出发引出了多样化的研究问题,说明了学界对这一问题倾注的心血。但是,由于大部制改革的现实性和紧迫性,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容易导向政治化,并且由于大部制改革经验的缺乏,使我国大部制研究面临诸多困境,使学界在研究大部制改革的理论基础时出现了巨大且微妙的分歧。
综合前文对我国大部制改革的研究,学界对大部制改革的研究主要表现出两个特点:功能性和政治性。“功能性”体现在学者几乎将大部制改革视为根除我国行政体制弊端,实现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灵丹妙药;政治性体现在将大部制改革视为实现“小政府”和“民主治理”的机会,在改革思路上强调政府职能分割和权力分享。功能性和政治性的研究给大部制改革以太大的期望,也对一项制度变革赋予了太多重担,反而遮蔽了真正的学术思考和经验研究。
不仅如此,学界对我国大部制改革的研究面临巨大的困境,最重要的就是理论研究的缺乏以及研究的非经验性,这也是大部制研究的功能性和政治性带来的后果之一。对于大部制的理论基础,有些学者利用韦伯的经典官僚制理论[21],但更多的学者以整体性政府理论为大部制改革提供理论基础[32][33]。官僚制理论强调行政管理体制的理性、结构的正式化以及层级化的控制体系②;而整体政府理论则相反,其更多地强调整合性、扁平化和网络化的治理模式,去除等级的僵化体系和由此造成的尾大不掉③,二者在理念上是相背离的,这既表明我国大部制改革研究缺乏理论基础,也造成了我国大部制改革研究缺乏理论积累性。
功能性和政治性,以及理论和经验研究的缺乏,使得学界对大部制的缺陷缺乏深入思考——虽然也有例外,如,施雪华和孙发锋对大部制改革优缺点的洞察[34],但总的来说缺乏深入探索、对不同大部制实践的系统性进行比较研究。同时,学界对大部制改革的逻辑、细节和改革的过程亦缺乏研究,任何一项改革的成功都依赖于对改革的过程和细节,以及对改革的理论逻辑的探索。例如,职能整合和机构重组是政府机构改革的基础[25],但对于职能整合的条件、职能的属性以及既有的政府机构设置的限制怎样影响改革的过程等具体问题的研究则有待深入。
六、破除“行政谚语”:进一步的推进路径
Simon批判古典行政理论的缺陷时认为,古典行政理论所概括的各种原则只不过是“行政谚语”,并且其中不同原则之间的要求往往相互冲突[35](p.46)。我国学者对大部制改革的研究从两个方面契合了Simon对古典行政理论的批评:第一,我国大部制改革的研究具有功能性特点,这些研究的结论正是一系列“原则清单”,忽视了不同原则之间的冲突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成本,并且我国大部制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冲突的,以冲突的理论基础得出的原则往往是冲突的。第二,我国大部制改革研究的政治性特点赋予我国的大部制以太多的价值性考量,忽视了大部制改革的基本逻辑,这有损于大部制改革的真正经验讨论④。
周志忍在研究英国的大部制改革时界定了两种大部制概念:一是政府部门设置的一种客观状态,其特点是部门数量少,各个部门的职责范围比较大;二是一个机构重组和整合的过程,其标志是同级别部门的归并。前者具有原发性,如美国和加拿大;而后者具有过程性,如俄罗斯和中国,甚至包括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国家[26]。这说明进一步的研究应该摒弃对客观状态的描述——那种功能性的和政治性的研究,而应该寻找新的理论基础,将注意力集中在经验研究之上——这恰恰是Simon破除“行政谚语”的表现。特别是在具体的理论指导下,对职能整合和机构重组的具体条件这一问题进行深入而细致的研究。
职能整合和机构重组主要是对组织结构变革条件的研究,所以进一步的研究应该着力探讨在中国大部制改革的过程中,影响职能整合和机构重组的变量。具体来说,需要说明的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哪些职能应该整合和重组,以及实现整合和重组的机制有哪些;选择不同的职能整合和结构重组的条件是什么?所以,进一步经验研究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推进:一是对我国地方经验的研究,这在前文已经讨论过,并有巨大的潜力;二是对我国行政机构改革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入研究,探讨政府组织结构变革的条件和逻辑;三是对不同国家的组织结构改革进行细致的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得出经验结论,而不是目前这种对不同国家的大部制改革进行“描述”式研究。总之,只有在理论的指引下进行广泛的经验研究,实现经验的理论提炼,才能对我国的大部制改革提供真正的指引和基础。
(本文有幸得到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李文钊副教授的指导,特此致谢。)
注释:
①对于制度细节对制度变迁成败的影响,可参见:Elinor Ostrom.Governing the Commons: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p.78-92;Elinor Ostrom,Larry Schroeder and Susan Wynne.Institutional Incentiv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Boulder:Westview Press,1993,pp.125-132.
②这主要体现在古典行政理论中,其中以韦伯的描述最为经典,可参见:Max Webber.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7,pp.67-69.有关古典行政理论的综述,可参见:Jonathan R.Tompkins.Organization Theory and Public Management.Belmont,CA:Thomson Learning,2010,chap.4,5,6.
③有关整体性治理,可参见:Perri 6.Toward Holistic Governance:The New Reform Agenda.New York:Palgrave,2002,pp.5-6;周志忍:《整体政府与跨部门协同》(《中国行政管理》2008年第9期)。
④这并不完全等同于行政学研究中的“价值”和“事实”的争论,虽然两者具有相似性。有关西蒙的“事实”与“价值”的讨论,可以参见:Simon,Herbert A.Administra
tive Behavior(4th Edition).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7,p.56.但这里主要说明的是,对于一项行政体制改革来说,摒弃纯粹政治价值的考虑——如权力分享或民主治理——有利于看清这一制度改革本身的逻辑。
[1]吴江.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历史经验[J].中国行政管理,2005,(3).
[2]李景鹏.回顾与反思:政府机构改革的经验与教训[J].中国行政管理,2005,(2).
[3]贺军.大部制改革即将启动[J].中国企业家,2007,(23).
[4]张成福,杨兴坤.建立有机统一的政府:大部制问题研究[J].探索,2008,(4).
[5]汪玉凯.冷静看待“大部制”改革[J].理论视野,2008,(1).
[6]李汉卿.试论我国大部制改革的政治进路[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9,(6).
[7]石亚军,施正文.探索推行大部制改革的几点思考[J].中国行政管理,2008,(2).
[8]张创新,崔雪峰.大部制改革与小政府模式辨析[J].中国行政管理,2008,(5).
[9]李院林,陈国权.大部门体制改革的实质与突破[J].中国行政管理,2009,(1).
[10]杨敏.大部门体制的改革逻辑[J].决策,2007,(11).
[11]陈天祥.大部门制:政府机构改革的新思路[J].学术研究,2008,(2).
[12]于朝霞.“大部制”改革正逢其时[J].理论前沿,2008,(7).
[13]李军鹏.大部门体制的推进策略[J].中国行政管理,2008,(3).
[14]宋世明.论大部门体制的基本构成要素[J].中国行政管理,2009,(10).
[15]沈荣华.关于推进大部门体制改革的思考[C]∥黄卫平.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IV.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16]倪星,付景涛.大部门体制:英法经验与中国视角[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8,(1).
[17]国家行政学院课题组.成都市大部门体制改革探索的个案分析[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9,(1).
[18]彭澎.广东大部制改革:比较与思考[J].探索,2010,(2).
[19]付金鹏,陈晓原.“大部制”的形态与前景:一项比较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2010,(7).
[20]李文钊,陈建国,毛寿龙.地方大部制改革的突破与启示[J].行政管理改革,2011,(2).
[21]竺乾威.“大部制”刍议[J].中国行政管理,2008,(3).
[22]丁希.论大部制改革过程中人员分流的阻力及其清除[J].湖北社会科学,2008,(10).
[23]李丹阳.关于“大部制”改革的几点思考[J].学术研究,2010,(11).
[24]H.Glennerster,A.Power,T.Travers.A New Era for Social Policy:A New Enlightenment or a New Leviathan[J].Journal of Social Policy,1991,(20).
[25]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课题组.职能整合与机构重组:关于大部门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J].天津社会科学,2008,(3).
[26]周志忍.大部制溯源:英国改革历程的观察与思考[J].行政论坛,2008,(2).
[27]崔健.俄罗斯大部制改革及其评析[J].中国行政管理,2008,(12).
[28]杜治洲.大部制改革的理论基础、国际经验与推进策略[J].现代管理科学,2009,(3).
[29]倪星.英法大部门政府体制的实践与启示[J].中国行政管理,2008,(2).
[30]周志忍.英国执行机构改革及其对我们的启示[J].中国行政管理,2004,(7).
[31]Richard Clarke.The Number and Size of Government Departments[J].Political Quarterly,1972,(43).
[32]王佃利,吕俊平.整体性政府与大部门体制:行政改革的理念辨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0,(1).
[33]李荣娟,田仕兵.整体性治理视角下的大部制改革完善探析[J].社会主义研究,2011,(3).
[34]施雪华,孙发锋.政府“大部制”面面观[J].中国行政管理,2008,(3).
[35]Herbert A.Simon.Administrative Behavior(4th Edition)[M].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7.
D63 < class="emphasis_bold">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8-7168(2012)04-0062-06
10.3969/j.issn.1008-7168.2012.04.010
2012-04-20
蔡长昆(1989-),男,湖北恩施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政策研究所硕士生。
杨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