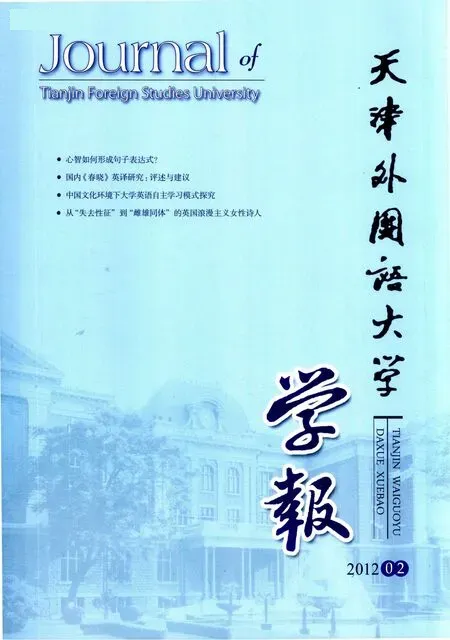岂止消闲:《礼拜六》翻译小说的文化阐释
2012-02-14修文乔
修文乔
(北京语言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83)
一、消闲的提出
鸳鸯蝴蝶派产生于清末民初,是从旧文学中蜕变而来,既带有旧文学、旧思想的特点,又受到新思想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巨大影响使新文艺得到了蓬勃发展。在正统文人看来,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不但属于通俗文艺,难登大雅之堂,而且宣扬封建思想和行乐观念,理应受到新文化战士们的讨伐。从文学革命一开始,新文学家们就把鸳鸯蝴蝶派作为重要的批判对象。沈雁冰批判鸳鸯蝴蝶派“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及“毁污一切的玩世与纵欲的人生观”,“潜伏在中国国民性里的病菌得了机会而作最后一次的发泄”(魏绍昌,1984:38,43,45)。郑振铎批判“鸳鸯蝴蝶派游戏的态度,颓废的生活”,呼吁“血的文学、泪的文学,不是‘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文学”(同上:51,57)。他在《文学旬刊》上以“西谛”为笔名发表《消闲?》一文,怒斥《礼拜六》和其他鸳鸯蝴蝶派杂志的消闲性,为鸳鸯蝴蝶派定下了“亡国”的判词(同上:58)。叶圣陶、成仿吾、胡适、钱玄同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无不对鸳鸯蝴蝶派笔墨相讥。
这种以五四新文学为标准所构建的一元文学格局长期以来遮蔽了通俗文学的实绩,阻碍了对文学史丰富性和真实性的认可。20世纪80年代学界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海外汉学界发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王德威,2005:1)的质问,范伯群先生(2009:1-17)更是主张知识精英文学与大众通俗文学双翼齐飞的“两个翅膀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中国文学经典经历了不断的重构与建立,在不断的解构与颠覆中,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多元并存的格局逐步构建起来。而民初翻译史,特别是鸳鸯蝴蝶派的翻译活动,在中国近现代翻译史研究中经常处于缺场状态。增强翻译史史识意识离不开对历史认识的性质及独特性的认识(蓝红军,2010:46)。本文试图通过探究鸳鸯蝴蝶派产生的历史背景,剖析其代表刊物《礼拜六》中言情、侦探和国民三大类型翻译小说的文化内涵,阐明这一民初文学期刊的价值取向。
二、消闲的缘起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前,由文学杂志、副刊和小报组成的“公共空间”曾掀起两股较大的文学思潮:一股是清末文坛由梁启超等发起,以开启民智为旨归的文学启蒙运动,意在改良群治,影响民心;另一股则是对前者浓重政治意味的反拨,即民初鸳鸯蝴蝶派的崛起,由此掀起通俗文学创作和翻译活动。
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面对西方列强进一步瓜分中国的严峻形势,中国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要实现富国强民的目的,光靠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远远不够,必须全面学习西方,实行维新变法。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行不通,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对腐朽顽固的清政府彻底失望,将改造社会、启蒙大众作为维新救国的新途径,并发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小说界革命”,企图重新定位中国传统的小说功能观,将历来用于茶余饭后消遣的小说改造为启蒙群治的利器。在这次文学翻译浪潮中,最早译介到中国来的新小说类型是政治小说,因为政治小说宣传西方的民主思想和政治体制,最契合维新派改良政治的需要。但政治小说的严肃化和高雅化倾向显然与普通民众的文化层次和阅读能力存在较大差距。在政治革命高涨的年代,这类肩负救世重任的小说还能为高度政治化的读者所接受,一旦革命失败,群众的政治激情消退,这类小说的读者群也随之迅速瓦解。
政治启蒙的落潮使文学走出“文以载道”的工具性价值观,消遣娱乐的文学观作为对它的反拨迅速走强。鸳鸯蝴蝶派萌蘖于20世纪初的十里洋场上海,成型于清末民初,兴盛于民国初年。这一文学派别“作者众多,但缺少组织,虽有少数同好成立过团体,但从无明确的组织纲领和系统的理论主张……只要写的是通俗类型的言情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读者就会自然而然地把他看作‘鸳鸯蝴蝶派’,虽然不准确,可这也是一种文化心理惯例”(刘扬体,1997:4)。鸳鸯蝴蝶派最著名的刊物是《礼拜六》,因此他们又被称为礼拜六派。这一文学流派的作家群最初多是南社革命作家,随着民初都市工商业经济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兴起,他们逐渐摆脱开启民智的桎梏,关注的焦点由国家政治转向了市民生活,通俗文学作品的创作和翻译活动也逐渐繁荣起来。
三、消闲的另类解读
《礼拜六》是创刊于民国初期的一份通俗文学刊物,也是活跃于民初文坛的鸳鸯蝴蝶派的代表性刊物。从1914年到1923年,它先后经历了创刊、停刊、复刊、终刊,前后共出刊200期,其中从1914年创刊至1916年停刊期间出刊100期,系小说周刊。除刊载创作小说外,杂志还发表了大量的翻译小说。从1921年复刊至1923年终刊期间的100期与前百期相比,文学作品数量更多,形式更丰富,除翻译小说之外,还出现译丛、偕译、译乘等其他翻译作品。
民初著译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有些作品有时很难分辨出是译作还是著作,因为这些作品上往往没有明确的标识。笔者只得自定辨识标准,将凡是符合下列一个或一个以上条件的作品认定为译作,以确定本研究所覆盖的范围,即标有“XX译”字样的作品、注有英文原标题的作品、注有原作者名字的作品、篇首或篇末附识、按语中透露出原作信息的作品。而由影戏改编的短篇小说也纳入译作的范围。按照这种原则进行统计,《礼拜六》前百期共刊登短篇翻译小说120篇、长篇小说4篇,后百期除了50篇短篇翻译小说和6首译诗外,还有41篇译丛、偕译、译乘等形式的译作。
经过笔者统计,《礼拜六》前百期短篇翻译小说的基本题材类型共有18种①,分别为言情小说(35)、侦探小说(14)、国民小说(12)、滑稽小说(11)、伦理小说(10)、语怪小说(6)、军人小说(4)、冒险小说(4)、社会小说(4)、历史小说(3)、札记小说(3)、实业小说(3)、童话寓言(3)、科学小说(2)、虚无党小说(2)、义侠小说(2)、沦智小说(1)、家庭小说(1)。其中,言情小说成为译作数量最多的,其次是侦探小说和国民小说。这种情况与晚清的情形似有很大不同。“侦探小说和科幻小说……与政治小说(包括虚无党小说)一起成为风靡清末民初……我国译界的三个最主要的翻译小说品种。”(谢天振、查明建,2004:35)这一翻译小说格局的变化固然与鸳鸯蝴蝶派文人的文学趣味和《礼拜六》的办刊宗旨相关②,但深层次原因则涉及近代小说观念的变革、社会政治局势和文化环境的变化等多种因素。
1 言情小说——浪漫、哀伤
“小说界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数年,救国新民旗帜领导下的小说创作和翻译也呈现出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然而,社会却愈加黑暗,小说界的政治热忱亦随之逐渐衰退。到1909年,晚清四大小说杂志③相继停刊。民国成立后,亡国的危机似乎有所缓解,但随之而来的却是革命果实遭到窃取。眼见社会比晚清更加黑暗腐败,人们深感愤慨和苦闷,整个社会充溢着感伤的时代氛围,这一普遍的社会情绪自中国清末民初开始一直持续到五四以后(赵孝萱,2004:81)。而言情小说的创作和翻译不过是这种社会心态在文学上的反映。
就文学的发展规律而言,小说创作和翻译题材的改变是文学自身变革的产物。小说在晚清一度成为政治的附庸,在其社会功能被无限放大的同时也丧失了可读性和审美愉悦性这一本体特征。民初小说从政治指挥棒下解放出来,救国新民理论让位于游戏消遣之说和人间儿女情愁。这不过是对“小说界革命”忽视小说基本特性的反拨,是小说对传统的自然回归。
言情小说的创作和翻译在民初的盛行也是作家和译者适应文化市场、迎合读者期待的必然结果。清末的写情小说直接开启了鸳鸯蝴蝶派创作和翻译言情小说的先声。1906年,在中国的新小说界出现了令人瞩目的中篇小说——吴趼人的写情小说《恨海》,这篇小说是在西学东渐之中,中国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主的先声。此后有天虚我生、李涵秋、符灵等作家一系列写情小说的诞生(阿英,2009:181-182)。而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1899)和《迦茵小传》(1905)更是引起读者相和、哀戚之声一片,以致严复有“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之叹。民初小说的商业化更是促进了这类题材小说的兴盛。当时的小说读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青年学生,爱情主题对这样的阅读群体自然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作为一个市场取向的通俗文学流派,鸳鸯蝴蝶派与读者的紧密关系自不待言。经由他们翻译的言情小说除了能反映大众的阅读品味,也影响了他们对外国文化,尤其是对现代浪漫爱情的想象。
鸳鸯蝴蝶派译者将新的故事典型和西方通俗言情小说的流行主题引进到中国的言情传统中。民初的言情小说打破了中国传统的才子佳人大团圆的惯例,体现出西方翻译小说的影响。“翻译文学在人物形象上改变了中国传统言情小说‘才子佳人’的模式,首先是增加了人物的牺牲精神和忏悔意识。”(袁进,2000:213)《礼拜六》第4期刊登了周瘦鹃的短篇翻译小说《郎心何忍》,男主人公密堪洛为了成全心爱的女子麦玲娜的贞操情结和婚姻幸福,甘愿牺牲自己神圣的爱情。在第59期周瘦鹃由影戏The Open Gate改编的小说 《不闭之门》中,郎才女貌的男女主人公于热恋中发生误会,而男主人公乔治的叔叔和女主人公蓓菂的姑母当年正是由于误会而错失良缘。两位老人出于忏悔之心劝说小辈,最终成全了两桩美满的婚姻。个人的牺牲精神和忏悔意识在小说中强化了人物的心理冲突,丰富了角色的内心世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自我意识的觉醒。第43期上翻译小说《化石缘》中的女人公爱尔司倍脱为追求自己的爱情违背父命,对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彰显了对个人本位价值观的尊重。第60期中的哀情小说《这一番花残月缺》描绘女主角临终的一幕充满了浪漫色彩和感伤气息,全然没有传统言情小说中死亡和伦理道德的交织及对于死亡场景中琐碎细节的交代。第39期上的《红楼翠幙》和第41期上的《玫瑰有刺》则展现了男主人公为情而死的动人画面。《礼拜六》的言情翻译小说向中国读者呈现了西方小说的价值观念和对于爱情的浪漫想象。
2 侦探小说——科学、民主
侦探题材小说在民初风头不减乃在情理之中,也是 《礼拜六》中的主要题材之一。1905年,侠人在《新小说》中写道:“唯侦探一门,为西洋小说家专长。中国叙此等事,往往凿空不近人情,且亦无此层出不穷境界,真瞠乎其后矣。”(陈平原、夏晓红,1997:93)而侦探小说层出不穷、瞠乎其后的特点恰好符合了《礼拜六》游戏消遣的宗旨和无情不奇、无事不奇、无人不奇的审美要求。《礼拜六》前百期刊载的四部长篇小说中的三部(《恐怖窟》、《秘密之府》、《孽海疑云》)都属于侦探题材,并配有插图,如《恐怖窟》主人公福尔摩斯的图片。这一现象在其他题材类型的翻译小说中从未出现过。
侦探翻译小说在民初受到青睐也与中国当时的政治背景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辛亥革命虽然不够彻底,但毕竟在形式上将专制政权变成了共和国体。中国国体的改变为民初侦探翻译小说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侦探小说宣扬法制而非人治,讲究人权而非皇权,要求科学实证而非主观臆断。这一小说类型输入的正是民初所需的西洋文明。
与中国传统的公案小说不同,西方侦探小说中一般会出现官方警员和私人侦探两种人物形象,且前者为铺垫,以衬托后者办案之神奇。两者分工明确,长官负责论案和断案,而后者只管破案。《礼拜六》中的侦探翻译小说加入了中国公案小说中从未有过的科学元素。在第31期上的《疗妒》和第42期上的《电》中分别出现了催眠术和电的利用。而在第8期上的《毒札》、第36期上的《怪客》、第38期上的《圣节奇案》、第41期上的《五万元》等翻译小说中,私人侦探均运用科学新法对案件进行侦破。在民初那样一个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都极不稳定的时代,侦探故事的主人公以科学方法维护法纪,伸张正义。这种传统道德价值和现代西方科技的结合为读者提供了心理上的稳定作用(孔慧怡,2000:93),也进行了科学和民主的启蒙。
3 国民小说——爱国、报国
《礼拜六》前百期中另一值得关注的题材类型是国民小说,与军人小说共同构成爱国、报国主题。1914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由于欧洲列强陷于大战,无暇顾及东方,为日本在中国进行扩张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全国各地掀起了各种各样的爱国活动,谴责日本试图灭亡中国的侵略行径,坚决要求政府抗日。
《礼拜六》自第37期④开始频繁刊载爱国主题译作,显然是对国难当头的社会现状的有力回应。其中有多篇取材于普法战争⑤,译者欲以法国军人和民众的爱国热情激励中国国民。天虚我生在翻译小说《密罗老人小传》篇首写道:“是书为法国著名小说家Guy De Maupassant 毛柏桑先生所著。法国文学界佥称先生为短篇小说之王。此篇出版,尤为社会欢迎,以其含有爱国思想,非徒作也。欧西学者类以小说鼓吹民气,使濡染于弗觉。法普世仇。故于小说中排斥尤力,将使人人心中具有敌忾同仇之念。一旦发泄,若决江河,莫之能御。今次战争,即其种因之结果也。亟译之以供吾国小说界之借鉴。”莫泊桑以普法战争为题材,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夜出杀敌,被捕后又临危不惧,最后英勇牺牲的老农民形象,借以歌颂法国人民在普法战争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天虚我生在译者序中介绍了译介这篇小说的目的,即激发中国人民心中的“敌忾同仇之念”。
在这一时期,关于战争、爱国、英雄的作品在《礼拜六》中密集出现,小说实已成为“鼓吹民气”的工具,而不再追求消闲娱乐。《礼拜六》第51期(1915年5月22日出版)至第58期(1915年7月10日出版)连载《国耻录》,以新闻实录的形式记载中国被日本侵略欺凌的历史。第47期刊登了读者慧侬女士题为“同胞速醒”的来稿⑥,呼吁国人抵制日货,储金救国。主编王钝根不但为第46期上的短篇爱国小说《弱国余生记》加了按语,怒斥日本的侵略行径,发出“不起自卫,行且尽为亡国奴”的疾呼,而且在第52,53,54,57期中多次刊登储金救国的青楼女子照,以激发国民的救国热忱。《礼拜六》奏响了一曲由编者、作者、译者、读者参与的救亡合唱。
四、结语
新文学刚刚从旧思想和旧文学中叛逆而出,对一切非革命的思想进行激烈地声讨和打击,为新文学的发展扫清了障碍,自有其历史价值和意义,但这种指责亦有失偏颇。以 《礼拜六》为例,鸳鸯蝴蝶派的创作和翻译作品不仅具有娱乐消闲的文学功能,对于西方浪漫爱情的表现及西方科学、法治精神的传播亦对国人深具启蒙意义,成为国人想象西方、构筑现代的媒介,借以影响、改变中国。面对亡国危机,《礼拜六》试图以创作和译作之力激荡中国人心和爱国情感。这些通俗文学作品还具备寓教于乐的教育功能,使人们在茶余饭后受到教诲和警戒,即通常所说的劝俗作用。这种方式尤其适合市民阶层,由于他们自身文化素养、生活习惯及职业特点等方面的制约,往往选择以娱乐功能为主的文学形式。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他们会潜移默化地匡正和改变自己的价值判断和人生追求。《礼拜六》于娱乐、休闲和趣味之中亦能达到劝世的效果,兼具娱乐和教育双重功能。
* 本篇论文曾在2011年 “第四届海峡‘两岸四地’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研讨会”上宣读,略有改动。
注释:
①由于刊物对小说的分类过于细致繁杂(希望从名目上吸引读者),我们只能将主题类似的译作划分到一起,如诙奇小说、神怪小说和述异小说的译作统一归为语怪小说类,而名目繁多的苦情、写情、哀情、忏情、奇情、惨情、怨情、痴情、喜情小说合并到言情小说名下。对于少数没有标明题材或主题的翻译小说则根据小说的具体内容确定其类别,如翻译小说《斗室天地》讲述的是俄报社记者在俄牢狱中的经历,属虚无党政治事件,因此将其归为虚无党小说。
② 主编王钝根在 《礼拜六》第1期上的《<礼拜六>出版赘言》中写道:“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卫生,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安乐也。且买笑觅醉顾曲,其为乐转瞬即逝,不能继续以至明日也。读小说则以小银元一枚,换得新奇小说数十篇。倦游归斋,挑灯展卷,或与良友抵掌评论,或伴爱妻并肩互读。意兴稍阑,则以其余留于明日读之。晴曦照窗,花香入坐。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故人有不爱买笑,不爱觅醉,不爱顾曲,而未有不爱读小说者。况小说之轻便有趣如《礼拜六》者乎?”
③ 包括《新小说》(1902-1906)、《绣像小说》(1903-1906)、《月月小说》(1906-1908)和《小说林》(1907-1908)。
④ 《礼拜六》第37期的发行日期为1915年2月13日,距离日本递交21条仅五天之隔。
⑤ 如第38期上的《密罗老人小传》、第42期上的《最后之授课》、第45期上的《血性男儿》、第47期上的《黑别墅之主人》、第49期上的《真是男儿》等。
⑥ “呜呼同胞!汝愿为印度人耶?汝愿为朝鲜人耶?岂以堂堂大国之民,而甘心为小丑之奴隶耶?呜呼同胞!今日何日?奈何犹征逐于酒食,流连于声色耶?呜呼同胞!汝之心苟未死者,汝之血苟未凉者,其速醒!速醒!储金救国,抵货惩仇,竭汝能力,保我疆土!勉哉同胞!好自为之。”
[1]阿英.晚清小说史[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
[2]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3]范伯群.多元共生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4]孔慧怡.还以背景,还以公道——论清末民初英语侦探小说中译[A].王宏志.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蓝红军.翻译史研究方法论四题[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3):44-48.
[6]刘扬体.流变中的流派——“鸳鸯蝴蝶派新论”[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
[7]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A].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8]魏绍昌.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Z].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9]谢天振,查明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Z].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10]袁进.试论近代翻译小说对言情小说的影响[A].王宏志.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1]赵孝萱.“鸳鸯蝴蝶派”新论[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