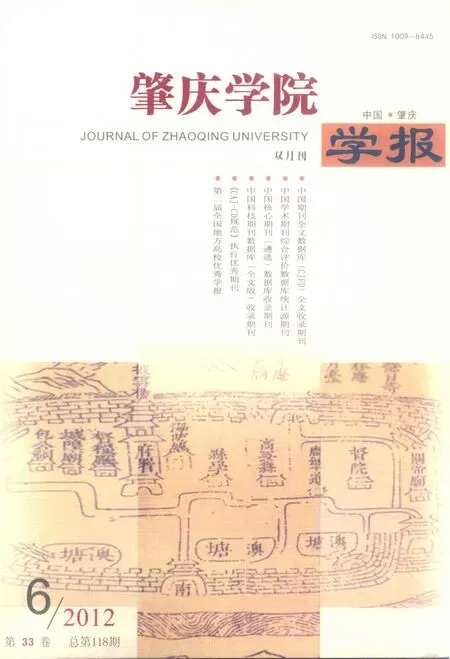论陈澧的学术经世思想与实践
2012-01-28钟玉发
钟玉发
(肇庆学院 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广东 肇庆 526061)
陈澧是晚清广东著名学者,为学宗汉,其所撰述的著作以考据学为主。但是,由于受到晚清时期内忧外患的冲击,陈澧中年以后的治学宗旨发生转向,他不仅批评汉学末流的弊病并兼采宋学之优长,而且力图学以致用。目前,学术界对陈澧其人其学的研究已有若干论著,但是尚没有人专门讨论陈澧的学术经世思想与实践。因此,有必要予以再考察。
一
陈澧(1810—1882),字兰甫,广东番禺(今广州)人,人称东塾先生。少时肄业于羊城书院、粤秀书院。道光十二年(1832)中举,此后屡应会试不中。道光二十年(1840),补为学海堂学长;同治六年(1867),任菊坡精舍山长,直至去世,前后计40余年。陈澧长期从事书院教学和管理工作,性情疏直平易,颇厌俗事,以读书、教学和著述终老一生,《自述》说自己:“生平无事可述,惟读书数十年,著书百余卷耳。”[1]10
由于受到两广总督阮元(1817—1826年在任)及其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所创办学海堂学风影响,陈澧中年以前治学旨趣及主要学术成就集中在考据学之中。他对汉学吴派和皖派开派者惠栋、戴震等人之学均表示服膺,其言曰:“国初诸老且不论矣,如惠、戴、钱、纪、段、王、凌次仲、张皋文等,著书皆有法,学者宜审观之。”[1]758他对阮元之学尤其推崇,曾表示:“阮文达公《诗书古训》,后之讲经学者当以为圭臬,此真古之经学,非如宋以后之空谈,亦非如今日所谓汉学之无用也。我辈宜崇尚之。”[2]192陈澧继承这一考据学治学理念,“中年以前治经,每有疑义则解之,考之。”[3]167他在晚年更明确表示:“余之学以考据为主。论事必有考据,乃非妄谈;说理必有考据,乃非空谈。”[1]357他还批评时人对考据之学的非议,认为:“近人诋考据之学,试思本朝之学所以能与汉、唐、宋各极其盛者,非考据乎?若无考据之学,则远出汉、唐、宋之下矣。”[1]383
陈澧治学兴趣十分广泛,读书广博,举凡小学、音韵、天文、地理、乐律、算术、古文、书法等无不涉猎。中年(35岁)以前,陈澧的代表性著作有《声律通考》、《切韵考》、《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水经注西南诸水考》等,几乎都是考据学力作。其中,“《水道》、《声律》二书,大学士曾国藩服其精博,象州郑献甫叹为有用之书。所考《切韵》,南海邹伯奇称为绝妙之作,超越前人。所考《水经注》诸水,江宁汪士铎亦惜未之见。其著述倾倒一时如此。”[3]6其他流传广泛的著述还有《三统术详说》、《弧三角平视法》、《摹印述》、《琴律谱》等,其学风气象十分宏大。
二
梁启超曾指出:“嘉、道以还,积威日弛,人心已渐获解放,而当文恬武嬉之既极,稍有识者,咸知大乱之将至,追寻根源,归咎于学非所用”[4]72。陈澧一生经历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朝,其时时局动荡不定,不仅发生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等,而且盐务、漕运、河工等“大政”也问题重重,这使陈澧等有识之士不得不关注现实社会危机,在治学方向上发生转向。他曾自述治学一生凡三变:“余少时志为文章之士,稍长为近儒训诂考据之学。三十以后,读宋儒书,因而进求之《论语》、《孟子》,及汉儒之书。近年五十乃肆力于群经子史,稍有所得。”[5]68因此,中年以后,陈澧力图以学风扭转世风,不仅批评汉学末流琐屑、无用,而且兼采宋学之长。
(一)力图以学风扭转世风。陈澧于45岁时编纂《汉儒通义》,又于晚年著述《学思录》(后以《东塾读书记》15卷刊行),力图调和汉宋学之争,并且“援经术为治术”,发挥学术经世的现实效应。他自述《学思录》的著述动机说:“读书三十年,颇有所得,见时事之日非,感愤无聊,既不能出,则将竭其愚才,以著一书,或可有益于世。惟政治得失,未尝身历其事,不欲为空论,至于学术衰坏,关系人心风俗,则粗知之矣,笔之于书,名曰《学思录》。……然天之生才使之出而仕,用也;使之隐而著述,亦用也。”[3]165因此,他本人虽然没有步入仕途,但是却寄希望于以学术培育人才,并进而服务于社会,他说:“政治由于人才,人才由于学术,吾之书专明学术,幸而传于世,庶乎读书明理之人多,其出而从政者必有济于天下。”[3]175
在陈澧看来,学风至关重要,具有左右世风的力量。他将《孟子·离娄》中的“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阐发为:“上修道揆,下谨法守;朝信道,工信度;以义治君子,以刑威小人;上兴礼,下勤学;事君以义,进退以礼,言必称先王;如此则国存而贼民灭矣。且以贼民兴,由于下无学。然则学问之事,所系岂不重哉!”[1]62作为饱读儒家经典的传统士人,陈澧认为,所谓“经学”是治世的根本,其言曰:“经学所以治天下矣。”[1]360又说:“谓经学无关于世道,则经学甚轻;谓有关于世道,则世道衰乱如此,讲经者不得辞其责矣。”[2]182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经学”为有用之学,他说:“惟求有益于身,有用于世,有功于古人,有裨于后人,此谓之经学也。有益于用者,不可不知;其不甚有益有用者,姑置之;其不可知者,阙之。此之谓经学也。”[3]179
由此,陈澧对时人不读书的风气颇表不满,他指出:“天下乱由于学术衰,学术衰由于懒读书,懒读书,乱天下矣。”[1]376又说:“天下之乱由于做官者不知读书,读书者不知做官。”[1]363在具体应该读何书的问题上,陈澧认为:“士人读书,当以《学记》为法,以《孝经》、《论语》为根本,各习一艺而博通之,求其有益于身,有用于世。”[1]759在其晚年之作《东塾读书记》中,陈澧变动“十三经”的顺序,将《孝经》、《论语》和《孟子》排在首位,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如其所引述的司马光之言“《孝经》、《论语》,其文虽不多,而立身治国之道,尽在其中。”[1]13又进一步指出:“《孝经》大义,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皆保其天下国家,其祖考基绪不绝,其子孙爵禄不替,庶人谨身节用,为下不乱。如此则天下世世太平安乐,而惟‘孝’之一字,可以臻此。”[1]15可见,陈澧如此推崇所谓“孝”,主要目的就是希望社会各阶层能各安其命,使混乱的社会秩序得到安定。
(二)批评汉学末流无用之病和兼采宋学修身之长。首先,陈澧批评汉学家不讲求“义理”。他说:“训诂考据有穷,义理无穷。”但是,“今人只讲训诂考据而不求其义理,遂至于终年读许多书,而做人办事,全无长进,此真与不读书者等耳!此风气急宜挽回也。[2]185”因此,陈澧认为,读书应以义理为归宿,以求有用,他说:“由汉唐注疏以明义理而有益有用,(繁酿之文无益无用者置之)由宋儒义理,归于读书,而有本有原,(师心之说无本原者弃之)此《学思录》大指也。”[2]182
其次,陈澧对方东树及其《汉学商兑》并不赞赏,批评多于肯定,但是却赞同其对“近儒”之学“无用”之评,他说:“方植之(东树)曰:‘毕世治经,无一言几于道,无一念及于用,以为经之事尽于此耳矣,经之意尽于此耳矣。’此中近儒之病。读经有当言道者,有不必言道者;有应念及用者,有不必念及用者。”[1]672-673原因在于,清代考据学家为学问而学问的风气如同晋朝的清谈、唐朝的禅宗与宋明理学之学风空疏、无用。他说:“解释辩论者多,躬行心得者少,千古如斯,良可浩叹!虽圣贤复起,殆亦无如之何,宋明讲理学如此,今人讲经学亦如此,即晋之清谈唐之禅宗,亦如此。”[2]185因此,他希望能通过学术扭转这种不正常的风气,他著述《汉儒通义》的宗旨就是“窃冀后之君子,祛门户之偏见,诵先儒之遗言,有益于身,有用于世,是区区之志也。”[6]115
陈澧为学主要尊汉,但是当他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35岁读到《朱子文集》时,对朱熹表示极为尊敬,认为:“读朱子书,以为国朝考据之学源出朱子,不可反诋朱子。”[1]11陈澧对朱子之学充满了敬意,主要是因为朱子之学可以修养身心与维持世道,他说:“朱子之学维持世道,自宋元至于今日,而衰微寖绝,何时复兴,则吾不得而知之矣。”[1]368他甚至认为,《朱子语类》堪当“朱子之《论语》”。他说:“《朱子语类》,精博之极,则学者所宜从事,所恶于语录者,陈言空论耳。不可以‘语录’二字尽行抹杀也。然则《朱子语类》,乃朱子之《论语》也。”[1]409因此,他于咸丰九年(1859)着手编纂《朱子语类日钞》,所录都是朱熹平日对学生在道德、学术等方面的教导,句句都是朴实说理之言。
陈澧认为,真正的学问应该无所偏党,他在《东塾读书记》中特列“郑玄”与“朱子”各一卷,旨在宗汉学的同时又兼采“宋学之善”,又一再批评汉、宋学者互相诋毁的现象说:“汉学、宋学迭相攻击,实无人细读郑、朱两家书。余欲著郑学、朱学二书,盖不得已,竟须成此二书,乃一生事业也。”[1]768
可见,陈澧提倡汉宋学兼采,其主要原因是基于道德修养层面的考虑,也即希望建设一种中正无弊的学术风气,借以扭转世风、养成政治人才并达到修齐治平的高远理想。
(三)推尊顾炎武经世致用之学。生逢乱世的陈澧对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极为推崇,甚至将他比作孟子,其言曰:“孟子论天下‘一治一乱’,而曰‘我亦欲正人心’。顾亭林之言,足以畅其旨。……亭林在明末,亦一孟子也。”[1]63《学思录》就是仿效《日知录》写成的,陈澧指出:“《学思录》排名法而尊孟子者,欲去今世之弊而以儒术治天下也。”[1]758他又重申:“《日知录》上帙经学,中帙治法,下帙博闻,仆之书但论学术而已。……吾之书专明学术,幸而传于世,庶几读书明理之人多,其出而从政者必有济天下,此其效在数十年之后者也。”[3]175几乎与顾炎武对《日知录》的期待完全相同。
陈澧对顾炎武“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之言极为赞赏,重申士人应该学与行并重,他说:“劝学,即博学于文也;奖廉,即行己有耻也。窃尝论之:《论语》第一句‘学而时习之’,即博学于文之初基也;《孟子》第一句‘何必曰利’,即行己有耻之要道也。亭林之言,与《论语》、《孟子》若合符节也。”[1]642因此,他将顾炎武这两句话揭于菊坡精舍前轩,以此教导诸弟子[3]96。
儒家学术从来就是一种有体有用之学,一方面它可使士人“成德”或“成学”,另一方面最终目的是要“措之天下,润泽斯民”,即经世致用。陈澧认为,国家治乱与人心风俗休戚相关。因此,他认为,欲国治,则必正人心风俗,欲正人心风俗,必须从儒家经典中找出路。这里,陈澧显然把儒家学问当作立身行事的准则。这种看法其实是中国传统的以学术领导政治,以儒家德治主义为核心,整合学统(知识)与道统(治术)于一体理想的重申。
三
陈澧不仅认为应该以学术扭转世风并改良政治,而且他也对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寄予深刻关怀,试图从学术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一)生逢乱世,忧心时局。在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期间,陈澧饱受战争带来的困苦、惊吓,三次为躲避战乱而举家迁徙。期间,陈澧生活、处境艰难:“深夜自思,天祗使我读书,置之于孤穷之境。书卷不得多,朋友不得多,……忧之至,愤之至!”[1]746陈澧第三次避乱横沙村时间长达3年之久,其时学海堂已经停办,经济来源中断,生活十分窘迫,正如他本人所称“值贼乱、夷乱,家计不给。”[1]11但是,就是在此期间,他完成了《汉儒通义》的编纂,寄托着他对时局、学术的关怀,他写信给桂文灿说:“时事如此,岂能不忧愤。即以家事而论,迁徙奔波,产业被焚,几无以糊口,亦岂能不愁思,然手无斧柯,虽有救乱之志,可奈何……”[5]66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英法联军兵临广州城下,而两广总督叶名琛不作战守计却相信迷信乩语,陈澧深表愤慨,作诗记其事曰:“叶中堂,告官吏,十五日,必无事。十三夷炮打城惊,十四城破炮无声,十五无事灵不灵?乩仙耶?点卦耶?籖诗耶?择日耶?”[3]633
(二)否定科举制度,抨击时文之弊。陈澧先后共7次参加会试,但均告不售,消耗了他从青年到壮年的年华,这使他对科举制度之弊认识十分深刻,由此表示对之否定。他说:“天下人才败坏,大半由于举业。”[3]175其中,他对所谓“时文”的弊端认识尤其深刻。他具体分析说:“时文之弊有二:代古人语气,不能引秦汉以后之书,不能引秦汉以后之事。于是为时文者皆不读书,凡诸经先儒之注疏,诸史治乱兴亡之事迹,茫然不知,而可以取科名、得官职。此一弊也。破题、承题、起讲、提比、中比、后比,从古文章无此体格,而妄立名目,私相沿袭,心思耳目缚束既久,锢蔽既深,凡骈散文字、诗、赋皆不能为。此又一弊也。”[3]77-78在陈澧看来,只有认真通读经书,掌握儒家修齐治平之术的人才算是真正的人才。
(三)力主禁止鸦片,抵御外来侵略。陈澧对鸦片之为害十分痛恨,认为:“二三百年以来,纷牣宇内,穷泰极侈,害理伤俗,近又益以阿芙蓉,毒螫我萌庶,攘窃我金钱。”[3]328他认为,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是中国人喜欢“洋货”,他作《炮子谣》纪其事曰:“炮子之来自外洋,外洋人至由通商。通商皆由好洋货,钟镖绒羽争辉煌。钟镖绒羽人人喜,谁知引出大炮子。吁嗟乎!炮子来,君莫哀,中国无人好洋货,外洋炮子何由来。”又对时人吸食鸦片深感担忧,诗曰:“请君莫畏大炮子,百炮才闻几人死。请君莫畏火箭烧,彻夜才烧二三里。我所畏者鸦片烟,杀人不计亿万千。君知炮打肢体裂,不知吃烟肠胃皆熬煎,君知火烧破产业,不知吃烟废尽囊中钱。呜呼太平无事吃鸦片,有事何必怕炮怕火箭。”[3]578-579
陈澧将鸦片战争发生的原因归结为国人喜欢洋货和鸦片未免失之简单,但是他立主抵御外侮的立场却十分鲜明。道光二十九年(1849),陈澧注意到《海国图志》,对“毅然以振国威、安边境为己任”的魏源十分赞赏,称之为“有志之士”,又认为抵御外侮的根本之道在于富国强兵,他说:“为今之计,中国贵乎崇廉耻,核名实,刑政严明,赏罚公当,则可战可守,外夷自不敢欺。不循其本,而效纵横家言为远交近攻、近交远攻之说,譬如人有虚羸之疾,不务服药培补,而但求助己者出与人斗,可乎?”[3]89-91
陈澧十分重视地理地图之学,认为它是了解“夷情”、抵制外来侵略的必要工具,他说:“自明以来,西海诸国咸来通市。今则攻陷省会,直窥京师”,原因在于对方了解中国的国情,但是中国人却对外人“懵然不知,犹以为极西荒远之国也,岂不愚哉!”因此,他主张“昔之考地理者,考九州之内;今之考地理者,更当考九州之外。”[1]407
(四)重视中西科技与工商业。面对西方入侵者的坚船利炮,陈澧意识到了所谓“圣贤”之说的空泛,他说:“时事不胜忧叹,孟子所云‘明其政刑,制挺可挞坚甲利兵’,斯为根本之计”[3]477。因此,他主张“兴艺”,他说:“‘兴艺’二字甚合鄙意,仆近于《学思录》发明‘不兴其艺,不能乐学’二句,并明人乐学而不兴艺,近人兴艺而不乐学。……故特发明‘兴艺’二字也。”[3]427他又将科学技术称为“实学”,指出:“世俗之所谓经学、小学,今尚有人,但少实学。若吾弟专于礼,仆专于乐,特夫(邹伯奇)专于天算,子韶(赵齐婴)专于地理,庶几此等实学不至遂绝,后起之士有所谘问。”[3]430
陈澧虽然对洋人及鸦片等洋货深恶痛绝,但是对“夷技”并不歧视。他在青年时代曾与侯康等人在广州学习算术,并于道光十五年(1835)、咸丰七年(1857)先手撰成《三统术详说》、《弧三角平视法》。他认为,近代中国科技已大大落后于外夷,原因在于人们对其重视不够,他说:“《考工记》实可补经,何必割裂五官乎?作记者,以一人而尽谙众工之事,此人甚奇特。且所记皆有用之物,不可卑视之。惟其卑视工事,一任贱工为之,以致中国之物不如外国。”[1]137他对明以来儒者不工历算之学进行批评,他说:“明儒不知历算之学,故西洋人以此技入中国,贻祸于今,如此其甚也!若明儒识历算,则西洋人为辽东豕耳。今人必当习此学,此吾所以殷殷然劝勉后生也。”并说:“考工之事,亦当讲求。”[1]638
不过,陈澧也如同时人一样坚持所谓“西学中源”说,并认定西学源自《墨子》,他说:“征君(邹伯奇)得《笔谈》之说,观日月之光影,推求数理,穷极微眇,而知西洋制镜之法皆出于此(按指《墨子》)。”[3]122同时,陈澧又认为,应该以传统的刻漏之术代替西洋钟表[1]745,显示了他作为传统士人的保守与落后。
陈澧还能突破儒者言义而耻言利的传统观念,对工商业表示重视。他指出:“观《考工记》文章之精美,则知古之文人学士,识制器之事。今之士大夫全不识,又不知商贾事,所以不如外夷。”[2]212因此,他呼吁应该允许中国商人出海贸易[1]407。
陈澧很少直接讨论政治问题,原因在于他认为自己没有足够的名位,他说:“余所以不敢为经济之说者,吾能言之而无权位,不能施用之。他人取吾言而施用,或有过差以乱天下,是可惧也。”[1]751但是,在陈澧所遗留下来的文字中也有一些属于时政建策,他自己就曾说:“《学思录》只论学术,然政事亦兼有之。君德、相业、六曹、侍从、台谏、封疆、郡县、学校、营武及民俗之弊,皆余波及之,无所不有。”[1]757他还曾列出了一些提纲性的时政条目,展现了他关注国计民生和以学术服务现实的理想[1]410。
四
陈澧身处晚清世运和学风转变的纽结处,因此试图从儒家德治主义传统出发,把清王朝的衰败和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归结为“道德废,人心坏,风俗漓”,希望通过学术来培育人才,改良世道人心,从而改善现实政治。他忧心时局、主张禁止鸦片、注重科技实学与改良教育,并提出一些具体“经济”建策,力图发挥学术经世的现实效应。
但是,陈澧以读书著述终老一生,因此面对现实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其所议论和提出的解决办法仍然未超出传统士人的藩篱。他既未能象龚自珍、魏源那样大胆地批判黑暗的社会现实、提倡“改制”、“更法”,也未能就海运、漕运、盐法、河工、军备等“大政”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革良策,更未能像曾国藩、张之洞等洋务派那样吸收近代西学和唱和所谓“中体西用”之说。钱穆说:“读东塾之书者,皆确然认其为一经师,终不得摈而不预之经学家之列也。凡东塾所欲提倡之新学风,大率如是,是其用心至苦,而成就亦至卓矣。”[7]689陈澧的言论与著述无非是为了发挥传统儒学中“道术”对“治术”的佐助作用,即以学术来调节社会现实危机和世道人心,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晚清时期所遭遇的社会总体性危机,正如龚自珍所指出的“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8]513。毕竟在多事之秋的晚清,汉宋相争也罢汉宋兼采也罢都与现实社会的需要渐行渐远了。不过,陈澧也意识到了所谓“圣贤”之说的空泛,因而主张“兴艺”,肯定科学技术的实用价值,并称之为“实学”。这也使我们不难理解他对当时传入的西洋文明并不一味采取排斥的态度,这与极端守旧的倭仁、徐桐辈又不尽相同,是他作为传统士人所表现出来的开明豁达的一面。
[1]黄国声主编.陈澧集(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杨寿昌,陈兰甫先生澧遗稿[J].岭南学报,1932(3).
[3]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C]//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长沙:岳麓书社,1998.
[5]汪宗衍,陈东塾先生(澧)年谱[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
[6]黄国声主编.陈澧集(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7]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8]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十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