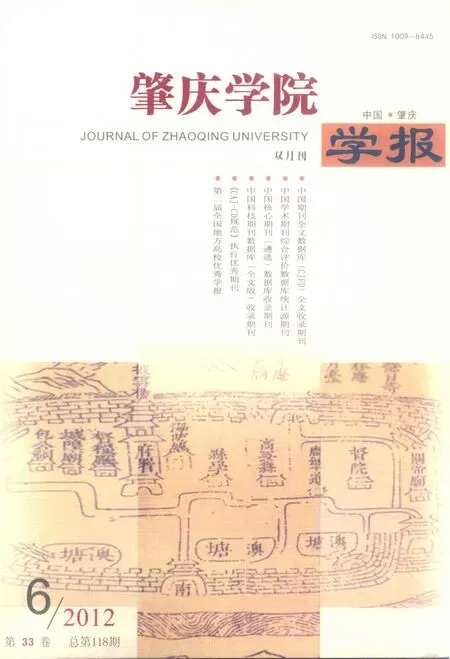现代“小诗”文化身份的鉴识——论胡怀琛的《小诗研究》
2012-01-28卢永和
卢永和
(肇庆学院 文学院,广东 肇庆 526061)
20世纪20年代的现代“小诗”运动,掀起中国新诗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其中,冰心的《春水》《繁星》、宗白华的《流云》、俞平伯的《冬夜》、刘大白的《旧梦》、汪静之的《蕙的风》、何植三的《农家的草紫》等诗集收有大量的小诗。“小诗”在当时亦称“短诗”或“短歌”,它被确认为一个特指的诗学范畴,归功于周作人。早在小诗运动勃兴之初的1922年,周作人于《晨报》副镌发表《论小诗》一文,从小诗的“定义”、“来源”、“特点”等方面探讨小诗。该文是第一篇系统论述“小诗”的长文,周作人也被公认为“小诗”研究方面的权威。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以总结之论,进一步提高了周作人的小诗研究地位。笔者无意否定这一学术“常识”,只想补充一个重要的学术事实:首次以专著形式系统研究小诗的学者是胡怀琛。胡怀琛在周作人发表《论小诗》的两年后,出版《小诗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一书。迄今为止,学界尚未对胡怀琛的小诗研究予以足够的重视①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论述“小诗”运动时未提及胡怀琛。另:中国期刊网(1911-2012)仅搜索到刘东方的《论胡怀琛的现代小诗研究》(《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4期)、《胡怀琛、周作人现代小诗研究之比较》(《齐鲁学刊》2008年第5期)两篇文章。前者对胡怀琛的小诗作了初步探讨,后者比较了胡怀琛与周作人小诗研究的异同。拙文侧重从小诗的文化身份这一特殊视角探讨胡怀琛的小诗研究。,本文拟对之进行探讨,以补学界之疏失。
一
胡怀琛(1886~1938),字寄尘,安徽泾县人,兼报刊编辑、大学教授、作家等多重身份,曾供职《神州日报》《中华民报》《万有文库》(古籍部)和上海商务印书馆等报馆编辑,先后在中国公学、沪江大学等多所大学授课。胡怀琛博学多才,勤于笔耕,计有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等著作170余部,内容涉及古典文学、新文学、文学理论、文法修辞、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历史学、民歌、儿童文学、文字学、目录学、地方志、教科书等,堪称人文学全才。胡怀琛与诗结缘颇深,有诗集《大江集》《江村集》《胡怀琛诗歌丛稿》等,涉及诗歌研究的有《海天诗话》《新诗概说》《新文学浅说》《中国诗学通评》《诗学讨论集》《白话诗文谈》《诗歌学ABC》等著述。胡怀琛为胡适改诗,并将由此引发的论争汇成《〈尝试集〉批评与讨论》(泰东图书局,1921年)一书出版,亦名噪一时。
胡怀琛在《小诗研究》中谈及自己的研究动机:“新诗出现了这几年,虽然有许多好的作品,却也有一大部分的不够成熟的作品。我以为在许多的新诗集之中,要算是小诗的成绩顶好。……因此触动我研究之心,时时把这个问题放在心上。……小诗为什么容易做得好?是小诗比长诗容易做么?”[1]1-2胡怀琛研究小诗,先是写了篇一二千字的小论文《小诗的成绩》刊载于《时报》,引发了同人的热烈讨论,后来他再加进一些新的认识,由此扩展为一本专著——《小诗研究》。《小诗研究》共14章,内含“诗是什么”、“中国诗与外国诗”、“新诗与旧诗”、“什么是小诗”、“小诗的来源(上、中、下)”、“小诗与普通的新诗”、“小诗与中国的旧诗”、“小诗实质上的要素”、“小诗形式上的条件”、“小诗的成绩(上、下)”等章节。该书前述“诗”的基本理论,以此为理论依托,后论“小诗”的实质问题。
关于小诗的来源,当时盛行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小诗来源于日本的俳句;另一种说法认为小诗来源于泰戈尔的诗。两说均与周作人有关。周作人在1916年发表的《日本的俳句》和1921年的《日本的诗歌》两篇文章中,皆以“小诗”之名指称日本的诗歌;其后于1922年发表《论小诗》一文,以“小诗”之名称谓“现今流行的一行至四行的新诗”,并指出“小诗”的外来影响:“它的来源是在东方的:这里边又有两种潮流,便是印度与日本。”[2]周作人的观点在当时乃至现在均有较大的学术影响力,其说亦可从一些小诗作者的自我陈述中获得支持。小诗作家冰心曾坦言:“我写《繁星》,正如跋言中所说,因看着泰戈尔的《飞鸟集》,而仿用他的形式,来收集我零碎的思想。”[3]
周作人强调小诗的外来影响,主要着眼于小诗的“新诗”身份。胡怀琛却不认可周作人的观点:“有人说:这样的小诗,是受着日本短歌的影响而始产生的。便是于民国十年,周作人做了一篇《日本的诗歌》,介绍些日本的短歌到中国来;这时候中国的新诗,方在勃兴的时代,将旧的格式,一律打破了;偶然见了外来的一种新的格式,觉得总是好的,尽力去学;所以日本的短歌,一到中国来,能使中国的诗坛,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很大的变化。于是中国的小诗乃盛行了。”[1]38-39胡怀琛认为:“日本的短歌的源流也很远,变化也很多,他也有一定的字数。不过翻译成了中国文来看,字数便无限制了。他的源流变化和中国新诗的关系很少。”[1]39
胡怀琛指出,从小诗创作实践来看,在日本短歌及泰戈尔的诗流入之前,中国诗坛已有很短的小诗,如康白情的《疑问》组诗、郭沫若的《鸣蝉》等。同时,小诗作为一种诗体样式,不但在中国的新诗坛有,欧美也同样存在,如美国诗人P.Onell写的短诗:“At the rude goodness/Of the rain/The flowers wince/But drink(译:雨的暴躁的仁慈,/群花畏缩而饮了)。”[1]47而从诗歌的精神溯源来看,日本短歌在发展过程中也曾受到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从诗歌的质实而言,胡怀琛认为泰戈尔诗歌的长处在于它的思想,而不是它的形式。“太戈尔的诗,理多于情。中国人做的小诗,虽然是学着太戈尔的形式,但是情多于理,或纯然是情。若带一些理,又往往近于格言。所以在实质上说,中国的小诗,并没有受太戈尔的影响。就是有也极少极少”[1]45。
胡怀琛否定小诗的外来身份,而从诗歌创作的一般规律来考察小诗:“诗本来是短的多,长的少,无论新诗旧诗,都是如此。除了长篇大幅的纪事诗以外,其他的诗,虽然不及普通所谓小诗这样的短,却也不十分冗长。”[1]51胡怀琛由此淡化小诗的“新诗”性质。另外,在胡怀琛看来,新诗相比旧诗,更适合做短:“旧诗要做得长一些,还可以拿词彩,声调来帮助。词彩绚烂,声调铿锵,内容虽然是空空的,却还是容易遮掩得过俗人的耳目。新诗是赤裸裸地,词彩,声调,都打扫得干净;倘然才力薄弱,而欲做长诗,那长诗一定无足观,连俗人的耳目也不能遮掩了。”[1]52由此可见,小诗是诗歌创作合乎自然的选择:“篇幅短,究竟容易做;略微有了一点意思,或者是本着一种自然的感触,随便写出来,也就是一首好的小诗。所以小诗的成绩,很可观了。”[1]44
二
胡怀琛认为,小诗虽为“新诗”,但留有旧诗的印痕。他在《小诗研究》中专辟一章“小诗与中国的旧诗”探讨此问题。胡怀琛指出,小诗篇幅短小,意蕴隽永,重含蓄暗示,这种诗体形式在中国古代大量存在:中国古代歌谣都是很短的诗歌;《诗经》里也有很短的诗;汉以后的五七言诗中也有短诗。另外,胡怀琛认为中国古诗中的“摘句”和小诗颇为接近。所谓“摘句”,即是把一首诗中一两句精彩的诗句摘录下来,摘句由此便成了“小诗”。摘句形式在律诗和绝句中多有体现。胡怀琛认为绝句的三四句,就是一首独立的小诗;律诗中的中间一联,再把他平分开来,也就是两首独立的小诗。比如,“寂寞空庭春秋晚,梨花满地不开门”两句,可写作小诗:“寂寞空庭,春光暮了;满地上堆著梨花,门儿关得紧紧的。”[1]60他把律诗中的一联“病多知药性;客久见人心”分开来,于是便写成两首小诗:1.“老生病的人,渐渐知道了药性”[1]61。2.“久漂泊在天涯,看透了人情事故”[1]61。同时,一些古代词里的摘句,本身就可视为小诗,如宋词蒋捷的《一剪梅·舟过吴江》中的“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花(应作“桃”字,笔者注),绿了芭蕉”。小诗与旧诗的亲缘关系,反过来亦可证明。在胡怀琛看来,现在流行的小诗,也可改为旧式的诗词。如冰心的小诗“生离——是朦胧的月日,死别——是憔悴的落花”,可改写为律诗:“憔悴落花成死别;朦胧残月是生离”[1]63。而她的另外二句小诗“白的花胜似绿的叶;浓的酒不如淡的茶”,可改写为一联律诗:“白花骄绿叶?浓酒逊清茶。”[1]63
胡怀琛亦从诗歌的文化血脉阐释小诗和旧诗的关系。他扼要地梳理了中国古诗演进的脉络:《诗经》里的诗表达的是温柔敦厚的感情;楚辞是长江流域的风气,给诗加进了神秘幽怪的气息;汉代诗歌受胡人影响,多了一层豪放雄壮的气概;晋代诗歌因老庄思想影响,多了一种玄妙高超的意味;唐诗因佛学的融入,有了觉悟解脱的见识。在梳理中国古诗“知识谱系”的基础上,胡怀琛对中国古诗作出定性:“中国诗的唯一特点,就是他用含蓄的方法,发表他温柔敦厚的感情。后来虽然加上了许多原质,发生变化,但是仍离不了温柔敦厚的本性。”以此为据,他揭示了小诗所表现的中国诗学传统质素,并进一步作出判断:“有许多好的新诗,他的实质,仍旧是中国固有的实质。或者小诗也是固有的形式变出来的。”[1]23他举胡适的新诗《希望》为例:“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开花好。/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急坏看花人,苞也无一个。……”胡怀琛认为这首新诗以“兰花草”来比喻新文化,“山中”指美国,但整首诗表达的是温柔敦厚的感情,形式是五言诗体。基于小诗和旧诗的内在相通性,胡怀琛倡导新诗作者多读旧诗,这样对新诗创作颇有助益。
在新旧文学汇流演进过程中,胡怀琛坚持中国文学的本体地位:“我以为欲研究中国文学,当然要拿中国文学做本位。西洋文学,固然要拿来参考;却不可拿西洋文学做本位。倘用拿西洋文学的眼光,来评论中国文学;凡是中国文学和西洋文学不同的地方,便以为没有价值,要把他根本取消了,我想是没有这个道理。”[1]1胡怀琛在中国文学研究观念上以中学为本,但他并不属于守旧落后派,他也看到了新旧诗体的歧异。尽管小诗与旧诗可以互译,但他并不鼓励人们都去做旧诗,在他看来,新诗与旧诗各有好处,不必是此而非彼。在《新旧文学调和的问题》一文中,胡怀琛指出,“文学作品只有好与不好的分别,没有新旧的分别。所以新旧二字,不成问题”[4]。胡怀琛认为文学作品只有好坏之分,没有新旧之别,他在探讨新诗与旧诗之别时指出,“现在讲新文学的人,做的一种诗,名为新诗;因此对于前头的人所做的诗,称为旧诗。新旧二字,是对待的;没有新诗以前,诗只称为诗,没有旧诗的名目;但是旧诗之中,也有古诗近体之别”[5]。在胡怀琛看来,文学新旧之名,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并未有质的内涵。
三
在20世纪早期新文学运动中,小诗是作为“新诗”的一种诗体类型得到普遍认可的。有论者指出,“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小诗’运动,是新诗在符号形式上实现了对旧体诗的变革,确立了自由诗这一主导形式后,针对新诗资源的不足和创作实践的消沉,力图借鉴外来资源,纠正早期白话诗的贫弱,寻求自身发展的一种有益的尝试”[6]。这段话基本明确了“小诗”的诗学定位:“小诗”是“新”文学,其理论资源来自外国。由于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同构关系,学者们在强调小诗的“新文学”身份时,往往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看待小诗(新诗)与旧诗的关系,过分强调二者分属不同的话语体系,由此而漠视了小诗的中国古典诗学传统。
无论是质疑小诗的外籍来源,还是考察小诗与中国古诗的渊源关系,胡怀琛实际上是有意模糊小诗的“新诗”身份。在他看来,“小诗”的名称不过是一种言说习惯,他曾和同道讨论过“小诗”的名称问题:“有人说:应该称为短诗。我以为小诗两字,在新诗界里,差不多人人都知道了,短诗反不及小诗普遍。本来旧诗里,也有所谓短歌行,在旧词里,也有所谓小令。短和小都是对于长诗而言的,并不必小是对于大而称的。我们称为小诗,长诗,也就像旧词家称小令,长调。这样说来小诗的名词,很妥当了。因此便决定称他小诗。”[1]2-3对于“小诗”之名,胡怀琛只是遵循“普遍”的说法,并未将它视为一种具有特殊诗学内涵的诗体。胡怀琛自己也写过一些小诗,如《月儿》:“月儿!/你不要单照在我的头上,/请你照在我的心罢!”他的体会是:“在当时我不叫他是小诗,只叫他是诗意。以为只有诗的意思,而没有做成诗;其实也就是所谓小诗了。”[1]64
时至20世纪,尽管新、旧诗体话语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胡怀琛却仍未重视小诗的“新诗”身份,这一点在《小诗研究》的思理逻辑上表现得尤为显明。在入小诗正题之前,胡怀琛先探讨“中国诗与外国诗”、“新诗与旧诗”等宏观理论问题。《小诗研究》全书不到100页,分量本不重,为什么还绕这么大的弯子?仔细推敲,其中别有深意,这实际上是为定位小诗的文化身份作理论铺垫,如他所言,“这本书是专门研究小诗的,本来只应该在小诗的范围以内说话;因为小诗和非小诗有连带的关系,欲说小诗,不得不从一切的诗说起”[1]3。胡怀琛所谓“一切的诗”,其意指向诗的普遍性质。胡怀琛的研究理路颇为清晰,小诗属于“诗”,而与新、旧的关系不大。对于诗的本体规定,胡怀琛在他的《新诗概说》和《小诗研究》两书中均强调两点:其一,“诗是表情的文字”;其二,“诗是有音节,能唱叹的文字”。从诗的本体属性来看,小诗与其它诗体有诸多相通之处,歧异在于表达的情感实质和艺术技巧的不同。他在比较中国诗和外国诗的不同时指出,“因为各国的政教风俗不同,所以国民性不同,所以在诗里的情也不同了”[1]5。在此基础上,胡怀琛进一步指出中国诗和外国诗的区别:“中国诗里的感情是含而不吐的,外国诗里的感情,是充分说出来的。外国诗里的感情,比较中国诗里的感情,要热烈的多。”[1]8在胡怀琛看来,外国诗“受了科学的感化,故思想多质实,又受了耶教的陶冶,故感情甚热烈”[1]9。可见,中国诗和外国诗的差异,本质上是文化的差异。
小诗到底是新诗还是旧诗?胡怀琛对此问题没有直接给出答案。他只是从形式和实质两个方面指出新诗与旧诗的差异。形式上,旧诗有音韵字句的束缚,新诗打破了这些束缚,可以自由言说。他同时也强调,新诗在形式上虽然没有音节的束缚,但也应该有自然的音节,“无论长到何地步,读起来觉得很自然,再也不能减一字;无论短到何地步,读起来很自然,再也不能加一字:这样才算完全好”[1]52。而在实质上,旧诗只是表达中国原有的感情和思想,而新诗则受了欧洲的感化,能够直接、热烈地抒情。他同时也认为,“这回加入欧洲输进来的实质的思想和热烈的感情,乃是当然的事。不过要经过一番融化的工夫,才能成熟。现在离成熟的时期还远得很,也许是永远做不到。譬如欧洲人的热烈的感情,乃是根于宗教而来的;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心,不但是薄弱,而且可说是没有;欲学他的热烈的感情,从何处学起呢?说到实质的思想,中国人所受的科学的影响,不知比欧洲人要薄弱得多少倍,而作诗欲学他的实质,又从何处学起呢?”[1]19胡怀琛认为中国诗歌讲求温柔敦厚,难以表达西方人那种热烈的感情。
认清了外国诗与中国诗、新诗和旧诗的区别,小诗的诗体特性已非常清楚:一方面,小诗作为一种中国诗,其文化根基在中国;另一方面,从时代发展阶段来看,小诗是新诗,它和旧诗有一定区别,但文化血脉是相通的:“温柔敦厚,乃是中国诗的本色;而意丰词约,又是中国文字的特长。中国人用中国文字来写小诗,自然是容易成,而且容易好。”[1]76据此,胡怀琛从实质和形式两方面对小诗作出概括:“小诗实质上的要素,第一是温柔敦厚的感情,其次乃是神秘幽怪的故事,玄妙高超的思想,觉悟解脱的见识”[1]72;“小诗的形式,除了自然及含蓄以外,没有什么条件。有天然的韵也好,没有天然的韵也好。大概可说一句:就是将一刹那间的感觉,用极自然的文字写出来,而又不要一起说完,使得有言外余意,弦外余音”[1]74。
结语
胡怀琛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关于小诗的理论探讨,表达了他对现代新诗的个人理解,其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看待中国新诗的固有文化传统。胡怀琛对小诗虽有系统研究,但并未把小诗提升为一种独立的诗体,而是探讨小诗与新、旧诗之间的绞缠、扭结关系。但无论如何,小诗毕竟是20世纪以后新兴的一种诗体,小诗的诗学观念并不是简单地回归传统,必然带有新时期文学的时代特征。如果“小诗”和“旧诗词”之间可以随意改写,“小诗”还能否称为一种新诗体?小诗在诗质和诗形上是否具有自身特定的诗学和美学内涵?这些是胡怀琛留给我们思考的问题。
胡怀琛既不是新文学圈子的人,也不属于保守派别,他力主“调和”新旧文学思想,由此造成旧文人方面既感到他不够旧,新文人方面又觉得他不够新。在文学观念剧烈碰撞的新文化运动时期,“调和”论由于理论立场的摇摆模糊,棱角不够分明,从而容易被人忽略,这是他的《小诗研究》逐渐被学界淡忘的主要原因。时至今日,如果摈弃中与西、新与旧的二元对立思维,而替之以一种中西文化兼容的心态,我们无法否认胡怀琛的小诗研究所具有的学术含量。
[1]胡怀琛.小诗研究[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
[2]仲密(周作人).论小诗[N].民国日报,1922-6-29.
[3]冰心.冰心选集(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204.
[4]胡怀琛.文学短论[M].上海:大中书局,1924:41.
[5]胡怀琛.新诗概说[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8.
[6]黄雪敏.20世纪20年代“小诗”运动[J].福建论坛,2007(2):9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