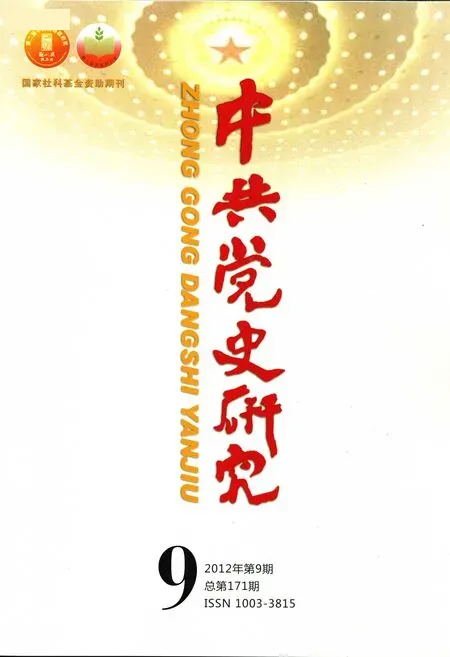中共党史论文论点摘编
2012-01-28
中共三次新闻改革与传媒公共性的变迁
许 鑫
中共新闻事业史上的三次新闻改革,既是新闻观念和新闻业务的改革,也是传媒体制、属性和功能的调整,深刻地影响着传媒公共性的发挥。在新闻改革前,中共报刊以政治属性为主,兼具一定的公共性。在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开展的第一次新闻改革确立了党报的党性、组织性、群众性和战斗性,使中共报刊向强化党性、弱化公共性的方向转变。新中国成立后,以中共党报为中心的新闻事业体系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在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并提出“双百”方针的文化背景下,第二次新闻改革着力于扩大报道范围、开展自由讨论和改进文风,强调尊重客观现实与新闻规律,试图由宣传本位回归新闻本位, 《人民日报》还提出“报纸是社会的言论机关”、“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它是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财产。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等理念,反映了当时新闻界对党报属性和功能的一次反思和超越。但这次改革被反右派斗争打断,传媒的公共性由此被长期忽略,及至“文化大革命”时期,传媒更异化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公共性消失殆尽。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新闻事业开始了第三次新闻改革,涉及新闻观念、新闻业务和经营管理等诸多方面,核心是传媒业的市场化转型。这次改革使中国传媒由单一的政治属性转换为政治和产业之双重属性,新闻工作者的专业主义理念渐次产生,加之网络新媒介的参与,传媒的公共性得以部分重生。传媒公共性的发展需要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市民社会等作为基础,最终取决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的变化,以及政治体制和传媒体制的深入改革。
(吴志军摘自《暨南学报》2012年第4期,全文约10300字)
推进“文革”研究进入历史学学术轨道——兼论中国“文革”研究的现状和前景
金大陆
近年来,海外和国内学界尤其民间的“文革”研究呈现涌动之势。海外研究以大批资料的整理、学术活动的举办和转向社会与区域研究等为学术特征。国内研究侧重于“文革文学”、“文革理论”和“文革运动”等方面的分析和推断,机巧地规避了耙梳“文革”史料的艰难和深入“文革”内部开掘问题的挑战,表明中国的“文革”研究尚未真正进入历史学轨道。民间的“文革”研究则在整理史料、撰写回忆录、接受访谈、聚会研讨以及通过港台出版机构或自印本、现代网络等形式问世的大量研究著述等方面率先呈现突破性态势,表明“文革”研究具有较为厚实的群众基础。但民间研究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尤其与现实政治发生或显或隐的联系后,有可能完全脱离历史研究的轨道。因此,未来的“文革”研究要注意规避“图谱化倾向”和“意识形态两极化倾向”,研究者应严格遵守史料为本的历史研究准则,坚持以学术立场审读史料和史实,才有可能真正产生具有学术意义和学术价值的作品。“文革”研究能否进入历史学的学术轨道,关键在于研究者能否以清醒的认知和态度遵守学术规范、追求学术品质。 (吴志军摘自《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全文约7600字)
借鉴与发展: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总体运思
李金铮
中国当代社会史亦称中国现代社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是研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变化及其规律的一门学问。它既是中国现代史的分支,也是中国社会史的分支,还是社会学、人类学的分支,也是一种特殊的研究方法和视角,相互之间并非非此即彼的排他性关系。综合学界相关讨论,本文认为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当代民间社会和普通民众的所有历史,不仅包括社会构成、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也包括民间社会、普通民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内容,从而极大地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和视野。同时,社会史研究还促进了历史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变革。由于社会史所涉内容包罗万象,其研究理论与方法应当是多元的,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外,自下而上的视角是社会史研究的基本立场,整体史观是社会史学者的根本追求,积极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是社会史学者的必备工具。资料来源也应当遵循多样化原则,包括文献资料、实物资料和视觉资料等,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民间文献、口述史料和文学资料。中国当代社会史尚处于初级阶段,应“专通并举”,既应着力于具体研究,在学习和借鉴已有成功论著的基础上前进,又要努力构建较为合理的中国当代社会通史体系,明确其研究内容、历史分期和基本线索等重要范畴。(吴志军摘自《河北学刊》2012年第4期,全文约14500字)
1920年代“打倒军阀”口号的历史遭际
王建伟
1920年代初期,国共两党均提出“打倒军阀”的口号,并将军阀与帝国主义之间的隐秘联系加以理论确证和阐述,获得了国人的普遍呼应与支持。为了与军阀军队的私有性质划清界限,国民党通过与苏俄及中共的多方面合作,确立了“政党领军”原则,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党军”体制,建立起一支不同于南北旧式军事势力的新式军队,有效地加强了“打倒军阀”口号的正当性,契合了当时以“文治主义”取代“黩武主义”的时代潮流。“党军”制度在北伐初期发挥了积极作用,推动了北伐战争的不断胜利,在社会舆论和时人观感中树立起国民党优于军阀的正面形象。但随着北伐战争的迅猛发展和旧式军阀部队不断被收编,国民革命军中的党代表制度不断受到日益膨胀的军权的侵蚀,北伐军的政治工作日趋衰微,军纪持续败坏,敌我之间的区分愈发模糊,“党军”迅速走向“军阀化”,“打倒军阀”的口号遭遇严重的现实困境。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蒋介石虽采取多种措施试图消除各地军人分治的局面,但受到严重阻碍,国民党在军事领域的党权支离破碎,“政党领军”、“主义治军”的建军目标逐步被“以军控党”、“武主文从”的现实取代。不久,在趋于激烈的国共之争和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中,国民党被不同的政治对手共同指认为“新军阀”,“打倒军阀”口号的政治有效性开始消解。(吴志军摘自《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全文约15000字)
葛兰西与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比较
黄卫星 李 彬
作为共产党领袖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和毛泽东都格外重视精神和意识形态力量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认为文化领导权的意义优先于政治和经济的统治,但他们的文化领导权思想亦有所差异。葛兰西通过考察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机制及其深层结构,主张通过有机知识分子从情感、道德、宗教、信仰和日常生活等方面影响市民社会,并获得其理解、支持和同意,逐步获得文化领导权;毛泽东则力主将一些强制性手段运用于文化的组织管理、政治控制和思想改造,突破了葛兰西将文化领导权归属于谈判和协商的单一途径与策略。可见,葛兰西将市民社会视为文化领导权的对象,而毛泽东认为文化领导权施与的对象应是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葛兰西认为有机知识分子应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提出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并与其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毛泽东则将劳动人民置于历史主人公的地位,要破除知识分子对人民群众的文化优势,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葛兰西希望国家更为长远宏阔的目标是创造更高级的新文明,这种文明形态不仅能够倡导广大民众的道德风范,而且能够发展出更为文明的“新人类”,新的政治文化的最高境界和最终目的是批判性、群众性和社会性;毛泽东则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应当是平民的、大众的、民族的,要超越精英的、高雅的、西式的五四文化传统,以维护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合法性。(吴志军摘自《清华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全文约17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