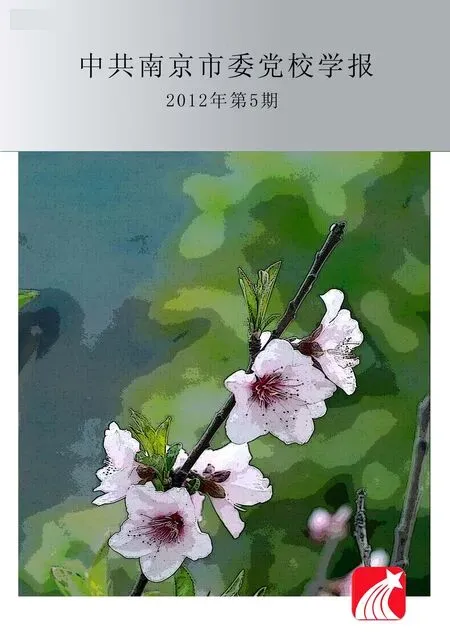政府干预经济的边界*
2012-01-27赵晓谛
赵晓谛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 江苏 南京 210001)
近代,在各种经济体制的国家,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已经大量存在,但是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是,政府的各种干预经济行为的效果并不一致,有些可以长期存在并无可替代,有的则不能实现预期目标,不得不中途退出。对于各种政府干预经济行为出现不同结果的问题,以往的研究一般地会从意识形态差异、决策正确与否、运作是否有效和技术手段是否完备这样一些外在方面予以解释,但其可以解释个别,却不能解释总体。与此不同,本文认为,作为集合的政府干预经济存在着自身的固有边界,任何政府经济干预行为发生在边界内时,它是有效的,反之,任何政府干预经济行为发生在边界外时,其固有约束机制将发挥作用,并导致边界外的政府干预经济行为归于低效或失败,并不得不退出。本文目的并不是为了给出判断各种政府干预经济行为合理与否的原则,也不是为了给某项政府干预提供决策依据,而仅仅是指出政府干预经济的边界固在,并说明在现实中,任何政府干预经济的决策,受此边界约束的机理。
一、从已有的讨论开始
在以往的经济学文献中,对政府干预的边界多有研讨,但其研究思路和结论各有不同。以下我们将讨论一些具有广泛影响的思想和观点,以说明类似研究与本文的区别。
公共物品理论通常被认为已经确定了政府干预的对象及范围,且具有广泛的影响,因此,公共物品理论可视作是对政府干预边界的研究成果之一。在公共物品理论中,以一物品的消费是否导致其他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为核心定义,区分出纯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并据此认为政府干预的合理范围应该是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私人物品由市场提供。
以公共物品界定政府干预的范围几乎得到了公认,在一些经济学家的文献中,毫无二致地都把政府干预的范围确定在公共物品,并将私人物品的生产归之于市场。曼昆(N. Gregory Mankiw)在其经济学原理中写道:“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是因为市场本身不能生产有效率的数量。但确定政府应该起作用只是第一步。政府还应该决定,提供哪些公共物品,以及提供多少”。他还说:“有效率地提供公共物品在本质上比有效率地提供私人物品更困难。私人物品由市场提供”。[1]布坎南也视公共物品为划分政府干预的界限,他在《公共物品的需求与供给》中写道:人们观察到有些物品和服务是通过市场制度实现需求与供给的,而另一些物品与服务则通过政治制度实现需求与供给,前者被称为私人物品,后者则称为公共物品。[2]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把政府支出区分为对收入进行再分配的政府支出和直接购买物品和服务的支出。对于后者,“我们把它划分为纯公共物品和为公众提供的私人物品。前者实际上是指公众共同消费的物品(如国防),而后者在原则上是而且经常是指私人能够提供的物品。”[3]
公共物品理论对政府干预经济的边界所进行的研究存在着明显缺陷,第一,公共物品理论试图界定的是政府干预的作用对象的范围,而不是政府干预这种行为的边界;第二,在公共物品理论中,由于公共物品范围本身就极不确定,因此政府干预对象边界也得不到确定;第三,该理论在现实中解释能力不足,经济现实是,政府的经济干预不仅广泛地发生于所谓公共物品领域,同时也大量地发生在私人物品领域。因此,公共物品理论对政府干预边界的解释并不充分。
基于自由的信念,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关于政府干预范围的思想同样具有极为广泛的影响。他认为政府的职责范围必须具有限度,在他看来政府的主要作用应该是国家安全和市场经济制度的保护人,只是“在这些主要作用以外,政府有时可以让我们共同完成比我们各自单独地去做时具有较少困难和费用的事情”。[4]
把政府干预限制在组织社会群体共同完成一些事情,是因为弗里德曼认为,虽然政府干预不可避免,但对于自由而言却是充满了危险,因此,“在我们这样做以前,必须具备由此而造成的明确和巨大的有利之处作为条件。通过在经济和其他活动中主要地依靠自愿合作和私人企业,我们能够保证私有部门对政府部门的限制以及有效地保证言论、宗教和思想的自由”。[5]
弗里德曼强调对政府干预的限制,着重的是提供一种保护自由的实践原则。他在《自由选择,序言3》中说道:“通过严格的自愿交换机制所无法实现的目标,或者很难实现的目标,在多大程度上应通过政府这一机构来实现?我们提出的原则,并非是要划一条明确的界限来标明这一程度。凡事要具体分析。每每提出一项政府干预计划,我们应该列表陈其利弊,之后进行比较权衡。”[6]因此,弗里德曼的理论,与其说是经济学研究,不如说是伦理原则的推广,他并未对政府干预的边界得出经济学意义上的成果。
概括地说,包括公共物品理论和弗里德曼理论在内的以往的研究,对政府干预经济的边界考察的共同点在于,其一,这些理论都是力图从政府干预经济的外部寻求其范围或边界,这些探讨是徒劳的,因为,影响政府干预行为是否有效的外部因素是一个无限序列,停留在外部现象的研究,不是只能得到一些经验归纳的结果,就是只能从研究者的某种自有观念或标准出发对现实进行强制疏理,其研究成果必然缺乏对现实的解释能力;其二,这些研究的目的都是力图对政府干预的决策提供理论上的指导,但从人类经济社会的演变历史就可以得知,企图让现实服从于某种理论只是一种幻想,这种幻想只能导致理论与现实的更加脱离。好的经济学理论只能解释现实,只有坏的经济学理论才企图改变现实。
二、政府干预经济的合理性
存在即合理,这一哲理同样适用于集合的政府干预经济现象。如果承认政府干预经济现象是一种长期存在,那么,其合理性就是在于它是一种当社会群体间发生合作障碍时的替代性品。因此,政府干预存在的合理范围也就是发生群体合作障碍的资源配置场合。
任何的社会经济资源配置都实现于社会群体的合作,而群体合作的基本方式是交易,这是由人类历史演变,经筛选而来的结果。
对于交易与合作之间的依存,以往的经济学家早有认知。亚当·斯密(Adam.Smith)认为,社会群体之所以选择分工并以此实现合作,乃是诱至于交易。而对于交易的生成,他将之归结为人类本身的,有别于其它动物的天性。他指出:“引出上述许多利益的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尽管人类智慧预见到分工会产生普遍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富裕。它是不以这广大效用为目标的一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渐造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7]
弗里德曼在其《自由选择:个人声明》一书中以铅笔生产为例,说明了交易与合作的一致:“成千上万参与制造铅笔的人,没有一个是因为自己需要铅笔去干那一行的。他们中间有的人从未见过铅笔,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每一个人都把他的工作看作是取得他所需要的货物和劳务的方法——而这些货物和劳务则是我们为了得到我们所要的铅笔而生产的。”[8]
但是,交易的适用是有条件的,比如财产权力的界定的不清晰、工程技术水平低下、分工的程度不够都会导致交易不能生成。因此,在一些资源配置场合,社会群体将面临需要合作,但却缺乏交易条件,因而无法通过交易进行合作的困境。
在社会各群体需要,但又不能经由交易进行合作的资源配置场合,各群体就必然会寻求另一种替代交易的合作方式,这就是由一个代表各群体利益的机构出面,联结各群体以共同承担所费成本的方式来进行合作,从而实现公共利益。对此,亚当·斯密指出,他那个时代君主和国家的职能包括:“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这些公共机关和大工程之所以要由君主和国家来建立和维持,一方面是由于它们“对于一个大社会当然是有很大利益的”,但另一方面,“就其性质来说,设由个人或少数人办理,那所得利润决不能补偿其所费。”[9]因此不能经由交易而进行合作。这种由一个代表各群体利益个人或机构出面,联结各群体以共同承担所费成本的方式来进行合作,其实质是对交易合作的替代。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这种个人或机构取得了政府的形式,成了公权力的拥有人,组织社会群体替代交易进行合作的职能依旧保存,只是在国家和政府的公权力运用中,组织群体进行合作的目的日益模糊,政府干预经济所具有的替代合作性质日益被公权力多用途运用掩盖了。
任何群体合作都是依规则而进行的。虽然交易与政府经济干预都可以达成社会群体之间的合作,但两者实行的却是不同的合作规则。交易所以能实现群体间合作,在于交易依据的是成本和收益对称的规则,即,一项交易之所以能够达成,在于交易各方都实现了成本与收益的对称,相反,如果有交易意愿的各方不能从一项交易中实现成本与收益的对称,则该交易将不能实现,因此,也就不能实现群体间的合作。
与交易所遵循的规则不同,政府干预所以能达成群体间的合作是由于遵循了均平规则。所谓均平规则,就是社会各群体平均分担成本和平均分享收益。其具体实行,表现为国家和政府向各群体征收税费,并以各种形式保障群体共同享受。均平规则所以能被遵循,在于它的原则仍然是各群体成本和收益对称,只不过,它实现的不再是各群体自身的成本与收益的对称,而是所涉群体的总成本与总收益的对称,以及各群体平均成本和平均收益的对称。
由此可以得知,不论是群体间的交易还是政府经济干预,其存在的合理性其实是共同的,即,都是源之于人类资源配置中的合作需要,所不同的在于,经交易进行合作是人类资源配置的基本形式,而政府经济干预则是对交易合作的一种替代。正是政府干预所具有的替代合作的性质,决定了政府干预的适用范围,即,它只能够存在于群体需要合作,但交易条件缺失的资源配置场合。
三、政府干预经济边界的确定
替代合作的性质使政府干预经济存在的合理范围已定,即,在群体需要合作但缺乏交易条件的资源配置场合,政府干预经济是必要的。但在现实中,各种政府干预经济的决策是不可能主动约束于此范围内的。在各种时期,各种国家和政府的干预经济决策实际上是盲目的,这种盲目无理性并不意味着这些决策缺乏尽可能理性的意愿,而是出之于决策者认知能力的局限,因此,任何的政府干预经济总是有理由但也总是盲目的。同样,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决策给出所谓理论上的指导使其合乎理性,只是一种幻觉,这种幻觉同样源之于人类的无知和自大。
政府的干预经济决策的盲目性,使其实践本质上只是试错而不是其它。盲目的政府经济干预,既可能进入需要替代合作的场合,也可能进入存在着交易合作,不需要替代合作的场合。那么,在现实中,合适的政府干预经济行为是如何从盲目的大量的政府干预行为中筛选而出的呢?这种筛选,既不是来自于某种理论指导,也不是来自于决策者的鉴别能力,而是来自于政府干预经济行为所依存的合作规则。
如前所述,政府经济干预的合理性仅在于它能够替代交易实现群体的合作,能否实现群体的合作便是一项政府经济干预是否合理的标准,因此,如果一项政府干预经济实施后导致的群体合作的成本是更高的,以致发生合作困难,那么该项政府干预经济行为就将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从而被淘汰。从个别的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看,影响群体合作成本以及导致合作困难的因素众多,但就集合的政府干预经济来看,共同的因素只有一个,即均平规则的运行。
均平规则的运行对实际上是盲目的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筛选,是通过两类场合对群体合作的成本的影响实现的。
在交易合作缺失的场合,即替代合作是有必要的场合,由于均平规则无可替代,社会各群体又需要实现合作,因此,均平规则被社会各群体接受,并共同遵循这一规则实现合作,又由于均平规则是能够实现群体合作的唯一规则,因此,均平规则运行对群体合作成本的影响也是唯一的,也即,只要群体合作得到了实现,其合作成本也是唯一的。合作规则的唯一导致合作成本唯一,其经济意义在于该合作的机会成本趋于零,因此该合作是经济的。所以,在这一类场合,由于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实现了群体的合作,实现了一项资源配置,就表明均平规则是适用的,合作成本也是经济的,该项政府干预行为就将持续进行。
在另一类场合,即政府经济干预进入了存在交易合作的场合。这时将形成合作规则拥挤问题,即,交易合作规则与均平规则在同一场合并存。合作规则拥挤将导致群体的合作不经济。其一,规则拥挤导致交易合作残缺,形成无效或低效率合作。在交易规则有效情况下,交易是自主进行的,交易什么,和谁交易,交易多少由交易各方自行决定。一个交易的实现或者不实现都具有其经济意义。实现了的交易表明该交易实现了各方的收益与成本的对称预期,从社会角度看,该交易也实现了一项有效的资源配置;而不能实现的交易则表明交易各方的收益与成本不对称,其经济含义实际上就是群体通过交易规则筛除了一项不经济的资源配置。但是,政府经济干预的进入使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政府行政或其它手段的强制干预,会导致一些不能实现的交易得以实现。其后果就是一项无效的资源配置不能通过失败交易筛除,反而变成了现实,同时,又由于交易机会挤占,可能导致合适的交易得不到实现。资源的误配导致了社会以及所有相关群体所承担的成本上升,也就是合作成本更高了。
其二,合作规则拥挤增加了社会群体合作的总费用。一项资源配置只是群体合作的结果,合作需要费用。遵循交易规则合作,所付合作费用即是交易费用。[10]当政府干预进入存在交易合作的场合后,社会除了为该场合仍在进行的交易及其规则付出费用之外,还必须付出均平规则运行必须的费用,包括资源动员,计划设定、组织实施和过程监督等费用。因此,在合作规则拥挤下,不仅不会出现所谓的交易费用节约,反而因合作规则拥挤,增加了社会为此资源配置事件所进行的合作的总费用。
其三,合作规则拥挤增加了群体搜寻和适应合作规则的费用。在仅有交易规则时,合作通过交易进行,群体并不用为搜寻另外适用的合作规则付出额外费用。但是,由于政府干预的进入,各种行政手段的推行,优惠政策的实施,使原有的交易规则在一些场合不再适用。与此事件相关的群体为了获利,就必须搜寻适用规则。在这些场合,针对行政法规的寻租,针对优惠政策而进行的投机,针对相关项目负责人的行贿都属于规则搜寻,其所付出就成为规则搜寻费用。较之交易规则单一实行时,群体所承担的合作成本都上升了。
其四,合作规则拥挤形成规则失效,导致社会群体的不合作。政府干预替代合作的均平规则与自主选择的交易规则,都以能够实现群体收益和成本的对称得以存在。但在规则拥挤状态下,这两种规则却会因对方的存在而导致自身的失效,以致双双失效。例如,有些群体可能因政府干预的政策优惠、行业或企业保护措施而得以维持了生存,实现了繁荣,但是,这与交易规则相违,这些群体往往就获得了交易规则下不可能获得的收益和规避了必须承担的成本和风险;另一种情况是,有些群体为了通过交易获取收益,付出了规则搜寻费用,但是,这与均平规则相违,这些群体不仅承担了比正常交易更多的费用和风险,而且还为均平规则付出了税费,显失平等。不论是均平规则还是交易规则的失效,其后果都将导致群体的收益与成本对称预期不能实现。在收益与成本对称预期不能实现时,群体间趋向于不合作,其通常表现为社会抱怨不公平的情绪上升,并会诱发类似美国2011年占领华尔街式的社会群体骚动。
至此可知,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尽管是盲目的,但在合作规则运行中,各种政府干预行为在现实中将被筛选。需要替代交易合作的场合形成政府干预的边界,而当政府干预进入不需要替代合作的场合,合作规则的拥挤将导致群体合作成本增加,最终,这种合作成本的增加会导致群体的不合作,政府干预经济行为将归于失败,从而不得不被淘汰。
结语
政府干预边界的确定,至少在认识上存在着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可以了解到任一项政府干预决策的合理与否,并不是通过理论来划分的,对其所进行的筛选和淘汰将由经济运行现实来进行。因此,从某种理论出发并以此支持更广泛的政府经济干预,并不可能得到的预想的结果;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这一边界的存在,可以了解到,作为集合的政府干预经济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既不是所谓市场失灵的需要,也不是某种理论支持的结果,而是政府干预固有的约束机制使其保持在了边界之内,使其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始终具有其合理性。
参考文献:
[1]曼昆.经济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詹姆斯·M.布坎南 .公共物品的需求与供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3]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
[4][5]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6]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选择[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7][8][9]亚当·斯密.国富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10]罗纳德·科斯.企业的性质[A].温特.企业的性质[C].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