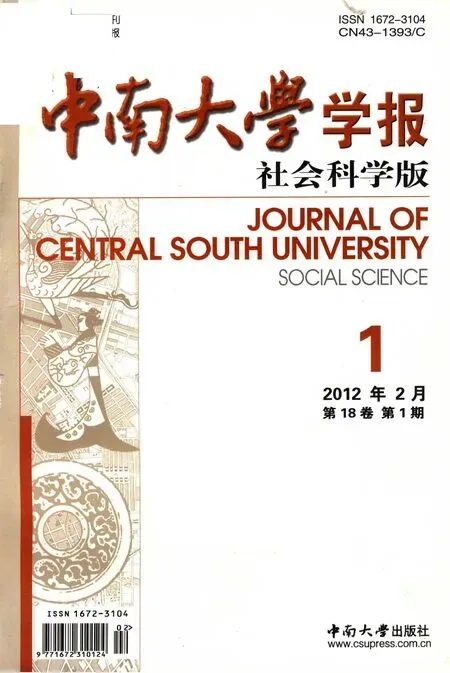宋太宗诏修《太平广记》主旨新探
2012-01-21袁文春
袁文春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东 广州,510006)
宋太宗诏集宋初文化精锐力量修纂《太平广记》(下文简称《广记》),为后世提供一部“稗说之渊海”。对于太宗诏修《广记》的意图,后人说法不一,其中一种较有影响的观点认为是为了消弥五代士怨,现代一些学者则提出娱乐消闲说,认为太宗诏修《广记》乃出于对小说娱乐性的偏爱。两种观点都具有合乎情理的证据,但如果从宋初的文化语境中去解读太宗诏编《广记》的意图,则不但可将两者整合起来,还可能有新的发现。
一、诏修目的的“消弥士怨说”和“娱乐消闲说”
认为太宗诏编《广记》出于消弥五代士怨目的的说法最早见于南宋王明清的《挥麈后录》,其卷一云:“太平兴国中,诸降王死,其旧臣或宣怨言,太宗尽收用之,置之馆阁,使修群书,如《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之类,广其卷帙,厚其廪禄,赡给以役其心,多卒老于文字之间云。”[1](53)这一说法对后世影响极大,元代的刘埙,明代的谈恺、胡应麟、陆深,直至近代鲁迅、胡道静等人都持相似的看法。但它也不是无懈可击的,南宋李心传《旧闻证误》卷一引述朱希真的话(即王明清之言)后,辩驳道:“按《会要》,太平兴国二年,命学士李明远、扈日用偕诸儒修《太平御览》一千卷、《广记》五百卷。明年,《广记》成。八年,《御览》成。九年,又命三公及诸儒修《文苑英华》一千卷,雍熙三年成。与修者乃李文恭穆、杨文安徽之、杨枢副砺、贾参政黄中、李参政至、吕文穆蒙正、宋文安白、赵舍人邻几,皆名臣也。杨文安虽贯浦城,然耻事伪廷,举后周进士第。江南旧臣之与选者,特汤光禄、张师黯、徐鼎臣、杜文周、吴正仪等数人。其后,汤、徐并直学士院,张参知政事,杜官至龙图阁直学士,吴知制诰,皆一时文人。此谓‘多老于文字之间’者,误也。当修《御览》、《广记》时,李重光尚亡恙,今谓因‘降王死而出怨言’,又误矣。《册府元龟》乃景德二年王文穆、杨文公奉诏修,朱说甚误。”[2](9)李心传的辨驳可谓有理有据,雄辩有力,可他只指出王明清说法之误,却没有另立新说。由于没有更好的解释,王明清的观点还是被后世许多学者所认同。鲁迅先生就对之甚为肯定:“宋既平一宇内,收诸国图籍,而降王臣佐多海内名士,或宣怨言,遂尽招之馆阁,厚其廪饩,使修书,成《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各一千卷;又以野史小说诸家成书五百卷,目录十卷,是为《太平广记》。”[3](63)另《华盖集续编》亦言:“此在政府的目的,不过利用这事业,收养名人,以图减其对于政治上之反动而已。”[4](230)
上述说法在鲁迅之后仍有响应者,不过,现代学者似乎更倾向从文学立场上推测太宗诏编《广记》的意图,将太宗对娱乐性的追求当作首要的考察因素。如聂崇岐《太平御览引得序》云:“愚意以为太宗之敕修群书,不过为点缀升平欲获右文令主之名,其用南唐贵遗臣,亦仅以其文学优赡,初不必有若何深意。”[5]这种观点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同,如郭伯恭、程毅中、李剑国、陈文新诸先生皆不同程度上认同聂氏说法。这种观点直接着眼于太宗本人意识,自然是合乎情理的,编纂《广记》本是由太宗下诏启动的行为,它自然是太宗意志的体现。太宗本有尚文之心,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云:“太宗当天下无事,留意文艺,而琴棋亦皆造极品。”[6](117)太宗将小说作为消闲之资,应是情理中的事,同时也符合当时的文化消费实际,欧阳修《归田录》卷二记载钱惟演的名言:“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因此以小说娱乐是当时较为普遍的文化消闲方式。但太宗毕竟是一国之主,如果将他置于宋初特定历史情境中,恐怕就不能完全顺着太宗个人情趣去理解这种既费时又费力的庞大文化工程了,太宗作为建国初期的国君,对任何举措更应该首先从治道角度去权衡考虑,更何况编纂《广记》是费力而耗时的重大文化工程。
宋初太祖、太宗都极重视前代图籍的保护与利用,太宗曾多次表达从书籍文献中求治道的意愿,“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苟无书籍,何以取法?”[7](71)以太宗身份来讲,读书自然要立足于用世与治道,他曾对近臣道:“朕每退朝,不废观书,意欲酌前代成败而行之,以尽损益也。”[7](528)太宗所诏编书籍,皆出于治世宗旨,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下有云:“太宗诏诸儒编故事一千卷,曰《太平总类》;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华》;小说五百卷,曰《太平广记》;医方一千卷,曰《神医普救》。《总类》成,帝日览三卷,一年而读周,赐名曰《太平御览》。”《太平御览》《神医普救》的用世宗旨无需多言,即使是作为文章总集《文苑英华》也出于“以文化成天下”(周必大《文苑英华》序)的治道宗旨,《太平广记》与《太平御览》等辅道之书同时编纂,其应世目的是不言而喻的,《玉海》卷五四引《会要》:“先是帝阅类书,门目纷杂,遂诏修此书。”以修《广记》等书来弥合异代士怨,消耗异代文化力量确实可以当作一种统治策略,但它肯定不是最好的策略。因为宋代初期正施行“文德致治”统治方略,是最急需文化力量的时候。太宗作为宋代极为英明的统治者,不可能随意地消耗当时最为精锐的文化力量,因此,太宗下诏编纂《广记》的根本宗旨,应在弥怨与消闲的目的之外。
二、诏修的主要目的应当是“神道设教”
(一)《广记》的志怪倾向与“神道设教”
《广记》的性质为小说类书,故清代纪昀称之为“小说之渊海”,小说本为不入流“小道”,班固谓小说“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言小说虽小道可观,然“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太宗乃“笃好儒学”的一代明主,《广记》编纂者也是当时精通儒学的贤者,这与孔子之“君子弗为”相违背。所以,《广记》中可能含有比“小道”更重要的因素。追寻这些因素,可从分析《广记》的取材倾向入手。
《广记》取材倾向在其类目设置上有明显体现。《广记》凡五百卷,分五十二大类(不计附录类目),一百五十多小类。大类中卷数最多的是神仙类,共55卷,下面依次是鬼类40卷,报应类33卷,神类25卷,女仙类15卷,定数类15卷,此外再加上异僧12卷,再生12卷,妖怪9卷,龙8卷,精怪6卷,幻术4卷,妖妄3卷,释证3卷,夜叉2卷,悟前生2卷,神魂1卷,灵异1卷,以及许多动植物小类中涉及的志怪内容,则志怪内容占全书大半以上。故郑樵《通志·校雠略·泛释无义论》谓:“且《太平广记》者,乃《太平御览》别出《广记》一书,专记异事。”[8](1818)《四库提要》也认为《广记》乃“多谈神怪”之书,“古来轶闻琐事、僻笈遗文咸在焉”。[9](3642)小说本街谈巷语之书,搜奇猎异是其应有之义,但问题是,《广记》成书并非全取街谈巷语,据书中所提供的引用书目可知其取材极为广泛,有的内容出自高文大册的正史著作,如《史记》《汉书》《后汉书》《魏书》《吴书》《吴志》《三国志》《晋书》《宋书》《唐史》《晋史》《国语》《南史》《北史》等等,所以说,《广记》内容的志怪倾向与编纂者的选材意图有关,而编纂者的意图也正是太宗的意图。从书中类目分析可知,《广记》内容的志怪倾向中隐含着宗教意图,这一方面曾礼军在其博士论文《太平广记研究》中分析得很透彻,他认为《广记》的92大类,据类目编排的先后顺序可以分为道教类、佛教类、世俗传统类及物类四个主要板块,其中前三板块类目依道−释−儒的顺序构成了三教合一的板块结构。而最后的物类板块从其精怪文化的民间信仰属性整合到世俗传统类目板块。另外他还从类目的卷数所占的比重方面详细分析《广记》的宗教文化特征:“道教类目只有五个,但卷数达86卷,占全书五百卷的17.2%。佛教类目为三个,卷数为48卷,占全书的9.6%。两者共有134卷,占全书的26.8%。而《艺文类聚》中的佛道宗教类目只有4卷,仅占全书一百卷的 4.0%;《初学记》中佛道宗教类目只有一卷,也仅占全书三十卷的3.3%。此外,世俗传统类目中,符命信仰和民间信仰是传统宗教文化内容,也属于宗教类目。其中符命信仰次板块类目有四个,卷数为29卷,占全书的5.8%;民间信仰次板块类目有十五个,卷数为117卷,占全书的23.4%。这两者加起来占全书的29.2%,占258卷世俗传统类目的56.6%。全书所有宗教类目的卷数加起来共有280卷,占全书的56%。再加上物类的精怪信仰,其比例可达到百分六七十。因此从宗教类目卷数所占的比例来看,也体现《广记》类目编排的宗教性特征。”[10](48)曾氏的统计是客观的,可惜他仅关注《广记》内容的“鲜明的宗教性特征”,并没有进一步探寻宗教性特征后面统治者诏编此书的深层意图。
如果跳出《广记》成书视野,联系宋初统治者“文德致治”的统治方略以及他们对释道积极扶持的态度来思考,其“神道设教”意图则更明显。还在武力征讨周边政权之时,宋太祖就为平定天下的文治方略作准备了,“乾德元年平荆南,尽收其图书以实三馆。三年平蜀,遣右拾遗孙逢吉往收其图籍,凡得书万三千卷。四年下诏募亡书,《三礼》涉弼、《三传》彭干、学究朱载等皆诣阙献书,合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开宝八年冬平江南,明年春遣太子洗马吕龟祥就金陵籍其图书,得二万余卷,悉送史馆。自是群书渐备”。[11](251)宋太祖执政16年内,聚书多达46000多卷,与唐代开成年间的秘阁藏书量相差10000多卷,宋太祖极具远见的文化保护措施,给后来太宗“文德致治”统治方略的实施铺设了坚实基础。整理前代文献典籍,正是太宗的统治方略之一,太宗对臣下言:“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苟无书籍,何以取法?”[7](571)宋初统治者认为德治之道存于文献之中,故求天下之治必先求治道于历代图籍,宋太宗诏曰:“国家勤古道,启迪化源,国典朝章,咸从振举,遗编坠简,宜在询求,致治之先、无以加此。”因此,为了在前代所遗文献书籍中寻求治道,太宗才诏令馆阁诸修撰《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巨书,《文苑英华》性质为文学总集,其修撰宗旨也强调“以文化天下”,而前两书则是为实用而编的类书,求治用之旨就更为明显了。两大类书修成后,太宗对之用功甚勤,据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下记载,《太平御览》原名《太平总类》,后因帝日览其书而改名:“《总类》成,帝日览三卷,一年而读周,赐名曰《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与《太平御览》由同一批儒者负责编纂,如果说前者荟萃经世之言事,那么后者作为小说类书,虽不及治世之大道,但也有益于治身理家,可为辅教之书。然《广记》内容以儒家所敬而远之的志怪为主,所以它不是一般的辅教,而是“神道设教”。这种意图在宋初统治者对佛道两大宗教的态度上可以得到明确印证。宋太祖即位之后便下令恢复被周世宗废除的佛教,下诏:“诸路寺院,经显德二年当废未毁者,听存;其已毁寺,所有佛像许移置存留。”[12](394)乾德四年,“沙门行勤一百五十七人应诏”“往西竺求法”,太祖“赐诏书谕令遣人前导,仍各赐装钱三万,行装钱三十贯文”。[12](395)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官派僧团。对于道教,宋太祖则是先选拔道官,后又禁私度道冠,并试验道士学业。太宗对佛教也是积极扶持。太平兴国元年,“诏普度天下童子,凡十七万人”。太平兴国三年三月,“开宝寺沙门继从等,自西天还献梵经佛舍利塔菩提树叶孔雀尾拂,并赐紫方袍”。[12](396)太宗在政治上崇尚黄老之道,谢灏《混元圣纪》卷八载,太宗尝对侍臣说:“清净致治,黄老之深旨也,朕当力行之。”[12](397)他多次召见道徒,大力兴建道观。此外宋初统治者还热心地替佛道两教整理、编刻典籍。开宝四年(971年),太祖命近臣负责《大藏经》雕版,至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共雕板13万块,收录大小乘佛典及圣贤集传共1076部、5048卷、480函。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刊行的佛教总集。太宗则于太平兴国年间设译经院,“置译经院于太平兴国寺,延梵僧翻译新经”,[13](325)大力培养佛经翻译人才。宋初两位统治者若出于宗教的热情,上述言行尚可理解,可事实上他们并不信佛信道,太宗说:“日行好事,利益于人,便是修行之道。假如饭一僧、诵一经,人何功德?”雍熙二年六月太宗诏建道场为百姓消灾,他说:“朕恐百姓或有灾患,故令设此,未必便能获佑,且表朕勤祷之意云。”[7]P596可见宗教在他心目中不过是”神道设教”的工具。如果佛道行为越出“神道设教”所允许的范围,则会遭到禁废,如太祖在开宝八年(975年),诏令禁止举行灌顶道场、水陆斋会及夜集士女等佛事活动,因为其“深为亵黩,无益修持”。又据《宋会要辑稿·道释》载,淳化五年(994年),太宗听说《大乘秘藏经》译文多处“文义乖戾”,即下诏勒令将其当众烧毁。宋代太宗曾明确其“神道设教”思想,《宋朝事实》卷三载太宗读《老子》,对侍臣曰:“伯阳五千言,读之甚有益,治身治国(之道)并在其内。至云‘善者吾亦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此方善恶无不包容。治身治国者其术如是,若每事不能容纳,则何以治天下哉!”[13](37)宋初统治者正是出于“神道设教”需要,诏令编集历代志怪故事,因而他们对道佛两教的偏爱与编纂者对《广记》中佛道志怪故事的偏重有着相当一致的对应关系。现在的问题是,宋初统治者为何热衷于选择“神道设教”的统治策略呢?在笔者看来,恐怕与赵宋王朝合法性论证意图相关。统治者对“神道设教”意图尚能坦言相告,但对于“神道”背后的政治用意,则有难言之隐。
(二)《广记》成书的特定语境:王朝合法性的神秘论证
宋初统治者热心扶持佛道,既出于统治目的,同时也为了统治地位的合法性论证。宋太祖原为后周将领,深受周世宗柴荣器重,可在世宗死后,却上演“陈桥兵变”,从世宗遗孀幼子手中谋取政权,另立新朝。因此,在儒家文化语境之下,赵宋政权的合法性方面存在难以圆说的困境。所以,宋初的统治者不得不求助于神秘文化,求助于宗教。事实上,在“陈桥兵变”前夕,神秘的谶言就为赵匡胤的背恩与背叛制造了合法性迷雾。如赵氏在后周的政治斗争中,以一块木牌上的谶语“点检作天子”,既打击了自己的政治对手张永德,同时也为自己后来上演“兵变”称帝制造了神秘的前兆。《宋史·太祖本纪》:“显德六年,世宗北征,(赵匡胤)为水陆都部署。……世宗在道,阅四方文书,得韦囊,中有木三尺余,题云‘点检作天子’,异之。时张永德为点检,世宗不豫,还京师,拜太祖检校太傅、殿前都点检,以代永德。恭帝即位,改归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周世宗为谶语所惑,去张任赵,最终令谶言变成现实,赵氏以顺从天意的名义谋取皇位,变周家天下为赵氏天下。其实宋太祖本人并不迷信,但他的新政权却极需要迷信的文化,所以他设法将自已神化起来,据《宋史·太祖本纪》记载,太祖从军前,曾经漫游无所遇,舍襄阳僧寺。有老僧善术数,顾曰:“吾厚赆汝,北往则有遇矣。”
佛道两教因此极力迎合帝王心思,为新生政权的合法性进行神秘性的论证。《佛祖统记》卷四三云:“周世宗之废佛像也——世宗自持凿破镇州大悲像胸,疽发于胸而殂。时太祖、太宗目见之。尝访神僧麻衣和上曰:‘今毁佛法,大非社稷之福。’麻衣曰:‘岂不闻三武之祸乎!’又问:‘天下何时定乎?’曰:‘赤气已兆,辰申间当有真主出兴,佛法亦大兴矣。’其后太祖受禅于庚申年正月甲辰,其应在于此也。”[12](394)类似的说法还见于《邵氏闻见录》卷七:“河南节度使李守正叛,周高祖为枢密使讨之。有麻衣道者,谓赵普曰:‘城下有三天子气,守正安得久!’未几,城破。……三天子气者,周高祖、柴世宗、本朝艺祖同在军中也。麻衣道者其异人乎?”[14](68−69)此外佛教还有“定光佛出世”之说,《曲洧旧闻》卷一云:五代割据,干戈相寻,不胜其苦。有一僧虽佯狂,而言多奇中。尝谓人曰:“汝等望太平甚切,若要太平,须待定光佛出世始得。”[15](85−86)至太祖统一天下,皆以为定光佛后身者,盖用此僧之语也。以上谶言正中宋太祖下怀,为宋太祖兵变夺权的合法性进行了神秘性的辩护。太宗则利用道教为自己在“烛影斧声”后继位进行神圣化,《宋朝事实》卷七云:“乾德中,太宗皇帝方在晋邸,颇闻灵应,乃遣近侍韲信币香烛,就宫致醮。使者斋戒,焚香告曰:‘晋王久钦灵异,敬备俸缗,增修殿宇。’仍表乞敕赐宫名。真君曰:‘吾将来运值太平君,宋朝第二主。修上清太平宫,建千二百座堂殿,俨三界中星辰,自有进日,不可容易而言,但为吾启大王言此宫观上天已定增建年月也。今犹未可。’使者归,以闻太宗,惊异而止。太祖皇帝素闻之,未甚信异,召小黄门长啸于侧,谓守真曰:‘神人之言若此乎?’守真曰:‘陛下倘谓臣妖言,乞赐案验戮臣于市,勿以斯言亵渎上圣。’须臾,真君降言曰:‘安得使小儿呼啸以鄙吾言,斯为不可。汝但说与官家,言天上宫阙已成,玉锁开,晋王有仁心。’翌日,太祖升遐,太宗嗣位。”[13](116)由此可见,佛道志怪之事对宋初统治者意义非同一般。这就难怪宋初的统治者对佛道两教持有特殊的好感。
由于佛道对宋初统治者特殊的意义,所以宋初统治者虽然以儒学为本,走崇儒之道,但仍设法在儒家“神道设教”思想笼罩下大量搜集以佛道内容为主的志怪故事。《广记》作为一部服务于统治者治世的类书,自然不可能随意为之。一般来说,以政府之力修撰大型类书,统治者都会极为关注,因为它关系到他们意志的表达,有的皇帝还会直接参与其中。如真宗诏令官员编纂《册府元龟》时,曾于“景德四年八月壬寅,车驾再幸编修之所,再阅门类。杨亿悉以条对编次,未及伦理者改正之”。[16]又如神宗时官员修《禄令》,“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以救,乃更其目曰救、令、格、式,而律恒存乎救之外”。(《宋史》卷一九九《刑法志一》)《广记》的编撰者除宋白之外,其余编者皆为异代降臣,所以太宗参与《广记》编纂事务可能性更大。据该书卷首所载《表文》,太宗曾作过编书的总体性指导:“编秩既广,观览难周,故使采摭菁英,裁成类例。”因此,太宗“神道设教”的宗旨与对佛道的特殊情感都有可能通过成书之“类例”体现在《广记》内容中。佛道志怪故事在《广记》所占的比重与所居位置,明确反映了太宗对佛道两教的好感。当然,太宗的好感是因为它们有利统治中的“神道设教”,这种用意隐含于《广记》类目卷数的设置上,《广记》“神仙”设五十五卷,“女仙”置十五卷,其实都是有特别用意的,因为“五十五”与“十五”皆出于儒家经典之首《易经》,《易·系辞传》云:“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易纬·乾凿度》云:“《易》一阴一阳,合而为十五之谓道。”这种数字的设置不会是偶然巧合,同是太宗诏修的《太平御览》一书,也分五十五部,取《易》之义,以示包罗万象,“成变化而行鬼神”。因此统治者“神道设教”的意图在卷数的设置中就有神秘的表达。
三、余论
以上论述了《广记》一书中所隐含的宋初统治者“神道设教”意图。按常理,作为“神道设教”之书,需通过印刷传播才能真正实现统治者的政治意图。可事实却相反,书虽已雕版,却仅将“墨板藏太清楼”,[17]这是否就否定了本文的观点呢?不是的。首先,本文所探讨的统治者本人的意愿,将书收板停印是由于“言者谓非后学所急”,并非太宗本人意愿,[17]此中的言者极有可能是儒者群体,否则不可能轻易阻挠帝王意愿。太宗以儒治世,故最终采纳意见,没有使书版进入印刷程序。此外,据王应麟《玉海》卷五四记载:“六年诏令镂板”以及书中的进书表所言:“六年正月奉圣旨雕印板。”(见《太平广记》卷前附刊《太平广记表》)可以推断太宗本有颁布此书之意。虽然《广记》书成而未印,可“神道设教”思想却在统治者间传播,成为他们或隐或显的统治策略。
[1][宋]王明清.挥麈录[M].北京: 中华书局,1961.
[2][宋]李心传.旧闻证误[M].北京: 北京中华书局,1981.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4]鲁迅.华盖集续编[M].鲁迅全集[M]卷三.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聂崇岐.《〈太平御览引得〉序》[C].《太平御览引得》[Z].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6][宋]叶梦得.石林燕语[M]卷八.北京: 中华书局,1984.
[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Z]卷二五.北京: 中华书局,1977.
[8][宋]郑樵.通志二十略[Z].北京: 中华书局,1995.
[9][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10]曾礼军.太平广记研究[M].上海师范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
[11][宋]程俱撰,张富祥校证.麟台故事校证[Z].北京: 中华书局,2000.
[12]佛祖统纪[M]卷四三.大正藏[Z]第 49册.日本东京大藏经刊行会,2001.
[13][宋]李攸.宋朝事实[M].北京: 中华书局,1985.
[14][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M].北京: 中华书局,1997.
[15][宋]朱弁.曲洧旧闻[M].北京: 中华书局,2002.
[16][明]李润京.册府元龟考据[M].北京: 中华书局影印,1960.
[17][宋]王应麟.玉海[Z]卷五四.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