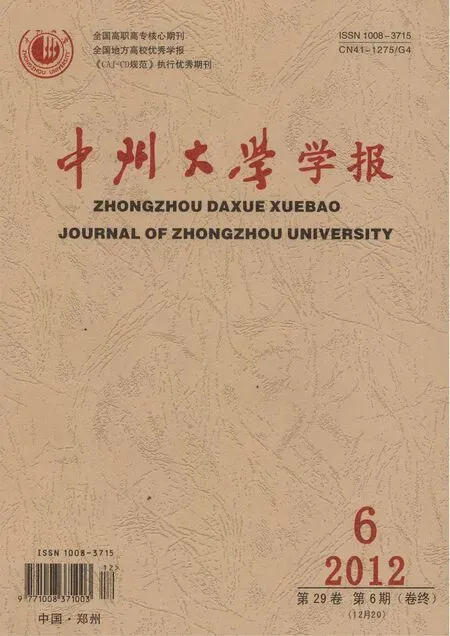地狱与天堂间的悲怆旅程
——《还乡》的存在主义解读
2012-01-21杨澜
杨 澜
(河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郑州450002)
哈代的重要作品皆为悲剧,他笔下的主人公大多不满足于现实,力图改变现实,却因为内在及外围的复杂因素被迫过着孤独、绝望的生活。从《还乡》开始,哈代小说中的田园风光被工业文明所玷污,往日的平静被喧嚣所取代。那些为个人信仰与命运抗争的人们不但得不到上天的仁慈帮助,还似乎被众神当作愚弄的棋子。作为一位怀有强烈人文关怀的现实主义作家,哈代对19世纪末的英国农村现状持深刻的批判与忧虑。哈代希望他热爱的农村恢复以往的乐园生活,又不愿看到这里与城市的差距拉大;另一方面,要想与时代同步,农村居民的素养是急待提高的,而问题的症结正在于此——大多数居民习惯于懒散麻木的生活,不愿也不能接受新的思想。而极少数头脑清醒、思维超前的人,即哈代笔下的主人公们,本应赢得尊重、取得成就,却因为言行与旁人格格不入而被众人误解、被诸神抛弃,最终被所谓的命运打败。
哈代对人生的看法与存在主义信奉的人生观基本一致,即痛苦是人生最真实、无法避免的体验,人的理想在现实面前是不堪一击的,人的力量较之荒谬的世界是微不足道的。《还乡》中的艾顿荒原虽然远离工业文明,但绝非净土或者乐土。这里的生活方式落后,居民的思想停滞,毫无信仰和理想可言。尽管固守自封,由于处于社会转型阶段中,种种强大的否定性力量给古老的荒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联断裂,呈现出疏离、异化的特点,具有典型的存在主义特征。首先体现在信仰方面:这里的大多数居民不再信奉上帝,不再定期做礼拜,对神职人员不再崇敬。信仰的丧失导致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和谐被打破,大多数居民生活在麻木不仁、随波逐流的状态中。传统的价值观念正在逝去,大多数本地居民对新的思想观念极其抵触。他们墨守陈规,麻木不仁,道德观念淡薄,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关怀也无处可寻。尽管远离尘嚣,这里并不是纯净的乐土;其贫瘠、荒凉的迹象倒是与亚当和夏娃受苦受难的失乐园极为相似。
一、荒谬与孤独
萨特认为,每个人都是孤立存在的,尽管与他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局外人”。在哈代的小说中,个体之间理解的缺乏与认识上的隔阂是普遍存在的,这正是“局外人”所面临的困境。存在主义关注的是个人和个体的问题,但并不否认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牵制、相互吸引与相互抵消的多重关系。这些关系不断交织与变幻,从而使个体也分解为多个侧面,从他人与个人的关系上折射出个体的不同侧影。这些侧影是分裂的,又同属于一个整体。由于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变得疏远,个人投射于他人身上的影像也变得支离破碎,无法还原真我,更难以拼接成一个完整的自我。而由于缺乏理解与沟通,个体根本无法期待他人帮助自我完成恢复。在这种情况下,个人遭遇了分裂与异化;自我的形象变得陌生,在他人眼中如此,在自我眼中同样如此——“局外人”的荒谬感由此诞生。“局外人”眼中的世界是荒谬的,同时也是孤独的,无所依靠的。
艾顿荒原浓缩了人的生存状态,这里乏味单调的生活一如居民们的精神世界,只有极少数人意识到生存的本质,却陷入更深层的孤独与绝望。这一点在当地居民对待尤斯塔西雅(以下简称尤)的态度上尤其明显:尤依靠外公生活,孤苦伶仃,本应得到大家的同情与关心。而她出众的外表,不凡的谈吐与孤傲的气质在众人眼中却成了异教徒般的罪状。在当地人眼中,尤目中无人、自私冷漠。试问一下,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被迫过着孤独寂寥的生活,得不到任何关爱,找不到交流对象,甚至被冠以巫婆的恶毒称呼,如何能够天真烂漫、活泼可爱?抛开尤自身的缺点不谈,艾顿荒原上的居民一开始就把她视为与自己格格不入的异类,并有意加以疏远。这些人为的行为增长了尤性格中的孤傲与冷淡。这本身就是悲剧:孤独的人渴望回归,而其身处的环境根本无法接纳她,孤独的个体因而成为“局外人”。
孤独的人更加绝望,但并未走向自暴自弃。投身爱情是她唯一的选择。选择怀尔狄夫(以下简称怀)实在是没有更佳选择之下做出的妥协:尤明知怀用情不专、资质匮乏,但他给予自己的激情似乎是茫茫黑夜中唯一的光亮。然而这一微弱的光亮也随着怀与老实传统的托马茜结婚而黯淡了。面对情人的背叛,尤做出的反应表明她远非众人口中行为放荡、没有廉耻的妖妇:尤找来怀,要求与之中断关系,这表明尤怀有强烈的自尊与道德感。爱情是她的唯一慰藉,然而爱人并非理想对象,她宁可放弃也不愿降低自己的道德标准。
从巴黎经商归来的克莱姆(以下简称克)还乡后,尤以为找到了改变命运的钥匙。而事实证明,他们的结合本身就是错误的,是荒谬的现实中另一桩荒唐的婚姻:尤渴望逃离荒原,在繁华的都市中寻找激情,体味人生;而克厌倦了都市与商业,决定在乡土中寻求安宁。二人的价值观与人生观背道而驰,却又不可避免地相遇、相爱了。婚姻本应是甜蜜爱情的硕果,却愈发明显地让二人感受到孤独与绝望。这是悲剧的,也是荒唐的。存在主义认为,世界是荒唐的,人们是麻木的,但生活本质上又是美的。尤与克结婚后,这对拥有良好教育、心智超群的青年男女不但不能享受青春、实现抱负,反而被困在落后贫瘠的地域,以砍柴为生。这是现代人遭遇的异化——身与心的异化,个体之间的相互异化,这是现代人荒谬的生存状态中最普遍的境况。
在艾顿荒原上,人不过是“放在乌木桌子上的两颗珠子”。人的渺小丝毫不会因为个人的意志和理想而改变。无论遭受痛苦还是安于现状,人似乎都无法改变外界环境,更不用说自己的命运了,因为命运被看不见的外部力量控制着。安于平淡的克丝毫没有觉得砍柴与自己崇高的理想相悖,而在来探望他的母亲看来,他就像一条不起眼的小毛虫。同样,遭到丈夫抛弃的尤也像一个不得不依靠荒原的小生物。当克得知母亲去世的真相而痛苦不堪时,世界的荒诞并未因此改变,人的痛苦与挣扎显得一文不值。
二、自由意志与自主选择
如何在充斥着荒诞与疏离的世界中认识自我、寻找自我并实现自我,是存在主义作品的重要主题。从《还乡》开始,到后来的《苔丝》、《卡斯特桥市长》及《无名的裘德》,都讲述了怎样在面临剧烈变动的社会中保存真我、拒绝异化、实现个人理想。存在主义认为,外界力量是强大并荒诞的,个体往往得不到正确的引导,无法正确认识自我;而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个体饱受种种异化力量的无情迫害从而陷入孤独和绝望的深渊;遭遇自我分裂、自我异化的个体很难实现自我,而以悲剧收场。个体与他人的对立永远存在:当个人被迫接受他人的标准,用他人的眼光评判自己时,他人便成了镜子,自己则被异化成为了镜子中的影像,是失真的,有悖于自我的。为了摆脱被异化的状态,个人必须做出主观判断,运用自由意志,进行自主选择。
克因为向往内心的平静,自主放弃了城市的繁华,当他满怀憧憬地回乡后,却遭遇了一连串的打击:首先,回乡办学的初衷受到质疑,众人的赞赏与羡慕很快被不解与疑惑所取代,甚至得不到母亲的支持。在乡民的眼中,巴黎珠宝商人远比乡村教师更成功,更值得追求。克本希望通过教育提升和感化同乡,无奈个体的力量太过单薄,不足以对抗强大的对手。乡民们看重物质财富和世俗地位,而克偏偏反其道而行之,选择了特立独行的孤独生活。他的特立独行是自主选择的结果,但同时也将自己边缘化,成了孤独的“局外人”。一开始,要忍受众人的非议与母亲的反对,对克来说并非难事,因为他收获了尤的爱情。而当二人的爱情之花迅速凋谢,加之克眼疾的恶化,克陷入了事业与婚姻的双重低谷。当生活的重创让克不得不放弃初衷,面对众人的不解与妻子的不满,克仍然拒绝向生活低头,不承认自己是失败者,这同样是克的自主选择。只有心怀坚定的信仰,才可以坦然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异;然而命运并没有因此而向克展露笑脸,他再次遭受了痛失母亲与妻子的双重打击。即便如此,克仍然选择坦然面对一切,既没有加入酗酒作乐、麻木不仁的乡民的队伍,也没有怨天尤人,一蹶不振。逆境是弱者的沼泽地,是强者的训练营;绝望使意志薄弱的人丧失斗志,使意志坚定的人更加渴望光明。克莱姆就是这样一位意志坚定的强者、目光远大的智者。他以敏锐的眼光审视自我与他人,不仅严于自律,更希望帮助他人摆脱盲目的生存状态。崇高的理想助他超越个人的得失甚至生死,从而实现人性的升华。亲人的离世和自身的眼疾使他成了一位弥尔顿式的斗士,一位存在主义式的英雄。
三、死亡与自我放逐
叔本华指出,生命意志是一种驱动个体生命活动的原始力量,因此它不会因个别有机体生命停止而化为乌有。故而,死既不是生的对立面,也不是一切的终点——死亡,尤其是自主选择死亡与生命意志并不抵触;相反地,它恰恰印证了强烈的生命意志。自主选择死亡意味着超越普通人对死亡的恐惧:普通人之所以害怕死亡,是因为将死亡等同于个体的消亡。而一旦超越个人的小世界之界限,将个体理解为永恒现象的若干客体之一,死亡也就不那么可怕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哈代小说中的人物主动迎接死亡,就显得格外勇敢而超脱。
另外,当欲望被压制,理想被践踏,美好被粉碎,死亡便成了最终的反抗。加缪认为,如果不能按照自身的意愿去生,那至少也得自由选择死亡吧。也就是说,生存既然是无意义的,死亡也许可以为无意义的生存画上浓墨重彩的句号。存在主义认为,主动地选择死亡也是自主选择最强烈的体现,是对生之无意义的终极反抗。哈代笔下的主人公同样可以从容面对死亡,选择死亡,超越死亡,他们将赴死变成了主动性的创造行为,从而赋予虚无以意义。在哈代看来,主动地选择死亡是另一种斗争:与其在荒诞的现实中苟延残喘,不如用最决裂的态度求得解脱。苔丝面对刽子手时从容镇定,裘德抱病淋雨只求一死。这些普通人不普通的行为都可以用尤丝塔西亚绝望的呐喊来解释:“如果上天对她的这种讽刺再进一步发展下去的话,只有去死才是唯一的解脱。”同克拉姆一样,尤不是懦夫:她敢于通过行动追求真我、改变命运,却囿于种种因素——恶劣的环境、疏远的亲情、虚弱的个性等。正因为尤不同于呆板保守的托马茜,她宁愿失去一切也不愿做命运的奴隶。对于用尽所有气力仍然被迫回到起点的尤,死亡更符合她骄傲的性格。哈代的悲剧主人公大多难逃死亡的悲惨结局:苔丝、亨查德、裘德皆是如此。然而同其他苟且偷生、混沌度日的人物相比,这些坦然赴死的主角更显得勇敢而悲壮。如同被警告会受罚却仍然为爱吃下禁果的亚当,他们或为了爱情,或为了胸中抱负而挑战命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豪情,已经超越了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境界。
四、结论
哈代作品中的主人公多数生活在疏离与异化的环境中,他们生活的环境与存在主义作品所描述的极为相似:怀疑与麻木代替了信仰与清醒,个人与集体、个人与他人的不和谐导致自我的孤独异化感日益严重。《还乡》作为哈代的代表性作品,体现了强烈的存在主义特征。《还乡》中的两位主人公都展现了对多诘的命运无所畏惧、对世俗眼光毫不顾忌的存在主义英雄式的特点。他们不满足于慵怠、停滞的生活状态,渴望实现自我,追求圆满的生活,却遭受一系列的打击,而以失败和死亡告终。他们的人性在痛苦的体验中得以升华,个人的力量在与荒谬直面对抗的过程中被提升。他们就像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虽然每天都要忍受巨石复落、再重新推之的循环往返,却仍然乐此不疲,直至耗尽精力与生命。尽管不是功名显赫的大人物,这些平凡的英雄在对抗世界的荒谬中实现了自身的价值,也体现了哈代本人对英国社会存在主义式的深刻反思。
[1]段德智.西方死亡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加缪.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M].杜小真,顾嘉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
[3]萨特.存在与虚无[M].陈宣良,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4]托马斯·哈代.还乡[M].孙予,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5]杨澜.回归与走失:《还乡》中主人公命运分析[J].中州大学学报,2008,25(1):45 -47.
[6]吴笛.哈代新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