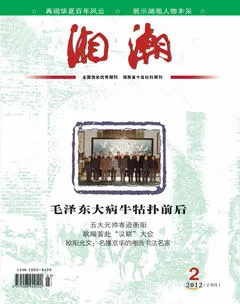惠特拉姆的中国情怀
2012-01-01
湘潮 2012年2期
2011年4月,澳大利亚总理朱莉娅·吉拉德应邀访华。她在为访华做准备的时候,看到一张澳工党元老惠特拉姆1973年访华时和邓小平的合影照片。这张照片引起了她的兴趣。
这张照片的故事,发生在38年前。1973年,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访华。这次历史性的访问,以“破冰之旅”的美名,记载在中澳关系的史册上。
率工党代表团访华
惠特拉姆访华之路,并不平坦。1945年,惠特拉姆加入澳工党,1952年首次当选联邦议会议员,1960~1967年担任工党副领袖,而后直至1977年担任工党领袖,创立了工党领袖在位的最长任期历史。作为年轻的澳大利亚工党议员,20世纪50年代就在议会上发表演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但是,澳大利亚国内保守派势力竭力阻挠承认新中国,顽固地与台湾保持着“外交关系”。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澳工党已在野23年,期间,中国与西方一些主要国家(如英、法)先后建立外交关系。特别是和加拿大建交之后,中加贸易额(我国主要进口加拿大小麦)迅速增长,同时停止了从澳进口小麦。1971年4月,作为工党领袖的惠特拉姆,在电台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确,在过去的这么多年中,我们装作中国不存在,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加拿大、意大利都承认了中国,美国乒乓球队也进入了中国。我们还需要犹豫吗?” 他打电话给一位认识韩叙(曾任外交部礼宾司长、驻美联络处主任等职)的澳大利亚新闻界人士罗斯·特里尔,请他牵线搭桥。他说,我要去中国访问,你帮忙想想办法。特里尔通过韩叙转达了惠特拉姆的愿望,周恩来得知后即向毛泽东报告。当得到中国外交学会发出的访华邀请时,惠特拉姆激动地抓起电话告诉特里尔:“为胜利欢呼吧!我们得到邀请了!”
在惠特拉姆率工党代表团访华期间,姬鹏飞代理外长和白相国经贸部长同澳工党代表团进行了会谈。周恩来长时间地接见代表团时,惠特拉姆向周恩来表示,次年澳举行大选,如工党当选,必同中国建交。周恩来说:“中国有句古话:言必行,行必果。用西方的话说就是,一个政治家,一个政党,实现他的政治声明是最得人心,也是最有价值的,希望你能将你的话变成实际行动。”话别时,周恩来还亲切地鼓励他说:“你还很年轻嘛。”惠特拉姆说:“我不年轻了,再过4天我过生日的时候,55岁了。”惠特拉姆一行访问上海期间,也就是4天之后,在上海市的欢迎宴会上,服务生奉上周恩来送的生日蛋糕,摆在惠特拉姆面前。他惊喜得说不出话来,宴会一结束,他立即回到房间,拿起电话对随访的澳大利亚记者说:“我在上海度过了我一生中最为快乐的生日!”10多年之后,惠特拉姆在撰写他的回忆录时,饱含深情地讲述了他同周恩来在北京初次会见的情形,特别提到了一个日理万机的大国总理竟然还能留意一个初次见面的外国人生日的事。惠特拉姆访华结束返回澳大利亚后,于7月30日向周恩来发了感谢电,称:“我将永远记住我们在北京难忘的会见,也将记得你所说的‘最微小的种子也可以产生伟大事物’的名言。我深信,你的伟大气魄将不仅对世界人民实现和平与友谊的希望做出巨大的贡献,而且还有助于中国重新获得在国际大家庭中的应有地位。”
惠特拉姆访华取得成功,在澳大利亚引起轰动,却招来联邦执政党自由党的攻击。保守势力恼羞成怒,污蔑惠特拉姆“像一条鲑鱼一样,被中国人玩弄于鱼钩之上”。殊不知,就在惠特拉姆访华后第4天,7月14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他已派基辛格秘密访华,双方已达成于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决议。消息传出,世界为之震惊,澳当局灰头土脸,工党和惠特拉姆本人却由于具有远见卓识而名声大震。1972年12月2日,澳大利亚联邦选举结果揭晓,澳工党以压倒多数击败自由党,赢得大选,成为执政党。惠特拉姆言而有信,1972年12月21日,澳宣布同中国建交。
揭开中澳关系新的一页
1973年10月31日至11月4日,惠特拉姆以澳总理的身份访华,中央十分重视这次访问,给予高规格接待。31日下午,周恩来亲自到机场欢迎惠特拉姆一行,当晚举行欢迎宴会。周恩来在祝酒词中说:“中澳两国人民一向相互友好。早在100多年前,就有不少中国人远涉重洋,侨居澳大利亚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同勤劳、智慧的澳大利亚人民共同劳动,共同生活,播下了中澳友好的种子。两国建交以前,中澳已有不少民间往来。我们两国建交以后,中澳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之后,惠特拉姆走上主席台致答词,他脱离了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兴奋地说:“我感到无比荣幸和高兴,在机场受到北京人民如此热烈的欢迎。一路上,我见到的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我满怀澳大利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访问贵国。”
惠特拉姆一行访华时间不算长,前后一共5天,日程却排得很满。
周恩来除亲自到机场迎送,参加我方欢迎宴会和对方答谢宴会之外,还4次主持会谈。11月2日下午,会谈结束后,他亲自陪同惠特拉姆到中南海会见毛泽东。曾亲身经历这次会见的中南海警卫员陈长江回忆说:“当时,周总理同惠特拉姆总理从大会堂出发,同乘一辆红旗轿车,来到中南海。在门口值班的我,见车一停稳便上前迎接。周总理请惠特拉姆先下车,然后两位总理兴致勃勃地一起走进毛主席的书房。会见照相后,记者都退了出去,毛泽东坐在沙发上,喝着茶,告诉客人说:‘我今年80岁了,腿脚不便,走路有些困难……’惠特拉姆见毛泽东精神不错,握手也有力,不由得赞赏说:‘使人感到你不到80岁……’毛泽东和周恩来笑了。很快,宾主双方在欢快的笑声中切入正题。会谈结束时,毛泽东说‘跟我一起走出门吧’。”陈长江注意到,尽管毛泽东走路困难,还是坚持把惠特拉姆送到客厅门口。通过中澳领导人频繁接触和会谈,双方在重要的国际问题、地区问题和双边关系上,有了深度的了解,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取得共识,签署了经贸协议和文化教育交流议定书。
会谈之外,惠特拉姆还参观了天坛(姬鹏飞代外长陪同)、故宫(北京市长吴德陪同)。我当时在北京外语学院英语系教书,外交部让我参加接待澳大利亚代表团,为惠特拉姆参观访问时做翻译。1973年“文革”尚未结束,周恩来特意安排返回工作岗位不久的邓小平(时任副总理)陪同惠特拉姆访问颐和园,出席记者招待会,陪同观看革命样板芭蕾舞剧《白毛女》等活动。这样,我有幸多次为邓小平和惠特拉姆当翻译。这里要讲一段有趣的故事。
11月3日上午,惠特拉姆在民族饭店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记者招待会结束后,我们在场的工作人员准备离开。突然,惠特拉姆走到邓小平身边说:“副总理先生,谢谢你出席记者招待会。我有一个请求,不知你是否同意。我来到北京之后参观了不少地方,但是没有去过天安门广场。你能陪我去吗?我们可以走着去吗?”邓小平对惠特拉姆突如其来的请求,稍微愣了一下,就很干脆地答应了。这可是日程之外的安排,事先没有准备。邓小平走到大门口,惠特拉姆也到了,我紧跟在两位领导人的后面。惠特拉姆个头高,步子迈得很大,邓小平虽是68岁的老人,却毫不示弱,步履矫健,两人步调十分协调。从民族饭店出来到天安门,少说也有4里地,一路向东行走在人行便道上,两位领导人没怎么讲话。快到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我猛然一回头,只见长安街路南的自行车道上,有一条长长的从西到东的自行车人流,骑车的人纷纷放慢速度,跟在领导人后边,边骑车边向这边张望。有人认出了邓小平和来访的贵宾,一手扶把,另外一只手高高举起,挥手致意。
邓小平和惠特拉姆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面,停下脚步。他告诉惠特拉姆,这是中国人民为了纪念从鸦片战争以来,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在历次起义和战争中牺牲献身的无名英雄而建。他让我把周恩来在碑上的题词翻译给惠特拉姆听,把纪念碑上的浮雕解释给贵宾。惠特拉姆仔细地听着,绕着纪念碑走得很慢,看得很仔细,有时还向邓小平提问。邓小平一一作答。
主持澳大利亚艺术展开幕式是惠特拉姆的活动之一。艺术展的内容是澳大利亚画家希尼·诺兰的大幅壁画,画中有一条大蛇腾空升起,背景由无数幅小画组成。惠特拉姆对前来参加艺术展的中外客人致辞,他深情地说:我出生于龙年,我之所以把这幅壁画介绍给中国朋友,是因为这幅画的风格是澳大利亚式的,但内容却包含中国的传统,因为在中国人们崇尚龙。我希望诺兰壁画能表达出我们此次访华的双重意义:它既有官方的一面,又有文化交流的内涵,从任何意义上说,这次访问令人鼓舞,充满活力,成果卓著。但愿这幅壁画象征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不断增强和蓬勃发展的两国友好关系。画展结束时,惠特拉姆把他亲自拟写的讲话提纲送给我,在上面签了他的名字。
访问结束的前一天晚上,惠特拉姆一行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告别宴会,周恩来、邓小平等都出席晚宴。晚宴气氛热烈友好,军乐团奏出《波特尼湾》,《羊毛剪子咔嚓嚓》等耳熟能详的澳洲曲目,惠特拉姆听到后非常高兴,连连称好,频频向周恩来和邓小平敬酒,还起身走向军乐团,向艺术家们致意。次日晨,惠特拉姆圆满结束访问回国,周恩来、邓小平到机场送行。
深深的中国情结
1973年后,惠特拉姆又多次访华,总数达11次之多。每当谈起对中国的访问,惠特拉姆都会自豪地说:我是唯一见到过中国三代领导人的澳大利亚领导人。对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他深怀敬仰和怀念。
毛泽东去世后,惠特拉姆在悼文中写道: “对于每一个访问中国的人来说,同毛泽东会见始终是一起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事件。他的非凡一生中所发生的事件,宛如一系列高大的里程碑矗立在悠悠岁月和人民的记忆中……半个世纪来,他一直是他的国家的人民的领袖;四分之一世纪来,他一直是中国政府领导人;40年来,他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领袖。毛泽东具有所有不但掌握世俗权力,而且还具有精神力量的领袖人物所特有的气质。我们的谈话范围涉及历史、当前问题、亚洲地区、文学和当代的一些人物。他很熟悉情况,知道西方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乐意对一些人物和问题发表意见……他的智慧和历史感深邃而又明晰。”
对周恩来,惠特拉姆无比钦佩,称颂周恩来既具有政治洞察力又有亲切和蔼的友善精神,说周恩来的睿智、沉稳和风趣,给他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2002年,惠特拉姆年过八旬,访华行程中再度访问天津,他不顾腿脚不便和酷热天气,认真地参观了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在留言簿上写道:“周恩来总理是我见过的最伟大的人。”
惠特拉姆在庆祝邓小平百年诞辰时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回忆同老一代中国领导人会晤的情景,特别清楚地记得当时邓小平陪他游览北京,讲述中国革命历史的情形。他说,邓小平思路敏捷,语言犀利,讲话切中要害,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高度评价邓小平的历史功绩,赞赏他在香港回归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政治智慧,在和英国撒切尔夫人谈判时坚持香港主权问题不容谈判。
惠特拉姆多年坚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建立两国关系,推动中澳友好关系的发展,功不可没,人们称他为“中澳建交之父”。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11次访华,显示出他深深的中国情结,把他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不为过。他说过:“当你置身于具有无穷无尽自我更新能力的中国时,你不能不感到自己的精神也为之一振。30年前在中国很多不可能的事情,现在都已成为活生生的现实。中国在经济和社会领域里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能促使我们深入地思考人类的未来。”
令人欣慰的是,39年之前老一代领导人开创的中澳友好关系,已得到承传和发扬。近10余年来,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多次访问澳大利亚。访问中,赞颂上个世纪70年代两国建交的历史篇章,还特别邀请惠特拉姆会面。2010年8月,习近平副主席访问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向他赠送惠特拉姆的著作《通往中国之路》。
2011年4月,澳总理吉拉德访华,我高兴地收到澳驻华使馆发出的出席吉拉德总理的午茶会晤的邀请。在吉拉德下榻的酒店,一间极具中国特色的古色古香的茶室内,我见到了年轻的吉拉德。我带去了当年惠特拉姆访华的珍贵照片册,把每一幅照片的故事讲给她听,惠特拉姆见了谁,谈了些什么,参观访问了哪些地方。我还告诉她那段鲜为人知的邓小平陪惠特拉姆走长安街,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故事。我还向她出示了惠特拉姆在诺兰壁画展览上的讲话要点原稿,把影印件送给她留念。吉拉德带着浓厚的兴趣听我讲述往事。她说,38年前,我还在上学呢,长大以后对惠特拉姆非常崇敬,他是老一辈澳工党领导人。这次我访问北京,知道了他当年访华的详情,太好了。茶叙快结束时,她送我一幅镶在镜框中的邓小平陪同惠特拉姆夫妇观看文艺晚会时的大幅照片,为我题词留念。她在题词中写道,感谢你让我分享了你对惠特拉姆访华的美好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