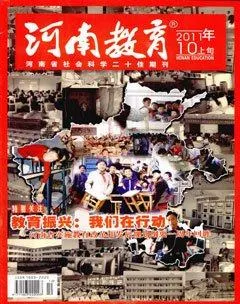“高效课堂”反思二则
2011-12-31王君
河南教育·基教版 2011年10期
作者简介:
王君,特级教师,现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西山学校,系全国中学语文优秀教师,全国中学语文教改新星,首倡“青春之语文”的教学理念。出版《语文创新教学探索手记》《教育与幸福生活》《王君讲语文》等专著。
课堂要实现教师和学生的双赢
近段时间观摩若干“高效课堂”,对两种现象深为忧虑。其他学科我不太懂,就只说说语文。
一是学生展示内容的应试化、低幼化。
“高效课堂”的主导思想是还课堂给学生,这没有什么问题。它甚至还是一种纠偏——传统课堂确实存在着教师霸占课堂、学生被边缘化的痼疾。但我非常期待看到的是课堂还给学生之后,学生做什么呢?
高效课堂的做法是学生在导学案的指导下先自学,然后课堂展示,互相质疑,教师点拨获取知识。从初衷来看,这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
问题出在导学案的内容。因为要便于操作——学生得分组展示,要适于板书,适于学生讲解,于是乎,导学案的内容就必须分板块,要能够很好落实。这样一来,“导学”成为了导“知识”。至于思想、文化、文明、情感、艺术等对于语文来说似乎更为珍贵的内容,却不太好上“导学案”,于是便被忽略了。
我前后观摩了若干堂“高效”语文课,学生确实情绪很高,互动性很强,但可惜讲解的几乎全是基础层面的东西。略微深入一点点的,也不过是练习册和参考书上的低层次内容。这实在不能怪老师,是学习的固定模式决定了内容的低幼化。
比如听《桃花源记》,授课老师自己也先跟我讲:王老师,这么上还是语文课吗?这样做确实非常为难我们的年轻老师。当学生课堂展示的全是“词性活用”“古今异义”“一词多义”等方面的知识时,我想陶渊明也会愤怒的。我听懂了他的言外之意:如果教学《桃花源记》,重心居然放在字词上面,这不是暴殄天物吗?
我跟他有一样的惶恐和痛心。语文学科和理科教学有很大的不同。其魅力恰恰在于知识的模糊性和情感的多元化。可以这么说,只有知识肢解,没有艺术和情怀支撑的语文课绝不会是动人的语文课——哪怕它适合于考试。
语文课跟相声一样,必须得“抖包袱”,在不断的情感濡染和理性感性交织渗透的引领中,带学生跨越千山万壑。语文需要审美,而一张导学案,把学生的思维全然固定,把所有历险过程全部定义为做题,这是语文的窄化和“死”化。
二是教师的边缘化。
看了几堂“高效课”,我最着急的还不是学习内容的应试化,而是教师的无所作为。这样的课堂模式完全固定,甚至学生朗读教学目标都是程序化了的。一个步骤接着一个步骤,学生确实动了起来,可是老师呢?有的面无表情地站在一边,有的无所事事地偶尔穿插几句话。从头到尾,却极少见教师有什么创造性的行为。
这也不能怪老师。导学案已经把老师完全“出卖”了,教学程序一目了然,教学内容明明白白。学生几乎不用独立思考,所讲内容在《课文全解》等一类书上都能找到。学生只需要照搬过来填写在“导学案”上,再板书到黑板上,即可夸夸其谈。加上课堂时间极其珍贵,老师被边缘化既是无奈,又是自愿。
据说“高效课堂”以教师讲解的多少来衡定课堂效益,认为讲得越少越好。还听说北大附中有一位很著名的数学教师,每一天都用秒表卡自己的讲课时间,最后终于把教师的讲解成功控制到了3分钟之内,于是皆大欢喜成为典型。
数学课这么上也许没有什么问题。较之于语文,数学确实明白透彻得多:即使课堂完全试题化大概也不会有人诟病,但语文真的没有这么简单。课堂上语文教师声情并茂的诵读、点拨本就天然属于语文的一部分。讲得过多肯定不好,但完全不讲或者讲得不精彩,就是语文教师对教学责任的推脱和逃避。
而这样长期把课堂“焦点”彻底让位给学生的做法,对语文教师的专业成长是很不利的。语文教师的职业兴趣来自于什么地方?前段时间和校长聊天,我提到一个观点:你给教师过生日送礼物很重要,关心教师的起居也很必须,但这些都是外在的力量。真正促进教师的职业兴趣蓬勃发展的,是教师在课堂上的高峰体验,是来自于师生的情感和智慧高度交锋融合之后产生的美感。只有这样的体验和美感,才能让教师痴迷于课堂,专注于教育。
讲与不讲,讲得多与少并不是问题的核心。关键在于教师是否讲到了学生的心中,是否点燃了学生的情怀和智慧。
教师的讲,如果极富个性和文才,对学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曾经读到这样的典故:
西南联大的国学大师刘文典,恃才傲物,不可一世。他曾和学生在三五月圆之夜,团团围坐在草坪上,吟诵《月赋》,那种情景,让钱理群先生都思慕不已。
同样是刘文典,有一次警报响起,他挟着一个破布包,往郊外逃窜,正好遇见沈从文夺路狂奔。刘文典火冒三丈,侧过身大骂沈从文:“我跑是为了庄子而跑,你这个该死的,你为谁而跑?”
刘文典自认为世界上懂《庄子》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一个是自己,另半个是冯友兰。每当刘文典开讲《庄子》,吴宓等西南联大几位重量级教授便前往听讲。刘文典旁若无人地闭目演讲,讲到精彩处,戛然而止,抬头张望教室最后排的吴宓,慢条斯理地问道:“雨僧兄以为如何呵?”吴宓闻听立即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吴宓号称清华四大教授之一,是钱钟书先生的授业恩师,尚且对其恭敬如此。
每每读至此,我总是震惊于刘文典的狂妄,但同时觉得,作为先生,首先是真性情,其次才是真学问。
老师有真性情,洒脱不羁,随心所欲,呈现一种自然生命的姿态。这种教学,就不再仅仅是知识的传播,而是一种生命的唤醒和启迪,它给予学生的必然是生命的浸染、熏陶、舒展,传递的则必然是自由天性的流露,个体生命的承担,独立人格的追寻。真实的生命,本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教育也该如此。而这样的老师,如果不讲,那该是学生多么大的损失啊!
俗语说,教师是靠“嘴皮子”吃饭的。讲的水平,任何时候都是衡量教师素质高低的重要因素。而教师,如果以“还课堂以学生”为借口,降低自己讲的质量,退化了讲的能力,这对于语文,实在可算是灾难了。
所以,课堂如果要真正高效,必须在两个方面实现突破:一是教学内容不能应试化、低幼化;二是教师在课堂上不能边缘化。课堂,只有成为师生双赢的场所,我们的教学才有希望。
把课堂瘦身坚持到底
上了未来班的分享课,中午听北师大的专家组评课。
余胜泉教授——跨越式教学的领头人作为专家进行评课。他们做这个课题十年了,试验学校遍布全国。余教授很专业,他一语中的,对我的课堂问题看得清清楚楚。
他听的是我的第四节作文课。这堂课很顺利,效果很好,师生都很振奋,但课堂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这我很清楚,却在备课时舍不得去改正。教学和人生一样,有时就这么纠结。
问题出在一则时事材料的取舍上。这则材料很鲜活,就是故宫锦旗事件和道歉信事件。我讲的是作文语言个性化的问题,和故宫事件有关联,但绝非最佳关联。于是,用还是不用,颇费了周折。最后我还是没有舍得删掉,而是选择把生活的源头活水引进课堂。作为可以给学生教益和启发的热点焦点事件,不在公开课上亮一亮,实在太可惜了。
但是,精彩的并不意味着就是最恰当的。
正如余教授说:故宫事件好是好,但就这一节讲作文语言个性化的课而言,它并非必须。如果这个环节换为“作文语言伪个性化”辨析,这堂课的思路会更加清晰,教学指向会更加明确,教学内容会更加饱满。
深以为余教授说的是,也为自己的糊涂好笑。虽然教龄已经不短,但还是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教师的修炼,真的是一个无涯的过程。
我的感受:教师备课,往往会经历三个阶段:一是苦于无材料,二是占据了很多材料,三是对材料进行提炼,留下最有用的材料。年轻的时候,往往在第一阶段苦恼,没有经验、没有存货,无米下锅。但很快就会进入到第三阶段:信息和材料太多太多,如何取舍及整合梳理?这个苦恼其实远远大于第一阶段的苦恼,因为这涉及教学内容的确定问题。
我的经验是,大凡好课,一定都是对自己占有的诸多“好材料”能够毫不留情地“下手”的课。而大凡有问题的课,都是囿于材料而忘掉或者部分忘掉了教学目标之本质的课。或者可以这样形象地说:大凡好课,都是脉络清晰眉清目秀的课,而不好的课,都必然是赘肉横生眉眼模糊的课。所以,为课堂“减肥”,应该成为教师的教学追求。
课堂“减肥”意味着精简教学目标,凝练教学线条,整合教学板块,减慢教学节奏。其目的是放慢教学脚步,给予学生更多的思考时间和思考自由,让学生真正经历生命发展的过程。
课堂“减肥”是对学生最大的尊重和对人性最大的宽容。我们现在动辄就说“高效”“速效”等,但千万不能理解错误了,这里的“效”和速度容量并无绝对直接的关系。我的理解,“效”该是“效益”,是在充分尊重学生特点和尊重课堂目标的基础上达成的最佳教学效果。贪多求全、贪新求异都是“效”的敌人。
我深知自己好创新,多激情,要达成自己的“高效”,确实需要为课堂“减肥”:精简教学内容,简化教学手段,放慢教学步骤。
想起了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缓慢》。这篇小说对我的教学很有启示。它触及了现代社会中快节奏、高速度而让现代人失去耐心为物所役的现实。昆德拉认为,在慢速和记忆之间,快速和忘却之间存在有机联系:“例如一个人在路上行走,突然想起一件事,但记不清细节。这时,他会极为自然地放慢脚步。反之,一个人急于忘记一件刚才经历的不愉快的遭遇时,必将加快步子以便逃过那段离他最近的时间。”在这里,昆德拉揭示了现代人紧张、快速生活节奏的本质:人被锁定在功利的忙碌之中,过去和将来都被抽空,回忆和眺望也就消失了。
课堂内容不恰当的旁逸斜出导致内容松散臃肿,导致必须用高速的课堂推进才能完成教学任务,这于我,是经常的事儿。
语文的课堂教学真的只能是农业而非工业。工业可以是快节奏的、大容量的、流水线的、批量出产的。而农业则是有季节的,时令的,成长规律的,是需要慢慢地播种施肥除草杀毒的,是需要阳光水分和等待过程的。
好的课是朴实无华的,急功近利、急躁冒进、揠苗助长都是不当的。语文教学,特别需要平静和平和,需要细致和细腻,需要耐心和耐性。好的语文课具备的模样:清瘦、轻盈、清奇。
我还差得老远,好好修炼吧!
(责 编 涵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