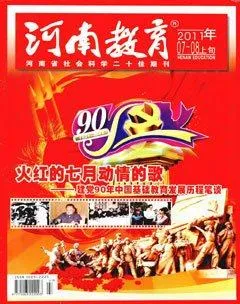我国近百年课改的核心精神与基本脉络
2011-12-31申宣成
河南教育·基教版 2011年7期
一部人类教育的历史,就是研究儿童和发现儿童的历史。在中国现代教育百余年的发展轨迹中,回归生活教育、强调学生主体同样是其不变的主题,而课程作为教育的“心脏”,教材作为教育的“行囊”,它们又共同演绎了教育变奏曲中最具震撼力的部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本文试图通过对百年课改历程中三个重要时段的分析,描绘出我国现代教育的核心精神与基本脉络。
一、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强调生活教育与儿童主体
20世纪初期的中国,经历的是亘古未见的大变局。在内忧外患中,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都显示出巨变的气象。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的大幕,毛泽东就是来自全国的十几位代表之一。而就是在这一年,他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一文中痛陈了课程过繁的弊端——“使学生立于被动,消磨个性,灭掉性灵”,体现了一个政治家对教育的洞见。同年10月,全国教育联合会在广州召开了第七届会议,提出了学制改革的具体方案,并引发了全国范围的热议。次年,中华民国北洋政府以大总统令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史称“壬戌学制”,此次学制的内容正是以广州会议为蓝本的。如果说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被公认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开端的话,“壬戌学制”则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影响最深的变革之一,它促成了中国教育从传统向现代的嬗变——不但完善了学校系统,加强了中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而且强力变革课程,为日益式微的教育心脏装上了一个有力的“起搏器”。
随之,全国教育联合会于1923年在上海讨论并发布了《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领导新学制课程标准制订的,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个是胡适,另一个是陶行知(两个人不但同岁,又同为安徽人)。前者是引领新文化的旗手,后者则是改革旧教育的新锐,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阵容的强大由此可见一斑。作为中国第一套课程标准纲要,它集中体现了新学制的理念,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强调学生的主体作用。这是陶行知先生所一贯倡导的。自从回国以后,陶行知就对那些“只管照自己的意思去教学生;凡是学生的才能兴味,一概不顾,专门勉强拿学生来凑他的教法,配他的教材”的先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先生收效甚少而学生苦恼太多”“把那活泼的小孩子做个书架子,字纸篓”,并倡导“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 力挺改“教授法”为“教学法”,这在教育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27年,陶行知应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邀请赴天津讲学,张伯苓建议他将“教学合一”改为“学做合一”。受其启发,陶行知豁然贯通,由此确立了“教学做合一”的理论。而张伯苓能够提出“学做合一”的建议,也正是因为他在教育理念上与陶行知是心有灵犀的。在为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所开设的课程中,张伯苓都格外重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例如,他于1909年就在南开中学成立了“南开新剧团”,和教职员工及学生一起创作演出话剧。他自己还亲自编导了第一个话剧《用非所学》,体现了其学做合一的教学思想。“南开新剧团”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主体作用,成为学生修身立学的重要阵地。南开中学的毕业生周恩来、曹禺等,都曾是“南开新剧团”的主要演员。周恩来还写过论文《吾校新剧观》,总结了“南开新剧团”活动的经验。陶行知和张伯苓的这种课程实践,不啻为当代活动课程之发端。
二是强调生活教育。“壬戌学制”确定了七项改革的标准,其中之一就是“注意生活教育”。这一宗旨直接影响了课程标准和教材的编制。1932年,初中国语课程标准的起草人叶绍钧(叶圣陶)与丰子恺合作编绘的一套国语教材《开明国语读本》,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精神。正如叶圣陶先生在编辑要旨中所言:“本书内容以儿童生活为中心。取材从儿童周围开始,随着儿童生活的进展,逐渐拓张到广大的社会。”其初小第一册第一课只有两行字:“先生早”和“小朋友早”,短短的两行字模拟了师生初次见面时互相问候的口吻,字体简单、插图生动,形象地展现了师生初次见面时温馨的一幕,极富生活气息。
三是改国文为国语。推行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大业绩之一,其对于教育改革更是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与陶行知力挺将“教授法”改为“教学法”一样,改“国文”为“国语”,表面上看来仅仅是一字之易,而实际上却是整个教育理念的转变。胡适认为,以往中学国文教学的失败,主要原因“不在于理想太高,而在于方法大错”,因为中学国文的目标是要“通解普通语言文字”,教的却并不是普通的语言文字,而是少数文人用的文字;目标是“能自由发表思想”,教的时候却不许学生自由发表思想,“硬要他们用千百年前的人的文字,学古人的声调文体,说古人的话”。而一旦将“国文”改成了“国语”,死的文字就变成了活的语言,学生的学习就和真实的生活联系在了一起。因此,当1920年教育部在北京开办国语讲习所时,胡适竟出席讲演十多次,并对教育部命令全国各国民学校一、二年级都改用国语教学大加赞赏,认为“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20年”。与此同时,胡适还以一个教育“门外汉”的身份详细论述了自己的课程设计思路,如:强调国语教学中演说和论辩的重要性,并提供了具体的方法(题目的选择、小组的人数、练习的次数等);主张用《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等白话小说作为语文教材;提出了古文的三步教法(质疑、讨论、指点)等。现在看来,这些思考和建议对当下的语文教学改革仍不乏借鉴的意义。
壬戌学制的颁布和课程标准纲要的发布,奠定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基础,也为民国时代的教育辉煌提供了制度的保障和课程的支持,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两弹元勋邓稼先、钱学森、钱三强,文化巨擘钱钟书等大师级人物,无不得益于此。
二、新中国教学大纲:聚焦减负增效与儿童自主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教育主要仿效苏联,将课程标准改为了教学大纲。1956年的教学大纲虽然较为细致,但是模仿痕迹太重,给人以生搬硬套之感,加上随之而来的“大跃进”高指标的影响,忽视了学生的接受能力,加重了学生的学习负担。1963年,整个国民经济进入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阶段,教育也进行了反思和调整。当时,中共中央分管宣传、教育的陆定一同志到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向在场的语文编辑抛出了一句话:“你们敢不敢只提工具性,不提政治性?”此言一出,四座皆惊,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说出这样的话需要多大的勇气呀?其直接结果是,1963年的语文教学大纲对于教材选文的要求,只强调了“文质兼美”四个字。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各个科目的教学大纲,与以往的大纲相比,自然更切合中国实际、更具有本土特色,从而对稳定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全日制小学算术教学大纲(草案)》就有如下特点:(1)第一次提出培养学生空间观念的要求,体现了数形结合的原则;(2)把整数四则运算由七个循环改为四个阶段,为建立中国化的整数教材体系打开了一条通道;(3)把口算和笔算由原来的分开编排改为混合编排,更利于提高学习的效率。正因为如此,1963年的教学大纲可以说是新中国教学大纲的奠基之作。著名教育家吕型伟先生就曾不止一次地说:“不是经常听